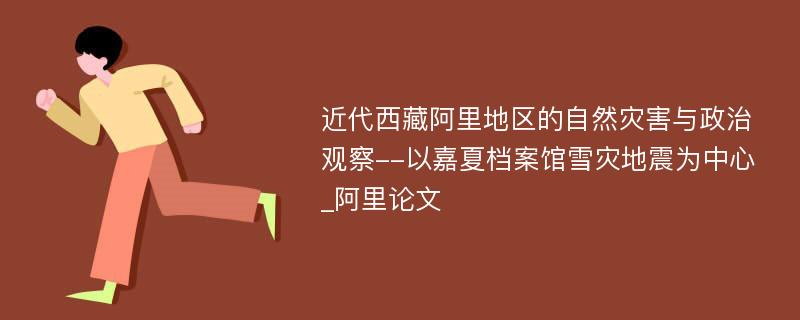
近代西藏阿里地区自然灾害与政治观察——以噶厦档案中的雪灾、地震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雪灾论文,阿里论文,西藏论文,自然灾害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D6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3)03-0022-08
过去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讨论,多从西藏整体出发,本文尝试深入到西藏内部,选取局部地区政治运行情况进行观察,从灾后政治的角度入手,通过非常时期的事务处理,探讨拉萨噶厦政府和阿里地方政府之间的日常政治。灾后政治可以使我们透过宗教迷雾直接观察和分析近代西藏地方政府运行机制,加深对近代西藏政教合一的理解。
一、雪灾期间的驿政困境与权力较量
阿里地区由于海拔高,气温低,冰雪灾害时常发生,对农牧业的破坏最大。西藏200年来最大的两次雪灾高潮期,分别分布在1827-1831年间和1927-1929年间,在这两次雪灾高潮期中阿里地区都首当其冲。①面对雪灾造成的冲击,阿里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往往无法正常运转,对地方政治的稳定构成威胁。1827年(火猪年)阿里地区卓学德萨部落遭到雪灾,牧户大多破产,加上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地方驿政无法维持,到1832年阿里地方官员不得不向噶厦陈明雪灾实情以及请求处置办法。呈文的开头颇为有趣,“含诸天在内的众生救星具足威德摄政诺门罕莲足师座尊前,卑职堆地噶本简言叩禀,祈请宏广法界予以宽宥”。②这一开头充分体现了政教合一的西藏政治特色,以佛经的口气撰写公文,在行文中藻饰大量的佛教词汇,通过文字的装饰在表面上将政务转变为教务,给西藏地方政治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
这份呈文写于藏历水龙年(1832),是直接上呈给摄政活佛的,当时正值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1816-1837)年幼,由第二世策墨林活佛摄政,二世策墨林活佛名叫阿旺绛白楚成嘉措(1792-1855),1819年起担任摄政,赐号“额尔德蒙额诺门罕”,直至1844年被驻藏大臣琦善参革为止,前后共摄政26年。③堆地噶本,又称堆噶尔本(stod sgar dpon),意为上部营官,在清代属边缺营官,是噶厦政府委派的阿里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通常设有二人。夏季驻噶大克,冬季驻噶尔昆沙。④雪灾的情况在呈文中所述如下:
此地属下的卓学德萨,过去牧户家境尚可。惟火猪年,由于大降以往闻所未闻的大雪,地方支应“勒”差之牲畜死绝,牧户皆已民逃亡。仅余头人洛赤等两户,穷黎维艰,途中驿站濒于中断。土鼠年蒙人主夏扎前来堆时,饬复呈文内谕:“二噶本为牧民生计自立应安排并宣布筹划措施。”⑤
卓学德萨(gro shod bde gsar),卓学为一地名,清代汉文文献中称之为“卓书特”,清代人一般认为这里与阿里的东部边界相邻。⑥其地位于今仲巴西北和措勤县以西的游牧地带,约相当于今仲巴县的隆格尔乡、仁多乡、帕玛乡、吉拉乡、霍尔巴乡、纳久乡、帕羊镇、偏吉乡一带。
所谓的“勒”差,是阿里地区一种特有的差税,阿里地区将收入和人头税合在一起,称为勒(leb),每年通过噶尔的官员向政府交纳,勒税的特点在于,首先对该地区所有税收进行评估,然后折算成勒,接着再将折算出来的勒数分摊到全体居民的头上,制订出税额。⑦由于受灾情较重,牲畜死绝,牧户逃亡,对基层政权来说,直接的困难就是驿站得不到所需物质支持,驿政无法运转。面对灾情,噶厦并不愿意直接出资施以援手,只是让两位噶尔本自己想法解决。土鼠年(1828)负责处理此事的人主夏扎,应即当时噶厦政府的资深噶伦——夏扎·顿珠多吉(bshad sgra don grub rdo rje ?—1840),他在1794年出任噶准,1808年左右成为噶伦,他后来主持了西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整顿赋役的工作——《铁虎清册》的清查和编定。据《十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他恰好在1828年时曾奉命出使阿里西边的拉达克,⑧可能在途经阿里之时对雪灾的善后事宜给阿里噶本作出过呈文中所引的批示。面对噶厦的不作为,两位噶本只好自己想办法。
我阿里三围其余宗谿对派人援助支差一事,认为各自均须支应驿站差役和边境山隘哨卡的防务等故无法派援工。上师官长钧旨不能搁置,故噶本辖区内部酌情从已破产的仲麦巴德萨瓦的草场上放牧,每年交付草钱来支应过往官商等人的代马金。互相结算立约,终使驿站在去年之前免于废置。⑨
噶本可能打算让阿里地区其他宗谿分出一本部分财力支援卓雪受灾部落以解决卓雪驿站人力、财力不足的问题,不过各宗谿都以自己本就有许多驿站差役和边防任务为由拒绝施以援手。这一办法实际上是噶厦政府不愿增加开支,而堆噶本政府又无力解决差户不足的问题的情况下,想用摊派的方式解决驿站困境,自然遭到阿里各地百姓的反对。为了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噶本政府后来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已破产的德萨部落的牧地出租,将每年收取的租金用作驿站的运行的费用,从而既不增加阿里其他地方的负担,又解决了德萨部落实际上已无支差能力的现实困难。这一办法使驿站艰难地运行到了1830年。但这一变通的办法似乎并不为噶厦所接受,1831年前来阿里视察的代本坚持要求按《水马清册》规定办理仲巴差役,致使仲巴人要担负两份差役,噶本委派的驿站事务遭到拒绝。而卓雪德萨部落因雪灾“大部分死亡逃跑,剩下是些孤独之人,几年间驿站恢复无望。”面对这一困境,堆噶尔本遂在1832年直接给摄政活佛上书,希望灾后援助事宜应由噶厦出资,而不能让阿里地方担负,“卓学德萨尔份差破产需扶助事,三宝为证,不应由阿里三围承担。”⑩在阿里地方政府看来,对受灾的卓学德萨部落予以实际的援助,应是噶厦政府的责任,不应该推给他们来做。因1827年的次雪灾而造成的驿站困难,竟然拖延到1832年仍无法解决,过去家境尚可的德萨部落在大雪之后元气无法恢复,噶厦与噶本之间互相推诿,似乎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境地。
在灾害面前,以噶尔本为代表的阿里基层政权和在拉萨的噶厦上层之间实际关心的问题,并不像佛教藻饰语言那样慈悲为怀,而是以维护各自的利益为中心。双方皆不愿意填补雪灾的损失。而雪灾对基层政权的破坏,使得驿政陷入困境。驿站对西藏来说,其作用又非常重要,藏地自然条件差,出行困难,政府官员和官商如无驿站支持,恐怕寸步难行。(11)由于阿里物质基础薄弱,灾后自我修复能力差,灾后围绕驿站的运行问题,噶厦与噶本都无力而为。实际上这一问题的处理,成了双方权力角斗的过程,雪灾后的权力较量在一百年后的大雪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阿里地区在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雪灾爆发于1927年9月,“自火兔年(1927)九月九日起,福祚衰败,发生非同一般之雪灾,黑白牲畜死亡惨重。”(12)此次雪灾持续时间长,波及地区广大,使阿里牧民生计受到严重影响,阿里地方政府面对这一严重天灾根本无力应付,只得向噶厦政府求助。
堆噶本在1928年6月的禀帖中称,“卑职阿里二总管禀告,阿里三围全体黎民、人畜疾苦难耐,去年齐声禀告后,至今未接到任何旨谕,似如饥荒逢闰月。今冬复昼夜连降前所未闻之大雪,眼见目睹南北上下全部百姓生活所依牛马等牲畜成批死亡。……自去年九月始,因连遭雪灾,支差的山羊、绵羊和马牛均荡然无遗,百姓沦为乞丐。桑仓、托钦和帕噶驿站负责地段及部落支应差役之牲畜已全部死亡,使百姓失去了生活所依,无法安居,只好去流浪讨饭。”(13)噶厦政府在接报后跟上次一样,也不愿承担灾后的援助工作,对此不闻不问。而噶本特别强调了牲畜死亡惨重,加上灾区地处驿站要道的特殊性,企图引起噶厦重视。
此次雪灾对阿里畜牧业造成的损失巨大,并非噶本有意夸大。档案中对各地受灾情况有详细的统计,如托钦达错(thog chen rta tsho)的一份报告中开列了所属的三个小部落的灾后财产清单,最后统计出三小部落原共有公母牦牛776头,绵羊、山羊6187只,马25匹。雪灾后剩有公母牦牛73头,绵羊、山羊1181只,马10匹。剩有牦牛接近原数的1/10;剩有绵羊、山羊为原数的1/6,剩存马匹接近原数的1/3。(14)托钦,又译为托克钦或托青,位于普兰县东北玛旁雍措湖边的霍尔乡东边不远处的219国道上,该地的标准地理坐标为东经30.7°,北纬81.7°。(16)达错是一种专职的驿差部落,是对当时的一种专门负责给驿站提供马、畜的物力的部落的称呼。噶本考虑到灾情严重,加上灾区地处阿里与拉萨的交通要道,驿差繁重,建议暂时减免当地百姓的部分差税:
牧业之百姓依靠牛羊牲畜支应差税、谋生。现牲畜死绝,无法交纳差税与过活。色雄聪巴、桑嘎、那仓东西帐蓬营盘、拉达克罗恰、赫米罗恰、盐税官、历任色雄债务余额之收取等代表之各项差徭,催讨不休。若不考虑暂时推迟交纳,则劫余之零丁男女差巴亦只得背井离乡。传送指令、呈文及三围各宗谿每年照例支应的马匹、驮畜差,即连一两匹亦无从派出。(16)
从这份禀帖中可以看到,阿里地区百姓的差税本就十分沉重。除了负担一般西藏农牧民所应负担的差税外,还有几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差税。
色雄聪巴(gser gzhung tshong pa),指的是黄金贸易差税,因阿里各宗和牧民部落都有质量与产量不同的金矿,故噶厦设置金税官——“色本”(gser dpon)于阿里,专门负责金税的征集,色本除了征收金税外,还委派隶属政府的官商从事贸易,所得利润上缴噶厦政府,这种官商称为雄聪巴。阿里地区须按照各地产金量所制定的《大宝库赋税册》内载明的数额上缴金税。(17)拉达克罗恰(la dwags lo phyag)和赫米罗恰(he milo phyag)指的是原属西藏的拉达克政权派往拉萨的年贡使团,前者由政府派出,后者由当地最大的寺院赫米寺派出,该使团是17世纪末卫藏—拉达克战争后双方达成的协议之一,近代以后尽管拉达克王国已被英印政府吞并,但这一传统习惯仍保留了下来,使团来往途中的劳役差税也是由西藏政府无偿提供,而这一负担就自然落到了阿里境内的农牧民身上。(18)阿里地区盛产湖盐,1915年噶厦在拉萨设立盐茶局,在各地分设守卡盐税官(tshwa shog)负责征收盐税,阿里地区的日土、普兰等地都委派有设卡盐税官。(19)阿里噶本认为,当地百姓负担上述差税在灾年实在太重,如不减免将影响到驿站差税的支应,恐怕会使驿站无法运行。
跟一百年前的卓雪大雪灾造成驿站中断一样,这次雪灾也造成驿差无以为继的问题。而这一点是噶厦政府最关心的,驿站不仅是政府指令、公文传送的重要纽带,而且也是西藏僧俗贵族们最重要的一种特权,驿政畅通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驿差对西藏人民来说,也是一种最为繁重的负担,故而每遇天灾,驿站就有中断之虞。民主改革前的大贵族噶伦索康对此有精辟的概括:
交通乌拉差役是噶厦政府管理西藏的中枢之一。西藏的交通要道有两条,每条道路沿线设有许多驿站,每个驿站之间的距离为半天路程,以确保某一地区的农民能够在一天之内在此驿站到彼驿站之间打个来回。这种驿站制简便易行,由于噶厦政府发放通行许可证,授权给乌拉证持有者要求沿途农奴百姓支应乌拉差役并提供驮畜,所提供的驮畜常常是数以百计,这些持有乌拉证的人还能够免费或以最低代价获得食宿。(20)
这种由噶厦政府发放的通行许可证(lam yig),也称为路引,是贵族和官商的特权,也是加在老百姓头上最为沉重的负担之一。此次大雪之后,阿里地方和部落头人与拉萨的噶厦政府之间围绕驿站的运行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争夺。
雪灾发生后,桑仓头人(位于今那曲地区申扎县境内)上报由于灾情严重,加上政府发放的路引使当地百姓已经背负了巨额的差税,因此头人趁雪灾之机提议政府暂停路引的发放,减免驿差,“去年屡遭雪灾,牲畜死亡甚重,所剩少许,支应驿站之岗卓拉顿各项差役,实感应接不暇,无法效命。故恳请上师、老爷慈悲为怀,于卑等支差,生活未得着落前,收回各类人员的路引。上述拉顿差赋甚重,百姓处于饥荒死亡之境,最好在卑民未得生计前,给予谿免。”(21)所谓拉顿(lag vdon),直译为“手出”,是指差民们用手捧出去的一切实物差和货币差。(22)
为使桑仓驿差减免后不致造成驿政中断,该头人提出让改则一带的部落接替桑仓的驿差,因为这些部落原来的负担较轻,“彼等仅为各自头人、官长支应少量差徭,而不需为上下各驿站服役,故较从容,今后,可令其人畜一并接替桑仓无来源之达错,而去支增额差役。”(23)为使上级政府理解桑仓的困难,头人在雪灾后立即向阿里噶本上报的全部落100多人受灾的损失清单,据统计整个部落原有牲畜总数为7014勒,计有公母牦牛3236头,绵羊19303只,山羊4416只,马182匹,雪灾剩有公母牦牛103头,绵羊971只,山羊193只,马34匹。按旧例将马匹从勒数内扣除,其余折合289勒,不足原有总勒数三十分之一,马匹不足五分之一,其余全部死光。(24)这一情况随即得到阿里噶本的认可。然而桑仓头人的建议,不单只是想噶厦政府对其进行灾后照顾,似乎还想借雪灾之机将本部落的原有赋役转移到邻近部落头上,从而替自己减轻负担,这一做法遭到噶厦政府的严厉斥责。
噶厦政府在随后发给阿里堆噶本的饬令中要求阿里噶本查处以桑仓为首的前后各驿站因雪灾擅自中断驿站差事的行为,并将带头中断驿站差役的头人捉拿治罪,在饬文中噶厦政府给阿里噶本的行文措辞相当严厉:
虽然你等受灾甚重,大量牲畜死亡,但是你桑仓驿站不用说不支负一匹马,而且根本不支负一点驿站所需食宿。还谎呈无有为政府商官支负的马匹、驮畜之具结,因不遵纪守法耍赖,以及霍堆巴假装与霍麦交厚,随意中断支派马匹、牲畜,此将导致上、下驿站彼此效尤。依据此事件违法行为,将其主要首领霍麦桑仓之一、二头人执事和霍堆头人,主犯逮捕流放,当众治罪,引以为戒。但虑及边民无知,如能改邪归正,此次给予宽大,不予治罪。(25)
由此可见,尽管西藏地方政府披着慈悲为怀的外衣,但作为统治行政中枢的噶厦仍然是一个十足的世俗政府,在具体政务面前,即使民生困苦,它首先考虑的仍然是维持统治体系的政常运转和自身利益不受影响。事实上,正是由于灾情严重,资源匮乏,政府才更倾向于从世俗事务的角度处理各种政治问题,在雪灾善后问题上,我们看到政教合一下的西藏政府,无论是拉萨的噶厦政府还是阿里的噶本政府以及部落头人,其关注点都纠缠于世俗政治利益上,无暇他顾,佛教慈悲只成为公文中的文字游戏。
二、地震期间的世俗政务与信仰行为
通过阿里雪灾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雪灾面前,西藏地方政府和社会更多地表现出世俗性的一面,这恐怕跟灾害造成的困难主要是物质利益上的问题有关。当自然灾害对物质财富破坏不致引起地方财政危机之时,则更多呈现出政教合一社会的一般政治样态。事实上也只有在基本不影响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才有可能腾出心思来考虑宗教问题,而当灾害危及政府的基本运转时,如前述的大雪灾那样,则宗教政治的特点便不明显了。因此阿里地震的善后事宜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特点会更加丰富。
地震在西藏的破坏力一般体现在对自然环境,对农田、水利设施和交通的破坏,以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6)不过地震在阿里地区的破坏力却远远小于雪灾,阿里地区处于羌塘高原之上,人烟稀少,在清代民国时期城镇化水平极低,一般城镇中只有宗政府和寺院建筑,其余居民多搭建帐篷居住。(27)由于几乎没有高楼大厦,所以不易造成大的伤亡。最为重要的是,地震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构成威胁,这样就不会使统治系统的某些重要机构如驿站等无法运转,灾害的善后工作的紧迫性也没有那么急切。在这种情况下,阿里噶本政府和拉萨噶厦政府对震后的问题的关注,就既有具体的世俗行政事务的处理,也有佛教观念中的宗教事务的考量。
1883年藏历九月,阿里普兰宗和噶尔通谿卡等地发生地震,噶厦档案中有次年的八月十二日噶厦给堆噶本的震后工作意见批复。地震造成宗府和谿卡房屋倒塌,灾情发生后,噶厦政府饬令阿里总管觉哲和哲德二位噶本前往调查。二噶本调查后对噶尔通震后的初步处理如下:
据报称:查从噶尔通废墟土石中挖出之粮、物、死牲畜皮等,已按库存帐目,查收回库,所缺部分应由有关人员备办交齐。库存帐目上未曾载有之多余财物及死牲畜皮张等,系属暂交财物,着暂交噶尔通谿堆本人保存;木料应设法从废墟土石下面挖出,备今后修建谿卡房屋之用。此事应切实通知各头人和百姓,共同效力。(28)
噶尔通(dkar dung),清代称为“喀尔多木”,其地位于普兰县城西北,拉昂错湖南岸。历史上这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城堡,13世纪前后噶尔通城堡是贡塘王朝在阿里的军事中心,负责监管整个阿里的政治与军事。(29)从报告中看,地震后当地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因地震而造成的财政损失,从地震废墟中挖出粮食等财物,特别是将震后抢救出来的物资验帐存库的一系列做法,可见基层行政的规训在灾害面前仍然有效。而要求将木料从废墟中清理出来,以备今后筑房之用,则体现出当地官员务实能力。事实上噶厦政府在地震后最担心的也是当地政府能否妥善处理灾后的世俗事务,首先噶厦提醒新任宗本处理好前任宗本任内的库存豌豆数量短缺案件,噶厦担心地方借地震之混乱之机,侵吞公共财产,叮嘱切不可以房屋倒塌为由,私吞公物。接着才给阿里噶本和普兰宗本发出修复被地震破坏的粮库、宗府等重要建筑的指示:
普兰宗和噶尔通粮库维修一事,不宜拖延,应在今年内开工,由噶本任修建总管并与新任普兰宗堆崔科·岗建巴共同办理。关于支派乌拉事,倘无力支应,可按尔等呈报及普兰宗噶尔通百姓公禀酌情解决,但不得无故蹂躏百姓。阿里总管应告诫所属官民,设法将宗府修筑牢实。所需木料,应先用拆房旧料,如仍不敷,方可拆掉宗府无用房屋。此系普兰百姓呈文所议,但应顾及将来,由尔噶本及普兰宗堆崔科等共同酌情办理。呈文所称要责成卸任宗本朗通巴担负木料差价,此事须将其任宗堆时对政府之胡作非为及利用木料贪污舞弊情事,详细具报,再凭核夺处理。切记。(30)
从饬令中看,首先,噶厦最关心的是粮库,要求今年内必须开始粮库的维修工程,并指派涉及此事的阿里地区地位和职权最高的两级官员——堆噶本与普宗本,负责办理此事。噶厦政府在阿里的行政建制,是以堆噶尔本为最高军政长官,称为阿里基恰,其下分设宗和谿,宗相当于县级行政机构,其长官称宗本或宗堆,谿的地位略低于宗,不过行政功能差不多。(31)普兰为宗级行政单位,而噶尔通则为谿卡级行政单位。与雪灾后民力维难,无法支差,以致噶厦屡屡需要严厉督促地方政府必须维持驿站差役不同,地震后噶厦反而担心地方政府因灾后修复工程而滥用民力,要求地方官与民间协商,不得蹂躏百姓。至于宗府的修复工程,噶厦指示更为详细,连木料的来源及使用的先后顺序都有规定,可谓设想周到。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到,地震后的困难,最大的是建筑物毁坏后修复之时所需的材料,震后物资匮乏,以致所需木料要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解决。这可能跟普兰震后的修复工程量较大有关。
有的趣的是,对于修复工程的木料费用,两位堆噶本似乎有意让正因豌豆案而被调查的卸任宗本朗通巴来承担,这样既可以获得修复工程的必要资金,又可以不增加地方负担,保障自己的利益。不过如此落井下石之举,噶厦政府当然是不能直接表示赞同的。噶厦的态度是并不愿意将地方灾后负担转嫁到卸任官员身上,认为这一办法只有在朗通巴确实犯有相关罪行时才可以执行,要求阿里地方政府就此情况作详细调查上报之后,再听候噶厦的审核意见。可见,噶厦在处理世俗行政事务方面,严守规则,且又手段老到。
从此事可以看出,地震后堆噶本作为阿里地方的最高长官,极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借机为自己争取好处,他们二人甚至因为地震之后所办事务有所增加,而向噶厦索取额外薪俸,噶厦对此批复如下:
今后修建宗谿房屋,由普兰宗宗堆崔科娃负责。尔二人本不需薪粮,至于现任职薪俸,鉴于阿里地区常薪较高,且又有相当一笔招待宾客之储备费用,为此些许小事,索取薪俸殊不尽合情。惟若实属必需,可在竣工后陈明理由,再行酌情裁处。(32)
对于堆噶本的这种无理要求,噶厦并没有予以严厉的声斥,反而跟他们二人摆事实,讲道理,尽管不同意发给额外的薪金,不过恐怕是为了不影响噶本对修复工程的积极性,噶厦在最后一句话里还给他们留了一点加薪的希望,可见噶厦办事手段的高明。这段材料读来,颇能使人感受到当时双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以上的措置中,噶厦似乎更像一个精明干练的世俗政府,甚至是在涉及震后寺院修复这样的宗教事务上也表现得法度谨严。在给阿里噶本的批复中,有一段对寺院问题的处理意见,颇值一读:
关于维修谢林寺佛殿、僧舍、寺庙庄园倒塌房屋,以及借用劳力、发放工资等事,寺庙百姓不求自力解决,惟图依赖政府,虽有所不当,但若过去修缮时,对方确曾借用劳力,并有公章文件可资查证者,自应予以偿还。此次修缮普兰宗府时,可斟情索还支用;若文据无政府盖章,则不得有徇情和超额支用等情,务仰妥办。(33)
甘丹颇章时期,普兰拥有阿里地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贤柏林寺(gshags vphel gling)。该寺位于普兰宗府的达拉卡尔城堡上,建于17世纪末。阿里古格王国于17世纪30年为拉达克王国攻灭,17世纪后期,拉达克与甘丹颇章政府发生冲突,五世达赖喇嘛派出以甘丹才旺为统帅的蒙藏联军击败拉达克,将古格故地纳入治下,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伤亡,事后甘丹才旺为了忏悔亡灵而兴建了此寺,“贤”即藏文“忏悔”(vgyod gshags)的省写。(34)饬文中的谢林寺,当即贤柏林寺的省称。贤柏林寺在地震中似乎损失惨重,佛殿、僧舍以及所属庄园房屋倒塌,寺院方面的打算是想政府出资维修地震中损毁的建筑。1752年,达巴地震后达巴寺的修复工程是在噶厦的指导,达巴宗的主持下,督导三大领主共同完成的。(35)事实上,论地位贤柏林寺远比达巴寺重要,然而此时的噶厦政府似乎更多的考虑的是维护政府的经济利益,严格要求照章办事。要求寺院自力更生,但是甘丹颇章政权的政教合一的特点也决定了对此要求不能完全回拒,所以也留了一手变通的办法。因为贤柏林寺与普兰宗府同处达拉喀尔山上,双方毗邻而居,过去普兰宗府可能借用过寺院的劳力,因此噶厦同意如果能够找到正式文件证明普兰宗府曾借用过该寺的劳力,则这次修复普兰宗府时可以酌情资助寺院的修复工作。
尽管噶厦政府犹如一个干练的世俗政府,但实际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之下,宗教信仰的因素也始终牵动着他们的神经。在不会过分增加政府运行成本的时候,宗教的因素就展示得比较明显了。在噶厦的批复意见中,就对普兰宗府内的六臂明王殿的修复有特别的指示:
宗政府神庙中六臂明王殿堂,若因重修必须移动佛像,须请喇嘛向神佛占卜。如决定移动,须由僧众修法念经,保持洁净,不得使神像损坏,并须暂移一旁,一俟修缮完毕,立即迁回原处供奉,不得掉以轻心。此外,切不可因迁移神像,成为地方发生不幸事件之根源。切切注意!(36)
与前面几段指示立足于世俗事务不同,这段饬令体现的是藏传佛教信仰的指导作用。佛像的移动与否在这里成为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大事,不过噶厦依法保持了之前一贯的严谨作风,对佛像移动的程序规定也是非常严格的。
仅从档案显示的来看,1883年的地震和其后的处理中,噶厦的表现可圈可点。既能将纷繁复杂的世俗事务中条分缕析,法度严谨而又不失灵活性,同时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也恰到好处。这可能与此时西藏的中枢政治局势较好有关。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年幼,由功德林十世达擦活佛(1850-1886)摄政,十世达擦活佛名阿旺贝丹,1875年任摄政,清廷赐号通善呼图克图。他在任内成功地抵制了英国入藏考察的企图,主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和坐床,政治经验丰富。(37)此时噶厦中还有两位比较能干的噶伦,然巴·拉旺多吉(ram pa lha dbang rdo rje)、拉鲁·意西罗布旺秋(lha klu ye shes nor bu dbang phyug)。然巴家族是后藏的军事世家,拉旺多吉在1871年为代本,因平叛有功而得到提升,最迟在1878年成为噶伦。而拉鲁家族则是当时最显赫的家族,益西罗布旺秋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长兄,1865年其父死后继承辅国公爵位,1866年时曾参与平定瞻对的叛乱,1868年被赐予三品官衔,在当时的贵族中声望颇高,约在1880年成为噶伦。1881年驻藏帮办大臣维庆视察定结驻军时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引发暴乱。事后然巴与拉鲁陪同驻藏大臣色楞额前往日喀则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38)故而面对1883年的普兰地震,噶厦上述的应对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在这次地震善后处置中,噶厦与噶本双方虽然各有所求,但处理尚算得当,其修复工程应大体完成得不错。这一点从20年后进入普兰活动的英国殖民者的叙述中可以得到证实,当时普兰宗本居住的宗堡建筑在城区东边的山顶上,宗堡是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在西边则是普兰的寺院群,居住着大量的僧侣。尽管由于宗堡位于山顶,缺乏水源,因此宗堡附近房屋不多。但普兰的房屋大多是由石头或泥砖砌成,看上去非常牢固和舒服。(39)
在政教合一的近代西藏政治中,通过抬高宗教地位,神化公共权力以及权力持有者,把统治体系描绘成理想社会象征,其统治也就是履行某种天职,但同时也使得政治形式受制于宗教价值观。尽管宗教形式在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在本质上政教合一下的政治运行仍是世俗的。阿里地区由于物质基础薄弱,灾害发生后,往往破坏性大,除了政府一般无力救助之外,因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还会使地方的基层机构的经济来源中断,而使得基层组织难以为继。近代阿里地区雪灾与地震期间噶厦与阿里地方政府的表现充分表明,由宗教领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在面临这些灾情善后工作时,宗教神圣性并不能使一个政府摆脱世俗事务,他们面对的局面比世俗政府还要复杂,面对灾害及其相关事务,这些世俗事务处理起来还相当繁琐和困难。同时,灾害在政教合一体制之下,往往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信仰行为,不过这一点只有在物质上的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时,宗教上的考量才会随之增加。
①孙冬虎:《西藏近二百年来的重大雪灾》[J],《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第49—55页。
②《堆地二噶本因阿里卓学德萨部遭雪灾事呈摄政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③丁莉霞:《策墨林活佛系统的沉浮与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第28页。
④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版)[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⑤《堆地二噶本因阿里卓学德萨部遭雪灾事呈摄政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6页。
⑥清末刘锦藻曾说,“阿哩为全藏之西鄙,东至僧格哈巴布山及玛尔岳木岭,皆接后藏卓书特部界。”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舆地考·西藏》[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699页。
⑦南希·E·列维妮著,格勒、玉珠措姆译:《西藏阿里传统税收制度之比较研究》[J],《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23页。
⑧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邓锐龄校:《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155页。
⑨《堆地二噶本因阿里卓学德萨部遭雪灾事呈摄政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6页。
⑩《堆地二噶本因阿里卓学德萨部遭雪灾事呈摄政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7页。
(11)国庆:《清代藏区驿传制度蠡测》[J],《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第71—78页。
(12)《霍麦桑仓驿站百姓遭受雪灾疾苦情形经堆噶本呈噶厦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14页。
(13)《堆噶本就阿里三围雪灾致使百姓牲畜死亡望削减差税事给噶厦禀帖》,《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40页。
(14)《托钦达错所属普兰觉姆、阿岗诺诺等三小部落雪灾前后牲畜数目呈噶厦盖印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21页。
(15)王远大、杰敦:《汉藏英对照西藏地名(续)》[J],《西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132页。
(16)《堆噶本就阿里三围雪灾致使百姓牲畜死亡望削减差税事给噶厦禀帖》,《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40页。
(17)夏札·甘曲班觉等编,计明南加译:《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机构》[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3)》[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18)Sonam Joldan,Relationship between Ladakh and Buddhist Tibet:Pilgrimage and trade,Tibet Journal,2006(3),p.50—51
(19)房建昌:《西藏盐业的兴起、发展及其衰落》[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42页。
(20)[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1)《霍麦桑仓驿站百姓遭受雪灾疾苦情形经堆噶本呈噶厦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15页。
(22)舒介勋:《解放前西藏的差税制度》[A],吴从众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221页。
(23)《霍麦桑仓驿站百姓遭受雪灾疾苦情形经堆噶本呈噶厦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15页。
(24)《堆地二噶本就桑仓达错、霍麦二部雪灾前后牲畜数目呈噶厦盖印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13页。
(25)《阿里噶本为雪灾牲畜死亡赈济事呈噶厦文》,《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第一卷灾异志——雪灾篇》,第132页。
(26)鲁克亮:《清至民国时期西藏地震研究》[J],《西藏研究》2005年第2期,第88页。
(27)黄博:《清代西藏阿里的域界与城邑》[J],《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第14—16页。
(28)《噶厦对阿里噶本觉哲等地震呈文之批复》,西藏科技委员会、西藏档案馆编译:《西藏地藏史料汇编》(第一卷),第92页。
(29)噶托仁增次旺诺布:《贡塘王朝史——化幻明镜》(藏文版),收入《西藏史籍五部》(藏文版)[Z],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30)《噶厦对阿里噶本觉哲等地震呈文之批复》,西藏科技委员会、西藏档案馆编译:《西藏地藏史料汇编》(第一卷),第93页。
(31)王献军:《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组织机构和职官制度——1751年至1959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第24页。
(32)《噶厦对阿里噶本觉哲等地震呈文之批复》,西藏科技委员会、西藏档案馆编译:《西藏地藏史料汇编》(第一卷),第94页。
(33)同上,第93页。
(34)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版),第110页。
(35)《达巴宗堆为修复震坏寺庙呈噶厦文》,西藏科技委员会、西藏档案馆编译:《西藏地藏史料汇编》(第一卷),第25页。
(36)《噶厦对阿里噶本觉哲等地震呈文之批复》,西藏科技委员会、西藏档案馆编译:《西藏地藏史料汇编》(第一卷),第94页。
(37)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西藏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33—942页。
(38)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邓锐龄校:《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26、147页。
(39)Charles A.Sherring:Western Tibet and The British Borderland,London:Edward Arnold,1906,pp 208—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