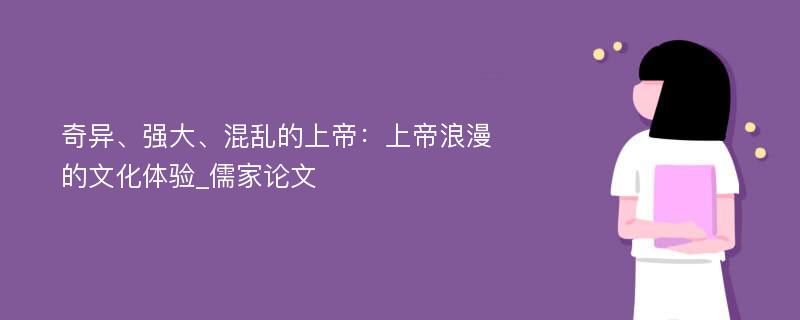
怪、力、乱、神:《封神演义》的文化品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位论文,封神演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中外艺术史,那些为传统文化结晶而成,又对传统观念起着正向强化功能的成功作品,固然赢得了本民族大众的喜爱而长盛不衰;但从发展的角度看,那些悖逆传统,为既定审美观所不容或难容的作品,因其体现着新兴文化观念,构成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动并使之嬗变、更新而尤为珍贵。我以为,就我国古典小说而言,《金瓶梅》可算“不容”的代表,《封神演义》则为“难容”的显例。
对于后者,清代褚人获曾在《〈封神演义〉序》中称引当时人的看法:“武王……其伐纣也,为堂堂正正之师,何尝为阴谋诡秘之说,如《封神演义》一文所云者。且‘怪、力、乱、神’四者,皆夫子所不语,而书中所载,如哪吒、雷震之流,其人既异;土行,七十二变之幻,其事更奇。怪诞不经,似当斥于仲尼之门者。”由此可见,《封神演义》为传统观念诟病或置不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恰恰高扬了儒家向所贬斥的“怪、力、乱、神”四字。实际上,正是在这里,《封神演义》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
一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不为一般论者所注意的“崇实黜奇”的思维模式。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作为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同,特别信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则律,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节奏。这样,在早熟的儒家理性主义精神滋养下的中国文化很早就形成了求是务实、不尚奇想的传统,极少对衣食之外的对象问奇询怪、妙想联翩。孔子所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子不语怪”便是这种精神的反映。走向极端,举凡一切有涉“奇”“怪”的事物都成了传统观念否定的对象。《礼记·王制》记载:“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异亦即奇,可见儒家对一切“奇异”之物何等深恶痛绝。《道德经》则载:“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把“奇物滋起”与“国家滋昏”并提,当作乱世的一个特征,显示了道家对“奇物”的否定倾向。明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四二也把“五方奇巧之选,杂然并集”看作世风颓败的标志。仅此数例,已可见传统文化崇实黜奇之一斑。
意大利文化史家维柯说得好,“好奇心,这是无知的女儿和知识的母亲,这种好奇心打开了人的心窍”〔1〕。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也曾断言:“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2〕。 传统文化务实黜奇的作风固然表现了中华民族脚踏实地的优秀一面,但也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诚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它“局限了人们思维的升华”〔3〕,“忽视对自然的改造, 对自然科学的研究”〔4〕黄铭远先生曾从哲学角度谈到这个问题, 指出中国哲学体系中缺少丰富而又深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几千年一直停留在用原始的朴素的元气自然论来解释物质的起源的水平上〔5〕。正是这种缺乏好奇心与惊异感的见怪不怪传统,长期以来阻碍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成熟与中国古代科技的更大发展。纵观中国科技史,我们发现,许多科技巨匠都出现在这种黜奇务实的儒家传统有所弛懈之时,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思想界玄学奇谈泛滥和文学界志怪小说浪潮迭起,科技界出现祖冲之父子、刘徽、裴秀、郦道元、贾思勰等大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农学家。晚明礼教传统崩溃,当文坛以“第一奇书”《金瓶梅》及《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的尚奇小说不胫而走之时,科技界出现古代罕有高潮,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王徵、徐霞客等巨匠纷至沓来。王徵把与传教士邓玉函合译的西方物理学著作命名为《远西奇器图说》,《徐霞客墓志铭》称徐霞客自幼“厌弃世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探奇测密”等,都从侧面透露了尚奇思想与科技发展内在联系的消息。
事实表明,崇实黜奇的传统观念限制了民族想象力的发展,阻碍了古代科技的进步。《封神演义》描绘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奇怪”世界,它以其超凡脱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向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提出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想象力的发展。社会学家李满先生在总结近二十年来大陆流行武侠小说的原因时说,“流行武侠小说被科学泰斗华罗庚称作‘成人童话’,著名科学家陈省身、杨振宁,著名人文学者章培恒、柏杨也对之爱不释手。至于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则更是趋之若鹜、为之倾倒了。其所以有如此魅力,大约可归结为‘奇异’二字”,并将流行武侠小说的特征和魅力概括为“奇境异景、奇缘异遇”,“奇招异术、奇功怪法”,“奇人异状、奇性异情”、“奇理深意、发人玄想”等四方面,“读之奇光异彩目不暇接,品之奇趣异味荡气回肠。”〔6〕实际上, 《封神演义》与流行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李满先生对流行武侠小说艺术奥秘的揭破也完全适用于《封神演义》。因为,作为我国武侠小说的“先驱”之作,《封神演义》与后世武侠小说,其“结构模式、叙述模式都是差相近似的”〔7〕,甚至在标榜“奇异”方面前者比后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试看作品所描写的昆仑山玉虚宫、终南山玉柱洞、青峰山紫阳洞,何处不是奇境异景;纣王侮亵女娲娘娘,子牙垂钓磻溪得遇文王,闻太师命丧绝龙岭,何时不是奇缘异遇;哪吒托身莲花,雷震子拍翅能飞,杨戬有百变不坏之身,个个都属奇人异状;伯邑考不受威逼色诱毅然受醢,文王装愚作痴忍咽子肉,马氏嫌夫无能弃夫而去又含羞自尽,何人不是奇性异情;至于奇招异术、奇功怪法更是比比皆是!所有这些,无不引发人无尽玄想。可以说,没有古代“土遁”“水遁”的奇想,就没有今日地铁、潜艇的发明,没有“金光阵”之类的奇想,就没有今日太阳能激光武器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不难看出,在古代的奇想与现代高科技之间,不过仅仅半步的距离。
二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斥力弱武、崇柔抑刚。这既表现在三元归一的主导一元儒家,也表现在辅相的二元道家和佛教。儒家的人格系统和审美范畴,固然存在崇尚阳刚的思想,但在总体上,仍是推许阴柔的,“子不语力”仅是此中一个最直截、最简单的信号。这里,我们要注意,在先秦儒家典籍中,与“力”相近的概念有“勇”、“刚”“强”、“武”等。《论语·公冶长》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吾未见刚者”,表明了孔子对勇、刚者的不屑。《中庸》则载:“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孔子对“宽柔以教”的君子的赞许与对“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强者的轻蔑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崇柔厌强的心态甚至影响到孔子对音乐的评价。《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乐记》疏称:“舞以文德为备,故云《韶》尽美矣,谓乐音美也;又尽善也,谓文德具也。虞舜之时,杂舞干羽于雨阶,而文多于武也。谓《武》尽美矣者,《大武》之乐,其体美矣;未尽善矣,文德犹少,未致大平。”由此可见,儒家开山宗师正因极度推崇“文”“德”“柔”“和”等阴性品格,才排斥“勇”“武”“刚”“强”等力的作风。实际上,《易传》在更多场合也是推崇阴柔美的,如坤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广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至于道家“贵柔守雌”的倾向更是首当其冲,《道德经》全篇充满了“坚强处下,柔弱处上”“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之类的表述。佛教强调“缘生性空”“无我无欲”,例如《涅槃经》“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当终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是处”,其守弱去强的人生理想与道家几无二致。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崇力的思想,如先秦法家主张“当今争于气力”,“力多朝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8〕, 但这一思想随着靠法家而起的秦王朝的灭亡而迅速失色,对后世影响甚微,因此,总体上并不改变文化贵柔斥力的特色。中国古代法家制度以文官为主,武将地位远低于文官,对待外来的武力威胁,希望用德化来征服,所谓“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结果国防废弛,屡遭侵略,都和这一传统密切相关。这既“影响着我国艺术的风格:偏重于柔美者多,偏重于壮美者少”〔9〕,又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发展。同欧洲人相比, 中国人带有更多阴柔羞涩特征,文弱平和有余,阳刚之达不足,制约了发展后劲。《封神演义》借正邪较量,大肆炫武倡力,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柔斥力的传统文化起到了补阳复壮的功效。
当然,《封神演义》推崇的力决不是单纯膂力、气力等体力。作品对这类力量并不欣赏。这从体力强壮的正反人物命运可以看出。在纣王杀妻诛子之际,方弼、方相挺身而出,背负殿下反出朝歌,“二人气力甚大,彼时不知跌倒几多官员,那里当得住他”,算是纣臣中首举反旗者,但最后在破十绝阵时自恃蛮勇,成了炮灰;“黄妃原有气力,乃将门之女,把妲己拖翻在地,捺在尘埃,打了二三十下”,但结果还是被纣王活活摔死;邬文化“力能陆地行舟”,纣王“千斤膂力冠群僚”,都落得个葬身火海的下场。这些描写表明:正,不能单纯靠体力成其正道;邪,更不能靠其膂力独撑江山。
《封神演义》推崇的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胆力。具备这类胆力的人物又分两种,一是商纣集团中正道直行,不忍坐视国家覆亡者,如杜元铣、梅伯、比干、商容等等,或力谏天子而遭枭首,或大骂纣王而被炮烙,或特来弑君而撞阶而亡,以其高尚气节、冲天胆力震撼了纣王朝的统治基础。这一胆力所赖以为基础的贤明政治的理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二是周武集团中的领袖人物和主要将领。如武王姬发明知“红沙阵”凶多吉少,为减轻西土祸乱,以万金之躯为轻,遭受百日之灾;姜子牙身为三军统帅,更是历经七死,从未退却;哪吒、杨戬等等也赴汤蹈火,决不胆怯。正是周武集团从上到下,一身胆力,不为强大的邪恶势力所吓倒,才将反抗纣王残暴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并引向胜利。
第二类是谋力,亦即智慧之力。“面对广阔的大自然,人自身的体力显得微不足道,智慧则显示了人更为本质的力量”,“运用智慧,尤其是运用机智和狡滑的欺骗战胜远胜于自身的对手”,“才是人所具有的最本质的力量。”〔10〕《封神演义》表现的智慧之力集中体现在周武集团群雄身上,它既表现在政治外交的战略策略方面,又表现在军事上的战术谋划方面。就前者而言,如西岐公子被醢为肉酱、文王仍然身陷囹圄已达七载之际,西岐留守政权在上大夫散宜生力主下,没有杀向朝歌,从而“造次胡为”,“陷主公于不义而死”,而是作出立即派人重赂奸臣的正确决策,“若奸臣受贿,必在纣王面前以好言解释,老大王自然还国,那时修德行仁,俟纣恶贯盈,再会天下诸侯共伐无道。举吊民伐罪之师,天下自然响应。”关键时刻的这一谋划,使文王及时摆脱牢笼回归西岐,奠定了经营西岐、并吞天下的不世之基业。又如纣王三十六路人马全被打败之后,姜子牙作出东征朝歌的战略部署,但武王囿于臣节和父训,不愿以下犯上,讨伐纣王,以免天下人笑他不忠不孝。针对武王的思想顾虑,也为了不给天下诸侯怀疑、防备西岐以口实,散宜生与姜子牙共谋以“观政于商”来统一内外口径,声称进兵朝歌只是“与天下诸侯陈兵商郊,观政于商,俟其自改”,“上可以尽忠于君,下可以尽孝于先王”,这既使武王以下广大将士不致背上“叛君背父”的思想阴影,又争取到天下诸侯的一致支持和拥护。一条标语省掉多少“思想政治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就后者而言,全书例子更多,如黄明反设圈套,裹挟黄滚与子黄飞虎共同造反;姜子牙同样将计就计,反设圈套使邓九公父女弃纣归周;金木二吒诈投守将,智破游魂关;杨戬多次幻形进入敌人腹中等等,无不显示了高超的斗争智慧。
第三类是功力、法力和器力。对这些力量的高度推崇,是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1.功力即一般武功之力,它能直接体现战斗者的本领,也是一般武侠小说用力最多之处。如黄天化连发掌心钉,打死魔家四将;邓婵玉一手五光石令纣王诸将和阐截诸神魂飞魄丧。2.法力指神仙作法之力,它是《封神演义》富于道家思想的一个特征。如清虚道德真君倒出神砂一捏,黄飞虎即摆脱闻太师追捕,安然逃走;姜子牙布罡斗,发符水,可以七月天冰冻岐山,又可以借北海水淹护西岐城。3.器力指各种法宝、法器之力,如混元金斗、化血神刀、打神鞭、五火神焰扇等等,皆具非凡之力。这些描写看似荒唐无稽,实则意味深长。如果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1〕,因而生产工具成为生产力要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可以说,各种战争时代的区别,也不在于为什么而战,而在于怎样战争,用什么武器进行战争,在战争生产力中,显而易见,武器成为重要的、有时还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三国演义》中,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道义与智慧的有无,主要取决战争者的勇敢和力气,如典韦、张飞、关羽等等人物;《封神演义》则用战争法宝替代了战争者的蛮勇。道高一尺也好,魔高一丈也好,高就高在法宝上面。这无疑可以看作战争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马克思曾经指出,“暴力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2〕。《封神演义》崇尚的力量以胆力为基础,以谋力为核心,以各种功力、法力和器力为直接表现形态。这种“以暴易暴”的暴力尽管不为保守儒家所接受,却是推翻反动暴政的必需。从文化的角度看,崇力思想确为阴性民族复趋健旺的一剂补药。
三
《论语·阳货》云:“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如果说正统儒家把自己看作正大的朱红和严肃的大雅之乐的话,那么,与正统儒家既统一又斗争的道释二家则无疑是恣肆的赤紫和不轨的郑卫之声了。赤紫不容夺朱,郑声不容乱雅,这是孔子的信念,也是此后一切正统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三驾马车,以儒为主的格局超常稳定和连续的一个基础。事实上,“儒家的纲常伦理,始终是各个朝代治国安邦的实质上的指导思想;统治者制定律定、朝纲朝仪主要依据的还是儒学典籍、保持的儒家传统;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仍被尊为最高道德原则;社会教育仍以儒学作为事实上法定的内容”〔13〕,一句话,儒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确实占据了独尊的、主导的地位。但在《封神演义》的艺术世界中,如日中天、光焰万丈的是道家,如月朦胧、清凉神秘的是佛家,儒家却成了最冠冕堂皇、又最软弱无能的代名词。这是《封神演义》首先从现象上对儒家地位的否定,可视为《封神演义》的第一层“乱”意。乱者,反也。
《封神演义》的艺术描写表明,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儒家是无能为力、甚至无法立足的;儒家要生存,只能仰仗于道家、受援于释家。以朝歌集团而论,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商容、梅伯、比干等文臣和欧阳淳、韩荣、窦荣等武将,他们内面对纣王这一邪恶暴君,外面对子牙这一强大对手,束手无策,惟有“文死谏,武死战”而已,“死”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就西岐集团而言,儒家的第一代最高代表是文王姬昌,第二代最高代表是武王姬发。文王恪守臣道,修仁布德,但无法避免七灾被囚、爱子被醢的下场。武王虽严守父训,但亦屡遭纣王讨伐,民众饱受干戈之苦;只有在得到道家代表人物姜子牙之后,西岐的天空才转阴为晴,充满了希望。试看道家,阐教也好,截教也好,他们无不具有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本领。没有道家中的邪派截教,纣王的江山早已不复存在;没有道家中的正派阐教,西岐的乐士亦将化为乌有。在人间,西岐的事业可以没有武王,但不能没有道家的术士姜子牙;在神界,诸神的职位更是直接由道家的元始天尊来敕封。一句话,天上人间,无道不立!而在正“道”(阐教)铲除邪恶的正义行动中,往往也还有西方佛教教主接引道人、准提道人的一份功劳,则显示了《封神演义》在高度推崇道家的同时,对佛教的一定重视。
这里我们要注意,《封神演义》中多次提到“三教”一词,乍一看,似乎是指儒、道、释三教,是将三教并重,其实不然。通观全书,“三教”一词在作品中的含义经历了三个转变,最初的确是指儒、道、释三教,并以儒为首,如第47回写道:“翠竹黄须白笋芽,儒冠道履白莲花。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元来总一家。”儒教是翠竹,是冠冕,是红花,显为三教之首。到第65回,三教之序则变成了道、释、儒,如该回写道:“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元来是一家。”道炼金丹,释炼舍利,儒修仁义,名虽一家,地位有别。到第78回、82回,“三教”的含义发生第二次转变,变成道家的阐教、截教和西方佛教的三教,儒教被悄悄抹去。这两回所写大破诛仙阵、万仙阵,布阵的截教,破阵的阐教和西方佛教,全是神仙大战,并无任何儒教影子。而阐教和截教实为一家道教之两派,故三教实变成了道释二教。到第84回,“三教”含义则发生了第三次转变,变成了是指阐教老子,元始和截教通天三位教主。因为前面朦胧言及的“三教共签封神榜”在该回已通过鸿钧道人之口,确指为老子、元始、通天三位教主受命“三个共立封神榜”。把西方佛教也撇开了,三教变成了道家一教。从“三教”一语含义在作品中的演变可以看出,在现实社会中仍然至高无上的儒家,在《封神演义》的艺术世界中则经历了一个从中心位置旁落,以至沓然无踪的过程。可见《封神演义》的作者是十分卑视儒家的。
不仅如此,《封神演义》还进一步从精神实质上否定了儒家的立足根本。众所周知,儒教作为礼教,在其“五常之道”中特别推崇“礼”,《荀子》以礼为“节之准也”、“强国之本”,礼的实质在于“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目的就是防止出现因不满现存统治秩序而发生“争则乱”的造反现象。所以孔子直接把“礼”与“乱”对立起来,称“勇而无礼则乱”〔14〕。而礼的主体又在于父子、君臣之礼,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间。”〔15〕父子君臣之礼的全面含意包括父慈、子孝,君惠、臣忠,是两两对等的,但实际上,由于父子君臣所处地位的不同,这一价值标准人为地向君父一端倾斜,臣忠与子孝被作为压倒一切的观念提升起来,成为传统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成为社会稳定的最重要思想基础。同理,家族同辈成员之礼,也特别强调年幼者对年长者的“悌”。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家国同构”的首要特征,〔16〕忠、孝、悌遂并列成为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所以,孔子又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7〕《封神演义》不仅从现象上把儒家置于“无用”的位置,而且从精神实质上否定了儒家忠、孝、悌的合理性,为“犯上作乱”者辨护张目,这可视为《封神演义》的第二层“乱”意。
首先,《封神演义》通过否定忠的极端形式愚忠否定了忠本身。文王恪守“君叫君死,臣不得不死”的教条,七载被囚,不敢怨君;受子牙左右诛伐崇侯虎之后,顾虑“有违天子之制而擅专征伐者,是为乱臣。乱臣者,杀无赦”的律典,在“孤与侯虎一般爵位,自行专擅,大罪也”的恐惧中郁郁而终:愚忠教条给他长期的肉体之苦后,复从精神上窒息了他的全部生机。伯夷、叔齐以“子不言父过,臣不彰君恶”阻止子牙吊民伐罪,并宣扬“至德无不感通,至仁无不宾服”,但一切不过痴人说梦,至德不通,至仁不服,只剩下徒劳无益的“守节饿死”。欧阳淳、彭遵牢记“食君禄而献其地,是不忠也”的古训,不愿忘君徇私,结果只是殉君先葬而已……对于朝歌文武而言,矢志忠君者惟有一死,弃忠叛君者,就是弃死归生,苏护、黄飞虎、邓九公等等就是明证。对于西岐君臣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文王愚忠,先囚后死;武王伐君,则广有天下;子牙等“彰君恶”“自专擅”“谋为不轨”,更是无往而不胜。儒家千方百计维护的“忠”实在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其次,《封神演义》还通过一些人物的命运描写来否定儒家的愚孝观。纣王之子殷洪殷郊在其母被害后持剑进宫,要杀父妃妲己,可谓不孝,虽然被纣王追杀,终被仙人所救,学成一身武艺;但后来为孝所动,又效力父王,结果一遭犁锄,一成飞灰。武王严遵父训,不伐朝歌,朝歌勘乱兵马车轮转来;昔父弃训,大周天下一鼓而定。黄飞虎若听父亲黄滚之直,回头归商,一门尽将族灭;逼父共同叛商,遂成西周开国不世之勋名。哪吒剜肠剔骨,断父子之情,一时魂魄无依,终究成就仙体。这些人物的命运清楚地表明,愚孝即死,弃孝即生。再次,《封神演义》还通过崇黑虎设计谋诛哥哥崇侯虎父子,云霄娘娘轻怠哥哥赵公明的肯定描写,否定了儒家的愚悌观。
当然,《封神演义》对儒家愚忠、愚孝、愚悌观念的否定是有着自己的“批判的武器”的。这“批判的武器”既渊源于古代天命观和民本思想,又直接受胎于晚明以李贽为发端的新思想浪潮。它包含如下三重蕴意:1.天命不可违。如黄飞虎等人再三说到,“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可见天命有归,岂是人力。”2.民愿主宰天命。如召公祝文中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姜子牙劝武王继续进军朝歌时说到,“惟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民命主宰天命,这就巧妙地将天命观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使传统的民本思想转换成一种类似“天赋民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新思想。纣将芮吉曾对邓昆说到:“你我如今虽奉敕协同守关,不过强逆天心民意,是岂人民之所愿者也!”“人民之所愿”在作品中占据了主宰一切的中心位置。3.贬抑君权进而否定君治。《封神演义》在强调民愿的同时,还抬高臣权抗敌君权,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不正,臣投外国”,“天下所共弃者,又安得谓之君哉!”最后上升到对整个封建“家天下”的彻底否定——“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明末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界最脍炙人口的这句口号成了姜子牙的坚定信念。这可视为《封神演义》的第三层“乱”意。
在冲击礼教的新思想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倡导三“乱”的《封神演义》必将进一步加剧传统文化思想基础的深刻裂变。
四
“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的《封神演义》,的确不是“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的产物,因此,以马克思关于神话的经典论述来衡量,它自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神话;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封神故事在民间世代流传的持久性,并且考虑到荷马的史诗也不是“不自觉的艺术方式”,但无人怀疑其神话属性的话,我们把《封神演义》看作神话而不仅仅是神魔小说或神异小说,当不为过,著名神话学家杨堃先生曾指出,“如果《封神演义》仅是一部神异小说,不是神话,那末民间宗教的许多神话,均将失去依据。”〔18〕在我看来,《封神演义》不仅是一般的广义神话,还是一部奇特的英雄神话。
如前所述,以早熟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务实黜奇、崇实抑虚的重要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上古神话的命运,一是遭轻视,任其湮没不闻。《论语·先进》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雍也》载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儒家圣人的这一态度一直被后世儒家所记取,例如号称“一代大儒”的隋代王通就是如此。《中说·天地》载:“陈叔达问鬼神之道。子曰:‘敬而远之’。”表面上是“敬而远之”,实际上是冷淡和轻视。二是被历史化的改造。儒家以理性主义眼光看待神话,一方面觉得荒唐无稽,不免轻视冷淡,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教化服务,便对神话进行了“合理”的、历史化和伦理化的阐释和改造。“他们以恢复其历史真相为由,将那些他们认为无法接受的超自然成分加以摒除,只保留平淡无奇的渣滓”〔19〕,例如众所周知的孔子对神话传说“黄帝三百年”、“黄帝四面”、“夔一足”等的解释。这种历史化的改造和传统文化重集体、不重个人的伦理追求相结合,决定了中国上古神话的第三种命运:具有反抗性的神话英雄的丑化和褪色。神话英雄作为神话的中心形象,“拥有强大个体的人格力量,能单独从事和完成许多英雄业绩。对于一个强调个体人格力量的民族而言,英雄神话是最好的精神武器,而对于重民族集体意识的文化来说,英雄神话则是一股逆流必须被斩断。”〔20〕于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作兵伐黄帝”的神话英雄蚩尤,成了《大戴礼》中的“庶人之贪者也”;《淮南子·本经》中“上射十日”而下除民害的神话英雄后羿,在《离骚》王逸注文中变成了“荒淫游戏,以佚畋猎,又射杀大狐,犯天之孽”的诸侯;《山海经·海内经》中“窃帝息壤以堙洪水”的英雄鲧,变成了《论衡》中不守本份,“欲得三公”、“欲以为乱”的造反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不得善终。中国上古瑰丽壮观的神话殿堂,在这三种命运打击下,早已只剩下断壁颓垣、残砖破瓦而已。
任何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民族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神话。“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神话形象的历史化,那末到了中世纪则正相反,历史人物经历了神话的过程……”〔21〕《封神演义》将武王伐纣这一稽诸史典的重大事件神话化,借此重塑上古诸神的形象,编制民族化的“神谱”,恢复神话英雄的威名,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反刍”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封神演义》与荷马的《伊里亚特》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的共同之处:成书形式,二者都是在民间长期口头流传的基础上,由文人写定;内容,都是追述古代战争;战争根本原因,都是得罪至上女神,《封神演义》是创世女神女娲,《伊里亚特》是天后赫拉;战争直接原因和焦点人物,都是美女,《封神演义》是妲己,《伊里亚特》是海伦;战争方式,都是诸神分派参与并决定战争的胜负;阵亡者结果,《封神演义》是灵魂上封神台,《伊里亚特》是灵魂入冥国。因此,可以说,《封神演义》描写的是一场中国式的“特洛伊之战”。通过这场战争,《封神演义》编制出一部包括“三界八部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在内的民族化的“神谱”。其特色在于:1.神的来源是仙和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或为逆天而行的犯戒之仙,或为助纣为虐的山精水怪,或为品行恶劣的奸诈小人;上至万恶之首的纣王,下至屑小卑微的马氏,他们和少数正派仙人君子同封为神,表明这仅仅是一个善恶不问、冰炭同炉的阵营而已。这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在民族宗教观念中,神与仙还不一样,对于仙,人们还稍稍恭敬、仰慕些,而对于神的态度则与对常人的态度竟无二致。”〔22〕作品第77回元始天尊说到,“根行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稍次,成其神道;根行浅薄,成其人道。”上封神榜的都是不能成其仙道者。2.神谱中没有一个宙斯式的最高主宰,神谱之上另有一个松散的仙统,也是没有一个最高主宰。在现实社会中,早在《封神演义》成书前的明代初年,民间宗教就形成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宫天神系统,以太上老君为首的散仙真人系统,以如来佛为首的西方极乐世界。而在《封神演义》的神话世界中,神界无至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的划分;仙界无至尊,元始天尊之上有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之上有鸿钧道人,鸿钧道人之外有资格更老、自由自在、不入何宗何派的女娲、神农、伏羲等等;西方极乐世界亦无至尊,教主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是师兄弟关系,情同手足。可以说,《封神演义》的神话世界是一个无君无父的世界(有些神生前有君臣、父子关系,死后封为同等之神,君臣、父子关系消失)。要而言之,《封神演义》的神谱世界是一个泯善恶、等尊卑的彻底平等世界。这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君父至上,忠、孝、悌等道德教条乃天理的彻底否定。
神谱无至尊,并不表明《封神演义》的整体神话描写没有中心人物。占据《封神演义》神话世界事实上的中心地位的是人间的姜子牙这一不像英雄的英雄。有论者讥讽姜子牙发迹前是个无能君子,孰不知大器晚成正是古往今来多少英雄的本色。姜子牙并不孔武有力,但多少壮汉豪杰任其驱遣;他道行并不高深,但无数得道大仙听其调度;他是凡人,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却由他来正式敕封。这个耄耋老翁之所以能成为全书中无可匹敌的中心人物,主要在于,他代表了一种和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新兴观念,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姜子牙固然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具有顽强的意志和韧性精神,难能可贵;但更可贵的在于,他眼界高远,不拘泥于“愚夫愚妇之小忠小谅”,坚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顺应人民的呼声,在多次打退中央政权的征剿之后,及时发动摧毁残暴专制的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斗争的前前后后,他处处照顾人民的利益,在救民于倒悬的同时,努力减小暴力斗争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如部下要求各遁进城,里应外合,一举攻破朝歌,姜子牙的回答是,“不然!今众人进城,未免有杀伤之苦,百姓岂堪遭此屠戮。况都城百姓,近在辇毂之下,被纣王残虐独甚,惨毒备尝,今再加之杀戮,非所以救民,实所以害民也。”和平占领朝歌后,他又传令“各门止许进兵五万,其余俱在城外驻扎,不可入城搅扰。如入城者,不可妄行杀戮,擅取民间物用。违者定按军法枭首!”姜子牙始终把“人民之所愿”作为一面旗帜高擎在手中,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把握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用旧的天命观包裹民愿的新内核,天命的不可抗拒变成了民愿的不可抗拒,由此,他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民愿决定论”,这就和一般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判然相别开来,显示出浓厚的近代色彩。
神话学家指出,“一个成功的神话能鼓励人们在旧理由不再站得住脚时去创造新的更可尊敬的使人们仍然相信它的理由。”〔23〕《封神演义》用神谱世界否定现实世界,否定了君父至上,忠、孝、悌至上的“旧理由”,同时为我们创造了民愿决定一切这一“新的更可尊敬”的“理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以后,曾经做过商人的姜子牙在《封神演义》中以神话英雄的面目,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几乎同时出现,决不是历史的偶然。应该说,姜子牙不只是个神话英雄,还是个真正的文化英雄。他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崭露头角之际,中国文化发展所呈现的新生机。
注释:
〔1〕《新科学》卷二《诗的形而上学》第一章。
〔2〕《形而上学》中译本。
〔3〕范楚玉《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4〕〔16〕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
〔5〕〔22〕《黄色文明——中国文化的功能与模式》。
〔6〕《流行风探秘》。
〔7〕参见李汉秋岳麓书社版《封神演义·前言》。
〔8〕《韩非子·显学》。
〔9〕敏译《中国美学思想史》卷一。
〔10〕欧翔英《小议史诗〈奥德修纪〉的阳刚之美》(《渝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13〕参见赵书廉《中国人思想之源——儒释道思想的斗争与融合》。
〔14〕《论语·泰伯》。
〔15〕二程《遗书》卷五。
〔17〕《论语·学而》。
〔18〕《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1 期)。
〔19〕昂利·马斯佩罗著、冯沅君译《〈书经〉中的神话》。
〔20〕张慧《英雄的陨落》(《西藏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1〕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语(《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第2期)。
〔22〕K·K·卢斯文著、耿幼壮译《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