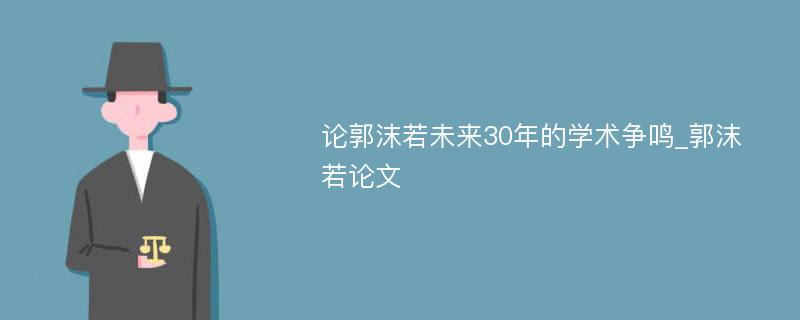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三十年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25(2002)04-0010-10
社会大变动、大转折的时代往往是学术争鸣的时代,郭沫若一生正值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实现民族独立和向近代化、现代化转换的时期,中西、新旧各种文化碰撞激荡、交融互动,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诸子百家峰起之时。作为百科全书式学者和坚定革命战士的郭沫若,在长达四分之三世纪里活跃在这个社会变革和文化嬗变的潮头,发起、倡导和参与了大小数百次的学术论战和学术争鸣。他在频繁的论争中不倦地探索和追求真理,不断地求异、创新,他对文化学术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碰撞激荡的过程中千回百转而汪洋瓷肆地发展起来的。
郭沫若对学术争鸣推动学术繁荣、启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对春秋战国的学术争鸣尤有独到的体悟。早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他就把春秋战国时代比拟为“第一次五四运动”,深刻地指出,是“社会的转变”“促成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群花怒放”,“由秦到现在两千多年了,我们依然感觉着春秋战国在学术思想史上是中国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思想学术,无论是南派、北派,都富有独创精神。……可惜自秦统一中国后,文化潮流便被中断了。”接着,他满腔热忱地预言:“以前是历史左右人的时代,以后是人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中国人又临到新的时代了!我们应该有计划地来创造历史。”[1](P13)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发展、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使郭沫若像在暴风雨中翱翔的海燕一样,从不畏惧学术论战和争鸣,而是始终主动积极地发起和参与学术论争,以推动历史潮流、文化潮流向前发展。
说到郭沫若对学术争鸣的态度,他在1924年《整理国故的评价》中有两点见解值得注意;一是他针对当时有关国学问题的讨论,既反对“笼统地宣传国学”的倾向,又批评“笼统地排斥国学”的弊端,指出当时所谓的整理国故,充其量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强调,学术应重在“新生价值的创造”,而不是“既成价值的评估”。二是他认为研究国学可让一部分人去做,但不能勉强人一例照办,由此讲到了一种多元文化观,指出:“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百川殊途而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以见出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2]在今天看来,郭老这里的两点重要见解,恰体现了两种精神:其一是文化学术贵在创新的精神,这是学术争鸣的目的,是学术发展的生命灵魂和结穴点。文化传承落脚于创新,充分占有材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考证,目的是打造文化精品,创造新的价值。其二是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多元文化和而不同,不同中见出大同,这是学术争鸣应持的态度和应有的氛围。这两种精神,纵贯郭老的学术生涯,正好形成他一生为开启新时代、创造新文化而参与和倡导学术争鸣、学术论战的相互联系的双重视角,透露出他对待学术争鸣与学术论战的立场态度、心态变迁和思维定势选择的重要信息。这两种精神在郭老1949年建国前的历次学术论争中,是一以贯之,有目共睹的。在郭老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中,有一些复杂的情况需要辨析,学者的看法也不大一致。总的说来,这两种视角常常作为郭老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的母题,促成他学术创新精神的重光和再现;但也有同这两种视角逆向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二种精神的贯彻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影响到他对学术论战、学术争鸣的不同态度,而这又同时代条件和政策环境有关。因此,本文着重就1949年以后郭老所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加以爬梳和分析。
一、后三十年郭沫若学术争鸣历程寻迹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成为国家领导人,担负了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他仍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术活动,倡导学术争鸣,发起学术论争。在他广泛涉猎的文史领域中,重大学术活动和学术事件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并且常常居于显著位置。大体说来,这三十年郭老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可划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1949年至1957年。这一时期郭老的学术争鸣有三类情况:
一是郭老作为中国唯物史观派史学的首倡者继续进行古代史的探索,主要是完善他在三、四十年代已经建立的奴隶社会学术体系,围绕奴隶社会与古代史分期问题与不同见解的学者开展争鸣。在这里,郭老是以学者的身份、平等的态度参加学术讨论的。他曾为郭宝钧披露发现殷代大量活人殉葬的地下材料,提供了殷商为奴隶社会的新证据而欣喜,又因郭宝钧对材料的释读有变而不悦;他曾针对“西周封建社会论”和“两汉奴隶社会论”的学术主张开展“两面论战”,据理力争。关于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问题上,郭沫若与范文澜的意见针锋相对,但都当作学术范围内的自由讨论,气氛融洽温和。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之所以生气勃勃,涉及的问题广泛,参加的学者众多,言路广开而顾虑较少,这同郭老身体力行的学术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例如关于殷代殉人是否为奴隶社会的证明问题(1950年),他就对持否定见解的作者杨绍萱作答,既指出他的判断不对,又检讨该由自己负责,是自己早年的错误观点对其影响所致,希望“根据史实把那种不正确的判断丢掉”。[3](P84-96)“对于西汉奴隶和佣假问题(1951年),郭老一方面对争鸣的作者王静如指出其有价值之处,同时诚恳地指出其错误之点;另一方面又说明自己多年来就想解决中国奴隶社会这个问题,因王文而引发学术思考和进一步探究的兴趣。[4](P811-812)对于崇墨非儒的不同见解(1951年),他则持定一贯见解,毫不退让。[5](P16)
二是郭老对于本来认为已解决的历史公案,因不同见解而引发了再争论。例如屈原问题,早在五四以来直至抗战期间就围绕屈原其人是否存在,屈原是否文学弄臣等问题有过多次争论。否定屈原的一方有胡适、卫聚贤、何天行、丁迪豪、孙次舟等人,他们基本承袭民初廖平否定屈原存在的思路,提出屈原其人是个虚构的“箭垛式”的“复合物”,主张屈赋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及其僚属的作品,[6](P146-163)认为屈原不过是“文学弄臣”,不应该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肯定和歌颂屈原的则有郭沫若、陆侃如、梁宗岱、姜亮夫、谢无量等多人。其中,就研究的深度、高度而言,以郭沫若的成就最大。他以坚实的学术底考证出屈原的生卒年代,在《楚辞》的考据训诂方面深化和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联系时代背景对屈原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了深层次的挖掘。郭老历史剧《屈原》的巨大成功,就是建立在这种坚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经过郭老等人的研究,不仅解决了屈原其人的有无问题,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使“学习屈原,研究《楚辞》,差不多成为了一种风尚”。[7](P19)但在建国后,1951年朱东润先生又重提《楚辞》作者问题,他承袭何天行之说,主张《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而《离骚》以外的屈赋则为刘安幕僚所作。郭老对这种看法连续撰文展开雄辩的论争,论点鲜明,论据翔实,态度坚决。与对待前述类型的争论采取温和态度不同,郭老用了些比较俏皮、挖苦的语言指责其谬误,并在其佚作中认为朱“史识毫无,文学见解亦甚卑下”,“不顾事实,一味好奇,可叹”。[8]这可能是因为屈原问题牵涉到第二年(1952)世界和平理事会能否把屈原列为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纪念的缘故吧。在这样大的原则问题面前,郭老自然是不会让步的。顺便说一下,80年代日本学者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被中国学者据理反驳,赵逵夫等从《战国策》中考订出屈原活动的史实,从钩稽先秦散佚的典籍中查出屈原的家世,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得到了确证。[9]
三是由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而被赋予了政治斗争性质的变了味的学术讨论。其中重大的有对《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因电影《武训传》而引起的武训是封建社会的奴才还是兴义学的教育家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武训进行批判的“一边倒”舆论,郭老为此两次在报上公开检讨,自己不该称颂武训。[4](P822)其实他对武训未作过研究,未写过文章,所谓“错误”不过是为《武训画传》题词时作过有保留的称赞。[4](P827)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郭老身居文联主席之位,只得紧跟表态,提出“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应该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加紧扶植新生力量”等三点建议。[10](P19-36)郭老虽然对这些被赋予政治性质的学术论争,口头号召积极参与,但他并未写文章参加批判。同时,作为文化界领导人,还主动为所谓“错误思想”的泛滥承担责任。至于由红学讨论延伸到对胡适“反动思想影响”的批判,郭老的态度则显得更积极一些。这一方面是他真诚地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是胡适,“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胡适”;[10](P25)另一方面,他同胡适的思想分岐由来已久,早在20和30年代古文字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过程中已同胡适学术思想有了交锋。自称“一出马我们就反对胡适”。[11](P145)当胡适蔑视地称左派是拿“没有东西”打“有东西”时,郭沫若以学术界初生之犊的勇气喊出就是要拿“有东西”来打倒胡适的“东西”。因此,在全国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时,郭老积极推波助澜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反胡风和反右运动,在当时的大气压下,郭老表态坚决,讲过慷慨激昂的话,但那已不属于学术论争范围,他也没有以自己的研究来为被批判者罗织罪名。
第二段是1958年至1965年,这是郭老倡导学术争鸣相当活跃、积极的时期,几乎每年有一个大讨论的专题。1959年是围绕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和替曹操翻案,1960年围绕武则天的功过是非,1961年围绕《再生缘》,1962年则围绕郑成功开展讨论。1965年,又就世传摹临王羲之《兰亭序》帖原作真伪问题发起讨论。在这一时期,郭老还积极参与了有关新诗发展方向及史学研究“厚今薄古”等问题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郭老的学术争鸣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历史研究与史剧创作结合。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发起的学术讨论,多是“作为创作的准备”。郭老“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12](P3)这是他创作历史剧的又一个盛产期。
二是中心围绕“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翻案”,[13](P476)以“人民本位”和“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18](P37)“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13](P476)“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要替曹操翻案”,[1](P409)写《武则天》剧本是为了还她作为发展贞观之治、为开元之治奠定基础的盛唐女开明政治家形象的本来面目。[15](P245)对于多遭否定的殷纣王、秦始皇,他都认为应该翻案。
三是在写这些剧本时,大量融入了郭老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和感情。他曾宣称“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他自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因而“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1](P408-409)写屈原、写武则天,也贯穿了自己的感情体验,同时又注意了历史的真实性。他也曾宣称屈原就是我!武则天就是我!他是把艺术的创造与历史的真实充分地结合了起来的。
四是由郭老发起的这几次学术讨论参加的规模大、范围广,讨论问题较为深入。在左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日益浓厚的情况下,郭老仍竭力贯彻“双百”方针,实践学术民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蔡文姬剧本和武则天剧本都曾主动征求戏剧家、导演、演员、学者等数十位朋友的意见。关于《再生缘》和《兰亭序》的讨论,尤其体现了这种真诚的民主学风。郭老是看到陈寅恪对《再生缘》的高度评价后才开始阅读它的。陈的高度评价使他感受到“高度的惊讶”。而在读过之后,他十分倾心佩服陈的看法,认为《再生缘》的艺术价值可以和印度、希腊有名的大史诗相比。他公开声称:“《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归功于陈寅恪教授”。同时又检讨自己属于“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类型。他先后两次登门会见陈寅恪,进行惬意会心的讨论,并公开承认正是陈寅恪的钩沉发掘,引起他四读《再生缘》的浓烈兴趣,而从事《再生缘》前十七卷的校订工作的。[1](P880,P929-930)近日由郭老校订的该书终于出版,这可以作为郭老民主、谦虚、务实学风的证物。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从来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谜。传世的近二百种帖子都是后世的摹本或临本。郭沫若从当时新出土王谢墓字迹及《兰亭序》与《世说新语》注引的《临河序》文字不同,怀疑连书法带文章都出于隋代智永的依托,这又引起了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先生的驳议。过去有人盛传郭沫若压制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久前高二适先生的公子高泽迥已撰文澄清了这一事实。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经章士钊推荐给毛泽东,毛致函郭老商议发表,郭接该稿后第五天《光明日报》就发表了高文,并无压制不发之事。[15]接着郭老又发表文章欢迎高文的发表,并表示,“《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1](P592)郭老对此采取的仍是他对待学术争鸣平等虚心商讨的态度。
第三段是1966年至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正常的学术争鸣可言。1966年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郭老在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上即席发言,表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16](P1328)对郭老这一表态,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表示异议。郭老于1967年8月25日在答复读者来信中说:“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17](P409)这是郭老在“文革”期间反思自己学术思想的真实心态,其深刻内涵值得玩味。尽管当时只有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而无正常的学术争鸣,尽管郭老连续经受了两次老年丧子的切肤之痛,他仍坚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导和关心考古发掘,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的发掘,关心云南昭通出土的西汉孟孝琚残碑的情况和下落,要昭通文物部门注意保护。[18](P407)因不涉及学术争鸣,在此不详述。二是写出了争鸣性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文革”后,此书甚为学者诟病。如从“火中凤凰再生”的郭老的真实思想看,仍不失为破传统、拓新意之作,可由此读出个中况味,近年已有一些论文进行读解。
“文革”后,郭老在世时间很短,精力日衰,不可能再发起和倡导学术争鸣活动,但他一直不辍笔耕,关注着民族的复兴和科学的繁荣。
二、学术争鸣与新价值的创造
学术发展的生命力贵在创新和养新。清代学者钱大昕著有《十驾斋养新录》,特地标出“养新”二字,并在自序中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咏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如以“新枝”、“新叶”比拟学术时累时进的创新成果,则“蕉心”“新心”体现做学问的功力和根底,“新德”体现学者常新的道德性情,这些都需要不断地涵养调养,不断地吸取养分,获取“新知”。以上诸端结合起来,良性互动,就是学术创新的全过程,而创新的关键又在“养新”二字。“养新”绝不限于学者的个人修养,重要的是在学术群体内以至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知”并催发“新知”成长的环境氛围,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养新”与“创新”的关系,也就相当于学术争鸣氛围与新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
郭老作为专博兼擅的文化巨人,作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开拓者和创新者,与时俱进,领异标新,“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取得许多创新的成果。”[19]郭老一生许多创新性成果就是在学术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是不断“养新”的结果。在建国以前,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是在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压制、打击和围剿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整个社会当然谈不到提供有利于学术争鸣和学术创新的环境氛围。但“反者道之动”,敌对势力的围追堵击,恰恰激发了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文化披荆斩棘,不断壮大,不仅在学术文化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而且日益赢得优势,赢得人心。而在进步的学术文化界内部,则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民主、和谐的学术空气,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所在的重庆天官府,就聚集了一批矢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众多的进步文化人,他们既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又在学术问题上持独立见解,经常相互争鸣,切磋问难,这无疑对学术创新起了很好的催生助长的作用。
正是基于对春秋战国和五四以来两次“百家争鸣”历史经验的深入研究和切身体会,郭沫若迫切地期待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群花怒放”的时代到来。当毛泽东1955年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剧发展方针,1956年又扩展为科学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郭沫若热诚拥护,高呼“‘百花齐放’万岁”。[20]在邀请陆定一到科学院作“双百”方针报告之后,他又发表《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一文,指出,目前我们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正充分具备着“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今天的百家争鸣,既不同于我国战国时代的诸子峰起,也不同于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过去时代的‘百家争鸣’只能经历得一定的历史时期,而今天和今后的‘百家争鸣’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可以保持于永远。”[10](P283-284)这是郭老发自肺腑的期望和呼吁。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党在国内阶级形势估量上背离了中国实际,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术文化方向上发生逆转,本应“保持于永远”的“双百”方针变成往往停留于纸面的东西。而这个严重的责任,当然不应由郭沫若来承担。就郭老自身而言,他是努力于学术创新,致力于争鸣环境养新的。在上述文章中他强调“百家争鸣”应该包含独创性的“标新立异”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步骤这两条内容,确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真知灼见。
郭老说,“为了使得‘百家争鸣’更好地展开,倒应该欢迎‘标新立异’。凡是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未有不是新异的。只要你有社会基础,有理论根据,你的学术价值迟早会得到广泛的承认。一时性的‘异’会转变为比较长远性的‘同’。反过来,尽管有一些东西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天经地义,只要失掉了社会基础和理论根据,就会成为无用的长物,不可理解的怪事了。”[10](P283)这里不是依然鲜明地体现出文化“贵在创新”的精神和“和而不同”的精神吗?
通观上述郭老后30年发起、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犹如建国前他在学术争鸣中取得创新成就一样,郭老在建国后仍然依靠或者伴随着学术争鸣而取得一次次学术创新成果。从学术创新的思维方式这一视角来观察,郭老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有益经验,突出特点有四:
一是通过价值重估发展学术。
按照前述郭老对学术研究的分类,有一类是考掘、整理国故式的对“既成价值的重新估评”,这虽不同于“新生价值的创造”,但往往是学术创新必要的基础工作。如郭老通过为期三年的整理和校订,校注出《管子集校》,堪称该项古籍整理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博大精深”,嘉惠学者无量。他还通过整理、加注,出版了《盐铁论读本》。而因写作《蔡文姬》,不惜花费精力对《胡笳十八拍》的作者和大、小胡笳的内涵六作考证,则可说是在学术争鸣中价值重估的典型例证。在《兰亭序》真伪上能跳出成说,在众人不疑处生疑,启发新的思维,不管结论最终是否靠得住,总是对破解中国书法史上一大谜起了推进作用。
二是通过翻案进行学术创新。
翻案是“标新立异”的一种形式,是学术创新、出新的一条途径,而“好翻案的脾气”也是郭老这样浸淫了崇尚今文经学传统的巴蜀文士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特点。在郭老后期学术争鸣中,“翻案”是取得学术成就最多的闪光点。例如对蔡文姬和武则天的研究和创作,既产生了两部名噪一时的剧作,又引出了两个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而且是参加争鸣的众多学者群体智慧结晶的成果。其一是由蔡文姬的研究引出替曹操翻案,这是郭老创作《蔡文姬》的主要动因。郭老带头写文章,同翦伯赞一道发起了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使曹操这个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特别是宋明以来被艺术加工为“奸雄”,以致妇孺皆知的反面教员形象,逐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虽不说最后盖棺论定,但一个对中国社会发展既有功劳也有过失的人物形象总算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二是由蔡文姬和武则天剧本的创作,引出了历史学与历史剧的关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关系的大讨论。郭老是主张历史学要真实,历史剧可浪漫,历史剧要建立在重要事件和人物必须真实的基础上,因此,郭老每次创作历史剧前都用很多时间来作历史研究并以此作为创作的酝酿准备。建国后的历史剧创作仍坚持了这种以研究求真实地的方法,但更加上了一个新的主张,就是“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我们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追求历史真实,实事求是,然后进行加工、想象和夸大。”“易卜生的写实手法有点过时”,要加上些浪漫主义。他还进而认为科学与艺术要结合起来:“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郭老这些见解,应该说是脱离了教条主义窠臼的、具有创造性和一定前瞻性的东西,对今天繁荣创作,发展文化,实践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也还有思考和借鉴的价值。
三是砂碛中淘取金屑。
1962年1月郭老在校对《崖州志》时,提出了“从糟粕中吸取精华,从砂迹中淘取金屑”的意见。这是郭老根据学术争鸣的经验得出的独到见解,也可视为学术创新的又一个思维方法。郭老善于从大量史料中发现问题,解决关键,即是淘砂取金之法。这里仅举《读<随园诗话>札记》为例。袁枚的《随园诗话》曾风靡一世,为性灵派的代表作,而随着时移代易,神奇朽化,“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郭老则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办法;“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从陈见中读出了新意,这本《札记》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上的重要随笔著作。
四是突破主流见解创立新论。
郭老在“文革”万马齐喑的畸形年代出版了《李白与杜甫》这部晚年的学术绝笔,书中时代烙印甚明,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甚深,且一反历来“扬杜抑李”的主流议论,因而在“文革”后受到诸多指责,甚至有人目为“溜须拍马”“逢迎领导”之作。其实,郭沫若对李杜评价是经过长期思考的。千余年来,一直存在着扬李抑杜派、扬杜抑李派、李杜平衡派的争论,郭老从年轻时起就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是个扬李抑杜派。不过,他在纪念世界名人的正式场合,倒是用理智说话,而不是诉诸情感,称颂为“双子星座”,采取了李杜平衡的提法。按照郭老一贯的务去陈言的创新思维,他要写一本扬李抑杜的翻案书,也是情之使然,理之所至,因为他早就看惯历史上“千家注杜、众口扬杜,一家注李、偏轻于李”的主流见解。郭老以异于主流派的见解,企图对历史上论李杜优劣的有关问题作一个总结性的研究,改变“千家注杜,太求甚解,一家注李,不求甚解”的局面,以此实现李杜学的创新,这似无可厚非。郭老以八十高龄,处于身心交瘁之际,尚把仅余的精力贡献于学术争鸣、学术创新,这是多么值得尊重和令人感慨的事。书中思路清晰,新见迭出,颇具功力。虽有某些硬伤和诸多缺陷,郭老“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创新精神仍闪烁其间,在学术史和文人心态史上自有其重要价值。书中借对李杜政治思想评论,曲折地透露自身心态,深刻地进行灵魂解剖,批评杜甫“每饭不忘君”和李白“日忆光明宫”的忠君思想,已经有学者提出是他生命暮年沉重的精神涅槃,是乱世浊流中的文化抗争。这种看法是颇有道理的。至于该书在“文革”潮流的影响下采用了偏狭的“阶级论”,这正是我们今日对它最不满意之处,但也是我们今日应该原谅它之处。
总起来看,建国后郭老在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倡导了多次重要的学术争鸣。这些活动为培育“养新”学术的活跃环境,为推动学术成果的创新起了良好的作用。郭老亲自倡导,又亲自实践,使他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争鸣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
三、学术争鸣与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
上面我们分析了郭老在建国后坚持学术争鸣和学术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成功的经验,这是我们开篇揭橥的郭老主张的第一种精神和视角。那么,若从他所强调的第二种精神来观察,即从培育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争鸣氛围,建设“养新”的学术环境而论,则郭老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和教训。总的看来,建国后郭老仍努力于就此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但不能不看到较之建国前,有所退步,有所退缩,个中原委很值得深思。
首先,看一看时代主题的转换和马克思主义地位的变化对学术争鸣的影响。
建国以前,郭沫若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家现身于新文化阵营,投身于敌、我、友诸种文化势力纷繁复杂的斗争、论争和竞争中。那个时代的主题是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学术争鸣直接或间接地是围绕这个主题和任务进行的。所以,在学术研究的内涵和思维定势上,主要聚焦于敌我营垒的胜负兴衰,目标集中在同反动势力及其文化作斗争上,当时从社会史大论战到围绕两个中国之命运和甲申三百年祭等几次大的学术论争,都带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性质,目标指向比较单一化,斗争方式比较简单化。其实,在先进文化和反动文化之间,有很大一块中间地带。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特殊国情下,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处于中间状态,是学术文化界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导下,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了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但在中国革命面临决战的紧要关头,当党组织在香港动员进步文化人士批判“第三条道路”之时,郭沫若也曾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把虽对人民革命怀有疑虑,但始终未曾与人民为敌的沈从文,指责为“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桃红色”作家,朱光潜、肖乾也被点名批判。这件事,暴露出郭沫若当时尽管出发点无可非议,但的确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带有“左”的简单化倾向。
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处境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跃居于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从旧社会里备受压制、被斥为异端的一家,变成处于统治地位、占居主流的一家。时代的主题词也发生着根本性质的变化,在解决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之后,重心理应逐步由“革命”转到“建设”上来。在建设环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如何面对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和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循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多元文化共同发展,这是与建国前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新鲜课题。建国后1956年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力图实现这个转换,突破前苏联独尊惟一、压制多元文化的日丹诺夫模式的一个创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疑是建设时期适应多元文化和谐共振、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但要坚持以“双百”方针来繁荣学术文化,则需要有对社会阶级状况特别是知识分子状况的正确分析,有健全的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为言论自由和学术争鸣提供切实的保证,还需要领导人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宽广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可惜的是,党在这些方面相继出现严重失误,“八大”路线被改变,时代主题词未能及时向建设为中心转换,革命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思维定势烙印太深,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术文化方向发生逆转,“双百”方针在浅表层面上成为点缀,百家被简单归结为“不是资产阶级一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争鸣,实际上是一家独鸣,一家独尊,重蹈罢黜百家,独尊惟一的历史覆辙,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21]在这种情况下,并未真正掌握话语权力的郭沫若,又怎能避免跟着党的失误而犯错误呢!
应当肯定的是,郭沫若作为我国学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始终笃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科学文化繁荣之道。在反胡风、反右派中和其后“左”倾错误日趋严重的岁月里,郭老始终不渝地呼吁贯彻“双百”方针,尽管他也服从政治讲了政治需要的话,但他内心却热切盼望和天真期望“百家争鸣、群花怒放”的局面“保持于永远”。就在“大跃进”的岁月里,他创作了101种花卉争放斗艳的新诗,各地群众还给诗人寄来了供他参考的各样花种和画稿。“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新,看罢牡丹看秋菊,四时佳气永如春”,这首诗道出了他的心声。他本人乐于争鸣,习惯于争鸣的游戏规则,注意以平等和民主的态度倡导和发起了建国后数次大范围的学术争鸣,推动了新中国学术向前发展。
在“文革”前十年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过程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同错误的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反复多次,历史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比如在思想文化领域,既曾提出和贯彻“双百”方针,在科学文化的若干领域开出了绚丽花朵,取得了明显成就;又不断用政治运动加剧“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使非主流文化也日益受到压抑、遭致弱化,主流文化也出现越来越封闭、现代化转换越来越困难的态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党员领导干部、行政官员和学者身份集于一身的郭老不得不陷于两难的境地,往往随着时势和上面调门的变化,依违于两可之间。既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得拥护铲除诸家“毒草”,独放一家“香花”,还要勉强自己相信一家独尊也能大放“香花”。这也可说是承袭了中国传统士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条件下的矛盾困惑心态。再加上对领袖毛泽东拥戴追随,视为“天纵之圣”,近乎盲从:“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22]郭老虽在两可之间依违,某些言行不利于百家争鸣,但他本质上是文人、学者,他的心同广大知识分子是相通的,他从未出谋、出手来整知识分子。尹达曾经讲过这个情况,郭老在学术论战中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有时出语激烈,文字尖刻,在解放前他是在野的身份,解放后身份变了,但是他论战的风格没有变,这就会给一些人造成压力,伤了感情,但郭老并未觉察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短处,也是一个可贵之处,他在自我意识中永远把自己看作学术界的普通一员,以致产生了他预料不到的一些矛盾和后果。这段话是讲得很实在,令人信服的。[23]
其次,看一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关系,以及处理好这一关系对学术争鸣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无疑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提倡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发展并不矛盾,搞得好是相辅相成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学说体系,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偏狭、封闭的东西。江泽民同志在乔治·布什图书馆有段内涵深刻的讲话,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从未来的世界趋势看,学术文化发展必定是多元竞争、和谐共振、互补互融的趋势。从我国当前的文化类型看,有主流文化,有非主流文化,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主流文化为主体,但不应也不可能封闭非主流文化,“不必兢兢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斥人以异”。[1](P27)历史早已证明,罢黜百家,独尊惟一,将会导致学术文化的枯萎。要以开放的心态欢迎百家的竞争,于最广泛的民族文化认同中,殊途百川同归于海。就文化的性质看,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以上这些不同类型文化的发展态势在建国后郭老在世时已经出现,我们的文化政策也一度作过有益的调整。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时代以前,这种调整一直未能进入到正常轨道,常是摇摆不定,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左”,“文革”期间就发展到了极致,体现非主流文化的各种学术固然受到攻击和排斥,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主流文化也受到压制和打击,先进文化被封杀、被摧残。假“无产阶级”之名一“花”独放的反而是反文化和伪学术。从这个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应当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认真思考如何对待主流文化与非主流的多元文化的关系,如何建立切实保障“百家争鸣”的体制和机制,如何制订和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真理、尊重创造的方针政策,如何以主流文化为主体,吸纳中外健康文化,创造和发展中国风格、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在这方面,对照郭沫若在学术争鸣问题上的得失,倒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面宝贵镜子。
郭沫若本来对此有相当超前、相当深刻的体认。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认识到必须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广收博采世界先进文化,各种文化况相发展、求同存异,逐步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创造和发展当今时代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郭老以中国文化为根底,广泛摄取域外文化,因而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吐纳中外、熔铸古今的学术成就。他在文化问题上的许多精辟的论述,至今是我们文化建设的宝贵理论财富。在建国后,特别是“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的特定环境下,郭沫若对于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关系的认识,他的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主张,显然较建国前有所退缩,文化开放的恢宏气势有所减弱,这也影响了他未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尽管有这些弱点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建国后郭老倡导学术争鸣,致力学术创新的多方面成就,是不能否定的。
收稿日期:2002-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