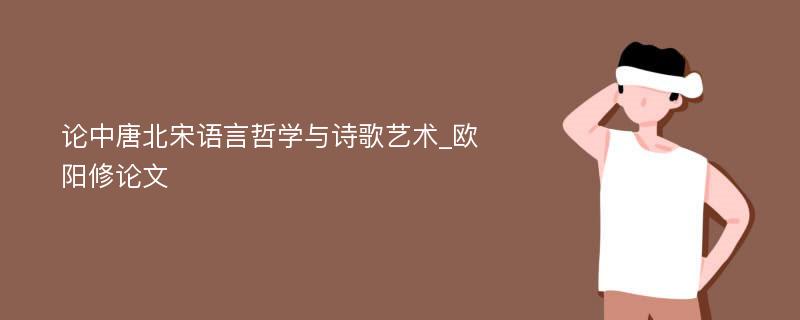
言尽意论:中唐——北宋的语言哲学与诗歌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诗歌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上,把中唐到北宋的文学看成一个时期的说法愈来愈受重视①。这种“中唐—北宋”说揭示了此时期的文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不因朝代的变迁而把它们硬性分开,对现行的文学史分期标准确有很大的修正作用。就诗歌而言,中唐到北宋最显著、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唐诗之变与宋诗之兴,其实质是诗歌语言的转型。从结果与风格看,此诗歌历程不妨称作“宋诗运动”。这场运动滥觞于杜甫,崛起于韩愈、孟郊、贾岛、李贺诸人,大盛于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家,正如葛兆光所分析,这就形成“一种诗歌语言革新潮流”,“表现”型的唐诗遂转型为“表达”型的宋诗②。
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尤其是语言艺术的精华,而诗人的语言观则决定着诗歌的语言——结构形式,语言转型的背后必定隐藏着诗人语言观的变化。相对而言,中唐以前的语言哲学主流是“言不尽意”,对语言的表达功能持怀疑态度,因而采取“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诗歌以意象的密集化和语序的省略错综为主要特征,重在表现感受;中唐—北宋的语言哲学主流是“言尽意论”,对语言的表达功能持乐观态度,相信语言能够而且应该准确详尽地传达世界的真相和主体的意志情感,并把它树为创作的最高目标,因而多用“以文为诗”的方法,写作重在与人交流沟通,诗歌尚意尚理,注重文字工夫。本文拟具体论述中唐—北宋“言尽意论”的语言哲学及其与诗歌艺术的关系,以便从此关系中探讨中外汉学界提出的“中唐—北宋转型”说③。
一 韩愈:语言“为用且博”,“不违于道”
从六朝到盛唐,诗人们大都遵循“立象以尽意”的创作原则,通过呈现各种物象来表现世界与自我,不在乎情感与意义的完整清晰,只在乎感受与印象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④。很显然,立象尽意的背后是对语言的怀疑,也不排除诗人在语言表现力方面的欠缺。更有甚者,是一味求象而忽略情感与意义。
处于盛中唐之交的杜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力图加以改变。作为承前启后的伟大诗人,杜甫沾溉后人甚多,其中就包括他的诗学语言观。他相信言能尽意,《敬赠郑谏议十韵》主张语言能够“毫发无遗憾”地表现意思,《戏为六绝句》其一赞扬庾信“凌云健笔意纵横”,其四批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意味着他对语言的信任,对具有强大表现力的、能够详尽地传情达意的诗歌语言的渴望和尝试。
杜诗在当时影响不大,到中唐始被人推崇,其中以韩愈学杜最为突出。安史之乱后,社会危机四伏,诗歌也走入歧途,意象往往限于风花雪月,不及社会人生;语言陈旧卑弱,表现力不强。试图化解时代危机的韩愈也力图把诗歌引上新的发展道路。元和诗坛常被后世视为中国诗歌的一大转折,富有象征意味的是,集中体现韩愈诗论的《荐士》诗即作于元和元年(806年)。韩愈在诗里有意识地论述了从《诗经》到唐朝的诗歌发展史,他批评六朝诗歌“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借推介孟郊的诗表达了自己的诗学主张。这段话常见征引,用以说明韩孟诗派的语言风格。这当然是对的,但换一个角度考虑,这段话也反映了韩愈对言、意、物三者关系的看法。“冥观洞古今”是指作者的意,“象外逐幽好”指诗歌要表现的物,实质也包括在作者的意里,“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即指诗歌语言详尽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横空”,一作“纵横”,合下句观之,则近似杜甫“凌云健笔意纵横”的追求。由此看来,韩愈是主张言能尽意的。许顗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两句云:“盖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指出了韩愈言与意合的主张。李光地说此诗未提及陶渊明,“与论文不列董、贾者同病,犹未免于以辞为主尔”,虽意在批评,却也道出了韩愈着力提高语言表现力的诗学追求⑤。
韩愈的古文理论也包含了言能尽意的思想,《答刘正夫书》认为文章“无难易,惟其是尔”⑥。“是”义为正确、合理,恰到好处,亦即达意精确。然则语言应当而且可能精确地传达意志情感,关键在于主体驾驭语言的能力。
此种认识根源于韩愈的语言观。在《择言解》里,他高度评价了语言的作用:“言起于微,而为用且博,能不违于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训,以推于生物”。认为言通于道,语言能明道传意,把语言看作传情达意、化今传后的工具。语言既可用于传道化民,也就可以详尽达意。由于语言的作用极其重要,因此需要慎重选择用语,否则,“及其纵而不慎,反为祸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推而论之,言不能尽意,并非语言天生的不足,而是说话者择语不慎、用语不精,因此,不应怀疑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而应加强自身修养,着力提高语言的表现力。韩愈尤其重视文学语言,《送孟东野序》称“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文学语言作为精华中的精华,更需要创作主体的锻炼琢磨。
韩愈言尽意的看法还散见于其他各处。《上襄阳于相公书》称赞对方:
故其文章言语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
认为言语和它表现的“事”之间存在同一性,强调用语的准确、得当和表现力。《送权秀才序》说“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写物”,明确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着一“穷”字而完全推翻了言不尽意论。类似的看法在《进学解》、《答尉迟生书》、《贞曜先生墓志铭》、《答孟郊》等诗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韩愈念念不忘的,一是相信语言能够表达思维,描述自然,二是动用理性的力量来锻造语言,推崇强劲的语言表现力,务求逼真吻合,“惟其是尔”,这是他毕生的追求⑦。到北宋中叶,韩愈的追随者在语言哲学领域高举的也是这两面大旗。更重要的是,正如季镇淮所指出的,在诗的创作实践上,韩愈“似乎特别重视语言的创造”⑧。《荐士》诗赞扬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赠崔立之评事》批评对方“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钟情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的语言,不满轻率未工的言词,赞成与反对所依据的评判标准都是语言,诗歌的创新最终落实到语言而不是意象,此视角后来成为北宋大诗人的共同视域,而这也正是“宋调”的艺术本质。
从作品看,韩愈实践了他的理论,至少在晚唐、北宋人看来是如此。司空图论诗虽与韩愈异趣,却能欣赏异量之美的韩诗,《题柳柳州集后》说韩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读之“不得不鼓舞而狥其呼吸也”⑨,点出了韩诗语言强劲的表现力。后来欧阳修等人也一致赞赏这一点,并重点指出韩诗意与言合的特点。
二 北宋的语言乐观主义
至北宋,梅尧臣比韩愈更进一步。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语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不尽之意可以从言外获得,其途径在“造语”,亦即言能尽意,只不过有言里言外之别,其座基仍在对语言表意潜能的乐观主义。至于“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则与韩愈《答孟郊》所谓“文字觑天巧”的精神相一致,都是相信语言刻画自然百态之功。因为相信言能尽意,所以需要在两方面用功,一是提炼诗意,追求“意新”;二是锤炼语言,追求“语工”。梅尧臣把诗歌的发展归结为意度与语言,而又特别强调“造语”在状物和写意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质上是把诗歌创作和发展最终归结到语言上。活动于仁宗至神宗朝的桂林僧景淳在《诗评》里宣布:
诗之言为意之壳,如人间果实,厥状未坏者,外壳而内肉也。如铅中金、石中玉、水中盐、色中胶,皆不可见,意在其中⑩。
明确把诗歌语言当作诗人意念的外壳,肯定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同一性,这比梅尧臣的认识更加直接、明晰和彻底。下面还将谈到,苏轼也隐约有这种观点。现代西方的某些“新理论”与这种认识如出一辙。贝特森曾说:
我的论点是,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11)。
俄国形式主义在批判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着眼于文学外因素而无异于隔靴搔痒之后,明确提出“诗句是一种具有语言学性质(句法的、词汇的和语义的性质)的话语特殊形式”,诗歌“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进而认为诗歌的本质就在于以语言为内核的“文学性”,对诗歌的研究必须聚焦在具体的语言结构上(12)。梅尧臣“造语”理论、僧景淳言意合一论的提出远在他们之前。
依照“语工”的标准,语意多歧就成了嘲笑的对象。《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曰:
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
这些诗病之所以可笑,是因为语言缺乏精确性、个体性和差异性,而这三者正是文学语言的生命所在。要避免浅俗可笑,就必须做到“语工”,即表达的精确高妙。
文学家梅尧臣“意新语工”的好诗标准得到了哲学家的认同。邵雍从言、意关系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作为儒家诗学纲领的“诗言志”说:
何故谓之诗?诗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不止炼其辞,抑亦炼其意。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13)。
既然诗的本质是言志,那么“言”就应该、而且理所当然地能够道出“心中事”。显然,在邵雍看来,“言尽意”是“诗言志”命题的应有之义,诗人对此不应有异议,而只需要锤炼命意与言辞,也即梅尧臣所谓达到“意新语工”。
欧阳修诗学韩愈,诗学语言观也上承韩愈,而且有更大的发展。其《六一诗话》云: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乃天下之至工也。
在标举诗学典范韩愈的“笔力”的同时,欧阳修也表达了自己对诗歌语言的看法:诗歌可以描写任何事物,诗歌语言任什么内容都能表达得好,关键在于诗人是不是“雄文大手”,即是否具备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无施不可”(14)、“曲尽其妙”涉及了言、意、物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对诗歌语言达意写物的乐观态度,其实就是韩愈语言理论的集中概括。只不过,韩愈未在语言方面对诗歌作过专门的具体论述,而隐约以宋之韩愈自居的欧阳修则进一步发展了榜样的言论,集中而鲜明地提出了新的诗歌语言主张。
与韩愈一样,欧阳修的诗歌语言主张也根源于他的语言本体观。在这方面,他比韩愈走得更远,直接反驳了儒家“言不尽意”论: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15)。
长期以来被奉为神圣宝典的儒家话语竟被欧阳修斥为“非深明之论”,北宋中叶的疑古、疑经思潮于此可见一斑。不必怀疑语言的达意功能,也不必采取“立象以尽意”的老套手段,“意”中自有“理”在,人的理性语言足以尽“理”,从而也就详尽地表达了“意”。
道学家程颐的“远近皆尽”说也包含着言尽意论:
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语虽有浅近处,即却无包含不尽处。……他人之语,语近则遗远,语远则不知近。惟圣人之言,则远近皆尽。
须是养乎中,自然言语顺理。令人熟底事,说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说得蹇涩。须是涵养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语,不妄发,此却可著力(16)。
凡人之语不能尽意;圣人之言无所不尽。与对象疏离隔膜,其表达当然说不上清楚;倘若内心真正把握了对象的底蕴,表达起来便详尽分明。由此看来,不是语言本身不能尽意,而是立言者是否达到了足够的表达水平,这与欧阳修对“雄文大手”的肯定是相通的。
综上所述,梅尧臣“意新语工”的标准实可概括韩愈以及仁宗天圣(1023——1032年)以后学韩派的共同追求(17)。“意新”指的是诗人与世界、诗人与传统的关系,乃就构思而言;“语工”指的是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乃就表达而言。试作简略说明。
韩愈写诗作文,不仅追求“词必己出”,也尽力做到意必己出。清顾嗣立《寒厅诗话》说:“韩昌黎诗,句句有来历,而能务去陈言者,全在于反用。……此等不可枚举。学诗者解得此秘,则臭腐化为神奇矣。”反用古人成语就是自出己意。此外,针对前人的某些说法,韩愈常常有意翻案出新,如许多批评家都指出他的《感春四首》之二和《秋怀诗十一首》之二独具翻案出新之妙(18)。伤春是传统一贯的主题,韩愈《感春五首》之一却“写出闲景兴”,“写得极乐”(19),一改旧诗意,也开了宋人“悲哀的扬弃”的先声(20)。阎琦把韩诗在语言上的创造分为巧喻、反用、去熟和用狠猛语、粗俗语四方面(21),其实前三项也是韩愈自出新意的方式。
韩愈力求新意的诗法至北宋中叶达于极盛,嘉祐四年(1059)以王昭君为题材原型的同题唱和诗就是一场“意新”大竞技。先是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新意迭出,引起学韩诸人的极大兴趣,欧阳修、曾巩、司马光、刘敞、梅尧臣等人纷纷赓和,率皆以议论为诗,于前人未到处各出己意(22),欧阳修甚至自认为平生最得意之作(23)。诗意翻新意识贯穿于宋人各类题材的作品,在咏史、咏物、题画、讽谕、抒怀等各类诗中,都能找到大量的翻案实例(24)。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先后都提出过诗歌应“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主张(25),自出新意当然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而诗歌题材也就相应地得到扩大。
在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韩欧诸人都相信并且要求诗歌能刻画出造化的真相,追求一种表现力度,他们用的是“镌劖”或类似的词语。韩愈《答孟郊》诗说“文字觑天巧”,是相信语言摹写自然的能力。《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夸赞对方的诗歌则云:“《望秋》一章已惊绝,犹言低抑避谤谗。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镌”义为凿、雕刻,“劖割”义为刺、雕刻,“镌劖”乃“加倍写法”(26),极言语言刻画对象的详尽力度。欧阳修和王安石在许多场合使用“劖刻”、“雕锼”等同义词,意思都指向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能详尽地、丝毫不差地刻画出造化的真相(27)。从同义词的递相沿用,可以窥见诗歌语言观从中唐到北宋的继承与发展。
从韩愈到梅尧臣、欧阳修,他们的语言哲学都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现对象,这在天圣前后学韩派诗歌里有显著体现。上引材料说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歌都被欧阳修赞为能写出造化的真相,其语言刻画对象的力度尤为欧阳激赏。据宋人记载,梅尧臣“欲极赋象之工,作《挑灯杖子》诗尚数十首”(28),可见他在这方面的操练。宋人谓梅尧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语“真名言也”,并具体称赞他的某些诗句为“状难写之景也”,某些句子为“含不尽之意也”(29)。清叶燮《原诗》卷四评论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歌说:“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从语言与思维的角度道出了二人的尽意特点。欧阳修的作品也意度尽出,其《明妃曲》“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两句被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视为“言意所会”的代表,叶氏同样称许王安石晚年诗“意与言会,言随意遣”。“宋调”起于韩愈,成于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诸人,盛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家,其间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就是语言哲学上的言尽意论。因为要用语言尽意,诗歌语言便趋向于明晰精确。本文开头所引葛兆光的论述,把唐诗(近体诗)称为表现感受与印象、埋没意绪的“表现”型诗歌,把宋诗称为表达情感与意义、语序完整、意脉清晰的“表达”型诗歌,无疑极有见地。
欧阳修在晚年把“斯文”托付给苏轼,后者在多方面继承、发展了座主的文化业绩和见解,其中包括言尽意论。苏轼对语言基本上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明确表示聪之诗可以作为聪“得道浅深之候”,认为语言能够呈现出说话者的某种情状,或得道的程度,把语言当作意度的征候。《题僧语录后》也持这种语言本体观:“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观其临祸福死生之际,不容伪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真伪之候,见于语言”。
这种语言的乐观主义态度很容易导致对早期儒家怀疑主义语言观的不满。欧阳修驳斥了《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经典话语,苏轼则对孔子“辞达而已矣”的标准作出新的阐释: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所谓“了然于口与手”,讨论的是言与意的关系,是相信言辞完全能表达主观意念,即“辞达”。对绘画语言,苏轼亦作如是观,《仪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强调“心手相应”,也即此处所谓“了然于口与手”。做到“辞达”并不容易。在言、意、物三者关系中,首先要求对物“了然于心”,即主观意念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达到这一步已经很难,故苏轼有“千万人而不一遇也”的慨叹,更何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但惟其困难,正见出诗人用语之工巧。在苏轼看来,陶渊明就是这样的诗人。在《书诸集改字》中,他评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认为“见”字可喜,而诸本作“望”便神气索然。可见问题不在语言能否尽意,语言本能尽意,关键看作者能不能找到传情达意的最佳话语——而这正是欧阳修的看法:“雄文大手”方能“无施不可”、“曲尽其妙”。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陶渊明的自适心态与用字联系起来,与梅尧臣把诗歌落实到语言是一致的,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诗歌的根本问题是语言问题。苏轼《评诗人写物》又指出:“诗人有写物之功。”强调用语言准确地表现客观事物,实质也是“曲尽其妙”。
三 中唐—北宋禅宗的“语言学转向”
与韩愈、欧阳修、苏轼诸人在儒学和文学领域反转传统语言观的思潮相呼应,中唐到北宋的禅宗对语言的表意功能也乐观起来。本来,禅宗不相信语言能把握存在、传承大道,甚至要求取消语言,对语言持虚无主义的态度(30)。但是,葛兆光对9至10世纪禅思想史的研究表明,这个时期佛教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从思想深层看,是语言从承载意义的符号变成意义,从传递真理的工具变成真理本身,大乘佛教关于真理并不是在语言中的传统思路,在这时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似乎真理恰恰就在语言之内”(31)。周裕锴师对禅宗语言史的考察也表明,受同时代儒家言意观的影响,宋代禅宗也走向了语言之途,认为语言是心的显现,把语言作为得道浅深的征候,相信言能传道。于是,“无字禅”变成了“文字禅”,禅宗从“不立文字”变成了“不离文字”。其中“文字禅”的公开倡导者、主张禅教合一的惠洪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语言观,他坚信语言文字本身完全能传达义理,甚至书面文字对理解义理也构不成任何障碍(32)。
尤可注意者,与苏轼并称的黄庭坚也相信语言的表意功能,不同的是,苏轼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阐发儒家的命题;黄庭坚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质疑禅宗的教规。作为古代禅师言行的文字记录,禅宗语录曾颇受非议,被认为无助于传道。针对这种非议,黄庭坚辩护说:
佛以无文之印,密付摩诃迦叶,二十八传而至中夏,初无文字言说可传可说。真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符证印空同文。于其契合,虽达摩面壁九年,实为二祖铸印。若其根契不尔,虽亲见德生,棒似雨点,付与临济,天下雷行,此印陆沉,终不传也。今其徒所传文字典要,号为一四天下品,尽世间竹帛不能载也。盖亦如虫蚀木,宾主相当,偶成文尔。若以为不然者,今有具世间智、得文字通者,自可闭户无师,读书十年,刻菩提印而自佩之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33)
若是钝根人,即使亲自见到高僧大德,也无法获传菩提心印;若是利根人,即使无师传授,也可以通过闭门阅读语录而自证心印,因为透过语言能够捕捉到说话者的意念。换言之,语录中的语言已经完全传达了前代大师的“意”,至于读书者能否悟道,就看接受者的素质——所谓“根契”——如何。庄子认为后人通过书本所读到只是“古人之糟粕”(34),早期禅师告诫学者“莫向文字中求心”(35),黄庭坚则认为通过读书能达到与古人契会心印的效果。两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就在于庄子和早期禅宗都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强调“道”的不可言说性,消极看待语言;而黄庭坚则对语言持积极看法,相信“道”可言说,言能尽意。黄庭坚是北宋后期站在诗学、理学和禅学交接处的重要人物(36),他对语言的乐观主义态度标志着中唐到北宋的儒学、禅学和诗学领域在言能尽意的语言观上达成了共识。
四 言尽意论与诗歌语言大变局
于是,在对待语言表意功能的问题上,传统儒家、道家的怀疑主义态度和禅宗的虚无主义态度基本被宋人的乐观主义态度所替代。于是,在诗学领域,随处可见对言能尽意的赞叹和满足。前引欧阳修对韩诗“曲尽其妙”的夸奖和叶梦得对欧阳修、王安石诗“意与言会”的评价就是显例。此时期的批评家相信语言完全可以与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念相契合,而此时期的诗人的作品也被认为达到了意与言的同一。有了这种自信,诗人似乎真的可以做到任什么内容都能表现得好。宋代诗论里经常可见对诗歌语言“曲尽形容之妙”的赞语,古人“言不尽意”的苦恼和遗憾被宋人“曲尽其妙,毫发无遗恨”的满足所取代(37)。由此出发,造语下字的精确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得到强调,多歧义的语言则被视为诗病,前引梅尧臣批评“语涉浅俗而可笑者”即是一例。又如:
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常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日:“此无乃是登溷之诗乎!”(38)
本意是写爱静堂而每日必到,结果却被人故意理解成每日如厕。并不是语言不能准确达意,而是表达者造语不工,没有描述出独特的“这一个”。因此,诗人需要锤炼精确高妙的语言,“觅句置论句法”,“要以溜亮明白为难事”(39)。
基于对语言的信任,宋人在言、意、物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据周裕锴师研究,大约可总结出两点:一是要求“意与言会”,强调主体意念的准确传达;二是要求“写物之功”,强调客体形神的准确刻画(40)。韩愈是这种理论的鼻祖,他们共同的语言观是言尽意论。一方面要求语言与意度契合无间,另一方面要求造语下字务求工巧妥帖。
无论是韩愈追求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还是欧阳修称许的“无施不可”、“曲尽其妙”,无论是梅尧臣的“造语”,还是苏轼的“辞达”,着眼点都在语言,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诗歌的根本问题是语言问题。由此可见,中唐—北宋的诗歌革新实质上是语言本体观的反转,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语言取代意象被视为诗歌的第一要素,诗歌的优劣不在意象的优劣,而在语言的表现力,在于表达的“尽”否和“造语”的“工”否。于是,韩孟诗派和李贺翻空出奇,白居易及白体诗人浅切务尽,贾岛及晚唐体终日“苦吟”,李商隐及西昆体避熟就生,梅尧臣操练“意新语工”,欧阳修、王令、王安石实践鑱刻露骨,苏轼以文为诗,黄庭坚及江西诗派醉心“句法”:注重语言革新是他们的一致追求。宋代禅宗被人称为“文字禅”,而典型的宋诗也被人称为“以文字为诗”。作为对本朝诗学的总结,南宋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有句法、造语、下字、锻炼等专门探讨诗歌语言的部门,足可见出宋诗学创作理论的语言学倾向,宋代诗学一路行走的是语言之途,中唐—北宋的诗歌发展实质就是一次“语言学转向”的运动。
言尽意论对宋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相信言能尽意,“意”也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要“炼意’,要求“意新”,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由此形成了宋代诗学中的“尚意”观(41),也扩大了宋诗的题材(42)。宋人的尚意主要是“言志”,更多的是主体的理性认识,倾向于明晰而非朦胧(43),在此背景下要求“尽意”,遂不得不“以文为诗”精确地表达出来,就需要“语工”,选择准确工巧的用语,终于走向“以文字为诗”。
本文是上海财经大学新进博士课题《社会转型与诗歌变迁:中唐到北宋》(211—b—230正)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清代叶燮《百家唐诗序》指出,中唐的“中”是“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即谓中国诗歌的发展以中唐为最大转折点。见《己畦文集》卷8,《郋园先生全书》本。游国恩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里把中国古典文学史分成六个时期,第四期是中唐到北宋末,视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转变时期。见游国恩《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526—539页。游先生也许是文学史分期问题上“中唐—北宋”说的第一人,林继中则专为这段文学写了“宏观”的文学史,见其《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②葛兆光《汉字的魔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94—210页。
③关于“中唐—北宋转型”说,详见李贵《典范选择与中唐—北宋诗歌的因革》“绪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张泽咸在研究“唐宋变革论”时也认为,从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来看,“重大变革都发生在唐代中叶”,更有力的提法应该是“唐中叶变革说”,详见他的《“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此椐“象牙塔”网重新校对整理的版本。
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26页。
⑤此段以上所引均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5《荐士》诗及相关注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527—540页。本文所引韩诗均见此书。
⑥《韩昌黎文集校注·韩昌黎文集第三卷》,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07页。本文所引韩文均见此书。
⑦朱熹说韩愈“第一义是去学文字”,“韩退之及欧苏诸公议论,不过是主于文词”,虽意在批评,却启发我们注意中唐——北宋儒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的问题。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7,中华书局1986年版,3273、3276页。此外,据孙昌武的研究,韩愈在诗文里经常谈“辞”、“文词”、“文辞”,多指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其中“文辞”一语在其文章中出现20多次,多是讲文学语言创造,而且韩愈以善文辞而自负。见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140页。
⑧季镇淮《韩愈的诗论和诗作》,《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437—459页。
⑨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狥”通“徇”,顺从。
⑩此据张伯伟的考订,见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499—501页。
(11)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186页。
(12)参见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载托多洛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特别是第56、77页。
(13)邵雍《论诗吟》,《伊川击壤集》卷11,《四部丛刊》本。
(14)欧阳修屡用此语,如《再论水灾状》荐王安石“无施不可”,是指人的才能;《六一诗话》称杨亿“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则与论韩愈一样,都指笔力。
(15)欧阳修《试笔·系辞说》,《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本。
(16)张伯行编《二程语录》卷10、卷11,《正谊堂丛书》本。
(17)关于天圣前后的尊韩思潮和学韩诸人,参见顾永新《北宋前中叶的尊韩思潮》,《北大中文研究》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贵《典范选择与中唐—北宋诗歌的因革》,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60—69页。
(18)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545页。
(19)何焯、程学恂语,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728页。
(20)“悲哀的扬弃”是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里对宋诗人生观的概括,见其《宋元明诗概说》,李庆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2—25页。
(21)阎琦《韩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2—79页。
(22)参见周裕锴师《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197—198页;张高评《唐宋昭君诗的文献学意义——以昭君和亲的反思为例》,《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年版。
(23)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424页。
(24)详见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36—115页。
(25)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6引《后山诗话》载梅尧臣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176页;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67,中华书局1986年版,2109页(本文所引苏轼文均见此书);黄庭坚《再次韵并引》,《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12,中华书局2003年版,441页。
(26)程学恂语,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812页。
(27)参见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214—222页。诗学韩愈的王令亦持此论,其《读老杜诗集》赞扬杜诗:“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见《王令集》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镌镵”乃综合韩愈的“镌割”、欧阳修的“镵刻”而成,意义相同。
(2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8,中华书局1983年版,145页。
(29)张磁《诗学规范》,《宋诗话辑佚》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623页。
(30)参见周裕锴师《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4—19页。
(31)葛兆光《语言与意义——九至十世纪禅思想史的一个侧面》,《新国学》第1卷,巴蜀书社1999年版。
(32)周裕锴师《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42—177页。关于北宋儒家言意观的转变及其对禅宗语言观的影响,参见周裕锴师《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9—25页。关于惠洪的语言观,参见李贵《论惠洪的人格心理与诗歌艺术》,四川大学硕士论文,1998年,19—21页。
(33)黄庭坚《福州西禅暹老语录序》,《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6,《四部丛刊》本。
(34)《庄子·天道》篇,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357—358页。
(35)《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慧然集,《大正藏》第47卷。
(36)关于黄庭坚在禅学、理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和他作为连接诗学、禅学、理学三大领域的代表人物,参见周裕锴师《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87—95页;黄宝华《黄庭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44—239页;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86页。
(37)参见俞成《萤雪丛说》卷1,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儒学警悟》本;范温《潜溪诗眼》,《宋诗话辑佚》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328页。
(38)魏泰《东轩笔录》卷15,中华书局1983年版,170页。
(39)吴坰《五总志》,《四库全书》本。
(40)周裕锴师《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410—412页。
(41)关于宋代诗学的尚意,参见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32—161页;谢佩芳《北宋诗学中“写意”课题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8年版。
(42)关于宋诗题材的扩展,参见王水照师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52—53、383—399页。
(43)详见周裕锴师《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410—412页。
标签:欧阳修论文; 宋朝论文; 梅尧臣论文; 黄庭坚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语言哲学论文; 韩愈论文; 诗歌论文; 禅宗思想论文; 苏轼论文; 六一诗话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