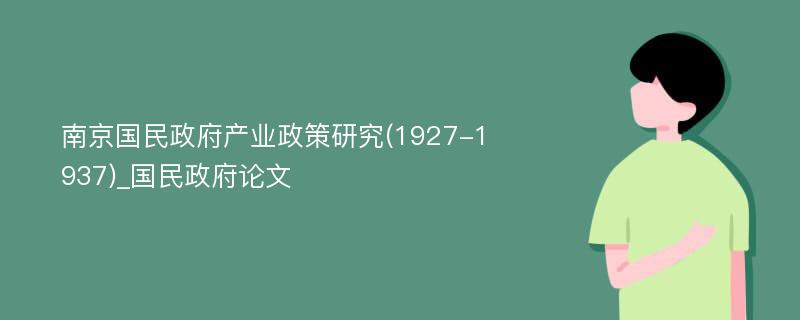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1927-1937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政策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0)01-0130-(07)
孙中山先生致力中国革命四十余年,曾经为国家经济现代化设计了宏伟的蓝图。其中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工业建设的主张,对中国国民党工业政策的方针和纲领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坚持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基于自己的政治目标,在工业政策中一方面参照孙中山的原则,试图实践;另一方面出于安内攘外国策的需要,采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将工业建设重点转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养民为目的”,对于手工业的维护与重工业基础的树立以及轻工业的鼓励同时并进的主张。
回顾孙中山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主张,研究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对认识3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和工业建设的艰难曲折道路是十分有益的。
一
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对于中国工业建设很早就加以注意,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制造机械、发展近代工业、修建铁路、发展交通运输以及改革教育制度等主张。五四时期,他在《实业计划》中更加明确地制定了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实现中国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的蓝图。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其中对中国工业建设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意见。综观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业建设问题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建设的原则
关于工业建设的原则,孙中山指出:“于详议国家计划之先,有四原则必为注意:(1)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2)必应国民之最需要。(3)必期抵抗之最少。(4)必择地位之适宜。”[1](P218)既体现了孙中山“造福于民”的爱国思想,更表现出政治家的务实精神。
(二)发展中国工业的计划
孙中山把发展中国工业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关键及根本工业”,是指交通运输及采矿、冶炼、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一类为“工业本部”,是指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及文化生活需要的工业。孙中山根据欧美工业革命后的现状,主张优先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他认为“当关键及根本工业既发达,其他多种工业,自然能全国的甚短期内同时发生。……人民有多工事可分,而工资及生活程度皆增高,工资既增多,生活必需品之价格亦增”,这就会带动“工业本部”相应地发展起来,“使多数人民既得到较高工资,又得许多生活必需品安适品而减少其生活费也。”[1](P347)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规划“关键及根本工业”中主张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首位。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没有交通事业的发展,其他工业建设“亦无由发展也。”[2](P168)其次,孙中山主张将矿业发展列入“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发展重点,在矿业中,他主张重点发展钢铁业。强调除了发展直隶、山西、湖北、辽宁的铁厂外,还要在广东、四川、云南及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新建钢铁厂。
孙中山对关系到人民衣食住行和文化需要的“工业本部”,主张在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同时,积极扶助和发展。他将“工业本部”具体规划为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五个部分,其中对关系到民生的粮食工业规划得尤为细致。针对国情,孙中山为粮食工业先后拟定了以下几项措施:首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3](P399)其次,测量农地,再次,研究增加农业生产的办法;最后,注重分配问题。[1](PP349-352)孙中山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平均分配粮食的具体办法,但他已洞察到只有粮食生产很充足,粮食分配很平均,“吃饭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此外对于传统手工业,孙中山认为还应予以维护。
总之,孙中山关于发展工业的计划,一方面在力求工业本部的发达,同时对于手工业的维护与重工业基础的树立及轻工业的鼓励同时并进。他的这些超前思维,给后人以弥足珍贵的启迪,成为中国国民党制定工业政策的重要渊源。
二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对孙中山关于工业建设主张非常重视。1926年10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发表了宣言,通过了《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具体拟定了北伐战争结束后,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工业政策实施计划,体现了中国国民党参照孙中山工业建设的原则,振兴民族工业的初步设想。
1927年4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为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有选择地参照孙中山关于工业建设的主张,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工业建设的指示和计划。
1928年2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吾党今后,必以强毅而坚忍之决心……,实现总理建国方略宏远之计划。”[4](P189)
1929年7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施政纲领中对工业建设作出了十三条规定,其中发展国营工业、提倡国货、调节劳资关系、改进劳工生活、救济失业工人、保护侨外工商等项,听起来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1930年3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最近建设方针决议案中对工业建设又进一步规定:
(一)煤铁油铜矿之未开发者,均归国家经营。政府得照总理所规定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在一定范围内,准外人投资或合资创办。其他特种矿之采取,应照总理所定准租与私人立约办理。
(二)中国之普通工业,在政府之提倡农业增加原料减轻原料之价格及政府施保护税则范围内,准其自由发展。
(三)中国之特种工业,在总理实业计划内所规定应新创设之厂,均由政府计划办理,并得借用外资及人员。
(四)政府应在两年内筹设(1)大规模之制铁炼钢工厂,(2)造船厂,(3)电机制造厂,得借外资兴办。
(五)党员应竭力扶助及提倡工业农业之发展,并协助政府禁止一切破坏工业之非法行为。[5](P50)
1931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工业建设程序案中,强调指出:“水利电气及钢铁酸碱煤糖煤油汽车等项基本工业,应由国民政府积极兴办,其余由私人投资兴办者,政府应奖励并予以切实保障。”[5](P52)
为实施国民党工业政策和计划,南京政府设立了工业行政机构——工商部,将工业纳入工商部管辖。1931年1月,工商农矿两部合并成立实业部,内设工业司,工业行政由工业司掌理。在此期间,陆续制定公布了一些奖励工业的法规,如《特种工业奖励法》、《奖励特种工业审查标准》、《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等。
毋容置疑,上述林林总总的计划和实施机构的设立对南京政府面临的“整个经济是传统式的、农业在其中占压倒一切的比重”,“手工业和现代式工业两者的产品相加的数额尚不及国内矿产物品总额的十分之一”[6](P343)的现状的改善不能说毫无积极意义,但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的距离却说明了:国民党拟定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标榜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护身符。南京国民政府的各类实施机构“都用提出一份相类似的、雄心勃勃的纲领来表明他们所作努力的正统性。然而“政府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可由它支配的用于工业发展的基金。”[7](PP99-100)1929年至1930年国民党内部先后爆发的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和规模最大的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导致国内“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南京国民政府致力的“改订新约运动”并未取得中国真正的关税自主,因此而增加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并且大多用在军事统一上。相反帝国主义利用与中国政府缔结的新的关税条约,加紧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加之政府的苛捐杂税,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南京政府国库支绌,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
三
中原大战以后,操纵国民党领导权的蒋介石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深感“欲解倒悬以出水火,舍建设无他术矣”。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为固本自卫计,国民政府更多地注意经济计划工作。1931年11月开始筹备全国经济委员会,1935年4月资源委员会应运而生。这些机构的建立对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计划的设计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制定了如下原则:“中国为逐渐实行总理实业计划,于在国际间平等互惠,不损害中国主权行政权之条件下,得充分利用外国之资本技术,以发展国内天然之富源,发展国民经济,增进国际福利。”“以上原则决定后,交国民政府详拟办法”。同时规定:“友邦或友邦经济团体,如能依照前项办法,对中国之经济建设,颇为善意之合作者,应由国民政府妥善协商,采取最有利之办法,以利进行。”[5](P53)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1932年11月,一个为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所辖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作为秘密“智囊团”组织在南京设立。它是蒋介石“用来防止现存机构对工业发展政策的方向和执行取得控制的手段”。国防设计委员会最初的班子里集中了近5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呼吁以统制经济去建立一个对日具有军事抵御能力的工业基础”。[7](P112)他们拟定的1932年至1935年间计划达到的基本目标是:“在华中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开发由国家经营的重工业和矿产业。这些将主要用于国防需要,并由经过训练的专家按照由第一步的全面计划朝着完全‘计划经济’方向去进行管理。”[7](P117)显然,孙中山的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国家资本的遗教受到重视。但是重工业的发展与原料开采决不是从新军阀混战中挣脱出来的国民政府所能承担得了的,必须寻求国际合作和援助。
为适应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需要,国民政府一方面将竭力向外拓展的德国作为国际合作的首选目标,一面拟定关于发展工业的措施。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工业建设的决议案规定的五项措施为:奖励生产、改良运输、开拓市场、召集全国工业生产会议、保护民营工业。[5](PP54-56)
上述计划和措施说明,国民政府出于“攘外”“安内”需要,自1932年起,中国工业政策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政府干预经济,寻求国际合作,着重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工业。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快全面侵华步伐。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全国资源委员会。1936年资源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计划中国防工业比重明显上升。
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的《促进救国大计案》中又规定:“一,立即举办以下之重工业与基本化学工业:钢、铁、机器、电料、电力、制酸。二,指导并监察全国轻工业之发展。三,扶助并促进乡村工业。”[5](PP71-72)不难发现,随着国内由内战转向和平,乡村工业开始列入国民政府“救国大计”。
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
首先,国民党为适应内战“剿匪”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将基础的、与军事相关的工业作为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发展的第一步,于是公路修建、交通运输、水利和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得到了政府扶持。例如:1932年全国公路总长度为44000英里,到1936年底公路总长已经增加到69000英里,其中新建的公路大部分在华中和西北。[9](PP500-501)据统计,1932年至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为修建公路共向15个省提供1200万元的贷款。[6](P358)
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铁路扩建受到南京政府高度重视,仅扩建铁路一项约付出1亿元。[6](P353)不可否认,粤汉铁路的完成、陇海铁路的向西延展,显然在日后抗战中起了积极作用。但1932年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为了应付内战,为调运军队及运输军需给养,占用了铁路运输的相当比例,加之修复扩充后的铁路因经营管理不当,使扩建的铁路未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
其次,国民政府在奖励扶植私营企业的同时,还自行经营多种不同的事业,表面上遵循了孙中山提倡的国家经营和民营的混合经济模式,但实质上公私企业之间的界限没有划分清楚。政府介入工业经济的手段,是利用对金融业的垄断介入了各种电力、采矿、治水及其他企业,如1935年币制改革以后,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利用中国银行的资产成立了数量众多的半官半私公司,进行多种活动,其中包括棉花贸易和汽车制造,到1937年,已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国内企业。[9](P151)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中,针对国家官僚资本严重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现状,严正指出:“振兴工业,凡一切与国利民福关系重大之事业,应以国营为原则……同时对一般工业,则力除与民争利之弊害,并与以积极扶助与保证。”[5](P64)表现出对政府官员的极端不满。
再者,由国家投资筹备的基本工业,除个别项目投产外,均因日本侵华的干扰,基本中断。如:1931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由退还英庚款数内拨付设备款310万元在上海真如开始筹建的“中央机器制造厂”,因卢沟桥事变被迫停止。选址浙江温州的“温溪造纸厂”,官股占390万元,1936年4月动工建筑,预计一年内完成,也因中日关系的变化被迫中辍。拟于1937年,由国民政府与四川、湖北、浙江、安徽、江西六省官商合办共同投资200万元的“中国植物油料厂”,未及启动,即因外患而停止进行。只有官商合办的“中国酒精厂”在选址上海浦东后,因资金、技术力量等筹备较为充分,于1934年底建成投产。
值得指出的,国民政府对孙中山强调的关系到民生的“工业本部”中“粮食工业”的政策实施是软弱无力的。正如外国学者易劳逸所指出的:“国民党人在南京政府的十年间,几乎没有为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做什么事。”“南京的领导人没有几个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因此农村的租佃关系一直没有改变,根本谈不上实行“耕者有其田”。易劳逸同时指出,国内的学者和农业专家们“的确在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却未能有效地用于农业。”[10](PP168-171)被国民政府列入比较急迫项目而得以实施投入的水利工程也是为了救急,因为1931年至1935年间长江、黄河多次洪水泛滥,水灾遍及全国十多个省,损失惨重,为了防洪,疏浚了长江、黄河等河道,部分堤坝得到了维修加固。
最后,我们不能否认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外国顾问与技术援助的利用。他们存在于政府军政各个部门。但军政事务专家多于民政事务专家。“民政方面洋员人数约共65名,包括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欧洲各国专家约35名和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的17名美国成员。在军事方面的总人数达175名以上,多数是些德国人。”[6](P375)这与国民政府寻求融资策略、加强国防工业和现代化军队建设需要的举措密切相关。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的“币制改革”得益于美国财政专家的指导,顺利实现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大批德国军事专家的聘用,适应了“攘外必先安内”决策的需要。在中德军事合作期间,德国军火输华为国民政府“安内”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仅1933年和1934年从德国购置军火所支付的国币高达1026.3万元,占进口总值的10.02%。[11]
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私营工业的发展虽没有完整的经济发展计划,但围绕“攘外安内”需要,以实用主义方式,对私营工业的发展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首先,对于充实国防工业有战略意义的私营工业给予奖励、扶持等优惠政策,如三酸工业(硝酸、硫酸、盐酸)、氮气工业,前者是化学工业的基础,后者是制造炸药的重要原料。政府一方面计划国营;另一方面采取免费运输、免征出口税、享有专制权等措施,鼓励私人举办经营。故上海、天津、唐山、西安、太原、梧州、广州等地私营设厂如雨后春笋。
其次,政府对某些满足国计民生需要的私营轻工业生产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督和管制。如面粉业、火柴业,上述工厂在全国分布较广,设备较完善,但由于洋粉、洋火充斥国内市场,加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销路骤减,面粉厂、火柴厂纷纷倒闭,为维持正常生产,国民政府则采取加征进口关税、规定产量、产销联营、限制新厂等办法,实施监督和管制。
再次,国民政府为适应对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对日益衰退的棉纺织业采取消极应付的措施。机器棉纺织业,是我国最早的新式工业,1935年,全国华商纱厂达95家,由于日本的侵略扩张活动和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致使全国华商纱厂95家中完全停工的达24家,减工的有14家,几及十分之四。[5](P104)与此相反,日商各纱厂,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很多新工厂开工。为此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请政府切实设法救济全国纱厂恐慌及推广土布销路以裕民生而维企业。”要求“政府联络金融界”给予衰落中的棉纺织业“实行低利贷款”。[5](P52)结果,国民政府只是以应付的态度,责成全国经济委员会注重于原棉种子改良推广、联络金融界组织合作社等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方法不了了之。尽管如此,由于国民政府出于政治经济上需要,有选择地实施了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中某些主张,现代工业的增长也是显著的,如,中国本部的电力产量在这十年内增加了一倍以上,1932年至1936年,各铁路运输工业产品的吨公里数额增加36%,矿产品增加了49%。[6](P348)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关于中国工业建设的主张,是中国国民党制定工业政策的重要渊源之一。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确立全国统治地位过程中,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政策制定给予了关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工业建设的计划,设立了实施机构。但应有现象和实际现象之间的距离说明:以军事统一为目标的国民政府使各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1932-1937年,由于内忧外患,国民政府开始认真对待孙中山的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国家资本的遗教。因此,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因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养民为目的”的遗教和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也使得推进中国工业建设的历程踏上了艰难曲折之途。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孙中山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铁路论文; 国民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