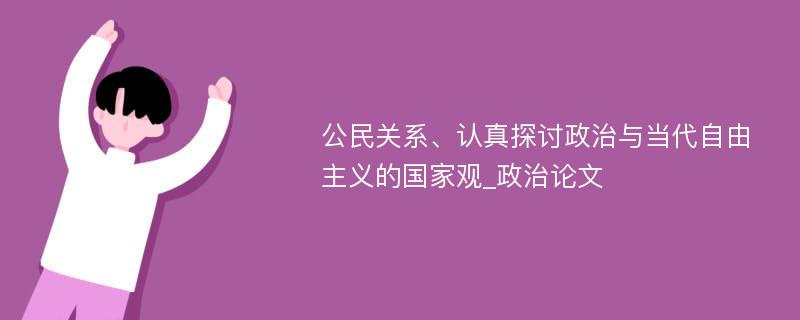
公民间关系、慎议政治与当代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公民论文,当代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哲学层面上讲,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最核心的焦点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我观问题。“社群主义者”基本上是一个被赋予的标签,而不是一个自觉、自愿的理论群体,但对自由主义自我观的批判似乎确实足以让人们断定存在一种“社群主义”的主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认为,自由主义的麻烦在于其“无所挂碍的(unencumbered)自我”②、“原子主义”③或“理想化的自在主体”④。而这种批判,至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如下观点:“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⑤基于这一批判,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社群主义就成了一些学者的主张。
但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批评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它明显缺少对社群本身的批判省察,而这恰恰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处于自由主义图景之核心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个性不仅由社群所型塑,也受到它的威胁,社会与政治权力的集中能同时作为压制和表达个人认同的工具。自由主义力求给这一复杂方程式的双方以应有的力量。在理论层次上,这一理解要求个人既被赋予对其社会的制度和先在假定予以批判反省的能力,同时被赋予对道德行动而言是根本性的非强制选择的能力。……拥有意识到自己社会中内在矛盾的能力,正是自由主义个性观所要求的那种反思的距离。”⑥也正因为如此,理论家们逐渐意识到,是否承认社群的价值,这并非争论双方真正的分歧所在,关键是我们要寻求何种社群,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应当转向这一问题。⑦简言之,一种什么样的社群才配享人们的尊重和忠诚,这个问题是争论双方都必须面对的。
进一步讲,自由主义当然承认,人们生活在种种不同的社群当中,而且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愿意尊重人们的种种社群生活与社群归属,它希望给予个人以尽量宽泛的自由,以便他们在不同的社群中找到或实现种种不同的善。但自由主义在国家的问题上却相当审慎。国家能够被设想为一种先在地规定人们善观念与身份认同的社群吗?这个问题才是这场理论争论的要害所在。也正因为把焦点自觉地局限于国家问题上,自由主义就可以说,自己并不必然要认为个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孤立的,相反,人总是生活于社会当中的,“恰恰是社群主义者似乎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积极地把他们拉到一起去集体地评价和追求善,个人将堕入迷茫与分离的孤立之境”⑧。在这方面,罗尔斯就是一个典型,因为他的理论自始至终都是以一种社会观为前提的:“各种各样的正义观是不同社会观的衍生物,而后者以对人类生活的自然需求和机会的不同观点为背景。”⑨他所坚持的社会观认为,社会是一个世代相续的公平合作体系。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阶段,他同样认为,这种社会观是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前提。⑩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以这场争论为背景来探讨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尤其是讨论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语境中,国家是否是,以及(如果是的话)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社群。我将基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批评,以罗尔斯的契约论(尤其是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的契约论形式)为中心,分析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当代构造。本文将表明,罗尔斯通过重新想象公民之间的伦理—政治关系,试图在自由主义和契约论的语境中把国家塑造为一种中立的、“政治性的”社群,这种国家观有力地响应了社群主义的诸多批评。但这种国家观把自己局限在“政治”的范围之内,因此面对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即政治自由主义语境中独立于整全性学说的“政治”概念是否存在,它又该如何理解。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向,本文认为,政治自由主义背后隐含着一种慎议性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s)的政治概念,它也必须以这种独立的政治概念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当代自由主义对政治社群的构造使之与慎议民主理论之间形成了本质上的契合,相对于传统而言,它是一种具有更强民主预设和民主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
一、私人与国家:传统自由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及其批评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从形式上讲主要表现为契约论,而从精神实质上讲则主要体现为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因此导向一种工具论的国家观。在霍布斯(虽然他是否算得上是自由主义者,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那里,自然状态中的个体既没有对善和利益的共同追求,也没有共同认可的正当标准。虽然从表面上看,每个人都追求生命保全并因此倾向于和平,但自然状态之所以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恰在于生命并不是一种共同的善,而是分散地为各个个体所拥有和珍视。结果,就霍布斯所谓的和平而言,“我们看重的对象是同一个东西,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它被看重的方式却是不同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仅仅从我们自身考虑而看重它。那一价值以及与之关联的理由是收敛性的,但它们不是共同的。”(11)霍布斯一再强调,在自然状态中,在利维坦诞生之前,“这一大群人天生并不是一,而是多”(12)。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统一的人格与身份认同,遑论一种社群生活和社群意识。每个人从自身生命保全出发,出于理性地考虑,放弃自己对一切东西的权利,从而结成了国家。据此,国家和主权者虽然几近绝对,但本质上却仅仅是保护个人生命的工具。洛克虽然强调生命、自由与财产等自然权利,但从推理逻辑上讲,也仅仅是改变了人们通过契约试图维护的利益的内容,而没有改变其工具理性化的推理本身。因此,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建立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财产。
在传统自由主义的逻辑中,从个人到国家,似乎并没有什么新的伦理内容产生出来,国家本身也没有内在的和独立的道德价值。国家或许很有力量,但终归是工具。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亦即自由至上主义立场的诺齐克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政治社会是一个由私人组成的联合体,进入政治社会这一事实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新的价值,“没有新权利在群体的层次上‘浮现’,联合的个人不能创造不是前定权利之总和的新权利”(13)。从伦理上讲,国家仅仅是个人的理性利益或私人权利的聚合而已。
这里的“个人”,若与古典观念进行比较的话,乃是典型的“私人”。对古希腊人来讲,“人”和“公民”的意思毫无二致,所谓生活,也就等于参与城邦的生活。而根据政治理论家萨托利的分析,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私人”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是由拉丁语的privatus(意即私人的)及其希腊语对应词idion的意义揭示出来的。拉丁语的privatus,指的是“失去”,这个词常被用来表示一种同社会的关系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生活方式。而希腊语的idion(私人的)与koinon(公共事务)比起来,甚至更强烈地表达了失去与匮乏之义。相应地,idiontes则是个贬义词,意指非公民,这种人是粗俗的、没有价值的愚人,他只管他自己。(14)因此,私人是缺乏健全的社会关系、只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不关心公共生活、没有社群归属的人。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无疑是空前地抬高了私人生活的价值,国家因此也被理解为纯粹是一种私人关系的结果。在民主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们看来,自由主义完全混淆了私人与公民的界线:“根据自由主义观点,公民与私人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他们把自己的前政治利益作为国家机构的对立面提出来要求得到满足。”(15)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前政治的,似乎没有把公民或公民群体的政治意志当做自己理论构造的构成性要素。我们了解这一疑虑,便为后文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分析埋下了伏笔——“政治的”自由主义如何可能是“政治的”呢?
这种工具理性及工具论的国家观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后果,它们使得自由主义的成长史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史几乎是相生相伴的。其一,它导致了公共政治生活在观念与实践上的衰退。正是这一点,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共和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强势复兴,因为“在共和主义的支配性假定之中,社会史家们已经找到了一种药方,去疗救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工具逻辑和去神秘化的理性,而这种逻辑和理性如此久远地主导了历史写作”(16)。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对公共政治生活与公共精神的强调、对自治的政治社群的追求,与传统自由主义的私人化风格是格格不入的。
其二,就是国家社群意义的湮没。至少自黑格尔开始,就对此作了强烈批判,他把国家当做一个伦理社群来看待,甚至当做一种“客观精神”。在当代,桑德尔则区分了工具性的、情感性的和构成性的社群观念,而社群主义心目中货真价实的社群则是构成性社群。据此,“说一社会的成员由一种共同体感所约束,不仅是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社群主义的情感和追求社群的目标,而且是说他们把其身份——其情感和抱负的主体而不仅是其对象——设想为在某种程度上由社群来界定,他们是这一社群的一部分。”(17)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唯有构成性社群才能满足一个完整的社群所必须具备的四个标准:必须共享完整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分享利益或把结合视为达成目的的一个手段;由面对面的关系所组成;关心所有成员的幸福并且根据互惠性的义务尽己所能提升幸福;社群是自我认同的核心,其关系、义务、风俗、规则和传统对我来讲不仅很重要,而且是使我之为我的东西。(18)社群主义希望以此摆脱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同样,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也有相似的要求,因为“个人自由只能在一种共和主义社群的自治形式之内才能得到充分保证,这一结论代表了所有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核心和神经”(19)。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必然意味着要诉诸共和主义的社群。(20)
由于这种工具理性是以契约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同时,契约本身又具有强烈的私人关系乃至经济关系的意向,因此,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就自然延伸到契约论方法了。最经典的批评仍然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契约关系是私人性的、任意的,用契约的思路来阐述国家问题,完全是把国家与市民社会(主要指经济领域)作了错误的等同:“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会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但是国家对个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而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21)
自由主义究竟是只能重申自身传统中的工具主义国家观,抑或也能够重新厘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本质,从而为社群主义的国家观留出一定的空间?特别重要的是,它还能够重新运用契约论的方法来克服工具理性与工具论国家观的局限吗?要回答这些问题,罗尔斯的理论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因为作为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理论系统,它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特征,而且它还继续采用了契约论的方法。
二、契约论与基于公民间关系的自由主义政治社群
我们可以发现,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中明确承认“社群之善”(22),而且他强调,政治社会是“社会联合的社会联合”(23),这种社会联合乃是非工具性的,因为正义的制度被认为“因其本身就是好的”(24),正义的公开实现是“一种社群价值”(25)。他还进一步指出,他所理解的良序社会不同于“私人社会”,后者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26)。转向政治自由主义之后,他也坚持认为,“一个政治社会自身就可以是一种内在善”(27)。这些表述似乎表明,罗尔斯本人并不像传统自由主义那样,持有一种工具论的国家观,它也不像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等同起来了。但有意思的是,罗尔斯恰恰采用了契约论的传统方法。因此,要理解他对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构造,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他对契约论作了什么样的改变,其中的推理过程又作了什么样的调整,从而可以抛弃传统自由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自己的抱负就是要把洛克、卢梭和康德开启的契约论传统提升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层次。但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洛克式的契约论作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典型而被罗尔斯排除在外了,理由就是它把国家视为私人性的联合体:“虽然自由至上主义观点也重用同意观念,但它根本不是一种社会契约理论。因为社会契约理论把原初协议设想为建立一个共同的公共法律体系,它界定和规范政治权威并适用于每一个作为公民的个人。政治权威和公民身份都通过社会契约观念自身得到理解。通过视国家为一种私人联合体,自由至上主义学说拒斥了契约理论的根本理念……”(28)言下之意,罗尔斯强调契约的“社会”性质。但这个说法仍然不是足够清楚,它没有说明,这种社会性的契约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克服自由至上主义的工具理性,从而避免把国家当做私人联合体的。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分析,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契约的各方是以什么方式、按照什么标准进行推理的。换言之,罗尔斯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理性概念,它与私人性的工具理性有何区别。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进一步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建构主义并不仅仅从实践理性出发,而是要求一种塑造社会观与人的观念的程序。”(29)关于社会与人的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刻画进行推理的主体,并明确实践理性原则所适用的问题的语境。……没有关于社会与人的观念,实践理性原则就会没有意义、作用或应用之处”(30)。也就是说,实践理性的背后还有两个问题:是谁在进行推理?这种推理及其结果打算用于调节什么样的行为或关系?第一个问题涉及推理者的身份,而我们知道,特定的身份往往蕴含着特定的伦理要求,因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总是需要根据特定的人际关系来确认,而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总是意味着不同的行为规范方面的要求或预期。第二个问题涉及推理所要适用的语境条件,人们可以为不同的情境进行不同的推理。
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谈起。如前所述,罗尔斯认为,各式各样的正义观是不同社会观的产物。他在对比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古典功利主义时就提出,二者间的区别源于社会观的根本不同。罗尔斯认为社会是一个世代相续的公平合作体系,而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观则强调对社会资源的有效管理,以便把欲望体系的满足最大化。但如何才能算是“公平合作”,则有待于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即通过揭示推理主体的身份并发掘其伦理要求,从而通过符合这种要求的推理来确定公平合作的具体原则。
这种关于人的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具体表现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也就是说,罗尔斯强调的是政治意义上的人的理念。而且,早在《正义论》阶段,他就明确提出,隐含在契约论传统中的正义观念“为民主社会建立了最恰当的道德基础”(31)。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还表明,政治自由主义乃是要解决民主传统中自由与平等、古今自由的调和问题。(32)因此,所谓政治意义上的人,就被确定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如此一来,订立契约的各方就不是传统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人了。那么,民主的公民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在确定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该如何进行推理呢?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念。这一理念在内涵与应用方面仍然饱受争议,但对本文的论题而言,有两点特别重要。首先,公共理性理念的核心是相互性(reciprocity)标准,因为罗尔斯虽然有时认为可能存在多种公共理性,但同时强调,相互性标准是它们共同的限制性特征。(33)其次,这一标准在罗尔斯那里的核心指向,就是公民们在涉及宪政根本要素与基本正义问题时要能够就自己的主张提出其他公民也可以接受的理由。罗尔斯所主张的政治正当性理念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相互性标准、从而也可以看出公共理性理念的本质要求:“基于相互性标准的政治正当性理念可表述为:只有当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为我们的政治行动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的,而且我们也合乎情理地认为其他公民也可以合乎情理地接受那些理由,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才是恰当的。”(34)显然,这里所包含的推理方式不可能是纯私人性的和工具性的,因为这样的推理及其所给出的理由肯定是其他公民不可能合乎情理地加以接受的,社会合作也不可能由此展开。事实上,正是相互性标准使得公共理性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特征。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追问,公民们为何要用公共理性进行公共推理?罗尔斯的回答可以很直接:这是民主的公民身份本身所包含的要求。公共理性的目标,是要从道德上确定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纵向的,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横向的,即公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种政治关系之内行使的政治权力总是由国家为执行其法律而设置的机构所支持的强制性权力。在宪政制度下,政治权力也是作为一个集合体的平等公民们的权力。”(35)既然公共权力是平等的公民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么,在事关公共权力如何运用的问题上,一个公民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可以为其他公民合乎情理地予以接受,就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唯有满足这个条件,才能体现平等的公民身份。这就是民主的公民身份的伦理含义所在。进而,从其伦理内涵上讲,上述两个方面的政治关系归根结底是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问题:我们按照对平等的公民之间关系的理解,择出一些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正义原则,从而就间接确定了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从头至尾,罗尔斯的契约论都不是直接去解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从公民间的关系出发的。同时非常明显的是,公民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它也是一种特定的伦理关系。
简言之,作为契约各方的公民,其平等的公民身份要求他们运用公共理性进行推理。罗尔斯因此强调,公共理性理念“隶属于民主的公民身份”(36)。在围绕公共理性理念所进行的聚讼纷纭的争论中,也有人意识到,对公共理性来讲,“关键之处完全在于民主的公民身份的本质”(37)。运用公共理性是公民的责任,是一种针对特定角色的伦理要求。罗尔斯将这种责任称为公民性(civility)责任,即“为自己的政治行动给公民们给出公共理由(public reasons)的责任”(38)。唯有符合这一条件的原则,才是合乎正义的原则。正是相互给出公共理由的要求,使得罗尔斯的契约论摆脱了传统自由主义对工具理性和工具性理由的依赖。既然公共理性意味着我们是从公民间的横向关系出发去间接地塑造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纵向关系,而这种横向关系是建立在公共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之上的,因此,对于公民而言,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私人性工具了。
根据这一点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出,国家或政治社会虽然不是工具性的,但由于它不是先在地规定了公民的身份认同(尤其是,除了民主的公民身份本身以外,它没有规定每个公民身份认同的其他更多或更深的内容)或善观念,而是反过来由公民间关系所塑造,因此,它就不像社群主义所设想的那样,享有对于个人的优先性。无论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价值的角度讲,这种优先性都不成立。不错,如前所述,罗尔斯确实认为政治社会也可以是一种内在的善,但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善并不是被给定的,它是公民们运用公共理性的结果。而我们知道,公民们运用公共理性的结果就是一套政治性的正义原则。所以,我们把政治社会当做一种内在的善,也就是认可这样的正义原则,认可由这些原则所调整的政治生活形式与政治制度。社群主义者往往批评自由主义,认为后者否认共享的善。例如泰勒就认为,“善”有两种含义,在广义上,它意味着我们寻求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更狭窄的意义上,它指向被看重的生活计划或生活方式。他认为,自由主义在狭窄的意义上不可能有公共善,但在更广的意义上,当正当的规则也能算作“善”,就可能有一种极端重要的共享的善。他还以“水门事件”中公民的普遍愤怒为例,认为“愤怒的公民认为被违反的正是正当的规则,一种自由主义的法治观念,那就是他们认同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当作公共善而奋起捍卫的东西”(39)。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与泰勒这样的社群主义者并没有实质的分歧。罗尔斯承认,“社会契约是许多个人——所有公民——为着他们确实共享的共同目的的联合。这种共同目的不仅是他们事实上共享的,而且也是他们应当共享的。”(40)我们无疑从这里看到了黑格尔的影子。不过,这种共享的目的,是且仅仅是一个基于民主公民身份与公民间关系的正义的政治社会,而不是一个先在的伦理实体意义上的社群。
相应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会主张对国家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与制度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未经反省的社群意识之上的。相反,“一种社群意识,就其依赖于正义概念而言,只有在所有人的权利和特权(privileges)能被每一个人在不被要求违犯他所理解的义务的情况下而被承认的地方,才有可能。”(41)这一基于正义的社群意识非常接近于哈贝马斯等人所主张的政治认同观念,它并非指涉政治之外的一种血统或生活方式的先在同构型,而是要将公民的忠诚直接导向一个作为自治的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据此,“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它也不应该受外来移民的触动)主要依赖于根植于政治文化的法律原则,而不完全依赖于一个特定的伦理—文化生活形式。”(42)
也正是基于上述对共享目的及相应的国家观的理解,罗尔斯非常慎重地与社群主义拉开距离,防止把国家理解为一种社群主义眼中的社群:“对于政治社群的期望确实必须放弃,如果我们用这样一种社群指通过认同同一种整全性学说而获得统一的政治社会的话。”(43)换句话说,国家不应当被视为一种构成性社群。但我们要注意到罗尔斯所提出的“如果”这一假定条件。一如他的建构主义强调正义原则是在政治的范围内被独立建构出来的一样,如果我们只是限定在政治的范围内的话,我们也可以把罗尔斯意义上的国家视为一个政治性的社群。而这个社群之所以是政治的,就在于维系这一社群的正义原则是在不“言及、了解或危及”(44)公民们各自持有的种种整全性学说的基础上而被构造出来的,对国家权力之行使的辩护没有诉诸这些整全性学说中的任何一种。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政治社群是一个政治中立的国家。这就使得罗尔斯同时捍卫了自由主义传统中关于个人自由、宽容的核心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一下,面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罗尔斯究竟在国家观的问题上采取了何种立场。如前所述,在黑格尔看来,在伦理领域只有从实体性出发或从原子式的个体出发这两种可能的观点,而罗尔斯则认为,康德和卢梭(注意,没有洛克)的契约观念代表着第三种选择,这种契约观念承认人们分享共同目的,即进入政治社会,这不仅是他们事实上共享的,更是他们应当共享的;同时它是理性的、假定性的而非历史的:“它不同于从作为独立于所有社会联系的原子的单个个体开始,然后从他们中建立一个基础。同时,它不使用作为精神实体、个体仅作为其实体性的偶然表现的国家观念,国家是一个舞台,个体在其中可根据每个人可视为理性而公平的原则去追求他们的目的。”(45)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通过对自由主义以及这种契约论传统的“政治”限定,罗尔斯提出了一个超越社群主义以及传统自由主义的新选项。
三、自由主义的政治社群与慎议政治:一个思考方向
从以上分析来看,罗尔斯的理论表明,自由主义似乎也能够把国家理解为一种“政治”社群。但这种“政治”社群是在“政治的”自由主义框架内构造起来的,因此,它能否真正构成一种可靠的国家观,就完全依赖于“政治的”自由主义本身在理论上是否是健全的。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恰恰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一方面,许多人强调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必须是形而上学的和整全性的学说,这其中自然包括社群主义者(46);另一方面,也有人站在民主主义或共和主义的立场上批评说,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中根本没有政治,或者是弱化了政治过程的意义,因为原初状态的设计及其推理体现的是一种“独自式的”道德推理过程,而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政治竞争或对公共事务的对话与讨论。(47)此时,仅仅说这种推理是由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进行的,似乎就不足以证明它一定是政治的,因为直接来讲,我们只能说这种推理是伦理性的、非工具性的,虽然它肯定与政治有关。这些质疑其实可以集中到一点:“政治的”自由主义有可能吗?
本文当然不能也不需要全面回应针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种种质疑,但我们可以从第二个问题切入来考虑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可以证明政治自由主义当中是有政治的,并且能够表明它确实是以一种政治的概念为基础的,那无疑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至少是解决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遗憾的是,罗尔斯本人没有直接为政治自由主义界定出一种政治(the political)概念,他只是强调了一种政治性的正义观念的三个特征:它适用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它是以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整全性学说的方式而被呈现出来的;它的内容是根据某些隐含在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的根本理念而表达出来的。(48)第一个特征显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整全性学说中切割出其政治部分,并认为它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第三个特征看似具有直接的政治含义,但只有当我们把民主与政治直接等同起来的时候,它才能算是对政治概念提供了一种解释。但这种等同明显有违我们的直觉,而且,我们也不清楚,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那些根本理念是否一定没有一种整全性学说的背景。况且,罗尔斯还曾说过,神授君权、专制等都在政治的范畴之内(49),这就更令人怀疑第三个特征对于解释政治的有效性了。第二个特征重在述说政治性的学说与整全性的学说之间的关系,但罗尔斯对二者的解释却明显是循环的。一方面,根据他对整全性学说的解释,它是同时包含政治的与非政治的价值与美德的学说,既然如此,“我们能够明白何为一种整全性学说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何为政治性的(学说)……因此,政治的理念在概念上先于整全性学说的理念”;但与此同时,如果政治性的学说被界定为独立于整全性学说而构造出来的学说,那么,我们逻辑上就需要先知道什么是整全性学说,“因为独立性预设了,我们已经知道一种整全性学说是什么,然后把政治等同为一种不诉诸这类学说的东西”(50)。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若要从罗尔斯的文本中直接找到对政治的界定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上文第二部分已经表明,罗尔斯式的当代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公民们运用公共理性、彼此就自己的行动提供公共理由的过程而得以完成的。因此,我们不妨回到这个过程上来。事实上,政治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之所以认为罗尔斯那里没有政治,正在于他们是从某种公民行动过程的动态角度来理解政治的。公民们运用公共理性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他们相互之间就国家公共权力的运用提出彼此的辩护理由。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政治自由主义的这个核心主张与许多批评它的民主主义者,尤其是慎议民主主义者的要求高度契合。因为慎议民主的追求就是要实现公民间的“相互辩护”(51)。换言之,慎议民主的主张是,“对集体政治权力的行使所作的辩护,要在平等者之间自由的公共推理的基础上展开”(52)。作为最深刻的慎议民主论者,哈贝马斯念兹在兹的主体间性,实际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相互辩护的要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慎议民主主义者们不仅是在倡导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而且也是在倡导对政治本身的特定理解。最典型的慎议民主主义者都认为自己是在复兴某种传统,包括雅典的城邦政治实践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慎思(议)(deliberation)的理论。当埃尔斯特说,“需要重申,这一发展代表着一种复兴,而不是创新。慎议民主的理念及其实际实施与民主本身一样古老”(53)时,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哈贝马斯则强调,民主的原始含义,乃是与理性的公共运用相联系的对话,这种范式为古典共和主义传统所保留,而被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式抛弃了。(54)而我们知道,政治的概念本身就其源头而言恰恰应当追溯到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古老的民主就孕育了政治的要义。对哈贝马斯及整个现代慎议民主理论深有影响的阿伦特,就强烈主张要恢复对政治的这种本来理解。(55)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慎议民主理论家们常常把“慎议民主”与“慎议政治”这两个概念交互使用,而哈贝马斯甚至主要使用的是后一个概念,或者“政治商谈”等。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解读为某种形式的慎议民主理论,那么,我们似乎就可以说,它所塑造的那种当代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确实是成功的。它同时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政治社群要求自由主义变得更加民主,自由主义应当是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56),因为唯有如此,它才可以承载政治社群的政治内涵。当然,慎议民主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之间的对立与争论,恰恰是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又一个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甚至比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要更加持久、更有生命力。因此,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慎议民主式解读就尚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工作需要深入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理论家们已经认识到,罗尔斯的理论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构造一种慎议民主的模式。(57)在慎议民主理论内部,也有人认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所提出的论点似乎确实有一个共同的要核:政治选择要成为具有正当性的选择的话,它必须是自由、平等且合乎理性的行动者之间就目的所进行的慎议的结果。”(58)
哈贝马斯本人对罗尔斯的一段评论则更加耐人寻味:“随着无知之幕拉得越来越高,随着罗尔斯的公民们变得越来越有血有肉,他们就会越深刻地感受到,他们受制于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理论上提前确定好的而且已经变得制度化了的原则与规范。……在其社会的公民生活中,他们不可能重新点燃激进民主的余烬,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关于正当性的根本性商谈已经在理论范围内发生过了,而且他们发现,理论的结论已经积淀在宪法之中了。”(59)他显然是站在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在批评罗尔斯,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原初状态中发生的故事乃是一种政治“商谈”。而慎议民主理论对罗尔斯批评得最多的地方,恰恰于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事实上是在“独白”,而不是对话或商谈。以此论之,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的评论反倒给了我们从慎议政治的角度解读政治自由主义的信心。
有人可能提出一种疑虑:上述解读的思路似乎是把“政治”与“民主”等同起来了,而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罗尔斯本人没能直接提供一种独立的政治概念时,恰恰曾经指出,这种等同是缺乏理由的。这会不会使得这种解读的思路陷入自相矛盾?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两点说明。第一,慎议民主显然不同于现有的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自然也不能等同于罗尔斯所谓的“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相反,慎议民主理论本身就是在对现行自由民主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予展开)。因此,当慎议民主理论家们从慎议民主的角度理解政治概念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在把现有的民主模式等同于政治本身。第二,根据上述解读,政治自由主义所需要的那种政治概念不是像罗尔斯所认为(至少可以从他的文本中推导出)的那样根源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而是存在于公共理性的运用过程,或者说公民们之问“相互辩护”与慎议的过程当中。根据慎议民主的理念,正是这种公共慎议或公共理性的运用过程体现着政治的本质,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本身自然就蕴含着民主的特质。政治的概念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疑是被泛化了,而慎议民主理论本身恰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克服政治的“身份危机”(60)的努力。当然,其成与败,就不是本文可以处理的议题了。
注释:
①本文的主要内容曾以“公民间关系与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当代构造”为题发表于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2012年第8期,感谢龚群教授约稿和《哲学与文化》杂志社刊用。《政治思想史》杂志的刘训练先生曾受邀评审此文,他希望拙文能以简体版本呈现给大陆学界同仁,承其美意,笔者在对文本内容作细微调整和补充后刊发于此。
②Michael Sandel,“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 the Unencumbered Self,”Political Theory,Vol.12,No.1(February,1984),p.86.
③Charles Taylor,“Atomism,”in his Philosophyand the Human Sciences:Philosophical Papers,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7—210.
④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李琨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7页。
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3页。
⑥William Galston,“Pluralism and Social Unity,”Ethics,Vol.99,No.4 (July,1989),p.722.
⑦Sibyl Schwarzenbach,“Rawls,Hegel,and Communitarianism,”Political Theory,Vol.19,No.4(November,1991),p.540.
⑧Will Kymlicka,“Liberal Individualism and Liberal Neutrality,”Ethics,Vol.99,No.4(July,1989),p.904.
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9.
⑩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34—35,107.
(11)Gerald Postema,“Public Practical Reason:An Archeology,”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Vol.12,1995,p.452.
(12)Thomas Hobbes,Leviathan,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Oakeshott,Oxford:Basil Blackwell,1957,p.107.
(13)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4,p.90.
(14)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
(15)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662页。
(16)Joyce Appleby,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90.
(17)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50.
(18)Jack Crittenden,Beyond Individualism:Reconstructing the Liberal Sel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2—133.
(19)Quentin Skinner,“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in Richard Rorty,J.B.Schneewind and Quentin Skinner eds.,Philosophy i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07—208.
(20)Philip Pettit,Republica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26.
(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3—254页。
(2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395.
(23)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525.
(2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527.
(25)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529.
(26)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p.521—523.
(27)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Samuel Freeman 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70.
(28)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265.
(29)(30)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107.
(31)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viii.
(32)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p.4—5.
(33)John Rawls,“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64,No.3 (Summer,1997),p.774.
(34)John Rawls,“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64,No.3,p.771.亦可参见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217。
(35)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p.482.
(36)John Rawls,“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64,No.3,p.767.
(37)Paul Weithman,“Citizenship and Public Reason,”in Robert P.George,Christopher Wolfe eds.,Natural Law and Public Reason,Washington: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0,p.129.
(38)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p.617.
(39)Charles Taylor,“Cross-Purpos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in Nancy L.Rosenblum ed.,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75.
(40)John Rawls,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Barbara Herman 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63.
(41)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p.88.
(42)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679页。
(43)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146.
(44)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12.
(45)John Rawls,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pp.364—365.
(46)例如,Michael Sandel,“Review of Political Liberalism,”in G.W.Smith ed.,Liber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Theory,Vol.III,New York:Routledge,2002。
(47)例如,Chantal Mouffe,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London:Verso,1993; Robert Alejandro,“What is Political about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8,No.1(February,1996)
(48)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p.11—14.
(49)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2nd.,p.374.
(50)Gerald Gaus,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Liberali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3,p.187.
(51)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99.
(52)Joshua Cohen,“A More Democratic Liberalism,”Michigan Law Review,Vol.92,No.6(May,1994),p.99.
(53)Jon Elster,“Introduction,”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
(54)Jürgen Habermas,“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in Seyla Benhabib ed.,Democracy and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23.
(55)Hannah Arendt,“What is Freedom,”in her Between Past and Future,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8,p.154.鉴于本文第三部分重在为政治自由主义可以依据的政治概念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考方向,同时限于篇幅,对于慎议民主理论中的政治概念将不予展开讨论。
(56)Joshua Cohen,“A More Democratic Liberalism,”Michigan Law Review,Vol.92,No.6,p.99.
(57)例如,Anthony Simon Laden,“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Thirty Years of Reading Rawls,”Ethics,Vol.113,No.2(January,2003)。
(58)Jon Elster,“Introduction,”Deliberative Democracy,p.5.
(59)Jürgen Habermas,“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Remarks on John Rawls' s Political Liberalism,”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2,No.3(March,1995),p.128.
(60)著名政治学者萨托利曾感叹政治的概念被滥用,从而引起了政治的“身份危机”。这个说法可参见Giovanni Sartori,“What is‘Politics’,”Political Theory,Vol.1,No.1(February,1973),p.17。
标签: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社群主义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群经济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