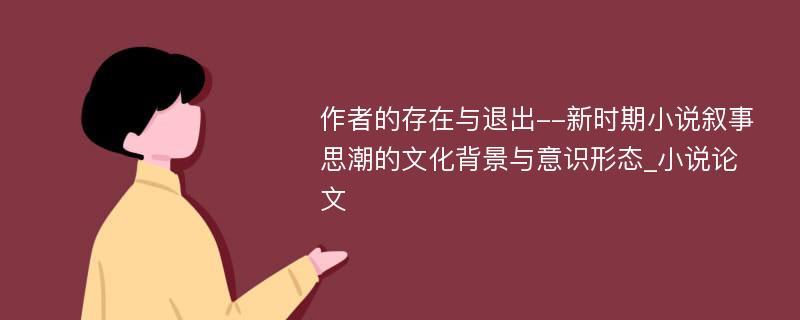
作者的在场与退场——新时期小说非全知叙事思潮的文化背景及其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化背景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小说发展至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叙事观念似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小说创作中,作者在其中现身说法、评头论足,自己操纵故事发展的“讲述”技巧越来越受到轻视,甚至摒弃;而主张“作者退场”,不介入,进行客观“显示”的叙事思潮大行其道。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主义的大师们在叙事技巧和叙事程序上所进行的试验,比如作者藏匿,替代叙述人或叙述焦点的选择,对审美距离的有效控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并且影响深远。中国新时期小说在叙事倾向上受这种“作者退场”的“客观化”倾向的影响非常明显,不仅在理论上一再被表述,而且实实在在地是创作中的实际状况。
但说来归去,“作者退场”只是个策略问题,作者无法在根本上从小说世界中脱身,无论作者表现得多么冷淡,多么中立,多么客观,他都会介入虚构的人物世界,只是作者在场的方式,或者说作者介入的方式不同而已。在现代小说中,作者在坚持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在叙事方式上所选择的控制虚构人物世界的方法就是选择替代叙述人采用非全知的限制性叙述视角进行叙事,作者退居幕后,以“隐含作者”的身份对文本进行隐蔽的操纵与评价。本文的内容主要是就新时期小说创作中限制叙事思潮出现的文化背景及其意识形态状况展开论述,侧重点在于叙述人的文化身份而不在他的语法及透视关系。
一、“我”的故事——“现代派”小说的主体自叙及“自我”的受阻
纳塔丽·萨罗特在她的著名论文《怀疑的时代》中说:“现在小说的主要问题在于从读者那里收回他旧有的贮存,尽一切可能把他吸引到作者的世界中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既有效又容易的方法。无疑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小说家经常采用这种写作方法。”[①]结合她全文的语境,萨罗特显然把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推到了一种本体论的崇高地位上来,她立论的依据仍然是“真实性”,但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客体的真实性——对外部世界详尽的、精雕细刻的描摹。这在她看来,要么是不真实的,“象那逼真模拟的画幅一样,看上去是立体的,事实上是平面的”,[②]要么是没有意义的,“这些表面的事物能让读者看到的东西,远不如他对四周迅速的一瞥或瞬间的接触所看到的丰富”[③],她所强调的是主体的真实性——人类心灵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在古典的实在论哲学中具有十足的主观性的、难于捉摸的东西才是不真实的,但在现代的主体论哲学中,心灵才是唯一真实可靠的东西。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萨罗特美学表述的现代哲学与现代心理学背景。
萨罗特至少在一点上肯定是正确的,即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是一个现代事件和文化事件。尽管第一人称叙事在小说的古典时代也存在,但那是技术层面和策略意义上的;而在现代小说中,第一人称“我”的叙事的大量存在,就不仅是美学上变革的要求,而且与现代世界复杂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是人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和主体论哲学思潮在美学上的反映与表征。第一人称“我”的叙事作为一种思潮在现代小说中出现,其意义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而且是本体论上的。
这从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以知青、“反右”、“文革”题材为主的“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就其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主题情致与这些小说作者的经历及思想倾向有很大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小说完全可以当作“复活的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这两代人的自叙传来阅读。但在具体的叙事方式上,我们却看到,这些作品大都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小心翼翼地避免第一人称主体自叙的渗入,这一方面与在叙事观念、叙事习惯上更喜欢更熟练于第二人称的全知叙事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作家主体意识与价值观念上的“社会本位”思想有关,作家不想让读者把这些故事读作作家个人的故事,而是希望被读作他人、大家的故事,从而达到一种社会性写作的目的。但到了1985年前后却集中出现了一批以第一人称主体自叙为其叙事特色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寻找歌王》,王朔的《空中小姐》、《橡皮人》,马原的《虚构》、《西望长安》,洪峰的《极地之侧》、《奔丧》以及刘毅然和残雪的部分作品等。这些第一人称的作品大量而集中地出现,其意味就有所不同了。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1985年有两个大的小说思潮炫赫一时,一是“寻根小说”,一是上述大部分被指认为“现代派”的小说(张承志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第一人称的主体自叙是一条贯穿性的线索,他的“自我“具有独特的内涵,所以他的作品并没有被置于“现代派”之列)。这两类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分野极鲜明。“寻根小说”几乎全部采用全知的外视角,叙述内容上至远古神话,三皇五帝,远至蛮荒的边野山寨,原始森林,有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叙述气魄,从叙述语态上看,叙述人博古知今,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知,无所不谈,表现出“究天下之理,穷古今之变”的自信,因此,叙述人自我定位在一种类似于“文化超人”的基点上。与此相反,“现代派”却把笔触坚定地指向自身,自身的情感、欲望,指向个人在社会中的不适感:焦虑、迷惘、惶惑。所以,“现代派”小说中主体自叙的大量出现是人本中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外化为、符号化为文本中的叙述意识所致。这些作品之所以被指认为“现代派”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叙事上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主体自叙,而是因为表现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离甚至是龃龉和对抗色彩。《无主题变奏》中的“我”对一切流行的价值观、价值形态予以拒斥,以一种“局外人”的冷漠外壳抵御外界的侵凌,以保持自我的独立。王朔小说中众多的“我”和“我们”以“麦田守望者”的姿态对理想、崇高、高尚、正经(被认为是假的、虚妄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袤渎和嘲讽。张承志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第一人称主体自叙是一条贯穿性的线索,但他的“自我”的精神气质与内涵独标一格,既不同于反主流意识的叛逆者,“局外人”,也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所欢迎、提倡的英雄形象,而是具有“孤独者”的多思敏感和“超人”的行动性的综合气质,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强人、硬汉形象。我们有理由宽容甚至欢迎这种“自我”的觉醒和对板结的文化价值形态的抗击姿态,因为它对单一而凝固的文化价值形态起到了疏松和丰富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同样有理由对这些所谓的“现代派”进行批评:他们的“自我”只是些空洞的外壳,没有被赋予多少具体的价值内容;除了愤世嫉俗、斥骂、嘲笑、消解以外,“自我”缺乏建设性的、有深度的价值内涵;所谓的“现代派”并没有成就一种现代的、精英化的、自信的、自我实现的人格与价值系统。因此,我们看到,新时期小说中的“自我”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模糊而脆弱的概念体。张承志小说中的那个“我”——一个个人主义的强人、硬汉形象并未被赋予一种充盈的思想、意识内涵,而且,这种强人气质的扩张还会来一种反秩序的精神倾向,因此,也不代表“自我”的一种正确向度。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化结构被汹涌的商业文化冲击得攻守失衡、左右支拙时,以自我,以个性主义,以精神和价值关怀为核心的精英文化并未乘势而高涨,取得自己的命名权,相反,而是变得更加进退失据。“自我”甚至在文本中失去了主体自叙的自信与勇气,日益成为一个旁观者和随俗俯仰的人。
二、“我爷爷”的故事——“寻根小说”的“他叙”与知识分子叙述人的退场
“自我”建塑在现实中的受阻,使一部分作家把对自我人格和民族精神的寻找触角伸向了自己血缘与精神上的祖先。于是,在小说创作中,簇生了一批“我爷爷”、“我奶奶”、“我叔叔”、“我婶婶”等的家庭或身边故事。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洪峰的《潮海》等。这类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相当独特,“我”既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叙事者——但事实上,作者叙事的焦点并没有固定在“我”身上,就是说,这类小说虽然在语法人称上采用了“我”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但在透视关系上却是“全知”的,它不是一种严格的“限制叙事”,也不是一种严格的“全知叙事”,而是叙事上的一种“杂交”现象。实质上即是由故事之外的“我”叙述的他人的故事,由于这些“他人”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我叔叔”、“我婶婶”,所以尽管“我”不在故事中,却是一个血缘和精神上的旁观者,意在突出作者在精神上的“在场”。这种在叙事上故意的“杂交”与乖张显然希图达到出人意表的修辞功能。
首先,“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叙事语式突出了外在叙述人的双重身份:其一是“我”的现实身份与政治身份,即与作者的一种现实性联想关系。“我”是当下的写作者,是一个作家,这种现实身份凸现了作者精神上的“在场”。其二是“我”的血缘与家族史身份,即“我”的历史身份,这种身份是“个人性”的:“我”讲述的是“我爷爷”、“我奶奶”、“我叔叔”、“我婶婶”的家族故事。和传统的全知全能第三人称叙事形态相比,这种对叙述人“我”的个人身份、血缘身份的强调实际上又促成了作者在意识上的退场,因为由“我”来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就弱化了作者意识(政治意识、社会意识、道德意识等)的介入与干预。在叙事功能上,叙述人的个人与血缘身份突出了故事的“口头”性质和私人性,从而也强化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民间性质,与同类题材作品全知全能的“书面化”表达和官方化、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规定在“互文”的意义上形成鲜明的比照。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和阿城的《棋王》(虽然《棋王》不是一个家庭史的故事,但叙述人“我”的旁观立场,“我”与被叙主体王一生的精神联系与《红高粱》在叙述方式上非常类似)在叙事意识和叙事立场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作家从主体自叙,也从“代言人”的主流叙事意识向民间叙事立场有意识地偏离的倾向,知识分子叙述人或人民的“代言人”的地位与作用悄悄地弱化或被置换。
《红高粱》中的“我”就其现实身份而言,仍然没有脱离知识分子叙述人这一基本格局,即从常规的思路上来阅读,仍然可以看作是“我”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但“我”的血缘身份却表明作者的叙述意识悄悄地置换与更替又改变了叙述人在传统文本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改变了整个文本的叙述语气及其意识走向。《红高粱》中的被叙主体是以余占鳌为首的一群草莽英雄,准确地说写的是一群土匪抗日的故事。若在传统的文本中,即使他们的抗日行动受到肯定,而他们身上的“匪性”与劣迹仍然会成为作家叙述意识中批判或改造的部分。就是说,他们要么不会成为主人公,要么整个文本的叙事结构就会改变,根深蒂固的政治视角肯定会在文本中设置一条批判性的线索,因为“土匪”作为一个政治语码和文学语码其基本内涵是被固定了的。座山雕(《林海雪原》)因为处在民族斗争的最后阶段,和共产党已构成直接对抗,这一土匪形象的反动性质是无法更改的,但即使象胡传魁(样板戏《沙家浜》)这样有过抗日举动的土匪形象,他也必须同时被放在反共的另一条线索被表现。尽管和座山雕相比,作者的漫画手法突出了他的草莽性质和喜剧色彩,但他作为一个反面形象的基本面貌没有也不会被改变。但《红高粱》通过选择替代叙述人“我”(和土匪是血缘上的祖孙关系)叙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把一个传统上复杂的民族与阶级斗争的政治故事改写、置换成了一场家族性的抗日传奇,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政治视角被悄悄地抽离,从而突出了讲述的个人性质、家族性质和民间性质。不但“我爷爷”余占鳌、罗汉大爷、“我奶奶”的抗日行动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就连他们身上十足的野性与匪性: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男女调情霸占人妻,高粱地里的野合等都被赋予了质朴诱人的光泽。《红高粱》宣告一种新的文本思路的降临:以民间传奇重写政治事件、重写历史。
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就其题材来说,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知青题材”小说的一部分,但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叙事意识已和同类题材小说在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内的思考大相径庭。王一生这一形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人格、他的人生态度、他的思想意识与他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思想背景和生活土壤格格不入,而是与在思想史的河流中久已被阻隔的逍遥避世、讲求内在的人格与精神自由的道家文化相榫合。很明显,王一生这一形象所表现出的整体思想倾向与价值观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已有了明显的偏离,故此,当时的评论在高度评价这一形象在艺术上成功的同时,不忘记告诫,这一形象的人生态度是“不足效法的”。这种偏离显然是有意为之,这可以从作者对替代叙述人的选择和所作的限定可以看出。第一人称的限制叙述人“我”首先将作者在语法人称和透视关系上置换出了文本,使作者对文本的干预只能以隐蔽、潜在的方式进行——直接的议论已经不合适,当然可以通过戏剧性的议论[④]来进行,比如“我”的间接评价。但作者基本上把叙述人“我”限定在一个“光学”的位置上,仅仅让“我”看到和转述王一生的行为,而很少意识参与,因而整个作品表现出的思想意识向度是“王一生式的”——不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而是相当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的人生态度。《棋王》标志着小说创作走出单一的政治意识之后拓展民间意识的新指向:传统的文人指向。
其次,突出一种“时间”主题。“我爷爷”、“我奶奶”、“我叔叔”、“我婶婶”的故事显然带有“寻根”的意象,但祖辈与父辈们的故事由“我”来讲述,就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历史与当下成为互为辉映的存在,语义也就在对比中产生。在莫言笔下,祖辈的铁血业绩和酒神精神显然暗含着对当下,对“我辈”精神贫弱的不屑和痛心疾首,用他的话表达,就是对“人种退化”的忧虑。而在苏童则是想在祖辈和父辈那里找寻自己的影子,想在一种精神史的框架中,在家族血脉与心灵史的意义上锚定自己的方位。“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缀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创作这些小说(指“枫杨树乡村系列”)是我的一次精神‘还乡’”。[⑤]
第三,突出“写作”的意义。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学创作是在认识论与反映论的意义上被认知,是与现实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因此,“模仿”与“真实”是文学范畴中最本真的概念。但在现代语言学与现代哲学背景上,语言被赋予了“创世”的意义,写作者——叙述人的在场/缺席才对“在”与“不在”有决定意义,因此凸现写作者存在和写作行为的文学写作观就有了盛行的充分余地。“写作”既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衍接寻找回答“我之所以为我”的精神发生史问题,也可以通过向乌有之乡的冒险创造一个经验世界(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就是说,“写作”既是作家的生存方式,是精神史的证明(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中“我”的声音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祖辈、父辈与我辈之间,从而贯通了三代人的一部精神史),甚至“写作”又是一个“神”,一个“新上帝”,具有创世的功能,除马原外,宋海年的《生死话题》、西飏的《季节之旅》等也表现出这种“写作”的特色。尤为突出的是新近出现的小说家张旻。他的大部分小说(如《情幻》、《校园情结》等)都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人“我”建立起一个经验世界(事件),然后再通过另外一个叙事人的叙述将刚刚建立起来的经验世界(事件)解构、打散,一再重复着“创世纪”又“失乐园”的故事,表现出作者对“写作”既崇拜又悲观的复杂情结。
三、“他们”的故事——“新历史小说”的边缘叙事和“新写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缺席与被审
若耐心细致地观察近些年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细微变化,我们还能获知这样的事实:知识分子身份的第一人称“我”渐渐地从自叙立场,朝旁观、陪衬、他叙和被叙的边缘性立场退却,“自我”的心理空间和精神史的构架为膨胀的物质化、欲念化的经验性表象所取代,而对叙述人的选择开始有意识地偏离作家的主体自叙立场,着意选择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性人物作为叙述人,不仅在叙事的形式上弱化了作者对文本的介入,而且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上也进行了悄悄地置换。“新历史小说”对近现代史的再度审视实际上就是一个再度编码、再度叙事的过程:作为社会代言人的全知叙述人和以自我、个性主义为本位的知识分子叙述人宣告缺席与退场,社会边缘身份的叙述人渐次登场,被“十七年”政治性话语,也被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的人文话语遗漏的边缘性、民间性题材得以呈现,政治化、人文化的意识形态结论被改写。如刘恒的《苍河白日梦》选择了一个百岁老人、一个封建家庭的奴才作为叙述人,苏童的《妻妾成群》选择一个小妾颂莲作为聚焦人物,余华的《活着》则选择了从阔少到小民、九死一生经历坎坷的富贵作为叙述人。这些叙述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身份的边缘性,意识上的非主流化和民间性。他们的这种特点使他们作为叙述人的地位和价值都被传统文本所轻视或遗漏,那么现在在他们口中或眼中再现的历史显然会是另一种模样,因此,“新历史小说”之“新”在于它通过叙述人的再度选择带来的新的历史意识。
这里仅以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为例做些说明。《苍河白日梦》从名字上来看就可以发觉,作者对历史沧桑感的感喟和兴叹的叙事意图就很明显。“苍河”与“白日梦”两个概念所涵蕴的沧海桑田,岁月逝水、人生如梦的意旨可以窥知作者意象化的努力。这一叙述意图在叙事策略上的保证就是选择了一个行将就木的百岁老人替代作者作为叙述人。对于作品目前的面貌而言,这一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一)百岁老人本身就是一颗历史的活化石,他的讲述具有浓重的历史沧桑意味。作品卷首语是这样的:“孩子,我的故事讲完了——老者W”,“老人家,我拿它怎么办呢?——作者L”这样的语言传递,也表明一种历史意识的传递,警世和觉世的意味非常浓。(二)叙述人作为佣人的家庭身份和作为边缘人的社会政治身份,相对于作为被叙主体的家族史和延伸意义上的民族历史只能是一个看客,一个窥视者,因此,他看到的历史具有猜测的和非正史的性质。而且从故事的传达方式上来看,它是讲述型的,而非叙述型的,有一个面对面的听者,受述人,这种说/听的讲述方式突出了故事的口语特征,而与书面化特征相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1)情节发展的非连贯性与扑朔迷离;(2)人物思想性格及其命运的相对模糊;(3)历史的神秘主义与悲观主义倾向。这最后一点是前两点合乎逻辑的结果。(三)百岁老人演说百年兴衰,喜笑怒骂,不拘一格,这种开放的内心独白式的叙述方式将超然与峻厉,优雅与粗鄙揉合在一起使这部作品在叙述基调风格上具有雅与俗,粗与细、刚与柔相混杂的特色,从而也渲染了历史的驳杂色彩。
“新写实小说”出现在87年前后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厌倦了“先锋小说”的话语叙事,而在感情上、阅读趣味上召唤小说的故事形态;而它出现的思想文化背景则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现实语境中的受挫有关。因此,这一小说思潮得以凸现的主要特征是:在叙事形态上拒斥它的抒情表意功能,重视日常经验的转述,由纯话语叙事转向模仿和故事叙事。若观察被视为“新写实小说”主要收获的一些作品,诸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方方的《行云流水》等,我们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叙述视角,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但聚焦于故事中的某个人物身上,让他起到替代叙事的作用。对于重模仿的小说而言,这一视角的叙事被称为“最佳叙述形式”[⑥]因为它的特征是“最大的信息量和信息提供者最小的介入”。[⑦]这种信息提供者即作者叙述人最小的介入,实际上造成了知识分子叙述人在文本中的缺席与退场,知识分子连同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成为“被叙”和“被审”的对象;传统文本中知识分子叙述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横捭阖,臧否时世,劝惩他人的风发意气消失了,批判与拯救的勇气没有了。小说写作成为作家记录公众日常生活的流水帐,在迷蒙、混沌的日常生活经验里,生活自身的逻辑代替了知识分子叙述人抒情、表意、达理的文本运行机制;散淡、灰暗的日常生活和低俗的生活趣味消解了诗性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生活,消解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一股低迷的文化失败主义情绪与氛围迷漫于“新写实小说”的天空。
《烦恼人生》是一篇单聚焦的作品,通篇叙述的是工人印家厚一天生活的流水帐,从文本结构上来说,不具有价值观上的对话性。作品的叙述张力存在于焦点人物内部,即是说,印家厚灰色的日常生活与他心灵中残存的梦想构成了这篇小说的真正叙述动机。小说的高潮应该是他收到一个叫江南下的同学写来的信以后,信中回忆起他们的知青生活和他以前的恋人聂玲。
印家厚把信读了两遍,一遍匆匆浏览,一遍仔细阅读,读后将信纸捏入掌心,他靠着一棵杨树坐下,面朝太阳,合上眼睛,透过眼皮,他看见了五彩斑斓的光和树叶。后面是庞然大物的灰色厂房,前面是柏油马路,远处是田野,这里是一片树林,印家厚歪在草丛中,让万千思绪飘来飘去。聂玲聂玲,这个他从不敢随便提及的名字,江南下毫不在乎她叫来叫去。于是,一切都从最底层浮起来了……五月的风里饱含着酸甜苦辣,从印家厚耳边呼呼吹过,他脸上的肌肉细微地抽动,有时像哭有时像笑。
现实与理想和梦的短暂交锋在他几乎麻木的心灵中引起剧烈的动荡。但他也只把这种动荡隐忍在心灵中,消解于心灵中。“少年的梦总是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认同了自己粗粗糙糙,泼泼辣辣的老婆,“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样呢?”只能自己安慰自己说,所经历的一切烦恼也是一个梦,“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这种单聚焦、单向度的文本,实际上放弃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叙述人自我张扬和裁判的权力,自觉认同于人物的价值观。所以蔡翔说:“《烦恼人生》预示着一种文化倾向,意味着知识分子开始不再沉湎于对这个世界的沉思冥想,亦不再对遥遥的彼岸充满一种神圣的渴望,而是直面人生的烦恼,开始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把现实和理想推向一个尖锐对立的人文环境,同时无情地拆除着所有附加于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装饰’,诗性消解了,浪漫主义消声匿迹,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普人的人生困境,而且尽可能真实地复制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⑧]这一评价是准确的,抓住了这篇作品及其所暗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的主要精神特征。
更值得解读的是她的另一个中篇小说《不谈爱情》。这篇作品选择了交叉性的限制叙述观点。聚焦人物一个是来自纯正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庄建非,另一个则是来自地道的武汉小市民家庭的吉玲。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的巨大反差本来不可能使两者走到一起,若用结构主义二项对立原则来命名的话,他们俩人分别代表语义关系中对立的两极S和反S。在这样一个平衡的对立关系中,若没有第三项的出现,平衡就不会被打破,那么也就没有故事发生。但事实上任何二项对立的设置,都会唤起人们潜在的打破这种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在对立存在的地方,人们就渴求着第三项的出现,而这第三项往往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潜在的行动力,常常代表着希望和理想,被赋予充盈的意识形态内容。那么,打破庄建非与吉玲之间平衡的第三项是什么呢?在吉玲是要逃出她的小市民家庭和有着耻辱印记的花楼街,过一种更文明的生活,她遇到了庄建非,通过对手的观察,她猜到庄建非来自另一个世界,于是她开始了她颇具心机的爱情攻势。而在庄建非则是由于他要为他汹涌的性冲动找到一个安全的归宿,特别在经历了与中年女人梅莹的性交往以后,打破了他对爱情所抱的浪漫幻想,看到吉玲颇有几分姿色,就自愿地在吉玲所布下的爱情罗网面前束手就擒。一个小家庭建立了,新的平衡出现了。在这一貌似平淡的故事中,一个重要的非常知识分子化的意识形态主题被解构了,即围绕爱情这一浪漫主义神话所形成的一套话语方式被颠覆了,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什么海誓山盟白头偕老,什么共同的革命理想都显得那样虚无缥渺,所谓爱情只不过是性的满足和一种务实的利用,因此是“不谈爱情”。
这篇作品还包括另一个故事段。小家庭的建立打破了旧的对立关系但同时建立了新的对立关系。虽然在庄建非与吉玲建立家庭的过程中,他们所代表的两种文化已初显锋芒,但必竞还没有正面交锋。两个人闹矛盾,吉玲住回娘家,吉玲的父母坚持非庄建非父母出面求情不回,于是两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交锋才真正开始,新的二项对立再次出现。那么打破对立的是什么呢?是庄建非的父母不得不放弃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向吉玲的小市民父母登门表示臣服。市民文化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自命高雅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在这一故事中,我们读到一个类似于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改造主题。这一主题大受对知识分子抱有敌意的王朔的欣赏,因此,在由他策划,梁天执导的同名电视剧中知识分子受到更为尖刻的嘲讽。
池莉以外,刘震云和方方的创作也是“新写实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在他们的代表作品《单位》、《一地鸡毛》(刘震云)和《风景》、《行云流水》中,我们不仅读到了知识分子叙述人在文本中的缺席造成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和精神立场上的退却,而且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站在客观立场,以冷静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实及思想意识所进行的审视或者说是自审,它让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叙述人在文本中退却的现实生活背景,是这一创作现实和文化现象的真实绵密的注脚。《行云流水》写一对教授夫妇有着良好的教养,有为事业献身,独立不倚的精神和人格,但经济上的贫困化,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世俗化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他们变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人格萎缩,生活与心理晦暗,酸腐可笑。这种在商品化社会中知识分子所受的“经济教育”与在“反右”和“文革”中所受到的“政治教育”(杨绛形象化地称之为“洗澡”)一样,对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在文化阵地上无法坚守。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就塑造了一个“反成长型”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小林开始时还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大学生,可经过几年的生活“教育”,他变成了一个“老婆能用微波炉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小市民式的角色。小林的思想经历是一个由理想、崇高向平庸、世故“还俗”的过程,与世俗性的环境不是表现为对立、抗争,相互改造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妥协、退让、互相调适的关系,这一形象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是极端世俗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与林道静、江姐这种“成长型”的英雄形象表现出的崇高与乐观主义精神,甚至与陆文婷、解净(《赤橙黄绿青蓝紫》)、何婵(《普通女工》)这些抗争型的平民形象所体现的柔韧坚定的朴素的人格力量相比都显示出从精神制高点上的极大退步。
小结
以上对限制叙事的简单论述力图避免从一般的审美意义上切入,而是试图挖掘这一叙事形态的现代文化意味。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以内聚焦为特征的限制叙事是小说致胜的法则吗?一度有人热烈地欢呼过小说的“向内转”,欢迎过“零度情感叙事”和“作者的退场”,甚至象萨罗特所说:“把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既有效又容易的方法”[⑨]?恐怕不是。首先,不折不扣的限制视角、作者退出文本是不可能的。“不折不扣的所谓内聚焦是十分罕见的,因为这种叙事方式的原则极其严格地要求决不从外部描写甚至提到焦点人物,叙述者也不得客观地分析他的思想或感受”[⑩]。其次,若重复上文的一个观点:限制叙事的大量集中出现是一个现代事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就新时期小说创作而言,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现象学哲学等对主体的重视和对主观真实性的倚重的文化思潮直接相关。九十年代以来,繁荣的市场经济创造出任何时代都难以遇目的新奇的社会景观与人文景观,加之以新的观念、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反思历史经验,因此一度“向内转”的新时期小说逐渐调整自己的“取景框”,更多的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和腾沸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小说的叙事形态上,以全知叙述切入的意欲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叙事规范已受到重视。第三,上文从几个方面的分析也表明,作者的退场与缺席带来的文化结果完全可能是破坏性的。
即使从一般的逻辑意义上,从价值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把握限制叙事,我们也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质疑:(一)限制性叙事的主要哲学与思想支点是,它比全知叙事更有可能达成叙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一观点是可疑的。事实上,局限着全知叙述人的所有因素几乎同时局限着替代叙述人和焦点人物,比如认知的局限性问题以及叙述人政治道德、文化立场问题不能不对替代叙述人造成限制和拘囿。“新历史小说”通过选择文化边缘人进行替代叙事,获得一种从民间立场审视历史的可能性。但有什么能证明“民间”更真实呢?若承认任何叙事都是一种主体性话语,任何“历史”都是“他的故事”(histroy his story),那么,民间也只能是一种叙事立场,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它也无法自名比别的立场更真实。韦恩·布斯说:“非人格化的叙述(即限制叙述,笔者注)可能促进本来认为正是它可以纠正的主观主义。对于努力使自己置身于自己作品之外的作者来说,努力消除明确评价的标志可能是特别危险的。虽然议论的确可能成为一种浮夸的主观流露的手段,但是在某些作者那里,构造这种议论的努力,却正好能够在作者的脆弱自我与他要使作品成功就必须创造的那个自我之间,创造一道合适的屏障。”[(11)]细究起来,这话是不无道理的。
(二)选择谁来作替代叙述人或聚焦人物同样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和伦理性。华莱士·马丁说:“一般说来,我们的同情是被那些我们了解其思想的人唤起的”[(12)],布斯也说:“选择了讲述这个故事的小说家不能同时又讲那个故事;他在把我们的兴趣、同情或爱慕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时,必须排除我们对其他人物的兴趣、同情或爱慕。艺术模仿生活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正象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必然对除了我自己或至多自己最亲爱的人以外的一切人都不公正一样,因此在文学中完全公正是不可能的。”[(13)]这就是说,叙述人或焦点人物实际上代表了作家的同情,至少是兴趣所在。他们的叙述,他们的意识渗透或多或少是对自我行为和自己思想的一种辩护;而没有被选作叙述人或焦点人物的人则始终处于被藏匿、被遮蔽、被书写的状态,他们被叙述意识的光亮所遗漏,处于无名和被动的失语状态;他们的行动得不到宽宥和谅解。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带普遍性的倾向是“男性视点”所体现出的男权话语中心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刘恒的中篇小说《白涡》为例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白涡》叙述了一个颇具现代感的婚外恋事故。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周兆路是一个生活上中规中矩,工作中事业有成的中年人,而且在仕途上面临着新的升迁。这时,他的下级,年轻漂亮的少妇华乃倩向他发出了爱的讯号。面对这一新鲜的诱惑他充分地表现出一个中年人的犹豫不决,既渴望冒险,渴望性的占有,又觉得愧对家庭,有违自己正人君子的人格,还害怕成为仕途上的障碍。在北戴河疗养时,他们共渡爱河。他有一种被毁灭的感觉。回到北京后,他尽力躲避着华乃倩,把每一次的幽会都看作是“最后一次”,但他最终也没能摆脱。这样一个婚外恋故事框架,在新时期小说中并没有多少新意,使这个平庸的故事变得不同凡响的我认为有两点。第一,作者避免了这一故事的道德主义倾向,也避免了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对人的“德性”和“兽性”的思辩性考察,而这两种文本在新时期比比皆是,而是通过这个故事“照亮”了“这一个”中年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灵魂幽秘,引发的思考既可能是道理伦理的,也可能是文化上的(有的批评者就认为是对“官木位”文化的思考),又可能是哲学和存在意义上的。我特别看重的是第二点:它的男性化本质。说穿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婚外恋或性冒险故事,女人只是个符号,是个“诱惑的夏娃”。作品选择了周兆路作为唯一的聚焦人物,他在婚外恋事件中的全部心理都是清晰的:犹豫、惶惑、焦躁、恐惧等等;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件事的道德态度也有一个条理的线索。事发后的惊异,渴望冒险又害怕惩罚,意欲脱离又总是被纠缠。因为他的被“透视”,因为有他清晰条理的心理过程作证,他让读者看到了他的灵魂:虚伪、怯懦。同时,他也为自己的灵魂作了辩护和开脱:他是个被动的失足者,是一个“被诱惑的亚当。”而华乃倩因为处在作品的聚焦之外却成了一个谜,一个陷井。对于周兆路来说,华乃倩因为她的诱惑者身份而成为一个陷井,而对于读者来说,却因为她整个心理的幽暗不明才是一个陷井。在故事中,华乃倩的心理被作者的叙述所遮蔽,除了语言和行为外,读者无法看到对其行为和语言进行支持的心理动机,因而她的行为——写纸条,对丈夫的苛薄,做爱时往大腿上抹防蚊油和她的言语——做爱时说“你真棒”,告诉周兆路丈夫阳萎等都在突出这个女人的淫荡和不道德性质。在她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夏娃的诱惑者品质,而且看到了夏娃身后的诱惑者蛇的品质:狡猾、贪婪、淫荡。无论是有意或者是无心,刘恒因为其男性视点(女性被遮蔽)再次重复了一个中国文学中的传统男权话语和男性意识形态主题:女人邪恶,女人是陷井。
注释:
(12)③ 均见《怀疑的时代》,载《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参见周宪为《小说修辞学》所写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⑤ 见《苏童文集·世界两侧·前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
⑥⑦ 见热拉尔·热耐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⑧ 见《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⑨ 同①。
⑩ 同⑥。
(11) 同④。
(12) 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 同④。
标签: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苍河白日梦论文; 红高粱论文; 读书论文; 烦恼人生论文; 棋王论文; 第一人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