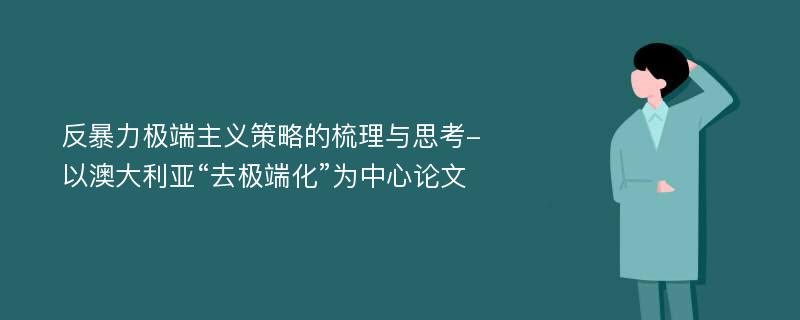
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梳理与思考
——以澳大利亚“去极端化”为中心
穆赤桑杰,兰 迪
(西北政法大学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陕西 西安710122)
摘 要: 反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强调“反激进化”的非强制性的“柔性”反恐怖策略,与目前主流的“刚性”反恐怖策略,即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模式”不同,该策略可以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改变促发恐怖主义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逐渐消除恐怖主义。基于严重的“内生性恐怖主义”问题,澳大利亚立足本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反暴力极端化措施,但是存在投入不足、针对性不强与风险泛化的弊端。我国当前面临的反恐压力较大,依据我国国情,可以有选择地借鉴澳大利亚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发展经验。
关键词: 反暴力极端主义;反激进化;去极端化
反暴力极端主义(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以下简称“CVE”)是当前世界各国、实务机构与理论研究者共同提倡的一种旨在通过非强制的方法来遏制恐怖主义蔓延、减少恐怖主义威胁的策略。该策略强调“反激进化”(Counter-Radicalisation),即通过综合措施来减少对社会、国家充满怨恨情绪的或者已经为极端主义激进化的个人跨越行为边界、蜕变为一名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激进化”与“反激进化”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语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含义。概念的不确定性浸透在应对策略的制定与执行当中,也就难以避免“CVE”自身的准确性欠缺与中心目标失焦。例如,有的国家将“CVE”的目标设定为改变一个人的极端行为或者极端思想,有的国家则认为应当行为与思想同时兼顾地“去极端化”,还有的国家认为应当从更为宏观的重塑社会整体凝聚力的角度切入。然而诸多基于不同导向的“CVE”都难以准确地告诉人们,“它究竟想反对什么”,以及“如何实现”。
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策略谱系,在制定“CVE”的过程中应明确其核心概念,并围绕这些核心概念构建起一个整体框架,便于执行者准确理解策略的内涵与精神以便认真贯彻,同时还要建立事后的、科学的策略效果评估体系,以利于及时检验执行策略方法的有效性,为后续的完善和改良提供镜鉴。在诸多“CVE”当中,澳大利亚的相关反恐怖政策极具代表性。特别是,为应对本国的暴力极端主义问题,澳大利亚在2010 年以后实施了大量的“CVE”项目,这些项目很好地展现了“CVE”在现实中是如何发生作用产生影响的。澳大利亚“CVE”的实践经验能够为我国的反恐怖策略的完善提供借鉴。
在完成钻孔施工作业以后,应立即开展清孔作业[5]。如果钻孔和清孔工作间隔时间较长,孔内底部的位置就会出现沉淀的情况。一旦沉淀厚度较大,还会出现混凝土夹层的现象,直接增加清孔作业难度系数。而在清孔作业阶段,要想规避塌孔与相关问题的发生,就要确保孔内部水头稳定性。
一、反暴力极端主义的源流
(一)传统反恐怖模式与“本土恐怖主义”
从以打击和消灭为核心的传统反恐怖手段转变为采用“CVE”的“柔性”策略,是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在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以后,由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模式”成为反恐怖的主流。该模式倡导以强硬手段给予恐怖分子“迎头痛击”,具体包括三个特征:广泛运用的军事手段、日益扩张的警察权限和无处不在的情报搜集。
“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暴力的威胁给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挑战。在由多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推进下的暴恐组织中,圣战组织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最主要威胁。为应对这种威胁,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依凭军事手段来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占据了全球反恐怖策略的主流。这些措施包括打击和预防,前者分为追捕、斩杀和截断,后者主要针对重点人物和基础设施进行防御。但是,在反恐怖策略的建构与实施环节中,均无暇顾及如何改变促发恐怖主义问题的环境。”[1]
(3)关于提供必需的施工材料。从目前来看,水利施工必需的各类施工材料通常应当包含水泥、混凝土骨料、钢材与其他施工材料。在这其中,混凝土骨料应当构成水利施工监控的要点。具体而言,投标人有必要承担全面运送混凝土骨料的相关操作,并且限定于7千米以内的最大运输距离。除此以外,关于现场施工还需配备粉煤灰、岩石炸药、砂石骨料与其他各类施工材料。依照目前现存的采购材料标准,对于上述各类材料都应当将其置于全方位的施工控制视角下,并且给出可行性较强的材料采购管理以及其他管理措施。
然而,2005 年左右,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的“本土恐怖主义”现象(Homegrown Terrorism),这给反恐怖政策制定者的认知和观念带来了较大冲击。以英国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爆炸案和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爆炸案为例,暴恐案件的策划者与实施者多为本国“土生土长”的公民,他们与“基地”组织这样的国际大型暴恐组织的联系是单向的,甚至没有联系。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恐怖主义的梦魇依然挥之不去,但是“内忧”的威胁远大于“外患”。有鉴于传统的军事打击难以适用于本国的恐怖分子,过分关注安全的现实导向为自由与人权的根本保障蒙上一层阴霾,更加关注社会根源性要素对恐怖主义影响的“CVE”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
2.社区参与计划
(二)欧洲的反暴力极端主义模式
率先行动的是欧洲。2003 年,英国制定的新的反恐怖纲要突出了恐怖主义预防工作的核心地位,即反恐怖应当首先致力于阻止人们加入恐怖组织,或者支持恐怖活动。2004 年3 月25 日,欧盟的《反恐怖宣言》首倡“CVE”策略,同年的《欧盟反恐怖行动计划》再次重申了将“CVE”应用于反恐怖活动的重要性。欧盟理事会亦在2006 年建立了反暴力极端主义专家小组。“激进化”开始受到理论界的一致关注。“在过去十年里,围绕个体是如何成为一名恐怖分子的研究都被贴上了一个简短的标签——‘激进化’。在今天,探讨恐怖分子心理活动的学术研究如果不涉及激进化就根本没有办法进行。”[2]“去激进化”的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欧盟的系列政策文件之中。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在应对21世纪汹涌澎湃的新恐怖主义浪潮中,当前的反恐怖行动无论是认知抑或实践尚处于早期阶段,打击手段是必要却非决定性的。只要促使个人蜕变为极端主义的信奉者和恐怖分子的诸多环境要素和条件要素没有被消除,宣称战胜恐怖主义的时机还远未到来。
(三)美国的反暴力极端主义模式
自2009 年以来,美国反恐怖政策走向出现变化,美国政府开始接受并采用“CVE”的主张。2011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新反恐怖政策,这是美国反恐怖策略变迁之标志。同年8月,联邦政府出台《赋予美国的地方合作者以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之权限行动计划》,该计划指出:“美国政府最为有效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办法,就是强化地方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在反恐怖行动中,美国政府主要扮演计划的推动者、会议的召集人与情报信息的提供者等三重角色。”[3]
二、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总体构成
(一)“公共健康模式”对反恐怖的影响
1.“公共健康模式”的提出
西方国家在建立“CVE”的总体模型时主要参考了“公共健康模式”(The Public Health Model)。在西方,“公共健康模式”主要是作为一种疾病预防的策略而提出的,起先被用于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中。与传统治疗慢性疾病方法不同,“公共健康模式”旨在将确定的方法进行分类和组成,进而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产生积极效果。该模式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预防,即寻求能够减少由该疾病引发的新案例数量的方法。第二层次是干预,即努力降低已知病例在当前人口中的比率。第三层次是遏制,即降低由该疾病导致的严重后果(例如死亡或者残疾)的数量。
2.“公共健康模式”的应用
“公共健康模式”在医学领域的成功促使其能够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得到运用。例如在危及公共安全的醉酒驾驶问题的治理活动中,运用“公共健康模式”原理可以将解决策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针对一般对象而实施的旨在降低潜在问题行为的方法,例如宣传和教育项目。第二层次是针对显露出有实施醉驾风险的人的早期干预,当某个人表现出某种特定征兆(例如惯常酗酒)即可以成为第二层次干预的目标。第三层次是针对已经实施了醉酒驾驶的人的治疗模式。“公共健康模式”的体系化思考方法为社会治理模型的整体建构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4]。
当前,很多实务机构与理论研究者都非常关注将这种“公共健康模式”运用到“CVE”策略中的可能性。其中一个支配性的理由是,“公共健康模式”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路,运用该思路对各类具体项目进行合目的性的分类,有利于在“CVE”的谱系中进行梳理和检验。
(二)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基本结构
1.一般化预防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我们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一是组织严密,二是纪律严明,三是信仰坚定。正是这3个因素,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代表、道德楷模、精神源泉和希望所在。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军队与党水乳交融,军队形象几乎成了党的形象的缩影。因此,锻造坚强有力的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标杆作用,是军队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高战斗力的基础工程,必须持续抓好。
鉴此,村落民俗志书写是不能不将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的。就学科传统而言,历史学追求对“真相”的探索,其研究强调证实或辨伪,而民俗学则关注民众文化的记忆、传承与运用。真正意义上的村落研究,不仅是要呈现被遮蔽已久的村民生活与文化,还要呈现村民的文化实践及价值建构的过程。遗憾的是,后者至今仍为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众多学人所轻忽。
(1)丹麦经验。2009 年丹麦发起了一个名为“共同和安全的未来:预防极端主义以及极端主义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蔓延”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减少青少年激进化的条件,并且加强全社会应对极端主义的能力。丹麦政府还向社会广泛发放宣传教育手册,帮助社会公众了解极端主义,强化对极端主义的警惕性。
早期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主要从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展开。2005 年9 月,维多利亚州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地方政府层面的反恐怖计划,即“保护我们的社区并应对恐怖主义的根源”。该计划借鉴了荷兰与英国的经验,强调采用有效的反恐方法,包括预防行动、铲除根源、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宣扬行为等。
(3)澳大利亚经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基金会制定的“社区认知训练项目”,即教育社区的意见领袖、教师、父母和年轻人了解激进化与暴力极端主义。该项目同时为警察提供培训,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掌握风险识别的技巧,为相关执法活动进行宣传教育。2015年2月,澳大利亚还发起了一个“极端分子对话项目”,即发动前极端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现身说法”,以促进全社会共同抵制暴力极端主义。
2.风险干预
第二层次即“风险干预”,即为那些显示出极端化迹象的人提供帮助,对象包括参与了有极端分子存在或者极端分子施加影响的社交网络的人,或者通过言行表达了对某一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的人。上述人员一般处于极端主义群体的边缘,或者虽然参加了恐怖组织但尚未实施恐怖活动,他们具有实施暴恐行为的极高风险,但是通过早期干预行为能够提前将暴恐袭击的“萌芽”扼杀在“摇篮”中。针对上述“危险的个体”实施的干预和帮助以对象自愿为原则。同时干预项目还包括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项目,项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识别“风险的个体”和如何为“风险的个体”提供帮助。
(1)挪威实践。在挪威的“反对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预防性谈话”是该计划的重要措施之一。谈话的一方是承担极端主义预防职责的警察和工作人员,另一方是参与了极端组织或者从事极端主义行为、表露极端主义征兆的个人。“预防性谈话”的启动可能是自愿的或者强制的,谈话的目标是对干预对象的人生定位和行为改变提供必要的指导。但是谈话并不隶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而言,谈话要求对方的家庭成员也参与其中,谈话中获得的信息可以提供给相关社区工作人员以便于开展后续的社区工作。“风险干预”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干预者与干预对象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即“建设性优于责难”。
(2)丹麦实践。不同于传统针对极右翼极端分子的反暴力极端主义措施,当前“CVE”面临的挑战是要应对参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当中的人,以及受到极端组织蛊惑尝试前往或者曾经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人。与挪威相似,丹麦的“安全与情报部”也建立了一个带有预防性质的“退出谈话”计划,针对的是那些与极端组织存在联系的年轻人。该项目指派的专家会同有极端风险的个人进行面对面的谈话,通过指导和鼓励帮助对方改变旧认知、建立新认知,以远离极端主义。
第一层次的“CVE”主要聚焦于“一般化预防”,方法是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指导社会一般人了解暴力极端主义的危害,并通过社会治理根除导致个体激进化的条件。“一般化预防”也会利用现有职能部门和机构进行专门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帮助心理学家、社区工作者、健康护理人员和教师了解和掌握处理激进化的方法。
在临床上,在排除其他原因的前提下,糖尿病患者出现与周围神经功能障碍有关的症状或体征,且以四肢远端感觉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病症,即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1]。该病症是糖尿病患者的严重并发症,其可诱发坏疽、溃疡、患肢感染等,严重时还可造成患者截肢,因此及早诊断和治疗意义重大[2]。本文选取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50例,按照其有无周围神经病变分为观察组1和观察组2,同期选择健康体检者25例为对照组,即对高频超声在诊断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探讨,现报道如下。
(3)德国实践。德国柏林在2011年实施了一个以预防当地年轻人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目的的项目,该项目主要为那些可能会前往国外成为“外国战斗人员”的家庭和社区提供帮助,该项目提供24 小时的咨询热线,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和社区提供服务。
3.去极端化
第三层次即“去极端化”,即帮助已经被认定为极端分子的人脱离暴力极端主义的关系网,并阻止其进一步的暴力行径。这种干预措施能够为起诉和监禁等强制手段提供一种可替代性的“柔性”办法。
需要注意的是,“去极端化”(De-radicalization)有别于“脱离”(Disengagement)。“脱离是一种行为的改变,即不再参与恐怖组织或实施恐怖活动,但并不意味着他的观念会发生改变。最低限度的脱离是一次暴力行动的暂时停止。脱离既可能是出于个人或组织的自愿,也可能是被迫。去极端化则代表着个体或者组织不再将暴力视为追求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合法方式,去极端化是一个阶段。”[5]
2005 年伦敦连环爆炸案后,伴随着“基地”组织鼓动下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澳大利亚政府在传统的军事打击以外,开始注重非强制的“柔性”手段在反恐怖中的运用。2005 年9 月27 日,澳大利亚政府的部长理事会举行特别反恐会议,提出建立旨在促进社会凝聚力、和谐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主要为83个具体项目提供资助,指导思想是:恐怖主义是社会内部分裂与对立的产物,通过恢复和促进社会整体凝聚力,能够构筑起遏制恐怖主义发展、减少恐怖分子威胁的预防体系。
(1)退出。“退出”计划是第三层次具有代表性的“CVE”项目。帮助和支持个体退出极端主义组织和群体的尝试最早始于20 世纪70 年代的欧洲,目的是帮助个人脱离极右翼极端组织。
1998 年,瑞典建立了著名的退出计划,即推动个人退出新纳粹组织,并实现由极端分子到普通公民的过渡。该项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动摇他们坚持的极端主义观念,并且通过组织来帮助他们重建社会关系网。该项目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参与了“白人力量运动”的极端分子,年龄在18 岁至25 岁之间,退出项目的期限为2~4 年。瑞典的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曾经对该退出计划的效果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通过该项目获得帮助的133名前“白人力量运动”组织的成员中,94 人成功地离开了该组织。瑞典根据该项目的经验,建立了一个“亚文化防范中心”,以开发风险防范、风险干预和去极端化方面的措施。
(2)矫治。第三层次的“CVE”去极端化措施还包括对实施了恐怖主义犯罪和极端主义犯罪的罪犯的矫治。典型代表是澳大利亚的“社会融入支持项目”(The Community Integration Support Program,简称“CISP”),该项目旨在对被监禁的暴力极端分子进行改造。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也有类似的实践经验。
三、澳大利亚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实践
(一)2005年以前的澳大利亚反恐模式
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案和2002 年的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后,澳大利亚的反恐怖策略重点强调打击与防范的强制性措施。在阿富汗,澳大利亚展开了“永久自由”的军事行动,在本国,大量的资金用于建设和扩展国内警察机构与情报机构的安保能力。澳大利亚颁布了新的《反恐怖主义法》,同时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建立“国家反恐委员会”(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负责一切反恐怖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相较于将恐怖主义视为经济、历史、政治、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的观念,堪培拉更愿意将恐怖主义视作单一维度的产物——恐怖主义主要是伊斯兰自己的问题。”[6]
当前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正式形成于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反恐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联邦应当与地方展开合作,制定新的反恐怖政策。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当前澳大利亚国家反恐怖政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已经被视为由专门的国家安全部门制定并执行的一种专业手段。”
(二)澳大利亚的早期反暴力极端主义模式
1.指导思想
粉条本质上是由直链淀粉基微晶连接而形成的三维网络结构,经干燥过程淀粉凝胶网络发生皱缩,变成淀粉浓凝胶的干制物[17]。将粉条置于沸水中烹煮时,凝胶逐渐吸水,非结晶区发生水合作用导致凝胶网络膨胀,随着烹煮时间的延长,凝胶网络逐渐崩解,因此小的凝胶碎片和可溶性成分会随之渗入水中,汤液变浑,导致煮后粉条质量下降[18]。
果蔬加工工艺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果蔬加工工艺的基础知识以及各种果蔬加工技术的原理、工艺及操作要点。在内容深度上,侧重于基本原理及工艺[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在理解各种加工原理的基础上,运用其方法掌握不同果蔬的加工技术,能够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和需求,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在2005 年的8 月,联邦政府还召集本国主要穆斯林社区的领袖举行会议,在会议后建立了“与穆斯林社区有关事务小组”,该组织的职责是为促进穆斯林群体的社会融入、预防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建言献策。但是,该事务小组面临着持续性的批评,例如小组的组成不能够代表澳大利亚本国多样化的极端群体;该小组的工作不能为极端主义因素施加影响,相反,该小组提出的建立由官方支持的“温和穆斯林”计划实际却在破坏穆斯林领袖对政府的信任[7]。
7月上旬用插秧机插秧,每插秧苗5 m,留鱼道1 m宽。水稻品种要选择叶片开张角度小,抗病虫害、抗倒伏且耐肥性强的紧穗型品种,如早籼807[7]、中早39、晚稻201、丰两优香一号等。环沟中安装诱虫灯4台,将水稻害虫诱集并被水产动物摄食。
3.地方实践
(2)加拿大经验。加拿大实施了一个针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保护项目,鼓励本国青少年参与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事务中。项目对象的年龄一般在14 岁至30 岁,方法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和社区组织授课和演讲,同时还发放反极端化的教育指导手册,例如“为处于人生困惑者的指导”“青少年网络爱好者的危险:源自网络的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等等。
抽水井非达西流问题两种数值模拟方法比较研究……………………………… 王志海,徐 亚,闫俊岭等(17.53)
2006 年维多利亚州发布了全新的反恐计划,即“一个安全的维多利亚:保护我们的社区”,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跨文化、信仰交流平台,鼓励社区参与的反恐行动,以及对反恐学术研究的资助。维多利亚州的“柔性”反恐怖措施为澳大利亚整体反恐怖措施的改善提供了借鉴。
(三)陆克文政府时期的反暴力极端主义模式
2007 年陆克文政府上台,反恐怖策略开始全面倒向反暴力极端主义模式。2008 年,联邦司法部部长Robert McClelland 指出,有必要以英国的预防战略为榜样,在加强与相关机构、部门和组织合作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些新的策略和手段帮助澳大利亚抵御极端主义的侵袭。同年,新的国家层面的反暴力极端主义机构建立,即“反暴力极端主义分委会”(Violent Extremism Sub - Committee,简 称CVESC),CVESC 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各州警察机构和联邦警察机构、第一部长办公室、多元文化事务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代表,机构主要负责全国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制定和实施[8]。
为避免资源重复浪费,并将现有资源最优配置于最需要的关键领域,CVESC 成立后提出了一个国家级别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基本框架,该框架提出了澳大利亚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四个基本目标:(1)识别与改变:甄别暴力极端分子,改变他们的极端主义观念和暴力恐怖行为,为他们脱离极端主义环境提供必要的帮助。(2)发现与支持:尽早发现有暴力激进化风险的个体,为他们提供早期干预措施,避免他们陷入极端主义环境。(3)构建与保障:全面提升社会应对极端主义的能力,保障社会的和谐、自由,消除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4)沟通与挑战:畅通社会不同群体与政府的沟通渠道,挑战恐怖分子的极端意识形态并通过多种渠道为社会公众提供可替代的文化产品[9]。
(四)2010年至今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
人力资本可以划分为:员工拥有知识的多样性;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员工的受教育背景或者高学历员工的比例;员工的基本技能;员工的学习能力或工作经验。
2015 年澳大利亚《联邦反恐怖行动述评》中将“反暴力极端主义”定义为“澳大利亚采取的旨在预防个体激进化并最终实施包括基于政治、社会或者意识形态目的实施暴力的恐怖主义行径在内的暴力极端行为的方法,该方法应当同时尽可能阻止个人预备实施恐怖主义支持行为和实行行为”。
2010 年7 月1 日,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接管反恐计划中的保障社会和谐与凝聚力项目。该项目原由移民与公民事务部负责,已成为目前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策略体系的主要措施。联邦政府亦解散了“与穆斯林社区有关事务小组”,不再采用单一机构而是用非正式的分散的方法来保持与穆斯林社区的沟通。另外,在《反恐白皮书》发布不久,司法部也发布了两个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计划,分别是“建构社会凝聚力和监督青少年项目”(该项目之前由新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性工作)和“提升社会应对极端主义能力项目”(该项目的运作时间为四年)。当然,上述项目的实施也再一次说明,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应当被纳入更为广泛的社会治理层面。
自2010年7月以来,共计87个独立的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澳大利亚国内实施,这是澳大利亚反恐怖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10]。
四、澳大利亚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缺陷与改进
(一)澳大利亚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缺陷
1.“风险干预”和“去极端化”的投入力度不够
澳大利亚的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策略主要集中在第一层次的“一般化预防”中,而在“风险干预”和“去极端化”层面的投入明显不够。据统计,仅有约13%的“CVE”项目直接为那些暴力极端分子或者具有激进化风险的人提供干预措施。
2.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针对性不强
澳大利亚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将构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视为遏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根本途径,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缺乏针对性,多数的预防努力都比较分散,部分项目与其他的“CVE”措施有重叠,且大多数项目主要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很少能够对暴力极端主义施加直接的影响,这严重影响了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效果。
3.“风险”认定泛化带来风险
在“谁是极端分子”或者“谁有可能被激进化”的“风险个体”甄别与认定方面,澳大利亚反暴力极端主义措施主要是根据地理和人口统计方面的知识来实现的。澳大利亚政府非常关注那些被主流社会排斥的特定区域。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些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具有显著的激进化风险,因为他们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低,且具有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背景,与主流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可能对社会存在怨恨情绪,容易被极端组织所利用和蛊惑。
这种过分宽泛的认定方法依据人口组成和地理学因素将反暴力极端主义的注意力集中于广泛的区域而不是将干预目标精准地限定于具有激进化可能性的个体,最终导致两个严重的问题发生:
第一是将许多人错误地设定为干预目标。实施暴恐活动的恐怖分子毕竟是极少数人,若缺乏精准判断依据的识别和干预,则可能错误地将大多数人纳入体系之内,也有可能遗漏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无法阻止其滑向极端主义。
第二是“风险个体”认定扩大化导致了被认定群体的污名化与标签化。不少澳大利亚当地的穆斯林认为,“CVE”是主要针对大多数的温和穆斯林的,现有策略实际是将本国穆斯林视为国家安全的问题,从而导致穆斯林整体的边缘化。被当局视为正当化的识别与干预措施,容易被穆斯林群体视为国家对该族群的监视和不信任。
当然,公平地讲,这一问题并非澳大利亚独有,在英国、荷兰与德国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此,作为一种非强制的“柔性”反恐怖策略,反暴力极端主义的边界也应当有更为清晰的界定,其目的应当更为明确。
(二)澳大利亚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完善
1.增加反恐怖政策的针对性
2010 年的《预防策略评估报告》指出,未来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体系,应当更为清楚地区分哪些社会治理策略是针对恐怖主义问题产生作用的。2011 年《反恐怖新战略》规定,未来的恐怖主义预防计划与社会和谐计划应当各自独立,内政部将主导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措施。
论文数据来源为民政部2017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CLIFSS),数据抽取江苏、吉林、甘肃、山西、湖南、云南六个省份,然后采用分层抽样,依次抽取3个州(市)、9县(市、区)、18个乡镇(街道)、36个村(社区)、540户低收入家庭(低保户或低保边缘户),总样本量为3240户。调查问卷从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生活情况、社会救助与相关服务、态度与意愿四个方面进行调查。对地方民政部工作人员进行入户与调查问卷培训,并派督导进行实时陪同指导,保障数据的科学性。
2.加深项目执行机构的多元化程度
DICSSAC一次冷却的喷射式凝汽器体积很小,可就地布置在距离主排汽管最近的位置,极大地减小排汽管长度,大大减小排汽压损。
澳大利亚政府鼓励由不隶属于警方和地方政府的社区发展相应的反暴力极端主义措施。特别是一些国家缺乏有效沟通渠道的社区和群体,需要这样的社会组织充当社区与政府、警方对话的桥梁。《国家反暴力极端主义评估报告》亦指出,大量的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CVE”工作已经强化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未来需要通过加大资金投入的方式来维持这些比较成功的项目,同时还要加强资源的优化配置。
关联规则挖掘是数据挖掘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传统算法是将多个关系连接成一个泛关系表。这种算法存在着性能较低、统计偏斜和信息丢失等问题。针对性能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元组传播的思想,提出了一些避免多表间直接连接的算法。但是,这些算法一般都是针对星型模式或者雪花模式的数据库,不可以直接应用于更加广泛的实体联系模式的数据库。另外,这些算法存在着统计偏斜问题。基于ILP(归纳逻辑程序设计)技术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可以避免统计偏斜问题,但是存在着效率低、可扩展性差等问题。
3.增加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投入
当前的“CVE”项目主要侧重于第一层次的预防,由于缺乏直接的反恐怖效益而充满政治风险。除了几个第一层次的新项目以外(如2013年启动的“网络反暴力极端主义”和“社区反暴力极端主义叙事”),未来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将重点支持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项目,例如改善风险识别与评估项目,为脱离项目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为地方社区工作者提供职业培训,建立家庭支持计划,等等。
参考文献:
[1][5]Rohan Gunaratna,Jolene Jerard,Lawrence Rubin.Terrorist Rehabilitation and Counter-Radicalisation:New Approaches to Counter-Terrorism[M].New York:Routledge,2011:1,27.
[2]John Horgan.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M].New York:Routledge,2014:82.
[3]The White House. Empowering Local Partners to Prevent Violent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R]. Washington: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1:3.
[4]Mrazek p,Haggerty. R. Reducing Risks for Mental Disorders: Frontiers for Preventative Intervention Research[M].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4:19.
[6]David Wright-Nevile. Fear and Loathing: Australia and Counter-Terrorism[J].International Terrorism,2005,156(2):2.
[7][8][9][10]Shandon Harris-Hogan, Kate Barrelle ,Andrew Zammit. What Is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Exploring CV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Australia[J].Behavioral Sciences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Aggression,2015,8(1):6-24.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192(2019)02-0043-06
DOI: 10.19536/j.cnki.411439.2019.02.008
收稿日期: 2019-02-26
作者简介: 穆赤桑杰(1992— ),男,西北政法大学2017 级刑法学(反恐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反恐学;兰迪(1985— ),男,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犯罪学、反恐学与中国刑法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去极端化视域下的‘柔性’反恐怖策略研究”(17CFX019)。
责任编辑:时 娜
标签:反暴力极端主义论文; 反激进化论文; 去极端化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