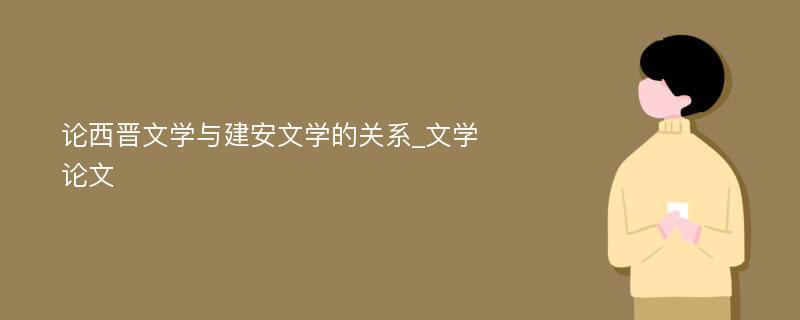
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西晋论文,文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西晋文学在时间上紧接着正始文学而来,但后人在论及西晋文学时,却很少讨论西晋文学与正始文学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多地将西晋文学与前一阶段的建安文学联系起来:“曹子建、陆士衡,皆文人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在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萧绎《金楼子》)“至於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颜延之《诗者古之乐章》)“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效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少论家更进一步指出二者之间的承传关系:“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沈约《谢灵运传论》)“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条。”(裴子野《雕虫论》)钟嵘《诗品序》论西晋文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踵武,即追踪;前王,即指建发三曹。《诗品》在讨论西晋诸子的文学创作渊源时,更具体地指明:陆机“源出於陈思”,潘岳“源出於仲宣”,左思“源出於公干”,张协、张华、刘琨则“源出於王粲”。“晋之辞意,瞻望魏采。”(《文心雕龙·通变》)“晋氏之风,本之魏焉。”(徐祯卿《谈艺录》)“晋诗渊源,其在魏乎!”〔1〕可见, 建安文学为西晋文学的渊源,已得到历代论家所公认。
作为一前一后的两个诗歌高潮,它们所处的背景,无论是时代特质、社会风气、还是文坛状况,皆有颇为相似之处。文学理论的建构更有一脉相传的发展。
一
汉末乱世,群雄并起,三分天下,逐鹿中原。雄心勃勃的曹魏集团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建安后期,曹氏兄弟争夺太子之位,造成曹魏集团分裂,随后司马氏的崛起,更使魏国内部形成倾轧争权的混乱局面,而对外争霸天下的战争亦始终延绵不绝。
西晋初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政局的安定,整个社会经济开始了全面的回升,并且在太康年间呈现一派“世属升平”(《晋书·食货志》)、“民和俗静,家给人足”(《晋书·武帝纪》)的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杨骏、杨皇后专权, 内乱开始。次年,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党徒数千人,进一步引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2〕。 接着便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3〕及加速西晋王朝覆亡的“永嘉之变”〔4〕。
可见,建安和西晋时期,都曾有过一阵子繁荣、辉煌的景象。但在其后,又都同样是走向混乱。这麽一种时代特质,从一正一反两方面刺激了文人的心态及创作;而正始时期,正处於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内乱白热化之际,杀戮惨烈,名士难以自全。这种极度黑暗的局势,较大程度地窒息了文学的发展,促使文人转向玄思哲理的探求,以期从中寻获精神的慰籍与解脱。
在儒学式微、纲常崩溃的汉末建安,个体意识与情感得到极大的张扬,形成了重情、以悲情为美的社会风气。正始名士未必不重情、亦不乏悲情抒发,但是,对玄思、尤其是对“圣人之情”的追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重情、尤其是以悲情为美的风气。他们的感情抒发,也往往带有较大程度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虚幻性。西晋初期,在奉名教为正统的司马氏压制下,玄学一度沉寂。文人更直面於现实人生,执着於个体自我。元康之后兴起的郭象玄学应时而变。其关注的重心也转回到现实万物之中:“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郭象《庄子·齐物论注》)效仿、追求“圣人之情”的作法也受到否定:“法圣人者,法其迹耳。”(郭象《庄子·祛箧注》)“人各自正则无羡於大圣而趣之。”(郭象《庄子·德充符注》)从而加强了人们对自我本体的执着及个人情感的抒发:“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於近情。”(《晋书·裴顾传》)“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卫夫人《笔阵图》)“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而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晋书·王衍传》)“感生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石崇《金谷诗序》)“秋夕兮遥永,哀心兮永伤。”(夏侯湛《秋夕哀》)“置酒高尚,悲歌临觞。”(陆机《短歌行》)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悲情抒发,继建安之后,又再次蔚然成风。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既是政坛领袖,又同时是文坛领袖,大兴文学,身体力行,并团结、带动了“建安七子”等一批文人,组成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或著书立说,探讨文道;或书信往来,切磋技艺;或置酒乐饮,吟诗作赋。从而形成了建安文坛的繁荣局面。而正始之际,虽也有“竹林七贤”名士集团,但其活动主要是溺酒啸游;其文笔交往,也主要是论玄证道。
西晋时期,也先后出现过较松散的文人圈子。西晋初年的张华居高位而“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於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张华传》)陆机、陆云和左思等皆受张华的赏识提携而扬名文坛:“(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破,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晋书·陆机传》)“司空张华见(左思《三都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有更新。’於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元康年间,贾后专权,贾谧参政。贾谧以其政治上的权势,聚结了一大批中青年士族文人,如石崇、潘岳、陆机、陆云、欧阳建、缪征、杜斌、挚虞、诸葛诠、王粹、杜育、邹捷、左思、崔基、刘瑰、和郁、周恢、牵秀、陈畛、郭彰、许猛、刘讷、刘舆以及刘琨等,世称“二十四友”。这个文人集团,虽尊贾谧为首,但石崇却是实际上的关键人物。尤其是文学多以石崇为中心进行:“(石崇)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即石崇)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往,令与鼓吹递奏。逐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石崇《金谷诗序》)金谷所赋之诗,除杜育《金谷诗》二首,潘岳《金谷集作诗》一首外,其余已经散佚。但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录,当时的文人曹摅、嵇绍、枣腆、曹嘉、欧阳建等与石崇赠答诗共有13首。此外,该集团的讲史活动,也有较浓重的文学色彩:“诸名士共至洛水戏,……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世说新语·言语》)“税驾金华,讲学谧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陆机《讲〈汉书〉诗》)这种登临游览、芳风雅宴、丝竹诗赋、吟咏赠答的风气,显然颇有建安邺下文人集团之遗韵。张华、石崇(及贾谧)皆身居高位,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对聚结文人,形成文人圈子,确实起了较大的作用。这一点和建安时期“魏武以相王之尊”、“文帝以副君之重”、“陈思以公子之豪”(《文心雕龙·时序》)来团结文人颇为相似。
从文人的创作实际看,不仅有名重一时的“太康之英”(锺嵘《诗品序》)陆机,还有张华、张协、张载、潘岳、左思等皆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时间才俊云蒸,各竞新声,大有曹子建所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盛况。诗、文、赋的数量不仅远远超於前代,艺术上更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详见下文),惟其如是,才形成“晋世文苑,足俪邺都”(《文心雕龙·才略》)的文学繁荣局面。这样一个繁荣局面,绝非阮、嵇“异翮而同飞”(同前)的正始文坛可以比拟的。
二
专注於玄理思辨的正始名士,极少有文学理论的探讨。降及西晋,探讨文学理论的风气才开始兴起。
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吴书是大业,既可垂不朽。”陆机也曾作子书未成,临终时叹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见葛洪《抱朴子》)二陆不仅以史书和子书为不朽事,同时也十分重视一般诗文创作。陆云就认为陆机的文章“已足垂不朽”(《与兄平原书》),并劝陆机拟和“清绝滔滔”的《九歌》,不然,“恐此文(指《九歌》)独单行千载”(同前)。陆机《文赋》末尾也称文章(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可以“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西晋文人以作文(包括史书、子书及一般诗文的创作)为垂名千载的不朽盛事,显然是受了曹丕文章不朽观念的影响。西晋时,出现了不少诗文总集,如傅玄的《七林》、荀勖的《晋歌诗》、《晋燕乐歌辞》、荀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还有挚虞集汇诸体文章的《文章流别集》。这些诗文总集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西晋文学的繁荣,更体现了西晋文人对文学的重视,及对文学体裁特征的深入认识。
对文学特质的考察,西晋文人普遍持审美的态度,如陆云便说:“文章当贵经(轻)绮。”在评论具体文章时,也常以“美”(绮)为标准:“省此文甚自难,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绮。”“《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祠堂赞》甚已尽美,不与昔同。”“《吊蔡君》清妙不可言,《汉功臣颂》甚美。”“《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武帝赞》如欲管管流泽,有以常相称美。”(皆见《与兄平原书》)又如傅玄曾论连珠体:“其文体,辞丽而言约,……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傅玄《连珠序》)皇甫谧则论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皇甫谧《三都赋序》)夏侯湛评张衡赋则云:“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若又造事属辞,因物兴口,下笔流藻,潜思发义,文无择辞,言必华丽,自属之士,未有如先王之善选言者也。”(夏侯湛《张平子碑》)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是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文人“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主张,集中体现了西晋文人对诗歌特质的审美追求。
陆机《文赋》在论及感情的抒发时曾说:“或奔放以谐合,务嘈瓒而妖治。徒悦目而偶俗,故声高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而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在这里,陆机对“情”的抒发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妖冶之情品调低下,固然不足取;但《防露》《桑间》之类的亡国之思,虽悲却不雅,亦不足论。“雅”有“雅正”之义,当指情感的健康、美好而言,可说是指情感表现的内涵美。仅是“雅”仍未能尽善尽美,所以,陆机进一步提出“艳”的要求。“艳”指描写、表现情感的文辞而言,可说是情感表现的外在形式美。“雅”而“艳”,便是陆机情感表现论的最高审美标准。可见,在“诗缘情而绮靡”的诗歌主张中,“缘情”与“绮靡”是密不可分的。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曹植曾在《七启》中认为“辨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陆机则把“缘情”与“绮靡”结合起来,从诗歌表现的内在美与外在美两个方面,进一步强调并完善于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徵。还要注意一点:陆机《文赋》在提倡“诗缘情而绮靡”的同时,也强调“期穷形而尽相”。陆机强调“穷形”“尽相”,首先就是为了促使“意”、“情”融汇於景物的“形”“相”描写之中。〔5〕如果认为“缘情”说本身侧重於内在美的价值取向,那么,“穷形尽相”说便是侧重於外在美的追求。以后者来表现前者,更使“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得以顺理成章的实现。
在文体的分类与风格方面,建安文人曾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体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并结合具体作家来探讨个性与风格的关系,指出徐干“时有齐气”,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曹植也认为“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文心雕龙·定势》)这些探讨虽然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毕竟过於粗浅。在此基础上,西晋文人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如对文体的划分,陆机分为诗、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见《文赋》)而挚虞则进一步分为诗、赋、颂、铭、箴、七发、诔、哀辞、哀策、解嘲、碑、图谶十二类。(见《文章流别论》)以今天文体分类的标准看,西晋文人分类确实不尽科学,但也毕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体特徵认识的深入。这显然是文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之一。在风格考察方面,陆机认为由於作家个性、审美趣味不同,作品的风格也就各有异彩:
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
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文赋》)即追求炫耀心目之美者,其文风则侈丽宏衍;以切理餍心为快者,其文风则严谨贴切;喜文辞简约者,其文风便显局促窘迫;爱论说畅达者,其文风则旷荡无拘。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显然得益於建安文人而又有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只对诗赋提出“欲丽”的审美要求,而陆机在讨论不同文体风格时,却全然采用了艺术的、审美的态度: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用今天的文学观点看,诗赋以外的八种文体显然不属於文学创作的范围,但陆机仍以“披文以相质”、“缠绵而凄怆”、“博约而温润”、“顿挫而清壮”、“优游以彬蔚”、“精微而朗畅”、“平彻以闲雅”、“炜晔而谲诳”等审美标准来厘定它们的风格特徵。在分析了这十种文体之后,陆机紧接着又来一段总结性的说明: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赋》)在陆机看来,这十种文体皆要达到体物多姿、格式多变、文思尚巧、文辞贵妍,并且要有声律色彩之美。这无疑更是文学化、艺术化的表现。由此可见,西晋文人强烈的审美意识,已浸淫到了非文学体裁之中。
综上所述可见,所谓“晋氏之风,本之魏焉”,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质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6〕尤其是西晋文人秉承了建安文学“情”与“美”的艺术精髓,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标志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晋文人对文学形式技巧方面的追求,也正是基於对文学必须绮靡的认识)。虽然正始之音对西晋文学也有所影响,但西晋诗“缘情”、“绮靡”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为对建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正始文学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於东晋时代,正如邓仕樑所说:“大抵潘陆诸贤,出於建安为多,过江玄风,则导源正始。”〔7〕
注释:
〔1〕邓仕樑《西晋诗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第17页。
〔2〕公元291至306年,汝南王司马亮、 赵王司马伦等八个诸侯王先后发动抢夺皇权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
〔3〕西晋后期,原居住在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鲜卑、氐、羯、 羌等少数民族,乘西晋内乱,相继入侵中原。这就是所谓“五胡乱华”。
〔4〕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夏,匈奴军队攻入洛阳,杀晋太子及王公百官三万余人,俘晋怀帝及其宗属送往平阳。是为“永嘉之变”。
〔5〕王元化:《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北京《文学评论》1978第1期第69页)以及Pauline Yu,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87,p.161.)。
〔6〕“晋氏之风,本之魏焉”,为明代徐祯卿语。 其原意并不象本文所论,而是持否定、抨击的态度,此处仅借其语阐己见而已。
〔7〕同〔1〕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