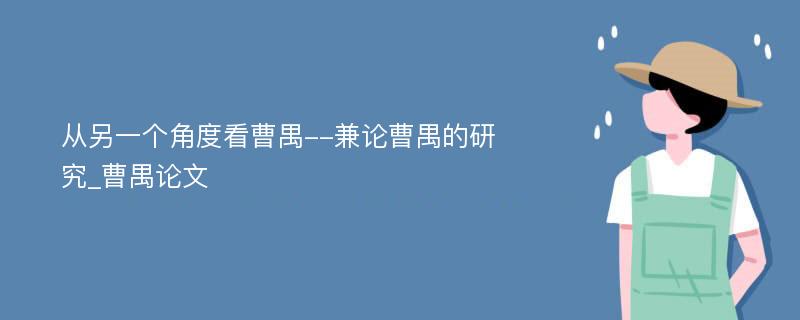
另一种眼光看曹禺——论胡风、吕荧的曹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眼光论文,胡风论文,看曹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禺研究,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可以追溯到1935年4 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搬演《雷雨》所引起的轰动。当时,日本东京的《帝大新闻》为此发表了日文专论,认为中国戏剧从“梅兰芳”阶段发展到《雷雨》,是一个飞跃(注:见田本相、张靖《曹禺年谱》第2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东京的《杂文(质文)月刊》,也发表了白宁关于曹禺《雷雨》的评论文字,指出曹禺“运用他灵活的手段,内容穿插得非常的生动,他是描写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及残酷的暴露着他们淫恶的丑态,用夏夜猛烈的‘雷雨’来象征这阶级的崩溃。”(注:《〈雷雨〉在东京公演》,文载《杂文(质文)月刊》创刊号,1935年5月15号出版。)继《雷雨》之后, 曹禺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戏剧作品,以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奠定并巩固了他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地位,因此也就有了号称“说不尽的曹禺”的曹禺研究
不过,话又说回来,曹禺及其剧作有其“说不尽”的一面,更有其能够说得透彻说得明白的另一面。只可惜,时下的研究者们终究不能觑破曹禺那种“超然的社会学的立场”(注:语出吕荧《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评杨晦的〈曹禺论〉》,发表于1945年8月《希望》第3期。),只能象剧中的“繁漪、仇虎、曾文清们那样,在那种由此岸与彼岸、现实与梦想、人之道与天之道的神秘的二元所网罗成的怪圈里面打转转、做文章。也正因为此,才显示出了跳出怪圈之外去打量曹禺及其剧作的胡风、吕荧们的高明和卓越。
一、胡风论曹禺
关于曹禺的剧作,胡风先后写过三篇评论文章。第一篇是“为了介绍《北京人》的演出”而写于1941年香港的《〈北京人〉速写》(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第二篇是根据1942年7 月在桂林海燕剧艺社和文化供应社文学组组员联合晚会上的谈话记录写成的《论〈北京人〉》(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第三篇则是1942年10月“为剧宣四队公演写的”《〈蜕变〉一解》。(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胡风晚年谈到写作这三篇评论的目的时,曾表白说“是想从见到的例子中找到些经验的教训”(注:见《胡风评论集》下卷第39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如果借用吕荧的说法,我们则可以说, 胡风这三篇评论是基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所达成的对于《北京人》和《蜕变》的“内容的了解”(注:语出吕荧《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评杨晦的〈曹禺论〉》,发表于1945年8月《希望》第3期。)。
在《〈北京人〉速写》一文中,胡风一上来就点破了该剧此岸与彼岸、现实与梦想的截然两分、难以调和:
……在我们的感受上,作者的挽歌是唱得那么凄伤,那么沉痛。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说,有些地方是达到了艺术的境界。但他在挽歌当中终于向往了的那“一种新的生活”,却使我们感到飘忽、渺茫,好象在痛苦底重压下累透了的人底一个仅仅为了安慰那痛苦的梦。所以,作者愈是把他底梦染上浓的色彩,我们愈觉得那梦和现实远离,好象是两种不能粘在一起的东西,被强缚在一起了。
针对着“剧作家的只好用一个不说话的梦来代替了许多要跳出来的、复杂的东西”,胡风提出了一个更高境界或者说是“纯正现实主义”的要求:“我们虽然也要求梦,但我们更要求由现实到梦的道路”。基于此,胡风指明了《北京人》所存在着的严重缺陷:
……作者在这里给予我们的是在灭亡的路上痛苦着的生灵,我相信,在努力的演出里面,演员和观众会要和作者一同叹息、苦恼、低泣、甚至痛哭。然而,在这叹息,苦恼、低泣,甚至痛哭的孽海里面挣扎着求生的意志和奋斗,还只是寄托在一个梦里,没有能够在“现实社会”这个原野上面冲出一道水光四射的滚滚的洪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论〈北京人〉》一文是在“纯正现实主义”的层面上对于《〈北京人〉速写》的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入。这种展开和深入突出表现在对于《北京人》的人物和主题的讨论及对于剧作家的艺术才能的分析上。
胡风认为,《北京人》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多余的人”,这本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概念,包括了曾浩、曾文清、曾思懿、曾文彩、江泰等对于社会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废物——“从整个作品说来,这种人物占多数,而且是写得最好的,因为照我们底理解,他们原是作者最熟悉的人物……”
第二种人是“托梦的人”,包括袁任敢父女、北京人、哑巴工人乃至小柱儿。“这类人物底出现,只是为了给灭亡下去的社会托一个梦,给那里面能够逃生的人物指示一条生路。因而他们本身底性格非常单纯,甚至可以说没有性格。”
第三种人则是介乎于前面两种人之间的瑞贞、愫方们。她们是“从多余的人所寄生的死亡下去的社会走向托梦的人所指示的生路的人物……关于瑞贞底觉醒过程,作者并没有能够表现出有机的变化,只是说明地说有一些朋友,看了一些书而已。至于愫方,就更谈不到什么觉醒过程,作者所依靠的只是加在她底身上的,由于过度的失望而来的压迫作用”。
谈到《北京人》的主题内涵的“社会的意义”,胡风写到:“恰恰和一些批评家所说的相反,它不但不是‘复古’的,而且是反封建的作品,有力的反封建的作品只不过他把现实的历史内容把握得单纯了一点,因而在艺术上也就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更巨大的力量,他的创造才能受到了限制罢了”
在批评《北京人》“主题孤立化”和“人物单纯化”的同时,胡风对于曹禺的艺术才能做了充分的肯定:
在他底笔下,人物底动作、言事,都是为了息息相关的彼此底心理动向。就《北京人》说,虽然在严格的艺术要求上还不免有一些浪费的地方和为了交代情节的拼凑的地方,但他决不使他底人物丧失了自己,决不使他底人物成为概念底留声机,即令那完全是从概念造出来的人物罢,好象他也能够把那概念变成某一程度的活的心理状态,用具体的语言和适当的动作使观众得到一个好象那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的假象。这是艺术家底最宝贵的才能。
《蜕变》是曹禺继《北京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大剧。表面上看,该剧“蜕”去了笼罩着《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部大剧的那一层神秘的氛围,俨然是一部纯而又纯的写实剧;实质上,剧中仿佛是从天而降而又专门替天行道的梁公仰,不过是剧作家此前不得不悬置于彼岸的“天之道”的坐实和显形,整部作品也因此成了“天之道’对于”人之道”的阉割和变性,梦想对于现实的拔高和扭曲。胡风的高明处在于一上来就把握住了女主人公丁大夫集“天之道”的救难者和“人之道”的受屈者于一身的二重性格:
为了加强她底受屈者的性格,在最困难失望的时候不得不送别她底独子到危险的战场上去,在劳瘁衰顿的时候不得不眼看着爱子底受伤、危殆,甚至得亲手把刀锋割破他底肉体;为了加强她底的救难者的性格,即使在悲观失望的时候,即使在悲观失望而又与爱子生离的时候,她也不能忘掉甚至疏远那些为祖国效命的微小的人民。
当做为救难者的丁大夫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而只能一味地受委屈的时候,剧作家只好祭起“天之道”的法宝,给丁大夫们派来了那位替天行道的救世主梁公仰——“这位梁专员,虽然带着形象的面貌,但与其说他是一个性格,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的化身。由于梁专员,她底存在才得到了保障,由于梁专员,围绕着她的一切就化腐朽为神奇。于是,由污暗走到了作者所设想的紧张热烈,再走到了庄严光华的境地。”
在《〈蜕变〉一解》中,胡风再一次亮明了他的“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
……我们自信并非不能理解作者。他经验了苦痛,兴奋和希望,这淤积起来就使他有了创造梦境似的心情。……不过,梦虽然可能是现实人生底升华,但并不是一切梦都会伸入历史底方向。我们知道艺术创造到底是统一在历史进程上面的人生认识底一个方式。在别的作品里面,作者在现实人生里面展望理想,但在这里,他却由现实人生向理想跃进。但据我看,他过于兴奋,终于滑倒了。
正是因为剧作家的过于兴奋、终于滑倒,那个秉赋着伟大的母性之爱的丁大夫终归不是一个真实而成功的人物形象,《蜕变》一剧也不幸堕入了反现实主义的歧途:
作者不仁,把这位梁专员当做替她(指丁大夫)卸去历史负担的刍狗,这刍狗式的人物,到第三幕第四幕,尤其是第四幕,就局促地容身无地,因为,作为权力底化身的他底存在,已经不能再有作用了。
就这样地,作者完成了他底主题,实现了他所企望的“蜕”旧“变”新的气象,但可惜的是,这个崇高的人格(指丁大夫)同时也就临空而上,离开了这块大地。她实际上并没有走进历史的行程,在“蜕”旧“变”新的过程里面,她终于成了一个任凭命运安排的弱者。
二、吕荧的《曹禺的道路》
胡风在对曹禺的《北京人》予以批评的同时,曾经不无遗憾地写道:
要研究一个作品,顶好得先看一看作者底整个创作发展方向,这样就更可以明白这个作品底来根去迹,表现在这个作品里面的作者底创作态度底特点……,但可惜我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曹禺先生底以前的几个剧本,有的看过,有的只看过一小半,有的也看过演出,但记忆已模糊,不能据以立论的。
也许正是鉴于好友的这一憾意,吕荧于一年之后写作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长篇大论——《曹禺的道路》(注:《曹禺的道路》发表于1944年9月,12月出版的《抗战文艺》9卷3—4期和5—6期。)。文中通过对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家》在内的六部大剧的通盘把握,来对曹禺的整个创作道路和发展方向进行考察。
关于《雷雨》的主题内涵和它在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地位,吕荧写道:
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妈妈(鲁妈),她“造的孽”犯下来的罪,她自己身受还不算,又由她的无辜的儿女用死来担代,天地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冷酷”的呢?不顾苦痛的生命的挣扎,尽管有的“悔改了”以往的罪恶,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周萍);或者有的仍然“踏着艰难的老道,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繁漪);却一律都在死亡的手里被窒息死去。就是两个一无过咎的初生的生命,一个纯真的女儿(四凤),一个纯善的少年(周冲),也不能逃去死的遭际;天地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残忍”的呢?而这个“残忍”的故事,显示着宇宙间“主宰”的真实相的一面,力量,魔。这一主宰是《雷雨》的主题。
……
但是这个二元的“主宰”,它比神秘的“命运”,比实证的“自然法则”(这宇宙性的“自然”,是被还原了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都“太大,太复杂”,作者“始终不能给他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在作者,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宇宙隐秘的理解”。而在读者,则仍是一个“迷离恍惚的观念”。
由于人物的真实,由于观念的虚渺,悲剧《雷雨》不是作为神秘剧,而是作为社会剧被欢迎了。《雷雨》不是真正的社会剧,不过它是作者向现实踏出的最初的一步,它的成功确定了作者努力的方向;这是一条伏线,引出了以绘写社会为主题的《日出》。
谈到《日出》,吕荧认为,它是“以绘写社会为主题的”,不过,它的主题的内涵中同样涵含着观念的玄学的成分——“《雷雨》中不出场的角色是雷雨,这时在《日出》中就是太阳。虽然它不像雷雨,是悲剧的主题,它是《日出》的生机,‘天之道’的象征。可是,它也一如雷雨,是二元的观念的产物。不过在《日出》里,社会学的一元远强于观念的一元,它不但显出了全身,隐没了观念的命运,甚至还以它的存在否定了它。这确定了《日出》的进步的社会学的基地”。
关于《原野》,吕荧认为,它与《日出》的“绘写社会”截然不同,是“一个纯观念的剧”。与《雷雨》中人物的爱与死只是悲剧的外形相仿佛,《原野》中仇虎的复仇与死也只是悲剧的形体。《原野》的主题,在于命运对于人的否定和人对命运的抗争。剧中的仇虎,并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农民(社会的人)描写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非现实的原野人(观念的人)描写出来的;他身上秉承着原始人的野性和蛮力,却终究逃不出命运的魔掌。仇虎所企盼的“黄金铺路的地方”,也只是一个观念性的存在,可看做是《日出》中“天这道”观念的再现。
相对于《雷雨》来说,《日出》是社会学一元的进步,《原野》是观念论一元的深入,而《北京人》则是社会学一元与观念论一元的再度调合。《北京人》的主题是绘写旧家庭的崩溃,这一主题的内涵中仍然存在着彼岸与此岸、梦想与现实、天之道与人之道相对立的观念论的一元。与《日出》中“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相对应,《北京人》中的“人之道”可说是曾家大院这个行将就木的腐朽家庭。原始北京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的观念的憧憬,则是《日出》中的“天之道”观念的重现。所不同的是,《日出》中“天之道”的太阳只存在于幕后,《北京人》中的“天之道”却外化成为酷似原始北京人的哑巴机器工人来到台前,帮助愫方和瑞贞从行将就木的曾家大院逃了出去。比之于《原野》中的仇虎只能用死来战胜命运来说,《北京人》中的机器工人明显地前进了一步,他最终凭着野性的蛮力救助愫方和瑞贞这两位“明日的北京人”走向了新生。
总之,《北京人》中颇具神秘性的对于光明的憧憬,是与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取同一方位的,观念论的一元与社会学的一元在这同一方位上既相对割裂又有所调合,而这有所调合,却又是以人物的“生活世界”和“性格内涵”的单纯和孤立为代价的。关于这一点,吕荧引用胡风《论〈北京〉》中的一段话来进行讨论:
那样一个大家庭和整个封建势力并没有彼此纽结的血缘关系,只是关起大门来开演一个悲剧,而对于暴发户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生活的社会交涉里面表现它的抵抗或迎合,只是单纯地负了一笔债和讨债的威逼,而且这也不过仅仅尽了促成这个悲剧上的一点观念上的作用。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而新的人生理想,新的力量的存在,也仅仅只在人物的对话里面说明式地暗示几句而已。
由这段话,我们看到的正是吕荧与胡风在“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上的一致性。基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吕荧对《北京人》在曹禺创作道路上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
不过在作者,虽然是这样,却在这中间肯定了新人的群体。《北京人》是作者向现实踏入较深的一步,向理想踏入较深的一步,向理想迈进较远的一步,向诗追求更大胆的一步;这是一个转化点,留有旧的痕迹,也现出新的方向。
《家》是曹禺继《北京人》之后创作的另一部大剧。吕荧认为,《家》与《北京人》一样,主题在于绘写旧家庭的崩解,所不同的是,《北京人》绘写的虽然只是一个“没落的封建的片断的家”,剧中观念论的憧憬却与社会学的走向取同一方位;而《家》绘写的虽说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全面的‘家’的画幅”,却因没有了画幅之外的对于光明的憧憬而与“家”之外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相对绝缘。
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不同,《蜕变》不是悲剧和否定性的剧,而是一部喜剧和肯定性的剧。和胡风论《蜕变》的观点相一致,吕荧认为,《蜕变》的主题就是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这样的主题,表面看似乎是社会学的,究其实质却是观念论的。剧中寄托着作者好人政治的理想的伤兵医院,其实是一个以替天行道之个人为中心的虚假的世界,与《日出》中的“天之道”的观念遥遥相对。作者以写实的笔法写虚假的存在,结果写出的只能是一幕与现实社会相背离的“一幕观念的粉墨画的喜剧”。
三、吕荧对于杨晦的一场论争
在《曹禺的道路》上半部分发表之后,杨晦也发表了《曹禺论》(注:杨晦《曹禺论》,发表于1944年《青年文艺》1卷4期。)一文。鉴于“杨晦先生的论文和我的见解,差异和距离很大,许多地方都值得商讨。而主要的是,在杨晦先生的论文里,形式的理解占着优势,压倒了内容的理解;因而对于读者对于作者,都不能提供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要点,反而在某些点上,助长了形式主义的倾向”,吕荧写出一篇题为《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的论争文章。正是在这篇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和遗忘的论争文章里,吕荧基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既“指正主题的内涵,揭露观念的玄学”,又“扩深作品主题的内涵,发扬现实主义”,更进一步也更为透彻地解答了曹禺研究中至今仍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三个最为基本也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曹禺本人的思想观念是什么样的?曹禺剧作的主题内涵究竟是什么?曹禺的创作道路又是循着怎样的轨迹和方向前进和发展的?(注:关于吕荧与杨晦之间的论争,可参见拙文《关于曹禺剧作的一次论争》。文载《艺术百家》1995年第3期。)
关于前一个问题,吕荧的答案是这样的:
曹禺先生的思想内容是社会学的,但是是一种包含有观念的憧憬的,超然的社会学。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才有《雷雨》中二元的主宰,《日出》书前对于老子“天之道”的向往,《原野》中对人类原始的性与力的肯定,这原始的性与力,终于以一个“北京人”的形象现出身来。在《雷雨》、《原野》、《北京人》里,作者都借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显示思想的憧憬或者寄托……在根本上,超然的社会学的立场,观念的“天之道”的憧憬,是作者绝大的阻碍,阻碍他进一步走向人民群中,走向现实主义,以至走向艺术的殿堂。——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正是由于吕荧基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的高境界上把握到了这个理解曹禺剧作的关键之所在,他对于杨晦的论争才显得高层建瓴、游刃有余。在吕荧看来,杨晦对于曹禺剧作的理解,之所以“在剧作主题的形式上兜圈子”,就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曹禺本人这种“超然的社会学的立场”。
“《雷雨》的主题是什么?”,这是吕荧与杨晦进行论争的第一个具体问题。
吕荧认为,《雷雨》的主题是为“雷雨”所象征的主使“天地间的残忍”的“主宰”。杨晦则认为,《雷雨》中的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人物,所谓的官商”,他的家庭是一个“跟他一样镀上金的封建家庭”,“无论是周蘩漪,是周萍,或是周冲,并且余势波及到四凤身上,都是在这样的封建家庭里所演的悲剧”。《雷雨》的主题,是“一个镀金的绅商家庭的悲剧”、“一个官僚资本家的家庭悲剧”;而剧中的“运命”、“性爱和血缘的纠缠”,不过是作者“艺术思想”上对于希腊悲剧的憧憬。
针对着杨晦对于《雷雨》的理解,吕荧首先指出,曹禺的《雷雨》虽然确实受到了希腊悲剧的影响,《雷雨》中的主宰,却远比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复杂得多。它既包含着希伯来先知们的“上帝”,希腊戏剧家的“命运”——观念论的一元;又包含着近代人的“自然的法则”——社会学的一元;是一个集观念论与社会学为一体的二元的观念。“杨晦先生认为作者仅仅是迷恋希腊悲剧,憧憬希腊悲剧,这见解是纯形式的,而且也太狭小”。
接着,吕荧又指出,《雷雨》中的周朴园,并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人物”,而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第一代资本家。他不仅有封建家长的顽固保守的一面,也有资本家不择手段的另一面。相应地,《雷雨》的主题的内涵中,既有反封建的成分又有反资本主义的成分。“杨晦先生的了解在形式上强调了《雷雨》的现实意义,而实际上则狭小了人物以至主题的内涵,甚至误解了主题”。
做为以上两个方面的归结,吕荧认为:
在《雷雨》里,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旨,并没有得到健全的生命。这样现实的意旨,归结起来,是以一个无形的“主宰”(雷雨)为中心的,这无论如何,是纯观念论的……在外形上,社会问题家庭关系与真实的人物扮演悲剧,在内容上,血缘纠结与虚玄的力量主使悲剧。
关于《原野》,杨晦认为,它是曹禺最为失败的一部作品,是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大退步。它背离了《日出》所走出的“现实的社会剧”的路子,把农民复仇这样的现实的问题,写成了比《雷雨》更富于神秘象征色彩,更远离于现实的作品。杨晦还认为,《原野》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剧作家的迷恋于不正确的艺术思想,迷恋于神秘象征的艺术表现方法,不从现实去了解社会问题,却从现实的社会问题里得出神秘象征的了解。
针对着杨晦关于《原野》的这种“形式的了解”,吕荧指出,所谓象征神秘是关联着内容的,决不单单是形式上的事。剧作家之所以在《原野》中“把社会问题神秘象征化”,是因为,立足于“超然的社会学立场”的他,要“借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显示思想的憧憬或者寄托”。
同样是着眼于“剧作主题的形式”,杨晦对《蜕变》大为推崇:《蜕变》在作者创作道路上,“是比《日出》更彻底的转变”。“在《蜕变》里,他运用的完全是写实的手法,没有一点神秘象征的成分,掺杂在里边,处理的是现实的题材,用的是写实的手法……,虽然他还没有把握到真实,只是随着当时抗战初期的乐观空气,接触了表面上足以使人乐观的现象而已。这虽然只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他在曹禺的艺术发展上,实在是平坦的一条大道。这前面没有‘神秘’,没有‘想象的荒原’,是一步一步更走近真实的道路”。
针对着杨晦这种“以手法的外形定前进和后退”的论调,吕荧论争道:《蜕变》的“写实”实际上是粉饰和背离了现实。作者从“超然的社会学立场”出发,用观念图式化了的人物来扮演这幕“蜕旧变新”的喜剧,所虚构出的不过是一个以梁公仰为中心的个人中心的世界,所表现的不过是好人政治的理想。这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相背离的。《蜕变》的所谓“转变”,实际上也只是形式和手法的变化,对于作品主题的内涵和剧作家的创作道路并无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转变并不彻底的《日出》,反倒写出了抗议黑暗现实的社会学的题旨,更彻底地“转变”了的《蜕变》,写的却是一部以脱壳式换汤不换药的“蜕变”为新生的中庸的社会学的喜剧。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与理解《蜕变》时的“以手法的外形定前进和后退”相一致,杨晦把《北京人》的出现称之为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再一次“退转”,杨晦认为,《北京人》标识着曹禺剧作由《蜕变》的“真实的进步”又回到了“《雷雨》的旧路”。它尽管“并不是那样完全地回到《雷雨》的旧出发点,没有充满《雷雨》里的那种‘雷雨’,神秘命运的思想,却变成事实的无可奈何,人性的不可救药了”。
在吕荧,一上来先把杨晦对于《北京人》的如此理解判定为“形式的了解”——“只看主题外形的变换,不顾作品主题的内容和思想的联系,不了解作者一贯的超然的社会学的立场和‘天之道’的憧憬”。接着,他重申并进一步发挥了《曹禺的道路》一文中已达成的对于《北京人》乃至于“曹禺的道路”的“内容的了解”:
《蜕变》中对现实题材的跃进,对抗战的乐观精神,是应受赞扬的,《北京人》中奇形怪状的猿人和原人的向往,是应受批判的,但这并不是作品的主题,并不能说,单由这一点就判断了一切。《蜕变》的主题,外形上是现实题材进一步的把握,可是这把握的内容却是中庸的社会学与观念图式化的表现方法进一步的发扬。《北京人》中外形上有观念的象征存在,然而主题的内容以绘写旧家庭的崩解为主。在绘写中,作者借《北京人》写了他的向往,同时讴歌了新人类的诞生,明确地说明了事实的可以奈何,人性的可以救药,肯定了新人(明日的北京人)的集体,这中间包含着《雷雨》、《日出》中社会学意旨的进展,与《原野》中性与力的憧憬的演化。这样,《北京人》在作者创作道路上,“这是一个转化点,留有旧的痕迹,也现出有新的方向。”
接着这段话,吕荧另有如下一段更一进步的发挥:
作者应该继续走外形前进,内容则在发扬中庸的超然社会思想的路,还是继续肯定新人集体的认识,抛弃观念论的天之道的观念,以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立场,深入现实、绘写现实;哪一条才是大路,当很明显的罢。
在全文的结束语中,吕荧更为明确地写道:
……我们希望曹禺先生更进一步,这决不是说,作者如果在形式奉行什么条规,写些什么题材或人物,喊些什么口号,就解决了问题;外形的接受新理论不是内部的接受,所以作者的剧里,有新社会学的意旨,但也有一些观念的社会观,人物观,以至于艺术观,这阻碍作者创造典型,完成诗。我们期望作者更进一步的面临现实,体认现实,深入现实。
事实上,此后的曹禺非但没有走上“纯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去以“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立场”创作出“纯正的现实主义”的戏剧作品,甚至于连《雷雨》、《日出》、《北京人》那样的“超然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剧本也再没有能够写出一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大悲哀。万幸的是,到了1947年,与胡风有师友之谊的路翎,终于写出了一部真正称得上是“纯正的现实主义”的戏剧作品——《云雀》(注:见《路翎剧作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云雀》和《云雀》与曹禺剧作的比较,可参见拙文《〈云雀〉:独标一帜——关于现代戏剧的一种考察》。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关于曹禺剧作的理解, 还可参见本人的硕士论文《诗:话剧对于戏曲的承传、借鉴和学习》。文载《戏剧——中国戏剧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为我们于“纯正的现实主义”剧作的高境界上返观曹禺的剧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四、关于路翎《云雀》与曹禺剧作的一种比较
《云雀》是一部四幕悲剧,1947年6 月曾由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附属剧团上演过。胡风为该剧的上演也写下过热情的赞语:
《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
性格,是现实的历史内容所造成的。所以,《云雀》虽然有四个人物,四种不同的代表的性格,但真正的主角却是通过这四个人物所演示出来的、冷酷而磅礴的、轰轰然前进的现实历史自己(注:胡风《为〈云雀〉上演而写的》。见《胡风评论集》下卷第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
在《云雀》的四个人物当中,男主人公李立人堪称是该剧的灵魂。根据剧中的交待,李立人是一个经历坎坷、背景复杂的人物,他从小受虐待,当过壮丁,上海二八战争时期卷入复杂的政治关系。在多少年的政治生涯中,他被利用,被出卖,被推入污泥之中。抗日战争时期,他脱离这种政治关系来到桂林,结识因失恋而致悲惨的陈芝庆。两人结婚后,李立人偕陈芝庆来到京沪线附近一座小城的紫桐中学任教。任教几年,李立人热爱着自己的工作和学生们,他确信,自己呕心沥血所从事的工作,是在“和旧中国抵抗,和旧社会争取阵地”。李立人的妻子陈芝庆,却以“为了灵魂而生活”的“有思想”的女人自居,不满意于丈夫的“疏忽”自己,不能忍受生活的平凡和清贫,冷淡了结婚初期一度立下的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心愿,痴迷于自己少女时代被人宠为“云雀”的那个旧梦。在这种情势下,陈芝庆落魄而无聊的旧情人王品群追寻而来并乘虚而入,以“爱情”的名义诱骗和纠缠陈芝庆,煽起她对于丈夫的仇恨情绪,挑起了陈芝庆与李立人夫妻之间的公开争执。在争执过程中,陈芝庆先是埋怨丈夫“老是不陪我出去买东西”;进而又谴责丈夫“你自私专制,你野蛮,你从来不懂一个可怜的女人的需要”,以至于卑屈地向丈夫乞求“美丽的谎话”;最终在连“美丽的谎话”都得不到的情况下,她放弃了对于李立人同时也是对于自己的争取,以自暴自弃的态度投进了王品群的怀抱。李立人在这场“我希望她抛开她底,她却要求我抛开我自己”的夫妻争执中,坚守着自己既负担起自己的生活又服膺于整个社会的做人原则,向妻子提出“负担起你自己的生活,没有谁能够给你保证一个漂亮的前途”的劝诫和要求,拒绝以“美丽的谎话”来换取“家庭的温暖”,以至于忍受着极其惨烈的心理矛盾,应允了陈芝庆的随王品群出走。
陈芝庆出走一个月后,与这场婚变相关的背景逐渐趋于明朗化。王品群采取“一擒一纵”的两面派手法,出卖了同事李立人、周望海和学生们,与官方和校方达成交易,当上了小报的主笔,并准备回学校取代李立人的教务主任的职务,而把许给陈芝庆的去上海重新开始生活的谎言抛脑后。同事周望海出于对“被侮辱被损害”的陈芝庆的同情,向李立人提出应该救助陈芝庆的规劝。心高气傲的李立人于一场情感大爆发中表白了自己在社会之大我与个人之小我、人类之大爱与男女之私情不能相兼、不能两全的悖谬情境中,对于牺牲小我以服膺于大我、牺牲私情以服膺于大爱的原则立场的绝对坚持,从而理顺了长期郁积在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就在李立人准备有所行动的时候,陈芝庆于悔恨中服下毒药回到家中,死在了自己与李立人结婚同居的婚床上,死在了真正爱自己也为自己所爱的李立人的怀抱里。在全剧的结束处,经历过这场爱与恨的精神洗礼的李立人,在同事周望海的劝慰下重新打起精神,与周望海结伴走向了新的生活。
就炼戏的功力而言,路翎的《云雀》明显逊色于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几部大剧。但是,始终没有走出自己“超然的社会学”的怪圈的曹禺,最终与李立人式负担起自己的生活并服膺于全社会乃至于全人类的进步、于险恶的现实斗争中脚踏实地走向崇高人格的精神完成的人物性格无缘。
《雷雨》中的“雷雨”象征着主宰天地之间的“残忍”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注:参见曹禺《雷雨·序》,田本相编《曹禺文集》第1卷第209页。),剧中的八个人物都处于“雷雨”的主宰之下而不能自主。《日出》中的“日出”所象征的是一个“满天大红”的所在(注:参见曹禺《日出·跋》,田本相编《曹禺文集》第1卷第447页。),在那里存在着“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但是剧中所有的出场人物又都与“日出”的光明无缘,他们只能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中玩弄他人或遭人玩弄。《原野》中的“原野”与《雷雨》中的“雷雨”相仿佛,同样是象征着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无论仇虎身上的“性”与“力”如何强悍,都敌不过“原野”的神秘力量,自然也就逃不出“原野”的牢宠。《北京人》中,满腔爱心的愫方眼见着曾家大院行将就木,却在一味地“忍耐”和“忍心”。有趣的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都悬置着一个乌托帮式的彼岸世界。《雷雨》中的周冲憧憬着“真真干净,快乐……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的“一个所在”;《日出》中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之上悬置着一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一个“满天大红”的光明世界。《北京人》中的袁任敢则鼓吹着“要爱就爱,要恨就恨……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的“人类的希望”。于是乎,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曹禺笔下这些不能提承自己的生活并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人物,又该如何走向为他们所憧憬和向往着的光明美好的彼岸世界呢?
《日出》第一幕中,剧作家在陈白露初次上场的舞台揭示里提供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但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然而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她走去打开门,发现那来客,是那穿着黑衣服,不做一声地走进来。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注:引自田本相编《曹禺文集》第1卷第235页。为了保证资料的可靠性,本文所论及的曹禺剧作全部依据于《曹禺文集》所录版本。)
事实上,《日出》中的陈白露最终没有意外地得到一笔财富,“那穿着黑衣服,不做一声”的“来客”也终于没有现出身来拯救于她,陈白露也就只有死路一条。同样地,《雷雨》和《原野》中也终于没有“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声”的救世主观出身来,把周冲送到他所憧憬的那样“一个所在”,把仇虎救往“黄金铺路的地方”,留给周冲和仇虎的归宿当然也只有死亡。
只有到了《蜕变》一剧,为周冲、陈白露、仇虎们求之不得的救世主才现出了真身,不过,这救世主并不是“那穿着黑衣的,不做一声”的不速之客,而是握有重权的官大人梁公仰。在梁公仰出场之前,剧中的丁大夫与周冲、陈白露、仇虎相仿佛,是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物。她所工作的伤兵医院,为置伤兵生死于不顾的当权者所把持,任凭她如何善良、如何高明又如何富于献身精神,都于世无补,眼看着连自己的一份工作都没有了保障。丁大夫连同她所在的伤兵医院获得拯救、走向新生的唯一希望,只在于握有重权并替天行道的梁公仰从天而降,奇迹般地惩办贪官污吏并委丁大夫以重任。一旦梁公仰整顿好了伤兵医院并委丁大夫以重任,丁大夫马上得以大显身手以至于成贤成圣。假如我们追问一句:要是梁公仰并不能从天而降并替天行道的话,丁大夫们又该怎么办呢?剧作家在《关于“蜕变”二字》一文中给出了答案——那就“需要‘忍耐’但更需要‘忍心’”了(注:见《曹禺文集》第2卷第42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4版。)。
《北京人》的出台,标志着曹禺的更为成熟也更为乖巧。曹禺在《北京人》中,已不再把已经泄了底气的“天之道”的彼岸世界高悬起来并加以神秘化,而是靠着具有原始和现代双重意义的“北京人”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原始“北京人”是五十万年前“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野蛮而纯真的人类始祖;现代“北京人”则是置身于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救世主——在袁任敢学术察勘队里修理卡车的哑巴工人,他秉赋着北京猿人丑陋的外貌和“野得可怕的力量”。《北京人》所反映的现实,也不再是《雷雨》中罪孽深重新旧参半的家庭和《日出》、《原野》、《蜕变》中或掠夺或仇杀或贪污的黑暗社会,而是一个关起门来自生自灭的旧式家庭。被圈定于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女主人公愫方,并不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谋求自救并救护自己所爱的人,反倒一味地“忍耐”和“忍心”,还诱劝一心想出走的瑞贞也象自己那样“忍耐”和“忍心”。愫方把自己的一生一世全部寄托在一个废人——她所爱恋着的曾文清——的身上,当文清在外边的世界里实在混不出个“人”样,象幽灵般溜回家中的时候,愫方的精神趋于崩溃;曾思懿的逼她为妾更使她忍无可忍。这时候,哑巴工人突然说话了,并充当起了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凭着一身的蛮力拧断曾家大门上的铁锁,救助愫方和瑞贞逃出无可救药的曾家,去投奔那个据说在五千年前曾经有过的理想世界。如此的愫方,自然与《云雀》中负担起自己的生活并服膺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李立人不可同日而论。更进一步说,《家》中一心向往着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的觉新、瑞珏和出走后还要指望大哥给寄钱养活的觉慧,与李立人同样地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继《云雀》之后,路翎也再没有能够写出足以令人称道的戏剧作品。这一切做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不能不令我们予以深思。对于这种“经验和教训”的深思,正不失为我们对于作古不久的曹禺和较早去世的吕荧、胡风、路翎们的一种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