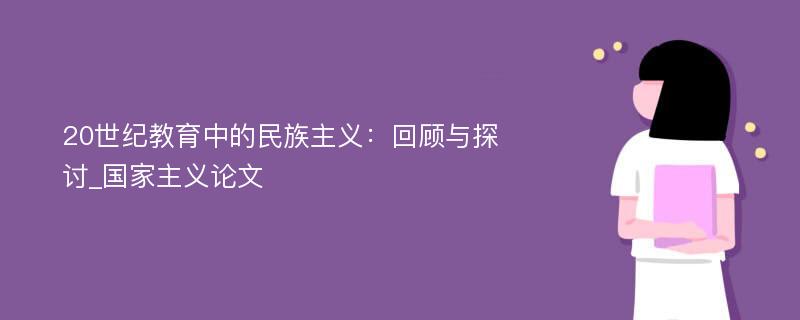
20世纪教育中的国家主义:回顾与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6-0003-11
舒新城曾经说过,教育哲学就是教育的理想。教育的理想各人都有,各地不同。乡下的老太太也有其教育哲学,因而也有其教育的理想,有其对于什么是好光景、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好孩子以及什么是好教育的见识。此说大体不谬,可以用于观察与理解个人的教育生活。然而,若要观察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教育生活,要分析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教育生活如何深受其所追寻的教育理想的影响,仅从芸芸众生个体的教育哲学或教育理想分析入手是不够的,必须分析那个社会或时代有广泛影响力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教育理想。无论在哪个社会或时代,这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教育理想都是主流教育价值观的来源,是驱动和引领无数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实践的精神力量,是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辩护的根本标准。纵观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发展和不断变革的历史实践,尽管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提出过种种不同的教育理想,开展过种种不同的教育试验,但百余年来对中国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实践影响最大最深的教育理想莫过于“国家主义”(nationalism)。可以说,它构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形形色色教育理想的主轴或基调,在整个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发展、变革、革命或创新的过程中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推陈出新,绵延不绝。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20世纪中国教育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进行初步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以引发教育哲学同行们的兴趣,并期待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学术讨论。
一
20世纪中国教育实践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不是中国的“特产”,它像许多20世纪的政治思潮、文化思潮、教育思潮一样,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从源头上说,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和我国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可以说与古代国家的同时诞生,是古代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培育国家意识、构造社会秩序的理想工具。柏拉图在其著名的《理想国》中曾称羡斯巴达的国家教育制度,明确反对雅典城邦将教育事务交给私人。我国古代的《礼记·学记》一开篇也教导国家的统治者,“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文,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但是,影响20世纪中国教育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却既不是对古希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借鉴,也不是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继承,而是直接来源于18-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时所产生并依赖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是欧洲近代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中国独特社会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并与欧洲各国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一脉相承、交相辉映。为了区别于古代的国家主义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也可以将这种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诞生相关联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称为“现代国家主义”(modern nationalism)。“现代国家主义可以被看成是通过新闻媒体、社交活动、公开演讲以及学校教育等诸多途径对国民性的创造,它唤醒了人们对于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遗产的自我意识,唤醒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要求人们对于某一国家在政治上的绝对忠诚。”[1]120德国的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法国的拉夏洛泰(Louis-Rene de Caradeuc de Lachalotais,1701—1785)等人都是现代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的热心提倡者和系统论述者。[2]422-474尤其是拉夏洛泰的《论国民教育》(1763)一书和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影响最大,经常为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所提及。拉夏洛泰在《论国民教育》一书中大胆地批判了耶稣会教育,提出“法国民族需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认为“教育的中心目的是: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团结感和为国家尽忠的能力”,从而对法国乃至西欧各国现代世俗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阐发现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奠基之作。[3]费希特在自己著名的演讲中用德语高度赞扬了德意志民族,认为她既有“伟大的天才”,也有“深邃的智慧”,大敌当前,他呼吁全体德意志人“警惕那些毫无知觉的奴役,因为它会从我们后代那里夺走我们未来解放的希望”,“我们必须立刻成为我们必须成为的那样,即德意志人”。[4]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是塑造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促进国家统一和国家认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关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二
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在19世纪中后期就通过多种途径陆续地抵达中国,引起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被普遍看成是应对国家危机的一个选项。1860年后,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开展的洋务教育和兴办的各种新式学堂就积极地体现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主张,其目的还是保存秦汉以来中国君主制和儒家文化传统。19世纪末期,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也是提倡和发展国家主义学说的著名学者。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列强争雄的时代,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存,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使得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刚刚诞生时就被赋予服务国家的使命,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在1912年之前,受制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信念,洋务派和维新派所主张的国家主义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味道,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现代国家主义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主要的差别在于洋务派和维新派所倡导之国家主义抽掉了由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现代国家之价值基础,如自由、平等、民权等,只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抽取了其对内凝聚民众、对外呈现主权要求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育不全的国家主义。
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政体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国家的外患未消,内患加剧,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尽管在这十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变革,废除科举制度,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颁布新学制,发展新式教育,但是根本无助于挽救封建国家的灭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新国家的建立,急需开展国家主义教育,通过国家主义教育来推行“三民主义”学说,培养共和国民,使新政权合法化。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孙中山曾说,“遍查古代和现代世界各国生存之道,如果我们想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我们就必须发展国家主义。……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习俗,但是却只有家庭和帮派的概念,而缺乏国家的精神。……因此,我们现在才沦为世界上最贫穷、最软弱和最低等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不热切地提倡国家主义,将四万万同胞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就会面临巨大的悲剧,国家荒废,民族解体。要阻止这样的危险发生,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通过培育国家精神来拯救国家。”[1]131这可能是最早的“教育救国论”,其内核是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即通过在青少年学生和广大社会民众中间培育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来拯救国家。
“随着现代国家主义精神和哲学的兴起,中国新的领导者渴望发展由国家控制的教育体系,崇尚国家主义的理想。这种渴望甚至达到了宗教般狂热的程度。”[1]pxii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得到了系统的辩护和论述,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实施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政策主张,出现了“国家主义教育学”的派别。这个派别的主力军是李璜(1895—1969)、陈启天(1893—1984)、余家菊(1898—1976)等人,其中以余家菊的贡献为最大。[5]1925年,年轻的余家菊出版《国家主义教育学》一书,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国家主义教育学思想。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到:“曩昔余游欧陆,道出安南、印度各属,得目睹亡国人民之憔悴,皙种子孙之骄傲,嗣居英法,更亲见国民习性之迥异,国际利害之冲突,与夫和平论者势力之脆薄,而恍然于战争之机,随处皆是,杀戮之祸,随时可作。回顾祖国,则不肖者方征诸于利欲之私,高明者又好为超国嫉种之论。卫国之心,自强之念,澌灭怠尽,几何其不载胥及溺乎?”[6]此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余家菊提倡国家主义教育的背景及目的,也反映了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提倡者们对于当时国家处境和命运的忧思。这种忧思不仅表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屡受外国列强欺侮导致的怨恨,而且也表达了对民国成立之后军阀割据、派系众多、政治动荡、国家四分五裂的不满,比其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和教育理想更能迎合当时知识阶级和社会舆论的口味,因而一时间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广为传播。
在余家菊看来,“国家”一词不仅意味着“土地”、“人民”和“主权”,而且也是一种“伦理实体”,是国民共同心灵成分和精神归属。他说,“个人扩大其自我,则自我与国家合一,所谓‘民吾同胞’、‘宇宙内事皆我分内事’者是也。我之所以努力于国家者,正所以完成其自我。我欲完成其自我,又必取径于服务国家。成己成人,本是一事,合而言之,大道乃现。更从国家言之,国家与个人性格之所表现而成。国家的善益皆来自于个人的贡献。……依据以上讨论,中国的教育目的,当使个人凝结其人格与国家之上,实现其自我与国家之中。”[7]基于这样黑格尔式的国家理论,余家菊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问题,认为“国民教育为立国之根本。国民教育不发展,无论政治失其凭依,即就国防言之,亦无术健全。”[8]70提出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国家主义教育培养自尊精神与独立气概;国家主义的教育发展国性而阐扬国光;国家主义的教育陶铸国魂以奠定国基;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维护国权以延续国脉。基于国家主义的教育精神,余家菊又厘定了国家主义教育的宗旨,提出教育国家化的具体政策建议:教育应由国家办理或监督;教育应保卫国权;教育应奠定国基;教育应发扬国风;教育应鼓铸国魂;教育应融洽民情。[8]363-364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条,涉及到国家的教育主权问题,强调要禁止教会、私人或外国人举办教育,收回由一些教会所把持的教育主权。教育主权问题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不仅一些教会学校不在政府部门注册,教师聘用、学生招收、教学科目设置、教学语言选用等都不受政府的控制。一些日本人在华开设的学校甚至根本不教授任何中文科目,学校的中国学生还被要求每天向日本的天皇鞠躬。针对这些情况,余家菊等人提出收回国家教育权的主张,有其进步的意义;①[8]364他提出的开展国庆日教育,国歌、国旗、国耻教育以及普及小学教育,注重军事训练等各项具体建议,也成为后来不同时期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
1927年之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长期的军阀割据的局面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的起义,建立自己独立的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共产党则在自己的根据地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尽管在教育宗旨、方针和内容上有许多不同,但是其共同的目的都在于如何通过教育来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知识与能力素养,以实现国家的彻底独立和统一,因此可以将它们看成是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新形式。至于余家菊等人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教育主张,二者也多有重视和发展,如加强对外国人和教会学校的管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等。但是,由于余家菊等人在政治立场上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学说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其国家主义学说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遭到了以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为首的坚决批驳。批驳者与提倡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开展国家主义教育或要不要培育青年人的爱国精神,而在于要青年人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教育能不能救国以及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上。[9]也正是由于余家菊等人以上的政治立场,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与三民主义教育思想渐渐合流,许多主张也为三民主义教育所吸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得到再一次的复活,“抗日救国”成为那一时期整个国家最高的教育理想。1937年8月,毛泽东就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0]193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实施,其中有关教育部分的纲领为:“(二十八)加强民众之国家意识,使能辅助政府肃清反动,对于汉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二十九)改订教育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1938年6月,毛泽东也再次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结合”,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教育任务:“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动民众教育。……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11]国共双方的教育,都着力于唤醒“国民意识”、振奋“民族精神”,训练抗日青年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精简课程内容等,凸显了国家危亡之际实施国家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当然,此时的国家主义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与推行者,已经不是余家菊等几位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是国共双方的领导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国家的成立,自然需要新教育来加以配合,而培养青少年学生以及所有社会大众新的国家意识,宣传新的意识形态,造就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就成为新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一方针政策,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教育工作发挥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1952年,教会学校、私立学校被全部接管,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所关注的教育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国家成为了唯一的教育举办者。此后,尽管不同时期国家的教育方针有所不同,但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一直在各级各类学校系统中得到系统而鲜明的体现,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毕业时都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国家服务。国歌、国旗、国语(普通话)、国耻、国魂等内容也一直是大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了新的更加明确的内容。国家主义教育的理想通过“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等诸多的命题得以表达。1958年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开始意识形态化,整个社会开始用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审视和安排一切的教育工作,教育工作失去其相对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附属物、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有了新的形态——“科教兴国”。“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12]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年的《中国教育与改革发展纲要》再到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都是为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以及随后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国民素质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教育事业已经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面转化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人们过于从经济增长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主要地被理解成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服务,教育本身甚至被作为驱动和保障经济增长的前提与动力,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经济主义倾向② 越来越明显。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也着上了新的色彩。
四
在对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产生和发展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进行历史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也存在着不少值得关注的学术论争。这些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关系问题上: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与人文主义。前三个关系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家主义教育学兴盛时期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后一个关系是近三十年学术界才提出来的问题。
在余家菊等人提出国家主义教育的主张时,有不少的批评者从国际主义(cosmopolitanism,今亦译为“世界主义”)的角度加以批评。有一派批评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已经成立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LON或国联),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作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之一,中国不应该提倡国家主义教育,而应该提倡国际主义教育,宣扬和平文化。这一派批评者因此认为,诞生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独立时的国家主义已经过时了,无需也不必再提倡。另有一派批评者认为,国家主义教育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国际主义即国际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攻击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要想赢得自己的独立,就必须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要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就必须联合同样遭受世界帝国主义统治之苦的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把解放全人类和解放全中国结合起来。同时,这派批评者嘲讽国家主义教育学派在如何赢得国家独立和尊严的问题上只寄希望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而忽视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只重视所谓的国民性、国魂的培育,而忽视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因而是一种空洞的理想。针对这些批评,国家主义教育学派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或辩护。对于前一种批判,余家菊认为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可并行不悖,讲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并非反对世界主义。他提出,“世界为扩展线,民族为出发点;世界为集团,民族为分子。分子尽可并立,而不必相扰。集团固为总体,而分子仍有个性。所以世界大同,仍可容忍分子之独立,而分子之独立亦无妨于世界之大同。信世界主义即不欲别人讲民族、讲爱国,似乎不免于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讥。若更就事实言之,则不能自立之民族,无讲大同主义之余地。”[8]146对于后一种批评,由于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根本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因而除了表明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场外,没有作出多少学术上的回应。毛泽东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为肯定农民自己办学的行为,把国民学校称为“洋学堂”,不仅教师的教育态度不好,而且教授的内容又脱离实际。他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教育家们,“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根据毛泽东、恽代英等人的观点,国家主义教育的主张,不能在学校或课堂里得到实现,必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对于这一点,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学者们是很难理解的,当然更谈不上赞同了。
关于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关系,有批评者提出,国家主义压制个人主义,是对个性的戕害。对于这种批评,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完全不能接受。余家菊认为,回答这个疑问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个性”与“民族性”的内涵与关系。他引用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1871—1965)的“个性”理论和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来说明“个性”与“民族性”彼此无碍,“民族性之特质也就禀赋在各个人身上,所以合于民族性的教育,绝不妨及个人。妨及个人的教育,据我看,或是抄袭的教育,因为抄袭的教育未必能合于本民族之各个人或大多数人。”[8]152余家菊明确反对将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个人主义离弃国家主义,则易于流为自私主义;即不然,亦为空具形式而无内容。”[13]324他举例说,像“教育的目的在教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一个人主义的教育主张,但是如果不说明“何为堂堂正正的人”,则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要说明其内涵,则不能不诉诸国家主义,因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服务国家、发扬国光以完成国家之使命者”。所以,他认为,“国家主义不但无碍于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实寓于国家主义之中”。[13]324
国家主义教育学说兴起之时,正是由杜威访华所普及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继续发酵之时,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由理论走向实践,深得当时中国教育界的认同和追捧。针对有批评者认为,国家主义是一种精英主义,而非一种平民主义(democraticism,也可以翻译为“民主主义”),余家菊等人也做了反驳。他反问道:“试问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究竟有何种不可相容之处?试问平民主义有离却国家之可能否?试问平民主义系产生于国家主义之下抑系产生于反国家主义之下?”[8]334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中国教育界盛赞的“平民主义”其实就是美国的“国家主义”,因此,平民主义教育就是“美国化”的教育,是另外一种的国家主义教育。所以,他们在中国提倡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主义教育是天然正当的。对于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关系,陈独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接受国家主义,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期望以平民主义来充实国家主义,反对或限制极端的国家主义。他说,“以世界优越之民族,由家族团体,进而为地方团体,更进而为国家团体。近世欧洲文明进于中古者,国家主义,亦一特异之征也。第国家主义既盛,渐趋过当,遂不免侵害人民之权利。……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现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第衡之吾国之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就之良方。”他用“惟民主义”来定义或充实国家主义。“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14]很显然,陈独秀所接受的国家主义只是“民主的”或“人民的”国家主义,而非任何一种国家主义。
关于国家主义与人文主义(humanism)的关系,是最近这些年提出来的问题。问题提出的背景大致是:由于各种形态的国家主义教育主张都强调国家价值的优先性,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忠诚、牺牲、服务和贡献,因此有可能会导致教育过程中忽视个人的存在,忽视个人兴趣和需要的满足,忽视个人多方面潜能的发挥等问题。一部分人担心,在朝向国家主义理想的教育工程中,个人仅仅被看成是实现国家主义理想的材料、原料或工具,而不是被当成独立的、完整的和有人格尊严的人来看待,不是被当成目的来对待。基于这种担心,最近这些年,在中国的教育学界,尽管很少见到有人公开地质疑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但是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潮却大有汹涌澎湃之势。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中谈论“人”、“个体的人”、“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意义”等主题越来越多,“素质教育”、“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口号也屡见不鲜。从一定程度上说,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日渐兴盛,而国家主义教育理想逐渐地失去色彩。尽管国家主义的若干标签还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和教育政策文件之中,但是事实上并不为人们所看重,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失去了作为教育理想所具有的召唤性质,在很多时候只是为某种教育改革或某项教育工作提供最后的合法性证明。在相当程度上,如何缝合国家主义与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之间的间隙是当前我国教育学界亟待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五
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中国的出现,就如同政治学领域国家主义的出现一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针对性。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蹂躏半个多世纪之久,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对外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对外争取独立和尊严,对内追求统一与和平,成为那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派政治势力,不管是真提倡也好,还是假拥护也罢,都高举国家主义的旗帜,以达到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凝聚党内力量、赢得民众支持的目的。这种社会历史的境况,正是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产生的温床,也与近代以来欧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主义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产生路径完全相同。在普鲁士,面临着拿破仑战争以来对于法国的弱势地位,正是由于从19世纪初期开始大力鼓吹和培育国家主义精神,促进了普鲁士各邦之间的认同和团结,在普法战争(1870—1871)中打败法国,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迅速地发展成为欧洲大陆的新兴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提出开放性的“脱亚入欧”与“和魂洋才”口号,同时不断地强化“国家独立”和“国民教育”的思想③,使得日本这个东方小国迅速崛起为敢于挑战世界秩序的亚洲强国,在甲午海战(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等战争中赢得一系列的胜利和巨大的国家利益。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包括教育精英们正是从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历史事实中受到深刻的启迪,才提出和支持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事实上,不独在20世纪初期是这样,整个20世纪的中国教育界,都流行着近代德国和日本因教育而崛起的历史神话,把它作为大力发展和优先发展现代教育事业的一个有力辩护。20世纪的其他教育理想,像人格教育、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全面发展教育、生命教育、创新教育等等教育理想都受其影响,或多或少地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
回顾20世纪以来教育中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兴起和嬗变的过程,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不同历史时期教育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和生死存亡之际,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主张“教育救国”;在国家陷入军阀割据、内部分裂的危险时,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主张“教育建国”;在国家独立和政权更迭之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时,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主张“教育兴国”;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时,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又主张“教育强国”,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不论不同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性质和内涵有何不同,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一直是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建立和推动现代教育事业发展的一股深刻力量。在20世纪多种多样的教育理想或思想体系中,国家主义始终居于一个核心或支配的地位,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成为主导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追求。依据这种教育理想,“国家利益的追求是教育改革的原动力,教育的每次改革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追求新的国家利益。”[15]
不难发现,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对于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支配性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的。首先,国家逐渐地赢得了教育权,国家以外的个人、社会机构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禁止举办任何形式的教育事业。虽然2002年12月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承认了民办教育的公益性和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依然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民办学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教育质量,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类人才。”“民办学校应当贯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至于外国个人和组织在中国合作办学,则于2003年9月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贯彻中国的教育方针,符合中国的公共道德,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热爱祖国,品行良好,具有教育、教学经验,并具备相应的专业水平。”“外国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和开展宗教活动。”这些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近代以来知识界、教育界一直关注的国家教育主权不受侵蚀和颠覆。其次,形成了浓郁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渗透在政治、历史、地理、语文、哲学等各个学科之中,影响着相关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和呈现,并通过升旗仪式、唱国歌、庆祝国庆节、以学生为主体的党团队活动等丰富多彩的学校文化生活体现出来。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国家意识、国家责任以及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精神得到很好的培养,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抗美援朝等期间,体现为积极的、进步的爱国主义行动。另外,正是在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召唤下,教育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得到了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系统的高度支持和配合,教育话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国家财政的教育投入水平不断提高,教育系统的改革和发展走着一条自上而下、行政主导的道路,教育公平的水平和教育质量都得到了有力的外部保障。诸如此类的因素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能够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迈过道道难关,迅速建立和支撑起一个规模庞大、体系完备、质量较好、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原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奇迹。
六
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动员了国家力量参与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对整个世界现代教育的发展都起着引领性甚至是奠基性的作用。然而,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对于整个现代教育和现代社会的贡献也并非总是积极的,也有其消极的或负面的东西。认识这些消极的或负面的东西,对于人们全面地、辩证地理解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理解现代教育与现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局限性在一开始就为人们所意识到。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教育国家化运动在普鲁士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反对的声音,卡姆佩(J.H.Campe,1746—1818)曾经总结过反对的主张,如国家不应该阻碍公民按他们自己的希望教育自己的儿童;国家不应该妨碍教育的自由;国家不应该有享受特权的学校;国家不应该给任何教师付报酬;国家不应该建立对学校的任何形式的控制和监视;国家不应该有自己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而应促进全社会在学校事业上主动性的发展。[2]440-441这种反对的声音可能受到西方古老的家庭教育传统和宗教教育传统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其保守性。那个时候,不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日本,教育国家化的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地开始。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们对于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反对就不仅仅出于传统的教育文化立场,而且是基于对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现实影响的实际观察了。正如斯格特(J.F.Scott)在《教育中国家主义的危险》(1926)一书中所说,“在国家的保护下,时常也得益于政府的大力鼓动,教育中逐渐形成了国家主义的教条。这种教条所产生的有害影响甚至超过历史上的宗教教条。在和平时期,这种教条所产生的影响还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当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这种经由学校所强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教条就会成为点燃沙文主义的火种。如果人们分析任何战争发生的心理根源,就会发现这一点。”[16]206皮科(Cyrus H.Peake)在《现代中国的国家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也敏锐地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经由学校系统反复灌输国家主义思想,人们形成了一种对待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非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明显阻碍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广为人们所承认的事实。”[1]pxiii正是在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支配下,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历史教育“都充满了自夸和自负。在每一个国家的教育中都有一种倾向,不像重视研究自己的祖国那样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国家的历史;都有一种倾向,从有偏见的国家主义立场来解读战争的根源。这种倾向在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三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学校在历史课教学中都基于一些片面的证据和战时的宣传来阐释战争爆发的原因,而不是基于无偏见的历史研究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被用来作为教导学生厌恶别的国家的主要工具。”[16]209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造就了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现代强国的崛起,但是也很快地就蜕变为种族主义(racism)、法西斯主义(fascism)、沙文主义(chauvinism)、军国主义(militarism)教育,主张对外侵略,对内实行集权统治,从而把它们和其他国家一次又一次拖入到战争的泥坑中去,给本国人民和他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20世纪中国教育中的国家主义理想尽管在形式上与欧洲和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但是却并没有发生质的蜕变,没有驱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从争取国家独立、统一和富强的道路走向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20世纪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究其性质来说都是自卫战争,而非侵略战争。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和平精神有关联,它使得现代中国尽管追求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但却不追求对外的扩张,坚持走睦邻友好与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过,尽管如此,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在推动整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同时,也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需要诚实和仔细地加以辨析与讨论。曾几何时,为了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我们的历史教材也像英国、德国、法国的历史教材一样,充满了“自夸和自负”,一方面不能帮助学生正确地了解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成就,另一方面也不能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别国的历史和成就,总是带着有色的眼镜去观察别国的历史、现实和人民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学校系统所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祖国还是有着休戚与共关系的邻国,或是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都是某种程度的一知半解,甚至还存在很严重的认知错误。这种状况已经影响了中国民众对于世界或别国事务的态度、立场和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还影响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曾几何时,为了培养学生服务国家、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号召大批青年学生完全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选择,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尽管在这些事件中,青年学生们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令人感动,但是一旦他们放弃个人的兴趣、爱好和选择,被选择到不适应的环境做自己缺乏专长的工作,其结果不仅个人的发展可能被延误或耽搁了,而且总体上说,国家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曾几何时,国家收回了教育权,将教育主权与学校的举办权完全等同起来,通过各种途径消除了教会学校、私立学校、乡村私塾等等,建立了单一的由国家管理和财政支持的国民教育新体系。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样做是顺应时代要求有进步意义的,对于建立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今天看来,也存在着值得讨论的问题。国家对教育权或学校举办权的独享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挫伤了社会组织机构或个人办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整个教育系统对于国家权力或政府行政的过度依赖,这可能也是导致如今人们所说的“行政化”问题的体制性原因。从历史上看,国家并不是教育事业天然的举办者和垄断者。国家对于教育权的垄断在西方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且本身也是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如何在尊重和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国家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角色,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联系越来越丰富,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许多国家的密切合作。为反映这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现象,一些当代的学者如沃尔隆(Jeremy Waldron)、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力图超越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重新提出了古希腊时期就产生、在启蒙时代得到发展、在国家主义产生之初就已经提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inism)主张,并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教育理想,致力于培养有同情心的“世界公民”(cosmopolitain citizen or the world citizen)。与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有很大不同,世界主义的教育理想强调引导学生将对于人类的“忠诚”放在对待国家、地区或各种社会群体内部忠诚的前面,并帮助他们形成对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传统进行批判性检验的能力、形成学生通过学习和关心意识到与其他人类或群体休戚与共的关系的能力以及想象性地同情他人的能力,等等。[17]这些主张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18]——新时期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必须考虑进去国际主义的因素,否则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就可能是狭隘因而也是危险的国家主义。
随着世界主义教育理想的出现,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21世纪会褪色吗?我看不一定。事实上,自从“9·11事件”发生以后,最早提出世界主义教育理想的美国学校,就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力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上强化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2002年3月7日,美国教育部制订了《2003—2007年战略规划》,教育部长罗德·佩奇在部长声明中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她经受着那些妄图毁灭民主与文明的人们的袭击,对此,她必须以决心、力量和怜悯作出回应。在国家所面临的众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中,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关注着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他还说,“9·11事件”“唤醒了沉睡的决心、爱国心和群体精神。……教育部将使教育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来源。”依据这个战略规划,美国联邦教育部致力于发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唤醒学校对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感”[19]7-8;在战略目标中,战略规划提出要“扶持高质量的、传统的美国历史课程”,“组织一些侧面影响大的活动,像忠于美国的宣誓活动,鼓励在全国学校中关注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我们也鼓励课程中贯穿美国精神和民主原则的教学”。[19]422001年,日本《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彩虹计划)也提出,“本教育新生计划以实现‘日本的复兴’为目标,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19]369俄罗斯在新世纪伊始,也颁布了《俄罗斯联盟政府关于教育兴国思想的决议》,以决定2025年以前俄罗斯教育系统发展的预期目标。在教育战略目标界定上,该决议明确提出,“建立俄罗斯社会—经济与精神发展的牢固基础,保证人民生活与国家安全的高水平”;在谈到教育的基本目的和任务时,该决议指出,“继承、保存、发扬、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人民珍惜祖国的历史文化”,“培育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非宗教性”、“保持和发展作为多民族俄罗斯国家团结因素之一的俄语的重要作用”;决议还提出,教育兴国,就是要通过超前发展教育,“把俄罗斯从危机中解脱出来,保障我们民族的未来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俄罗斯公民的生活和尊严”。[19]412-419阅读以上世界各国21世纪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形成于19世纪、兴盛于20世纪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旗帜到了21世纪依然会高高飘扬!
收稿日期:2011-10-16
注释:
① 余家菊先生认为,“外国在我国内设立学校,不存政治侵略之心,即怀经济侵略之图;不怀经济侵略之图,即具有文化侵略之意。如赔款学校,其动机多在政治的与经济的方面;如教会学校,其动机则多在文化侵略,而其结果则实为政治侵略与经济侵略的前驱。吾人为国家之生存计,为文化之延续计,为社会之安宁计,而主张收回之,实不得已也。”(参见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上),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
② 周作宇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趋同趋势。多样化办学模式的出现和市场力量的介入是其显著特征。在市场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经济主义”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其一,在知识经济或所谓新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被强化,由经济价值界定高等教育的目标。其二,由经济关系界定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关系。其三,由经济投入界定高等教育的内部质量。其四,由经济利益诉求界定学术人员的行为驱动力。经济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大学的身份具有深远影响。潜在的结果是,由于夸大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而使大学的功能窄化;由于服从于外部的现实利益而使大学的独立性受损;由于大学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边界模糊化而改变大学成员的行为,进而改变着大学的身份。(参见周作宇:《论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其实,“经济主义”倾向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而且广泛地存在于一切教育领域。
③ 福泽谕吉作为近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念念不忘的就是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提出,“把我国的独立作为终极目的。就好像把今天的人世间一切事物融化成一个东西,而把所有这一切都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这样,这种手段就会多至不可胜数。举凡制度、学问、商业和工业等等无一不属于这种手段。……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采取各种方法手段才能成功的,所以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同时也非多不可。(然而),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的目的。……维系目前日本人的心,为此一法而已。”(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93-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