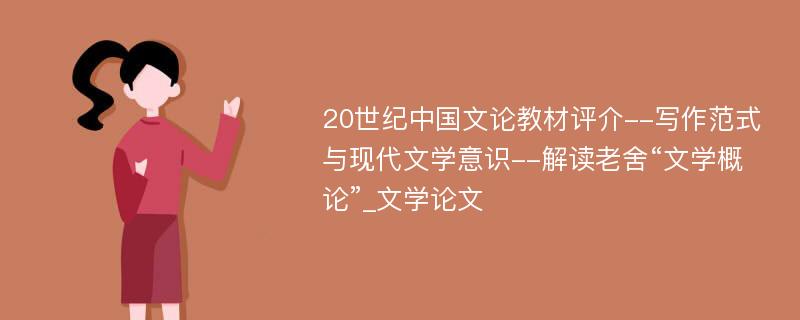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教材评估——文学理论的书写范式与现代意识——读老舍《文学概论讲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老舍论文,范式论文,讲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核心论题。文化的冲突和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表现在各门学科的体系建构中。在此,回顾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回看五四前后文化冲突和现代转型最为激烈的时代,学界前贤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对于推动今天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变革,对于新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拟选取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该书为老舍先生1930—1934年在齐鲁大学的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为例,看看早期中国文学理论的思想趋向和写作体例,以期为当代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寻找借鉴和灵感。
五四以后,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我国传统思想的局限,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在文学理论上则体现为对建立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追求,它包括的内容,一是引进西方的文学思想,二是梳理并发掘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利用两种资源建立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老舍先生便是当时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一员。老舍对中西文学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对文学有着独立思考的文学家。相比当时的田汉等人,同是文学家的老舍并不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其《文学概念》更趋近文学的特性,其写作体例也更有自己的特色,如他对文学学科的辩证理解,对诗歌特点的形象介绍,对文学形式的灵活态度等。需要说明的是,与田汉等人的《文学概念》一样,老舍的《文学概念讲义》从体系构架、问题视域到基本观点都受到了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影响,而本间的《文学概论》又吸收了英国批评家温彻斯特《文学评论原理》的影响,这也反应了中国当时吸收西方思想的一个特点,即以日本为中介间接接受西方。但老舍的这种借鉴意义重大,不仅以后的各种文学概论都以此为蓝本,而且在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前,中国文艺学界翻译引进的也主要是本间九雄《文学概论》里所援引的书籍。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共有十五讲,按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谈中国历代文学思想;第二部分,从文学的特质、创造、起源谈何为文学;第三部分讲文学的形式,包括文学的风格、体裁和种类;第四部分谈文学批评。从目录看,老舍并没有如中国后来的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文学理论那样从文学的外部关联看视文学,而是主要从文学内部来谈文学,80年代初文艺学界的“向内转”、文学的“内部研究”即此之谓,在此,老舍先生是从其所接受的西方纯文学观来看视文学理论问题的,这构成了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其次,从个人文学创造的体会以及对中西文学历史发展的透彻理解出发,老舍先生表现了某种现代性特征的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在此基础上,老舍提出了富于时代特点的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价值的文学思想。这些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以文学家笔法书写文学理论,把文学理论的抽象性结合于文学现象的具体性和文学体验的生命性,这对于当前文学理论的书写体例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在正文之初,老舍梳理了我国古代文论并作了评论,其看视之点是老舍接受的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这种文学观认为,艺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是审美,舍此艺术别无他图。西方纯艺术论最早可追溯到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论,其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移情说、距离说、内模仿说等各派心理学美学,当时风行西方的柏格森和克罗齐的直觉论美学,王尔德、波德莱尔等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则构成了影响中西的纯艺术论大潮。从这种纯艺术观出发,老舍对古代文论的载道传统多加以否定批评。老舍批评了古代文论中“文”与“文学”不分,把文学与“道德”、“政治”等相依附的弊病,对于《文心雕龙》则得出了“《文心雕龙》的影响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为它塞住了自由创造的大路”(19页)的结论。造成老舍如此立论的原因当然是文学理论的探索期急于学习西方,并以西方文学观念衡量中国即以西释中的结果。在西方逻格斯中心论和现代纯艺术论看来,中国传统文论的载道观和非体系非逻辑性特点当然是要加以否定的。正是基于此,老舍放弃了后来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以纯文学观为视点,老舍对于从文学内部谈文学的说文者则给予了肯定,如对陆机《文赋》的评价是“对文学已有相当的体认了解”。老舍接受的是西方现代心理学派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的根本动机就是人的心里的表现,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感情,因此,在他看来,袁枚可算作中国最大的文学批评家。
这种纯文学观也影响了作者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评价。老舍认为新文学是“文学革命的一个局部问题……不是讨论文学的本身”(34页)。对革命文学的评价也不高,认为“以文学为工具的,文艺变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的侍候他”(35页)。老舍始终主张从文艺来谈文艺,即使在第五讲里对文学在特定时期的功用有所肯定,他仍然反对违背文学本身的特质直接宣讲政治。从中国后来文艺社会学的极端发展来看,老舍先生的这种告诫真是先知先觉,对于当前文艺学界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联的讨论也颇有启发。但是,今天看来,基于时代文化的特殊性,从纯文学观出发,老舍对我国古代文论的评述难免有失偏颇,对中国文论和文化的特殊性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更没有对之加以利用和创造性的转化,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初期,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的文学和文化选择的普遍特征,这一特点被后来的学界称为以西释中或以西例中。中国当代文艺学在反思百年古代文论转换的问题时,以西释中被认为是百年文论失语的最大根源。但这种批评在我看来是过于苛刻,它缺乏对于前人的同情性理解。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初期,在文学理论的草创时期,没有对西方的全面接受,没有对西学范式和学科建制广泛的吸纳,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不可能实现,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也无从谈起。我们在批评以西释中的同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学科规则和学术规范正是在这样的“矫枉过正”中实现的。因此在当前文艺学看来是缺点的老舍先生的西学眼光,在我看来正构成了本书的特点,也正是这样的眼光实现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
第二,老舍主张向西方学习。那么,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呢?首先,要学习西方理论体系的明确性和系统性,“对于研究的对象须先有明确的认识”,此即西方的“科学”的治学方法,这正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缺乏的。但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并不能错误地加以理解,老舍举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评量一切文学的例子来说明文学理论不是僵死的,而是流动变化的,从这种思维出发,老舍反对给文学下明确的定义。老舍认为,对于什么是文学恐怕永远不会得到最后的答案,因为科学定义就意味着“经过逻辑的手段,从比较分析归纳等得到那一切文学作品所必具的条件。这是一个很大的志愿,其中需要的知识恐怕不是任何人在一生中所能集取得满足的”(1页)。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老舍也多次强调了文学观念的历史性,认为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而发展变化的。因此,讨论文学的特质才是更妥当的办法。那么文学的特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老舍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以载道等观点把文学看成是理智、意志的载体是不恰当的,文学的特质不是理智,因为讲理的有哲学,供给我们知识的有科学。老舍认为文学的特质之一是感情。虽然感情的具体内涵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人们读文学是为求感情上的趣味却是万古不变的。可以看出,这种观点与当时田汉等人一致,它来自西方现代的心理学美学和浪漫主义理论。对于个性解放时代的情感抒发而言,这种文学观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老舍也看到了伟大的文艺常常有伟大的思想和哲理,但是他认为,“文艺中怎样表现这思想与哲理是比思想与哲理的本身价值还要大得多”(40页),否则的话,文艺便与哲学无异。道德也不是文学的特质,因为文学有美,美也是文学的特质之一。那么,文学家怎样将美传达出来呢?回答是通过想象。文学以文字为工具,要用文字表现形象具体的世界,非有想象不可。老舍以诗意语言总结文学的特质: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它们飞起来的那点能力;文学是必须能飞起的东西。老舍认为,文艺的社会背景、作家的历史等都足以帮助我们更多地认识一些作品的价值,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没有这些,文艺本身的价值并不减少。老舍认为文学是一种创造,是人心灵的创造。那么人们为何要创作呢?回答是:为满足个人。老舍认为,没有人不想表现他自己的,这种表现力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促动人类做事的原力,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性都是通过个性心灵表现出来的。可见,老舍的观点来自日本的厨川白村,后者又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文学观。
这里,文学表现情感说、文学与哲学的关联、文学的三个特质以及文学诉诸想象等观点现在看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后来苏联化的文艺学理论体系中,这些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反而被祛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老舍对于前此中国文学思想增添了多少新东西,也不是老舍的观点对于中国当代文艺学历经曲折后回归文学本体的借鉴价值,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对于文学特质探讨的思维方法的现代意义。在现代西方反黑格尔反形而上学的声浪中,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模式被逐渐抛弃。当前中国致力于文艺学边界扩张和文艺学范式变革的学界中坚则自觉地应用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和王一川撰写的《文学理论》中,作者均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伊格尔顿和卡勒对于文学的反本质主义观点成为其理论支援,文学不再在社会结构中获得本质性规定,比如王一川区分了本质和属性,以属性论取代本质论,以对文学概念的语言学追寻厘定文学的现代含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先生以其对文学历史的深刻领悟暗合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创造。对于文学的起源问题,老舍也表现了某种现代思维的特点。老舍认为有三种人喜欢研究文学的起源,一是研究院的学者,二是历史家,三是艺术论的作者。他们都想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文学,这是他们的好处。可是他们也想把研究的结果做得像统计表一样固定,这是他们的局限。老舍认为,文学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是随时代生长的。虽然艺术的产生和需要有关,但是我们不能拿原始人类的实用艺术解说今日的艺术,况且,初民的装饰、跳舞、音乐是否也有美与情感在其中是值得讨论的。所以虽然“文学的起源确是个有趣味的追讨,但是它的价值只在乎说明文学的起源,以它为说明文艺的根据是有危险的”(60页)。作者还批评了与文学起源论有同样弊病的另一种倾向,即以现代的文学趋向否认过去文艺的价值。看看今天仍然书写在各类艺术概论和文学概论里的艺术起源论,看看老舍先生对于艺术起源本质论思维的批评,我们会慨叹,学术的进步是多么缓慢!
第三,老舍对文学现象有着自己深入而独特的理解,他的批评也带有鲜活的个体体验性,语言深入浅出,读来亲切流畅而不乏趣味,常以具体的例子和生动的比喻代替抽象的说理。这样的例子在讲义中真是信手拈来:如在第十三讲论诗中,老舍没有给诗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在与其他文艺的区别中指出诗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感情。因为有了强烈的感情,才激起了诗人的奇妙的想象,进而唤起物我之间的新的感觉。接着作者以雪莱和苏东坡为例,指出诗之所以使我们狂喜,是因为它是感情找到了思想,而思想找到了文字。最后老舍总结说:“我们不愿提出诗的定义,也不愿提出诗的功能,但是,在前边的一段话中,或者可以体会出什么是诗,与诗的功用在哪里了。”(133页)再如在说明风格不等于修辞时,作者指出苏东坡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个极普通的字作成了一幅伟大的图画,而左太冲的“树则有木兰梫桂杞櫹桐棕桠楔枞”只能是砌墙似的堆字。三言两语便深刻地表明风格不只是以修辞为能事的。在论及想象的复杂过程时作者更是运用形象的语言使之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假设文学家的心是甲,外物是乙,外物与心的接触所得的印象是丙,怎样具体的写出这印象便是丁。丁不仅是乙的缩影,而是经过甲的认识而先成为丙,然后成为丁——文艺作品。……再具体一点说,甲是厨子的心,乙是鱼和其他材料,丙是厨子对鱼与其他材料的设计;丁是做好的红烧鱼。”(55页)等等。
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界,文学理论多为中文系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编写,由于对具体文学现象的隔膜以及惯于对文学本质的哲学思考等原因导致了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理论化和抽象化,对于文学理论的教学以及理论与批评实践的互释来说,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以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例,该书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结构逻辑框架,以中西文学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展开论述,最后对中西文学思想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考作一比较。阅读全书发现,作者基本上没有引用文学作品,完全是以中西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组接文学理论,即看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学思想对于这一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由于缺乏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印证,也没有文学批评实践的范例,文学理论教材显得抽象飘浮,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的互释,文学现象对于文学理论的本源性意义以及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现象的理性观照等都无法得到体现,对于教学的生动性要求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缺失。文学理论的形象性生动性并不仅仅是教学的需要,它有更为根本的哲学缘由。作为对本身是生命体验的文学而言,理性的语言在获得明确性的文学认识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学感兴生命的遮蔽和扼杀,这一点在西方现代美学有明确的意识。柏格森认为,理性思维只能在事物的外围打转,我们应以绵延把握事物的本质,克罗齐强调审美直觉,尼采以诗意语言表达哲学,海德格尔伸张“是”本身的自由性和超语言性,维特根斯坦把审美活动置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德里达解构诗与哲学之分等等都说明,作为审美之凝结,我们应以诗意的语言而非逻辑理性的语言言说文学,只有诗性语言才能接近本是生命体验的艺术审美。这一点,中国传统的诗评即以诗言诗、以禅喻诗等话语方式具有独特的价值。再看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术语成篇,语言枯燥,使得文学概论的学习成为学生的一种负担。当前文艺学的困境除了理论陈旧、知识老化、缺乏对新的文学现象的观照等原因外,教材写作的抽象性,对于活生生的文学现象的亲和性的缺失也是其弊病之一,再看看老舍先生的文学讲稿,我们是否能够获得一些启示呢?
当然了,作为探索时期的文学理论,现在看来,老舍的《文学概念讲义》具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如对文学语言研究的浅陋,对读者阅读的缺失,对文学的文化性的不够重视等,但这些按照解释学的说法,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传统视域,我们不能以从时代获得的“厚爱”苛求前人,关键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老舍先生可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重温旧书,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有此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