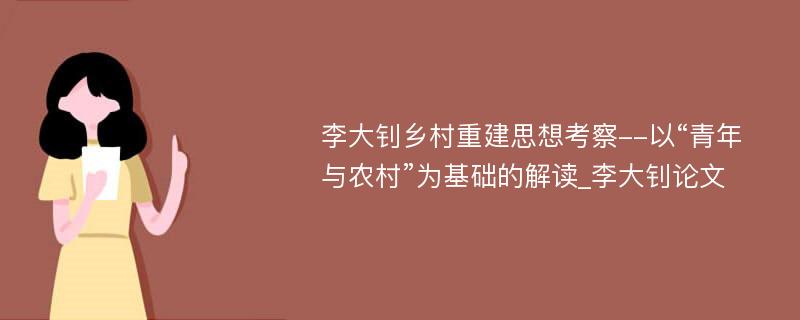
李大钊农村改造思想考察——基于《青年与农村》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思想论文,李大钊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8)04-0054-05
《青年与农村》是李大钊写于1919年2月的一篇充满激情的政论文。一些学者曾据此文的若干段落断言李大钊为民粹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早期共产党人,甚至认为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民粹主义并无不同。①李大钊究竟有没有受到俄国民粹派思想的影响?他是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传播了民粹主义?这些问题的解答既需要我们正确理解俄国民粹主义,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是基于何种思想取向与现实背景。
一
《青年与农村》写成于李大钊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全文篇幅不长,但主题鲜明,呼吁青年人“到农村去”,改造农村、建设新国家。文章交织着两条清晰的思想线索,即李大钊的民众观和青年观。
《青年与农村》表达了李大钊一贯的民众观。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演进的伟大力量以及将他们动员起来参与直接的革命行动的重要性。他把自1916年以来形成的“民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民众之意志”、“民众之思想”视为历史和政治的最终起因。②因此,《青年与农村》中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设计:中国的革命,必须从底层的解放开始,从对农民的教育与动员开始。与此同时,李大钊看到了民众的伟力与民众的“愚暗”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农民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中国的解放;另一方面,农村状况的恶劣和农民面临的野蛮统治又使得解放农村的任务异常艰巨。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解决这样一种现实困境不能靠农村自生自发的力量,需要注入新鲜的青春的活力。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李大钊逐渐形成了一种“青年情结”,他在《〈晨钟〉之使命》、《青春》、《青年与老人》、《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中热情讴歌了青年,赞美青年的生命本能和“自由意志”,将青春中华之再造的美好理想寄予青年,并“默许其独享之权利”。但是,李大钊又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同农民一样也身陷现实的困境,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但并不知奋斗的方向。《青年与农村》以一种特别低沉和忧郁的笔调描述了青年人在城市的生活,认为青年羁留在了无生气的官僚把持的都市,愚蠢地为自己的官僚生涯竭尽全力,而不愿意到农村去,这样的结果不仅自误,而且还会辜负了农村。因此,知识青年应该肩负起双重的使命到农村去,一是参与“手足劳动”进行自我历练,二是帮助农民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们应该学习俄罗斯青年的榜样,和农民打成一片,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发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脱去愚昧”③的道理。
《青年与农村》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五四运动酝酿过程中的思考方向和行动目标。在“尊劳主义”和“劳工神圣”的社会氛围中,在各种社会改造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这篇文章吹响了鼓舞青年走向直接革命的号角。
二
李大钊的“到农村去”的号召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有着怎样的关联,这是我们正确评价李大钊的农村改造思想的关键。
俄国民粹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既有自命为“民之精粹”的英雄主义一派,也有“以民为粹”或“粹藏于民”的平民主义一派。但总的来说,他们在思想主旨上相近,即崇尚人民的力量,“对农民存在感情上的依恋,并且对于农民自身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④。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即村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达到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性区别,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从民粹主义中吸纳了民主主义的成分,但他们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从来都是很严厉的,认为民粹主义所信仰的村社制度事实上正被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削弱,而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将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
李大钊接触到俄国民粹派的有关思想,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从辗转获得的关于早期民粹派“走向民间”运动的资料中发现了一种有借鉴意义的社会改造模式,他尤其欣赏在这一运动中那些试图与农民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出来的时代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场俄国民粹派青年的运动正好呼应了他的青年观,他希望中国青年仿效俄国青年,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⑤。《青年与农村》的内容进一步表明,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俄国这场“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运动的革命性,以及它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改造的借鉴意义。他在《青年与农村》中表达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努力解救农村、与农民结合的思想,就社会改造的动力与方式而言,与早期民粹派的思想确有相通之处。如果说李大钊社会改造理论没有直接取自俄国民粹派的东西,那它们之间至少也“存在着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⑥。这种“共鸣”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和精神上的优越性。俄国民粹派认为,都市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产物,充斥着工人的赤贫和资产者的贪婪,以及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都市为依托猛烈地冲击着广泛存在于俄国乡村的民族传统。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与俄罗斯传统模式之间的冲突使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下意识地寻求“俄罗斯精神”的支持,以维持民族传统与民族认同,他们将目光投到最具“俄罗斯精神”的广大农民身上。
李大钊的农村改造理论也建立在都市与乡村的对立之上。他把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描绘成一幅质朴的田园生活,而对污浊的城市生活极度反感。《青年与农村》将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进行了鲜明的对比:“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上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这样的对比,目的在于帮助青年人作出明智的选择:“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⑦这种对农民阶层的道德称颂和对农村生活的憧憬在李大钊的思想中独具特色,即使在他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1922年,他同情和向往乡村生活的思想感情仍然洋溢在他的许多文章中。
二是青年知识分子对农村觉醒负有义不容辞的使命。俄国民粹派相信,俄国农民中盛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即“米尔精神”(村社精神)是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广大俄国农民手中掌握着国家的未来。但是,由于农民无法真正拥有土地和自由,仍然生活在痛苦与不幸中,他们并不能自觉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俄国农民缺少对自己的任何尊重,愚昧地忍受一切形式的压迫。”⑧与此相对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充满着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激情,他们偏向于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他们赋予自身的使命,即解救痛苦中的人民。因此民粹派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超越社会阶级的且有道义责任和领导能力的自主阶层”⑨,在解放农民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李大钊认识到只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但他并不主张农民经常进行自发、分散的反抗,也不认为他们具有这种意识与能力。而且,农村的教育机关很不完备,“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农民“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⑩因此,不能指望那些“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他寄希望于在都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希望他们为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解放,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激发农民身上潜在的政治自觉。由此,李大钊将他对乡村改造的目标与青年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结合在一起,目的既在于解救乡村的颓败,也在于激发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
李大钊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与民粹派思想有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只是表现在实践的、形式的层面而非思想主张层面。迈斯纳曾指出:“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而是过去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迹感染了李大钊,引起了他的想象,似乎这些事迹可以在中国仿效。”
三
李大钊在1919年5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正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之前,即他写作《青年与农村》时,他仍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广泛地寻找各种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实践模式。他的思想体系中有着多种元素,包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西方宪政民主理论以及日本新村主义政治思潮等,民粹派思想也是其中一种。当时李大钊主要是通过日文译本间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他对以村社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民粹派思想的了解是不充分的和片断性的,甚至还存在着误判。例如他认为早期俄国民粹派在农村的实践酝酿了俄国“彻底的改革”的新机,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与年轻的民粹派在俄国农村早期活动有关联,但事实上,十月革命并非前期民粹主义者活动的结果,民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在根本原则上存在差异。(11)因此,很难说李大钊完全掌握了俄国民粹派的思想内涵。李大钊的“到农村去”与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在形式上的某种联系,并不能证明其改造中国的政治设计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就思想内涵而言,俄国民粹派思想与李大钊的社会改造思想是两个差异甚殊的体系。
首先,对农村传统与社会主义目标关系的认识不同。俄国民粹派对农村抱有幻想,它最重要的思想特征,就是把传统的农村公社(村社)视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俄国村社是一种充满宗法家长制传统的古老的农村所有制形式。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他们把落后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认为它能够合理分配土地、合理经营并萌发劳动组合的生活,因而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他们希望通过保存村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
但这种村社机制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虽然和俄国一样,也是以农立国,但中国农村私有制的发展要比俄国更充分,中国农村并没有天生的集体主义者,不存在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传统与机制。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后,并没有现成的条件用以发挥民粹派所说的农民的“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因为中国农村“根本不具备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12)。《青年与农村》高度肯定了乡村生活的价值,也表达了对这种生活的由衷的向往,但李大钊在此文及其他文章中从来没有对中国农村的传统抱有幻想。相反,他常常痛心于农民的不觉悟,他们“不幸生活在组织不良社会制度下,眼看人家一天天安宁清净去求知识,自己却为衣食所迫,终岁勤动,蠢蠢的像牛马一样,不知道人间何世”(13),“世界潮流已竟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在那里,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还只是听官绅们宰割蹂躏,作人家的良民”(14)。正因为对农民大众的深刻体察,他将解救“愚暗”农民的责任赋予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希望青年人对农民进行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教导他们认识共和为何物,培育他们的国民意识,从而为立宪政治创立一个“立宪的农村”。
其次,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工业化的态度不同。俄国民粹派痛恨西方资本主义,怀有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这是由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民粹主义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的。虽然李大钊也像民粹派那样赞美过乡村的前工业化生活,但他对乡村的好感与其说是一种基本政治倾向,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流露。他并没有像俄国民粹派那样,对西方的工业化持深恶痛绝的态度,这与他的乡村生活根本改造的设想有关。他认为,人们无法依靠中国乡村的任何现存的机制或条件,必须准备好对农村进行根本的改造,具体方法就是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寄希望于工业化的未来。此外,他在提出“到农村去”的同时,还提倡开展工人运动。1919年3月,他曾著文为唐山煤矿工人罢工因没有“工人组织的团体”领导而失败感到惋惜。在这一点上,他与民粹派有根本区别。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表示,青年人追求民主政治,应立足于建设立宪的民间,帮助农民掌握选举权,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设想实际上还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这与他正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事实并不矛盾,他当时十分关心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广大农民如何培养自己的宪政意识,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一时期,由于他还没有完整地树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思想,他对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理论的探求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在对待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存在差异。俄国民粹派崇拜人民,更崇拜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觉性,这使得民粹主义运动带有革命的唯意志论色彩。19世纪60年代,民粹派青年基于对农民的崇信而到农村去,他们穿上了农民服装,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散发鼓动革命的小册子,和农民交谈,宣传重新分配土地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号召农民反抗沙皇,反对宗教,建立社会主义。在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或者遵循巴枯宁的建议,将农民视为一个整体,对他们进行政治化教育以帮助他们弄清楚是如何被压迫的;或者追随拉甫洛夫,把与人民一体、与人民同甘共苦、形成集体的革命意识视为己任;或者接受特加乔夫的观点,认为人民不仅没有能力独自进行革命,在思想上也消极保守和缺乏革命性。总之,民粹派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解救”农民,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改造自身的必要性,他们更专注于使“劳动分子知识化”。
受俄国民粹派的革命实践启发,李大钊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他痛惜中国的“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15),表现出“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因此,中国的解放需要借助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性,而青年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理性,宣传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唤醒民众的斗争意识。但是,与俄国民粹派不同的是,李大钊更主张知识分子应在工农中改造自己。他多次在文章中强调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应该到农民中接受教育,因为怠惰的青年还没有真正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他们到农村去,不仅是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还是从城市的腐败影响中挣脱出来的机会。在农民中,知识分子除了做启蒙工作外,还要和农民一起劳动,“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16)。他后来将他主张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解释为,“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17)
由此看来,李大钊的农村改造计划实际上是双重的改造,即农民的改造与青年知识分子的改造。李大钊对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强调不仅不同于俄国民粹派,而且还纠正了此前的新文化运动脱离工农群众的缺点,这一思想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题之一。
正如迈斯纳所评论的那样,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青年与农村》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18)与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相比,李大钊较早地意识到中国农村解放的意义和农村现存的困苦,认识到青年人的责任与自我改造的必要,最早提出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青年与农村》是研究他的这一思想的重要依据。
注释:
①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莫里斯·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都提出类似的观点。国内学者李默海在《民粹主义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审视》、马宏在《五四时期拜民主义思潮评介》等文章中也赞同迈斯纳的观点,新加坡学者顾昕则直接认为“《青年与农村》是一篇典型的民粹主义文章”。
②参见〔日〕后藤延子:《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③《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9页。
④〔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⑤《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8页。
⑥〔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92页。
⑦《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51、652页。
⑧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6页。
⑩《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9页。
(11)参见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12)〔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94页。
(13)《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33页。
(14)《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9页。
(15)《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61页。
(16)《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52页。
(17)《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18)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94页。
标签:李大钊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农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