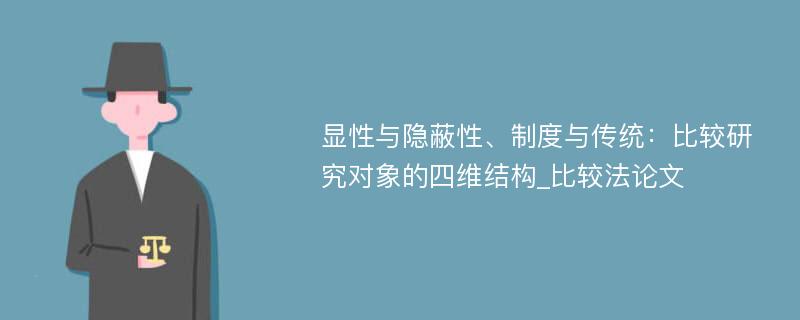
显性与隐性、系统与传统——比较法研究对象的四维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显性论文,隐性论文,四维论文,研究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1)03-0087-06
比较法面临着一场尴尬:比较法的范围无所不包,但又一无所有,她成了一个“灰姑娘”。其原因正如大木雅夫所言:“比较法不是像民法或刑法那样以法典为基本结构、从各种不同角度几乎穷尽所有法律问题进行详尽考察的学科分野,甚至不能说已形成了确定的体系。”[1]前言怎样划定比较法的“领地”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她的体系呢?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比较法则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比较法则亡。想要确定她的体系,就得先确定她的研究对象。深度剖析比较法的研究对象,可以发现:比较法的研究对象有两个并列的层次维度、一个系统维度和一个传统维度。本文希冀通过描述这个“四维结构”来框定比较法的研究对象。
一、框选比较法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比较法的研究对象包罗万象。如果以1900年为始点,① 可以看出,在早期,比较法学者倾向于具体细节的比较。例如,1903年法国的朗贝尔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比较法著作《立法共同法研究——比较民法的作用》,[2]55美国比较法大家威格摩尔的成名巨著《关于普通法审判中的证据法系统的论文集:包括美国所有相关法令和司法决定》写于1904年,[2]275这两部代表那时比较法研究状况的著作都是以具体细节比较为主。窥一斑而可知那时比较法的面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中国,竟没有一部比较法总论性质的书。② 但是,细节比较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会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就像动物学家在研究大象或蛇等动物时,只用显微镜观察它们各自的细胞是无法把握象与蛇在形态上的区别一样。”[1]62鉴于此,在比较方法上出现了一场转移,即从微观比较③ 转向了宏观比较。④ 久负盛名的威格摩尔于1928年出版其3卷本著作《世界法系概览》,就是“宏观比较”方法的“牛刀初试”。自此以后,功能比较⑤ 与文化比较⑥ 的方法相继兴起,比较法的研究对象遂呈扩张之势。直至书本中的法律、行动中的法律、法律的环境、条文、制度、文化、行为、思维习惯、历史根源、实践方案、一般功能以及发展等都被纳入了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中。[3]175
比较法的对象就像普洛透斯的脸那样变化万千,面对这张脸,我们该从何处入手才能理出个头绪呢?尽管比较法的目的多种多样,[1]67-68但是,其主要目的只有一个——为规制目标社会求取最优规则,其延伸方式有两种:制定最优的规则和优化现有规则——其他目的无非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目的作为匡选比较法研究对象的出发点。比较法虽然提供了比较模式来实现这个目的——求取最优规则,但是,使用这个模式的前提是:使用者知道目标规则群是什么。而规则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为了探清目标规则群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了解规则群后面的决定因素。以为规则只含存于实定法之中的观点从来都是实证分析法学派的一厢情愿。自然法学派认为规则后面还潜藏着“法的理念”,社会法学派更主张不同的社会习俗、“不同的文化对于同样的规则会赋予不同的含义,在规则的适用中也会作出不同的解释。”[4]因此,“我们不能把仅在国内通用的实定法看成法的全部。”[1]15-16不能以为框定了制定法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框定所有的目标规则群。在比较法研究中,实定法只是显性研究对象,它仅是冰山一角。它背后潜藏着“法理念”、隐藏着一套社会习俗、社会文化等诸多制约因素,它们也应该成为比较法的研究对象,它们构成了比较法的隐性研究对象。这就是比较法研究对象的“显性”与“隐性”维度,两个并列的层次结构。
另外,无论是理解和比较显性对象,还是理解和比较隐性对象,都必须要有系统的眼光。耶林就曾指出,不能把法律秩序当作无数泛规范的堆积,而应将其作为一个有机体。这必然归结为,进行比较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功能必须重新放回法律秩序整体的结构关联中加以确认。[1]94任何目标规则群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们与整个关联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理解目标规则群所处的整个系统,就不能理解目标规则群是什么。这样,也必须将目标规则群背后的整体框进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中来,这就构成了研究对象的系统维度。同样,不追溯目标规则群的发展流变过程,也不能真切地理解目标规则群是什么。“对一项法律制度的最好解释常常藏身于其历史而非它现在的运行中。”[5]73所以,目标规则群后面的传统也应被框进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中来,这就是它的传统维度。这样就以“求取最优规则”这一目的作为出发点,朝四面八方拓展,组合成了一个四维结构,牢牢地框定了比较法的研究对象。
二、层次维度上的研究对象
随着概念法学的瓦解,法的单一性已经成为过去的迷梦,它的多层性早已在我们面前展开。实定法仅仅是它的第一层或者表层的面相,它背后的要素若隐若现,但却不可小觑,它们与实定法一起在规制人们的行为,甚至决定了实定法的实效。如果说实定法是比较法研究的显性对象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比较法研究的隐性对象。显性对象与隐性对象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划分层次只是出于便利。韦伯曾强调:“那些应被称为法律的规范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法律、惯例和习惯属于同一个连续统一体,其中一个向另一个的转化是难以觉察的。……在这个连续统一体的哪一点上人们应当假定一项‘法律责任’的主观概念的存在,这完全是个术语学和便利的问题。”[6]2为了便于理论的分析,我们仅将实定法纳入“显性对象”里面,将实定法以外的所有“附生性要素”都归入“隐性对象”这个大容器里面。
在比较法学的发展史上,隐性对象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它经历了一个从显性对象中痛苦分娩的过程。“最初曾经使用的是‘比较立法’。因为当时欧洲大陆各国明显地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并开始采用类似的法律制度,在此背景下,通用这一术语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及至法学家们认识到制定法并不能涵盖法的一切之时,就不能不用更广义的‘法’取代了‘立法’一词。”[1]58这个时期,显性对象与隐性对象还合为一体,都是作为比较法研究对象的“法”。此后,虽然功能性比较方法和文化比较方法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了隐性对象在比较法研究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根据特文宁和奥赫绪以及雷曼等人的研究,“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欧陆的比较法研究虽确立了基本范式,但这种基本范式的表现之一为:“主要研究民族国家的官方实在法,很少涉及国家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渊源。”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比较法学虽历经反思与批判,但是,成效不大。比较法学仍然存在“关注书本之法,忽视行动之法”的局限与缺陷,特别缺乏对“行动之法”的实证研究。[7]当我们展望新千年时,隐性对象能否独立出来,还未可知。
隐性对象的强大制约力量使得对显性对象的解释依赖于对隐性对象的解释。一方面是作为整体社会环境的隐性对象对显性对象的制约,正如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如果要使各种各样的微观比较能够富有意义,还必须重视所阐释与实际运用的被比规则在外国法律秩序中有关的一般制度的环境。”[8]8在这里,被比规则就高度依赖与其本国和外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作为价值理念存在的隐性对象也制约着对显性对象的解释,勒内·达维德甚至说道:“在某些法律团体中,运用某些一般的格言或某些最高的正义原则时也可以程度不同地引申解释以纠正对现有的正式规定的严格执行。”[9]18当然,显性对象对隐性对象的依赖力随着显性对象的不同而不同。下面将以国际统一法律运动为例说明这一点。
促进国际统一法律运动是比较法的功效之一,因此,比较法的显性对象除了包括国内实定法以外还应包括国际条约。一般来说,国际商事法律统一化高于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的统一化,早在1936年,比较法学家拉贝尔就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货物买卖法》,这部著作后来成为了指导海牙统一买卖法的“圣经”。[2]145反观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统一化的进程是如此的步履维艰,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挖。用显性、隐性二层结构来分析的话,原因很明显:附生在商事法律背后的隐性对象少于附生在婚姻家庭继承法律背后的隐性对象,附生的隐性对象越多,隐性对象就越复杂,理解显性对象的难度就越大,从而直接制约了学者对显性对象的比较与优化,最终制约了它的统一化进程。从外表上看,那就是:显性对象附生的隐性对象越多,它对隐性对象的依赖性就越强。
隐性对象应该引起比较法学者的重视,并独立地撑起比较法研究对象的一个维度,因为,“在他本国法律体系中由某一规范发挥的功能,不是由外国法律体系中的现行的法律规范完成的,而只能在一定的法律外的诸现象中找到,这只有通过对法律后面的实际状态的研究才能发现。”[8]52按照极端的法律解释学的观点,法律一旦被制定出来,它的制定者就已经死去了,法律文本的意义就只能在社会中寻找,如果忽视了隐性对象,我们在理解显性对象方面总是会感到欠缺的。有人说:“只有站在文化的角度上,我们才有可能真切地理解和把握各个民族的法律现象,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感受到人类的法律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10]这句话可以换成这样来讲:只有站在隐性对象的角度上,我们才有可能真切地理解和把握显性的法律现象,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感受到人类的法律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相同的法条,对于法国律师与美国律师会具有不同的意涵;类似的法锤,对于英国法官与中国法官也具有不同的意蕴。”[7]这是为什么呢?仅仅深挖法条背后的隐性对象还是不够的,法条背后的系统和传统维度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三、系统维度上的研究对象
既然比较法的目的是在比较目标规则群的基础上求取最优规则,那么,为实现这个目的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找出不同社会中的被比规则(目标规则群),第二个任务是理解这些目标规则群。每个社群的法律体系都如此庞杂,如何找出对应的被比规则呢?“在不同的国家,相同的问题可能是用不同的法律甚或不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的。如果仅仅从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出发,就无法找到比较的对象。”[11]可谓一语中的。从条文本身出发只会迷失在条文的“密林”中。所以,我们须要有更高的视角,能鸟瞰整个“密林”,像老鹰一样在万里高空准确定位目标规则群之后“直捣黄龙”。只有站立在整个法律系统上,我们才可能拥有整个鸟瞰的视角,不将系统纳入研究对象中,无以拥有这个视角。还是茨威格特和克茨说的好:“比较法学者如果想要在外国法律制度中找到某些规则在功能上同本国一定的规则旗鼓相当,他就必须在某种程序上具有系统上的想象力。”[8]50“猎取”了目标规则群之后就要着手去消食、去理解它,这是接下来的任务。但是,规则本身只是一堆符号,如何才能啃掉这堆“硬骨头”呢?庖丁解牛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在于他对整个“骨架”了如指掌。所以,欲明了这堆符号的意思,须将它们放在其所处的整体环境中来理解;欲比较目标规则群,须先比较规则群所处的整个系统。为了完成这两个“前定”的任务——猎取和消食目的规则群,都不能让整个法律体系逃逸出比较法研究对象的“魔掌”。
宏观比较方法的比较对象也是整个系统,比较法学家莱茵斯坦认为:“宏观比较是‘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比较。’”⑧ 但是,宏观比较的目的乃是寻求整个系统之间的异和同,这样宏观比较就会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微观要与宏观很好地结合起来,“虽然对法律规范的比较考察不能不考虑法律规范存在的文化环境、社会背景及其实际作用等因素,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忘了法律规范在比较法中的主角地位,否则那种考察就不是法律比较,而变成文化比较、社会比较等其他类型的比较。”[11]这里之所以提出要在系统维度下将整个法律体系纳入研究对象,并不是为了比较整个法律制度的异同,而是为了更好地定位和理解目标规则群,系统比较是为规则比较服务的。因此,在借鉴宏观比较的系统视角的同时也不能抛弃规范比较的“优良作风”。上述的显性与隐性二维层次同样会将系统维度上的研究对象分割为显性系统和隐性系统。
显性系统就是整个实定法体系,被“猎取”的目标规则群首先得放在这个体系中来理解。大木雅夫以《法国民法典》原第767条为例说明,如果不考虑当时的法定财产制是动产与取得财产共同制,就不能理解这个条款的功能。[1]95有时整个显性体系甚至会“搁置”某个法律规定,例如,“伊斯兰的教义不许可立法者变更属于穆斯林神圣法典的法律规定;而这一禁条并不妨碍穆斯林各国的君主实际上能通过各种保安或程序的手段使一条规定陷于瘫痪或给一条规定的实施加上各种条件,却并不因此使公认的教义受到影响。”[9]19由此可见:显性系统对目标规则群的含义的“重构”和“扭曲”不可谓不大矣!再说隐性系统,它是指除实定法以外的影响目标规则群的整个系统。有些目标规则群在显性系统中看似“出淤泥而不染”,实际上,它已经深深地被隐性系统感染了。茨威格特和克茨就曾举例言明:《德国民法典》第145条虽然明确地规定了要约的不可撤回性,但是德国的商业惯例已经频繁地消减了要约的约束力。[8]52-53因此,“在解决应处理的法律问题中涉及有关法律规范或法的惯例的一切情况,理所当然应当对孕育所比较的法律规范的背景条件及其现实功能加以确认。”[1]94与显性系统对目标规则群的影响相比,隐性系统对目标规则群的影响更加隐幽,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比较法研究对象中,隐性系统值得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是被忽视,但我们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四、传统维度上的研究对象
欲理解一个人,须知道她的过去;欲破解规则背后的文化密码,须在历史的长河中艰难跋涉。“对当下最内在的本质之洞观途径依然在于通过对过去的洞观。”[12]过去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某个规则的产生?同一个规则,在其他国家是否已经产生或曾经出现过?背后的因素是否相同?哪些是决定性因素?那些是次要因素?是什么因素促使了某个规则的嬗变?各个社会中,嬗变的方向是否相同?为什么不同?没有规则可以“遗世而独立”,英国现代法律史学家梅特兰在论述“诉讼形式”的顽固性时曾形象地说道:“令状制度虽已封尘于历史中,但他们却仍从坟墓中影响我们。”⑨ 谁想丢掉传统,谁就丢掉了现在。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动态组图,可赋予我们超越系统的信息。加拿大学者格伦2000年出版的《世界的法律传统:法律的可持续多样性》一书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者没有选择‘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等概念,而是选择‘法律传统’作为其理论构建的起点。他认为前者是静态的概念,无法满足动态反映法律交流的需要,也无法代表考察世界各种法律现象所需要的中间立场。”[2]440传统维度的引进势必大大地拓展比较法研究对象的范围,借助法律史的长镜头,目标规则群的含义将得到更精确的阐释;高鸿钧先生更是称赞道:“《世界的法律传统:法律中可持续的多样性》一书,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强调法律的历史和传统之维,纠正比较法研究主要关注现代法的倾向。”⑩ 当然,强调传统之维、眺望法律的过去的目的还是为了深度地比较现代法。
同样,显性与隐性二维层次也会将传统维度上的研究对象分为显性传统和隐性传统。显性传统是指“传统法律”,指某一选定社会从古到今的所有实定法;隐性传统是指“法律传统,”是指选定社会历史上存在的与制约和影响法律的各种因素。在前一个概念中“传统”是形容词起修饰作用;在后者,“传统”是个名词。当然,如果不作层次分析的话,“法律传统”是包括“传统法律”的一个大概念,格兰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没有划分层次的“法律传统”大概念。显性传统就是实定法叠加出的传统,现行实定法规则的含义有时必须借助这个显性传统才能看清它的“庐山真面貌”,例如,清末民初,学习“泰西”、变法图强时对“和奸罪”的存废就有争论,而这有关系到什么是“和”,历代成文法对此有不同的规定。早期,只有妇女在非法性行为中表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态度才会被认为是“和”;但到了明清两朝,刑律变严苛了,凡妇女在非法性行为中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拼死的反抗态度的,都被认为是“和”。[13]如果不对显性传统作一番考察,就很难了解系争之“和奸罪”的含义。莱布尼茨在《新方法》中说道:“为了概观地演进重要的法学命题,必须采用历史方法,即从作为历史发展终点的现行法出发,一直追溯到已归于失效的古老的法。”⑩ 在显性传统中,以任何目标规则群为中心都可抽出一柄“规则的历史之剑”,现行规则就是这剑的剑柄。就像剑的锋芒寓于剑身一样,规则的含义寓于它的历史之流中。如果忽视了显性传统,我们拿在手中的只是一个没有剑身的光秃秃的剑柄。
当笔锋转至隐性传统时,顿感“古愁莽莽不可说”。隐性传统的“若隐若现、若即若离”让许多比较法学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即使穷其一生研究隐性传统,都很难有明显的结果,隐性传统是比较法研究对象中最难的一块。从格罗斯费尔德的这句话中可见一斑:“一种不涉及法律史的、技术的功能性比较法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并产生着错误的结果。我们必须从某一给定文化的基本元素开始,因为它们确定着任何技术细节的地位。”[14]不仅要从给定文化的基本元素开始,还要从给定文化的基本源头开始。在这样一个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更遑论结果?但是,其难不足以掩其贵。隐性传统对理解目标规则群的作用无须赘言。仅举一例即可,在法国,解除通常是由法院宣布的,而与此相对,德国的解除则是根据债权人对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一番跋涉之后,比较法学者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在于隐性传统,在于:“法国的解除制度来源于教会法,作为神职者的法官所考虑的是拒不履行契约乃是一种犯罪,从教会的立场出发,可否把对方当事人从契约义务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无关紧要,但必须对这种罪过加以制裁。因此,法院理所当然地参与解除,这一制度为《法国民法典》所继承。与此相反,《德国民法典》是仿效《普鲁士普通邦法》的产物,而《普鲁士普通邦法》的有关规定从根本上是以对法官的不信任为基调,试图排除法官的裁量,以详细的规则确保其自动适用。因此,德国的解除制度是作为当事人的形成权而构成的。”[1]97-98总之,与隐性系统一样,隐性传统在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中不应该被忽视,而应该被重视。
五、结论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新的比较法研究对象,也不在于批评已有的研究对象,而在于析理出比较法研究对象的四个维度,此结构构成了一张密网,框定了比较法的研究对象。因为比较法的目的是制定最优规则和优化现有规则,为了达致此目的,就必须考察目标规则群背后的“附生性要素”,即从显性层面进入隐性层面;同时,欲了解目标规则群,不仅要综合分析目标规则群所处的整个法律系统,还要深究其历史传统,否则,对目标规则群的理解就会存在偏差。一旦法律系统与法律传统进入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中,一旦他们遭遇显性与隐性的二层次,就会被切割为四块:显性系统、隐性系统、显性传统和隐性传统。当我们比较不同国家法律中的相似条款时,就必须同时也比较这些条款各自所在的实定法体系,不如此,就不能全面地理解被比较的条款的意涵,这样,法律的显性系统就必须被纳入到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中来;同理,当我们为了比较法律条款而不得不比较条款的背景条件等因素时,实际上就是在比较法律的隐性系统;而当我们为了比较现有的规则而比较传统法律和法律传统时,就是在比较法律的显性传统和隐性传统。这样,以寻找和优化目标规则群为出发点,显性、隐性、系统和传统四个维度就将比较法的研究对象细化为四个领域,比较法的研究对象由此就变得清晰了。
收稿日期:2011-04-25
注释:
① 这一年,在巴黎召开了首届国际比较法大会,人们一般将此作为比较法诞生的标志事件。(参见:李秀清等:《20世纪比较法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9页。)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参见: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② 据何勤华先生统计,“清末民国时期共出版比较法著作40余种,比较法论文150余篇。在这40余种著作中,比较宪法类有22种,比较民法类有4种,比较商法、比较行政法类各有3种,比较刑法类有5种,比较劳动法和比较法总论各有1种。”(何勤华:《比较法在近代中国》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5页。)唯一一部以“比较法学”命名的著作是龚钺的《比较法学概要》,(龚钺:《比较法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但是,“此书仅有比较法总论之名,并无比较法总论之实。”(何勤华:《比较法在近代中国》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5页。)
③ 微观比较就是:“确认构成各个法律秩序的法的基本粒子,即法律规范、原则、概念和制度,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异同,将所得到的结果应用于各种目的的研究。”参见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④ 宏观比较所比较的是“不同国家的法律秩序(Nationaler Rechtsordnungen)的时候,这样可以在大局上进行,也就是说,通过对不同的法律秩序的精神和样式以及它们通常使用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法相互比较。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⑤ 功能比较是指:“即不从特定的规则或制度出发,而从特定社会问题出发并发现解决问题手段的规则或制度来进行比较研究。”(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比较法中关于功能主义的讨论,参见:Ralf Michaels,The Functional Method of Comparative Law,in: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eds.Mathias Reimann and Reinhard Zimmerman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ter 10); Michele Graziadei,The Functional Heritage,in: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eds.Pierre Legrand and Roderick Munda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⑥ 文化比较就是对法律文化的比较。参见黄文艺:《论当代西方比较法的发展》,载米健主编《比较法学文粹》(第二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⑦ 转引自高鸿钧:《比较法研究的反思:当代挑战与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61页。
⑧ 转引自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⑨ 转引自李红海:《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从梅特兰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⑩ 参见高鸿钧:《比较法研究的反思:当代挑战与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65页。在这篇文章中,高鸿钧先生将书名“Sustainable Diversity In Law”翻译为“法律中实体的多样性”,据笔者估计高先生可能是将“Sustainable”看成了“substantial”,产生了笔误,遂在引用时根据原文作了更正。
(11) 转引自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