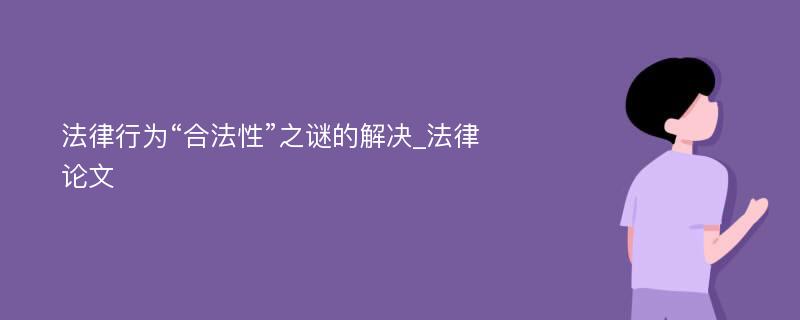
法律行为“合法性”迷局之破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法性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法性”究竟是否构成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这大概是我国民法中最大的谜团之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制定之前就已经展开。①《民法通则》第54条以立法条文的方式确定,“合法性”是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为了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特征,避免出现“无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之类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表述,《民法通则》还进一步创造了“民事行为”这一上位概念,以涵盖具有合法性特征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合法性存在各种瑕疵的“无效的民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之类的民事行为。
不过,《民法通则》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并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学术界对《民法通则》确立的法律行为概念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反对的意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②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背景下,于2002年首次提交给立法机关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仍然维持了《民法通则》的做法,将“合法性”作为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③学术界20多年的批评和讨论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立法者对民法学界理论成果的关注不够。但要想说服别人,首先必须说服自己。但问题是,民法学界在学理上并没有把这一问题彻底说清楚。这也是理论界对立法的批评未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国民法典编纂进程的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越发显得迫切和重要。为此,笔者不揣冒昧,主要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切入对法律行为“合法性”问题的分析,尝试解开这一长期困扰我国民法理论的迷局。
一、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种的法律行为
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我国学者在论述法律行为时,通常先论述“法律事实”的概念和分类体系,在法律事实的分类体系中,法律行为被认为是法律事实的一种。④虽然法律行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在法律事实的分类体系中,它被界定为一种“法律事实”,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在笔者看来,深入分析这一归类方法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本意,是解开法律行为“合法性”迷局最为重要的切入点之一。
民法理论之所以关注“法律事实”概念,主要是为了从“动态”角度来把握民事法律关系。根据通行的理论,在民法领域,法律事实就是导致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变化、消灭的原因。⑤需要立即指出的是,所谓的从“动态”角度来把握民事法律关系,在实质上就是运用三段论的法律适用模式对法律规范进行适用的过程。在这种三段论的法律适用模式下,首先假定,针对某种“事实”存在着一定的法律规范(大前提),然后分析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出现了该“事实”(小前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适用有关法律规范中对该“事实”所规定的法律后果(结论)。为了能够支持这种三段论的法律规范适用模式,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也必须具有“事实假定—法律后果”这样的逻辑结构。“法律事实”理论不过是对这些规范中的“事实假定”的归纳和整理而已。⑥
虽然民法学者在论述法律行为概念的时候,习惯于将法律事实作为论述的起点,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将法律行为在体系上归类于法律事实的一种与法律行为概念本身存在以下诸多难以吻合的地方。
1.在体系上将“法律行为”归类为“法律事实”就意味着相对于客观法律体制而言,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其法律后果有待于法律规范去评判的纯粹事实。“法律事实”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构成了客观法律规范中预设的“事实假定”,除此之外,它自身不包含独立的法律性价值。
但这样来理解法律行为,将导致难以解释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之间的差别。根据通说,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所可能具有的法律效果由法律直接规定,后者所发生的法律效果则取决于构成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中的“效果意思”,或者说是“法效意思”。⑦“法效意思”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当事人就其有关行为是否发生以及——更加重要的——发生何种法律效果的自主安排和设定。按照这样的定义,作为法律“事实构成”之前提的法律行为本身已经包含了“法律效果”的因素。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事实”,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法律效果一方面被当作法律评价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成为法律评价的结果。⑧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此法律效果”(法效意思中的法律效果)不同于“彼法律效果”(作为客观法的评价结果的法律效果),这样的确可以化解上述逻辑上的困境。但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修改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认为法律行为中的效果意思所针对的不是法律层面上的效果,而是纯粹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效果。⑨
2.在“法律事实”意义上理解法律行为将使后者受到“法律事实”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内涵的限定。法律事实,顾名思义,就是指发生于外在世界中的客观情况。“客观性”是“事实性”最基本的前提。从这个角度看,任何纯粹主观性质的“意愿”、“打算”,等等——比如说,我“想”干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属于“事实”的范畴,也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法律事实”。但根据通常的法律行为理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意思表示,是内在的效果意思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示于外部世界的过程,并在其中结合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在意思表示的逻辑结构中,表意人的“主观意愿”和“表示行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缺一不可。⑩
如果严格遵循“法律事实”概念的内涵,“意思表示”这个范畴在客观法律规范的视野下,可能具有的法律意义只会是“客观事实”意义上的外在“表示行为”,内在的“主观意愿”完全不具有作为“法律事实”的意义属性。这样,本来兼具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法律行为在“法律事实”的概念中将完全被“客观化”。但是,这种客观化与强调意思表示结构中的主观层面上的“效果意思”具有重要法律价值的法律行为概念是难以吻合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意思表示理论中的“表示主义”理论其实也对意思表示进行了客观化处理。但是,“表示主义”理论严格说来不过是主张在确定表意人“主观的效果意思”的具体内容时必须依据外在的客观标准而已,其目的仍然服务于确定“主观效果意思”的具体内容,而绝不是认为法律评价不应该针对主观性的内容。(11)这与只将客观的外在表示行为本身看作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律事实”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此,严格说来,我们不能在将法律行为归类到法律事实体系中去的同时又试图赋予法律行为中的那些不具有客观事实属性的“内在效果意思”以“法律事实”的属性。根据“法律事实”概念,主观性质的“意思”、“意愿”是无法成为法律评价对象的。
3.有学者试图从法律调整方法的角度来研究法律行为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法律对社会生活关系存在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法定主义调整方式,另一种是法律行为调整方式。在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下,法律主要从“事实构成”以及该事实所具有的“法律后果”的角度来调整社会关系。这时,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事实构成”必须由法律预先确定,并且内在地包含作为法律规范中的“事实假定”部分。但在法律行为调整方法下,法律并不去确定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事实构成”本身,它把“事实构成—法律后果”这样的调整方法放在法律行为的层面上,本身只限于通过对法律行为进行“效力性判断”来实现对社会生活关系的间接调整。(12)毫无疑问,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如果运用这种分析框架来分析法律事实体系,我们将会发现,“法律事实”概念在实质上以三段论式的法律规范适用模式以及“事实构成—法律后果”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为前提,因此,它在事实已经预设了一种法定主义的、对社会关系直接调整的模式。而法律行为一旦被认为从属于法律事实体系,从逻辑上来讲,也必然采取的是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但是,根据上面提到的观点,法律行为制度所体现的却是一种与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恰成对照的、以法律行为为中介对社会关系间接调整的模式。
面对这样的情况,除非我们放弃这两种法律调整方法划分的理论,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法律行为调整方法在体系上应该从属于法定主义调整方法。但这也会产生问题:两个存在种属关系的范畴,不应该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划分,正如我们不能认为“人”与“男人”是一种合理和有效的两分法一样。
综上所述,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与法律事实概念所蕴涵的“事实性”(不包含法律性因素)、“客观性”(不关注主观意愿因素)以及事实构成上的“预先确定性”都难以吻合。将法律行为纳入到“法律事实”体系中并不合适。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民法学界长期坚持从“法律事实”体系进行分析,并且勉为其难地将法律行为归类到法律事实体系中去呢?原因就在于,民法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作为法律关系理论以及法律事实概念之前提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并且将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事实概念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理论前提”。(13)
根据法律实证主义理论,人类生活中各种形态的社会关系在受到法律的评价之前只具有“事实性”的价值,必须在受到法律的“调整”(也就是评价)后,才可能具有“法律性”价值,转化为法律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是一种主张由国家垄断“法律性”、“规范性”的理论,不允许,也不承认“法律性”和“规范性”之类的特性可以与实在的国家法律规范的“调整”相脱离。只要接受了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这一前提,接受法律关系理论和采用广义的“法律事实”概念几乎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并且,根据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只要我们坚持认为社会生活中一切“法律性”效果都来自国家立法者及其创制的法律体制,我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将作为一种私人行为的法律行为从法律事实体系中剔除出去。这也正是法律行为在“法律事实”的分类体系中显得非常“别扭”,但现代的民法学者们却又始终坚持将其归类到这一体系中的根本原因。(14)
二、法律规范对法律行为进行调整的方法
虽然“法律事实”概念本身以三段论式的法律规范适用模式为前提,以“事实假定—法律后果”这样的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为前提,但民法理论早已确认,法律规范对法律行为进行调整的方法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并且用来对法律行为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也具有特殊性。分析这两个方面的特殊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致使法律行为“合法性”特征带来理论困惑的根源。
1.客观法律体制对法律行为的调整通常并不表现为关于法律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而是表现为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评价,而评价的结果无外乎是法律行为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有效等。(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理解法律行为的独特性,就必须在理论上解释清楚,法律上的“合法性判断”与“有效性判断”之间的关系。效力性评价,从原则上来讲,不是针对“事实性”因素的判断,而是针对“规范性”因素的判断,是关于某种“规范性”因素是否应该得到承认的判断。“有效”或者“无效”的判断是针对某种带有规范性的安排而作出的,不可能是针对一个客观事实。(16)例如,对于“过失导致他人受伤”这一事实,我们不可能进行“效力性评价”,不能说这一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而只可能作出关于这一行为“合法”还是“违法”的判断。相反,法律针对当事人作出的规范性安排,如对“甲承诺10天后向乙给付款项10万元”,则可以作出效力性评价,认为甲付款承诺“有效”或“无效”。
更进一步地说,合法性判断针对的是一种事实性质的陈述,有效性判断针对的是一个规范性质的陈述,这两者所针对的对象并不相同。也正因为两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同,两者的判断结果也不同。合法性判断的结果是某一事实是否合法,因此在法律上是得到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有效性判断的结果是,作为被评价对象的“规范性安排”是否有效,是否可以具有“规范性”效力。总而言之,有效性评价针对的是为他人设定义务的行为,不针对任何事实性因素。(17)
具体到客观法律对法律行为所进行的“调整”上来,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并不是当事人试图通过法律行为来落实的具体行为本身,而是体现在“法律行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规范性安排”在实在法层面上是否被“承认”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评价的结果是“有效”,那么体现在“法律行为”中的规范性安排就具有与实在法相同的规范性意义;相反,如果评价的结论是“无效”,那么体现在“法律行为”中的规范性安排就不能获得与实在法相同的规范性意义。
可以注意到,客观法律对法律行为进行调整的方法非常类似于一个处于法律效力等级的金字塔结构之中的上级法律规范对下级法律规范所进行的“调整”。根据规范分析法学的理论,上级法律规范对下级法律规范的调整就表现为依据“承认性”规范对下级规范是否“有效”而进行的“效力性”评价。这种评价所针对的客体是“创制下级规范的行为”,评价的结果则表现为,下级立法行为以及基于这一立法行为而创制的规范,根据上级法律规范中的“授权性规范”标准,被认定为有效抑或是无效。(18)
其实,法律对法律行为的调整与上级法律规范对下级法律规范的调整存在类似之处,绝非偶然。虽然在民法发展史上出现的法律行为理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所有的理论、学说都不否认,归根结底,法律行为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相联系,是当事人创制其私人层面上的规范的行为,是私人层面上的“立法行为”。(19)客观法律对这种私人层面上的“立法行为”进行“调整”所采取的方法,必然在结构上类似于根据上级法律规范对“创制下级法律规范的行为”进行调整的方法。其调整的结果也会表现为,针对私人层面上的“立法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规范”在客观法律的层面上作出是否有效的判断。
2.客观法律用来对法律行为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并不是通常的对具体行为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而往往是一种“承认性”的法律规范。仔细观察法律为了调整法律行为而设定的具体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与通常的“具体行为指示”意义上的法律规则不同的是,这些规则往往是一些“管辖性”、“程序性”、“授权性”的法律规范,并不针对具体行为。(20)例如,“私人约定不得改变国家强制性的法律”。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管辖性”规定,它为私人制定规范设立了外部边界。又如,“因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无效”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私人制定规范时的“程序性”规定:如果存在胁迫的情况,意思表示就不能具有法律所认可的规范性效力。再如,“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的法律规定其实是一个关于哪些民事主体有权从事法律行为的“授权性”规范,这一规范在本质上与“乡镇政府不得制定涉及税收的规范”的规范相同,都是“授权性”规范;违反这些规范的法律后果就是有关创设规范的行为无效。
需要注意的是,“承认性”法律规范关注的是对创制出来的规则的“效力”进行评价,是解决“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承认规则”对某一法律或者法律行为所作出的“无效”的判断,它的全部法律意义就在于:被判定无效的规则无法获得作为作出该判断之前提的法律体系所具有的规范性效力。强调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某个设立规范的行为也可能成为客观法律从另外的角度对其加以法律上“合法性”判断的“法律事实”。例如,通过胁迫或者欺诈的手段与他人订立契约。对于这一现象,法律一方面可以依据“承认性”的规范去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但是法律也可能去关注作为一种“法律事实”的“胁迫行为”或“欺诈行为”所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从事这些行为的人将因此而承受相应的法律制裁。但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法律对因胁迫而从事的“法律行为”的“调整”,毋宁说是法律对胁迫或欺诈行为本身的调整。对此,笔者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进一步来说明:当某个法官因为徇私枉法而作出判决时,我们一方面确认,该判决的形成因为程序不合法而“无效”,这是针对判决法律效力的判断;另一方面,这一判断并不影响该法官徇私枉法的行为被认定为“违法行为”从而受到法律的追究。
将法律调整的这两种不同角度区分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法律规范类型不同的背景下,“合法性”以及“违法性”的内涵和法律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3.一般而言,法律在对法律行为进行“调整”时作的是效力性评价,并且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主要是“承认性”法律规范。在这种背景下,即使说可以对法律行为作出“合法性”或“违法性”判断,也必须注意到,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合法性”或“违法性”判断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存在重大差别。
既然是一种规范,“承认规范”也面临着被违反及其法律后果的问题。因此,从广义上看,当然可以在“合法”、“违法”的意义上来讨论违反“承认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必须注意的是,此种意义上的“合法”、“违法”概念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内涵。举例来说,假设存在这样一条法律规定:“私人的约定不能改变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其合同中约定“依据本契约关系所产生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这时我们的确可以说,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当事人“以私人约定改变强制性的法律规定”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为它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但是,这种“违法性”所导致的唯一法律后果就是当事人的这一约定“无效”,因此,这一约定将不具有法律层面上的规范性价值。除此之外,在当事人之间不产生任何其他法律后果。事实上,把这一情况中法律所作出的“无效”认定看作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由法律施加的某种“制裁”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我们此时不能确定谁将是这种“无效”的法律定性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也很难说“无效”的认定构成了一种法律“制裁”。不仅如此,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无效”的认定不但不具有“制裁”的色彩,反而还具有保护的意义,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无效的情形。(21)
出现这种情况有着深层原因。严格地说,作为法律规范之一种的“承认规范”的确要体现作为效力评价之依据的法律规范——“上级规范性安排”——对作为被评价对象的“下级规范性安排”的控制,但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作为控制者的“上级规范”与作为被控制者的“下级规范”并不分享一个统一的价值基础。(22)这一点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客观法律所要追求的目标,如维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关系中的弱者、维护公共秩序等往往不是从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所试图追求的目标。因此,当客观法律基于“承认规范”宣告法律行为无效时,对当事人而言,这种无效的认定并不能一概地认为是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可以在一种最宽泛的意义上用“合法”与“违法”来对法律行为作出判断,但由于这种界定与相应的判断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中出现的“积极性因素”及“消极性因素”无法建立起具有一致性、规范性的联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针对法律行为作出的“合法”、“违法”判断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而且,勉为其难地对法律行为作出这种判断甚至会影响“合法”、“非法”的法律判断与对应的法律后果中的“积极性因素”、“消极性因素”本来应该具有的规范性联系。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法理论中,一直不关注从“合法性”、“违法性”角度对法律行为进行定性。甚至有学者不惜为此而修改“违法性”本身的定义,认为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单纯的意思表示,根本不可能完全脱离其环境事实而构成违法行为,而任何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必然属于事实行为。(23)这种理论想要强调的就是,“违法行为”概念是对客观事实所作的法律判断,不属于“事实世界”的“规范性安排”,应该从“违法行为”的概念中剔除出去。就此而言,“合法”与“违法”的判断只能针对一个“实然”的事实,而不能针对一个“应然”的规范性安排,因为对于后者而言,它只存在“有效”与“无效”的问题。
三、在“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法律行为
综上所述,通过将法律行为归类到“法律事实”体系中的分类方法,实际上是将法律行为看成了一种“法律事实”,而这种定性与法律对法律行为的实际调整方法并不一致。事实上,在受到法律调整时,法律行为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事实性”范畴,而是被当作一种“规范性”范畴受到调整的。这突出表现在法律对法律行为进行的是效力性评价,并且用以对法律行为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主要是“承认性”规范。这种不一致,根源于“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不可通约的性质。“事实”(to be)与“规范”(ought to be)两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众所周知的常识。(24)
对法律行为而言,同样需要判断它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事实性”还是“规范性”。如果认定它是一个“事实性”概念,那么关于它的“合法”或“违法”的定性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认定它是一个“规范性”概念,那么根据前文的分析,对于它的“合法”或“违法”定性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有意义的只是对它所作的“有效”或“无效”的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以“事实性”为基础的法律行为理论被我国的民事立法者和理论界所接受,但这一理论并不是我国民法理论的独创,而是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25)并且,这种起源于德国民法的理论在欧洲国家也不乏支持者。(26)因此,这里进行的理论反思并不是简单的针对我国民法理论的“纠错”而具有一般性的意义。
1.以“事实性”为基础的法律行为理论,由于存在难以避免的内在困境,因而无法在逻辑上贯彻到底。这导致“法律事实”理论体系采用各种方法来淡化其内在的矛盾,回避针对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所衍生的问题。这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中,法律行为通常被归入法律事实体系。根据这种分类,法律行为在原则上被认为具有“事实性”特征,因此也可以对其作出“合法”与“违法”的判断。事实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也的确针对“法律上的行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从这一角度进行了划分,但划分的结果却不是“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而是“适法行为”与“违法行为”。“适法行为”之下包括了“事实行为”与“表示行为”:“违法行为”之下则包括了“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27)
撇开这一分类体系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不论,(28)其中出现的“适法行为”概念就显得非常奇特和突兀:究竟是依据何种标准将它与“合法行为”区分开来?它与“合法行为”究竟有什么区别?对这些问题,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根本没有解释清楚。(29)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无法说清楚的。认真推敲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上对这两个概念的说明,就可以发现,“适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在内涵上并不互补,相互之间并不互为“反概念”,因此,这一所谓的“划分”本身就不是一个在逻辑上有效的两分法。为了适应这一划分而创造出来的“适法行为”,因为不存在一个逻辑上与之相对的“反概念”,所以,它自身的内涵也是难以确定的。
当然,如果一定要去论证“适法行为”概念存在的价值,对其作某种“同情性的理解”,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法律事实分类体系通过它可以在理论上淡化逻辑上的矛盾。由于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除了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还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等违反法律针对法律行为的规定,因此存在效力有瑕疵的法律行为类型。对于后面这种情况,用“合法行为”来界定这些法律行为的属性显得很不合适。为了回避这一问题,在概念命名的问题上“虚晃一枪”,回避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采用一个内涵模糊的“适法行为”概念,一方面可以保留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的统一性,将无效的和可撤销的法律行为都归类到法律行为概念中;另一方面,又可以去维持一个表面上似乎成立的法律事实分类体系。
但即使经过这样的调整,严格地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既然“表示行为”已经在体系上属于“法律事实”的一种,那么它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事实行为”呢?难道“法律事实”意义上的事实性概念不同“事实行为”意义上的事实性概念?因此,问题仍然存在:“事实性”概念与“规范性”概念属于不同的世界,遵循不同的逻辑,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将两者熔铸在一个逻辑分类体系中。任何试图用强调“事实性”因素的法律事实概念去统摄强调“规范性”因素的法律行为概念都是在自设一个没有出路的理论“迷局”。理论上存在的关于法律行为“合法性”问题的困惑不过是这一迷局的表现形式之一。
2.以“事实性”为出发点来理解法律行为,将其看作“法律事实”的一种,其实是否认私人之间的利益安排具有“规范性”价值,这实际上是否认私人能够充当其私人事务的“立法者”,否认私人的“意思自治”。这种取向与在本质上是私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工具的法律行为制度相冲突。
如前文所述,一个将法律行为囊括在内的、无所不包的“法律事实”体系其实是主张由国家立法者垄断“法律性”(“规范性”)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体现。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私人为自己的事务“立法”,这最多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由于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被认为是唯一的立法者,相应的,“法律性”或“规范性”之类的特质只可能与作为这种立法权运作之产物的客观法律相联系,私人对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安排在接受法律“调整”之前不可能具有“法律性”(“规范性”)的意义(暂且不去考虑“法律行为”这个概念中的“法律”如何理解的问题)。(30)在唯我独尊的国家法律体制面前,法律的调整对象只可能具有“法律事实”意义上的“事实性”内涵。正是依托于法律实证主义和国家法制主义所提供的这一理论预设,民法理论将“法律事实”体系看作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并且坚持将法律行为纳入其中。但上文已经提到,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具有内在的“规范性”因素,它是一种关于“应当”(规范性)从事某种行为的安排。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应当”不具有法律性的价值,但法律在对它调整时却不可能采用那种针对客观事实进行调整的方法,而必须采取“效力评价方法”。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法律生活中会出现具有内在的“规范性”特性的法律行为,并且为什么它本身会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其实,法律行为制度的存在与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时存在着“直接调整”与“间接调整”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相关。所谓的直接调整,就是由法律规范对现实世界中的事实进行“事先的”分类、总结,归纳、提炼为类型化的“事实构成”,然后直接对其作出法律上的评价。由于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都事先在法律中得以明确规定,因此,这种调整方法也是一种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但由于立法者的认知能力有限和社会生活的变动不居,这种法定主义调整方法的立法成本高昂,而且很容易僵化,脱离实际,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法律会采取间接调整的方法,也就是“授权”个人对涉及其利益的社会关系设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并且运用这些规则去调整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限于通过对个人“设立规则的行为”进行“效力性”评价来进行控制,以此实现对社会生活关系的间接调整。在间接调整方法下,立法者与个人之间在“规范形成”上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分工:个人被授权去形成调整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国家则制定框架性、程序性的规范,去监控私人层面上的“立法行为”。(31)
考虑到法律行为制度的这种特殊功能,否认其具有“规范性”因素,将其纳入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法律事实”范畴,显然存在严重的定性偏差。而“法律行为”在实质上是“私人创制规范的行为”,所产生的规则将成为调整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因此,在体系上将“法律行为”归入到“法律规范”的体系中而不是将其归入到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法律事实”的体系中,才是一种合适的定位。(32)
只要我们承认立法者不可能一概地运用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只要我们承认私人“意思自治”在一定程度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法律行为内在的“规范性”。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必然要脱离于作为被调整对象的“法律事实”体系,而从属于作为调整依据的法律规范体系。
3.承认法律行为在本质上具有“规范性”,虽然面临说明法律行为的“规范性”性质及其效力来源之类问题的困难,但这样界定法律行为却与该制度本身所蕴涵的尊重意思自治的精神相契合。虽然笔者在上文多次批评从“事实性”的角度界定法律行为基本属性的理论,强调“规范性”才是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但的确不能否认,法律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究竟具有什么特征?这种“规范性”是否具有法律性价值?如果它具有法律性的价值,它的来源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直到目前在学理上都没有得到妥当的论证。(33)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探讨,在这里不再详细展开。笔者只是想简要地指出,现代民法理论所遇到的说明法律行为“规范性”、“法律性”及其效力来源等的难题来源于“法律性”、“法律的效力来源”等问题上发生的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的法的基本理论范式的转型。产生于“主观主义”的法的范式之下的法律行为理论(也包括主观权利理论),在“客观主义”的法的范式下,在结构上都会出现内在的张力。(34)法律行为究竟是具有“事实性”还是具有“规范性”,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出现模糊,也主要是源于法的基本理论范式从“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的转换。在“主观主义”的法的范式下,个体的理性意志被认为是法产生的终极根源。根据这一理论前提,作为个体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便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在“客观主义”的法的范式下,法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于个体意志的客观秩序,这时作为个体意志之表达的法律行为能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就成了一个问题。(35)
现代实证主义的法学理论之所以试图否认个体作出的安排具有“规范性”、“法律性”价值,主要是因为这种理论倾向于从客观、普遍、抽象的角度去界定“法律”以及“法律效力”现象。在个别性、特殊性的层面上,实证主义的法学理论认为只存在“法的适用”问题,而不是“法的创制”问题。由于法律行为具有主观、个别、具体的特征,如果承认其本身具有内在的“规范性”、“法律性”,其实就等于承认“法律效力”可以以一种主观的、特殊的、具体的方式来产生和运作。这与实证主义对“法”和“法律效力”等概念的理解难以吻合。(36)为此,实证主义的法学理论为了追求自身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强调法律行为本身没有内在的“法律性”、“规范性”价值而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事实”。
不能说这种论辩毫无道理。它至少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客观主义”的法的范式下,由于处于法律规范创制体系最具体的层面上,因此,通过法律行为所创制的规范是最具体化、个别化的规范,这导致法律行为本身的“规范性”特征在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法律体制看来相当微弱,以至于试图将其排除出去,将其归类于“法律事实”,以“法律适用”模式而不是“规范设定”模式来对法律行为进行定性。这就如同我们通常认为法官根据法律对具体案件作出判决是“适用法律”,而不是被授权针对具体案件来“创制更加具体化和个别化的法律规则”一样。(37)
虽然如此,考虑到法律行为的内涵及其所追求的价值,认定其具有“规范性”才更加符合法律行为制度所具有的尊重和促进私人意思自治的内涵。这是因为,法律对“事实性”因素的评价是“合法”与“违法”判断;而对“规范性”因素的评价是“有效”与“无效”判断。这两种判断模式为当事人留下的自主行为空间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与“违法性”的判断相联系的是法律上的消极后果(法律上的制裁);而与“无效性”判断相联系的则是当事人对其私人利益的安排“不具有法律上的效果”,但“不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并不意味着这种安排不具有其他社会层面上的效果。如果当事人自愿地去追求其安排在其他社会层面上的效果,法律的态度是放任的,除非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上落实其私人利益安排的具体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8)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法律行为的“事实性”或“规范性”的不同认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赋予私人自由活动空间的方式:前者把一切活动包括私人之间的活动置于国家法律的直接控制之下;后者则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事人留下了在国家法律之外来实现其私人利益安排的空间。出于尊重和促进私人意思自治的目的,后一种认定显然更加符合法律行为制度的应有价值。
四、解开法律行为“合法性”的迷局
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那种强调法律行为“合法性”特征的理论所具有的意义并评价其利弊得失。当我们真正地理解了一个事物,把握了它的内涵时,它将不再成其为一个“迷局”。
强调法律行为“合法性”的理论,根据我国学者的考证,源于苏联民法理论。(39)结合前文的分析,这一理论具有这一“出身”毫不偶然,甚至具有某种必然性。
虽然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理论中,不乏从“法律事实”的角度来理解法律行为并进而认为可以而且应该从“合法”与“违法”的角度对法律行为作出判断,但很少有国家如同《民法通则》那样,将“合法性”作为法律行为概念得以成立的前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法律行为“合法性”特征的强调?在笔者看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压制私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强调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全面的干预。从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不同方法来看,直接调整方法(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相对于间接调整方法而言,能够更加直接地贯彻体现在客观法律规范中的立法者的意志和价值判断。这种直接调整方法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就是主张,体现在法律事实中的利益状态(如果有的话)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一切都必须与体现在法律规范中的立法者的价值判断直接保持一致。相比之下,通过法律行为进行间接调整时,客观法律并不直接赋予社会事实以法律上的评价,而是首先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对其相互之间的利益状态进行评价,作出规范性的安排,法律只限于对当事人作出的规范性安排进行“效力性”评价。这种“效力性”评价固然要体现法律规范中蕴含的价值判断,但它对具体社会生活关系的评价毕竟是一种间接的判断,并且作为其评价对象的由当事人自主形成的规范性安排已经体现了当事人的价值判断和诉求。(40)从这个角度看,在间接调整中,法律对社会生活关系干预的程度不如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来得强烈、直接。进而言之,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没有为私人意思自治留下空间,而以法律行为作为中介的间接调整方法则为私人的意思自治留有余地。
任何试图否认法律行为的规范性特征,将其认定为法律事实,从而强调对其作出“合法”与“违法”判断的理论,其实都是试图减少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间接调整的空间,强化法律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压制私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任何个人行为都必须直接地与体现了立法者意志和价值判断的客观法律规范相吻合。虽然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确有民法理论主张从法律事实角度出发去理解法律行为,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法理论仍然将尊重私人的意思自治作为法律行为制度的基础,因而往往淡化对法律行为作出的“合法性”判断。但对于那种认为法律就其本质而言是“国家意志”之体现、在法的基本价值的层面上否认个体意志的价值、否认意思自治的民法理论来说,“合法性判断”正是体现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直接控制的手段。
2.以公法特别是刑法的法律调整模式去看待私法领域中的法律调整模式,抹杀公法与私法两者在基本理念和法律调整方法上的重大差别。在公法特别是刑法领域中,当事人的具体的行为义务(作为或者不作为)在原则上必须由法律规范直接规定。但在私法领域,当事人具体的行为义务在原则上并不由法律规范直接规定,而是由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来设定,法律规范不过是通过“承认规则”“间接”地对当事人设立义务的行为进行控制而已。在这两种不同的法律调整模式下,“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和标准是不同的。在私法领域,原则上存在着两重结构:法律规范对法律行为进行的是“有效性”判断;对当事人具体行为的“合法性”判断的依据是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所设立的规则,而“合法性”判断标准是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体现了设立相关规范的当事人的意志和价值判断。在公法领域,由于个人不参与法律规则的形成,因此,由法律直接针对当事人具体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判断的标准是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志和价值判断的客观法律体制。(41)
强调“合法性”是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否认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法律性”)的价值,是否认作为私人意思自治之表现的“私法”——由私人参与形成的,对私人之间的利益作出的规范性安排——是一种“法”,而主张一切法律都具有“公共性”,法律必须而且只能是体现立法者意志的产物。这是一种将公法的法律调整模式——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泛化的做法,完全忽视了公法与私法之间在基本理念和法律调整方法上的重大差别。(42)
法学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否认存在“私法”,认为一切法律都是公法的理论来自苏联,又同样是在苏联民法理论中出现了强调合法性是法律行为本质属性的论调,这完全不是一种巧合。唯有真正体会到私法理念的实质就是意思自治,放弃那种认为立法者是法律唯一创制者的观念,才可以理解:强调合法性是法律行为本质属性的理论其实是一种与私法理念和精神背道而驰的错误理论。
3.试图以预先的“合法性”判断来说明法律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的来源。在认可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法律行为其实就是私人被国家法律体制授权在一定情况下制定调整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规则。意思自治,形象地说,就是承认私人也是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之一,其所作出的规范性安排具有一种内在的、被推定的“规范性”(“法律性”)。但由于私人的“立法行为”受到控制,在例外的情况下,其制定的规范可能被上级规范认定为“无效”,因此将不具有法律上的规范性和约束力。这是在承认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对法律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的性质及其来源的解释。
如果否认意思自治,换言之,认为私人做出的调整其利益关系的规划不具有任何法律性价值,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设想,但由于法律对社会生活关系的调整在许多情况下必须借助于法律行为这个中介,因此,不可能存在一种法律制度能够完全地、排他地采用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43)无论如何,法律在实现对社会生活调整的时候,都必须或多或少地依靠私人来参与“形成”和“确定”调整其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规则。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参与形成的规则也被认为具有“规范性”(“法律性”),这是那些不承认意思自治原则的民法理论也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原则上否认意思自治原则,同时又对私人之间的安排在一定情况下将具有“规范性”或“法律性”的现象作出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特征来解决问题:之所以在有些情况下,私人对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规范性安排具有法律意义,能够作为调整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存在,主要是因为,它已经事先接受了客观法律的评价,并且被评价为“合法”。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来源于其合法性。
但这种解释所带来的问题远比其解决的问题要多。从“合法性”判断并不能推导出“有效性”判断,这两者不是一回事。笔者在上文已经论述,从法律用以实现对私人从事的法律行为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性质来看,与其说法律对其进行的是“合法性判断”,不如说是“有效性判断”。并且,即使某个人从事的法律行为被认为“违法”,也并不一定存在法律上对其行为的消极评价(制裁),除非该行为同时构成一种事实性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否则不存在除了被认定“无效”之外的任何其他法律后果。
正是因为无法从“合法性”的角度去解决、论证和处理法律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法律性”)意义,所以,将“合法性”作为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的理论扭曲了法律行为本身作为一种私人创设规范的行为的内涵,造成了一些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当事人对其有效性存在争议的法律行为是否是法律行为,可以进行“效力补正”的法律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法律行为类型都无法与建立在“合法性”前提之上的法律行为概念进行对接。(44)
五、结论
强调法律行为“合法性”特征的理论,拒绝承认私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倾向于认为一切法律都具有公法性特征,要求所有社会关系的调整都必须直接由国家立法进行掌控,以体现其价值判断。该理论是建立在对法律行为的本质究竟是“事实性”还是“规范性”的错误定位的基础上的,没有认识到法律行为是私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自主形成调整其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法律行为更多的应该属于“规范”的世界,而不是属于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事实”的世界。正是由于对法律行为基本性质的定位出现错误,“合法性”判断与“有效性”判断之间的区别被混淆,以“合法性”为前提的法律行为理论才不能解释法律对法律行为的调整方法是一种以效力性判断为中心的间接调整方法。
虽然强调法律行为“合法性”特征理论的前提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大量支持者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但由于对私法理念特别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高度压制,这种理论实际上滑向了法律实证主义理论上的一个“极端”:国家法制主义。国家法制主义理论在法律规范创制的问题上,主张实行最严格的“国家垄断”,不承认私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在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层面上享有“立法权”。因此,这也是一个在实质上否认可以存在“私法”的理论。而这种极端的理论仅在苏联时代存在过一段时间。关于这种理论存在的错误,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兹不赘述。
在解开法律行为合法性的“迷局”,认清这一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之后,我们需要做就是,在中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坚决地抛弃这一错误理论,让它彻底成为历史!抛弃这种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将标志着我们真正走出了催生这一理论的那个特殊时代。
注释:
①(12)(15)(21)(23)(28)(31)(39)(44)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1页,第49页,第124页,第129页,第117页,第121-123页,第31-76页,第92页,第102页。
②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427页;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429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511页。王利明教授虽然认为对法律行为“合法性”的强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的来说,他对这一理论持批评的态度。梁慧星教授在关于法律行为概念和特征的论述中对“合法性”问题也是避而不谈。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7页。另外,也有学者也就此问题发表了相当分量的专题研究论文。参见高在敏、陈涛:《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1编“总则”第4章第58条。
④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⑤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⑥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⑦(4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第142页。
⑧(19)(22)(38)Cfr.,G.B.Ferri,Il negozio giuridico tra libertà e norma,Rimini,1997,p.40,p.53,p.60,p.60.
⑨事实上,的确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效果意思,并且建构相应的法律行为概念。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在德国民法理论中,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就有学者试图挑战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中的效果意思理论,代表性的人物是Lotman,Kohler等。Cfr.M.Ferrante,Negozio giuridico:concetto,Milano,1950,25ss.
⑩(14)(40)Cfr.,E.Betti,Teoria generale del negozio giuridico(ristampa correta della II edizione),Napoli,1994,125ss,13ss,54ss.
(11)(26)Cfr.,F.Galgano,Negozio giuridico (Premesse problematiche e dottrine generali),Voce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Vol.27,944ss,6ss.
(13)(24)(30)(33)(36)Cfr.V.Scalisi,La teoria del negozio giuridico:a cento anni dal BGB,in Rivista di diritto civile,1998(1),pp.535-536,p.547,p.548,p.540,p.550.
(16)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66页。
(17)(32)(41)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第155-156页,第156-157页。
(18)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吴玉章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229页。
(20)这些规则在分析法学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二性规则”(次要规则)或者是“承认规则”。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5)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页。
(27)虽然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分类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区别,但整体框架是相同的。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页。
(29)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玉波将其理解为“法律所容许之行为,应受法律之保护”,这与合法行为的内涵完全相同。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史尚宽先生将其理解为“法律所许之构成法律事实之行为”。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史尚宽先生的界定其实是很模糊的,尤其是其中的“法律所许”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清楚。严格说来,法律事实只有构成与否的问题,而不存在什么是否“为法律所许”的问题。祖国大陆的民法学者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上的“适法行为”概念,有的就直接理解为“合法行为”。参见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虽然也有学者试图赋予其某种特殊的含义,但由于无法确定这一定义的“反定义”,因此也是不成功的。
(34)Cfr.,W.C.Sforza,Diritto:principio e concetto,Voce di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Vol.12,637ss.
(35)Cfr.,M.Ferrante,Negozio giuridico:concetto,Milallo,1950,12ss.
(37)关于“司法行为”与“立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在法律行为制度上的确表现出一定的模棱两可。支持法律行为是一种个人被授权从事的“立法行为”的理论也主张其中带有“司法”色彩。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将legal transaction翻译为“私法行为”是受到法律行为的英语术语表达的影响,通常的翻译应该就是“法律行为”。
(42)Cfr.,S.Pugliatti,Diritto pubblico e diritto privato,Voce di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Vol.12,697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