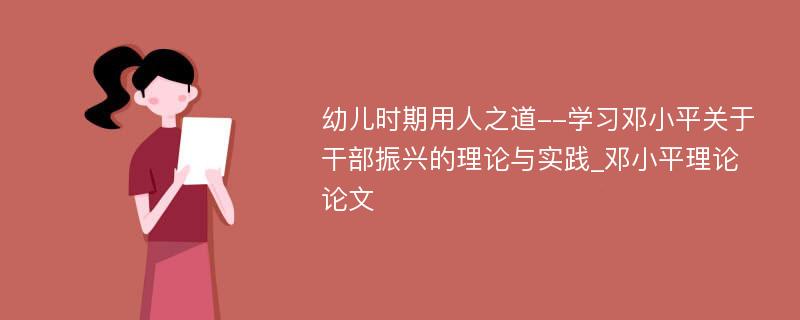
用人之道 当其壮年——学习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壮年论文,之道论文,用人论文,干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系统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如何选拔接班人,选拔什么样的接班人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这里,就其中的几个重要观点作些分析。
(一)“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
“年轻化”讲的是干部的自然条件,是对于干部年龄和身体素质的要求。对这里的“年龄”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要作辩证的理解,用他的话说,就是“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
首先,“年轻化”是一个整体概念,是对整个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总要求。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个群体中的人才互补,可以增强人的智能的社会功能和定向聚焦效应。邓小平同志把群体互补效应原理应用于队伍的建设,强调整个干部队伍尤其是各级领导班子,一方面要有一定数量的老同志,因为“老同志是骨干”,他们经验丰富。“如果离开了现在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一切任务都不能完成,也就不可能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老同志“岁数太大,精力不够”,还“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并且,“几种年龄的干部也应该有个比例”。总的要求都要讲年龄梯次结构:既要年轻力盛的年轻人,又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要有阅历丰富的老同志,形成一个老中青年结合的、素质优化、结构合理、智能互补、工作高效的领导集体。
其次,“年轻化”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年轻化”不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唯一条件,而是与其它“三化”有机联系的。“革命化”始终居首位,“知识化”、“专业化”是对干部能力素质的要求,既与“年轻化”相并列,又是对“年轻化”的补充。另一方面,不同层次领导班子中,老中青的含义和比例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上层的“青”,可能相当于中层的“中”,或基层的“老”。一般地讲,越向上层,年龄越高一些。中、下层领导班子中必须中青年人占多数,高层班子中也要力求多一些中青年人才。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中,邓小平要求与会同志考虑“两个五十”的问题:“下届的中央委员是不是可以选出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并认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而且要求在高层领导班子中,中、青年干部的位置要靠前,不能“总是排在尾巴上”。
另外,“年轻化”是一个动态概念。领导班子中老中青各占多少比例才算合理?班子成员多大年龄才算“年轻”?这个“比例”和“年龄”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80年代初期,“军队曾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团级三十岁左右,师级四十岁左右,军级五十岁左右”。而现在各级年龄又分别往前递增了3至5岁。同时,“年轻化”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只能逐步完成。
总之,“年轻化”是对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总要求,全面的、科学的涵义应该是:领导班子要形成年龄梯次结构,使各区段年龄的人才能够扬其长、避其短、尽其能。
(二)“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
邓小平同志不无忧虑地注意到:“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因此“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他反复强调要在四个方面实现用人思想的解放。
一要强化“后来居上”的意识,“不要看不起年轻人”。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足,不能胜任。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要求老同志辩证地看待年轻人的经验问题:一方面,“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更何况,“现在一些青年同志的知识,比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少”。而且,他们“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同那些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的干部来比,他们更了解群众,更了解实际。……我们绝不要低估这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另一方面,总的说来,年轻人的经验的确不如老同志,但“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事实上“政治表现好,又肯干,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各行各业、各地区、各单位都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和提拔他们”。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打破框框,“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二要打破传统的“台阶”观念,把年轻人“快点提拔上来”。在干部升迁的“台阶”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作过深邃的思考。他一方面要求人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另一方面又主张“干部要顺着台阶上”。这里包含着“破”和“立”的辩证法。邓小平同志要“破”的是那种干部提拔“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的狭隘的、过时的观念和那些对年轻干部层层设卡的错误作法;而要“立”的则是一种新的台阶观念,并“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种新的“台阶”观念,邓小平解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的实际锻炼过程”。为把这个过程落到实处,邓小平认为,干部的提升不能只走“官”道,各行各业都应有不同的台阶,如专业技术干部就可以设立助教、讲师、教授之类台阶。1977年,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决定恢复科研人员和大专院校的职称,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创造这些新的台阶,就等于给优秀中青年干部“搭了个比较轻便的梯子”,可以把他们“快点提拔上来”。
三要克服“论资排辈”的错误倾向,“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早在1956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党的提拔干部的工作,仍然有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它的主要危害是压抑人才的成长,不按照人的实际才能升迁进退,使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同时还滋长了某些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惰性。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在这一点上,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如。“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提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并强调说,这种论资排辈的制度再不改革,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下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反而不能解决呢?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大胆地把我们过去的干部选拔制度同资本主义作了鲜明的对比,并把它上升到“孰优孰劣”的高度,对用人思想的解放,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四要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注意社会公论”。在资历、辈份上附着血缘、派系、裙带关系,甚至掺杂个人的恩怨,依感情办事,凭关系用人,从而造成任人唯亲,是“论资排辈”的一种副产品。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好像我们党里有一种风气,就是在老干部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谁拥护自己谁就是好干部。不客气地讲,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针对这种倾向,他提出了用人要“取信于民”、“注意社会公论”的新思想。他反复强调,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用干部要使人民满意,让人民放心,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因为,“人民是看实际的”。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用人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是因为他把是否能发现和使用人才提到党和国家成败兴亡的高度来认识,把实现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与交替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和“政治交代”。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和使用人才看作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只有具备这种政治家的风度才会真正实现用人思想的解放。
(三)“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出发,顺利实现新老干部交接班,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队伍年轻化思想的基本落脚点。历史上,斯大林,毛泽东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把这一历史性的、跨世纪的战略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十分迫切了,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
新老干部交接班,不是个人或对立集团之间的权力转移,而是为着实现共同事业的一种承前启后的合作奋斗。因此,邓小平认为,解决干部交接班问题,总的原则是既合作又交替。只讲合作不讲交替,干部队伍就会老化下去,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就没有组织保证;只讲交替不讲合作,老干部的作用不能继续发挥,新干部的成长也会受到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实行合作交替,领导班子里就要有老有中有青。“老的一下子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老中青相结合,符合我国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无论对哪级领导班子,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必须坚持的。二是搞好合作交替,领导成员中就要有进有退。“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这是一道手脚,不要以后再来搞运动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老同志的带头作用。首先,老同志要带头“选人”。有了接班人,才能交接班,否则,“合作”也好,“交替”也好都是空话,“到时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但在选人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关键是“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如果不是老同志带,选人也不会积极,你就是勉强下命令选人,也不一定选得那么准”。因此,“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并强调:“现在任何一个老同志和高级干部,合乎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就看他能不能认真选好合格的接班人”。其次,老同志要带头“让位”。“进”是第一位的,但“出”也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说的很清楚:“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去,新的进不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只要“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但鉴于我党干部队伍的现状,老干部是骨干,为数不少,邓小平认为,“这项工作要有步骤地进行”,“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为此,他提出建立顾问制度来解决这个矛盾。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在军队提出设顾问的问题,认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1982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作了《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的专题讲话,再三强调:“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其宗旨是“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只要退休制度推行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从那时起,直到党的“十四大”作出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决议,中顾委走过了十年的光辉历程,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这期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进展的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并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四)“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在解决接班人方面的经验教训,着眼于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集体交接班的原则。在1980年8月同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他强调,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在新老干部合作交替中,我们必须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集体选拔接班人,形成可靠的集体接班。根据这一原则,邓小平自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考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接班问题。其间,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邓小平认为:“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经过近十年的考察选拔,终于组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使中央核心领导层在年轻化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顺利地完成了两代领导集体的交接。
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使邓小平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国际上不少人担心“邓之后”中国的政策走向,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他清醒地意识到:“现在看来,我的份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把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利于长治久安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整个80年代,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后,邓小平同志及时作了两项特别的“政治交代”:“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并语重心长地说:“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总之,“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并坚信:“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