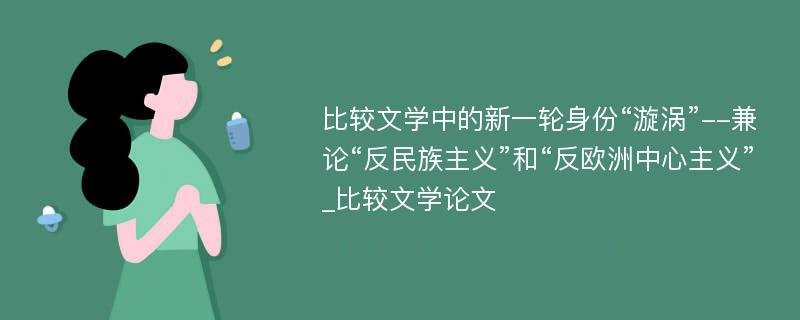
比较文学的新一轮身份“漩涡”——兼谈“反民族主义”与“反欧洲中心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欧洲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漩涡论文,新一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文学在其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其身份“漩涡”,而且每出现一股理论新潮,它就被缠进又一轮身份漩涡。从上个世纪初最早的名实不符之辩,到20世纪中期的“比较文学危机之争”,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发展方向之见”,无不由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一拨拨新论所致。时至今日,在各种“后”学,即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大潮的冲击下,在这当今电子信息高速发展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阴影中,比较文学的“漩涡”不仅依旧,而且还陷入了更深一层的漩涡中心——“反欧洲中心”和“反民族主义”。这一情形发生在上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里,其所引发的争论在1995年出版的、由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查尔斯·伯恩海默所编的《多元文化时代中的比较文学》[1]一书中体现得最充分。漩涡依旧,影响仍在,不能不予以评说。
一、反欧洲中心与反“民族主义”
伯恩海默在这本书中建议,比较文学在这世纪之交的微妙关头,由于文化发展出现了全球一体化和跨学科的强劲势头,因此,比较文学既应彻底反思并放弃其顽固的欧洲中心倾向,又应将其关注的中心由文学转向文化并扩大为对其他文化文本的研究。书中所收集的十多位学者的论文,针对伯恩海默的建议,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如科勒(Jonathan Culler)、布卢克斯(Peter Brooks)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没有必要将比较文学重新界定为比较文化”,而应当“接受留给我们比较文学的独特身份和重要功能——从比较的角度研究文学,并且考虑到文学的各种国际呈现形式”[1](P97-106,117-121)。这可以说,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学研究立场出发的学科传统之见。
另一种相反的如裴莱特(Mary Louise Pratt)、周蕾(Rey Chow)、吉努韦斯(Elizabeth Fox-Genovese)等则支持报告的建议。他们从理论出发,又回归理论,想以文化研究理论假设置换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周蕾,还以其华裔学者的身份补充指出,用非西方的经典来取代西方经典,并没有解决文化霸权问题,因此对欧洲中心的批判应以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为“前提”,否则“一个曾经是‘欧洲中心’的多元语言主义,将很容易换成非欧洲语言的一套标准而无需安上欧洲中心主义的语言知识等概念之名”[1](P107-116)。说得明白点,其意思是说,例如西方国家总习惯把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等称作“大的”或“多数”语文系,而把中国文学、印度文学等列入东亚系、南亚系中并称之为“小的”或“少数”语文系;但印度裔学者玛优姆达(MAJUMDAR)提出,应“改换视角”倒过来称“英国、法国、德国的文学,只是一种‘准民族文学’”,而与印度文学相对应的应是欧洲文学[2](P6)。这么一来,按照周蕾的意思就是用印度的“论语”,继续推行没有欧洲中心多元语言主义的印度民族主义的中心霸权。所以周蕾主张既要反欧洲中心主义,又要以反民族主义为“前提”。
对她这番话语,我们可作如下逻辑关系的概括表述:
由于当今全球多元文化的发展特点,比较文学研究应搞文化研究并反欧洲中心主义,再加上周蕾所说、伯恩海默在该书“绪论”中所肯定的反民族主义;所以,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比较文学,等于反欧洲中心主义加反民族主义的文化研究。若采用大家熟悉的数学公式,即:
∵比较文学=文化研究
∴全球化多元文化=反欧洲中心主义+反民族主义
当然,上述的公式化简,不仅显得简单机械,而且还有荒谬之嫌,那就是既反欧洲中心主义,又反民族主义,而且要干净彻底,那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岂非成了海市蜃楼?成了虚无主义?可以肯定这绝非周蕾等人的本意,因为他们希望在后殖民时代“如此多样的语境中”,关注“边缘化或被压制状况的声音”,克服“与权力控制机制相联系的话语”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并为此还必须反对籍“他者”之名再复制其他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问题,方能最终“以寻求更世界化的跨文化途径”[1](绪论)。然而,乌托邦的许诺,毕竟经不住理性的思考和实际的检验。因为问题接踵而至:比较文学转为文化研究是否就能“放弃”其顽固的欧洲中心呢?纵然加上了“反民族主义”或“批判民族主义”的前提,在当今世界学术对话语境中,在非西方并被殖民过的国家尚有不同程度“失语”的情况下,能真正导向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文学”这一学科宗旨吗?是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还是欧洲殖民国家曾盛行一时并至今未绝的“欧洲民族主义——欧洲中心”,才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大敌呢?问题的关键是:
抽象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同历史总体现实中的曾被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欧洲和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否等同、等效的同一码事?
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客观存在事实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当它越出欧洲疆域时是同殖民主义、同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等行经“等同”的。换句话说,在世界背景下,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侵略和排斥‘他者’的工具”。一部血淋淋的世界近现代殖民史,一部中国从鸦片战争起,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屠杀南京城的百年民族耻辱史,就是最有力的明证。之所以如此,乃是民族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一个从正面作用到反面作用的变化过程”,正如西方权威的《方塔那现代思想辞典》所概括的,它既是“一种以属于某一个由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历史纽带连接在一起的集团的感情、并通常和某一特定地区相一致的”,同时它又是“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民族国家吹捧为理想的政治组织形式,故而要求它的公民把对它的忠诚看得高于一切”[3](P559-560)。前者是一种历史形成的传统积淀和客观存在,而后者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信念。正是这后者,发展到后来,在欧洲滑向了沙文主义——“一种杂有仇外主义的过头和不合理的民族主义”,再进而陷入了纳粹主义——主张“雅里安人种最杰出的德国人,具有‘统治民族’的种族优越性”、“恶性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在德国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实现其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野心”的罪恶泥坑[3](P120)。在欧洲疆域之内,它给欧洲人民带来了空前浩劫,并留下了至今难忘的余悸;而在欧洲之外,它被欧洲殖民者利用为大肆侵略和排斥“他者”民族的工具,并同军事上和贸易上的竞争、牺牲他国民族的扩张以及帝国主义行径等同起来[3](P560)。他们既仗其“船坚利炮”,将欧洲各殖民国的版图,扩张到了全球各地;又手捧“基督福音”及其意识,连同其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和强权公理、物种进化和弱肉强食、莎士比亚和拜金主义等鱼目混珠地推销浸润到世界各处,给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痛苦。
需要指出的是,与欧洲和殖民国家相反的是,民族主义对殖民地国家和民族来说,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不仅同其民族意识、民族情结、民族传统、民族认同等紧密相关,而且还同其民族生存与否的基本人权紧紧相连。就连西方《方塔那现代思想辞典》也说,“是殖民地民族和少数民族,对其有被更强大国家征服危险而进行反抗的原动力”,“曾经是亚洲和非洲政治觉醒的原动力”[3](P560)。由殖民主义血腥侵略与统治所激起的可歌可泣的殖民地人民反抗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以及当今第三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被殖民国家争回自身民族独立、民族生存、民族权力和民族发展的斗争。一个众所皆知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向德国宣战的胜利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非但争不回来被德国强占的胶东半岛的主权,反而继续沦为丧失主权的耻辱境地。纵然是胜利者的巴黎和会,那也是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殖民国家的和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再次充当被“侵略和排斥”的“他者”的和会。可见,在欧洲和第三世界之间、在殖民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历史并不赋予欧洲的民族主义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等价、等值、等同的同等功能。
到了如今“殖民者走了”的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上述不同等功能之差异,是否已消失殆尽了呢?
全球化(Globalization)起自20世纪的60-80年代,盛于90年代。起先它是批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传播媒体和影视音乐等方面主宰第三世界国家,使之形成中心与边缘关系,从而忽略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工业和接受情况等的一种说法。后来,它成为述说全球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向世界各国传播的科技、贸易与文化,从而使全球进行许多规格化和标准化的世界政经体系一体化的重要文化现象。所以,“全球化”说起来是通过强化世界各处社会联系的作用,以促使本地的发展;或通过“时间—空间”的压缩和不同地方跨距离的互动,以形成全球化的社区[4](P4)。但是这种全球化其实并非是彼此互动的真正全球化,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因为,这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在全球的蔓延及其消费意识形态的传播,“强化”他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去“认同”和“归属”其许多“规格”和“标准”的全球化。透过现象可清楚地看到欧洲中心和殖民帝国主义这一承继实质。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雄厚跨国资本实力,究其形成的条件和基础而言,是先天存在着其殖民他国所获得的经济优势“原罪”。而且这种优势从赤裸裸的军事政治的公开侵略,承继到资本并转化成科技、传媒等商业化和文化意识上的强势,过去是“显性”地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今天则“隐性”地表现在文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及其意识中。过去是“一个国家势力的扩张,通常是以征服的方式掠取别国领土;征服别国领土上的居民,使之处于强加给他们的外来统治之下,并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剥削”[3](P409)。而今天则是“文化帝国主义”,即“运用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去吹捧和传播外国文化的价值和习惯,从而损害本国的文化”[3](P411)。所以,在貌似公平公正的“全球化”中,仍然隐性或显性地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或透过经济资本,或透过文化生产结构,或透过国家机器组织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继续对第三世界和原殖民地国家进行结构性的剥削,包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商品倾销的巨大盈利、廉价劳动力的无情压榨等。与此同时又籍其文化资讯的单向交流,以将第三世界的意识,通过对其“全球化”“规格”和“标准”的认同和归属,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彻底的“同质化”。仅从全球的出版与学坛舆论来看,情况就是如此。当今世界约有五百种文字,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出版物为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5](P49),亦即欧洲语言。而学坛情况则正如汤林莘(John Tomlinson)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所说,只有西方富国的“全球化”:“某些书籍与期刊得以在最具有权势、最富裕的国家当中流通,而这些流通的著作,通常也就被举作代表了某项特定问题的‘全球性辩论’。”[6](P29-30)透过现象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在经济贸易上还是文化交往中,实际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西风压倒东风”的差异。“事实上,任何一种显示出文化差异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主义色彩。”[7]显示出文化差异的东西,说白了就是由于其中存在支配(domination)他者的权力,即由欧洲狭隘民族主义——殖民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意识优势的欧洲中心话语权力;而被其支配的“他者”,仍然是被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与民族。
可见,历史和现实都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纳粹主义是必须彻底否定和反对的;欧洲的狭隘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在当今的活性表现——欧洲中心话语权力是必须批判和警觉的。而对于过去被侵略、被殖民而今天仍处于不拥有话语权力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同他们的争民族生存、争民族地位和争民族发展的正当民族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是不能作为如欧洲狭隘民族主义那样同等来加以批判和根除的。否则,就像釜底抽薪一样,不仅损害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学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也不仅削弱世界多元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走向“跨世界化的文化途径”的“世界文学”,而且还会继续强化那“顽固的欧洲中心倾向”的话语霸权及其“异化”魔力。
因为,拥有话语权力的欧洲和原殖民国家,同丧失话语权力的第三世界和原殖民地国家,在彼此进行对话的语境中,双方是处于不同的“异化”魔掌中的。使用的虽然是双方都须遵守和认同理解的言谈规则,然而这些“游戏规则”却是由拥有话语权力的前者所制定,也就是开始于殖民时代并出自于欧洲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的规范,经由殖民时代的历史而维系至今,使后者不得不去适应、去接受、去认同,全球化时代的广泛知识领域,包括科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宗教等,无不隐性或显性地存在着其话语权力拥有者的意识范式及其视角在内。纵然不作任何价值判断的地理概念,亦然如此。例如对阿拉伯地区,中国传统的指称是“西域”,但由于以欧洲眼光看是其近东、中东,使我们现代也随之称“中近东”。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京成立的审讯战犯机构,也同样随之称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凡此都像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规律一样,都是“死者抓住生者”——“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8](P42),都是由过去的殖民时代造成并延续至“后殖民”时代今天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不过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有所不同的是:劳动换成了话语,有产者换成了有话语权力者,无产者换成了无话语权力者。但有话语权力者同无话语权力者双方,通过“死者抓住生者”的语境——“游戏规则”所进行的评语活动,却仍然是同样的异化规定:既表现在话语活动的结果上,又表现在话语的行为中,而且还表现在话语活动的本身中。因此,有话语权力者,在更加肯定自我的同时,则更加否定无话语权力者的“他者”。与此同时,无话语权力者的他者,在更加否定自身的同时,又更加肯定有话语权力者的对方;拥有话语权力的“自我”更增值其“自我”的“自我”,而无话语权力的“他者”则更异化为“他者”的“他者”。话语活动本身就使无话语权力的“他者”更边缘化,有话语权力的“自我”则更中心化。对无话语者来说,这是异己的话语活动,话语属于对方——拥有话语权力的欧洲和西方,这种话语活动是其民族自身的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伯恩海默、周蕾等人还要说,在批判欧洲中心之前须加上“批判民族主义”的“前提”,以实现“跨世界化的文化途径”,就只能是一张极度夸张的讽刺画。因此,主张用“多元文化”比较研究来置换比较文学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顽固欧洲中心”,也就只能是给欧洲中心主义再添砖加瓦了。这正如美国的希伯尔斯教授,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中撰文所指出的:“欧美——或者全世界——的文学文化理论都是欧洲的理论,后者对多元观的理想也是带有欧洲特性的理想。”[1](P198)
二、比较文学中的“顽固欧洲中心”
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也同样如此。尽管还在比较文学学科形成的早期,歌德早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一个多世纪来的西方比较文学家也一再重提这一理念,然而他们却忽视了歌德“世界文学”精神的真正所指。正如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在90年代发表的《比较文学批评概论》一书中所说,“不可否认,所谓的‘比较文学’通常被人误解”,因为当今时代,欧美的学者还认为“世界文学首先就是所有有价值的作品的总和,杰出的总集:它是世界性的文学名著”[9](P15)。其实,“世界文学”,按歌德的原意是要人们将视角越出欧洲语言文学的狭窄圈子而转向世界。歌德批评诗人马提森(1761-1831)自认为是诗神缪斯惟一宠儿的偏狭文学观,他指出,当德国人还在刀耕火种时,中国人已经在写小说了,他在比较分析了中国小说的“道德、礼仪、节制”这一使中国文明维持几千年并将长存下去的特点时说:“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所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顾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做。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0](P113)可是,歌德的这一要求,即跳开四周环境的小圈子去“环顾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却在比较文学学科形成过程中,就被当时“欧洲文学”研究的主流所淹没。
就在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在欧洲从“正面”走向“反面”的时期,意大利的马志尼(1805-1872)就写了顺应欧洲时代潮流并名噪一时的《论欧洲文学》,他的视野完全就在欧洲之内而非歌德的“世界文学”,他在论述了欧洲各国文学文化的相互联系后强调:“单一民族的历史即将结束,欧洲的历史即将开始。”[8](P13-14)由欧洲民族史,到欧洲民族的欧洲史再到世界史,如弗郎西斯·约斯特所说:“世界文学和世界史从现代意义上来说是两个平行的概念。”[10](P14)也就是,比较文学没有走克服欧洲民族中心的“世界文学”之路,而是走的欧洲中心的世界史道路。诚如西方现代比较文学家库尔提乌斯在《文学研究导论》中所总结的:“西方文学组成了各国民族文学的历史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本身则体现在每一个民族文学之中。每一首抒情诗、每一部史诗或每一个剧本,不论其各自特点如何,都是部分地借鉴自共同的材料,并因此而使这一共同体得以巩固和永久。……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11](P5-6)
当比较文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以后,这一“病灶”也随之浸润进这门学科并烙上了深深的欧洲狭隘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胎记。写了第一本《比较文学史》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在其书末的总结中说:“各民族力求扩充其语言和文学通行的范围。在欧洲各民族争霸的奋斗中,其主要的特征便是大家都用语言文字为竞争的利器……各地重又将欧洲的军队,欧洲的思想,以至欧洲的风俗语言输入亚洲腹地。这是历史上欧亚两洲势力互相消长的大概。至于近世,则西方知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亚细亚除极少数偏僻的区域外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如是,欧亚两洲文化之渐趋一致,已属意中之事了。”[12](P461-466)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比较文学发展中,这一欧洲中心痼疾也一直未能根除。无论是法国学派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还是美国学派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无论是学科理论,还是实际研究,尽管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从影响研究主攻的有交往关系的各国文学,拓宽到跨语言界、跨学科界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然而“其顽固的欧洲中心倾向”却始终未曾“放弃”。
权威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这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拉丁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古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13](P61)全书所述,也确都限于欧洲文学之内,而欧洲之外的各国文学,压根就不在其视野之中。
时隔近半个世纪的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在其1974年出版的权威著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对东亚和欧洲诗歌之间的比较究竟能显示什么最终事理……至多也只能得到一些被归纳为普通常识的基本特点。”[14](P8)其视角依然限于欧洲。过了十年,当他来华讲学并亲身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的蓬勃生气后,明确承认比较文学“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心”。“我们应记住,从历史上来说,我们的学科侧重于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欧洲”。并反省自己道:“这种观点长期一直在比较文学界流行,而我本人在我的书里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回想起来颇为后悔。”[15](P30)
欧洲比较文学的实际研究,从最早的由贝茨收有两千个条目的《比较文学目录》(1897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由韦斯坦因、雷马克、费歇尔分别编纂的同样比较文学书目,也都主要限于欧美文学之内,涉及东方文学的论著,不是一无所有就是绝无仅有[16](P27-57)。
而到了20世纪末,所谓后殖民时代的今天,这种情况已普遍引起国际学界的焦虑。西方不少学者也开始清醒认识到,之所以如此,正如美国东方学者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引用石约翰的断言:“只有西方‘从来没有从外界观察自己’。”[17](P79)并指出,必须打破欧洲文化范围的限制,方能破除欧洲中心。连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佛克马教授也承认:“总之,跨文化的检验——对结果的检验曾过久地被限制在一种文化范围之内,现在它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会为我们对科学假设普遍有效性的期望提供一个基础。”[18](P41)近年来活跃于国际学坛、并广有影响的英国学者波斯奈特进而提出:“现在已到了我们确认比较文学的后欧洲模式的时候了,应重新考虑文化认同、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含义、时期划分和文学史等关键问题,并坚决摈弃不顾历史的美国学派和形式主义研究。”[19](P41)
倘若我们能跳出形而上的二分对立观,就不难发现,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欧洲中心同作为各种显性或隐性帝国主义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就如同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民族主义生存权同作为惟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信念一样,是应当给予区分的。因为历史形成的欧洲中心,是它发展过程中吸取各民族文化文明的客观存在,其优秀部分是属于人类文化文明的共同财富;这就如同古代历史上,灿烂的中华文化曾独领风骚,也就因为她不断吸取和融汇异域他族文化文明的成果、并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一样。优秀的文化文明来自全人类也属于全人类,正如比较文学家维斯坦因所说:“接受影响并不可耻,就像输出影响并不光荣一样。”[14](P8)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它是建立在人具有社会性、其彼此间交流与对话是永恒的这一历史现实基础上的。因此,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学人家什么和自己干什么,是不能盲目跟风的。笼统地要么反欧洲中心,要么反民族主义,这种既割断历史、又脱离实际的现代非此即彼的怪病,是不利于我们正常思考和学术健康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当多些亦此亦彼的辩证思考方好。
收稿日期:2003-01-02
标签:比较文学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全球化论文; 他者论文; 话语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