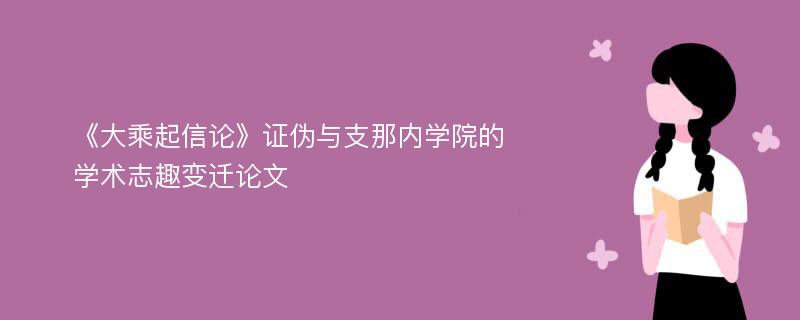
《大乘起信论 》证伪与支那内学院的学术志趣变迁
季芳桐,王 虎
摘要 :近代佛教复兴代表人物杨仁山先生创立金陵刻经处,一方面刻印经书,一方面培养人才,其学术志趣是兼顾各宗而归于净土。由于人生转折的契机在于阅读《大乘起信论》,故极其推崇此部著作。而接班人欧阳竟无则偏好有宗,并不惜余力地证明《大乘起信论》是伪作,引发了教界、学界的争鸣,也改变了内学院办学的志趣。其中原委大致与当时中日学界的讨论形势以及个人名利心相关。
关键词 :《大乘起信论》;证伪;学术变迁
金陵刻经处从成立到至今已经走过了150多年的历程,这是件非常值得重要的文化事件①。与金陵刻经处相关联的衹洹精舍、支那内学院也已度过较长的历史岁月,其历史长度虽不能与刻经处相比,然贡献却不在其下。在那段共存的岁月里,金陵刻经处与衹洹精舍(后与支那内学院),一方面刻经、流通,一方面研究问题、培养人才,可谓相得益彰。若无精舍(或内学院),刻经处的学术地位不会如此高;若无刻经处,精舍(或内学院)的研究成果也难以迅速“物化”,进而影响教界、学界。当然,若仔细阅读它们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金陵刻经处的宗旨一百多年始终未变,而精舍与内学院的办学志趣却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物的交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下面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杨仁山于1866年创立金陵刻经处、衹洹精舍,以弘扬佛教。精舍是研究教义、培养佛学人才的,刻经是刊印流通佛教经典的,两者工作内容虽不相同,然都是佛教的复兴事业,都有益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杨仁山居士与佛教结缘,开始于二十七八岁。年谱载:同治三年甲子,二十八岁。
归葬朴庵公于乡,事毕回省,感时疫,病久。自是厥后,率为居士学道之年矣。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觉甚微妙,什袭藏奔。嗣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搁置案头,未暇寓目。病后,检阅他书,举不惬意,读《起信论》,乃不觉卷之不能释也。赓续五遍,窥得奥旨,由是遍求佛经。久之,于坊间得《楞严经》,就几讽诵,几忘身在书肆。时日已敛昏,肆主催归,始觉悟。此后,凡亲朋往他省者,必央觅经典,见行脚僧,必询其从何处来,有何刹竿,有无经卷。一心学佛,悉废弃向所为学。[1]593
显然,《起信论》、《楞严经》是其转向学佛弘法的转变契机。换言之,这两部经论在其人生道路的选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年间,创办金陵刻经处后,杨仁山对于《起信论》、《楞严经》仍然非常重视,其拟定的《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中,要求学生第一年,阅读:梁译《大乘起信论》纂注、直解、义记,以及《楞严经》纂注、正脉疏、讲解等。其《学佛浅说》载:
学佛者当若之何? 曰:随人根器各有不同耳!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断知解,彻见本源性地,体用全彰,不涉修证,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种根器,唐、宋时有之, 近世罕见矣! 其次者从解路入, 先读《大乘起信论》, 研究明了, 再阅《楞严》、 《圆觉》、 《楞伽》、《维摩》等经,渐入《金刚》、《法华》、《华严》、《涅槃》诸部, 以至《瑜伽》、《智度》等论。然后依解起行,行起解绝,证入一真法界,仍须回向净土,面观弥陀,方能永断生死,成无上道。此乃由约而博,由博而约之法也。又其次者,用普度法门,专信阿弥陀佛接引神力,发愿往生,随己堪能,或读净土经论,或阅浅近书籍,否则单持弥陀名号,一心专念,亦得往生净土。虽见佛证道有迟速不同,其超脱生死,永免轮回,一也。[1]326-327
杨仁山希望人们依据自身根性选择修佛方法,认为除去利钝根外,从解路入者,首先应阅读《起信论》,然后按《楞严经》、《圆觉经》……之顺序,一部一部阅读下去,最终证入一真法界。于此可知,《大乘起信论》、《楞严经》无论对于杨仁山还是对于一般根性的学佛者,都是一部重要的入门典籍(起码杨仁山是这样认为)。杨仁山先生熟悉佛教各家各宗,并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宗各派。其《十宗略说》对于律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天台宗、贤首宗、慈恩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皆有介绍,并指出如此排序(即从律宗到净土宗)之理由:
出世三学,以持戒为本,故首标律宗;佛转法轮,先度声闻,故次之以小乘二宗;东土学者,罗什之徒首称兴盛。故次以三论宗;建立教观,天台方备,贤首阐华严,慈恩弘法相,传习至今,称为教下三家;拈花一脉,教外别传;灌顶一宗,金刚密授,故列于三家之后。以上各宗,专修一门,皆能证道;但根有利钝,学有浅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须念佛生西,以防退堕。即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观弥陀,亲承法印,故以净土终焉。[1]156
设计方面的因素。主要有设计水平的高低、图纸质量的好坏等,具体表现为工程设计采用不成熟的技术方案,设计错误、遗漏或缺陷,图纸供应不及时、不配套或出错等。
梁启超认为,按照佛教依法不依人的原则,纵然此论非马鸣所做,非真谛所译,只要符合佛教教义有何不可?!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恰恰反映了跨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当时金陵刻经处可谓人才济济,复兴之龙象可见。学者梁启超从学术史角度评价了此类现象。他指出金陵刻经处所以能够聚齐这么多有识之士,应归功于时代风气和杨仁山的吸引力:
石埭杨文会(即杨仁山)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2]306
雨水通过图3(a)中“1”所示的缝隙进入“2”所示的夹层;夹层中的螺栓(如图3(b)中“3”所示)和呼吸孔(如图3(b)中“4”所示)未采用防水密封垫,导致水沿着螺栓和呼吸孔进入电流互感器箱体内部,如图3(c)中“5”所示。
吕澄看来在“性寂”与“性觉”是关键所在,《起信论》倡“性觉”,是中土儒家的思想反映,与印度佛教的“性寂”说大相径庭,故非印度佛教思想;从修养角度看,“性觉”强调返本的功夫,“性寂”则重视“革新”的功夫,故“返本”不是真正修为的方法。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教界的反弹,彼此之间展开了辩论,由于争辩双方都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孰是孰非很难判定。可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支那内学院的学术志趣已经发生变化,已经大不同于衹洹精舍的志趣了。
Taking a0 = 84 μm, xd = 37.5 μm, γc = 0.9545 and γd = 1 into Eqs. (9) and (10):
二
作为杨仁山的弟子欧阳竟无继承了金陵刻经处的事业,于1922年创立支那内学院,招收学员,习法相、唯识要典。倡在家居士可住持佛法之义,以奠定居士道场之基。同时编刻唐代法相、唯识要典和章疏,出版年刊《内学》、《杂刊》。应该说,这时的支那内学院近似现在的佛教学校,早期的衹洹精舍有似古代的书院。内学院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培养学生,这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是考试录取的佼佼者,在这里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掌握佛教义理尤其有宗的义理;一方面是学术研究,大致在二十年代前后,欧阳先生等工作的重点是《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证伪工作。
著名佛教学者吕澄先生认为:
安知非当时有一悲智双圆之学者,悯诸师之哄争,自出其所契悟者造此论以药之,而不欲以名示人。此在我国著述界中,殊不足为奇也。在论主之意,并未尝欲托古人以为重。及既传于世,共赏其玄异而不审其所自来。有好事者则谓是非马鸣不能作非真谛不能译也。辄以署之,而传者因之,于是转成作伪之文矣。以吾所见,或是如此,姑陈之以备一解。抑吾更有言者,无论此书作者为谁,动机何等,曾不足以稍损其价值。此书实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实中国、印度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以佛家依法不依人之义衡之,虽谓为佛说可耳。于马鸣乎何有!于真谛乎何有![2]306
这里既阐述了十宗前后排序之道理,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各门宗派虽有差别,但门门皆可入道。于此可见,杨仁山居士对各家宗派并无特别偏好,更无门户之见。所以,衹洹精舍对于人才培养,各宗皆有。正如弟子欧阳竟无所言:唯(杨仁山)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杜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夥矣。然其临寂遗嘱,一切法事乃付托于唯识学之欧阳渐,是亦可以见居士心欤[1]587。
比较杨仁山的衹洹精舍与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可以发现彼此之差异:杨仁山的衹洹精舍重视《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将其视为必读书;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则不懈余力证明《大乘起信论》、《楞严经》是伪经伪论,因为义理偏离了印度佛教。这是其一。其二,杨仁山的衹洹精舍,对于各宗各派都能够平等对待,培养的弟子精通各家宗派;支那内学院则侧重有宗,弟子虽研读其他宗派理论,然最终都归于有宗。门人熊十力说:“竟师之学,所得是法相唯识。其后谈《般若》与《涅槃》,时亦张孔,只是一种趋向耳,骨子里恐未甚越过有宗见地。”此段见解未必尽是,然偏重有宗是一定的。应该清楚,这里彼此差异,实质反映两者学术志趣的变化。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类变化,即作为杨仁山门人为何偏要不懈余力地证明其师杨仁山推崇的经典《大乘起信论》、《楞严经》是伪作?支那内学院在办学过程中为何不能兼顾各宗而欲偏有宗?需分别探讨。
金陵内学院的欧阳先生以及弟子吕澄、王恩洋等人获此信息后,并不认同此番见解,而是沿着证伪的路径继续走下去,即从义理角度证明其伪。欧阳指出《起信论》的过失除了薰习之义以外,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超越的正智无漏种子:
从史实与理论观之,《起信》与分别论大体相同也如彼;以至教正理勘之,《起信》立说之不尽当也又如此;凡善求佛法者自宜慎加拣择,明其是非。然而千余年来奉为至宝,末流议论,鱼目混珠,惑人已久,此诚不可不一辨也;(即如《起信》有随顺入无心之说,谈者遂谓无分别是智,有分别是识,佛之遗教依智不依识,即是去识不用。然根本智无分别,而后得智则明明有分别,又与智相应者亦明明有分别之识,安可以无分别是智等概为解释?无分别有分别系有所对待之言,正未可以一句说死。至于佛教依智不依识云云,盖谓依智得证圆成而如量知依他起性,依识思惟分别则多为遍计所执而不能当理也。反观《起信论》家所谈,非错解之甚乎?)今故因论正智有种而详言及之。[3]41
具体情况是这样: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讨论。日本学者望月、村上等人经过探讨认为:《起信论》非马鸣所造,非真谛所译,而是公元563年至592年中国人的著作。思想家梁启超获此信息非常惊喜:
从以上的考证看,《起信论》的理论已经接触到佛学的根本原理“心净尘染”,但随着魏译《楞伽》的误解,却构成一种似是而非的“真心本觉说”。它认为众生的心原是离开妄念而自有其体的,可称“真心”,这用智慧为本性,有如后人所解“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一般,所以看成本觉。在论中形容这样的“真心”是大智慧光明的,遍照法界的,真实识知的,乃至具足过于恒沙不思议功德的。它说得那样头头是道,就给当时佛家思想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修为一方面,依着我国学人“先立乎其大者”的传统,当时有许多家都想循着它的途径去把握“真心”作为总源头。要照圭峰《禅源诸诠集都序》所分析,一代禅教的各种学说,几乎都和这样思想有关。最明显的是禅家的“息妄修心宗”、“直显心性宗”和教下的“显示真性教”,虽然他们主张悟入有渐次和顿超的不同,但都从把握“真心”而入,并且由悟而修以达到恢复原来面目为目标。而依据“真心”的本来具足功德,将修为方法看作是可以取给于己,不待外求。这些都使学人走上了反本还源的路子。圭峰对此曾有很显豁的说明:“我等多劫未遇真宗,不解返自原身……今得至教原文,方觉本来是佛。故须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还源,解除凡习,损之又损,以至无为,自然应用恒沙,名之为佛。”(见《原人论》)可是,这种说法,与印度佛学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印度的大乘佛学解释到“心净尘染”这一原理时,都用本寂的“实相”做注脚。像龙树说“诸法实相如涅槃”(寂灭之义。见《中论》);无著、世亲又强调“实相”的“自性涅槃”(见《摄大乘论》等)。他们从认识上着眼,以为众生一向来由于迷妄、错误的认识,都得不着“诸法实相”,但这“实相”自存,并不因错误认识而有所改变,所以视为寂然。这又意味着“诸法实相”仍是可以认识到的,认识还是可以改正的。如此说“心性本净”,就只有规范的意义,举出了“可以是”又还“应该是”的标准,并非就“已经是”那样了。所以在无著、世亲的学说里,更详细地解释了清净法有四层:“自性清净”只是“应得”的,“离垢清净”才是“至得”的,还有“所行道清净”和“所缘言教清净”都属于“能得”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佛学的重点放在“能得的清净”上面,由此到达了离垢,才成就“应得的实际清净”。由此,真正的修为方法,应是革新的,而不是返本的。众生之心原没有清净过,如何由不净改变到与规范一致的清净,这要有新式的成分加入,逐渐地改革,最后才面目一新。并不像旧来所说“明镜尘昏,拂拭净尽”就可得之的。中国隋唐的佛学,受了《起信论》似是而非的学说影响,不觉变了质,成为一种消极的保守的见解,并且将宇宙发生的原理,笼统地联系到“真心”上面,而有“如来藏缘起”之说,又加深了唯心的色彩。这些都丧失了佛学的真精神,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后来义学家更变本加厉,将《起信》思想看成印度佛学最后进展的一阶段,以为马鸣之传,由坚慧等发扬,自成一系,还超越了无著世亲之说。这是虚构历史(坚慧说与无著贯通,原属一系,而误会为两事),抹煞了学说变迁的真相。今天,如果要认识我国过去佛学的实质,判明它的价值,并撇开蔽障去辨别佛学的真面目,都非先了解《起信论》思想的错误不可。我们用考证方法,揭露了《起信论》的伪书、似说,并始终坚持这样的论断,其用意就在于此。[4]368-369
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皆为近代学术大师,他们皆不约而同地与佛教发生关系,实际上是晚清以来学佛风气使之然。当然,杨仁山(文会)精通 “华严”、“法相”、“净土”等各宗,视野开阔、胸襟旷大,也是大家皈依刻经处的重要因素。中华民国初年杨仁山去世,欧阳竟无主持刻经处工作。
三
我国佛教思想系统,入隋唐以后,三论蜕变为天台,摄论蜕变为法相,地论蜕变为华严。以吾观之,《起信论》所占位置,不过扩地论宗土宇为华严宗先驱而已。然则《起信论》无甚价值可言耶?曰,是大不然。《起信论》者,消化印度的佛教而创成中国的佛教之一大产物也。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比较优劣,此别一问题。但凡属文化力伟大之国民,承受外来学说,必能咀嚼之,变化之,加入自己之国民特性以成一新系统。我国之于佛教正如此。而《起信论》及其所导出之华严宗,正其代表也。总之,“此书实为人类最高智慧的产物;实为中国、印度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2]306
断层构造为成矿后的破坏构造,破坏了赋矿构造及矿体的连续性,间接控制了铁矿体的赋存和分布[2]。EW向断裂使得南盘的铁矿层上升,表现在第二个背斜南翼上升,并出露到地表;而受NE向断层构造破坏,断层北西盘呈阶梯状下降,单断层带表现为沿NE向断裂西盘下降,构成一系列西翘东陷的断块,有利于铁矿层的保留。
综上,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学生身体动作的表现形式,运用器械的多样性,在团体动作中不同的运动路线,对团体的编排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实际的教学中,应更多的考虑学生的特点以及器械本身的特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让学生在每一堂课中受益。
首先,我们不怀疑欧阳竟无等对于佛教、对于杨仁山的感情,我更愿意相信其坚守“依法不依人”的观点,愿意相信其自信如此作为,于佛教发展有利。但是,是否可以采取 “中庸”的方法?一如梁漱溟所言:
内学院欧阳先生既为仁老门下,其徒吕秋逸(澄)诸君更属后学,乃其言论主张竟然大反乎仁老的训示,贬斥《起信论》及《楞严经》。据吕君语我,他将有《楞严百伪论》之作,其著作曾否写成未详。我非盲从于人者,对于此经此论卒相信内院之批判不诬。然而不从考据角度来说,我又觉得此两书内容所发挥者仍然代表佛家,不必排斥。——此末后一点或难邀内院首肯。[5]855
表3可见,健康教育后对艾滋病患者需公开身份、是否愿意与艾滋病患者共处一室等6项态度均显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慢跑能增加大学生的积极幸福感,对心理烦恼和疲劳感无影响;慢跑结合音乐可以增加大学生的积极幸福感,能有效地降低大学生的心理烦恼感,对疲劳感无响应。两种类型的慢跑,即慢跑组和慢跑结合音乐组的对比:在积极幸福感上,运动后慢跑组和慢跑结合音乐组无差异;在心理烦恼感上,慢跑结合音乐比慢跑更有效地降低大学生心理烦恼感;在疲劳感上,慢跑比慢跑结合音乐更能降低大学生的疲劳感。
从相信“内院之批判不诬”,进而又觉得“此两书内容所发挥者仍然代表佛家,不必排斥”。这样既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也不伤害教内的感情,真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然而欧阳先生却是观点极鲜明(如上所述),态度极坚决。就其缘由,大致是个人名利和性格使之然。如人所熟知,佛教是由中国传入日本,早年日本多向中国学习,只是到了晚清以后,中国的佛教典籍保存、整理、研究却逊于日本。以至于在某些领域只能“照着说”,即“照着”日本学者的观点说,一如《大乘起信论》作者的问题。作为中国学者当然不甘心处于此种状态,他们希望“接着说”,即希望通过自己的探讨之成就,接过佛教的话语权。《大乘起信论》讨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缘,或许欧阳竟无等支那内学院诸位看准了这一机会,比较高调地进行了义理方面的证伪工作。且立论若能成立,不仅可以推翻千百年来汉地僧众崇信的经典,又能引起学界之极大反响。所以,欧阳竟无以及吕澄、王恩洋等,相继投入证伪工作。教界的印光大师早已看出他们的证伪工作夹杂着名利思想:
“——《起信论》之伪,非倡于梁任公。乃任公承欧阳竟无之魔说,而据为定论,以显己之博学,而能甄别真伪也。欧阳竟无乃大我慢魔种。借弘法之名,以求名求利。其以《楞严》《起信》为伪造者,乃欲迷无知无识之士大夫,以冀奉己为大法王也。其人借通相宗以傲慢古今。凡台贤诸古德所说,与彼魔见不合,则斥云放屁。而一般聪明人,以彼通相宗,群奉之以为善知识。相宗以二无我为主。彼唯怀一我见,绝无相宗无我气分。而魔媚之人,尚各相信,可哀也。”(复李觐丹居士书)
总之,欧阳竟无等是借证伪之名而求名求利。门人熊十力也有类似观点,在《与梁漱溟论宜黄大师》一文中指出:
(欧阳)竟师之学,所得是法相唯识。其后谈《般若》与《涅槃》,时亦张孔,只是一种趋向耳,骨子里恐未甚越过有宗见地。如基师之《心经幽赞》然,岂尽契空宗了义耶?竟师愿力甚大,惜其原本有宗,从闻熏入手。有宗本主多闻熏习也。从闻熏而入者,虽发大心,而不如反在自心恻隐一机扩充去,无资外铄也。竟师一生鄙宋明儒,实则宋明诸师所谓学要鞭辟近里切着己,正竟师所用得着也。竟师亦间谈禅家公案,而似未去发现自家宝藏。禅家机锋神俊,多玄词妙语,人所爱好。恐竟师谈禅,不必真得力于禅也。竟师气魄甚伟,若心地更加拓开,真亘古罕有之奇杰也,不至以经师终也。竟师为学踏实,功力深厚。法相唯识,本千载久绝,而师崛起阐明之。其规模宏廓,实出基师上。故承学之士有所资借。如章太炎辈之学,谈佛学与诸子,只能养得出一般浮乱头脑人扯东说西而已,何能开启得真正学人来?竟师于佛学,能开辟一代风气,不在其法相唯识之学而已。盖师之愿力宏,气魄大,故能如此。若只言学问知解,如何得陶铸一世?竟师气魄伟大,最可敬可爱。惜乎以闻熏入手,内里有我执与近名许多夹杂,胸怀不得廓然空旷,神智犹有所囿也。因此而气偏胜,不免稍杂伯气。其文章,时有雄笔,总有故作姿势痕迹,不是自然浪漫之致也。其文字雄奇,而于雄奇中乏宽衍,亦是不自然也。凡此皆见伯气。竟师文学天才极高,倘专一作文人,韩愈之徒何敢望其项背耶!竟师无城府,于人无宿嫌。纵有所短,终是表里洞然,绝无隐曲。此其所以为大也。吾《新论》一书,根本融通儒佛,而自成体系。其为东方哲学思想之结晶,后有识者起,当于此有入处。吾学异于师门之旨,其犹白沙之于康斋也。虽然,吾师若未讲明旧学,吾亦不得了解印度佛家,此所不敢忘吾师者也。[6]19
这里,“惜乎以闻熏入手,内里有我执与近名许多夹杂,胸怀不得廓然空旷,神智犹有所囿也。因此气偏胜,不免稍杂伯气”。是指欧阳先生夹杂名利思想与霸气。当然,追求名声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况且如此作为,也能给自己领导的支那内学院或中国学术界带来名声。理解到了这点,欧阳先生以及支那内学院的激烈言行也就易于理解了。至于说内学院偏向有宗,这是历史事实。学术界有不同风格学派、学者存在本是正常现象,然只以有宗作为唯一标准以评价其他经论之真伪得失,则失之偏颇。欧阳先生等支那内学院之失,即在于此也。
新疆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属典型的大陆性干燥气候。尤其是处于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南疆部分地区,气候异常干燥,年降雨量较小,缺水严重,而当地土壤沙化现象严重,土壤保水能力差,缺水与土壤保水能力差的现状无疑增加当地棉花种植成本,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
其实,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角度看,宗教典籍出于庶人,由民间重构的情况多得很,基督教的《摩西五经》[7],儒家的《周礼》,乃至道教的经典(模仿、吸收接纳佛教的就更多)等都存在相似情况。至于,佛教也不例外,佛教典籍自然也会有或佛说或菩萨说之类。只是,在署名时,往往会借用宗教创始人或宗教中的圣贤人物,以增其影响力或权威性。《周礼》就是典型:它既非周代所作,也非周公、孔子所作,大致是在秦焚书坑儒之后,汉代的学者所作,很可能是一批有识之士作为(类似集体构建)。如此一来,将其视为“伪书”也是有依据的。但是,书籍之伪,与文物之伪(赝品)本不一样:文物之伪(赝品),常常是无价值或价值不高的代名词;而经典之伪,除去署名不合规外,往往不影响本身的学术价值(仅就上述经典而论)。基督教的《摩西五经》、儒家的《周礼》状况都是这样,故至今仍被列为宗教经典。总之,大家知道这些典籍的成书过程就可以了。若不是专门从事文献学、版本学研究的,则没必要深究了。何况佛教有“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说,凡是符合“三法印”的即为佛说,反之则为非佛说。换言之,是否合乎“三法印”更为重要,至于是译作还是撰作(从文献学角度看有一定意义),其余并不多么重要,也无排斥之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宗教经典的质疑、批评等,既要考虑典籍的真实性,也要考虑信众的普遍感受,要兼顾大众的心理。文学家鲁迅曾说过,有婴儿出生,如果贺客说:这孩子将来长命百岁,主人家一定会欢天喜地;如果贺客说:这孩子将来会死,则肯定会被暴打出门,尽管他说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显然在社会生活中,一种真实的道理,不合习俗,不合时宜,也会不受待见。可见,合乎情理非常重要,欧阳竟无的证伪严谨性毋容置疑,但是否顺乎信众之情,则不一定了,从教界的反映看基本是负面的。笔者完全认同梁漱溟先生的看法:相信“内院之批判不诬”,又觉得“此两书内容所发挥者仍然代表佛家,不必排斥”。这样既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也不伤害教内的感情,可谓两者兼顾,合乎中庸之道。此虽然是后话,但对于今天的典籍考证工作仍有参考价值。
四
总之,衹洹精舍与支那内学院学术志趣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两者之间也有一以贯之的地方。比如两者都在倡导居士佛教,并且都身体力行,杨仁山是居士,欧阳竟无、吕澄等,也都是居士。换言之,都是有信仰的佛教学者,都愿意为佛教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其次,杨仁山、欧阳竟无主持金陵刻经处工作时,刻经处刊刻精选经书的宗旨也一直延续着,至今未变,因此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佛教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 人群分布 性别:男24名、占20.17%,女95名、占79.83%;职业:医生25名、占21.01%,护士62名、占52.10%,实习生15名、占12.61%,进修生5名、占4.20%,保洁人员12名、占10.08%;工作年限:0~5年65名、占54.62%,6~10年 31名、占26.05%,11~15年14名、占11.77%,>15年9名、占7.56%。
注释 :
①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佛教复兴基地,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太虚、吕澄等一大批思想家或佛学家,皆在这里学习过。
参考文献 :
[1]杨仁山.杨仁山全集[M].合肥:黄山出版社,2000.
[2]清华大学国学院,主编.刘东,等,选编.梁启超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3]王雷泉,编.欧阳渐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4]吕澄.吕澄佛学论著选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6.
[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6]熊十力.论学书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7]成祖明.威尔豪森的《以色列史导论》与现代圣经批评: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中的《摩西五经》[J].世界宗教研究,2016(3).
The Falsification of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 and the Academic Changes of China Buddhism College
Ji Fangtong, Wang Hu
Abstract : Mr. Yang Renshan, representative of Buddhism revival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established Jinling Buddhist Scriptures Publishing House. It published Buddhism doctrines and cultivated Buddhism talents as well, and its academic interest was to study all the Buddhism branches while returning to Sukhavati. Because the turning point in his life was reading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 , Mr. Yang Renshan praised highly of this book. While his successor Ouyang Jingwu preferred Buddhism schools and spared efforts to falsify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 It led to the contention in Buddhism circles and academic circles, and changed the academic interest of the college. The contention and the change attribute to the then China-Japancontention situation and desire for fame and fortune.
Keywords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 ; falsification; academic changes
作者简介 :季芳桐,男,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宗教哲学与文化;王 虎,男,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刘智《天方性理》整理、翻译及研究”(项目编号:15AZJ005)。
中图分类号 :B94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9)01-0163-06
(责任编辑 李 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