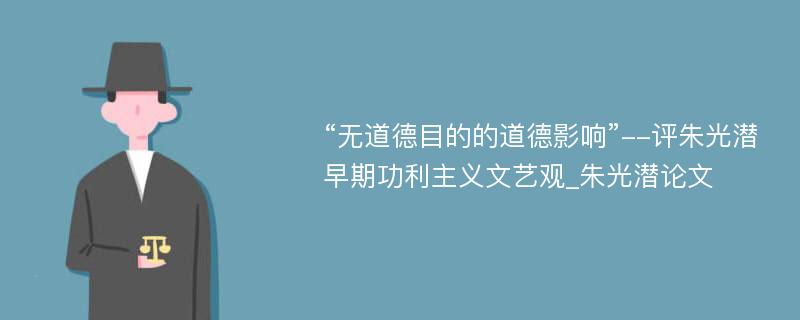
“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评朱光潜早期文艺功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目的论文,功利论文,文艺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朱光潜1949年以前的各种文艺观点中,被误解最厉害的莫过于他的文艺功利观了。在人们印象中,他是个“否定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联系”的人,是个强调文艺“超现实”的“艺术至上论者”[1]。 这一点,甚至于他自己也承认。1956年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他在清理自己1949年以前的文艺思想时曾说:“我的基本论调是把艺术看成超社会、超政治、超道德的。这表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上”[2]。然而,只要我们不是片面“摘句”式地对待朱光潜的文艺思想, 而是细读他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直接论述文艺与道德、文艺与人生关系的篇章,则会发现:人们原来的“印象”并不确切,他自己的“承认”也与事实相违。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呢?
根源在于朱光潜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本身的复杂性。这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他的前期(1949年以前)思想中,确实比较突出地存在审美活动和文艺活动“超现实”、“超功利”的观点,但是他也在许多地方阐发了艺术与现实、与社会、与道德的紧密联系,对于文艺如何发生社会影响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问题是,在他的整个著作中,谈文艺“超现实”、“超功利”的内容多于后者,以至掩盖或让人忽视了他的文艺与现实密切关系的论述。二、朱光潜1949年以前的美学思想并非铁板一块,其自身经历了重大变化。在1931年前后完成的《文艺心理学》初稿和1932年出版的《谈美》中,他基本接受康德、克罗齐一派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审美活动和文艺活动同任何实际功利效用是相对立的。但是,在193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和1936年正式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他已开始越来越自觉地批评形式派美学的缺点,尤其是在文艺与道德、文艺与整个现实人生关系等问题上,他的观点发生了重要转变。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转变,而仍然把他看作一个纯粹的形式派美学论者,这怎能不导致对他的文艺思想发生误解呢?翻开《谈美》,“开场话”就写道:
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3]
类似这样的话,在朱光潜的早期著作里俯拾即是。人们据此把他看作“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认为他“否定艺术的社会性和功利性”,当然不是空谷来风,而确实是有根有据的。问题在于,这主要是他1933年以前的观点,在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他便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十九世纪后半期文人所提倡的“为文艺而文艺”,在理论上更多缺点。喊这个口号的人们不但要把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完全分开,还要把艺术家和社会人生绝缘,独辟一个阶级,自封在象牙之塔里,礼赞他们唯一尊神——美。这种人和狭隘的清教徒恰走两极端,但是都要摧残一部分人性去发展另一部分人性。这种畸形的性格发展决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艺术,因为从历史看,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4]
诸如此类申述艺术与人生、与社会联系的话,在他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的著述里,也是反复强调的。对此,我们显然不该视而不见或一概抹煞,而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清理。这清理对于消除以往对朱光潜的误解,发现对我们文艺理论建设有用的积极成果,都是有意义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光潜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里注意了艺术与人生、与社会的联系,但是他的文艺功利观与当时蓬勃崛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对文艺的要求,仍有相当差异;他对“左翼”文艺家简单地用文艺作为宣传工具的做法,更是公开表示反感。为此,他当时受到了“左翼”文艺家的激烈批评,他自己也作了反驳。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他与当时“左翼”文艺家之间的分歧?这不仅是朱光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涉及到如何评价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因而不应回避。好在今天与当时已相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已能够站在超脱当事人的“庐山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双方的论争,发现应该记取的教训和可以吸取的经验。
二
朱光潜关于文艺功利关系的论述,在《文艺心理学》第七、八两章里谈得最为集中。第七章“文艺与道德(一):历史的回溯”,主要从中国和西方两条线索,检讨历史上各家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看法,以“看清各家争点所在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5]。 第八章“文艺与道德(二):理论的建设”,在衡量“文艺寓道德教训”和“为艺术而艺术”两说缺陷的基础上,着重申述自己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看法,意在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朱光潜认为,以往关于文艺与道德的探讨,之所以越争论歧见越多,离解决问题的道路越远,关键是在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都存有很大弊端:
在历史上文艺与道德的问题闹了二千年之久,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卷入战团,到今天还没有得到一个结局。这件事实固然显出问题的繁难,同时也引起我们怀疑从前人讨论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陷。就态度说,他们都先很武断地坚持一种信仰而找理由来拥护它。就方法说,他们对于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不是笼统地肯定其存在,就是笼统地否认其存在。其实就某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密切相关,是不成问题的;就另一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应该分开,也是不成问题的。从前人的错误在没有认清文艺和道德在哪几方面有关系,在哪几方面没有关系,于是“文艺与道德有关”和“为文艺而文艺”两说便成为永远不可调和的冲突。[6]
基于这种认识,朱光潜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力戒笼统的泛泛之论,注重细致的具体分析。他突破形式派美学孤立地研究美感经验的窠臼,把美感经验放在整个审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上,分“在美感经验中”、“在美感经验前”和“在美感经验后”三个阶段,来具体探讨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文艺与道德关系密切,在何种情况下两者应相互分开。这样的探讨,不仅在方法上别具一格,新人耳目,而且得出的结论也与以往不同,颇具启发意义。
在美感经验中,即在心中猛然见到一个完整优美意象的瞬间,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会暂时忘去名理的判断和道德的思考。比如西门庆引诱潘金莲原是不道德的行为,武松拒绝潘金莲的引诱原是道德的行为,但在《水浒传》和《金瓶梅》的作者和读者看,这两篇道德对立的文章都同样地入情入理,同样地精彩有趣。作者创造武松、西门庆和潘金莲艺术形象时,注意的是如何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不是对他们下道德判断,如让道德感涌入笔端,常常会破坏形象塑造。同样,读者欣赏这几个艺术上成功的角色时,在觉得入情入理的精彩有趣的顷刻,观赏的只是艺术形象本身,而无暇从道德观点上去褒奖武松或谴责西门庆、潘金莲。因此,在美感经验发生的瞬间,艺术和道德是可以分开并应该分开的。
但是,美感经验毕竟只是人的生活中稍纵即逝的暂时现象。一个艺术家不仅要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常生活,而且在突然得到灵感,产生美感经验之前,要进行学问储备、经验积累,要了解人情世故、思量社会道德等种种问题。所以朱光潜指出:“稍纵即逝的直觉(美感经验)嵌在繁复的人生中,好比沙漠中的湖泽,看来虽似无头无尾,实在伏源深广。一顷刻的美感经验往往有几千万年的遗传性和毕生的经验学问做背景。道德观念也是这许多繁复因素中一个重要的节目。”[7]这就是说, 一个文艺家会发生何种美感经验,会进行什么样的形象创造,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已被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个人性情、学问修养以及道德观念等等,在无形中指定了大致的方向。因此,像莎士比亚、陶渊明这些作家,即便无意于在作品中表现道德观而道德观仍然自现。从此可见,文艺作品中的道德因素,实有不可避免的一面。
至于在美感经验之后,文艺与道德的密切关系更是显而易见。许多文艺作品,如屈原、阮籍、杜甫、白居易、陆游、元好问诸人的诗歌,绝大部分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作者原来就有意或无意地渗透一种人生态度和道德信仰到作品里去,人们在欣赏或评论它们时,就不能不顾及其人生态度和道德信仰的价值。以屈原或杜甫的诗来说,他们的杰出人格和忧世忠君的热忱,本身就是决定其作品价值的重要成分,人们欣赏或批评它们时,从中受到道德教益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事。退一步说,即便一些被认为丝毫不含道德因素的作品,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谢灵运和王维的写景诗,以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等,虽然没有任何道德说教的成分,但能在潜移默化中引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实际上对人的精神仍发挥了陶冶性情的作用,仍是文艺具有道德功用的表现。
这里的关键是对“道德”含义的理解。在朱光潜看,文艺作品中所蕴涵的“道德”,决不应是一般的道德说教或宣传口号,而应是对人生世相的正确认识和深广同情。他曾这样评析传统的“文以载道”说:“如果释‘道’为狭义的道德教训,载道就显然小看了文学。文学没有义务要变成劝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头讲章。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决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8] 由此可见,朱光潜肯定文艺的道德作用,但反对狭益的“文以载道”论,而主张通过深广地表现人生世相,以文艺自身的独特品格去发生道德影响。
三
那么,如何以文艺自身的独特品格去发生道德影响呢?
朱光潜认为,从文艺产生道德影响看,文艺作品可分为三类:一、一般认为不道德者,二、有道德目的者,三、有道德影响者。
一般认为不道德者,主要指坊间流行格调低下的黄色作品,或宣扬打斗加色情的武侠小说等。这类作品要么本身无艺术可言,要么即便有艺术性,作者意图也不在营求艺术,而在刻意表现感官刺激,对读者和社会都会产生“有伤风化”的坏的影响。人比其他动物高尚,就因为在饮食男女之外,还有较崇高的追求。文艺的责任在促进这追求,而不是把人引向完全饮食男女式的蝇营狗苟的生活。作者写这类作品,“大半有意迎合群众的心理弱点,借艺术旗帜,干市侩勾当,不仅在道德上是罪人,从艺术观点看,他们尤应受谴责”。朱光潜认为:“他们的作品根本不是艺术,所以不能作道德与艺术问题的论证”[9]。
所谓有道德目的者,就是作者有意要在作品中寓道德教训。这类作品很难一概而论。有的毫无艺术价值,如中国无数的“戏善书”和“阴骘文”、法国大革命时期带宣传性的戏剧、华兹华斯歌吟基督教教义的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等,都是显著的例子。 但有的作品虽有意渗透某种道德教训,却并不有损其很高的艺术价值。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小说,以及易卜生、萧伯纳诸人的戏剧,都带有明显的在作品中张扬某种人生信仰或道德观念的意味,却并没有因此动摇它们作为世界名著的地位。有鉴于此,朱光潜提醒道:“我们不能因为作者有道德目的,就断定他的作品好或坏”。他认为,即便有意寓含道德教训,这类作品照样可能具有“极大艺术价值”[10]。
然而,朱光潜却并不主张有意在作品中鼓吹道德教训,而是更倾向于作品“无所为而为”地发生“道德影响”。他特别强调“有道德目的”与“有道德影响”的重要区别:“有道德目的”是指作者有意宣传一种主义,拿文艺来做工具;“有道德影响”,是指读者看过一种文艺作品后在气质或思想方面发生某种变化。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是“无为而为”。他认为在文艺活动中,“最可注意的是没有道德目的的作品往往可以发生最高的道德影响”。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就目的说,并没有什么道德观念要宣传,就内容说,所写大半是女逐父、夫杀妻、臣叛君、弟弑兄之类不道德的事迹;但人们真正了解一部悲剧以后,精神上不是觉得颓丧而是感发兴起,不仅情感仿佛经过一番净化和升华,并且对人生世相也获得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可见,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但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往往并不存心要教训人。所以,朱光潜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第一流艺术作品大半都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11]。
朱光潜之所以特别推崇“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作品,是由他文艺功利观中潜藏的深刻矛盾决定的。一方面,他认为文艺是人超越于动物而有较高精神追求的体现,其重要特征就是与实际人生拉开一段距离,再造一个摆脱实用功利世界的精神园地,供人在忍受现实苦楚和不幸之余“避风息凉”。如果文艺家创作时就预先抱有道德教训的目的,则易消除艺术审美世界和现实功利世界的区别,由丧失艺术价值进而丧失艺术对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艺术是自然和人生的反照,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真正伟大的作者,必须了解现实人生”[12]。由于文艺家与常人相比,有较真挚的性情,较敏锐的感觉,观察比较深刻,想象比较丰富,因而他们的作品“是启发人生自然秘奥的灵钥”。朱光潜认为,这“启发”对于道德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13]。就此而言,“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观照和了解,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帮助我们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础”[14]。
朱光潜文艺功利观中潜藏的这种深刻矛盾,是文艺本身即隐含这种矛盾的反映。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就意识到这种矛盾,极其深刻地认为这矛盾是个难以解决的带有“二律背反”性质的命题,并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来概括这矛盾的性质[15]。朱光潜提出的“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看法,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受到康德的启示。在康德那里,所谓“审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指审美判断与利害关系及任何外在目的都无关,所以具有“无目的”的特征;但人在审美时去掉一切利害和道德内容后还剩下形式,这形式因无形中可以给人以心理愉悦,所以又具有“合目的”的性质。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强调的是文艺的绝对“超功利性”。但朱光潜的“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观点,却在维护文艺“超功利”、“超现实”特征的同时(没有道德目的),又肯定了文艺与现实的联系及社会功利作用(有道德影响)。这样,他一方面坚持了文艺的独立性和文艺表现人生世相的特殊方式,另方面也顾及到文艺的社会性及其对现实人生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光潜调和他文艺功利观中两方面矛盾所做的勤苦努力,更可见出他力求使文艺与道德关系的探讨在理论推进一层,“求一个较满意结论”的学术进取精神。
四
正因为朱光潜更看重“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所以他对文坛上某些作家有意借文艺去宣传政治信条和道德教训非常反感。这反感引起了他与当时的“左翼”文艺家的一场论争,其原委还得从他的一贯学术立场谈起。
朱光潜一贯认为,学术和艺术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要能够自由思想;学者和文艺家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要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身份”[15]。他从二十年代初发表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起,至三十年代初从欧洲留学回国止,虽然时时都在对现实进行“文化介入”,撰写了大量著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却时时注意与现实激烈的政治变革和党派斗争保持距离,坚持知识分子的超然态度和独立人格。当时他所处的客观环境,即长期在国外生活(英、法留学八年),不论是地理空间上或社会生活的不同上,都帮助他比较容易地实现了自己坚持学者“独立自主的身份”的理想。
然而,1933年7月他回到国内后, 随着对国内文坛的逐渐熟悉并投身进去,他很快发现保持多年的“超然态度”和“独立人格”已难以维持,觉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面临政治的“压迫”。1937年初,他发表《中国思想的危机》一文说:“中国知识阶级在思想上现在所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所谓‘左’,就是主张推翻中国政治经济现状,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行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是很鲜明的,观者一望而知。至于所谓‘右’,定义就不容易下,这个暧昧的标签之下,包含一切主张维护现状者,虽不满意于现状却不同情于苏俄与共产主义者,虽同情于苏俄与共产主义而却觉得现时中国尚谈不到这一层者,甚至于不关心政治而不表示任何态度者。政治思想在我们中间已变成一种宗教上的‘良心’,它逼得我们一家兄弟要分起家来。思想态度相同而其余一切尽管天悬地隔,我们仍是同路人;一切相似而思想态度不一致,我们就得成仇敌。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感到这种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种压迫。”[17]
这里所说的“压迫”,说穿了与当时“海派”和“京派”的尖锐对立密切相关。“海派”主要指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主要指当时京津地区的一批知识分子。朱光潜回国受胡适之聘,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自然被看作“京派”一分子。京派在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和《新月月刊》时最为兴盛,但随着他死于飞机失事后便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为了使京派再振作起来,请朱光潜任主编,和杨振声、沈从文、叶公超、周作人、朱自清、林徽音、废名一起组成一个八人编委会[18],创办《文学杂志》。在该刊的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朱光潜对当时学术界和文艺界的状况,较为全面地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一面倡导“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风气,一面批评左右两派“都是老鼠钻牛角”,对政治“压迫”可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抗争。这抗争在他当时写的许多文章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以下面两段话说得最为明确和集中。在《现代中国文学》一文里,他说:
本来新文学运动的倡导人大半是自由主义者,在白话文的旗帜之下,大家自由写作,各自摸路,并无一种明显的门户意识。“左翼作家同盟”起来以后,不“入伙”的作者们于是尽被编入“右派”的队伍。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要文学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在中国尚未成为事实,他们也只是有理论而无作品。不过他们的伎俩倒被政治色彩不同底人们窃取,近二、三十年文学界许多宣传口号都是这种伎俩的应声。我们看见许多没有作品的“作家”和许多不沾文学气息的文学集会。[19]
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一文里,他指出“口号教条”是低级趣味的一种:
存心要创造艺术,那是一种内在的自由的美感活动;存心要教训人,那是一种道德的或实用的目的。这两桩事是否可合而为一呢?一箭双雕是一件很经济的事,一人骑两马却是不可能的事。拿文艺做宣传工具究竟属于哪一种呢?……从史实看,大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可是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大半并不存心要教训人;存心要教训人的作品大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所以我对于利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一事极端怀疑。我并不反对宣传,但是我觉得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作品既难成功,就难免得反结果,使人由厌恶宣传所取的形式因而厌恶到所宣传的主张。……我本不想说出这番不合时宜的话来开罪许多新作家,但是我深深感到“口号教条文学”在目前太流行,而中国新文学如果想有比较伟大的前途,就必须作家们多效忠于艺术本身。他们须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以至于读者的尊严;否则一味作应声虫,假文艺的美名,做呐喊差役,无论从道德观点看或从艺术观点看,都是低级趣味的表现。[20]
对于朱光潜的这一系列文学主张,当年的左翼作家觉得是对革命文艺的攻击。茅盾批评他“对于实际情形的缺乏理解,在他论及文坛现状时,尤其显著”,并认为《文学杂志》所标举的“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宗旨,是“欺人的漂亮话”[21]。周扬指摘他在《文学杂志》发刊词中“反对文学‘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甚至‘为国防’”,主要是“朱先生以为艺术的目的正是要使你摆脱繁复错杂的现实世界,而‘替人生造出一个避风息凉的处所’”[22]。巴人讽刺他“以心理的距离冷看投水女人的姿态底美妙”[23]。郭沫若更是把他的文艺观点认作“反动文艺”的一种代表[24]。近年来,有的论者在反思以往现代文学研究时,指出这些批评“并不完全合理”。因为朱光潜主要是从文艺自身特点和规律出发,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上述批评则完全是从时代政治要求出发来对待其观点,“只能计量出它政治意义单薄”的一面,忽略了其尊重艺术自身规律的“更为重要的一面”[25]。
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朱光潜讲究“纯正审美趣味”的文艺思想及推崇“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功利观,与当时左翼文艺家突出阶级意识和政治思想,强调“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观,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文艺体系,彼此发生尖锐冲突是必然而又自然的事。从文艺自身的要求看,朱光潜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基本论断,无疑是切中当时文坛时弊并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例如他批评“左翼作家同盟”的门户意识,即“左联”文艺政策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就始终没有得到纠正;他反对用文艺做宣传工具的“口号教条文学”,当时左翼文艺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就此而言,朱光潜的观点比起左翼文艺家的看法远为深刻和合理,因为他的论点不仅显示了维护文艺自身特征的艺术良心,更显示了一个学者与时流抗争的学术勇气。[26]
但是,实际情况却以朱光潜的观点被左翼文艺家严厉攻击,更多知识青年同情和支持左翼文艺运动而告终。这原因不难理解。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崛起,在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对立之时,整个社会爱国热情和政治意识空前高涨。在这种时代气氛中,社会的现实需求无疑更倾向于“拿笔杆代枪杆,寓文略于战略”的左翼文艺一边;而朱光潜呼吁“作家们多效忠于艺术本身”的论调,自然是时代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不得不落入曲高和寡的窘境了。如果说,左翼文艺家因更多地着眼于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以及对现实功利的直接介入,一定程度上与文艺本身规律相隔膜;那么朱光潜的文艺观点,则因执著追求纯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的审美效应,与时代的要求相脱节。
正是如此,在我看来,朱光潜当年批评左翼文艺缺点的话,其本身并没有错,只是说话的时机不对,不合当时的“时宜”。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开创者和建设者之一。他所致力建构的一套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代表了诸如沈从文、梁实秋、李健吾、梁宗岱等一批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的审美选择。这种审美选择如果早在“五四”时期出现,它会被看作对于封建狭隘的“文以载道”论的一种反拨,看作文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受到礼赞。但是,它出现得太晚,直到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三、四十年代才登上文坛。此时,非阶级、非政治的超然态度,既容易受到“左”、“右”两边的夹攻而难以存身,又不免被激进的左派文艺家目为反阶级、反政治的思想而受到抵制和批判。当时代需要政治力量去改变现实时,他却要用谈美的方式去洗刷人心;当时代要调动一切因素服务于眼前的实际利益时,他却说文艺要超越这种功利而保持自身价值。结果,尽管他竭力维护的审美态度和文学趣味十分纯正,但由于不合时宜,还是被时代更为汹涌澎湃的浪潮所卷没和抛弃了。
这一切,对于朱光潜来说,固然是悲剧,但对于那只有血与火而排斥美的时代来说,又何尝不是悲剧呢!好在那政治与艺术激烈冲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当年充满政治鼓动作用和战斗激情的作品早已被人淡忘,而被视为落后以至反动的朱光潜的美学观点和文学思想,却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魅力。这胜于雄辩的事实,不是告诉我们许多值得深长思之的东西么?已有论者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朱先生这些三十年代美学著作的政治上的负作用将大为减弱,它们的学术价值相对地显得更加突出。”[27]这看法已为新时期以来的美学发展和文艺发展所证实,还将在未来得到更加充分的印证。
注释:
[1]参见蔡仪写于1948年的《论朱光潜》,《美学论著初编》 (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
[2]《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31页。
[3]《谈美》“开场话”,《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6页。
[4][6][7][9][10][11][13][14]《文艺心理学》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16、310、320、318、317、319、325页。
[5]《文艺心理学》第七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94页。
[8]《谈文学·文学与人生》,《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61页。
[12]《谈报章文学》,《天津国民日报》(1948年2月2日);又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352页。
[15]参见康德:《判断力批评》(宗白华译)上卷第一部分“审美判断力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9—82页。
[16]《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 又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80页。
[17]《中国思想的危机》,《大公报》1937年4月4日;又见《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514页。
[18]朱光潜写的“自传”里,说当时的编委会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和我”(见《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5页)。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有意没有提到叶公超,叶后来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任外交部长,又可能因记忆有误,以俞平伯代替了废名。
[19]《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 月);另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327页。
[20]《谈文学·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 《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84页。
[21]茅盾:《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载《文学》第9卷第1 期, 1937年7月1日出版。
[22]参见周扬:《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23]参见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1939年4月16日。
[24]参见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出版。
[25]参见刘锋杰:《京派批评观》,《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26]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所著《中国新文学史》里,说朱光潜的文艺见解“在功利主义弥漫的三十年代,这真是一副清凉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参见《中国新文学史(中)》第255页, 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
[27]李丕显:《朱光潜美学思想述评》,《美学》第4期,第90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标签:朱光潜论文; 文艺论文; 谈美论文; 道德论文; 有道论文; 文艺心理学论文; 朱光潜全集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