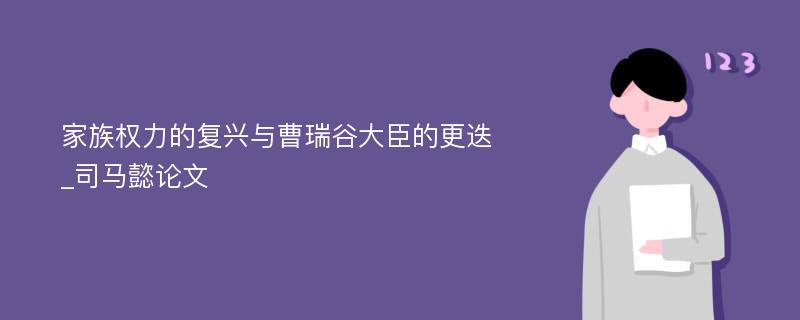
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族论文,大臣论文,势力论文,曹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如所周知,晋之代魏是通过所谓“禅让”的方式得以完成的。但实际上其谋篡的过程颇为漫长,前后历三代而成。纵观司马氏篡位的全过程,其关键在于司马懿辅政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为之奠定了基础。不过,司马懿一生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变故,哪一件事标志着其势力崛起并决定了魏、晋易祚的历史走向呢?对此,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10中说:“魏之亡,自曹丕遗诏命司马懿辅政始”,卢弼《三国志集解》卷9 引清人王懋竑语亦谓“懿受文帝遗诏辅政,已有不臣之心”,这一看法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实为马后炮式的自作聪明,他们把“起点”夸大成“标志”了。更多的学者则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诛杀曹爽集团为标志,如《三国志集解》卷9引王鸣盛语云:“魏氏之亡,始于曹爽之诛”。确实,通过此举,晋之代魏大局已定,但这一看法又太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其实,纵观司马懿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在上述两个事件之间的魏明帝曹睿顾命大臣之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确立了司马懿的政治地位,而且标志着世族势力的复兴。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一直缺乏深入了解,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文献记载的匮乏和失实。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记载,多是晋人留下来的材料,这是不能据以为信史的。据《晋书·王沈传》,沈受命“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所谓“多为时讳”,就是他们受到司马氏的压力,无法秉笔直书。《魏书》为晋朝官修,那私人所撰史书又如何呢?鱼豢所著《魏略》,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指出其“事止明帝”,但实际上羼杂了许多后来的“异闻”,《史通·题目》则称该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陈寿《三国志》亦为私人所撰,素有良史之誉,但同样受到压力,在有关问题上采用曲笔之法,并非尽为实录。王夫之明言:“《三国志》成于晋代,固司马氏之书也”(注:《读通鉴论》卷10)。赵翼指出“其体例已开后世国史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注:《廿二史札记》卷6“《三国志》书法”条)。 在古代集权专制状态下,文人修史,其时愈近,其言愈隐,这自有其难言的苦衷,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普遍现象。二是历代史家对魏、晋替嬗多从曹氏与司马氏之争的角度着眼,故往往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而缺乏通达的卓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13页,黄山书社1987年版)
陈先生的论断揭示了魏晋之际王朝兴废替嬗的社会原因和实质,这是以往历代考据家都不明白的道理,以此为指导来考察当时的史实,对很多不起眼的问题会有焕然一新的解释。《孟子·尽心下》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吾生也晚,且才疏学浅,然近读魏晋遗史,颇多疑惑,受孟子之怀疑精神和陈寅恪通达史观的感召,兹就魏明帝顾命大臣的改易问题略加考论,以证此事为司马懿之得势和世族复兴的标志。
二、汉晋之间寒门与儒学大族的升降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中论述魏明帝立嗣、遗诏顾命大臣及亡国之祸曰: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依陈寿的意思,曹爽若立长君,即可维系国祚,以免大权旁落;即便立幼主,理应托付专人,而明帝却以宗室代表曹爽与朝臣代表司马懿共同辅政,造成了两人的斗争,以致“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陈寿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他关注的只是曹氏与司马氏之兴废,自然流于皮相,不明真谛了。
细阅当时的有关史实,我们可以发现魏明帝在辅政大臣的安排上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其结局并非他所能控制的,而是统治阶级上层激烈斗争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司马懿夺取辅政大权以及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政治变革及统治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升降,是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自东汉中期以来,世家大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量的田庄,控制乡里的选举和舆论,其代表人物则世代为宦朝廷,在思想文化上尊奉儒学、崇尚礼法。世族的兴起带来了士风和制度的诸多变化,出现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注:仲长统《昌言》。)、“贡举则必阀阅为前”(注:王符《潜夫论·论荣篇》)的情形,他们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阶级,必将全面登上政治舞台。然而,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和天崩地解的下层社会的动乱,打乱了正常的历史进程,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世族势力的发展暂时受到了阻碍,他们在地方的军事代表如袁绍、袁术、刘表、刘焉等纷纷失败,而在战争中崛起的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都出身寒微,并不同程度地推行了抑制大族的政策。就曹操而言,他出身在最为当时士人鄙视的阉宦家庭,尽管他早已跻身士人之列,但“四世三公”的袁绍仍斥其为“赘阉遗丑”。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在他们的政治措施、文化观念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官渡一役,曹操击败袁绍,在政治上崇尚“法术”与集权,用人唯才而轻道德,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评中概括操执政特点:“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这是符合史实的;在文化上,曹操重文辞、倡通脱,不恪守儒家礼法;在生活上曹魏立后不重门第,颇为士众讥讽,以至有“曹氏自好立贱” (注:《三国志》卷5《后妃传》)之说。曹操的这些政策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但基本内容都为其后继者所沿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故晋人傅玄有言:“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注:《晋书》卷47《傅玄传》)验诸史实,此语不虚。明帝时杜恕上书直言:“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用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至慎也。”(注:《三国志》卷16《杜畿传附杜恕传》)对此,儒学大族人物是不满的,魏文帝和明帝时,他们不断要求复兴儒学、尊崇“三公”,都说明了这一点。
确实,明帝执政颇得乃祖曹操真传,大行法术之治,以收集权之效。史称其少时颇得曹操宠爱,“朝宴会同,睿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 (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世语》、孙盛语)。为太子时,不与大臣交结,即位之初,侍中刘晔独被召见,出则谓群臣言:“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 《世语》、孙盛语)东晋史家孙盛也说:“闻之长老,明帝天姿秀出,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命辅导,帝皆方任处之,政自己出。”(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世语》、孙盛语)《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则载其“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又称“明帝好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至大辟者”。这种统治作风与早年袁绍抨击曹操“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缯缴弃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注:《三国志》卷6《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情形完全一致。
不过,从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看,汉晋间寒门势力的得势只是暂时现象,而儒学大族则根深蒂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在社会动乱状态下,不得不暂时屈服于曹魏的统治,但他们一直在积蓄力量,图谋恢复旧序。曹操一死,他们便将九品中正制度改造成维护世族利益的工具,他们的代表人物正逐渐掌握曹魏的军政大权。在此过程中,代表世族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司马懿。对此,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儒家豪族是与寒门出身的曹氏对立的。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豪族不得不隐忍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曹操死后,他们找到了司马懿,支持司马懿向曹氏展开夺权斗争。袁绍是后继有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后来,他们通过司观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自己手上。(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13页,黄山书社1987年版)
三、司马懿之发迹与魏明帝改易辅政大臣的真相
儒学大族为何会选择司马懿为代表呢?这既与其家世有关,也与他在曹魏政权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关于司马懿之家世,《晋书·宣帝纪》载:
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
据此可知河内司马氏自东汉以来世代为将军、太守、尹。又据《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朗祖父俊“博学好古”,父防“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数十万言。……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由此可见司马氏崇尚儒学与礼法。司马懿为防之次子,“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官渡战后,他一度“不欲屈节曹氏”,拒绝曹操的征辟,这显然是对出身寒微的曹氏不满。
不过,经历了巨大社会变故的司马懿与东汉末年的“雍容讽议之士”不同,其性格“刚断英特”、“内忌外宽,猜忌多权变”,他看到曹氏势力正盛,于是转而“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遂安”。 (注:《晋书》卷1《宣帝纪》)建安二十四年(219), 懿竟上书劝曹操称帝。由“不欲屈节曹氏”,转而向操称说“天命”,这显然是一种“权变”。清人王呜盛曾喟叹:“(司马懿)少壮则为魏画篡汉策,及老则又为子孙定篡魏策,兴亡若置棋,亦可叹矣。”(注:《晋书》卷1《宣帝纪》)然而, 历曹操之世,懿未得重用。他任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和朱铄同为太子“四友”。因曹操继嗣未立,诸子相争,懿支持曹丕,史称其“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注:《十七史商榷》卷24“大谋奇策”条),对曹丕之立有大功。故魏文帝时深得“信重”,历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给事中、录尚书事、抚军将军等军政要职。黄初七年( 226)曹丕死,诏懿与曹真、曹休和陈群“并受顾命”,辅佐明帝。五年后真、休二人相继病死,而陈群为“文人诸生”、“从容之士”,并未实际带兵,而司马懿长期都督荆、豫、雍、梁诸州之军事,位至太尉,又西拒诸葛亮于秦陇,并在景初二年(238 )率兵灭亡长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获取了极高的声望,实际上控制了曹魏的军事大权,成为儒学大族和元老重臣的代表人物。
随着司马懿地位的上升,无论从维护其家族利益,还是从迎合世族社会的愿望的角度考虑,他都会有所表现。《晋书·后妃传·景怀夏侯皇后传》的一段难得的记载正说明了这一点: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后雅有识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
据此,夏侯徽为司马懿长子师之妻,师“每有所为,必豫筹画”,故知其父子“非魏之纯臣”,他们怕事情外泄,谋害夏侯氏以灭其口,今日看来,此举正可谓欲盖弥彰。
对司马氏势力的潜在威胁,魏明帝是有所觉察的。《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
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为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所谓“帝忧社稷”,实际上就是明帝对儒学大族势力复兴之势忧虑,从他与陈矫的对话看,显然对司马懿是否为“社稷之臣”表示怀疑。与此同时,性格鲠直的高堂隆临死前口占疏文曰:
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注:《三国志》卷25《商堂隆传》)
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指的正是手握兵权的司马懿,胡三省便直言:“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矣”(注:《资治通鉴》卷73胡三省注)。他希望魏明帝以宗室人物领兵,削弱司马氏的力量。然而,如上所述,司马懿势力的壮大,不仅是其家族的问题,而且代表着儒学大族的整体利益,陈矫称他为“朝廷之望”,说明他已得到广大士大夫的拥戴。王夫之分析当时士人心态指出:
魏之且移于司马氏,祸在旦夕,魏廷之士或不知也,知而或不言也。隆、矫知之而不深也,言之而不力也。当其时,懿未有植根深固之党,未有荣人、辱人、生人、杀人之威福,而无能尽底蕴以为魏主告。无他,心不存乎社稷,浮沈之识因之不定,未能剖心刻骨为曹氏,徊徘四顾而求奠其宗祜也。(注:《读通鉴论》卷10)
他以为曹魏没有真正的“忧国之臣”,“祸在旦夕”。确实,曹魏政权的社会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广大朝臣暗中多倾向司马懿,这也正是魏明帝忧虑之所在。
然而,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魏明帝既已怀疑司马懿并非“社稷之臣”,自然会有所提防,他产生了“使亲属广据权势”的想法,即重用宗室人物,以对抗司马懿及“朝臣”的力量,从而引发了激烈的辅政大臣之争。据载,景初二年( 238)十二月,年仅30余岁的魏明帝病重,然其无子,收养了两个宗室子弟为子,并决定以8岁的曹芳为太子。芳年幼,自然无法亲政, 故明帝将上述想法付诸实施,任命曹操子燕王宇为首辅,又以曹肇等人协助,形成了一个宗室顾命集团。《三国志·魏书·燕王宇传》:
(景初二年)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
同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也载:“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以上诸人,宇、爽、肇为宗室子弟,至于夏侯氏,曹操之父本出自夏侯氏,且又通婚,秦朗为曹操养子,素得明帝信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曹魏宗室辅政集团。
曹宇诸人执政之后,首先把矛头指向世族朝臣代表司马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载:“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以施行。”又《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枳关西还长安”。当时司马懿征辽东未还,曹宇、夏侯献等企图径直将其派往关中,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对大族“朝臣”中其他实权人物如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他们也意欲排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称放、资“久专权宠,为(秦)朗等素所不善”,《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世语》说得更明白:“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由上述考证可知,曹宇等人执政虽仅有四天,但他们已表现出了明确的政治意向,即打击儒学大族的代表,遏制其控辖朝政的势头,这也是魏明帝的意思。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明帝于十二月辛巳命曹宇等辅政,却于甲申将其罢免,可谓旋进旋黜,前引《燕王宇传》说:“受署四日,宇固深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刘放传》说得更生动:“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资固赞成之。”根据《三国志》的多处记载,魏明帝之更替辅政大臣,其因有二:一是曹宇等人“陈诚固辞”;二是明帝对他们的能力有怀疑。事情真这么简单吗?细心考订,上述情节皆为捏造。查《通鉴》,司马光不用《三国志》的记载,而依《汉晋春秋》和《世语》立说,《通鉴考异》称:“按陈寿当晋世作《魏志》,若言放、资本情,则于时非美,故迁就而为之讳也。今依习凿齿《汉晋春秋》、郭颁《世语》,似得其实”。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甲申,明帝‘气微”,曹宇诸人“有所议”,仅留曹爽一人守侯,刘放、孙资乘机“突前见帝”,劝明帝改换辅政,理由有四:一是提醒明帝“忘先王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二是“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三是“燕王拥兵南面”,限制他们入宫;四是警告明帝“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有壅隔,社稷危殆”,所谓“外有壅隔,让稷危殆”,实际是暗示操纵军政大权的司马懿和“朝臣”有不满之情,并有倾覆社稷之危。当时明帝已神智不清,放、资举曹爽代定,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明帝从之,但即刻又反悔,放让明帝立诏,其实帝已“困笃”,“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出而大言:“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宇诸人“相与泣而归第”。
由上考可知,魏明帝临死前突然更换宗室辅政大臣,且以司以懿“相参”,并非其本意,完全是世族“朝臣”代表刘放、孙资策划的一次阴谋政变。他们举曹爽,明帝便问“堪其事不?”爽也无准备,“流汗不能对”,孙资代答“臣以死奉社稷”。(注:《三国志》卷14《刘放传》注引《世语》)他们之所以之样安排,因为必须一名宗室辅政,相较之下,曹爽有“庸才凡品”之称,易于对付。放、资二人在明帝绝气之际改变了他意欲“亲属广据权势”的打算,代之以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
因此,对魏明帝顾命大臣之改易,切不可以一般的宫廷权力斗争视之,它是汉魏以来寒门与儒学大族长期斗争的产物。刘放、孙资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迫使明帝改易顾命人选,黜退燕王宇等人,尽管有各方面因素起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世族朝臣的利益,在于他们的背后拥有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阶级的支撑。由于文献记载的不足,当时诸多朝臣的态度已无从祥述,但从明帝改易顾命大臣之后他们无任何不同反响看,显然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至于司马懿、他虽不在洛阳,但毫无疑问题,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决定了他仍是这一政变的核心人物。根据一些材料的分析,司马懿此时虽领兵在外,但他对洛京政局的变化有遥控之力,懿与放、资诸人早有关连。清人王懋竑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文帝、明帝受腹心之托,膺社稷之重寄,不同一言之谏争,而且阴结刘放、孙资以为内主,卒以倾魏。(注:《三国志集解》卷9注引)
对此,《晋书·宣帝纪》有一段记载可以证实:
先是,诏帝便道镇关中,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
由此可见懿与放、资等在当时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所谓“手诏”,正是刘放等伪造的,可以说司马懿与长期控制曹魏中枢机要大权的刘放、孙资等已结成了集团,正是他们内外呼应,才完成了这次决定未来历史走向的政变。司以懿诸人的结党及其辅政大臣地位的确立,是他们对曹魏皇权的第一次挑战,这标志着寒门与儒学大族的斗争又到了一个转折关头,预示着儒学世族已踏上了全面复兴之路,仅就曹氏、司马氏之争而言,这也是司马氏代魏的第一回合的较量,此后政治斗争的格局亦基本形成。
标签:司马懿论文; 魏书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集解论文; 魏明帝论文; 三国志论文; 汉晋春秋论文; 曹操论文; 读通鉴论论文; 魏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