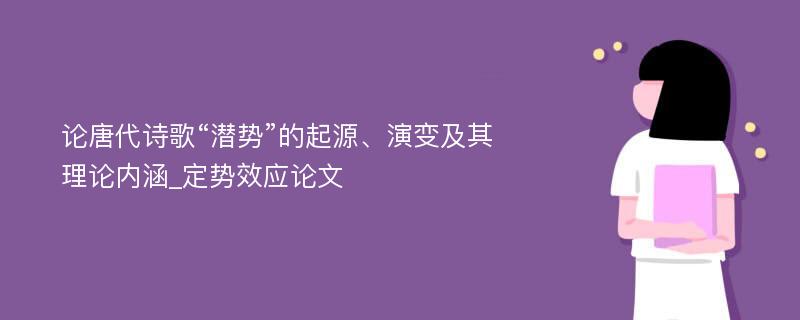
论唐代诗格之“势”的源流演变及理论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唐代论文,内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3)03-0001-07
萧华荣先生认为唐人诗学的最大特征“主要就是走向诗艺的精微化”[1],这一看法可谓卓识。因为此时的诗学话题,已从先前有关缘情写物、穷形尽相等一般艺术规律的探讨,转而深入研究缀章属对、调声病犯、章法布局、象境韵味等细微问题,这从现存的唐人诗格类著作可见[2]。此类书多半罗列诗法,回避禁忌,条目酷细,义项晦涩,不加解说,仅呈例证,前人对之多作低评,如杂集诗格而成的《文镜秘府论》作者空海即认为其“勘彼同异,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3],王夫之甚至对其中的杰作皎然《诗式》亦目为“画地成牢以陷人”[4]。其实,如果不为成见所囿,联系时人所承袭的文化传统和其时诗学环境,重新审视诗格,激活其理论因子,可促进古典诗学的研究的深入。
在阅读唐人诗格时,一个看似容易明白、细思又不易解的术语,频频闪入眼帘:“势。”由于时人未对“势”界定意义,谈论时又花样翻新,随意创立名目,结果“势”义越发漫衍朦胧,不说还可意会,越说越难理喻,以至于一些文论史、诗论史对之或回避解释,或处理过于简单化[5]。就笔者所见,张伯伟先生从禅学角度解释“势”[5],新颖独到,胜解纷呈。本文受其启发,尝试对“势”之诗学意义抽绎辨析。
在汉语字词搭配中,“势”作为词素,使用率高,意蕴含混,用法灵活,可和许多字组合成词,应用颇广,内涵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有的指事物处于某种状态状况,表征意义模糊笼统,如山势、虎势、颓势、局势、气势等;有的指某种人为的、可以凭借的力量,如权势、势力、势利、财势等;有的意义已虚化,指不太显明的政治、军事等社会内容状况或情态,如情势、阵势、态势、威势等;有的指事物力量集聚,将要呈现某种发展趋向,如来势、势头、趋势、势必等;有的指可利用的某种有利条件,如顺势、助势、趁势、就势等;有的指拿腔作调,故意摆出某种矫饰的姿态行为,如作势、把势、势派、势头等;有的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某种难以抵挡的力量,如势均力敌、势不两立、势如破竹等;还有一类,属现代科学术语,如电势、位势、势能等。从以上可见,由“势”字所组词语,搭配之随意,意义之繁杂,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从字源意义上追溯,它指称一种“力”。如许慎说:“势者,盛力,权也。”(《说文解字》)虞翻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象》),也以“力”言势:“势,力也。”高诱注“各有其自然之势”(《淮南子·修务》),同样以“力”目“势”:“势,力也。”看来,力的强弱、大小及分布状态,往往决定事物的外在情态面貌。从“力”理解“势”,应成为论说基点。
中国古人以“势”为论说术语,历史久远。如果分析先秦子书中“势”字意义,指称军事状况或情态最值得人注意,以《孙子兵法》为例说明。本书中“势”字出现十四次,分别见于《地篇》、《势篇》和《地形篇》。据李零先生考释,“势”在《孙子》中多指“作战的态势”,是“战争中人为、易变、潜在的诸因素。它与‘形’相反,多指随机的和能动的东西,如指挥的灵活,士气的勇怯,等等。在《计》中,作者把‘势’看作是利用优势,制造优势(‘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本篇(指《势》)中,作者则强调指出,‘势’是以‘奇正’之术(兵力的战术配置)为主要内容,并且在实施中要取决于士兵临战的实际发挥,特别是随环境变化的‘勇怯’(‘勇怯,势也。’)”[6]。孙子论军事,最鲜明的特征是不着眼于具体战术方法,而重视将帅的预先谋略与临时权变,这就使其兵法超越了一般的形而下因素,诸如征募兵员、训练调教、装备设施、军令条例等具体事项,而论述将帅如何根据瞬息万变的战争事态,制定相应对策以取胜。孙子重视战略问题,主张统摄全局,不以攻城陷地、争夺微利而丧失了“全国为上”(《谋攻》)这一军争圭臬,故特意拈出“势”字,说明战争策略,提醒将帅要从当前的“势”即时刻都在变动的事态(这与事先对敌情的侦察、兵力的调遣、灵活的战术有关)出发,制定正确对策,抓住有利战机,出奇制胜。故审“势”而不死守成法,就成了为将大要。“势”在孙子,是客观事态发展和人为军事调集活动相结合而产生的,是敌我两方力量在一定情况下转变的综合因素,而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故“势”在兵事中,也是潜在、暗蓄的力量,是由双方实力的比较和人事的变动造成的结局。孙子有关“势”的思想,与《周易》朴素的辩证思维相通。《周易》以太极为中心,选取八类自然现象作为元素,并比附天象人事,抽象出八卦,以玄机灵动来演绎世变、推测人事,具有天人合一的思维特征。其用语高古深微,除极少数关涉上古史事外,时以形象表意,大都超越时空局限,毫无定指,任人拟议变化,给解释者提供了无限的诠释空间,表现了东方民族智慧的圆融通贯,给人的启迪在于:仰观俯察,根据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事态现时状况或预测事态发展方向。《周易》所用来观测、预料事态变化的根本思想,与《孙子兵法》有关军争之“势”的论述内在思想一致。从两书可见,重视变易、以“势”论事的思维方法,很早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之中。
到汉代,子书中“势”与其他字组合成词,也是人们论事说理的常用话语。据《诸子集成》[7]统计,《春秋繁露》中“势”出现17次,《法言》中“势”出现1次,《淮南子》中“势”出现106次,《新语)中“势”出现58次,《新书》中“势”出现3次,《盐铁论》中“势”出现35次,《论衡》中“势”出现29次,《申鉴》中“势”出现4次,《潜夫论》出现35次。逐一分析,发现众书多从时事政治立论,故所用的各类“势”,多与国情事况形态有关,表明决策者对事态的分析,其蕴义基本未超出本文开始列举的“势”义分类,与我们的论旨相关不大,可略而不提。但是,汉魏时期,书画论对“势”的引入,倒成为认识诗学之“势”的契机。
在汉代书论中,“势”已为人们所接纳并反复使用,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具有独特内涵的理论术语。如崔瑷《草书势》、蔡邕《篆势》采用形象的语言,初步分析并描绘出草、篆两体字体由于不同的笔法运用,所导致的不同笔迹走向特点。蔡邕《九势》[8]最早揭示出“势”产生的哲学基础,把它与衍生自然万物的阴阳因素联系,说明“势”产生的根源:“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由于其时认识水平所限,他还不能明白说明“势”的成因,而指出“势”具有人力不可左右的神秘特点——“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已揭示不同的“势”在组成字的形体结构时产生的不同作用:“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趯之内。”从以上可见,书论之“势”,主要指各种笔势,即运用不同笔法所造成的线条不同流向、走向所呈现的状态及其给人们的动态视觉印象,“势”的形成与人们运用不同笔法组字的间架结构方式有关,整篇书法的“势”感与其章法安排有关。为了更好说明书论之“势”,且引三位学者说法。周汝昌先生说:“‘势’的内容,包括较广。每一笔画本身的势,众画结联上的势,字与字间‘章法’上的势,大约可以概括为一句简单的话:势就是关系问题。关系不清,道理不明,最多能写出作为文字字体的‘死’的符号,必然写不出作为书法艺术的‘活’的形象。‘关系’或‘势’的重要,即在于此。”[9]周氏从笔画间的关系理解“势”,说明它产生于间架结构中。沈尹默先生说:“笔法是任何一种点画都要运用着它,即所谓‘笔笔中锋’,是必须共守的根本方法;笔势乃是一种单行规则,是每一种点画各自顺从着各具的特殊姿势的写法。……笔势是在笔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因为时代和人的性情有肥瘦、长短、曲直、方圆、平侧、巧拙、和峻等各式各样的不同,不像笔法那样一致而不可变易。”[10]沈氏把“笔势”与笔法结合,指出其产生的基础在于艺术技巧。白鹤先生说:“势是行动之力,或行动之状态,前者如火势、水势,后者如手势、姿势。……重在如何发挥用笔的定式,使之产生力量,即是指如何运笔的问题。……(又)是一种奋发之力及其姿势,是以点画用笔的动态的分析和运笔中的动势的运用和发挥。……重在强调运笔的轻重缓急和因势而来的毫端正反逆侧等的变化。……是法的力量和精神的表现。”[11]白氏从运笔中潜存的力度解“势”,认为是法的力量与人的精神的形象再现。总之,书法字迹中的“势”感,来自不同笔法,笔法的运用中又蕴含着书者个人独特的生命力——“气”和所欲表现的笔意——“情”,带有对外在物象的模拟和主观情思的吐露之意,在字迹线条或流畅或涩拙或庄重或谐趣的变化中,书者的生命感受与个人情思通过书法之迹表现出来,给人一种动态、流变的力感,可以说“势”是笔者之气、抒情之意、运笔之力的合体。
从汉以后,以“势”论书法,变前此的零星散论成为系统论述,人们所赋予它的理论意义也随之深化。由于长期书写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技巧,书法中某些富于表现力的笔势,被一些理论家归纳总结定型化,提出了五花八门的书势、笔势。有的进行理论概括,如卫恒《四体书势》[8],从书法风格的演变,分析古科斗书、篆书、隶书、草书四体书法特征,认为“书势”是书法显示出的动态,具有节奏感和流动性,由于书体差异,造成书势的千差万别。有的分论各体书势,如杨泉《草书赋》[12]、索靖《草书势》[8]以形象的语言,描述了草书势的多样性,其中孕含了书者的情绪意态。到后来,托名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8],提出笔“势”创造之法,“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下笔之初笔法力量应收敛蕴蓄,不可过分张扬显露,并从不同笔法的运用所造成的十二种笔势所呈现的状态,说明“势”对于书法成败的重要。另一托名王氏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8]也说明书写草字“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伏,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认为草书之“势”并不单调划一,可以广泛吸收其他书体的字体状态,把各类笔势融为一体:“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这与先秦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物一无文”[13],追求多样因素的融会,产生艺术美的思想相通。从萧衍以后,“势”已作为稳定的术语广泛用于书评,如《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等等。
魏晋时期,随着“势”义的逐代积淀,它还越出书法畛域,被移植到画论之中。如顾恺之《画评》[14]用“势”5次,提出画人物应“布势”、画壮士现其“奔腾大势,激荡之态”、画马应尽“马势”、画佛应有“情势”、画池应呈其“形势”,他的《画云台山记》[14]用“势”3次,也要求画自然山水,应把其各种态势表现出来,宗炳《画山水序》、梁元帝《山水松石格》、姚最《续古画品录》也与其思想相通。后之论者,举不胜举。对绘画中“势”感的生成,韩昌力先生做了精辟论述:“就绘画而言,主体生命力(元气)的扩张导致某种精神的骚动,这种骚动使身体各部位产生同构的波动效应,最后借助手所控制的毛笔——起伏、波动、偃仰——而得以释放转化,使内气外化显现为‘有’,当‘有’呈现的一刹那,抟气结集的虚无白纸被破分为阴阳两极。如此发展笔笔交错,阴阳相生,构成内外、有无、物物的呼应与冲突,这就形成了一种势的关系。”[15]从此观点,他认为:“势”产生于气的生发,主体从物象的呼应联结中发现和感悟到气的力量及形态;“势”是线条运动变化、色彩添充延续与人的形体组织在气的主使下的结合;“势”给人以力感,但又不完全是物理的实在能量,也包括心理能量向自然能量的外在转化,因此从“锥划沙”、“屋漏痕”、“万岁枯藤”中才能感受到力感;更重要的,“势”是知识学养和对自然感悟、经营布置的组合,而情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势”还要超越物象的一般性,追求内在生命力与自然活力的融合,使气摆脱客观物象的单调而扩张。因此,我们认为,以“势”评画,注重整个画面的生机气韵与画家生命力的契合,其中融铸了主体的艺术感受、个性气质、艺术技巧和对自然的静观自悟,决定了整体艺术风格。
除了书画论大量用“势”外,唐代禅学也对“势”的思想有所发展。禅学追求定慧合一,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和任运不拘的静观自得,认为凭借书本知识领悟佛法佛理,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注重深察默会,寻求灵机洞开,恍然大悟。禅学大师对于徒弟所发问的“佛法”、“第一义”、“西来意”、“涅槃”等佛学根本问题,都不正面回答(其实也很难回答),而是采取似答似疑、似答似问、反诘、双关、隐谜、诗化偈语、作各种姿态等方式暗示、接引他们,使其独立体悟,心揣意会。同时,禅师根据学人的慧根深浅,因类施教,应机接化,勘辨其修证深浅。师徒的对答,往往充满令人会心的、巧妙的机锋和譬喻,外人难晓其义,而对话者由于心意契合,在意会中理解,精神随之而愉娱。以《五灯会元》(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发电子版《北大语料库·五灯会元》统计)为例。本书用“势”114次,其义有五,除力量、人名中字及禅师与僧人平素言谈时所涉及时间、地形时用字外,最主要有:一、禅师在启悟徒弟时,为了激发思考,除从语言上开导外,还随机应变,作出各种动作,让弟子从中体会,如猛噬之势、患风势、拨眉势、掀禅床势、抽坐具势、斫牌势、除帽势、覆钵势、斫额势、背抛势、拽鼻势、轮椎势等等。二、禅师在富于启示的偈语中用字,内容也多种多样,如“奇怪石头形似虎,火烧松树势如龙”,“楼阁凌云势,峰峦叠翠层”,“瓶有倾茶势,篮中无一瓯”。据张伯伟先生考论,禅宗大师语“势”,“偏重于上下语的搭配安排”,注意选择具有“动感的词加以形容”[5]。由以上可见,禅学用“势”字,除如张先生所言,与禅师讲究言辞用语有关,也与禅宗的运思方式有关。这对揭示诗学之“势”的意义,有一定提示作用。
如果我们把认识视野再扩大一下,从唐人文化传统、生活艺术氛围来看,就会感到书画禅之“势”对其时诗学引入“势”这一概念有潜在的意义。由于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文化格局对读书人长期的熏陶滋染,书画理论中“势”的思想,必定会对唐人诗学思想有影响;由于禅宗在唐代兴盛,其对士人处世态度、生活观念冲击触发,禅“势”的认识观念和思维方式,对其时文人的思想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当然,如果从诗学观念的流变考察,刘勰《文心雕龙》有关“势”论,对唐人诗论中这一观念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
在《文心雕龙》[16]的十五篇(《诠赋》、《杂文》、《诸子》、《论说》、《檄移》、《封禅》、《奏启》、《定势》、《熔裁》、《声律》、《夸饰》、《附会》、《物色》、《才略》、《序志》)中,“势”字共出现43次,最令人兴奋的是《定势》中的22次,它与文论思想关系密切。本篇中“势”多与指称文章体制、样式的“体”相对,关乎文章具有相对稳定状态的总体风貌。对“势”的意义,以下几种看法较有代表性。铃木虎雄认为《定势》是“对文学作品随着其体裁的不同也应有不同的修辞方法的见解加以说明”[17],把体裁与修辞手段联系,虽看出了形成“势”的内因,但尚未抓住关健。范文澜解释:“势者,标准也,审察题旨,知当用何种体制作标准。标准既定,则意有取舍,辞有简择,及其成文,止有体而无所势也。”“所谓势者,既非故慷慨,叫嚣示雄,亦非强事低回,舒缓取姿;文各有体,即体成势,章表奏议,不得杂以嘲弄,符册檄移,不得空谈风月,即所谓势也。”[18]范氏提出“势”的内涵流动不定,又是决定文意、辞、体的一种模糊标准,仍未把“势”义明确揭示。郭绍虞认为“势是作品所表现的语言姿态,即语调辞气。”[19]郭氏把“势”义落实到具体的语调辞气,但未从决定“势”的因素展开论述。周振甫说:“定势就是文章的体势,即文章的体裁及其所具有的一定的自然趋势。”“定势就是按自然形成的趋势来确定体式。”“按照不同的内容来确定不同的体制和风格,这就是定势。”[16]周氏与范氏一样,主要强调“势”的流动性,未对其义作更多辨析,但指出其与风格的关系。詹牓《文心雕龙疏证》认为:“在《定势》篇里,‘势’和‘体’联系起来,指的是作品的风格倾向,这种趋势本来是变化无定的。《通变》篇说:‘变文之数无方。’‘势’就属于《通变》篇所谓‘文辞气力’这一类的。这种趋势是顺乎自然的,但又有一定的规律性,势虽无定而有定,所以叫作‘定势’。”詹氏在揭示“势”义变动不居的同时,又指出其主要指向文章的“文辞气力”,强调自然与规律。上述观点,各揭开了“势”义的一角,可就此再作辨析。
从《定势》看,“势”义可从以下几方面认识:从产生根源看,它与情、体有关:“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刘勰指出,虽然为文之法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以情为立言之本(《知音》即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文章的体制、样式从根本上说是由情决定的,人们根据体式的不同遣词造句,把情寓于篇章字句之中,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势”。“势”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范式、套子,要根据所抒之情选择与之相契之体,而言辞在不同之体的布局,即导致不同的“势”,“循体而成势”就成为体与势的基本关系——“势”从属于体,体定而势出。但是,情虽先于立辞,决定辞所表现的内容,但辞也并非完全被动,为了更好地达情,人们会按照体的特点妥善安排辞,因此“势”最终成为什么状态,仍需要人为的修饰加工,“情固先辞,势实须泽。”故“势”不是什么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它是情在一定的文体要求、语言安排下产生的表达效果。虽然“势”的形成与人工的安排有关,但刘勰认为文章之“势”要追求自然,即趁着有利的情况而形成体式,追求自然之趣:“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这样一来,当然要求情、辞、体在文章中水乳交融,尽量泯去人为痕迹。故作者作《定势》,实际上文章之“势”是无定的,他提出这种思想,是要人们从情、辞、体三方面把握“势”,寻求确立“势”的规律。既然“势”在文章中是无定的、多变的,同时又与事物的特质有关,“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故作者反对那种以一定之“势”而律一切文体的做法,提出“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因此,刘勰作《定势》,并未确立什么固定的“势”,让人去恪守,而是教人深入体会辞、情、体在文中的关系,巧妙地安排,从而确立文章之“势”,其中蓄含着艺术的辩证思想。为此,作者根据不同文体的写作目的、语言风格,提出不同的“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对于那些不遵守为文之规律,着意追求诡巧之势的人,作者严厉批评,并提出在一篇文章中要“定势”,关健要在字句的“正反”,即处理好语言运用的正统与变异,从对立与和谐之中,把“势”凸现出来,而对当时作者的错误倾向批评:“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刘勰所论,在于强调以变为“定势”之法。
从汉魏以来书、画、文论及禅学有关“势”的意义来看,与体相关的气(即人内在的生命力)、情、辞、力(即作品中的内在情感力量),成为影响“势”之面貌的主要因素,而唐代诗格对“势”的认识,就是对其具体的论说。
唐人在讨论诗歌的艺术机制时,把“势”作为重要范畴使用,论者列举了不同的“势”,并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其形貌,均引诗句为证,几乎不作论说。如佚名《诗评·诗有四势》[2]引用四句诗,昭示四种诗“势”:“《咏雪》诗:‘漭荡缤纷下无际。’此毒龙势也;‘旋从风势乱纵横。’此灵凤含珠势也。‘飘来平处添愁起。’此乃猛虎出林势也;末句云:‘济得民安即太早。’此乃鲸吞巨海势也。”
徐寅《雅道机要·明势含升降》[2]也引用八句诗,列举诗之八“势”:“洪河侧掌势。诗曰:‘游人微动水,高岸便生云。’丹凤衔珠势。诗曰:‘正思浮世事,又过古城边。’孤雁失群势。诗曰:‘人情苟且头头见,世路欹危处处惊。’猛虎跳涧势。诗曰:‘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云雾绕山势。诗曰:‘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纲疏。’龙凤交吟势。诗曰:‘昆玉已成廊庙器,涧泉犹是薜罗身。’孤峰直起势。诗曰:‘山中携卷去,[牓]上得官归。’猛虎踞林势。诗曰:‘窗前闲弄鸳鸯绣,壁上时看獬豸图。’”
神彧《诗格·论诗势》[2]以鸟兽草木的形态,喻示诗之十“势”:“诗有十势:一曰芙蓉映水势。诗曰:‘径与禅流并,心将世俗分。’二曰龙潜巨浸势。诗曰:‘天下已归汉,山中犹避秦。’三曰龙行虎步势。诗曰:‘两浙寻山遍,孤舟载鹤归。’四曰狮子返掷势。诗曰:‘高情寄南涧,白日伴云闲。’五曰寒松病枝势。诗曰:‘一心思谏主,开口不防人。’六曰风动势。诗曰:‘半夜长安雨,灯前越客吟。’七曰惊鸿背飞势。诗曰:‘龙楼曾作客,鹤氅不为臣。’八曰离合势。诗曰:‘东西南北人,高迹此相亲。’”九曰孤鸿出塞势。诗曰:‘众木又摇落,望君君不还。’十曰虎纵出群势。诗曰:‘三间茅屋无人到,十里松门独自游。’”
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十势》[2]以动物的不同动作形态,分别引诗说明,喻示诗之十种“势”:“狮子返掷势。诗曰:‘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猛虎踞林势。诗曰:‘窗前闲咏鸳鸯句,壁下时观獬豸图。’丹凤衔珠势。诗曰:‘正思浮世事,又到古城边。’毒龙顾尾势。诗曰:‘可能有事关心后,得似无人识面时。’孤雁失群势。诗曰:‘既不经离别,安知慕远心。’洪河侧掌势。诗曰:‘游人微动水,高岸更生风。’龙凤交吟势。诗曰:‘昆玉已成廊庙器,涧松犹是薜罗身。’猛虎投涧势。诗曰:‘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龙潜巨浸势。诗曰:‘养猿寒嶂叠,擎鹤密林疏。’鲸吞巨海势。诗曰:‘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
从以上所举例,可见唐人论诗时对“势”的重视。有的诗论家甚至把“势”作为诗歌创作成败的关健,如神彧《诗格·论诗势》论诗首重“势”以为明“势”之后,方可谈到构思、字句问题:“先须明其体势,然后用思取句。”皎然也把“势”作为其诗学最重要的问题提出,《诗式》[2]开篇即“明势”,描述大自然山川形态的千奇百怪,瞬息万变,说明诗“势”的千变万化:“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然后,描述诗思的开合变化,点出奇势产生的不同形态:“或极天高峙,崪焉不群,气腾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再以大江大河水波的平静明亮深厚,说明“奇势”的互相触发,愈加增加了诗歌的内蕴:“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互发。)”最后,说明凡古今名作都在“势”上下功夫:“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矣。”又指出诗歌气象混沌,就在于对势经意的安排:“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并向人们提示,初学者作诗,如若借用他人诗之“势”,用思精巧,虽不全出己心,亦不失为佳作,这就是作者所欣赏的“偷势”:“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阃城之中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作诗之时,如果构思与景物不相融合,没有兴感与外景相融,则诗“势”受到影响,可见“势”关乎诗的整体面貌:“脱若思来景遏,其势中断,亦须如寒松病枝,风摆半折。”唐人还接受书画论中“势”的思想,认为“势”即是力,是作者内在的充沛饱满之生命力的体现,如徐寅《雅道机要·明势含升降》明确说“势”可产生极大动能,艺术的匠心独出就在于巧心安排这种力,让它流溢于字里行间:“势者,诗之力也。如物有势,即无往不克。此道隐其间,作者明然可见。”因此,从诗之情感力度的强弱、轻重,可以感受到作者生命力、意志力的状况。唐人认为,在具体诗歌创造中,语言运用与作者兴感密不可分,而“势”的产生随情感的勃动而形成:“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皎然《诗式》)这一看法,与《文心雕龙》“循体而成势”的思想一致。同时,“势”的形成还与“作用”——作者的艺术构思有关,而构思除情感的酝酿、形象的构成外,重要的就是字词句的安排有序,如若思与意合,结构整体缜密,那么造“势”就很顺利,反之则蹇碍:“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势有通塞者,谓一篇之中,后势特起,前势似断,如惊鸿背飞,却顾俦侣,即曹植诗云:‘浮深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同上)由此可见,“势”最终导致艺术风格的生成。总之,尽管唐人诗格多不给予“势”明确的意义,而以形容语描绘不同诗势的状态,但从上面所引,可初步得出如下结论:一、“势”是诗中具有的可变性因素,诗的表达旨趣、方法不同,“势”就会相异;二、“势”与诗的体裁有关,并由情感而决定,体裁与情感融合的不同,导致“势”呈现各种面貌;三、“势”与构思联系,构思深浅与否,影响“势”的形态;四、“势”与诗中所充溢的“气”——作者的情感力、生命力、意志力有关,生命之气充斥于严密的语言结构,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使人感受到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形之于文章,即阅读时人所感受到的语言气势,而气势的不同形成诗的整体艺术风格。可以说,“势”是充溢于诗之体式中的气、情、辞、力和谐统一体。
唐代以后,“势”作为文论术语,普遍用于诗文评。如宋景淳《诗评》[2]:“凡为诗要识体势,或状同山立,或势若河流。”元佚名《诗教指南集·诗立体势》[20]:“古之善吟者,若吟一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言近而指远,则有赋、比、兴在其中矣。”明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质顺势,融熔而不自知。”(明万历浙江思山堂本《李空同全集》卷六一)胡应麟《诗薮·外编》[21]卷五:“工部诗尽得古今体势。”清贺贻孙《与友人论文书四》:“(为文)高以崇其体,博以壮其势。”(同治九年敕书楼刻本《水田居集·文》卷五)刘大櫆《论文偶记》:“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22]有趣的是,王夫之尽管极力批击唐人诗格的弊端,但其论诗仍离不开“势”,且把它作为主宰诗“意”的肯綮:“(作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他欣赏谢灵运作诗善于取势,结果诗歌达到“天矫连蜷,烟云缭绕”的混沌气象:“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他甚至认为:论诗若不论“势”,就无以缩万里于咫尺,难以有宏伟气慨;论诗若不识“势”之真谛,则如拙劣的画作“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4]从王夫之的论述,可见“势”这个中国化的理论术语所具有的魅力,因为它屡屡为论者引用解说,积淀了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意义,故内涵丰富,生机无穷。
[收稿日期]2003-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