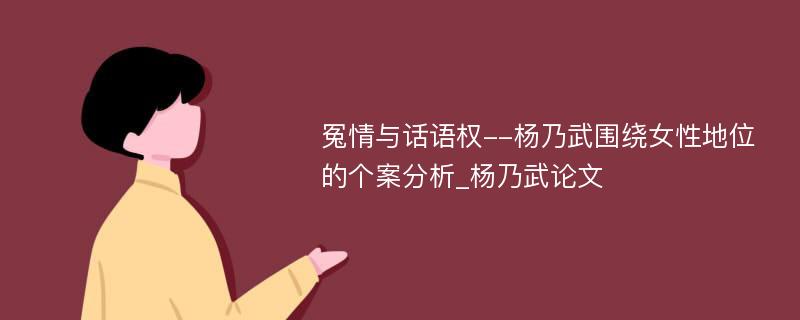
冤案与话语权——围绕女性立场而对杨乃武案的一个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冤案论文,而对论文,话语权论文,立场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我国古代直至近现代的法律现象中,冤案始终像幽灵一样徘徊其中,对此我们已是见怪不怪。不宁唯是,对自古至今的一些大冤案我们还始终津津乐道:有史以来不知有多少冤案被评弹、被说唱、被搬上戏曲舞台。它们承载着对我国一种独特文化——冤案文化的集体表达与记忆。黯然失色的是,对于冤案何以历朝历代都那么多、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历朝典籍皆集体失语,毫无意识。勿庸置疑,这种意识只能产生于近代以后的特定群体——法学家群体的研究中。而随朝代更替法典规范——其主体无一例外地是刑法(刑罚)规范——愈加精致缜密的古代中国偏偏“不存在着辩护的法学家阶层,似乎也根本不存在着专门的法律培训”,(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8页。) 因而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的自治性在二千余年的古代中国未曾出现。(注:美国当代法学家昂格尔曾分析说:“在古代中国,行政命令和法律规则之间并无明确界线;没有摆脱统治者顾问身份的可辨认的法律职业;没有置身于道德和政策论据之外的特殊的法律推理模式。”因而,中国古代的法是非自治的,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并非是一种法律秩序。参见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以下。) 无自治性当然就无自觉治理之行为,所以为减少及防止冤案产生的制度性措施历来缺乏,讼狱不断也就冤屈不绝。
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试图运用美国法社会学家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的纯粹法社会学理论,并结合古代帝制中国法律与社会的历史现实以晚清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案”为个案,(注:发生在晚清同光年间(1873~1877)的杨乃武案(一般称之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就其知名度而言堪称是晚清四大冤案之首(另外三个为“杨月楼案”、“张汶祥刺马案”和“太原奇案”)。但对杨乃武案的专题性研究在法学界及社会学界还相当缺乏,据笔者所见仅一篇,即郑定、杨昂:《不可能的任务:晚清冤狱之渊薮——以杨乃武小白菜案初审官刘锡彤为中心的分析》(《法学家》2005年第2期)。其他资料性编著主要有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编的《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策来编著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王先生那本《真情披露》可谓名副其实,该书第二部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抄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杨乃武案的“奏折”“具题”“上谕”等二十份。本文的研究在资料上主要得益于此书,特此鸣谢。) 从案中当事人——小白菜这一女性视角来透视冤案是如何产生的。当然,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冤案。但既然它们都具有“冤”的共性,那笔者以为,解析其中一个大冤案是如何产生,对于整体上认识我国古代冤案何以层出不穷不无裨益。有道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在民妇与举人之间
其实,本案最初的案情并不复杂。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九日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突然暴病身亡。因第二天尸体口、鼻内流出血水,其母疑是中毒而死就到县衙喊告要求验尸。知县刘锡彤带领仵作、门丁赶赴尸身现场前,生员陈竹山正好来给他看病,向其“提及葛毕氏曾与杨乃武同居,因不避嫌疑,外人颇多谈论。搬家后,夫妻吵闹剪发。今葛品连暴亡,皆说被葛毕氏谋毒”(语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定案”折)。仵作验尸时出现试毒银针未用皂角水擦洗等违规操作行为,相验认为是烟毒。门丁则与之争辩说不像是自服烟毒应系服砒毒。结果,仵作就含糊报称服毒身死。惑于传闻、轻信门丁的刘锡彤不问所服何毒就草率地断定葛品连系中毒身亡。随后将葛品连之妻葛毕氏即小白菜带回县衙。开始审问时,小白菜供称对丈夫葛品连中毒之事毫不知情。刘锡彤加以刑讯,小白菜不堪忍受,又因丈夫尸身验系服毒,难以置辩,所以作了与杨乃武因奸谋毒的枉供。“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刘锡彤先入为主的判断通过刑讯淫威的手段成了“事实真相”。草菅人命的他一开始就将此案“办”成了冤案。被诬攀的杨乃武之后也屈打成招,但他不甘心遭此天大的冤狱,漫漫伸冤之路由此迈步。
案发前两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举人。举人伸冤,在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颇为罕见。因而,杨乃武伸冤惊动了朝野,使得它在形式上膨胀成一个“独立”的大案。事物的逻辑——它不等于逻辑的事物,是由刑逼小白菜而派生出来的杨乃武冤屈案后来完全掩盖了“小白菜毒毙本夫葛品连”这一本案。换句话说,自杨乃武伸冤开始,案内司法资源与案外舆论视线全都集中到派生之案身上,本案反被弃置不顾了。案情畸形发展到这步田地,原因在于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与小白菜的民妇地位不对称,从而使得整个案件的社会结构处于极不均衡状态。(注:案件的社会结构,是唐纳德·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法律案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与方向。布莱克认为,案件的命运就取决于案件的社会结构。参见布莱克著:《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中文版序言,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第四部分将利用这一理论详细分析本案。)
民妇小白菜被刑讯逼供成冤,但正如下文所分析的那样她无法伸冤,所以在马拉松式的七次审理中皆不见她鸣冤。杨乃武则是另一番“风景”。他饱读诗书擅写诉状,更厉害的是,他新得的举人身份给他带来了足够多的社会资本,(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是社会学的一种理论研究范式,其概念内涵界定不一,核心是指一种大有用途的稀缺的资源和关系,参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使其伸冤之举能够坚持下去。在此案一审中,杨乃武就有干兄弟监生吴玉琨、堂兄增生杨恭治等五人联名向知县刘锡彤递交公禀,证明小白菜供称的杨乃武与之交砒霜的时间纯属枉供。之后杨乃武在狱中写了大量的伸冤材料,由其胞姐、妻子等向杭州各衙门散发申诉,并两次北上京控。此等声势浩大的伸冤运动得到了上海《申报》的跟踪式报道,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红顶商人为之慷慨解囊,(注:此案引起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关注,杨妻詹彩凤第二次北上京控的资费就是胡出的。当然,这也缘于胡当时的西席吴与同和杨乃武曾同过学,吴的引荐与此关系甚重。这其实就是杨乃武有而未读过书、未上过学堂的小白菜不可能有的社会资本之一。) 同籍十八名京官更是为他“联名呈控逐款鸣冤”(注:浙籍十八名京官联合向都察院提出呈词请求将此案解到刑部重审后,都察院随即上奏,此奏折促使慈禧太后下决心将本案提交刑部重审,引号所引为都察院在奏折中对浙籍京官陈情上书的概括。本案最终能平反与都察院的此番上奏关系至密,而它又得归根于浙籍京官的联名呈词。)。社会舆论力量就这样整体倒向了杨乃武,同陷冤狱的小白菜则无人理会。一边是小白菜“零伸冤”及被冷落遗忘,一边是杨乃武持久热烈的伸冤运动及广受支持,此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对比情形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深远无比。它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此案各级判官,使他们难以想到并相信小白菜同样有冤、从而对刘锡彤刑逼而来的结论不予质疑,撇开本案而日夜熬审派生之案。刑部后来在结案的奏折中指出,是案“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语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折),此等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
本案原未查清,派生之案当然难以究明。即便钦命复审也变成了在关键案情之外东鳞西爪的消耗战,真相难寻,“信谳”难定。唯有到了刑部那里,承审官员在山穷水覆中回到此案的起点,审查刘锡彤定案的过程、依据,才发现“又一村”——原验草率,并通过重验发现真相让冤狱昭雪于天下。
二、阶级与个人
阶级,作为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是瞿同祖在研究分析我国古代法律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的经典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提出来的。瞿先生把阶级看作我国古代法律的两大特征之一,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主观的社会评价和阶级意识以及客观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各方面”。(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9页。瞿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法律的另一特征为家族主义,参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一章“家族”及第三章“阶级”、第四章“阶级(续)”。) 凭着这些主、客观条件,那些贵族与官吏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社会上、法律上的特权阶级。特权阶级所具的身份地位使得其在主观心理上对下层贫贱之民充满着傲慢与偏见。遇有断狱听讼,他们的这种心理不是被驱除,相反,为求迅速了结案子,此等心理反而被激活并愈加强烈。讼狱过程中,当他们通过刑讯使由此种心理产生的主观臆断“司法化”时——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这么干——冤案往往就诞生了。
杨乃武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此案由知县刘锡彤诬认尸毒、刑逼小白菜引发而来。始作俑者刘锡彤何以会“诬认”、“刑逼”呢?如上文分析,先入为主是刘锡彤产生诬认的关键。而“先入为主”的根源就在于刘锡彤对一介民妇小白菜的傲慢及偏见心理。草率相验、臆断定论及刑讯逼供等等都是以这种心理为基础的。
不但刘锡彤,整个官吏及社会上层阶级对小白菜都存有此种心理。这在他们的奏章、舆论中毫无隐瞒、随处可见。如给事中王书瑞在“请钦派大员,秉公查办以雪奇冤而成信谳”的上奏中将本案定性为“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连诬攀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一案”(注:参见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刑科给事中王书瑞折,转引自王策来编著,前引书,第27页。)。王这句臆断定性的言语在此后的上谕及其他官员的奏章中广为引用、流毒甚远。给事中边宝泉在“重案未惬众议,请提交刑部审办由”的奏折中认为平反此案“于吏治民生具有裨益。非徒为杨乃武一人昭雪也”(注:参见光绪元年十月十八日户科给事中边宝泉折,转引自王策来编著,前引书,第61页。),其言外之意一目了然:小白菜本是谋毒的淫妇,昭雪之事与她无干。而在杨乃武自己写的伸冤诉状里及浙籍十八名京官的呈词中,他们对小白菜更是极尽傲慢与偏见之能事,诬蔑之词跃然纸上。杨乃武在二次叩阍原呈中,先是一句“上年十月初九日,有葛毕氏毒死本夫葛品连身死一案”,继而诬告小白菜曾经赖婚、与他人有过奸情等等。(注:参见《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载《申报》1874年12月7日。学政胡瑞澜在复审此案时,查明小白菜不曾赖婚亦无与他人有奸情之事,杨乃武纯属诬告。参见光绪元年十月初三日胡瑞澜奏折。) 浙籍十八名京官在向都察院的呈词中说小白菜“迹近狭邪,丑声早著”。(注:参见《浙籍十八名京官向都察院的呈词》,转引自王策来编著,前引书,第71页。) 对此案采取跟踪式报道的《申报》舆论也不例外,其对小白菜的傲慢与偏见心理路人皆知。如1875年8月30日《申报》的一篇报道,标题就是“审余杭谋夫案出奏”。在《葛毕氏起解琐闻》的报道中更把小白菜说成是“平生滥与人交,据其自或谓所私者,可坐四五席云”的娼妇。(注:《葛毕氏起解琐闻》,《申报》1876年4月18日。)
由上可知,在此案的司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阶级——以官吏为主的阶级——对个人——一介民妇小白菜——的构造。这种构造的成因主要在于杨乃武是个读书的举人。大多是由中举而来的官吏阶级下意识地为了读书阶级——未来的官吏阶级——的身份、名誉而力主平反杨乃武,诚如浙籍京官夏同善在上奏中所述,“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注:转引自俞金生编:《杨乃武案探源》,中国天马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布莱克教授曾分析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组织在法律行为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孤立的个人是组织团体状告的最好靶子。(注:参见唐纳德·布莱克著,前引书,第43~44页。) 而在“断狱听讼”中,阶级的力量与组织的力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为把此案办成“信谳”的铁案,皇上应奏而先后下了十四道谕旨。官吏阶级所要求的“信谳”无非是要给杨乃武伸冤昭雪,而孤家寡人的小白菜就成了他们“同仇敌忾”的目标。不止杨乃武,小白菜同样有冤,并且纯属官吏阶级刑讯逼供而来。但在控制着话语权的阶级面前,失语,成了小白菜凝固的、唯一的表情。
三、小白菜:无法伸冤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九日,已经审理了三年有余的杨乃武案终于在北京海会寺这个原与本案毫无瓜葛的地方迎来了它的高潮与尾声:开棺重验的结果显示葛品连确属无毒因病而死。长期以来葛品连系小白菜谋毒致死的“信谳”“神话”被彻底打破击碎了。但三年多来灵肉饱受摧残的小白菜,还因“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实属不守妇道”(语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折)而被判杖八十。从刑部大牢回到余杭的小白菜因无亲无靠、生活无着而割断红尘削发为尼,二十二岁的她从此伴着青灯黄卷度过了五十三个春秋。
小白菜这般悲惨结局在古今冤案中可谓绝无仅有。一个简单得奇怪的问题,是明知自己被冤枉的小白菜为什么不鸣冤叫屈呢。不难推断,如果案发后小白菜跟杨乃武一样为伸冤奔走呼号、上下求索,那北京海会寺重验的惊世之举极有可能大大提前,这样不但她自己和杨乃武的沉冤能早一日昭雪,而且还能重重缩减本案冤狱悲情的范围及深度。(注:除本案的直接当事人杨乃武与小白菜外,其亲属、亲友及一些案外无辜之人也广受牵连,其中还有四人丧命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详见王策来编著,前引书,第214页以下。本案审理中未见贪赃枉法、官官相护的丑恶现象,因而那些后来被革职的大小官员,除刘锡彤等草菅人命的庸吏外,亦多半属于本案的悲剧人物。) 但检视个人的身世与地位,环顾其家庭及背景,我们不免恍然大悟,伸冤对小白菜来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小白菜自幼丧父,八岁时便跟随再嫁之母到余杭县城,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十一岁时其母就与邻居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而葛品连亦为早年丧父之人,成年后在县城一豆腐店当帮伙。同治十一年三月小白菜与葛品连结婚,夫妻俩租邻居杨乃武家的一间屋子入住,直到第二年六月因杨要求提高租金而搬出。“既嫁从夫”是中国女性的婚姻宿命。葛品连成为婚后小白菜生活中的唯一寄托与依靠。但葛品连——小白菜原是要托付终身的男人——突然在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暴病而去。“三从”是我国古代女子的纲常守则。不幸如小白菜者,从小无父可从,结婚两年不到就陡然无夫可从。本来“夫死从子”,但阿斯克勒庇俄斯还没有来得及赐予小白菜可从的儿子。(注: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生育之神。参见[德]奥托·泽曼:《希腊罗马神话》,周惠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3页。) 家,一夜之间离小白菜而去,留给她的是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小白菜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这样的孤家寡人一个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及法制体系下当然是被冤有份,伸冤无门。因为“传统之中国文化完全不承认‘个人’的存在,而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更没有‘个人’的立足之地”,(注: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更何况此等个人乃一介民妇。“女子无才便是德”,小白菜没教育无文化,举人杨乃武能在监狱里写叩阍辞呈,但她做不到,所有的冤屈都只能往肚里吞。同时,杨乃武还有妻子、胞姐等奔走于杭州及京城各衙门为其伸冤。可小白菜呢?丈夫死了。兄弟姐妹吧?一个也没有。母亲、婆婆早已把她看成是毒夫的娼妇,哪还能想到她有什么冤。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但生来只会在家相夫教子的小女子能有什么熟人?以前的房东杨乃武算一个,但被自己诬攀的他正跟官府一样在指控她是谋毒本夫的淫妇。
所以,在官府刑逼所出的冤狱面前,民妇小白菜根本没有话语权。名义上她是本案的当事人,可实际上她对本案的发展进路及未来结果没有丝毫的干预度和影响力,其情形几如被置之案外。名实分离莫过如此,冤狱命运莫不由此。
四、社会结构与冤案
美国纯粹社会学教授唐纳德·布莱克在运用其理论解释法律时,创造出当代美国法律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纯粹法社会学。1989年出版的Sociological Justice(《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此书的中文版序言里,布莱克说:“纯粹法社会学的核心是案件的几何排列,或者用本书的语言说是案件的社会结构。通过运用这一术语我指称的是法律案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谁与谁发生冲突;谁会作为第三方参与冲突;如律师、证人和法官。这些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大?谁的社会地位高,谁的社会地位低?案件的命运取决于它的几何排列。”(注:[美]唐纳德·布莱克著,前引书,中文版序言。) 布莱克认为,法律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即法理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前者的焦点在于法律条文,目标在于作出决定,它是实用的,而后者焦点在于社会结构,目标在于提供解释,它是解释性的。不同于传统的认为法律根本就是一种规则,其生命在于逻辑,因而相同的案件就会有相同的法律结果,社会学模式认为法律是可变的,它随各方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注:参见[美]唐纳德·布莱克著,前引书之“引论”部分。) 布莱克的社会结构理论及社会学模式分析方法对于我国古代(甚而近现代)的法律、司法具有不容置疑的解释力。因为自古以来非法律因素对案件结果的影响甚至重于法律规则本身是我国的一大法律传统,正所谓“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注:[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研究此案的由来及其司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两组平行的社会结构。如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此案发生不久就被人为地分解成两个案件,即本案——“小白菜毒夫致死”案和派生之案——小白菜诬攀杨乃武因奸同谋案。这两个案件的社会结构不可同日而语。在“小白菜毒夫致死”案中,一个是身兼数职——警察、法医、检察官、法官——的知县,他有的是权力而且能不受监督地滥用权力;一个是地位卑微、已成为孤家寡人的民妇。而且“这里不存在对相互争议的主张由享有权威的第三者来下判断的构造”。(注:[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对于刘锡彤验尸时的草率、妄为,小白菜难以置喙,一个没受过教育、从未与官府有什么来往的民妇怎么知道银针要用皂角水擦洗三次才能试毒呢?对刘锡彤的刑讯逼供,小白菜惟能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来个枉供以求解脱,尽管她心里最清楚丈夫身死与她毫无干系。所以,这个案子凭着判官刘锡彤诬认尸毒、刑逼小白菜因小白菜无法伸冤而迅速了结。但后一案件就复杂得多了。堂堂举人杨乃武非一次大刑能成就“信谳”定案。他懂得伸冤,而且有众多亲友,更重要的是有由其举人身份赢得的一个官吏阶级在为他鸣冤奔走的大好局面,这使得该派生之案的社会结构处于动态平衡中,草率定案不可能。但很快查明真相结案,同样不可能。因为被人为分离开来的本案与派生之案原本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试想:没有所谓的小白菜谋毒,何来的小白菜诬攀呢?正是在这种相互钳制的构造中,整个案件的社会结构极不均衡,冤狱就在这种畸形的结构中获得了它生长、蔓延的空间。
那么导致此案中途分解,而且是分解成两个社会结构差异如此悬殊的案件的原因又在哪里呢?窃以为,答案非它,正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是个身份社会,一切都决定于人的身份。而占社会人口一半的女性其社会地位之低几如没有身份,对此历朝法律都是明文规范。(注: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妻的地位”一节中,对我国古代妇女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有详尽的论述,参见瞿著,前引书,第112页以下。) “三从四德”的纲常名教变成束缚中国古代女性的“无我教”。(注:“无我教”是辜鸿铭在《中国妇女》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断言:“一个妇女的荣誉——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并忠实于她的丈夫,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她丈夫活着。事实上,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的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参见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案发前小白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大妇女的典型:贫贱生活、卑微地位、“不学无术”。生活中一旦发生意外,她们的命运就完全交给了无形的老天爷或有形的“包青天”,所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她们来说是真正的“神话”“诳语”。丈夫突然暴病身死对小白菜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她陷进了一无所有、无亲无靠的漩涡,对一切都只能逆来顺受、无力抵挡。在当时的社会秩序及法律制度下,女性是位卑的弱者,是听凭官吏、贵族这个特权阶级主宰、摆布的群体。以至于,费正清把社会特权阶级所强加于妇女的这种低下地位,视作中国这个身份社会里的等级制的表现方式之一。(注: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个非等级制社会,但从男尊女卑这个角度来观察,妇女又事实上构成了社会的另例等级,一个低等的群体。有权利就必有救济,这是近代西方法律秩序的“宗教”。但在东方中国古代社会,广大妇女既无权利又无救济,完全成了一种非人格化的主体。源自于专制君主意志的法律及适用法律的行政官吏都是为社会人伦纪纲秩序服务的。而在人伦纪纲秩序下没有独立身份的妇女,不享有任何话语权。她们生来具有的那点原始理性——非通过后天教育而获得的理性——也早已被人伦纪纲秩序摧毁。在讼狱中,没有理性的她们被从头到脚非人格化了,成了纯粹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就像此案中的小白菜。
以社会整体结构的宏观视角观察,我国古代以伦常纪纲为本位的社会秩序制度,有着内在的非正义性格——对妇女群体的非正义。在这样的非正义社会结构里,讼狱变冤狱对妇女来说真是司空见惯。但社会终究是相互勾连在一起的整体,尊贵的男人不可能摆脱卑微的女人而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所以,对妇女制造冤屈,一旦其未能自然熄灭于萌芽状态,就难免要牵连上男人阶级中的一个或多个,从而使冤狱在社会群体中延伸开来,其蔓延的面积难以估量,后果超出想象,就像此案。在社会的局部非正义结构难以自主地调整的情况下,如此讼狱变冤狱,由女性而男性,由局部而整体的悲剧发展路径是非正义社会结构的必然归宿。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提出,正义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注: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概言之,杨乃武案是中国古代社会非正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此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古代冤案,尤其是有女性涉及其中的冤案之孳生过程中的作用实值得我们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下面谨以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贡斯当一段有关于此的思想结束此文:
“在我们庞大的社会里,在如此复杂的关系中间,一切事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所谓局部的非正义,是社会灾难的无尽源头。权力并不能把它们约束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个别野蛮的法律,就能决定整个立法的性质。个别非法的措施,就能使任何公正的法律失去不受侵犯的保证。……可以想像,对未被证实有罪的人采取一次惩治措施,所有的自由都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注:[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