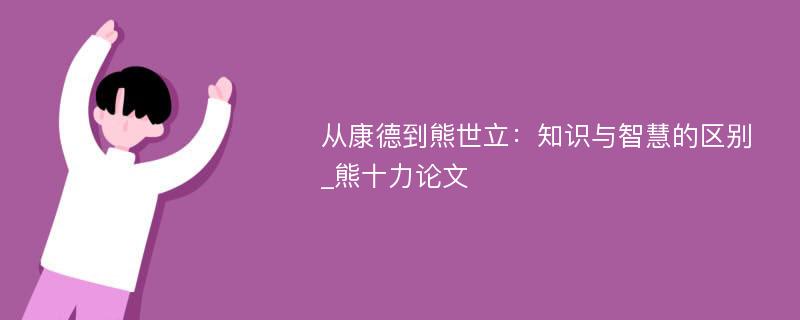
从康德到熊十力:“知智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到熊十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2-0113-06
一、康德与西方“转识成智”传统的断裂
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也就开始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冲动。人类最早的哲学活动是从对人自身的“惊讶”开始的:人类对它不同于周边事物,包括其他动物的区别所在感到惊讶和好奇,视人为具有“道德理性”的动物。但是,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和可能的?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标志着希腊哲学的正式开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希腊人称哲学为“爱智之学”,而苏格拉底更明确宣称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你自己”。所谓“认识你自己”,就是发现人的品格与德性,并对此作出说明。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人的美德与具有美德是一回事情。所以他提出这样的命题:“德性即知识。”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德性的培养与获得必须通过知识。为什么德性的培养有赖于知识呢?苏格拉底是这样论证的: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是美好的;凡认识这些的人决不会愿意去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它们的人也决不可能将它们付诸实行。因此人可以通过学习与认识获得美德。循着苏格拉底的思路,柏拉图将“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真正的知识或最高的知识是关于“善”的知识。但与苏格拉底不同,他除了承认“善”是最高的知识之外,还肯定人类有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有助于达到关于最高善的知识。在柏拉图看来,德性之外最可靠的知识是数学和几何,所以他从研究数学和几何开始,试图建立起他的“理念论”。对他来说,理念是划分为等级的:人可以从对最低的理念的认识开始,层层递进,最后达到最高一级的理念——关于善的理念的认识。从以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德性即知识”的论述来看,他们的思想理论包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前提预设:1.肯定人是有“理性”的,而理性其实包括两种:思辨理性与道德理性,前者(思辨理性)又可以说是知识理性。2.知识理性有助于达到道德理性。或者说,人对道德理性的掌握必须通过知识理性。对这两个前提条件的考察,构成康德“三大批判”要解决的问题的重点。
其实,早在康德以前,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就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点。近代以来,它表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与通常人们认为经验论主要关心外部世界的知识问题不同,经验论最早的哲学冲动并非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而是人生论或价值论的。所以,几乎所有早期经验论者对知识问题的讨论,都由对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所引发,只不过经过中世纪的神学洗礼,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更多地与上帝存在、自由意志与灵魂不灭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价值与意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对于上帝、自由与灵魂不灭问题的讨论。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这样认为:“人只要观察别人的语言和行动,就有理由相信他人亦有心灵和能思的实体;而且他既然知道自己人底心理,则有思索能力的他便不能不知道还有一个上帝。”[1](P549)洛克写作《人类理解论》,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道德与宗教的问题。休谟写作《人性论》的冲动也是由对“人性”的好奇引起的。通过对“人性”的考察,他得出结论:“我们的神的观念也有同样的缺点,不过这对宗教和道德学都不能有任何影响,宇宙的秩序证明有一个全能的心灵;那就是说,这个心灵的意志是恒常伴随着每个生物和存在物的服从的。不再需要有其他东西去对宗教的全部信条给予一个基础,而且我们也无须以最高存在者的力量和功能形成一个明晰的观念。”[2](P85)同样,唯理论者笛卡尔也想“以几何学方式论证上帝的存在”。他说:“一个属性包含于一种事物的本性中或概念中,这就是说,这个属性属于这一事物,人们可以确信它是在这一事物里面的。但是,必然的存在包括在上帝的本性或概念中,因此,我们就可以说必然的存在在上帝中,即上帝存在。”[3](P222-223)即使是怀疑论者的帕斯卡尔,也怀疑人的理性最终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也同样寄希望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而否认权威的力量。他说:“世上所呈现的事物既不表示完全排斥神明,也不表示神明之昭彰显著的存在,而是表示有一个隐蔽的上帝存在。万物都带有这种特性。”[4](P251)因此,他愿意采取“打赌”的方式来解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这种“打赌”,虽然是一种怀疑论,却毕竟未对于人能否通过知识与理性认识上帝完全放弃希望。以上经验论、唯物论甚至怀疑论者从探讨知识问题入手,寻求知识、人类理性与宗教、上帝问题之间的联系的方式,可称之为“转识成智”的方式。
只有到了康德,西方哲学这一悠长的由知识与理性入手寻求上帝或道德问题解决的思路才发生了彻底断裂。康德明确宣称,现象界归现象界,本体界归本体界;人的理性只能达到关于现实界的认识,而现象界背后的本体世界是人的理性所无法认识的。问题在于:康德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追溯康德心目中的“知识”究竟为何物说起。康德认为知识有两种:纯粹知识与经验的知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这样谈到“纯粹知识”与“经验的知识”之间的区别:“所谓先天的知识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乃指绝对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与此相反者为经验的知识,此仅后天的可能,即仅由经验而可能之知识。当先天的知识未杂有经验的事物在内,则名为纯粹的。”[5](P28)纯粹知识又可以称为先天知识,它脱离经验而存在,却是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康德看来,像时空、因果这样的范畴就属于纯粹的知识。康德还认为,这些纯粹知识可以通过思辨理论而获得,因此,《纯粹理性批判》就力图对时空、因果这样的范畴如何经由思辨理性而获得作出证明。问题在于:像上帝存在、灵魂不灭、自由意志这样的观念是否能通过思辨理性而达到呢?在康德看来,回答是否定的。《纯粹理性批判》通过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否定得出结论:“我今主张‘凡欲以任何纯然思辨的方法在神学中使用理性’之一切企图,皆完全无效,就其性质而言,亦实空无实际,且理论在自然研究中使用之原理,绝不引达任何神学。”[5](P453)尽管思辨理性无法证明上帝之存在,但也无法否定之。因此,康德试图引进“实践理性”来对上帝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这里的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指道德理性,它是人在遵循道德律命行事时的自由意志等义。他强调说:“我之所谓‘实践的’乃指由自由所可能之一切事物。故在‘行使吾人自由意志之条件而为经验的’之时,则理性对之只能有一统制的使用,且仅能用以产生‘其在经验的法则中之统一’。例如在处世条规中,理性之全部任务,惟有联结‘吾人之欲望所加于吾人之一切目的’在幸福之唯一目的中,及调整‘所有到达此唯一目的之种种方策’与此目的相合而已。故在此领域中,为欲到达感性所提呈于吾人之种种目的起见,理性只能提供自由行动之实用的法则;不能以吾人以纯粹的而完全先天所规定之法规也。此后一类型之法则,即纯粹的实践法则,其目的完全由理性先天所授予,且非以‘经验的条件所限制之形相’加于吾人,乃以绝对的形相命令吾人者,当为纯粹理性之产物。此种法则,即道德律;故惟道德律属于理性之实践的运用,而容许有一种法规。”[5](P547)这样,康德事实上是将人的理性划分为两种: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而这二者之间是分离的:理论理性只适用于对经验界或现象界,像上帝存在、灵魂不灭这样的领域属于超验界,它只有借助于实践理性来解决。
应该说,康德这一划分经验与超验的思路对此后整个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自此以后,人们普遍采取了康德式的将自然律与自由律二分的方式:经验世界或现象界遵循自然律,道德领域属于超验界或“物自体”的世界,遵循自由律。例如,文德尔班就认为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事实的世界与价值的世界;与这两个世界相适应,存在两种不同的知识:“理论”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这两种知识之间无法过渡。康德关于现象界与本体界二分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从此之后,西方哲学家普遍放弃了从本体论角度对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寻求,而将这一问题留待神学家来解决。
二、熊十力论“转识成智”
就在西方哲学界普遍放弃从知识入手寻求道德与价值问题之解决的时候,熊十力却对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重新讨论,并将“知智之辨”作为他哲学思考的中心话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是熊十力而非康德,成为古希腊“德性即知识”这一思想谱系的真正传人。当然,熊十力并非接着西方哲学传统,而是接着中国儒家哲学传统讲的。
在《明心篇》中,熊十力解释“智”与“知”的用法说:“智之一字,在先哲经籍中有泛称,有专称。专称则简称智,而其义与知识迥别。泛称则知识亦得名智。智与知识有别,儒家义旨如是,道家义旨如是,佛家义旨亦如是。但是,三家对于知识的看法则互有不同。其所以互不同者,实由于三家各有其所谓智在。智与知识有分,此一主张在中国古学中确是中心问题所在之处。每一宗派的哲学,其各方面的思想与理论都要通过这个中心问题而出发,仍须回到这个中心来。”[6](P230)那么,到底什么是“智”?熊十力说:所谓智是“性灵之发用”,他又解释:性指生命,性有“昭明之德,明者灵明也”。[6](P231)这说明智是作为道德主体性的人的一种功能,它类似于康德所说的“道德自由意志”。在《明心篇》中,熊十力从如下四方面分析智之含义:1.智“用晦而明,光而不耀,智之恒德也”。[6](P231)其意指智常凝敛于内,不向外驰散,因此它有深厚的涵养。这是对智的特性的一种描述。2.智“无知无不知者”。[6](P233)智一方面寂然无妄想,故说无知;另一方面又感物而动,明烛物则(事物之规律),故说无所不知,而且它还“穷理抵乎到普遍”。[6](P232)这里点出了智慧与知识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智是知识成立的前提与条件,它相当于知识的“范导性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3.智是人类的一种内部生活。他说:“动物进化至人类,始著见内部生活。其源则深远、充实、不可测;其内容则扩大、丰富、不可量。”[6](P233)这里指出有无内部生活是人与动物之根本区别点。这种内部生活,是就人的道德世界与精神世界说的。他解释这种内部生活说:“智主乎内部,则性海流通,一切意念乃至事业莫非天机油然之动。业习之非恶性者,将皆转而顺天;其恶性者,不得现起,久之自然消灭。如此,则习藏亦转化而合于性海,人道乃实现天德而益弘大矣。”[6](P233)可见,人类正是通过智的这种内部生活得以变化气质,而成就道德与精神价值。这里智既是道德生活本身,同时亦是道德生活的发动者和完成者。这是就智的道德功能方面说的。4.知识不即是智。这是从否定方面说明智与知识的区别。他一方面承认知识离不开智:知识之成就必有内在的“了别作用”以深入于外物,故智是知识何以可能的内因;另一方面,若无外物的引发,则亦无知识。这一说法颇类似于康德关于知识生成的两个条件:感觉经验与先验范畴。总之,从这四个方面的分析,熊十力认为智指人的精神与道德世界,但它具有能动性,而且可以成就知识。
熊十力对智的理解如上述,那么,什么是他心目中的“知”呢?在《明心篇》中,熊十力对知没有作明确的界定,但从他对“知”的意义理解来看,知既指道德知识同时又指自然知识。但无论自然知识也好,道德知识也好,它们都属于“外部的知识”。因此所谓“转识成智”就是将外部的自然知识或者道德知识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问题在于:这何以可能?这里,他引述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话来加以说明:习指习染,它可以说是一种很宽泛的经验;人生在世,各人的习染各不相同,甚至相距甚远。性指人的道德本心或德性;虽然由于环境的不同,由此带来人们的习不相同,但人之为人,却有共同的道德本心或德性。在他看来,孔子这话是儒家关于“转识成智”思想的最好说明。但熊十力认为,儒家虽然在理论上承认习可以转化为性,在现实中的习却未必都转化为性。因此,对于儒家来说,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习可以转化为性,而是要问:习如何可以转化为性?如果说前一问题问的是习转化为性的根据的话,那么,这后一问题问的就是习转化为性的条件与途径问题。熊十力将习区分为两种:善习与不善习。他说:“本、习二心之辨,主张转化旧染之恶习,创生新的善习,以弘大本心之善端。”[6](P164)在他看来,只有善习才可以转化为性,而不善习则无法转化为性。那么,习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有善习与不善习的区别呢?他提出人是有“独立体”的存在来解释这个问题。人作为独立体本来就有本心,这种本心是产生善习的原因;但人既为独立体,是被抛在世上的动物,其性常驻在“变化密移”中,未有暂时歇止之时,这种前后密移的过程还会有“余势潜流”产生,这种余势潜流相当于人的行为的惯性,它也就是习。他说:“夫人之生也,莫不有本心。生而成为独立体,亦莫不有习心。杂染之习(即不善于习),缘小己而起,善习依本心而生。”[6](P163)按说,人作为独立体既被抛在世上,就容易为习心支配和左右,其习将只会是“不善习”,但他认为,人的本习究竟是不可泯灭的,善习的发生亦时时不容于己。这样,人生事实上是善习与不善习相战的战场。而人生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确立,就在“人生要在保任本心之明几,而常创起新的善习,以转化旧的杂染恶习,乃得扩充本心之善端而日益弘大”。[6](P163)在他看来,这就是做人的要求与准则。
从这里看来,熊十力理解人之所以可以转识成智的条件是因为人有本心,而其途径则是创起新的善习,转化旧的恶习。而这种创新转旧,其实就是道德的自由意志行为。人作为独立体,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道德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熊十力称为“自力”。他说:“人生而含灵禀气,已成独立体,便能以自力造一切善行与不善行。”[6](P162)我们知道,康德也将自由意志视为人的道德行为何以可能的条件,但他不能解释它的来源问题,只好视之为“公设”。这里熊十力则认为道德的自由意志是人生而具有的,其作用不是如康德所说的那样执行“绝对律令”,而是要将人自身“变化气质”:将不善习去除,扩充善习。既然善习与不善习皆为知识,这种自由意志的存在,就为人的转识成智提供了可能。
对于熊十力来说,他承认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有待于转化为智慧,但他并不否认知识的作用,并且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知识除了有其独立的征服外部世界的作用之外,还有助于形成智慧。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转识成智”不仅不鄙视知识,毋宁说,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前一个问题:知识有其独立作用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近世之人莫不以为科学智夺天工,福被人类,不可谓其弱于德,更不可谓其涂奥,殊不知庄生在二千年前早以‘强于物’一语遥赞科学。自有科学以来,其方法则谨严、精详、周密、准确,与其辅助感官之工具皆与日俱进,强之至也;其成绩则积世、积人、积智之发见与开辟,累积雄厚,乃至大通宇宙、改造宇宙,强哉矫也。现化科学当犹未尽其强力,将来强之所至实未可量。”[6](P229)关于知识有助于智慧的问题,他是这样认为的:知识中本来就蕴含有智慧。从这种意义上说,智慧可以说是知识的“发用”与“上提”。例如,他谈到作为知识的“染习”说:“吾人幸有经验于事物之一切习染不曾消失,其成为习藏中种子常出现于意识界而为记忆。人心本息息与天地万物流通,息息与未知的事物相接触,记忆作用则恒与天明之动合为一,时时唤起已往一切经验,协助而且策动天明,俾解决新接触之许多未知的事物有所依倨,而后对于新事物之了解减少无数困难。习染之助于智,此乃事实昭然,不容否认也也。”[6](P239)科学知识如此,道德知识更是如此。他谈到古人如何重视道德的知识在成就人的道德时的作用说:“《易》之《观卦》对于人生之观察深微至极。三爻之辞曰:‘观我生进退。’《象》曰:‘未失道也’云云。此言返观自我之内部生活,以考验为进为退,而自警也。……五爻之辞曰:‘观我生’,《象》曰:‘观民者’云云。按此中义旨深远。民字古训:民,冥也,冥然无知也。观民,犹观冥也。观我生而必观冥者何也?我之有生,非如幻化,更非从空无中忽然有生,应说我生自有真情。然而人自有生以来,则为形气的躯体所锢蔽,乃冥然莫能自识其真性。故观我生者,必观察我之奈何无端而陷入冥间,破其冥暗,则可自识真性矣。”[6](P228)这其实是说,人要能转识成智,是以道德知识为前提条件的。正因为如此,熊十力认为,传统的儒家其实并不轻视经验知识,毋宁说,倒十分“尊知”。他说:“孔子不独不反知,而且尊知。《易大传》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其重理智、爱知识之精神,可谓强烈矣。孔子尊知,故倡导格物之学。”[6](P238)即便如此,在熊十力看来,儒家之所以重视格物之学以及尊知,归根结底不是别的,乃由于它可以就成道德。或者说,知识是作为达成智慧之工具与途径来发挥作用的。
三、熊十力论“转智成识”——兼论“由智化境”问题的提出
其实,熊十力除了论述“转识成智”之外,还强调要“转智成识”。所谓“转智成识”,是指将智慧转化为知识,它与“转识成智”刚好是一相反的过程。问题在:这何以可能?对于熊十力来说,这回答是肯定的。为什么智慧要转化为知识呢?首先,这是知识的内在要求。他说:“智本无昏扰相,然必用在万物万事上发起一切知识,方见其有神龙变化、春雷震动之妙。”[6](P239)又说:“人生而有良知,良知必发用于事物,而开展为知识,此无可遏绝也。”[6](P245)其次,知识须有智慧作主,方才可以为善而不为恶。他谈到律师富有法律知识,而讼者无理,律师可以其财而为之辩护,以及医师富有医药知识,而受坏人之贿可用其医药知识干坏事说:“知识与智分离,此人类中所以从善者少而流于恶者多也。”[6](P247)所以,“孔子之学以知识与智合一为常理,其要在保任良知作得主,知识自不离于智耳”。[6](P249)再次,知识须有智慧寓于其中,方才为真知识。他谈到知识的形成过程时说:“知识固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反应,然知识之成,毕竟有内在的主动力深入乎物、了别乎物,才成知识。此主动力即吾人本心天然之明,所谓智是也。”[6](P240)总之,在熊十力看来,智慧转化为知识的问题,其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知识转化为智慧。
可以看到,无论是谈论“转识成智”也好,“转智成识”也好,熊十力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有一前提条件的,这就是体用不分、即体即用的本体论。在《明心篇》中,他将这种本体论概括为如下三点:1.宇宙实体具复杂性而非单纯性。他说:“实体的性质非单纯也。哲学家或以为实体唯是单纯的精神性,或以为实体唯是单纯的物质性,皆逞臆成说,与实体不相应也。”2.体用不二。他解释说:“体者,实体之简称。用者,功用之简称。实体变动成为功用,而实体即是功用的自体,不可求实体于功用之外。譬于大海水变动成为众沤,而大海水即是众沤的自身,不可求大海水于众沤之外。故说体用不二。”3.心物不可分割。他说:“心、物皆为功用的两方面,非具体故,不可分割。”[6](P161)正是从这种体用不分、即体即用的思考路径出发,熊十力破除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的对立,也破除了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对立。
对于这种思考路径,熊十力有相当的自觉。在《明心篇》中,他将以往哲学家们的本体观归结为三种:1.“计执实体是超脱乎法象之上而独在”。这包括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佛教的真如观,乃至唯心论哲学的绝对精神等等。2.“计执实体是潜隐于法象之背后”。[6](P289)这当中典型的有佛教的唯识宗,其在哲学上属于多元论。3.“计执实体是空洞寂寥。包含宇宙万象”。这是指老子的本体论,也包括某些宋儒,如张载的思想。概而言之,熊十力认为,以上所有这些本体观,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脱离宇宙万有而去凭空构造一种宇宙实体。他说:“古代哲学之本体论,大概罕能拔出于三见窠臼之外,尤以第一见为大多数哲人所最易游履之通途。古代大学派之本体论,是其人生意义之所寄托。如道家建立虚无为本体,则其人生意义在返无,其主张去知去欲,不独个人之修养如是,凡所以理群立教之道亦无不知是者。佛家以涅槃寂灭为主体,则其人生意义在归寂,厌离五蕴,毁灭生命。古代哲人在本体论上自造迷雾,心物之本相不可得而明,人之用其心者亦无有正向。”[6](P291)这里,熊十力正确地看到了本体论与人生观的相依关系,但他的矛头所向与其说是他所说的中国传统的道家与佛学本体论思想,不如说是西方以二分法思维方式为导向的宇宙观与本体论思想更为恰当。长久以来,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一直是以二分法为基本取向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统一的宇宙过程被分割为现象背后的本体,故西方哲学所谓的“本体论”研究与其说是对“宇宙本体”的研究,不如说是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体”的研究。而经过康德哲学的摧毁廓清,这种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体”最终被证明是人类理性所无法达到的。与此相关联,既然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要寄托于本体,而本体又无法被人类的理性所把握,故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的求解只好交付给上帝。这就是当康德发现“转识成智”问题无法解决时,最后所得出的结论。
然而,熊十力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本体论思想,其哲学意义与其说是为西方长久以来所纠缠的“转识成智”问题提供了一条思路与途径,不如说是扩大了哲学形而上学思考的地盘。如前所说,人类形而上学的冲动与追问本是从对人何以会具有“道德理性”这一问题开始的,因此追问形而上学就是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这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与人生哲学同义。然而,长久以来,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定势下,宇宙、人生的统一过程被分割为现象与本体,而所谓形而上学又变为本体论的同义词。因此对形而上学的追问只成为对本体论的追问。具体到人生哲学上,哲学家们追问的只是知识能否达到人生的智慧与德性,也即“转识成智”是否可能的问题。其实,从“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本体论思路来看,既然知识与价值不可分离,那么,除了“转识成智”之外,“转智成识”同样也应是人生哲学,包括形而上学追问的主题。熊十力对以二分法为代表的西方本体论思想的颠覆,其真正意义就在这里。
但是,就哲学形而上学的追问而言,熊十力关于“转智成识”的思想却仍然有待补充和拓展。在考察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时,熊十力除了看到知识可以转化为智慧之外,还提出智慧须转化为知识,这是他的慧识所在。但是,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毕竟不能涵盖形而上学问题的全部。应该说,形而上学既然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问,那么,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就永远处于形而上学的中心。但是,哲学形而上学把握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其与宗教以及艺术之不同,就在于其对人类理性的强调与重视。这种人类理性,既包括理论理性,同时也包括实践理性或者说道德理性。哲学形而上学既然是以理性方式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把握,那么,对这两种理性如何去把握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考察与反思,也就是形而上学。这样,假如我们将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目标以“智慧”一语表示之,可以认为,哲学形而上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其实有两个:“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这里“转识成智”就是知识如何转化为智慧的问题,它强调的是用人类的理论理性,包括知识,如何去达到对人生意义与价值世界的觉解;而“由智化境”则指将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觉解转化为个人的实践,它需要的是人的实践理性。
可以看到,经过这样的转换,熊十力提出的“转智成识”可以是“由智化境”的一个内容,但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部。因为“由智化境”中的“境”指称的是人的整个实践行为,归根到底,“由智化境”是指在人的所有实践活动中如何体现人追求的价值理想问题。而“转智成识”中的识(知识)只是人类诸多实践行为中之一种,并不代表人类实践行为之全部。但无论如何,熊十力通过对“转智成识”的论证,说明了知识当中包含有价值,知识当中须体现人生的理想与价值,这是他的贡献所在。他的“转智成识”说以个案考察的形式,说明了哲学形而上学中的重要环节——“由智化境”说的成立与可能。
然而,应该看到,无论是对“转识成智”的考察,还是对“转智成识”的考察,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熊十力的哲学形而上学并没有完全展开。熊十力对于“转识成智”与“转智成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宇宙本体论。但对于他来说,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宇宙本体论只是一个先验的设定。我们要问:何以宇宙本体是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呢?对此,熊十力没有进一步诠释与回答。这样,他最终也就无法回答西方以二分法为前提的怀疑论者的挑战。熊十力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以独断论的味道,其原因盖出于此。其实,宇宙本体中现象与本体的最后统一依赖于对意义与价值的诠释。但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熊十力的视野,它是当今哲学诠释学面对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2-01-01
标签:熊十力论文; 康德论文; 本体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人生价值论文; 纯粹理性批判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自由意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