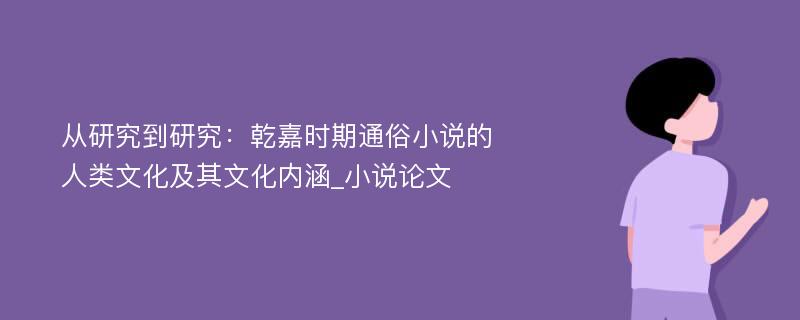
从书坊到书斋:乾嘉时期通俗小说的人文化及其文化内涵II,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文化论文,书斋论文,通俗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108-05
一、从书坊到书斋
从物化形态来说,常把唐代的俗讲变文作为通俗小说的源头。宋元时代的说唱艺术促成了白话通俗小说的诞生。因此,通俗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俱有了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商业色彩、市民色彩,就与书坊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存最早的话本、讲史平话皆为瓦子所刻。明代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兴盛,书坊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冯梦龙受书坊主之托编辑了“三言”,凌蒙初在“二拍”的序言中表示书坊主的请求无法推脱,只好编改当代故事。(注:《二刻拍案惊奇序》,《二刻拍案惊奇》,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像余象斗、余邵鱼为代表的余氏家族,熊大木为代表的熊氏家族,都经营书坊,也都编写了许多通俗故事书。明代后期话本小说、历史演义、神怪小说等的成批刊行,书坊间的仿效和竞争当是重要的因素。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繁盛,而这些小说又多文字粗糙,相互间的抄袭,改头换面的重刻(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魏忠贤轶事》写魏忠贤事;《新史奇观》、《新世弘勋》、《顺治皇过江传》与《铁冠图》、《铁冠图分龙会》等皆写李自成事),无疑为书坊主操纵的结果。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应作如是观,如烟水散人在《赛花铃》的题辞中述说了书坊主请他作美人书的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许多通俗小说是书坊制作出来的。也许可以举出独立于书坊运作系统之外的例子。如蒲安迪就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称为典型的文人小说,(注: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把《醒世姻缘传》也称为“文人小说”。(注:见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第3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实际上它们是由传统的民间说唱素材演化而来,不是文人的独创。作品中的不少意蕴其实都是素材本身所固有的。
高素质文人的参与,如李贽、汪道昆、金圣叹、毛宗岗等人在通俗小说完善化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真正的文人小说必须由书坊回到书斋才有可能诞生。因为文人小说应是个人的创作,或称作密室创作。明末清初这一转变已经开始,如《西游记》、《水浒后传》和李渔的某些白话短篇小说,都有了较为鲜明的文人品格,但直到乾嘉时期才形成大的趋势。乾嘉时期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如《儒林外史》用了十多年时间(乾隆四至十四年)才完成,《红楼梦》据作者说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瑶华传》在完成后又反复修改了四年(嘉庆四至八年),另外如《绿野仙踪》、(乾隆十八至二十七年)《歧路灯》(乾隆十三至四十三年)、《野叟曝言》等用了作者十年、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用如此长的时间显然不是为了赢利,不是受书坊主之托而写作。实际上,许多小说创作完成后并未立即付印,而是藏于家中,或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亲朋间,如《儒林外史》于乾隆十四年前后定稿,至嘉庆八年才有卧闲草堂本问世,《红楼梦》乾隆十九年前后完成,直至乾隆五十六年才有程甲刻本问世,《歧路灯》乾隆四十二年定稿,至清末民初才有印本,《希夷梦》完成于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十四年才有刊刻本,而《野叟曝言》的作者甚至不愿将此书付梓。
不急于刊刻行世,不是由于不够重视,恰恰是由于作者将小说创作当作个人的事业,当作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著述。如《雪月梅传》的作者镜湖逸叟表示要以此书而“立言不朽”:“惟念立言居不朽之一……予虽不克如名贤著述,亦乌能尸居澄观,噤不发一语乎?”(注:镜湖逸叟《雪月梅传自序》,《雪月梅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荔云为《西湖小史》写序说:“仆与蓉江厚交十余载,知其词赋文章终非沦落者,今有《西湖小史》一书,已足以藏之名山,传之来世矣。”(注:李荔云《西湖小史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3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虽然以前也有人将通俗小说和史传相比,但有的出于愤激之言,有的仅仅抱着欣赏的态度,而且毕竟呼应者了了。相比之下,乾隆时期的文人小说家真正意识到了通俗小说独立存在的价值。如果说书坊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那么可以说是从书坊到书斋的转变促进了文人小说的产生和繁荣,促进了近代小说意识的产生。无论如何,小说创作应为“创作”而不是“制作”,是个性化的事业,而个性化只有在书斋中才可能实现。当然,从书坊走向书斋只是近代小说产生的第一步,因为只有小说再一次从书斋步入书坊时,近代意义的小说才可能真正诞生,但这一步却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二、从外到内
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应是心灵的创作,但初期的通俗小说,由于书坊的介入,更多的是关注外在的社会现实:历史的循环,王侯将相的荣衰,英雄的传奇经历,才子佳人的艳遇,危机四伏的商业冒险,小市民的悲欢离合等等。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作者把小说当作教化的工具(所谓醒世、警世、喻世、醉醒石、清夜钟等),最终流于外在化、现象化。清初的话本小说作家如李渔、圣水艾衲居士把话本小说转化为个人抒写媒介,显示了通俗小说由外向内的转化趋向。
乾嘉时期的通俗小说文人化、个性化的转变是非常缓慢而稳重的;它们相对于同期仍很流行的通俗讲史小说来说,显得结构单纯、意义明了,解读它们似乎不需要高深的哲学素养,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些文人小说家并不想把小说写成隐奥的形象化哲学讲义,他们渴求的仅仅是个人抒写;个人的怀抱、个人的事业功名梦、个人的才华。如:夏敬渠“足迹遍天下,抱负奇异,郁郁不得志,乃发之于书”,(注:西岷山樵《野叟曝言》序,《野叟曝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即为《野叟曝言》。《绿野仙踪》是“呕吐生活”、 “笔代三挝”,作“祢衡之骂”。(注:李百川《绿野仙踪》自序,传抄本。)乾嘉时期文人小说关注的焦点也因此有了明显的变化,对与个人紧密相关的问题的关切掩住了对社会问题批判的热情。对士人来说,科举功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通俗小说从开始即关注市民问题,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写作后,科举在通俗小说中得以反映,如冯梦龙编写的“三言”中即有《老门生三世报恩》、《赵伯升茶肆遇仁宗》、《钝秀才一朝交泰》、《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篇,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清夜钟》第五回和第十三回,《鸳鸯针》第二卷等。但这些小说或充满功名从天而降的侥幸,或着眼于阴德报应,或侧重于道德批判。乾嘉时期的通俗小说才集中地对科举制度本身进行反映批判。这一方面是基于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等对八股考试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清代的士子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实。有清一代,士人入仕之途异常狭窄,三年一乡试,五年一会试,士人的青春年华于等待中逝去。即使中式也并非即能入仕,国家官职位数有限,许多职位又为满人世袭,另外又有各种捐纳、恩荫之例,这就必然造成雍滞之弊;(注:刘兆瑸《清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对汉族士人来说,还有一重无法消除的民族樊篱。在这样的形势下,比较清醒的士人站在科场之外,对之进行较为深入的反省批判。其中当然也有对科举功名的热念,如《跻云楼》中柳毅为科举功名而跋涉;但更多的是失望以至绝望,如《桃花扇》中侯、李二人不求功名,只愿安居乐业,《镜花缘》中唐敖对科举入仕心灰意冷,林之洋更视科举为畏途,《梅兰佳话》中的梅生在状元及第后也马上上表辞官,等等;也有对科举制度的更为深刻的否定与批判,如《儒林外史》揭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心灵的腐蚀,对人格的玷污,《红楼梦》把否定科举功名作为宝黛知心的关键因素,等。
但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士人否定了科举功名,也就只好将胸中抱负化为纸上事业。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虚构了形形色色的事业成功的主人公形象。与以前的通俗小说相比,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家不仅仅渴望功名富贵、佳人美酒,他们最迫切渴望的还是才华的发挥,事业的成功,个人价值的实现,《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学道成仙后,凭法力斩妖除魔,劝人向善,又充当总兵府幕僚,出谋划策,平定判乱,摄取府库赃银,赈济灾民,救护朱文炜,帮助他建立不朽的功业,助林润得中进士,终于了结严奸一案;《希夷梦》的作者虚构了浮石岛国,让韩速、仲卿于岛国治河理砂,除奸平叛,安邦安国,使浮石大治,“文德端淳,武备整暇”;《雪月梅传》中的岑秀历经磨难,终于成为文武全才、智勇兼备的抗倭英雄。……这些小说主人公无疑为作者的化身,作品中的辉煌事业是他们的白日梦。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固然与清前期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也不应忽视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乾嘉考据学以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为已任,原始儒家的济世理想再一次被张扬。不少学者反复表示,他们从事考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世,如汪中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注:汪中《与朱武曹书》,《述学》卷六,道光光绪间伍氏刊本。)戴震说:“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注:戴震《戴东原集》卷九,第12页,民国年间上海涵芬楼影印经韵楼本。)卢文绍说:“盖圣贤当其不遇时,则赡一身而犹不足,然其具固在,我实足以拯一世而有余。”(注:卢文绍《与陈立三书》,《抱经堂文集》,乾隆乙卯年刊。)……值得注意的是,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考据学者一样,我为科举不第,怀才不遇者,如吴璿、李百川、丁秉仁、张南庄、汪寄、黄瀚、黄耐庵、陈天池、夏敬渠……相同的境遇,相同的抱负,使学者和小说家获得了强烈的共鸣。
文人小说中女子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自小说诞生以来,女子就一直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在文人创作的小说中,女子或为文人表现自己风流的媒介,或为文人怀才不遇的寄托。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开始由才美型转为胆识型,但她们的胆识仍多表现在与破坏阻挠她们的爱情的坏人的斗争中。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中仍有对不幸女子的同情,但更多的是对她们文才武功的赞美,如螭娘和虓儿帮助柳毅审明冤狱,斩捕妖孽,诛灭叛逆,屡建奇功(《跻云楼》)。《镜花缘》设置了一个男女位置颠倒的女儿国,又让才女参加科举考试,对女子倾注如许多的关注,难怪有的论者把它称为张扬女权之作。《儒林外史》中的沈琼枝不满于小妾的卑微地位、寄生生活,靠自己的能力谋生,走出了解放的关键性一步。对女子的同情、理解和赞美,固然是明代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沿续发展,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小说作者在女子身上寄托了自己无法施展的抱负,发觉了士人走出书斋,改革社会,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女子走出闺阁,步入社会的相似之处,同样迫切,也同样艰难。
比起以前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更突出了男女的平等,在男女才貌相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相知的因素,如《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已有近代爱情影子,《儒林外中》中庄征君、杜少卿两对夫妇相亲相爱的婚姻生活,一改以前的虚幻的浪漫,显得朴素而真实。爱情婚姻是人生的一大主题,由爱情婚姻而诞生的家庭是艰难跋涉后的憩园,更是士人治国平天下理想破灭后最后的避风港湾,这也许是文人小说对婚姻如此关注的原因,是《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对爱情倾注那么大心血的原因。
当然,这一时期的文人小说也注意到了其他社会问题,如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官场腐败的诅咒,对道德堕落的警示等等,但这一些比起与文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来,远不重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作为背景来使用的。
科举、事业、才华等问题也为普通大众所注意,但无疑在他们关注的焦点之外。文人小说家的创作动机即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是大众读物,有的小说家甚至在序跋中作了明确说明,陶家鹤为《绿野仙踪》写跋,就指出“此书与略识几字并半明半昧人无缘,不但起伏隐显穿插关扭,以及结构照应,彼读之等于嚼蜡;即内中事迹,亦未必看得透也”。(注:李百川《绿野仙踪》自序,传抄本。)
三、从激情到感伤
通俗小说本是市民文学。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既表露了市民大众对历代帝王秘史、英雄征战的好奇,也表现了编著者评价历史、供现实借鉴的雄心。早期的话本小说把生活本身作为欣赏对象,表达了市民对生活的关注和热情,也反映了编写者的乐观信念。
然而中国文学有感伤的传统,也有以感伤为美的审美习惯。通俗小说兴起后,正统诗文中的感伤也洇入小说中,特别是在文人参与编写修订后。如《三国演义》卷首对历史虚无的慨叹,有浓重的历史幻灭感,自不待言;小说中魏的胜利,蜀的灭亡,也意味着正统道德的失败,有的论者就认为体现了道德悲剧意识。(注:刘裕绍《明代小说史》,第59-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但以前的通俗小说中感伤情绪的流露是偶见的,乾嘉时期文人小说中的感伤情绪、幻灭意识则较为普遍,如考虑到康乾时代是清王朝最为繁荣的时代,这一现象更值得注意。
《希夷梦》中韩仲二人一心反宋复国,梦入浮岛,后知宋又为元所灭,顿看破历史循环的空幻,抛弃尘世修道成仙;《锋剑春秋》中齐国被灭,诸神离去,孙膑痛哭:“为臣非不欲尽忠报国,奈天命已定,臣亦不能逆天行道也。”《瑶华传》中瑶华知明朝气数已尽,感叹“天命使然,难以回逭”,流露出时势不可逆转,人力无可奈何的感伤,这是一种深沉的历史幻灭感。《红楼梦》的作者虚构了人间天堂大观园,汇萃了凝天地精化,成为人间美好象征的女子,演出了超尘绝俗的爱情故事,但大观园不久即随着贾府的没落而败落,大观园中的女子或死或散,作者借石头的历练将富贵荣华归为一梦,而一僧一道的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更加强了人生虚幻、万缘皆虚的感觉;《儒林外史》,在小说临近结尾处,感伤色彩渐趋浓厚,“三山门贤人饯别”,虞育德对杜少卿说的话平淡的语调中蕴着浓浓的悲凉,最后作者以一曲《沁园春》结束全书,“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这是作者儒家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深沉无奈的叹息。在更多的情况下,感伤是一种余韵,在小说主人公的人生归宿选择上透露出来。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更多地写到主人公最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优游卒岁,如《歧路灯》中谭绍闻在黄岩县令任上一年即借母病辞归。《梅兰佳话》中梅生状元及第后即上表辞官,敲棋赋诗于林下……。
用感伤主义的文学传统无法解释在号称盛世的乾嘉时期中如此普遍的文学现象。文人的穷愁不遇当是原因之一。文人小说的作者如李百川过着“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马牛”的生活;(注:李百川《绿野仙踪》自序,传抄本。)丁秉仁一生游幕各地以求温饱;(注:参考张俊《清代小说史》第26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张南庄“身后不名一文”;(注:海上餐霞客《何典跋》,《何典》,工商出版社1981年版。)汪寄死后不久,子贫为佣;(注:《南游两经蜉蝣墓并获〈希夷梦〉稿记》,《希夷梦》,辽沈书社1992年版。)曹雪芹晚年绳床瓦牖,食粥度日;吴敬梓家财散尽后穷困潦倒……他们把对个人身世的感伤与对乾嘉时期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的直感结合起来,转化为小说中的历史、人生的幻灭感。更多的文人小说中充满的是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伤感。如《九云记》中杨少游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经圣僧点化,才醒悟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春梦;《儒林外史》对儒林丑类的批判,对泰伯祠祭祀场面的不厌其烦的渲染,对汤镇台、萧云仙政绩的描写,都流露出作者对儒家理想主义的向往、憧憬和执着,而断垣残壁、斜阳、凄清的琴声,还有青灯古佛,在结尾处融成感伤的尾音。这些小说中前半部的用世激情和后半部特别是结尾处的幻灭感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就在这对比中可看出作者思考的深刻、探求的执着、选择的艰难,因此文人小说中的感伤中蕴含着无奈,是无奈的感伤。所以,这些感伤小说既是对士人命运、对儒家理想的哀挽,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委婉的批判。“我意先秋感摇落”,他们或许只是将个人的身世之感写入小说,而后人却能从中体味到盛世的末路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感伤小说是时代的挽歌。
这种挽歌情调只有文人小说才会具有,因为只有文人小说家才脱离了书坊的操纵,回到书斋,对社会人生进行冷静深入的思考。“小说这种散文艺术是密室工作的产物。”(注:参见中野美代子《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在密室里写小说,读者通过印刷媒介在密室里阅读它,当作者和读者一对一关系成立之时,即是近代小说形成之日。”(注:参见中野美代子《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这种创作和阅读的一对一关系在《金瓶梅》上已经初备,因此中野美代子把《金瓶梅》称为近代小说的先驱,但她否认《金瓶梅》是近代小说,进而否认中国有真正意义的近代小说。(注:参见中野美代子《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实际上,虽然由于印刷出版技术和资金的限制,乾嘉时期通俗小说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比不上近代,但毕竟文人在书斋中创作的小说已通过印刷或以手抄的形式,被人们在密室里阅读,里面的故事是不适于在喧闹的都市公开宣讲的,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个人的故事,倾诉的是个人的心声,表达的是富于个性色彩的感情。因此,如果把乾嘉时期的文人小说称作近代小说的开端,也不能说是夸大其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