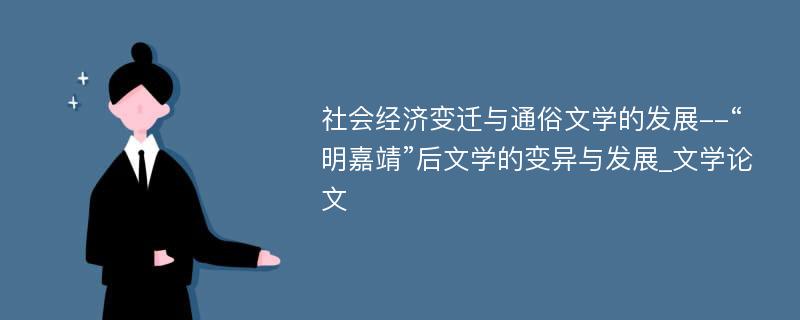
社会经济变迁与通俗文学的发展——明嘉靖后文学的变异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社会经济论文,通俗论文,明嘉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的广袤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它的结构的多元性,而不可能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绝对模式社会。[1]中国文学历史的悠久与内涵的丰富,决定了它在自身发展中与纵向的社会阶段需要和横向的多元社会反映构成的阶段性特色和相对关系我们不仅可以用魏晋时期动乱的中原社会照样孕育出文学的自觉时代那类史实来证明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逆向特征,也可以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起来的东部社会分娩出多彩的平民文学这类史实来证明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同向特征。文学是人的一种特殊行为结果。它虽然不像普遍的经济行为那样更具物质属性,仍不可缺乏其对物质的依赖。文学仅限于颇多“自我”意识的文化人小圈子中的时候,它似乎可以脱离物质的世界,自诩高雅,从而成为一种狭隘的精神寄托;当它突破文化人的小圈子,进入平民世界,它便与物质世界融为一体,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成了社会消费的对象。换句话说,当社会的经济发展使文学不再成为少数文人雅士独专的“雅趣”而转变成为大多数平民享用的“俗趣”之时,文学便在整个社会的大舞台上更为活跃地发展,显示出它更强的生命力。
一、明嘉靖后文化市场的构成
明嘉靖后文学的变异,首先就在于原本发源于民众社会的文学,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市场,文化人即使对它修饰加工也是为了把它放回到这个市场中去,成为民众消费的对象。通俗文学这个概念,对此时的文坛发展更具有概括意义。什么是通俗文学?就是平民欣赏的文学,就是由于合乎平民大众审美情趣而进入文化市场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
入明,文化市场的规模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规模化、城市及其市民阶层的扩大和文化消费观念的成熟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而发展起来的。
大运河南北贯通,虽是在元泰定二年(1325),[2]但全面疏浚并开始发挥巨大经济效益则是永乐年间,[3]直到清末。这期间虽然河道时浚时淤,时修时坏,但运河对中国东部经济和南北物质、文化交流的功绩不可抹杀。这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再加上以北京为枢纽的八条干线驿道商路,[4]构成了一个有利于商品流通交换的国内经济交通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级市场的繁荣[5]与正在走向海洋经济(世界性经济)的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开始碰撞,两者之间的推拉力促进了自十六世纪开始繁荣起来的中国海外贸易。虽然明清两代朝廷因种种原因不时采取禁海政策,但民间的海洋经济活动从未停止。通向东、西洋的航线始终有商帆往来,沿海从广州到泉州、宁波,从台湾到福建,从南直隶到北直隶(即从江苏到天津)的航路不断得到拓展。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交通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城市和商埠集镇。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十分久远,但明代旧城市的扩展与新城镇的产生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工商经济是扩城或建城的主要原因,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工商的城镇,这些城镇在历史的进程中又因工商业的繁荣而不断地发展;其二,城市中工商市民的比率增大。
据考查,原来作为都市、府、州、县署所在地的大中城市和商埠,在明初至中叶,因其工商业功能而大有发展的有三十余座。明中叶始,又有二十余座城市发展起来。[6]发展较快的新兴城市,大部分位于华东及沿海地区,立于大运河畔和交通干线枢纽之地。明清之际由于战乱,不少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受到破坏,有的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但由于当时经济复苏较快,城市的重建也是十分迅速的。总的看来,明嘉靖前后发展最快的城镇位于运河两岸、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的口岸、商埠和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不仅出现了像天津、德州、临清、济宁这类以商埠起因的专业城市,也出现了江南盛泽、王江泾、乌镇、南浔这类以丝织业起因的专业集镇,并发展出了北京、江宁、杭州、苏州、广州、汉口、扬州、佛山八大工商中心城市。[7]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商经济效果的巨大差距,在诱使大量商贾、手工业者涌向城镇,活跃在东部地区的同时,也逼迫因生活艰难而又遭到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起来。自宋代开始人口比重增大的东部地区,进入明中叶以后,人口数字倍增。在清初出现一段时间的下降之后,又立即呈持续增长形势(见表一和表二)。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和府州,都在华东沿海地区。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个地区的城镇也是发展最快的。
表一:明清人口密度超过平均数的城区比较排行榜
(单位:人/平方公里)
序
洪武26年万历6年 顺治18年
乾隆14年
道光10-19年
(1394)(1578)(1661)
(1749)
(1830—1839)
号 政区
密度
政区
密度
政区 密度
政区
密度
政区
密度
0
平均
19.1
平均
36.5
平均 20.9
平均
41.6
平均
75.3
1
浙江 114.4
浙江 140.5
浙江 118.9
江苏 211.8
江苏 424.6
2
江西
58.4
江西
95.3 南直隶 56.2
山东 162.2
浙江 293.0
3 南直隶 48.0 南直隶 93.6
福建 53.0
安徽 133.1
安徽 228.9
4
山东
39.6
山东
85.2
山东 50.6
浙江 122.4
山东 211.4
5
福建
32.4
山西
72.6
江西 45.5
河南
80.8
湖北 177.7
6
山西
27.8
河南
53.0
山西 43.0
福建
65.1
福建 154.3
7 北直隶 47.8 北直隶 37.2
山西
63.0
河南 148.6
8
河南 24.5
江西
46.6
江西 134.9
9 北直隶 42.9
广东 105.9
10 湖北
41.6
山西
97.8
11 湖南
87.9
资料来源: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表12、13
表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人口密度最高府州排行榜
(单位:人/平方公里)
序号 府州名
密度 序号 府州名
密度
1
江苏·苏州 1073.21 16 湖北·武昌 394.53
2
浙江·嘉兴 719.20 17 浙江·金华 369.48
3
江苏·松江 626.57 18 山东·沂州 363.56
4
浙江·绍兴 579.55 19 安徽·凤阳 345.68
5
安徽·庐州 563.11 20 福建·漳州 327.13
6
山东·东昌 537.69 21 安徽·宁国 326.98
7
江苏·太仓 537.04 22 江西·临江 325.86
8
浙江·宁波 523.26 23 山东·临清 322.64
9
江苏·镇江 522.54 24 山东·莱州 321.33
10 四川·成都 507.80 25 福建·泉州 317.52
11 浙江·杭州 506.32 26 安徽·池州 316.62
12 浙江·湖州 475.21 27 安徽·颖州 314.89
13 江苏·常州 447.79 28 河南·许州 309.17
14 山西·蒲州 423.88 29 广东·广州 306.84
15 安徽·太平 410.96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
城市的发展与人口的膨胀成正比,说明的是市民的增长。在急剧增长起来的市民中,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这里仅以运河两岸的大中城市为例,略作说明。
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天津,是海运和运河运输的交会处,工商业者占全城总户数的65.5%。[8]
临清城,“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涌,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成化十一年(1475)“户部以游宦侨商日渐繁衍,并令占籍”,这些“游宦侨商”后来又在城外的汶卫二水两岸形成了新城区,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自“砖城西北至东南长二十里,跨汶卫二水建新城”。[9]
济宁,“济州关南侧,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10]
扬州,原本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明中叶开始,成了淮鹾总汇,大量的盐商富贾麇集于此。万历年间,盐商多达数百余家,旧城一再延扩,仍然人满为患,新城在商贾的资助下,得以兴建并迅速发展起来。[11]
苏州,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统计,“苏州有会馆四十处”还有“公所一百二十二处”。[12]“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13]
杭州,北宋初的十世纪末时已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14]到了明嘉靖年间,在原本填街塞巷的坐贾居民中又新添了大量的行商,“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15]杭州位于运河南端,东濒大海,是北接中原,西望湖广、江西,东迎福建、广东、台湾的枢纽,又是中国大宗特色商品丝棉、绸缎、茶叶的产地、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商业、手工业人口极多。
在膨胀起来的市民人口中,文化人的比率也在迅速增加。这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促使文化市场发展的人才因素。光有商人及其他行业的市民作为文学消费者,还不能构成文化市场,还必须要有生产者。我们现在还很难找到具体说明市民中文化人比率的资料,但有两类人物就可以成为一支为数不小的文化人队伍。
第一类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文化人。首先是城市居民中的读书人和外地进省、府赴考而滞留的举子。明清两代,东部省份,特别是江南地区,试子夺魁率很高。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明代,自洪武四年到万历四十四年245年之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244人,其中东部的南直隶(包括后来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东六省就有213人;清代,乾隆元年诏举博学鸿词,先后选举267人,其中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占201人。这种高比率,既与人口密度相关,也与文化人的基数相关;它既说明东部省府文化人之多,也说明名落孙山的举子之众,城市中落魄好闲文化人日见增加是无疑的。其次是自己不参加科考却与科考有间接关系,即为科考文化人服务的文化人。象《金瓶梅》中写到的温秀才、水秀才,《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匡超人。他们往往身兼数职,既辅导试子,又帮闲富豪。
第二类是专事文化事业的文化人。这类人或从屡试不第的试子中转化而来,或因才气而乐于舞文弄墨,或鄙视仕途而著书立说,或因生活贫困被迫卖文,或慕都市繁华而来寻找繁华乐趣,或为文化繁荣而来寻觅文化知音。而在经济发达的文化都市,又往往培养出自己的文化缙绅和兼儒(商)之商(儒)。江南地区的金陵、扬州、苏州、杭州因其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文化深厚而成为文化人荟萃之地。即以扬州为例,“地分淮海,风气清淑,俗务儒雅,士兴文艺,弦诵之声,衣冠之选,夐异他州”。[16]著名文化人汤显祖、袁宏道、张岱、吴嘉纪、王士祯、洪升、孔尚任、吴敬梓、曹寅、王念孙、王引之都曾在扬州居住过,他们的作品写过扬州,他们的作品有的写成于扬州;扬州也出现了像汪中、焦循、阮元和“八怪”等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和文化名人。这些人可称之为荟萃扬州的高雅之士,而其中就有不少是倡导通俗文学的革新人物。除此,更大量的是名气不大或名不见经传的平民文化人。
明清两代东部省份文化人荟萃还可以从学术风气和藏书之习来看。明代学风当以浙江、南直隶和江西为最盛,浙东学派在这三省传播最广,学者群起。清代,江苏、浙江为学术的发祥地和根据地。据萧一山《清代学者著述及其生卒年表》统计,清代970名著名学者中,江浙占550人。藏书之习,也是江浙为甚,著名藏书家当以百数。吴晗先生的《两浙藏书家史略》列明代浙江80家,其实远不止这个数目。嘉靖以后,江浙藏书家辈出,甲于天下。以浙江为例,茅坤的“白华楼”,沈节甫的“玩易楼”,项元汴的“天籁阁”,范钦的“天一阁”,胡应麟的“二酉山房”,胡震亨的“好古堂”,朱彝尊的“曝书亭”、“潜采堂”等等,皆著名于世。学术风气与藏书之习决不是个人的行为,它需要浓厚的文化气氛作基础,浓厚的文化气氛与文化人荟萃和活跃是成正比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城镇市民中,一方面是占有绝大比例的商人、手工业者及其他行业的人们,一方面是逐渐扩大队伍的文化人。当商品经济活动成为人们的主要行为时,前者参与经济活动,赢得了物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后者若不能或不愿参与经济活动,便缺乏物质。当由于商品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城镇市民除了物质追求外,又萌发并发展起更广泛的欲望,还需要精神食粮之时,作为需要的前者与可提供的后者就有了交换的可能。这种交换,明以前不是没有,只是进入明嘉靖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和市民人口的增加,更为普遍而规模生产化,更为合理而不以为耻。
入明以后,文化人为商人撰写墓志铭、传记已成一种风气,李梦阳曾为歙商鲍弼撰有《梅山先生墓志铭》[17];文征明不仅给商贾撰墓志铭,[18]还撰有《重修苏州织染局记》、《苏州织染局真武庙记》碑文。[19]明中叶始,文化人与商富的关系已不是传统的对立,刘教正《思斋杂记》云:“天顺初翰林各人送行文一篇,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也,叶文庄公云:时事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成化间则闻送行文求翰林者非二两者不敢求,比前又增一倍矣。则当初士风之廉可知。正德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志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廿两甚至四五十两,与成化年大不同矣”。[20]有的文化人看准同行试子登榜之心,编卖选文,以获其利。上海王光承,“过目成诵,博学能文,善书,为古文词精绝,岁科常第一,坊家争请选文,遂有《易经孚尹》、《墨卷乐胥》、《名家雪崖》、《考卷右梁》、《白门易社》诸书行世,贾人获利无算”。[21]可见《儒林外史》之马二先生者今天专门从事高考、考研辅导的人在四百年前大有人在。《拍案惊奇》卷一写文若虚仿学名人字画,点缀扇面以企图发财,说明文化人卖字画盛行到赝品充斥市场。看来,文化已不仅是一种精神需要,其本身也可以进入市场,成为一种物质生存手段。
于是文学以社会的精神需要和文化人的物质需要,成为文化市场中主要组成部分了。
二、文学从自娱走向消费
文学的传统,一直是自娱。文学是心志、性情、道理的载体。即使小说(指唐宋传奇)也不例外,所以中唐时期曾有过关于韩愈的《毛颖传》的一番争论。[22]其实,这是文化人自居文坛,或以高雅,或以道统自诩的一种传统。唐代的“俗讲”和宋元的“说话”已开了向平民社会传输文学的不同形式,宋元话本的白话形式已为文学走向大众奠定了基础。加上前文所述文化市场中的供需条件已经形成了,文学从过去的自娱走向大众的消费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23]
《小说书坊录》[24]根据现有资料、收录了宋元明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刊刻情况:明代正德以后,刻坊134家,刻小说228种,其中署明地名的为54家,包括南直隶26家、福建15家、浙江4家;清代顺、康、雍、乾时期116家,刻小说369种,署明地名的21家,其中江苏12家。这里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考,明代杭州书坊兴盛,今日可考的有名的刻坊便有24家。众多的刻坊主要集中在商业城市,如金陵、扬州、苏州、杭州,福建的建阳也是著名的书坊之地。所以胡应麟说:“凡刻之地有三:吴、越、闽。”[25]
小说的消费,可分两种情况,一是买书来阅读。二是听书,或租书,或抄书。二者的区分主要是由于消费者不同经济情况形成的。
第一种买书阅读,主要是经济比较宽裕的市民。我们现在很难找到明清不同时期确切的书价资料。明代的板刻、印刷、造纸手工业发展很快,但并不能直接说明书的价钱低廉,只能说明当时书的买卖十分兴隆。书价同书的雕刻、印刷、纸张、装帧质量有关,还同书的印量有关。元末明初,宋濂读书全靠借书来抄,那是因为他家穷,可见买书不易。[26]明清时,文人互赠刻书的礼俗盛行,但这是自费刻书,印量小,很难论以市场价格。清初,《通鉴纲目》一套,二两一钱银子;《明纪本末》一套,六钱八分银子。[27]这是山区农村的价格,而且是同族熟人之间的转让。至于小说,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古本小说刻印情况看,有精有粗,有优有劣;有的配以精美的插图,有的插图则粗陋以致难分人物;有的字大,有的字小。价钱肯定高下悬殊。有学者研究《西游记》一套的价钱是30两银子,[28]这相当于三四十石白米的价值。似乎不确,贵了一点。但即使减去一半,家中若不宽裕,是不可能买来读的。但当时书坊生意兴隆,小说刻本众多,又相当流行,说明市民生活比较富裕,尤其是商人。
凌濛初《拍案惊奇》被书贾看中,投入市场,成为畅销书,“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于是他又写了《二刻拍案惊奇》。[29]冯梦龙、李渔是十分典型的文学家兼商人,他们把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销售都兼任起来,刻印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特别是合乎平民百姓口味的小说。福建建阳人余象斗是名闻南北的大书商和编书家,他的书不仅题材广,质量也好,价格较低,流传海内外。[30]还有更多的文化商人和书坊主结合起来,密察市场消费行情,把受欢迎的小说一再翻刻印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当时刻印次数最多的四大部小说(见表三)。有的人则改变书名再行刻印,使之成为一种软广告,增加吸引力,如《三国演义》改为《第五才子书》,《好逑传》为《侠义风月传》,《红楼梦》为《金玉缘》,《荡寇志》为《结水浒》。有的书商请出名人或假托名人之名,对小说评点批阅或添油加醋,以增加原书的魅力和可读性。出续书、编选本也是当时书商的好手段。凡名书如《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有续书,续书之中不乏文人续书泄情的情结,但应书商之请也是主要动力。抱瓮老人的《今古奇观》、梦闲子的《今古传奇》,别本《二刻拍案惊奇》、《警世奇观》等书则把当时人们喜读的白话短篇小说选辑刻印,其市场效应和影响力都大大超过被选的原著。明清时期,书商之间互相翻刻小说的现象很严重,石印本《株林野史》的扉页有这么些字:“此书得于内庭秘本,刊印非易,同业幸勿翻刻。”这是在声明版权,也许是一种软广告,但它说明的事实是当时的翻刻现象。
表三:明嘉靖后至清末民国初年刊刻次数最多的白话小说排行榜
序号 刊数
书名
1
62 三国演义(包括三国志通俗演义)
2
47 红楼梦(包括石头记)
3
42 水浒传
4
34 西游记
5
33 今古奇观(抱瓮老人编本)
6
28 东周列国志
7
26 玉娇梨、金瓶梅
8
24 封神演义
9
23 镜花缘
10 22 平山冷燕
11 21 儒林外史
12 20 龙图公案、好逑传
13 19 儿女英雄传、说岳全传
14 17 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狄青前传、五虎
平南狄南演义、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
15 16 二度梅、双凤奇缘全传、粉妆楼全传
云合奇踪玉茗英烈全传、平妖传、
16 15 拍案惊奇、荡寇志、南宋志传通俗
演义、说唐演义全传
资料来源:韩锡铎、王清原编纂《小说书坊录》、胡文彬编著《金瓶梅书录》
如此热热闹闹的小说刻印业,足以说明买书阅读的人为数不少。前文已说到江浙一带藏书家很多,这些藏书家大多是官吏、缙绅和文化人中的学者,还有一些是商人。这些商人依自己的财力和需要购买各类图书,有的巨商大贾的藏书量大大超过缙绅、学者。徽籍扬州盐商程晋芳“独好儒,购书五万卷,不问生产,罄其赀”。[31]盐商马曰騄兄弟“家多藏书,积十余万卷,筑丛书楼贮之”。[32]藏书家藏书与市民买书阅读当然有差别,但在其丰富的藏书中,文学书籍、小说刊本也必然占有相当的数量。
第二种是听书。这是下层市民中收入低而又爱好文学且喜以耳听为痛快方式的人们消费小说的方式。明清说书业十分兴盛,是宋元说唱艺术的新发展,它在全国各地又有不同的形式,如明代的平话、词话、陶真、弹词、宝卷,清代的八角鼓、子弟书、扬州评话、苏州弹词、广东弹词等等。[33]说书活动主要是在城市中比较盛行,每天一段,听众必须交费,这都合于市民的生活节奏和消费水平。乡村也有,方式略有不同。明末最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34]其实,若从更广的角度来说,听书不仅是下层市民消费小说的主要方式,也是其他层次市民消费小说的一种形式。听书与读书不同,可以不受文化水平低的限制,听者与说者又有交流,加上说书具有第二次创作的特征,艺人声情并茂的表演与即兴发挥,往往使听众得到更多的愉悦。
关于租书业,这里有一则材料可以直接说明当时租书业的兴盛。道光丙申有四宜斋抄本《铁冠图分龙会》四册二十一回,该书里面有一印记:“书业生涯,本大利细。涂抹撕扯,全部赔抵。勤换早还,轮流更替。三日为期,过期倍计。诸祈鉴原,特此告启。”上横刻“四宜斋”。[35]这“四宜斋”是租书铺子无疑。租书业的兴盛说明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大发展,也说明了不能或不愿买书而又想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多。
抄书,原是读书人的优良传统,但作为小说文学消费的抄书则是另一回事,以抄的手段来实现阅读的动机,或是因无力买书,或是因无法买到书,或是抄比买划得来。在现存大量古本小说中有不少是过抄本。除去内府精致的抄本,作为大众流行阅读的有:《浪史》、《僧尼孽海》、《幻影》、《剿闯通俗小说》、《红白花传》、《金云翘传》、《灯草和尚》、《株林野史》、《海角遗篇》、《七峰遗编》、《载花船》、《铁冠图分龙会》、《珍珠舶》、《斩鬼传》、《东游记》、《风流悟》、《野叟曝言》、《绿野仙踪》、《歧路灯》、《虞宾传》、《怡情陈》、《风流和尚》、《浓情快史》、《三续金瓶梅》等等。其中有的有多种抄本,如《斩鬼传》;有的一开始是以抄本流传,如《野叟曝言》。其中有的抄写年代并不久远,也许是近代人所抄,只是难以辩认,权且存疑。《红楼梦》的抄本是该书版本的一大系统,目前已发现的就有十余种,这是学术界皆知之事。[36]在抄本中可以发现,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居多,世情小说居多,禁书居多。数十万上百万字的巨篇抄作工程大,非佳作不抄,演史、神魔刊刻比例大,世情刊刻相对较少(见下文分析),而且世情小说中的艳情小说由于禁毁和道德的原因,刊刻更少,所以世情小说特别是艳情小说常以抄本流行。在小说的消费中,抄书以阅读是比较复杂的现象,原因很多,读者、抄者的经济状况只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通过抄书获得欣赏正说明市民文学消费欲的强烈。
无论是买书来阅读还是不买书而通过听书、租书、抄书来欣赏,文学已经在相当广泛的范围从文人独占的自娱圈子中走了出来,走进市场,走向广大市民消费的柜台。
三、文学从道德说教走向愉悦闲适
文学从自娱自乐走向消费,从文学创作自身来看,实质上解决了文学为谁而写的问题,而为谁而写又与写什么紧密相关,不解决写什么的问题,为谁而写就是空架子,文学就不能在进入市场后产生市场效益。过去的文学为文人自娱服务,自己需要什么就写什么,抒情,泄愤,明志,论道,都从自我出发。文学进入市场,就要为消费者服务了。作者的“自我”就应与读者的需要结合起来了。
仍以小说为例。根据目前收集通俗小说书目较全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从明代正德(主要是嘉靖)年间算起,到清代道光年间为止,约有各体长短篇500种(集)。若以独立的故事为分析单位,在500种(集)小说中约有2330个长短篇故事(不包括开篇入话)。其中演史故事(含英雄传奇)270个,神魔故事260个,大多数为长篇;世情故事1800个,大多数为短篇。演史故事多为前代,神魔故事不少年代不明或不受年代限制,世情故事则多为当代。半数以上的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大多数佳作名篇和大多数作家也都出自这一地区。再看表三,[37]各类题材的小说都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基本上是平分秋色。在城市市民中,职业、年龄、文化程度、个人经历都可以形成不同兴趣的读者和听者群。从一般欣赏心理来看中老年喜欢演史,青少年欢迎神魔,豪爽者偏爱英雄壮举,青年男女热衷男女情事;至于街谈巷议、奇闻轶事、悲欢离合,在市民中是很有市场的。广大农村,演史、神魔更受欢迎。文化人、商贾好风流艳情,传统心态浓重的人们则爱好忠君贤臣、义夫节妇。
但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根据表三资料来源作的统计,“三言”“二拍”的刊刻远不如今日人们想像的那样多,《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刊刻4次,《警世通言》3次,《醒世恒言》4次,《拍案惊奇》15次,《二刻拍案惊奇》1次。总的看来,世情小说的刊刻次数,短篇不如长篇,原本不如选本。其原因也可从市场中去寻找。世情小说中,短篇数量大大超过长篇,这说明短篇的创作和编辑速度快,更新快。有不少短篇集子中的故事往往是简短的街谈巷议和道听途说以及公案讼状,其再刻的价值不大。即使在“三言”“二拍”中,也并非篇篇上乘佳作。好的短篇小说有两种前途:一是进入精彩的选本,如《今古奇观》;二是进入长篇小说诸如《金瓶梅》及其后来的才子佳人世情小说和施公、彭公、包公之类的公案小说,成为其中的情节组成部分。这二者实际上都是经过编选者和创作者的再次用心,以市场行情、消费者的需要为标准的。
看书、听书到了用钱才能实现的时候,兴趣、娱乐便成了第一需要,而传统的道德教化动机便以更多的形式渗透到情节人物之中,而不是如明初“五伦全备”那么生硬直接了。
诚如古人所云:“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38]文学的娱乐作用既是第一的,也是普遍的,文化人、工商业者,君子、俗民,乃至道学家们也不例外地在实际生活中享受文学的这一特征。
“以文为戏”,在唐时已有争论,在明初又有人说了出来,[39]但当时仍局限于文人的自娱,写作是自遣、练笔,阅读则以资谈笑。明中叶后,文人“以文为戏”的观念则愈偏重于娱乐。“月之夕,花之辰,衔觞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宫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姝,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40]不仅小说,历来文人学者视为道统载体的散文,也已偏离正统载道、明道的轨道。唐宋派已倡扬“本色”,主张文章“自胸中流出”,只是“直写胸臆”,“独出于胸臆”。[41]归有光的不少佳作,如《项脊轩志》,开始述写平淡之中蕴含深情的普通生活,直接影响了晚明公安派“性灵说”并开晚明小品散文的先河。晚明,袁宏道、张岱等人的散文去粉饰,求本色,尚俚俗,追情趣,给人们以闲适愉悦之感。
对平民百姓来说,“以文为戏”便是把小说作为娱乐来用了。“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42]这不仅是小说的历史起源,也是通俗小说新作品的起源,是通俗文学需求的动机。所谓的市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里之猥谈”。[43]《金瓶梅》中西门庆常把应伯爵拉在身边帮闲,应伯爵能随时传达这种猥谈是对西门庆的诱惑力之一。明清两代世情小说“写什么”,当从市民的这些需求中去把握。“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44]古今杂事琐谈,便是大众欲读欲听之事;开眼界,得愉悦,便是平民消费文学之动机;不管是真是假,只要怪怪奇奇。平民所需要的文学就是写这些东西。文化人写小说、编选本,也就去搜寻挖掘这些东西,冯梦龙、凌濛初在他们的小说序文中也都十分坦白地承认了这种创作和编辑动机。[45]冯梦龙搜集编辑的《山歌》、《桂枝儿》,皆来源于平民百姓。[46]
走向市场成为消费商品的文学,其审美标准与传统的道德伦理常发生冲突。于是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便划出了一条分水岭,主张“真情”“童心”,顺乎民众的便是反传统的进步作家、思想家;死守道德说教,或“发乎情,止乎礼义”,反对通俗文学的便是保守派。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冯梦龙、凌濛初、汤显祖、李渔、曹雪芹等等一大批可以称得上反传统的进步文学家们虽然不像田汝成、李绿园那般顽固保守,却都有不止一次的说教表现。这只能用矛盾和局限作解释。
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学观的核心。历代文化人和学者多有提倡文学对道德的责任,不必赘述。明中叶始,道德责任开始动摇。其原因很多,从文学内部的发展来看,台阁文学以其庸俗应酬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内容已使人们对道德说教产生了怀疑,而前、后七子的复古又在形式上表现出恢复传统之路不通;文学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促动起来的通俗文学因娱乐动机却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于是在文学的创作实践中,脱离道德责任理论而“适俗”。[47]这是一部分作品,特别是一部分世情小说作品的表现。
但情况是复杂的,当文学已经从自娱走向市场,由道德说教走向愉悦闲适,仍有相当多的文化人一方面写出市民们欢迎的作品,包括一些非道德反道德的作品,一方面又仍在前序后跋、字里行间反复申明自己的道德责任感,表示自己在教化劝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呢?不可否认,习惯了的传统思维及其思想与新鲜的文学实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矛盾地存在着。拥有这种矛盾的人应当是痛苦的,特别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创作结果与自己的思想背道而驰,传统的人格受到近乎自我否定的遭遇时,他一定会感到内心的悲哀,至少是沉重的。但在我们所认识的“矛盾人”之中,却很难发现有精神上的痛苦者。冯梦龙不是,凌濛初不是,汤显祖、李渔也不是,曹雪芹有痛苦,但那是为少男少女真情呼喊的“一把辛酸泪”。憨憨子说他曾对《绣榻野史》不满,原以为“可以娱目,不意其为谬戾”,于是束之高阁。不料,他在书肆中却“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感慨不已,“慨然归取而评品批抹之”,他说他要学孔子删诗之法,将“淫书”付梓,“因其势而利导焉”,“将止天下之淫”。[48]以文学之“淫”,“止天下之淫”,这便是明清之时热衷于平民文学的文化人在发生观念与实践矛盾之时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正如李贽所刺,是“装许多腔”。[49]男女之情、“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50]“商业利益的追求压倒了鼓吹经传的原则”,[51]迎合市民消费需求以换取自己物质生活需要已成了文学创作的第一动机,“止天下之淫”不论是否装腔作势,在读者、听众那里往往是多余的,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时代文学特征的事实。
文化人谋利把道德责任和种种说教作为幌子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市场,却也导致了小说中的道德说教在客观上并非没有审美意义,特别是那些溶注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血脉之中去的道德行为与道德言论,仍可以对读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审美(教育)效果。小说的接受者是多元的,各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当道德融于形象,付诸语言,读者“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52]是一般的接受过程。文化市场的繁荣,不仅是文化人多题材、多形式的创作,更是因为有对各类题材和文学形式的多元消费者。至于那些道学家式的为教化而约束文学,为教化而扭曲小说创作的说教,诸如田汝成批评《水浒传》“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之类的诅咒,[53]李绿园的《歧路灯》卷首附《家训谆言》81条开篇,故事发展中动辄以“为贤者讳,不忍详述”来中断情节和人物行为,已经是很尴尬的表现了。[54]
标签:文学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二刻拍案惊奇论文; 扬州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明清论文; 拍案惊奇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