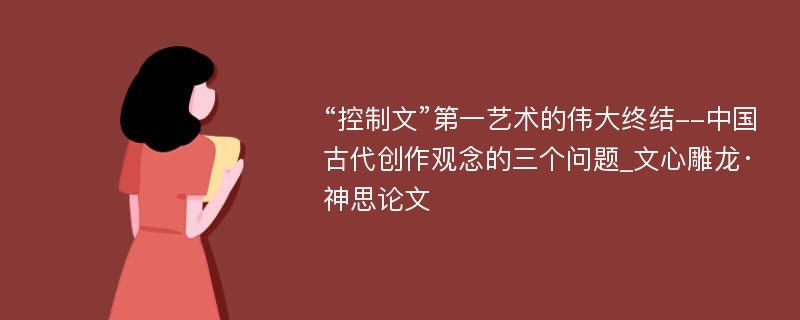
驭文之首术 谋篇之大端——中国古代创作构思论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端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之首论文,构思论文,论三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驭文之首术
构思是文学创作的关键环节,刘勰以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神思》,以下简称《神思》),对构思奥秘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创作论中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构思的本质、方式及心理条件三问题,对古代构思论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构思的本质:意象的酝酿
创作构思大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意象的酝酿,二是对意象传达方式的斟酌、思虑。比较起来,古代批评家更重视前者。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用意象这个概念来说明创作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的意象即指活跃于作者内心而又尚未形诸笔墨的形象,即章学诚所谓“人心营构之象”(《文史通义·易教》)。
说意象的酝酿是构思的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
1.它是文学创作的关键一环。“窥意象而运斤”的说法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只有当意象在作者心中孕育成熟,才能可能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进入表达阶段。这层意思在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有着更详尽地说明:
故画竹者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孰视,视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画竹而必须“先得成竹于胸”,意思就是说,艺术创作的第一步必须孕育出一个成熟的意象,然后才谈得上艺术表现,即把胸中之竹转化为画中之竹。可见,意象的酝酿对于整个创作过程来说是决定性的,它制约着创作活动的成败。离开了意象的酝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创作。这一点古人已有过很多论述,例如沈德潜就指出:
写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谓意在笔先,然后著墨也。惨淡经营,诗道所贵。倘意旨间架,茫然无措,临文敷衍,支支节节而成之,岂所语于得心应手之技乎?(《说诗晬语》卷下)这个说法直接把苏轼的画论引入文论,并把它嫁接到“意在笔先”的古老命题上,这里的“意”也就成了意象的同义语。比起苏轼的说法,沈氏进一步从反面揭示了在意象育成前,创作其他环节的活动是无法展开的。勉强为之,也充其量只是“临文敷衍,支支节节而成之”,就不是一个出于内在需要,释放能量的过程。这样,创作的快感就为一种“茫然无措”的苦恼所代替,写作也就成了一种“求其一字一句出于安排而成于补缀”(钱谦益《瑞芝山房初集序》)的机械制作,这已经跟文学创作无缘了。
意象既然是育成的,那末,这就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对此,古人常用“生”这个词来形容。如《文镜秘府论》谓:若文思不来,“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黄庭坚认为,诗文“必待境而生便自工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刘熙载亦云:“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艺概·赋概》),这里的“境”、“象”都有“意象”的意思。这些看法都标志着这样的事实:意象的酝酿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创作的关键就在促使意象的成熟。对于这个生成过程,古代批评家们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曾作过不同程度的描绘。其中陆机与刘勰的论述比较全面,他们分别在《文赋》、《文心雕龙·神思》中正面展开了这个过程:起初,作者“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而后则须“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对纷乱的情思、景象进行加工;于是“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意象在作家心中逐渐清晰、丰满起来。而当意象一旦具有了鲜明、生动的感性特征,亦即达到了苏轼所说可以“执笔孰视”的程度时,它也就宣告成熟了,作者也就可以“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进入表达阶段了(以上引文见《文赋》、《神思》)。这里我们只是稍稍接触了一下意象的生成理论,然而我们通过对这些论述的梳理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古代批评家们对意象孕育在创作中的地位是认识得相当明确的,几乎可说是达成共识的。
2.成熟的意象是作家由构思进入表达的直接推动力。古代作家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理想的写作境界应是作者兴会淋漓、身不由己地被一股强大力量推着进入写作状态,这就是古人所谓“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文镜秘府论》)的意思。那末这股推动作家由构思进入表达的力量来自何处呢?答曰:来自成熟的意象。古代文论在谈到写作动力的本原时通常都归结为主体内部的情感激荡,这无疑是正确的。如《乐记》谓:“情动于中,故形于文”,刘勰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钟嵘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等等,这些说法同我们说的写作动力源于成熟意象有没有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所谓意象事实上即包含了情感(意)与形象(象)两个方面,二者合二而一,而以情为主。陆机在论意象的生成过程时就这样描述:“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文赋》),刘勰亦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神思》),都兼指情、物两方面。后来的一些批评家大都沿着陆、刘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中以章学诚的讲法为最透辟。他以为“人心营构之象”,实即“情之变易为之也”,是“意之所至”的结果(《文史通义·易教》)。这表明在古人的观念中意象并不只是客观物象的简单移入,而是在物象中融铸、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样,意象的酝酿实际上也就包括了两个同步前进的过程,即随着形象在主体内部愈益鲜明、丰满,与之浑融为一的情感蓄积也就越来越深厚,情感的激荡也就愈来愈强烈。当内在意象终于发育成形,其情感能量的蓄积,发酵也就达到了临界点,于是“境会相感,情伪相逼,郁陶骀荡,无意于文而文生焉。”(钱谦益《瑞芝山房初集序》)这说明写作的直接动力源于情感的激荡与源于意象的成熟实即一回事,并不矛盾。清昱人王昱说:“胸中有得,技痒兴发”(《东庄论画》),非常恰切地揭示了意象酝酿与传达的关系。当内在意象经过孕育终于达到瓜熟蒂落的程度时,作者内心克制不住的表现欲就随之而生了。可见,这所谓“技痒”,实在只是内在意象驱动的结果,是“兴”之所至的必然反应,“技痒兴发”说明“胸中有得”,表现欲的强烈标志着意象的成熟。
二、构思的方式:直觉与理性
创作构思既然从本质上说是对意象的酝酿,那末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考察另一重大问题,即意象到底是理性的产物,还是直觉的产物,或者说,创作构思究竟是自觉的,还是非理性的。
关于这个问题古代批评家的意见颇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直觉的产物,“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人力无须参预其间,因此他们主张“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梁书·萧子显传》);但也有不少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创作还须依靠理性,必须惨淡经营,“竟日思诗,思之又思”(方回《跋昭武昱文卷》),这样“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等等,对于这些看来彼此对立的看法该怎么看?我们以为理解古人比简单地判定其是非更为重要和有益。由于古代批评家们的表述常常是经验性,感悟式的,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因而常易引起一些误解。倘若我们从意象生成的角度来考察这些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包含着部分真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构思奥秘的探索,各有其理论价值。
如上所述,构思实质上是对意象的酝酿,那末,构思过程也就可按意象的成熟度分为受孕、孕育与成熟三个时期,而在不同的时期内思维的方式和特点是不尽相同的。
意象的受孕,或称为感兴、灵感,是构思的起点,它基本上是直觉的产物。创作主体在外界的感召(刺激)下,心灵受到震颤,产生了最初的冲动,从而为日后意象的诞生布下了种因。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苏轼说他的作品是外物“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的产物,“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江行唱和集叙》),金圣叹说得更好,“诗者,人人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与许青屿书》),郑板桥说他画竹动机的获得是晨起看竹,心有所动,“胸中勃勃,遂有画意”(《画竹》)。这些经验之谈无不揭示了意象受孕的非理性特征。也就是说,创作感兴的发生并不是主体有意寻觅而得,相反倒是出于意外,自动降临的;人的意志不能随意支配感兴的发生。意象受孕期的这种非理性作用所带来的能量直接推动作家进一步构思下去。因此,古代批评家特别强调创作应该“伫兴而就”,“乘兴而发”,而不要勉强。刘勰就指出,创作应该“率志委和”(《文心雕龙·养气》),“无务苦虑”,“不必劳情”(《神思》)。《文镜秘府论》也认为感兴不能以苦思求得,倘若文思不来必须“放情却宽之”(《论文意》),用制造宽松心境的方法来为感兴的发生创造条件。谢榛说得更明确“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卷二)。意思非常清楚,构思的第一个环节必须仰赖直觉,理性此时倘占据主宰地位则不仅无助于感兴的发生,反而会扼杀创作的生机。
意象一经受孕就开始了它的孕育过程。随着创作冲动的发生,主体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直觉摆脱了理性的约束,活动相当自由。这主要表现为想像异常活跃,思绪纵横驰骋,“感召无象,变化不穷”(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文心雕龙·物色》),一时间万象叠现,“万途竞萌”(《神思》),完全打破了时空的限制,突破了自身感觉经验的局限,这些丰富、生动的想像似乎都是不费吹灰之力自动浮现于作者脑际的。这是构思中必经的一环,无此环节,主体的心理机能便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为进一步的加工提供必要的能量与材料,构思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但是不是在孕育期内,理性可以不必参预进来呢?也不是。因为在构思初始阶段,作者脑际浮现的形象虽丰富、生动,却杂乱无章,并不都适宜进入作品;有些形象虽可进入作品,却粗糙、模糊、飘忽不定,这时就需要主体的理性机制发挥作用,对涌入脑际的纷纭万象加以审视、取舍、加工、提炼。《文镜秘府论》中说:
文思之来,苦多纷杂,应机立断,须定一途,若空倦品量,不能取舍,心非其决,功必难成。(《论体》)
这里讲的就是主体要理性地对纷涌而来的文思加以择别,而只有经过了这一番过滤、筛选,文思才可能明晰,主题才可能确定,构思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这时对于那些已被主体接纳进入酝酿过程的意象而言,已不能像初始时那样完全放任活动了,而必须由主体进行一番加工、提炼的工作,这就是刘勰所谓“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即把那些尚属单薄,模糊,甚至还欠确定的形象、意念加以雕刻,施以规矩,从而使它们确定成形,鲜明生动,这一工作恰须借助理性之力。这是构思中最关键,同时又是很艰苦的一环,古人所谓“取境”、“造境”、“炼意”,王昌龄所谓“精炼意魄”(《诗格》),杜甫“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等说法大抵指这一环节而言。
当意象经过孕育终于成熟,即将进入表达阶段时,直觉与理性仍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从直觉来说,主要表现为伴随着意象成熟而来的强烈的渲泄冲动。这种源于主体内部的骚动使得作家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犹如骨哽在喉,必欲吐之而后快,“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朴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能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钱谦益《虞山诗约序》)这时作家又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主宰,为这股强大力量所支配,从而出现“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谭友勇《汪子戊己诗序》)的现象,于不自觉中受着内在驱力的推动进入表达阶段。而从理性来讲,则主要表现为对表达方式的选择、斟酌。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创作主体能否准确无误地传达出他所感受到的内在意象,也就是求得古人所谓言意间的契合,这又是一个很不简单,甚至相当艰苦的过程。陆机说作家在创作时“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刘勰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行”(《神思》),苏轼则叹词达为难,以为“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可见,这是创作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这就需要作者充分发挥理性的作用,调动自身的艺术素养,殚精竭虑地艰苦搜求,煞费苦心地布局谋篇、遣词造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皮日休《皮子文薮》)等说法,以及贾岛对“僧敲月下门”中用“敲”还是用“推”的反复斟酌,王安石对“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的选择等等都足以说明对表达方式的思索、斟酌,必须发挥理性的作用,从而缩小言意间的差距,乃至最终使二者契合,使内在意象能了然于口与手。
总之,在构思过程中,直觉与理性须共同运作,才能最终育成意象。需要指出的是构思中直觉与理性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互相交融,难分彼此的,就是构思与表达的界限也常常不是像我们在文中所述那样划然分明,我们只是为着论述的清晰起见,才将这个过程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单纯的环节。
三、虚静:构思的心理条件
构思的发生除了外界提供一定的刺激外,主体的心理条件也是很关键的。具备什么样的心态才有可能进入创作的佳境呢?古代构思论认为,虚静的心态是保证构思顺利进行的前提。
虚静的思想源于先秦诸子。在老子、庄子、荀子、管子的思想中都有对于虚静的论述,但他们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的。其基本思想是,人们内心的虚静状态有助于对外物的正确认识。刘勰首先把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创作,《文心雕龙·神思》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指出了虚静的含义就是排除干扰,保持澄静空明的心境,虚静的作用即在酝酿文思,这就揭示了虚静说的基本思想。从现代眼光来看,虚静说中包含着丰富的创作心理学内涵,具体说,可以有这样三层含义:
1.虚静的状态为构思活动提供了一个最佳心理空间。虚静的要义即在排除干扰,保持心地的空虚、宁静。先秦思想家认为,心虚是接纳万物,认识世界真相的前提。同理,文学创作亦须排除干扰,使胸中廓然无一物,打扫出一个清明的空间,保证创作构思的顺利进行。那末怎样才能达到虚静状态呢?虚静说提供了两种方法:其一,排除来自外部的干扰,这就是说要暂时中止感官对外界信号的接受。这是因为创作贵在感兴,作家兴会淋漓之际构思就比较顺利。然而感兴又是极易因受干扰而消失的,葛立方说:“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韵语阳秋》卷二)这样,“收视反昕”(《文赋》),屏绝外界干扰,保证作家心不外驰,专心构思就显得很重要了。而在实际的创作活动中也确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如刘宋画家顾骏之“尝结构层楼以为画所”,每当作画时,便“登楼去梯,妻子罕见”(谢赫《古画品录》),独自一人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隋代诗人薛道衡每当酝酿文思便躲到空室之内,面壁而卧,不许人来打扰,甚至不容许室外有人声;宋人陈师道只要一得佳句便急忙赶回家中卧于榻上以被蒙首,有时甚至把家里的婴儿、犬、猫都寄放邻家(见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这些特殊的写作习惯,其作用就是不让感官接受外界刺激,使主体免受干扰,保证构思顺利进行。其二,排除来自主体内部的干扰,也就是要抑制功利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心而生的欲望可能对创作的干扰更大。一个人如果充满了功利欲望是很难集中精力于艺术创造的,即使写出作品来也不免带着尘俗之气,“鄙野村陋,不逃明眼”(刘学箕《方是闲居小稿》),即便艺术上巧妙精致,也最多不过“只与髹采圬墁之工,争巧拙毫厘也。”(李目华《书画谱》)文艺创作是一项审美活动,需要主体具备超功利的态度,这样才能使作者在创作中进入自由之境。因此古代批评家们非常强调作者在进行创作前必须自觉排除内心欲望,“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神思》),“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朱熹《答巩仲至》),“平其争竞躁戾之气,息其机巧便利之风”,“摆脱一切纷更驰逐,希荣慕势”(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这样,摆脱了物欲的干扰,才有可能进入一个超功利的审美境界,并最终完成作品。
2.虚静状态可以保证作家在构思时专一集中。虚静的另一要义就是心志专一,聚精会神。在荀子那里,虚静更完整的说法是“虚一而静”,他并且解释“一”的含义道: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荀子·解蔽》)这就是说,对认识主体来说,要透彻地认识对象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目标,不能一心二用同时注意多个对象。当主体排除了内外两方面的干扰之后,就为主体的专一凝神提供了条件。这样看来,在虚静说中便包含着这样的内涵:保持心地的虚静不过是一个手段,使主体能专心致志才是目的。而文学创作上的虚静说因此也就关涉到创作心理中的审美注意问题。如上所述,创作构思本质上是对意象的孕育,那末当主体在投入这项工作时,他必然充分调动起一切心理机能,全神贯注于这一目标,以至他无暇去注意与此无关的事物。据说司马相如在构思《上林赋》、《子虚赋》时,精神高度集中,“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接”,即对外界景象到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程度,因而就表现一种“忽然如睡”,恍惚迷离的痴迷出神之状。这就保证了他构思的顺利进行,使他沉浸在艺术想象之中,可以“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思绪泉涌,终于“涣然而兴”,最终写出了作品。(见《西京杂记》)又如贾岛也常因构思诗句而陷入沉思,以至对周围情景全然不觉。某次,他骑驴上街边走边构思,由于过于专心,竟在不知不觉中冲撞了权贵的车驾,因此被囚禁了一夜。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在创作中忘掉一切,因为只有当作家进入身心俱忘的境界时,才意味着他“用志不分”,凝神专注于意象的孕育。也唯有在这样的状态中,主体才能以异常的敏锐去捕捉灵感,以异常的洞察力去观察物色,以异常的感受力去体验物象,以至与物象融合为一,进入构思的最佳状态,从而在自由随意中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3.虚静的状态有利于诱发灵感。灵感是创作得以发生的启动器,没有灵感便不可能有文学创作。古代作家都很重视对灵感的捕捉,他们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程度不同地体会到虚静心态较易诱发灵感。例如有些作家发现在夜深人静时写作较易获致灵感。刘昭禹诗云:“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唐诗纪事》卷四十六)。谢榛说他有一次深夜静卧,吟咏诗句,“忽机转文思而势不可遏”,不经意间灵感袭来,诗思泉涌,由此他发现,“凡作文,静室隐机,冥搜邈然,不期诗思遽生,妙句萌心。”(《四溟诗话》卷三)有些作家则说诗思常生于“杳冥寂寞之境。”(《韵语阳秋》卷三)谢徽自叙创作体验说:当作家“一室燕坐”,“几案间冥默觏思”时,脑海中就很容易浮现出生动的意象,“神与趣融,景与心会,鱼龙出没巨海中,殆难以测度。”(《缶鸣集序》)周济则以为作家只有在“沉思独往,冥然终日”的情况下,才能写出佳作(《介存斋论词杂著》)。这些说法都揭示了虚静心态与灵感降临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与上述说法相比,皎然与况周颐的看法似乎更全面、透彻。皎然指出:
“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诗式》卷一)说得虽简明,但却全面,展示了灵感降临的过程及条件。这就是说“佳句纵横”是“神王”的结果,而“神王”的获得则又须以“意静”为前提,这就揭示了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主体的虚静状态(意静)有利于诱发灵感。与此相似而说得更为详尽的是况周颐的一段话,他自叙自己的创作体验: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暝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己;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卷一)这里作者一开始为我们描绘的就是一个杳冥寂寞,夜深人静,没有干扰的环境,这是形成虚静状态的外部条件。然而仅此还不够,要真正进入创作,还须运用修养功夫,“湛怀息机”,排除内心功利欲望的干扰,把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才能达到“万缘俱寂”的虚静心态,这相当于皎然说的“意静”。创作的心理条件具备了,主体的心理功能便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感觉变得异常敏锐,“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等待着灵感的到来,这大致就是皎然所谓的“神王”。只有在这时灵感才悄然降临,“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的冲动发生了,“心头忽视之一声”响起来了,作者心潮澎湃,思绪起伏,创作的闸门由此打开。而待到感兴消失,作者从高度兴奋中清醒过来时,脑海中原先浮动的“境象”顿时消失,而先前被遗忘的现实环境又一一重现于目前。可见,虚静心态是灵感爆发的前夜,因而也就是保证创作顺利进行的前提。这里包含着的丰富的创作心理学内涵是颇值得今人玩味思索的。
标签:文心雕龙·神思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镜秘府论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四溟诗话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