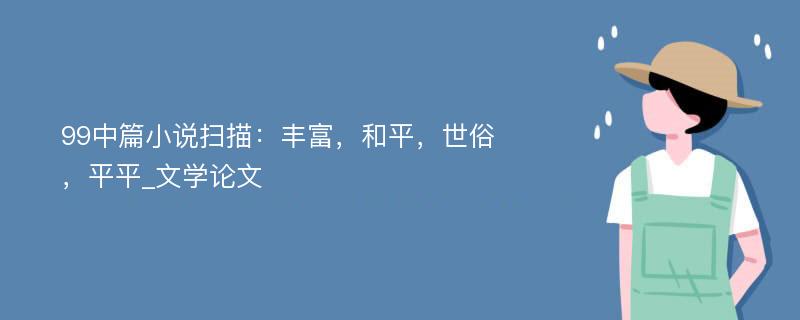
’99中篇小说扫描:丰富、平和、世俗、平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篇小说论文,平和论文,世俗论文,平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篇小说创作而言,1999年是平常的一年,我们虽然在1999年读到了一批相当不错的作品,但这其中又明显地缺乏大家之作,震撼人心之作。然而,1999年又是不平常的一年, 不仅是因为1999 年连接着20世纪与21世纪,在时间上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一种承上启下的特殊意义,而且还因为1999年中篇小说的创作态势确实有着某种意味深长的变化与启示。概括起来,1999年中篇小说创作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作者年龄的构成有了比较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二是呈现出多样多元的态势,三是大众化与世俗化,四是平面化。
一、作者年龄构成的年轻化
展读1999年的中篇小说,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老一辈作家,包括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曾经是中坚力量的王蒙、陆文夫、邓友梅、蒋子龙、韩少功、张洁、谌容等中年作家开始淡出中篇小说的创作,个中原因,一是由于这些作家有部分人将精力逐渐转移到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来,或是主要的精力已不再用于文学创作,二是对于迅捷变化的时代的整体把握与反映已显得力不从心。中篇小说由于它的容量和篇幅的特点,它不像长篇小说那样可以让人从从容容地简笔繁笔,架构人物与文本结构,它也不像短篇小说一样可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截取生活的某个断面即可敷衍成篇,它不仅要求作者能及时把握住生活及变化,也需要作者透视生活的能力,可以说,很多时候一篇中篇小说就是一段生活史。作为世纪更替的一个年头,人们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与以往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生活的方式和节奏也日益多样和丰富起来,新的生活构成,新的语汇,新的观念,新的符码,使得老一辈的作家们在把握上多少有点吃力。于是,我们很自然地看到,构成1999年中篇小说创作主力军的是铁凝、王安忆、莫言、何立伟、池莉、方方、李肇正等中年作家,而充满了生机与变数的则是北村、迟子建、何顿、邱华栋、韩东、朱文、张旻、徐坤、徐小斌、夏商、海男、程青、卫慧、刘燕燕、周珺这样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了。无疑,因为他们与当下生活更为契合,他们更容易感知与理解当下生活的种种现象与变化。六十年代作家,七十年代作家,甚至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年龄的日渐年轻化无疑也是现时社会生活的快速多变的一种反映,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却也因为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清新和锐气,因为他们对多变生活的快速反映而活跃了整个中篇小说的创作。
二、文学的多样化与多元化
和以往相比,中篇小说创作的覆盖面更为广泛,题材和表现手法也都更加趋于多样化:官场、商贸、情感、城市、乡村、历史;写实、古典、浪漫、现代、后现代……等等,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所涉及,所有技术手段都可以为我所用,伴随着题材的拓展与表现手法的日益丰富自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篇小说的面貌也较之以前显得更加丰富而有特色。同样是描写乡村,《青草如歌的正午》(迟子建《十月》第2 期)显现出一个心智不正常的人于封闭混沌之中的温情与善良;《播种》(孙慧芬《湖南文学》第3 期)描写了两个辛劳的女人将各自生活中的不幸归罪于对方,相互仇恨而又相互隔绝;《乡间的迷茫与忧伤》(张小小《时代》第4 期)状写了已经进城的“我”亲身感受到的乡村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重贫乏与狭隘枯燥。三篇作品明显地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叙事风格。即便《1960年的乡村》(星竹《时代文学》第1期)与《1958年的堂吉诃德》(艾伟《江南》第4期),同是以过往的那个极左时代为背景描写乡村,前者表现了生产队的干部与一个普通的妇女为了全村人的生存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瞒产藏粮,后者记录了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麻木的村民中的孤寂。同样是描写都市,作家所选取的角度,所描写的对象,所传递的信息也是各不相同迥然有异的。在《睁大眼睛睡觉》(毕飞宇《钟山》第5 期)中伴随着一个刑满出狱的青年的行踪,读者几乎可以同样感受到都市夜晚的五光十色与喧嚣吵闹;而在这样的膨胀了的喧闹当中,《亭子间里的小姐》(李肇正《青年文学》第8 期)对欲望的抗拒与最终的妥协便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储福金《平常人生》(《十月》第3 期)试图通过一个本分的下岗女工形象,以源于传统文化的淡泊当中的坚韧来回应人生的变故与坎坷;而许春樵《找人》(《青年文学》第1 期)则透过老景的双眼以冷峻的语言漫画的笔法勾勒出了现代都市人的众生相,挥洒下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辛酸泪;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大家》第3 期)将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躁动矛盾分裂的社会心态发展到极端,塑造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城市女性形象,女主人公白昼的白领身份与夜晚的妓女生涯象征着狂乱当中的叛逆与和谐……这些作品,既让人感到丰富多彩眼花缭乱,又让人觉得有着某种意味深长的巧合与必然,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带有某种典型意味的心态和趣味,尴尬与困惑。
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与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文学审美观念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在比较宽松的氛围当中,作家得以较为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文以载道”的作品有人喝彩,一地鸡毛的故事也有人欣赏。“个人化写作”在1999年有了相对充实的内容与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以说主要表现在中篇小说的创作上,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学现象。北村的《周渔的喊叫》(《大家》第1期)、 夏商的《休止符》(时代文学)第1期)、海男的《女人专》(《大家》第1期)、鬼子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 程青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时代文学》第5期)、 李大卫的《地震中的提琴手》(《人民文学》第7期)、卫慧的《神采飞扬》(《钟山》第1期)、张旻的《求爱者》(《花城》第1期)、 刘燕燕的《飞鸟和鱼》(《大家》第6期)、周珺的《清水美衣》)(《特区文学》第1期)和《被挡在门外的女孩》(《花城》第5 期)等作品构成了中篇小说创作当中更富有活力的一道景观。“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是在文体以及叙事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试验,他们作品当中所表露出来的理念与审美情趣亦确实与传统的“宏大叙事”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莫怀戚的《透支时代》(《当代》第5期)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篇小说既像是一部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言情室内剧,又像是一篇推理侦探小说,堪称新人类一族生活的生动写照。吴越这个人物形象,以及她的处世哲学都十分新鲜而耐人寻味。吴越和“我”的婚外恋自始至终都是和利害、欲望、感情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的。“而吴越既非真诚之人,也非虚假之人,她是最让人头疼的半真半假之人”,文中“我”自白道:“其实说爱不一定确切,确切地说应该叫需要。人们常常将爱与需要混淆……的确只有需要是不可抗拒的。”如果说我们在《玫瑰灰的毛衣》(黄蓓佳《钟山》第3 期)中多少还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婚外恋的困惑与批评的话,在莫怀戚的词典里“透支”这个词的含义就已经相当模糊含混了。莫怀戚以及新生代作家不约而同质疑的是,当旧有的一切标准或者说大多数标准开始变得不再切合实际,甚至是土崩瓦解的时候,究竟什么是透支,究竟为何就不应该享有,就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了。“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为我们的文学画廊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别样的人物,敏锐地反映出当下的生存状态。“新生代”笔下的人物和老一代人相比,也许活得更本位更自由,可在自由的状态下又体会到了新的不自由。在挣脱了束缚之后的失重状态下既有愉悦,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痛苦困惑。旧有的麻烦的解决与新的烦恼的相应相生,人性的多义性复杂性矛盾性,这个曾被掩盖与压抑了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困扰着“新生代”作家,也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文学观念的多元造就了文学审美形态的千差万别与多彩多姿,既有黄发清《城市谎言》(《长江文艺》第11期)、石钟山《夏日机关》(《十月》第6 期)这样的贴近现实揭露体制的弊病与顽症的充满锐气的作品,也有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十月》第5 期)和《谁翻乐府凄凉曲》(《人民文学》第2期)的那种怀旧的把玩式的贵族情结。 有周珺《青水美衣》的空灵飘逸,也有何玉茹的《最后时刻》与谈歌的《无处告别》(《长城》第2期)的实实在在。 阎连科的《金莲,你好》(《钟山》第1 期)对历史与文学的重新诠释有别于刘心武的《妙玉之死》(《时代文学》第2期), 亦不同于张宇的《潘金莲》(《莽原》第3期)。 当“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面旗帜的时候,现实主义的风采依然,许许多多的作家依然在保持着“对平民倾诉的热忱与敬意”(凌耀忠语)。《光和影子》(何立伟《收获》第1 期)表现了大起大落的商海当中人物的沉浮与失落;《婉的大学》(梁晓声《小说家》第5 期)状写了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新的生活观念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到了被称为一方净土的大学校园;何申的《热河官僚》(《小说家》第5 期)以一种平民意识喜剧手法描写了绰号“何大官僚”实则是善良热心的小人物的尴尬与闹出来的各种故事;凌耀忠的《朱先生的婚姻杂碎》(《天津文学》第5 期)以一种恬淡细致的笔调描写了朱先生人生的卑琐与落寞;而苏童的《驯子记》(《钟山》第4 期)用当下生活的符码、以传统的小说手法,讲述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亲情伦理。在传统(文化观念、叙事技巧)与现代(生活形态)之间形成的张力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审美的和文化的价值。
三、文学的大众化与世俗化
随着文学的回归或者说是复位,文学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便成为了一个可以预料的必然结局,而文学的多样化多元化进程自然也在促使着文学的回归。从整体上来说,后撤是20世纪90年代最为显著的叙事策略,这个特点在1999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也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作家,越来越多的读者将中篇小说定位在作为审美艺术门类之一的文学作品本身,而不再等同于其它的什么,或当作其它的什么替代品。许多优秀的中篇小说使人想起了文学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情感的记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却又是恒久永存的场景与画面,细节与动作。很难说清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十月》第1 期)给我们讲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和生活,然而白大省却又实实在在地寄托了芸芸大众的喜怒哀乐,在平实的文字中读者触摸到的是温宛而辛酸的日常生活。莫言的《我们的七叔》(《花城》第1期》、 胡发云的《死于合唱》(《新创作》第6期)、池莉的《乌鸦之歌》(《上海文学》第9期)、王安忆的《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芙蓉》第5期)、 叶广芩的《醒也无聊》(《中国作家》第3期)、 石钟山的《角儿》(《长江文艺》第7期)等小说无论切入生活的角度是历史还是现实, 但透过历史和现实浓墨重彩地写的实际是人,是普通而平凡的人。正如这些小说一样,1999年的中篇小说大多数写的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众,展现的是当下生活中平民大众的悲欢离合,反映在小说中的审美旨趣指向的也是大多数受众的审美旨趣。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先锋性的探索性的小说文本已不再风行甚至难得一见,尽管1999年各文学期刊纷纷打出“文本实验”“凹凸文本”等旗号,但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的小说文本已很少。对话、交流与诉说取代了启蒙,小说家们不再承担新时期甚或“五四”以来的以文学传播思想启蒙的使命,文学于是在审美的意义上开始回归到文学自身,审美感受与审美愉悦越来越受到作者与读者的注重,这似乎表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传统在此遭遇到了当下文学规则的颠覆,崇高、使命、责任弱化,而琐碎与平庸似乎随处可见,小说中最常见的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不过,随着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小说题材必然会有相应的变化,但是小说的精神、小说的实质是不会有多少变化的,小说能感动读者的因素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英雄精神、乐观与豁达、正直与真诚,宽容与理解以及真善美依然动人,在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在一些琐碎平庸的“一地鸡毛”后面,它们也依然动人。能否将这些小人物的家长里短写出内涵写出深度,却又是考较作家小说写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也是作家们在这个时代的责任。1999年虽然没有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以写小人物的家长里短而引起轰动的作品,但也依然不乏优秀之作。王安忆的《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讲述了上海淮海路的一条里弄里一个小女子的故事,表面上看作者好像写得相当随意、琐碎,其实,琐碎只是表相,作者于此建构的,是上海市民阶层芸芸众生的心灵世界。与其说作者热衷于上海的市民阶层的琐细人生,倒不如理解为她实际关注的是生命的本真状态以及生命状态因时因人而异的不同呈现和流向。《光和影子》《石库门之恋》(李肇正《十月》第2期)、《鼻孔里的子弹》(红都《莽原》第5期)、《扬起扬落》(邓一光《钟山》第4期)等等,在这些作品当中, 写的虽然都是小人物的情感与悲欢,然而文本传达出来的作家的心态却是一种大起大落之后的平和与沉思,关注的焦点也不约而同地由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进程转向了人生本身,而不再有意无意地摆出各种姿态,大声疾呼也罢,痛心疾首也罢。可以说,在经历了文学边缘化的痛苦之后,作家们以更为平常的心态创作出来的作品,多了人间的烟火气,多了真诚,多了对现实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关注,少了虚假,少了说教,大众化为它赢得了大众,也赢得了文学的生命力。
1999年的中篇小说中以各种政治事件为题材的也有一些,与以往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它们更多的是以政治事件为背景,着力展现的仍然是人,是特定历史时段特定历史事件里的人,诸如《死亡游戏》(从维熙《收获》第2期)、《1960年的乡村》《1958年的堂吉诃德》等。 可以说这也是后撤的叙事策略的另一表现。文学从中心话语地带撤离,日益的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后撤也使得文学不再是政治的工具,政策的图解,无论这种图解是正向的抑或反向的,并且因为距离而使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双重的可能性。其一,因为从中心的后撤而使自己可以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更为客观更为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政治及政治事件;其二,后撤使文学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并进一步使自身的独立性和文学特质及个性得到发展。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文学的审美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文学进一步回到了文学本身。因为如此,这些小说才写得更为个人、平实,和以前相比,也更为文学,更为丰富和自由,更富有人情味。
四、平面化:令人担忧的深度缺席
文学的回归,甚至是源于某种矫枉过正式地对于政治、理想、道德的有意无意的疏离,导致了一种带有普遍意味的偏差,即文学的庸常化平面化。缺乏激情,缺乏灵性,缺乏想象力,缺乏提升与深度似乎是1999年中篇小说创作的通病。在创作上使人感觉到了在平实当中流于平庸,在摹写当中甘于平面的倾向。譬如官场小说,《选举》(毕四海《人民文学》第1期)、《无根令》(阿宁《人民文学》第7期)、《陈宗辉的故事》(祁智《收获》第1期)、 《买官》(田东照《山西文学》第3期)、《腐败分子潘长水》(李唯《小说界》第2期)写得都相当精彩,相当细腻,但多少又显得单薄了一些。仅仅满足于对现状的描摹(哪怕这种描摹十分生动传神),无疑削弱了文本的内涵与深度。《人生瞬间》(何顿《人民文学》第12期)这篇作品写得生动活泼,平民色彩市井气十分浓厚。故事中的几个人物,老三,老易,健毛,罗平距离读者、距离生活都很近,许多场面也都很逼真,夹杂着方言的口语化叙事让人很有一种现场感,应该说这是何顿的一贯风格,他也特意以一种“反崇高”的姿态探求生活的另一种真实,无聊,琐碎,荒诞,无意义,偶然。然而这种以戏剧化的手法夸张地放大生活的一种真实,在得到了一种真实的情况下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平面化。割裂生活的联系与逻辑,或者忽略这种联系与逻辑,强调片面的真实固然可以给写作和阅读带来快意和冲击力,但我们也不可能不注意到,片面的真实其实是另一种的不真实。《上午打瞌睡的女孩》是一篇具有撕裂力量的小说,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冷漠,人的自私和生活的无奈在此被很好地展现了出来,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他人即地狱的思想虽然不无震撼力,然而这种片面的深刻当然也就阻隔了文本内蕴的丰富和发展。
琐碎感、无聊感、想象力的贫乏有时是以一种极端的、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韩东的《花花传奇》(《花城》第6 期)以一只名叫花花的猫为小说主要描写对象,很生动具体地描写这只公猫的排泄物,身上的跳蚤,这只猫如何进行“手淫”,死了以后尸体僵直成一根绳子状,“我”如何提着装着这具猫尸的购物袋出入城市的各个场所……也许作家在本文中另有深意,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实在难以从中获得什么审美的愉悦,甚至有不知所云之感。此类写作,无异是对文学审美的谋杀。描写对象的无限扩大化,阿猫、阿狗,牙齿与粪便通通可以不加选择地“入画”之后,就难免泥沙俱下,简单地用当下生活的一些符码去置换过去的带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的标记的符码,并非是通往文学的捷径,也远远不能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
放弃对于人生的思考与艺术上的沉淀过滤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照相式的复印机式的反映生活固不足取,想象力的滥用也是值得商榷的。阎连科是一个很有实力也很有潜力的作家,但他的近作《朝着东南走》(《人民文学》第3期)和《耙耧天歌》(《收获》1999年第6期)却让人感到某种虚妄的敷衍。以《耙耧天歌》为例,小说描写了一个母亲以自己的血肉、骨头和脑浆治愈她的呆痴的孩子的故事,作者沉醉于自己对于乡村生活的熟悉与叙事语言上娴熟技巧的时候,却堕入了情节设置上的故作离奇魔幻状的误区,有意无意地在渲染一种愚昧、狭隘、封闭、残忍的氛围与生活。文学的想象力不仅是编织故事演绎情节的能力,而且还应该是一种更为深广的对于人与社会、自然、时间,以及这四者之间的关系的再现与全新的整合能力。当有太多的作家太多地在读者面前堆积着无聊、疯狂、欲望,以至一地鸡毛已经获得了某种经典意义的时候,也许重提理想道德、重提灵魂的光芒并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期待着充满灵性与激情的大气之作,期待着使人的心灵能够更加丰富崇高的作品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