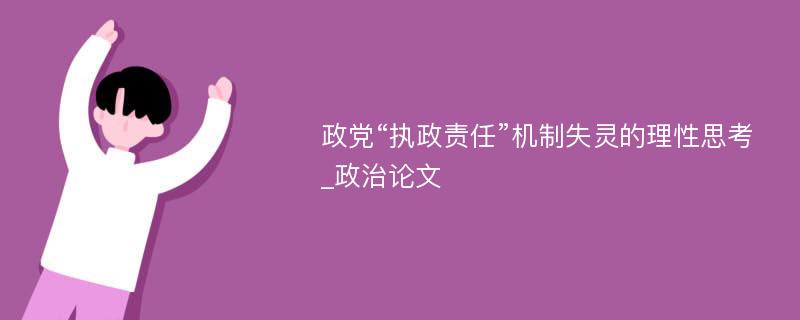
对政党“治理责任”机制失效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理性论文,机制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法治社会里,政党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执政党应承担“治理责任”。一方面是政党受民众所委托,执掌国家政权。由于受选民信任、选举压力的影响,迫使其追求政绩:另一方面,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宣称实行宪政,法律至上,主权在民,在法律上对执政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执政党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运用权力,就必须承担责任。一旦执政党有违法违宪行为,将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制裁,承担如弹劾、通过不信任案、引咎辞职等“治理责任”。
结合政党政治的实际情况,一般认为执政党的责任与义务承担必须实现以下条件:(1)制定了有关政党的法律法规;(2)执政党有违法违宪的事实;(3)有个体或团体对执政党提起诉讼;(4)制裁机关拥有制裁所必须的权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有着极大的困难,“治理责任”承担难以实现;即使受到制裁,现实中的政治腐败、政党集权专制仍然层出不穷,这些使人们对执政党的责任与义务承担机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疑虑。对此,本文将从多角度、理性地探究产生这一问题的原由,并提出若于使执政党有效承担“治理责任”的途径。
一、“治理责任”机制失效的多角度分析
目前执政党“治理责任”承担机制一般是以宪法、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并依靠国家权力机关强制实行。但历史与事实说明,承担机制单独籍借法制的形式,其效果是有限的。
一是法律的局限性极大的降低了执政党“治理责任”机制的有效性。“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有关执政党“治理责任”机制的法律法规尽管作为一种高度助益的政治生活制度,但是,它像其它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一些弊端。其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固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天然的刚性因素,部分源于与其控制相关的程度。对这些弊端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势必造成对执政党“治理责任”承担操作的困难。
政党政治中,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力量依赖于这些组织的和程序所得到的支持范围及其本身的制度化水平。“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表现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一致性上。同样,任何特定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都能以其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一致性衡量。”(注: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第14页.)目前执政党的“治理责任”法律法规水平,它与政党政治相匹配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一致性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僵化性的法律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活动规范错综的政治关系。由于法律规则是以一般的和抽象的术语来表达的,所以它们在个别情形中有时只能起到有限约束作用。正如柏拉图认为,一般性规则,由于它们不具有无限的可变性与复杂性,不可能公正处理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具有无限的可变性与复杂性。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尽管法律是一种不可或缺少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法律具有一般性与普遍性,所以它就可能因此而给解决每个个别案件带来困难。
二是执政党对政治体系的高度控制,使执政党“治理责任”的实施困难重重。执政党在政治体系中,以其独特的政治角色发挥着巨大作用:政府的组织与控制、政治领导的选择与甄拔、利益的表达与汇集、国家权力的运作等。政党在自身的活动中,不仅通过权力和政治制度等体制内形式,而且还运用政治社会化的体制外形式,组织、指导、影响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等领域。实践与事实表明,执政党通过同时操纵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流程,“三管齐下”,能获得效果较好、效率较高的控制。
现代政党的执政方式大抵上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通过大量事实与分析可以得出,政党制度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制度,由于固有的缺陷,未必总是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在形式与内容上有不少地方与其它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相悖,如选举制度、司法制度,以及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原则。“在我们最早的记忆中,政党政治一直是一种精明的和耍手腕的事情,并不总是正当的”(注:吴江、牛旭光著:《民主与政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1年4月第1版,第86页.原载于美国《西北地区报告》第76号,第915页,《史蒂文森选举委员会案》.)。例如两党制首创在英国,在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就英国的政党政治而言,责任内阁制日益嬗变为政党内阁,即实际上是由执政党组阁并由执政党向议会担负政治责任的内阁:一是执政党掌握了议会过半数票,可以驾驱议会的一切,名义上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至上”,实际上执政党决定一切,已变成“执政党至上”;二是内阁既被称为实际进行工作的议会委员会,同时又是首相(党的领袖)领导的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三是内阁集体向议会负责,内阁更迭就是执政党的更迭,只要多数在手,议会的信任投票也只是要挟议会的手段;一旦失去对多数的控制,便根本无法通过诸如调整政策或撤换阁员等办法来维持原内阁;四是内阁有权提前改选议会,日期取决于执政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而且,英国的大法官由执政党的议员担任,他既是当然的上院议长,又是全国首要司法官员和内阁成员,一身兼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职权,没有严格按照分权原则。
三是无治理责任院外活动的崛起使执政党“治理责任”承担的主体模糊不清。“负责任的政党”应当是:“1、为选民提出并阐述各种可供选择的政治立场;2、就有关的各种问题对民众进行教育并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简化,以便于民众作出抉择;3、为公职招募同意政党立场的候选人;4、组织并指导候选人的竞争公职的运动;5、确保当选官员中选后负责任的贯彻执行党的政治立场;6、组建立法机关以确保党对决策的控制。”(注:[美]托马斯·戴伊等著:《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1年8月第1版,第180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负责任的政党”模式已经陷入混乱境地,政党制度以种种迹象表明正在走向衰落;选民们的决定并非主要受政治考虑所驱使。大多选民们根据候选人的形象、当时的好或坏标准以及传统的选举习惯进行投票,而不是在他们对于种种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作为民主决策代理者的各政党本身在结构体制上并不民主,政党本身就是寡头政治家,受活跃的、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的精英集团所左右。活跃的政党精英(例如出席全国大会的代表)所持的政治观点并不反映普通群众的意见。政党意识“通常由少数积极分子操纵,几乎根本不涉及其支持者的大众”(注:[美]托马斯·戴伊等著:《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1年8月第1版,第191-192页.),政党的忠实信徒随时间流逝而日益减少。大多数民众仍保持原登记的状态,以便在政党的预选中好参与选举。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标榜自己为独立的人士,因此,在普选中未经征求政党的意见就进行投票,一票两投的现象也在与日俱增;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已经取代政党,充任政党交流的工具。通过电视,候选人可径直来到选民的起居市。如今,竞选运动基本上是一种传播媒介的活动,候选人不需要党的工作者逐街逐巷地传递他们的信息。
作为政党衰落的一个后果,利益集团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系统。在美国,“法院反对资助政党的命令,主要规则改变,只选出一人的选区的兴起及其院外活动集团的出现,以及选举‘改革’全都有助于摧毁标准的美国政党。它在全国范围、环形公路以内成百上千的特殊利益院外活动集团所取代,这些集团真诚地认为他们有权代表公众说话”(注: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 周叶谦译:《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8月第1版,第265-266页.)。院外活动的崛起,正逐步扩散、在世界各政党政治中蔓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政党及其政党活动被只关注相对狭隘利益、独立于党派之外活动并且没有治理责任的利益集团所冲击。
四是道德约束的无力。法律主要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信念的驱使、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强制来保证实施。执政党的政治腐败促使整个社会道德的下滑、普遍而持久的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权钱交易,滋生的“腐败文化”使社会道德受到严重腐蚀;并且,党派成见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使人的道德堕落,因为在政党中无论判断什么问题都以党的利益为标准。党中成功的领袖,党内就把他当英雄一样地看待;虽有过失,大家也不追究。执政的领袖如果在外交上采用失误的政策,或者反对党以热诚的精神对这种不正当的政策提出反对的质问的时候,本党内公平的批评一定是寂无所闻的;“因为一个人在党中容易为党见所蒙蔽,致不能见到真理,或者恐怕自己批评的话说出来,容易成为反对党拿去作攻击的资料。即使政党的领袖确有滥用权势作循私舞弊的行为,其本党也必定竭力为他掩饰文过的。”(注:[英]詹姆斯·布赖斯 著:《现代民治政体》,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1月第1版,第119页.)
二、机制的转变是使责任承担有效的关键
综上所述,在政党政治里,法律作为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但仅凭借法律这一种社会控制力量显然不够。实际上,执政党的“治理责任”的承担,还存在一些其它可以补充或部分替代法律手段的、能够指导或引导人们行为的其他工具,如权力、行政、道德和习惯等,这些也是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执政党的“治理责任”的承担实现,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外,也应多渠道、多途径的进行。这就要求建立起一种摆脱单纯依靠制度、利用多种手段与工具来实现“治理责任”的新承担机制。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是新承担机制的显著特点。制度是保证国家和社会“合理”存在与有序运行的基本规则。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有关执政党“治理责任”承担的法规,限制执政党权力的行使,最大限度的保护其它社会成员和团体的利益,并将执政党侵害的机会降低到最小程度。在着重“治理责任”的政治制度部署和立法必须遵循的正规形式时,一些非正式手段亦不可偏废。历史表明,除了法律外,道德,习惯传统以及社会力量都是规范行为的力量。要规范强大的执政党的行为,除了制订完善的法规,还必须发展非正式手段,对执政党“治理责任”承担形成一种综合的社会制裁机制。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十分重要,“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注:[美]道路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新的责任承担机制必须实行权力制约与均衡的原则。政党执掌政权,“如果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注: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因此,“分权与制衡”是权力配置合理的重要方法,也是使政党政治“治理责任”承担机制有效的根本原则。这就要求国家权力由不同的组织机构分享,政党之间也应遵循制约与均衡,要求大力培育市民社会,包括各社会团体组织、压力集团。
三、有效承担“治理责任”的若干设想
政党政治价值观的重新建立。综合对政党政治提出的指控主要是四个:政党促使腐败、政党促使行政无能、政党分化社会、政党促成社会矛盾冲突。对政党政治的弊端,华盛顿早就警告过“政党精神”对美国政府体系的“有害影响”:政党“总是分散公共议事机构的注意力,削弱公共管理机构的力量。——政党以没有多少根据的猜忌和种种假警报扰乱社会,引起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敌意,挑起暴动和反叛——它开启通向外国势力和腐败的大门,而这些又通过党派激情的渠道极为方便地进入政府本身。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制于另一国的政策和意志。”(注: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第436页.)“……出于这种理解,党派问题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解决方法。问题的根源在于腐败:政治活动者丧失公民美德和追求私利。如果腐败发生,谋求利用政府权力达到它们自己目标的那些集团就可能控制政治程序。”(注: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 周叶谦译:《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8月第1版,第214页.)根据多元主义理论,党派问题来自于这样的可能性:一个团体,或一个集团,将支配立法或行政的程序并破坏作为构成模式基础的谈判和妥协。党派统治有效地剥夺了其他团体表明它们意见的机会。如果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政治程序将遭到破坏,自由将陷入危险之中。
其实,政党政治应该促进政治发展;这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原因。其具体内容包括:1、维护并实现人权。权利、自由权、自由的人本主义是宪政的本质精髓。宪政承认人自身拥有尊严。并因此有权获得实现其生命潜能的机会。因此,对任何权利,尤其是对那种可能伤害他人的权利都有限制。正如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每个人在行使其权利和自由时,应该只受到那些由法律所规定的旨在确保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适当认可和尊重的限制的约束”(注:转引《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美]卡尔·弗里德里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8月北京第1版,第103页.)2、保护各种利益表达和综合的机构和部门的广泛兴起。有能力在国内外环境中制订并执行集体目标的专门的政治行政领导部门产生和政治行政机构的兴起:用以表达政党、利益集团和通讯工具这类广泛从事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活动的机构的兴起。多元政治体系的标准之一是现代国家中人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程度,另一标准是个人和集团为了进入和影响决策过程而彼此竞争的程度。3、正义与秩序的实现。执政党执政必须实现“(1)国家对正义负有责任;(2)政治正义性构成法的规范批判尺度;(3)公正的法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合法形式”的目标(注:[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3页.)。为实现“公正”地普遍化,必须对自由进行限制,因为“公正的一个起码条件是:禁止任意性”(注:[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9页.)。政党制度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它的实际表现形式——政党政治的价值并不在于追求一种没有限制的权力,而在于最大限度实现政治公正。4、政治体系的维持与适应。政治体系的维持与适应,参与、服从与支持,司法程序的公证,福利、安全、自由都是评价政党政治的重要标准。“维护秩序和……安全……,看来已几乎成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遍目标,它无疑是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所提供的主要价值之一”(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459页.)。
进一步健全有关执政党承担“治理责任”的法律制度。一般而言,目前政党法律法规的形式有宪法条文、选举规范、政党基本法、专项政党法等几种形式。每一类型各有特点,但都必须对政党起到规范、制约作用。从理性化、模式化角度考虑,执政党法治应包括以下制度:
①形式制度:法律规定执政党执政权力的来源(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执政党掌握权力的方式(如法定、选举等),以确定执政党执政资格的合法性。
②构成制度:即执政党有哪些权力,这些权力管理的对象是哪些事务,这些权力如何分配和划分,行使权力的组织及其结构等。
③限制制度:主要是确定执政党权力的界限,侧重于规定、禁止执政党获得某些非法权力。执政党不得采用某些方式行使法定权力等。
④运行制度:执政党法定权力运用行使的过程、方式、规则及程序等。
⑤保障制度:即对执政党权力机构和组成权力机构、执政党个体成员行使权力的法定保障制度。
⑥责任制度:执政党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对执政党法治进行规范和制约的关键。要建立执政党的权力责任制约机制,它应包括政治责任、违宪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⑦监督制度:包括对执政党监督制度、违宪审查等制度。
促进良好法律秩序的形成。执政党法治,除了要有完整的、有序的法律制度以外,更需要一个由法律建立和维护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是社会关系的这样一种状态,它是法律规范和法制实际实现的结果”、“法律秩序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了的法律”;“法律秩序能够被看作是法的实现的终点”(注:[苏]П·С·雅维茨著:《法的一般理论——哲学与社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04页.)法治下的法律秩序的基本目的还是通过法律对法律主体(包括执政党)建立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其内部的各种关系的协调状态。
法律秩序的形成,需要进一步增强组织机构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组织乃是一种权力或权利的物化方式或集合;而法治国家,也可以说是各种合理合法的组织的集合。合理性的组织结构,不仅为法治状态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襁褓,而且为其发展、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哪里社会组织的合理形式居统治地位,哪里就呈现出理想的法制”(注:戈尔丁著:《法律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8页.)。要保障组织体系和各个组织的有效性,从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上说,主要是形成合理的组织特性,即相对的独立性和相互制约性,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有效性和职业性法律组织,尤其是司法机关,独立性应加强。除此以外,进一步培育市民社会,广泛成立各种社会组织、利益团体,沟通利益的表达并建立实现的渠道,形成一种与执政党相对独立性的力量,维护社会组织的利益,促使“治理责任”得以承担。
促进法律秩序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国家及各种法律主体的自觉活动,需要发挥各种法治组织的能动作用,包括有目的地设定理想的法律秩序模式;建立法律秩序由理想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转化机制;启蒙与更新法治观念等。另一方面,法律秩序要求各法律主体自觉或强迫遵守法律,树立对法律自觉的信念和不可动摇的信任;同时国家应加强执法力度,迫使人们强制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