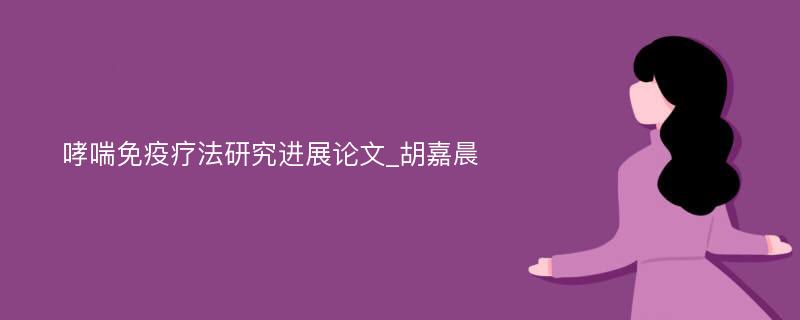
胡嘉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药学部;浙江杭州310016)
摘要:气道炎症是哮喘严重程度和持续性的关键,最近的研究揭示了过敏性炎症中关于树突细胞,Th2细胞因子,Treg细胞以及2型固有淋巴细胞的新的免疫机制,以及靶向气道平滑肌的新的治疗途径。这些进展显示关于气道炎症的新靶向疗法的发展会潜在的带来治疗效益。本文将对现有哮喘免疫疗法以及过敏性炎症和哮喘的新机制和靶点做一个综述。
作者简介:胡嘉晨,男,药师,Email:3414108@zju.edu.cn 电话:15868821799
哮喘是多种细胞及细胞因子参与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以肺部可逆性气流阻塞,气道黏膜炎症和高气道反应性为特征,持续的过敏性炎症是影响其严重程度和持续性的重要原因之一[1]。支气管镜气道活检以及诱导痰检测验证了哮喘气道的炎症性质[2,3]。分析显示,在轻中度哮喘中气道表现为主要由Th2驱动的炎症反应,其由CD4+辅助型T细胞驱动并表达细胞因子IL-4,IL-5,IL-13且与气道内升高的lgE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密切相关。后来的研究发现,在更严重的哮喘病例中会同时存在多种表型,包括之前提到的Th2型炎症,还包括Th17型炎症,可见于中重度哮喘,表现出增加的中性粒细胞水平;在少数情况下会出现寡粒细胞型炎症,该种表型的炎症可能不是受免疫系统调控的,仅见于重度哮喘[4]。
轻度间歇性哮喘的传统治疗按需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β2受体激动剂是运用最广泛的哮喘治疗药物,但仍因临床响应不佳且存在潜在危及生命的副作用受到争议。对于轻度持续性哮喘,传统治疗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与短效β2受体激动剂,中重度患者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与短效β2受体激动剂,发作期间所有患者都可能需要口服糖皮质激素,最严重的患者可能需要定期口服糖皮质激素。轻度疾病患者往往不按处方服用药物,仅在症状发生时使用,而不是预防症状,而病情较重的患者定期服用处方药物但往往不能缓解症状,很显然需要开发新的抗哮喘药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过敏性炎症和哮喘的发病机制,并提供了可能的新治疗方法。本文接下来将总结当前哮喘的免疫疗法并介绍新的机制和靶点。
当前哮喘免疫疗法
维生素D受体。连锁和精细定位研究确定了维生素D受体与哮喘易感性相关。维生素D是人体免疫的重要调节因子,对免疫系统进行微调适当应对过敏性炎症。其通过下调树突状细胞并上调Treg细胞的功能在免疫应答中扮演变阻器的角色。同时,维生素D还在气道平滑肌上表达,高浓度的维生素D可松弛平滑肌并阻止其增殖[5]。维生素D还能促进气道上皮细胞对吸入糖皮质激素的吸收[6]。临床试验数据明确支持了维生素D在儿童哮喘中的使用,一项研究通过衡量住院和急诊的访问量估计维生素D在减少哮喘急性发作方面效果与吸入糖皮质激素相当[7]。但由于对日常哮喘症状控制没有疗效,其在临床上的应用较低。
单克隆抗体。抗IL-5和抗IL-4/IL-13的单克隆抗体已被开发,这些药物减少嗜酸性粒细胞,减少口服类固醇使用并减重度哮喘的恶化。另一类Th2型细胞因子-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确认与哮喘相关的基础上,成为开发单克隆抗体的新靶点,首个TSLP单抗Tezepelumab正在临床试验中被测试。一项IIb期临床试验中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接受tezepelumab的患者年哮喘发作率降低了71%[8]。此外,同时靶向先天和获得性免疫的单克隆抗体也正被开发。该类药物可有效治疗重度哮喘,占成年哮喘患者的3%-10%;缺点在于价格昂贵,因为治疗成本问题在临床应用较低。
过敏性炎症的新机制和靶点
2型固有淋巴细胞。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确认IL-33基因与哮喘相关,其被认为有预警细胞因子的功能[9]。许多关于预警细胞因子(IL-25和IL-33)如何激活2型固有淋巴(ILC2)细胞的研究正在展开。ILC2细胞不仅参与黏膜的稳态,还与炎症反应的启动有关。有研究显示神经肽受体基因Nmur1在小鼠ILC2细胞中高表达,且在IL-25刺激后NMUR1的配体神经介素U(NMU)可在体外激活ILC2细胞,体内联合给予NMU与IL-25会极大增强体内过敏性炎症[10]。这种炎症反应同样在Th2哮喘中发现,因此,NMUR1信号通路可能成为合适的治疗哮喘的新靶点。与许多其他免疫机制一样,阻断这种反应会不会产生感染等不利影响即如何安全的使用这种机制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目前而言,相关试验尚处在基础的研究水平上。
树突状细胞。关于过敏性炎症中抗原递呈细胞的调节也取得了进展,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根据树突状细胞类型的不同通过不同的机制调节其功能,如促进CD103+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产生Ⅰ型干扰素,并减少CD11b+经典树突状细胞产生促炎细胞因子[11]。和维生素D受体一样,mTOR还影响其他许多免疫过程,如控制效应T细胞数量,B细胞应答以及其他一些过敏性炎症相关的潜在免疫过程。最近的研究发现小鼠模型中mTOR同时调节肺内CD103+树突状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的代谢和积累,而虽然肺中mTOR缺陷的CD11b+树突状细胞数量没有变化,但这些细胞将代谢重组从诱导嗜酸性粒细胞Th2型炎症向嗜中性的Th17型应答倾斜,后者具有更高的临床严重程度和更差的预后。在mTOR缺陷的CD11b+树突状细胞中检测到脂肪酸氧化升高及几种促炎细胞因子的生成。脂肪酸氧化升高抑制脂肪酸氧化可限制平衡向Th17型应答倾斜而中和IL-23可以逆转该进程恢复嗜酸性粒细胞表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该进程依赖CD11b+树突状细胞[11],靶向经典树突状细胞可能对过敏性炎症的治疗有益,但距离相关药物的开发仍有许多研究要做。
Gq蛋白偶联受体。G蛋白偶联受体是细胞膜表面最大的一类跨膜蛋白,与大量正常生理活性密切相关,其异常的活化或表达,也是多种重要流行病的发病机制,目前,靶向单个G蛋白偶联受体的药物被用于降低呼吸道张力,然而治疗效果通常有限。一项研究假设药理阻断Gq蛋白可以作为一种中枢机制来实现有效的诱导支气管松弛,发现FR900359为Gq蛋白的一种膜渗透性抑制剂,可有效抑制小鼠和人气道平滑肌细胞的Gq信号[12]。FR900359在小鼠,猪以及人体气道组织的体外试验中显示能阻止支气管收缩并引发持续呼吸道松弛,同时在小鼠哮喘模型体内减少了呼吸道阻力而不会对血压和心率产生急性危害[12],提示Gq蛋白的药理阻断可能是哮喘疾病支气管扩张的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其能否成为支气管扩张剂的新的选择,仍需更进一步试验以确定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这些研究可能持续许多年。
总结
传统的抗哮喘疗法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逐步修订推广对防治哮喘取得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而免疫疗法当前在哮喘的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不多,主要是因为其疗效(维生素D)和成本(单克隆抗体)的关系,因此仍需研究新的抗哮喘疗法。近年来关于哮喘和过敏性炎症机制和靶点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这些研究很多都是基于对全基因组分析和筛选发展起来的。这些新研究的治疗方法和靶标有很大潜力,但是也存在问题。首先,随着免疫疗法引入治疗,如何精准预测患者对免疫疗法是否敏感也是治疗成功并降低治疗成本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当前对哮喘的分型仍非常原始,应当增加分子表型的应用以与特定的药物治疗反应相联系。其次,虽然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的重度哮喘患者对新的治疗方法需求迫切,临床试验仍需确定新免疫疗法对包括轻中度患者在内所有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最后,跟单克隆抗体类似的治疗成本问题仍会限制新免疫疗法的应用。只有明确降低新免疫疗法的治疗成本,才能真正推广过敏性炎症及哮喘的精确治疗。
参考文献
1. Durham A L, Caramori G, Chung K F, et al. Targeted anti-inflammatory therapeutics in asthma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J]. Translational Research, 2016, 167(1):192.
2. Poston R N, Chanez P, Lacoste J Y, et al. Immunohist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ellular infiltration in asthmatic bronchi[J]. 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 1992, 145(1):918-21.
3. Pavord I D, Pizzichini M M, Pizzichini E, et al. The use of induced sputum to investigate airway inflammation.[J]. Thorax, 1997, 52(6):498-501.
4. Israel E, Reddel HK. Severe and Difficult-to-Treat Asthma in Adults[J]. N Engl J Med, 2017, 377(10):965-976.
5. Himes B E, Koziolwhite C, Johnson M, et al. Vitamin D Modulates Expression of the Airway Smooth Muscle Transcriptome in Fatal Asthma[J]. Plos One, 2015, 10(7):e0134057.
6. Xystrakis E, Kusumakar S, Boswell S, et al. Reversing the defective induction of IL-10–secreting regulatory T cells in glucocorticoid-resistant asthma patients[J].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06, 116(1):146-155.
7. Brehm J M, Schuemann B, Fuhlbrigge A L. Childhood Asthma Management Program Research Group. Serum Vitamin D levels and severe asthma exacerbations in the Childhood Asthma Management Program study[J]. Journal of Allergy & Clinical Immunology, 2010, 126:52-58.
8. Corren J, Parnes J R, Wang L, et al. Tezepelumab in Adults with Uncontrolled Asthma.[J]. N Engl J Med, 2017, 377(10):936-946.
9. Yang D, Han Z, Oppenheim J J. Alarmins and immunity[J]. Immunological Reviews, 2017, 280(1):41-56.
10. Wallrapp A, Riesenfeld S J, Burkett P R, et al. The neuropeptide NMU amplifies ILC2-driven allergic lung inflammation.[J]. Nature, 2017, 549(7672):351.
11. Sinclair C, Bommakanti G, Gardinassi L, et al. mTOR regulates metabolic adaptation of APCs in the lung and controls the outcome of allergic inflammation[J]. Science, 2017, 357(6355):1014.
12. Matthey M, Roberts R, Seidinger A, et al. Targeted inhibition of Gq signaling induces airway relaxation in mouse models of asthma[J].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7, 9(407):eaag2288.
论文作者:胡嘉晨
论文发表刊物:《医师在线》2018年第1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9
标签:哮喘论文; 炎症论文; 细胞论文; 树突论文; 受体论文; 免疫论文; 气道论文; 《医师在线》2018年第14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