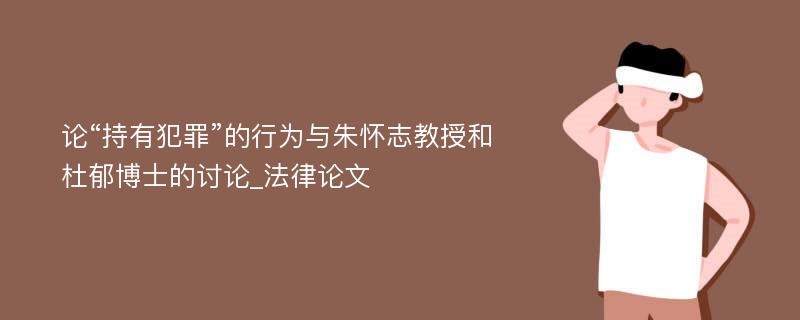
也论“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兼与储怀植教授、杜宇博士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博士论文,方式论文,储怀植论文,杜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08)05-0117-04
在“持有犯罪”引入国内刑法理论之前,犯罪行为方式就是作为和不作为两种类型。在“持有犯罪”引入国内刑法理论之后,围绕着犯罪行为方式到目前为止形成了第三种行为方式肯定说与第三种行为方式否定说:前说认为在作为与不作为这两种行为方式之外,犯罪行为还有与之并列的融作为与不作为于一体的第三种行为方式①;后说又分为:(1)“作为说”,即认为持有属于作为的范畴②;(2)“不作为说”,即认为持有属于不作为的范畴③;(3)“择一说”,即有的情况下是作为而有的情况下是不作为[1]。“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究竟有哪些类型呢?由于“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是该类犯罪的首要问题,故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由于储怀植教授率先提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是与作为和不作为并列的所谓第三种行为方式[2],现又有杜宇博士以“类型化思维”为其作“有力”佐证[3],故本文同时也是与二位学者商榷。
一、“持有”的“作为”定位
(一)“持有”不属于第三种行为方式
笔者认为,“持有”是否应为犯罪行为的第三种方式,首先应着眼于“持有犯罪”的行为特征。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积极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其现实表现是行为人的直观有形的身体动作或物理运动,如抢劫、盗窃等。而“持有犯罪”,以非法持有毒品罪为例,我们显然不能说毒品持有者没有对毒品实施动作,因为持有者恐怕暴露总是要对毒品进行包装或再包装、寻找藏毒地点、藏匿毒品、经常或适时转移毒品。由此看来,我们把“持有”归属于作为或把“持有犯罪”归属于作为犯罪,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为什么不可以说非法持有毒品罪是行为人积极实施刑法禁止持有毒品行为的犯罪呢?在“持有犯罪”中,不仅有“动”,而且还有“静”,但笔者认为,“持有犯罪”中的“静”是以“持有犯罪”中的“动”为参照物,是指持有人对非法持有物作出的人体动作过程中的停顿状态。并且,“持有犯罪”中的“静”恰恰是其“动”的后续性状态并可作为“结果”反过来说明其“动”,而刑法规制“持有犯罪”恰恰是针对其“动”,因为如果“持有犯罪”始终处于“静”之态,则其便不可能引发或“延伸”出所谓“下游犯罪”,或不具有引发或“延伸”出所谓“下游犯罪”的危险性,从而“持有犯罪”本身也就不成为其为犯罪,即不具有犯罪化的必要性。
“持有”是否应为犯罪行为的第三种方式,还要来分析一下持“持有”是犯罪行为的第三种方式这种观点的理由及其推论。在率先提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是第三种行为方式的储怀植教授看来,“以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为准绳,可能存在三种形态:动;静(静止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动静相融。‘作为’具有动的行为特征,‘不作为’具有静的行为特征,‘持有’具有动静结合的特征。”[4]可见,储教授是把“持有”兼具“动静结合的特征”作为“持有”是犯罪第三种行为方式的理由。由此,我们能清楚地看出论者的推论过程:由于动是作为的行为特征,静是不作为的行为特征,故动静结合的行为既不完全属于作为,也不完全属于不作为,而应与作为和不作为相并列而构成第三种行为方式;由于“持有”正好具有动静结合的特征,故其属于第三种行为方式。储教授的理由及其推论貌似严密,但却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论者在动和静之外把动静相融或动静结合作为物质运动的第三种形态,无论在物理学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都是讲不通的,因为在此两门科学上,物质存在形式只有两种即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既然物质运动包括人们实施某种行为并不存在所谓的第三种形态,则以所谓第三种形态的动静相融或动静结合来论证人们行为的第三种方式便产生了逻辑上的错误,即“前提虚假”或“理由虚假”而“推不出”。第二,按照“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物理学和哲学原理,人们实施某种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存在着动静相融或动静结合,这原本是一种正确的认识。但是,“持有犯罪”中的动静相融或动静结合在本质上有别于储教授所说的动静相融或动静结合。如上文分析,“持有犯罪”中的“静”是以“持有犯罪”中的“动”为参照物,是指动的停顿状态而言;而储教授所说的动静相融或动静结合的“静”却是指向了不作为犯罪中的“静”。不作为犯罪中的“静”是以应为某种法律义务为参照物,是指行为人在该法律义务面前的消极状态。因此“持有犯罪”中的“静”与不作为犯罪中的“静”显然不是同一概念。那么,储教授用“持有犯罪”中的“静”指向不作为犯罪中的“静”或用不作为犯罪中的“静”替代“持有犯罪”中的“静”,则明显是违背了逻辑学上的混淆概念错误。以混淆了概念的前提去推论,其逻辑错误仍归结为“前提虚假”而“推不出”。如果遵循逻辑上的“同一律”,“持有犯罪”中的动静相融或动静结合应是放在“持有犯罪”行为的内部结构中去考察,而不是放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实际上,任何犯罪都存在着“持有犯罪”中的“动静结合”,即“动静结合”是任何犯罪的自然特性,因为任何犯罪都是一个过程,而此过程之中总有行为的停顿。只因为如此,“动静结合”便无法构成一种独立的所谓第三种行为方式。
储教授除了通过所谓“持有”具有作为的动的特征和不作为的静的特征来论证“持有”应为犯罪行为的第三种方式外,还通过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概念关系来论证其观点,如“论证持有是第三种犯罪行为形式这一论点的关键首先要说明:刑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关系不等于形式逻辑中‘白’与‘非白’的关系。非白在逻辑上是对白的全称否定判断,二者之间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形,这是形式逻辑上的排中律……然而刑法上的‘不作为’与‘作为’的关系并非如是……刑法上的不作为并非是刑法上的作为的全称否定,所以二者不存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关系。”[2]411笔者认为,否认刑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之间是全称否定判断是不正确的,因为刑法上的作为是不应为而为,不作为是应为而不为。所以,同样作为犯罪行为的种概念,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概念关系是全异关系。但是,在形式逻辑中,具有全异关系的两个概念之间又可具体分为两种关系即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矛盾关系是指具有全异关系的两个种概念外延之和等于其属概念的外延的情况,如人可分为男人、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全异关系中的矛盾关系。矛盾关系意味着一个属概念之下只有一个正概念和一个负概念,而不会再容纳第三个种概念;反对关系是指具有全异关系的部分种概念的外延之和小于其属概念的外延的情况,如财产犯罪可分为抢劫罪、诈骗罪和盗窃罪,其中任意两个罪之间都是反对关系。反对关系意味着具有全异关系的两个概念之间可以容纳第三个或更多的种概念。那么,刑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是全异关系的哪一种呢?只能是矛盾关系而非反对关系,因为刑法只是把不应为而为和应为而不为这两种情况作为犯罪对待,即刑法规范中只有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的相对,此如霍布斯所言:“罪行……是以言行犯法律之所禁,或不为法律之所令。”[5]在储教授看来,“犯罪行为的典型形式‘作为’的涵义是刑法禁止实施的行为(违反禁止规范)。而‘不作为’的组成词‘作为’恰恰是刑法要求实施的行为(违反命令规范)。‘持有’属独立的第三犯罪行为形式,既非作为也非不作为。”[6]按照储教授之见,“持有”犯罪就没有规范可违反了,因为在刑法中规定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授权规范不可能为“持有”犯罪所违反,而在命令规范与禁止规范之外又不存在着独立的第三种规范或掺杂命令规范与禁止规范的混合规范。如此,则“持有”犯罪将因无规范可违反而不成其为犯罪了。或者这样来看问题,当把作为型犯罪与禁止性规范相对应而把不作为型犯罪与命令性规范相对应,同时又把持有型犯罪的行为方式说成“既非作为也非不作为”即作为与不作为的混合体,则等于说与持有型犯罪相对应的是既禁止人们做什么又命令人们做什么的混合规范,即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的混合体。试问,这样的混合规范能够保障公民的行动自由并实现刑法的应然机能吗?实际上,之所以有人坚持持有型犯罪的行为方式是融作为与不作为于一体的所谓第三种行为方式,是因为同样坚持持有型犯罪的“持有”是第三种行为方式的杜宇博士等学者强调刑法“类型化思维”的结论[7]。按照杜宇博士所强调的“类型化思维”,既然持有型犯罪的“持有”是“动静结合”,则“持有”既不能归属于单纯的“动”,也不能归属于单纯的“静”。而若将“持有”非要在“动”与“静”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归位,则既不可能,也不太必要。那么,“持有”干脆“自成一类”。在笔者看来,刑法“类型化思维”确有其合理性并值得提倡,但并不能以此得出持有型犯罪的行为方式是融作为与不作为于一体的所谓第三种行为方式,因为作为和不作为本身又何尝不是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括?按照西方大陆刑法理论,无论是违法类型,还是有责类型,构成要件都是犯罪的“类型”[8]。那么,当作为或不作为本身占据着构成要件的核心,则作为或不作为本身也应是“类型化”的存在。而如果应该把作为和不作为本身也看成是刑法“类型化”思维的体现,则融作为与不作为于一体的所谓第三种行为方式体现的是“类型化”还是“类型化的混合”或“类型化的混杂”?因此,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而既然作为与不作为之间是矛盾关系,故把“持有”作为与之并列的第三种行为方式是缺乏逻辑根据的。之所以如此,是由刑法规范的种类所决定的。在笔者看来,“持有”只不过是犯罪行为的作为方式中的一个“方式”即作为的一种样态而已。假如我们能够采取某种标准从作为方式中再划分出“持有”来,则作为是属概念,“持有”又是其种概念而已。
(二)“持有”也不属于不作为
有人说:“从持有本身看,既然法律将其规定为犯罪,那就意味着法律禁止这种状态的存在,而这种禁止暗含着当这种状态出现的时候法律命令持有人将特定物品上缴给有权管理的部门以消灭这种持有状态。因此,在法律禁止持有某种物品的情况下,持有该物品的人就负有将该物品上缴有权管理该物品的部门的义务。如果持有人违反这种义务,不主动上缴该物品,而是继续维持持有状态的存在,那就是刑法所禁止的不作为。”[9]笔者认为,“持有犯罪”的对象是违禁品,而“违禁”二字已经表明着对特定物品不得非法持有之禁令,而“持有犯罪”的刑法规定便是不得非法持有之禁令的法律形式。而恰恰当行为人以作为方式实施非法持有时,才构成对禁令的违反,即不作为本身无法构成对禁令的违反。试问,看到违禁品不予捡拾,更不予藏匿,能构成“持有犯罪”吗?按照“持有犯罪”的规定,当行为人一实现非法持有状态时,则即构成犯罪,此时仍言行为人负有上缴违禁品的义务岂不是说刑法既要处罚又要期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从我国现有的所有法律规定来看,公民并不负有发现违禁品并积极将其上缴的法定义务,而“持有犯罪”的规定只不过是喝令其不要积极非法持有罢了。因此,把“持有犯罪”当作不作为犯罪是经不住推敲的。
二、“持有”的“作为”定位的意义
以往凡是持“持有”应归属于行为方式中的作为的观点的人都未指出这种归属确定的意义所在,而这无疑减弱了其论证力度。对“持有犯罪”的“持有”在行为方式中作出恰当定位将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一)对“持有”行为方式的恰当定位能够维护刑法行为理论的完整性
虽然持第三种行为方式的人也是在行为这个大前提之下讨论“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问题,但由于其自觉不自觉地分别将动与作为、静与不作为、动静结合与所谓第三种行为方式相对应,这就破坏了只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的行为的完整性。对行为完整性的破坏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容易招致纯自然意义上的“状态”即其所谓动静结合中的“静”成为刑法的否定评价对象,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10]
(二)对“持有”行为方式的恰当定位能够强化“持有犯罪”的立法理由
中外刑法之所以规定“持有犯罪”,立法者主要是以预防相关犯罪为立场,如功利主义的杰出代表边沁在论述“施恶能力之剥夺”和“为防止主要犯罪而禁止次要犯罪”时所认为,立法者的策略与守护士相似。禁止贩卖、制造伪造货币的工具、春药、易于隐蔽的武器、或其他可用于赌博的工具,禁止制造、持有某种补网或者其他陷套野兽的工具,隔绝对恶的刺激——犯罪的工具与媒介,这些方法犹如在窗台上安装铁栏,炉火旁设置网格,勿将锋利和危险的工具放在儿童所能触及的地方。而除了确定主要犯罪之外,还要确定作为主要罪行的预备和表明预备意图的大量次要罪行。因此,一个警惕性强的立法者就如同一个有谋略的将军,他应仔细侦察敌人的所有情况,从而破坏和打烂敌人的计划。为此,他对荷兰传闻的一种形状如针的杀人工具的制造、销售和持有行为应作为谋杀罪的从行为予以处罚[11]。预防尚未发生的相关犯罪是立法者规定“持有犯罪”的主要立场,而报应有些难以证明的相关犯罪则是立法者规定此种类型犯罪的另一立场。如我们所知,在我国现行刑法中,非法持有毒品罪是被安插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这一节罪之中,这表明立法者另有目的,那就是不使狡猾而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走私、贩卖、运输或制造毒品罪行的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即非法持有毒品罪烙上了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的印痕。推定立法者的这一目的是有现实根据的,那就是当一个人持有毒品时,该毒品既可以是将被用来走私、贩卖或运输,也可以是经过走私、贩卖、运输或制造而来。无论是预防相关犯罪,还是报应相关犯罪,刑法规定“持有犯罪”多少都有点“有罪推定”之嫌,因为被意图预防的相关犯罪是尚未发生的,而被意图报应的相关犯罪又是难以证明的。因此,“持有犯罪”也就成了“影子犯罪”。对于这样的“影子犯罪”,刑法规制的理由不能“莫须有”,那么,我们仍应回到这类行为本身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上来。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同一法益,作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总是重于不作为方式。这时,“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归属确定的意义在立法规制的理由方面便体现了出来:只有积极的作为或可以视作难以证明的先前罪行的较为确凿的掩饰,或可以视作尚未发生的后续罪行的较为确凿的先兆,而持有人的人身危险性才能“厚重”到犯罪的程度,从而“持有犯罪”作为“影子犯罪”的“有罪推定”色彩才能被根本抹去。
(三)对“持有”行为方式的恰当定位能够实践并明晰刑事责任的证明理论
在笔者看来,在刑事诉讼中,原告一方,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自诉人,都负有犯罪行为的事实性和违法性的证明责任,而如果将“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定性为纯粹的不作为,则其事实性和违法性将无从证明,因为在一个人的住处偶然搜出另一人放置而该人自始不知的毒品,我们能证明这种场合之下犯罪行为的事实性和违法性吗?因此,我们只有将“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定性为作为,才能通过持有者积极的身体举动来证明“持有犯罪”的事实性和违法性。探究“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归属的意义所在等于为明确“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归属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这是以往对“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持作为观点的人所忽略的。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探讨“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问题并非无聊的文字游戏,而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本文开篇便说“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问题是该类犯罪的首要问题,道理便存于此。
总结全文,“持有犯罪”的“持有”不能归属于所谓的第三种行为方式,这是刑法规范的种类所决定的;“持有犯罪”的“持有”只能归属于行为方式中的作为,这是“持有犯罪”的行为结构所决定的。而对“持有犯罪”的“持有”在行为方式中作出恰当定位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着相当的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2008-06-11
注释:
①关富金博士学位论文:《持有犯罪研究》,北京大学法学院2001年,第31-32页。
②陈英辉硕士学位论文:《非法持有犯罪研究》,武汉大学法学院1998年,第26-29页。
③王立重硕士学位论文:《论持有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95年,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