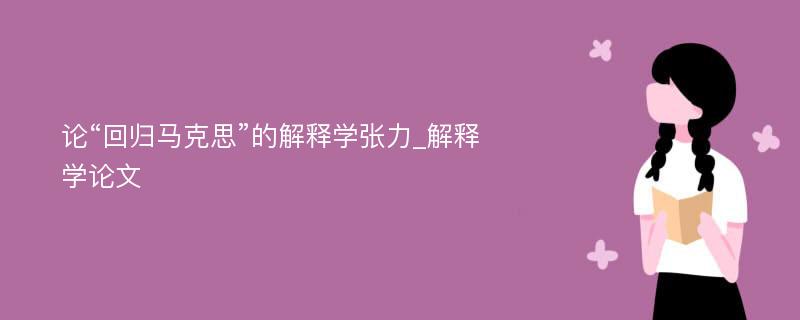
论“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马克思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作解释学上的区分,差不多是肇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回到马克思”是这一思想倾向显白的意图。在本文中,“回到 马克思”哲学的题旨,倒不是基于采用一种类似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重新对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做“原本”与“副本”的区分,而是意在大致地描述出“贴近” 马克思的文本自身所规定的某些解释学原则,并由此重新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回到马 克思”这一口号的实质意义在哪里?
一
经常有人谈论说,“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不同于“回到康德”,它不是一个认识论观念,它表达的是一种“复原”或“重建”马克思的解释学观念。但是,人们并没有留意的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种解释学观念上的“重建”和“复原”,就差不多总是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这样貌似文学的问题入手的。一旦解释者被抛入这样的问题,就会面临当代解释学的那个尴尬处境——要在他明白那解释所要说明的东西之前先去明白那解释: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是解释者所要指涉或重新做解释的“对象”,解释者必须思考马克思所思考的东西,以免有所歪曲。但是,这个所谓“对象”本质上是非对象的,非现成的,因为它所涉及的完全不是既定的客体,如果它已 经是对象化的,从而也就是一个既定的客体,那么解释者就无须重建它,要对某一既定 客体的把握只需有足够眼力就行;另一方面,解释者在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时候,总已经 就马克思哲学这一名词的意指有所领会,有所指引,有某些最初的理解,简言之,有所 对象化。我们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第9节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独白这样 一个最能纯粹地体现表象的独特性的活动中,也要出现对词的哪怕是想象的表象。”( 注:参见张详龙:《朝向事情本身》,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因为,名词 需要指涉,要不是总已经有所特型化、对象化,或者指涉某某类型的事物,往后的解释 、概念的理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真实的情况往往是,解释者一开始思索,因为一些 经典的段落固定在他的思维中,他往后对文本的解释仿佛就是对这些经典段落的安排。 照此理解,由此所发生的解释学过程就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视界融合的过程,也同时就 是趋向于敉平阅读与误读界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谁也控制不了的。
所以,伽达默尔的误读(理解)即为解释的理论有足够的说服力,原因就在于此。这样,彼特洛维奇的如下忠告的理由就既不特别又可能是无害的,他说:“不能把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注:B·彼特洛维奇:《现代哲学》,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这里,我们除了赞同彼特洛维奇的论断外,还需要进一步提醒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也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先驱一样,为其他人开辟了他们自己并不曾走的道路,以至于马克思不可能在后来的追随者身上重新认出自己。“聪明的”读者总能就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见解添枝加叶,采取立场,讨论,阐释,等等;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总会出现比一个学说的创始人的意图所包含的更多或更少的东西。这种错失能否被允许,必然有一个否定性的评判标准就是,尼采所做的说明:文本在其纯粹的和真正的形式上是无法接近的(有如康德的物自体)。一般说来,解释学观念就是在与“对某一话语的一切参与活动都是可公度的”这一认识论假设作斗争。(注:参见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8页。)
这一解释学观念涵括了马克思被各种各样的方法所解读、并常常被阅读者同化到自己信仰的微光迷蒙中去的可能性。的确,在面对什么才是马克思的著作中传授的真正教诲这一问题时,有传统的、肤浅的和外在的解释,也有聪明的、深入的和精到的解释,这 两种解释往往又是冲撞的。仅就我们随意地宣称“那是马克思的思想”或“这儿我感觉 到黑格尔的影响”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者的意见争执,就会如同传说中国王的三个 女儿都说自己从父亲那里得的指环才是真金的纷争一样,也就必然地令人沮丧。更何况 彼特洛维奇发现马克思主义被怀揣不同思想动机者致命地玷污了,究竟该听信哪一种说 法呢?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误读已成当今解释学的格言,那么为了真正回到马克思而不遭到挫败,那种不急于从马克思那里寻得现成的教条的做法也许就显得比较聪明。因此,在我们还不太懂得怎样阅读马克思的时候,施特劳斯所倡导的对待经典思想文本的理智上的诚实、敬重态度及其作为解释者的美德倒是值得效法。施特劳斯对经典文本充满深情,他将对真理的追求视为一种共同的、通过交往产生的追求。经典作品这个“观念”在施特劳斯的著作里就是一种通向现实之窗的交往形式。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施特劳斯相信,“通过了解修昔底德的智慧,我们才智慧起来;但如果我们在了解修昔底德的同时,没有认识到正是通过了修昔底德我们才逐渐变得智慧,那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变得智慧的,因为智慧与自知是不可分离的。通过了解修昔底德,我们会越来越智慧,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修昔底德的智慧。”(注:转引自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从施特劳斯这里的慎思明辨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即使我们当中的数不清的解释者把坚持本真的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却又因为声称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以某种方式隐含了评价原则的理论知性(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范畴,那些评价原则与知性范畴一道都是可变的,它们随时代而变。于是,几乎不用说这样的声称,便不可能阻止那些辩驳去怀疑马克思主义具有表达当代世界变化的能力。
这里的问题同时也就表现为,仅仅是要把马克思拿来拷问,并根据他本人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来审读他留给我们的著作。这么说来,我们也就可知,何以一般地说来,上述的那种看法总是未能使马克思哲学走出被边缘化的危机,反而最终稳当地坐落于现当代 之历史主义的“洞穴”,而且,首要地,它只是衷情于提出种种要求使我们看到马克思 那里没有注意到的或者一直缺少的东西,于是,无论是因马克思盲目而造成的“看”的 缺陷,还是因我们占了后见之明而洞察秋毫,在把眼睛当作工具的哲学中,比谁视力好,“这大约真是我们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套路”(注: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二
在我们梳理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的关系问题时,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面对一切思想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之现代性状况,施特劳斯解释学显现出了强烈的“还原性”和“排他性”。他相信通过贴近阅读(close reading),或坚持作者的原意应该最终支配我们的阅读的方法,能够达到对文本的完全复原或重建,而这种“复原”作为一种“解释”,应该是诸多解释当中最好的一个。不言而喻,在伽达默尔等人那里只是可能的情形,在施特劳斯的思想当中却是现实。这显然是,施特劳斯解释学受到“与古典解释学之绝对主义有染”的攻击的原因。伽达默尔说,虽然“存在着足够的理由使我们不要把非历 史地思维的可能性看作空洞的可能性”,但是,施特劳斯坚持以过去的作者理解自己的 方式来理解他们,就“低估了一切理解所具有的困难,因为他忽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陈 述辩证法的东西”(注: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1999年版,下卷 ,第704—705页,第703页。)。依伽达默尔看来,施特劳斯与理解的历史性作斗争,他 所批判的,正是“历史地”理解传统思想所要求的,即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我们无法像 先哲们领会自身那样领会他们。在施特劳斯这一批判的背后,有着近代启蒙主义和传统 思想追求永真的主导观念。至此,“他反对他所谓的历史主义的论据首先也是在历史的 基础上提出来的”(注: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1999年版,下卷 ,第704—705页,第703页。)。
这一矛盾,如果是被伽达默尔以一种误解的方式而解说出来的,那么它将导致误解了的施特劳斯形象:他是一个致力于建构一种阅读所有文本的普遍方法理论的、且在气质上靠近狄尔泰那样的浪漫解释者。
依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把马克思作为解释学思考的对象,就像马克思理解自身那样来理解马克思。这仅仅只是一个真诚而保守传统的诉求,它不仅会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解 释者来说,其头脑远不是简单的像“白板”,而完全暴露于当代解释学的反诉之中,而 且它所要越过理解上的历史藩篱进行哲学对话的可能性的最终依据,仍然浸染于现代历 史意识之中。换用阿尔都塞的讥评,这是虚妄的“无辜的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可以说是以怎样“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为中心引线而展开的。阿尔都塞明确地将回到马克思的意图称之为“有罪的阅读”,即他表达为从哲学角度阅读《资本论》,在他看来,只有在《资本论》中,才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4页,第6页,第6页,第13页。)阿尔都塞引用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的寄语指出,“为了试图理解马克思 究竟思考过什么,我们最起码应该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从而‘[为]自己思考’马克 思究竟思考过什么”(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页,第246页,第169 页,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23页。)。这里显示了:当代解释学的阅读理论与 阿尔都塞的“有罪”阅读理论起码是并行不悖的,但事实上并不相互覆盖。伽达默尔的 思想是从海德格尔来的,并结合了一些黑格尔的东西,阿尔都塞的深层理论背景则源自 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阿尔都塞将回到马克思比况于回到弗洛伊德,回到弗洛伊德意即 回到“已经建立、确立和巩固在弗洛伊德自己身上的这个理论”(注:阿尔都塞:《列 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18页。),因 而,当阿尔都塞假定《资本论》包含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 家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我们在意识层面上能意识到、观察到、并能够检验的现实问题 ,但是阿尔都塞却从无意识层次来解读马克思的正文。
依阿尔都塞看来,在传统的阅读观念中,作者在文本中清晰地表述了一切,读者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只在一旁被动地理解。这种对文本“真相”的解释只是一种被动的“观照”、“反映”,这一阅读观念除了忽视意识层面上的听、读与说、写不具有直接性和完全性的同时,也忽视了历史结构对作者的客观作用。马克思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敏感于某种哲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含义,我们只是从马克思开始,才从理论上对传统的阅读和写作的含义产生怀疑,马克思以与弗洛伊德、尼采本质上同样的方式,看到了解决 人的异化和压迫这一人类的匮乏问题过程中所产生的虚假意识,“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 克思,就是因为他建立了历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历史差别的哲学,而这一 切归根结底是在破除阅读的宗教神话的过程中完成的”(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 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 、24页,第6页,第6页,第13页。)。
半吊子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所说的“阅读的宗教神话”,就是试图抹去阅读与历史性的距离。比如,黑格尔从存在中直接读出本质的“绝对知识”和青年马克思用来缝 合工人被异化的劳动本质的直接的价值预设,都抹平了理论阅读和现实历史的距离。相 反,《资本论》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这些距离和间隔使它们自身的效果阅读不出来并 使对它们进行的直接阅读的幻想达到其效果的顶点:拜物教。阿尔都塞批判的焦点就是 这种令阅读者放弃自己的历史性,或明明是有罪的阅读,却自以为是无辜的阅读的拜物 教。所谓一打开马克思的著作读一遍,就马上产生“我正在与大师直接对话”的狂喜, 这正是阅读拜物教的幻觉效应,它本质上乃是“宗教阅读方法”(读《圣经》那样的宗 教般神秘阅读方法),从这幻觉中醒来,阿尔都塞要求我们做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 ,“我们必须转向历史,才能把这种读的神话消灭在它的巢穴中”(注:参见路易·阿 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版,第4—5、24页,第6页,第6页,第13页。)。在阿尔都塞的眼中,一个好的阅读者 将会提防幼稚地阅读文本,这种阅读遗忘了历史结构的客观作用,预设了作者的独立存 在和阅读者的直接阅读。
当阿尔都塞认定,马克思假定了历史结构不能与明显可见的关系相混淆并且对它们那隐蔽的逻辑加以直接阅读的时候,他将按照“这个”(马克思的)方向,发明一种新的阅读方法,来替换掉那种仅仅使“马克思变成了斯密”的旧的阅读方法,这种新的阅读方法不仅使马克思能够提出对古典经济学而言“从来没有被提出来的问题”,而且作出正确的回答。(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4页,第6页,第6页,第13页。)援这种由问题结构牵引,并且把隐藏在文本里的某些思想症候地显示出来的痕迹(包括表述中的沉默、某些概念的阙如、它的论证的严格性的空白等等)作为线索去阅读,就会“使语言表层的连续性解体”、“救出被旧的问题结构压抑的新的问题结构”、“给予被隐藏的言说以生命,并进行重构。所谓阿尔都塞的马克思研究,自始至终是根据症候性解读的马克思研究”(注:参见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第253—255页。)。当成年的马克思,确切地说,阿尔都塞的那个马克思找到原文深处的无意识结构时,阿尔都塞确信,马克思哲学的整个悖论就凸显出来了: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没有被当作“哲学”生产出来,或者说,马克思接受了传统哲学的陶冶,但马克思拒绝“哲学”写作,“他几乎从不谈论哲学……却依然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实践了他从未写过的哲学”(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页,第246页,第169页,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23页。)。
这里,阿尔都塞的看法无疑是准确的。问题在于,应该如何来理解马克思非哲学式地写哲学这个悖论?阿尔都塞以为,马克思没有把哲学当作“哲学”来写作,是为了避免落入到对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游戏中,哪怕是采取对立的形式,也会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页,第246页,第169页,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23页。)记住阿尔都塞的这一提示很重要,它实际上是意味着要求马克思的读者,不应该把马克思当作一个传统意义上批判知识分子——被理性主义传统责成要把真实的东西从虚假的东西中解救出来——类型的“作者”,马克思 由此提出“消灭哲学”并把这一任务交给无产阶级。我同意(在我与阿尔都塞意见一致 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它更像具有一套理论,一套在特殊的实践(治疗)中能 认识和改造其对象的精神分析方法。因此,言及阅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哲学也就 不能被当作运用理性的理论体系,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的哲学来阅读,而应该当 作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虽然也有概念,但那些概念同时也是实践形 式,这实际也是阿尔都塞用“哲学实践”的说辞所暗示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 哲学实践的性质的理解,阿尔都塞强调说,它“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 新的)哲学实践”(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 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页,第246页,第169页, 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23页。)。“新”就“新”在它已经不再是那种沉思冥 想,一味从事着“解释”世界的哲学。所以,阿尔都塞“制造”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当作 一种新哲学,而应该当作一门科学,一门完全不同的科学,但仍然是科学。
这样,阅读的“有罪”性就被推到了极端,因为它在学理上以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解释为前事的。这种解释对自身所提出来的要求,按照施特劳斯解释学来看,至少不自知 地被假定为比马克思本人还更为真实地理解马克思。虽然阿尔都塞正确地揭示了:像马 克思的著作这样有综合性内容的文本所必然具有的字面意义和深度意义区别的事实,因 而必须被纳入新的理论思考范畴。以新的理论为中介,有助于重新聚集以前一直被忽视 掉的马克思著作中的微言大义。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最为警觉和最为现代 的再阐释”(德里达),从思想结构看,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上述作用,阿尔都塞深怕 我们固执地囿于马克思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那种方法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他要求我 们这些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读者,去悉心地倾听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所发出的“空洞 的声音”,抓住这门科学在充分“论证”的外表下包含在自身中的弱点。从而生产出马 克思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科学可以发挥出进步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不在于它所 知道的东西,而在于它所不知道的东西”(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 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 页,第246页,第169页,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23页。)。概言之,他希望提 出一个“完全创新了的”马克思。
不难看出,阿尔都塞通过考察马克思的思想过程来解释马克思理论自身中存在的矛盾。就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譬如,他通过症候阅读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亦即马克思主义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突然转变成作为科学的理论。这里,显然假定了只有作为解释者的阿尔都塞意识到了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断裂”,马克思本人未曾意识到,只有后来居上的历史审查才能注意到文本的方方面面,使这种“断裂”大白于天下。这样说来,创新性是不是也就变成一种无始源和无目的的“新”写作,一种“冥思苦想”,一种总“想”冲破已有界限的“想”?在这种“想”的背后分明同样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神话:把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转换成本质上是古文献研究,我们研究过去19世纪的马克思的作品,不是因为它们可能包含永恒的真理,而是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理论从不成熟到成熟发展的阶段,展示了马克思为设法逃离意识形态偏见而进行的漫长斗争。匪夷所思的是,马克思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
在我们看来,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形成时期绝对地看成一种“断裂”,其最大的危险恐怕不在于由此招致对其著作完整性的肢解(尽管那种阿尔都塞式的把在马克思的两本书之间出现的矛盾或曲异,常常说成是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变动。若矛盾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则会在没有任何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断定其中的一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样的方法的负面影响是显然的),而是他用来解释马克思的术语却不能翻译成马克思自己的语言,进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关联排除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之外。阿尔都塞与马克思的两次“诀别”——第一次是与早期马克思的“诀别”;1978年,这一次是与整个马克 思的一种“诀别”——是他独创新的思想的开始,但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主题:克服马 克思的局限的需要。一旦阿尔都塞以“确认马克思学问的杰出成果及其今后应有的可能 性”为意图,但所采取的方式不仅“恰如调查死者的遗产,做财产目录那样”,而且所 做的“尽是消极面的财产目录”。他的主题自然就带有了自戕性的味道:“回到马克思 ”仅仅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性”。(注:参见今村仁司:《阿尔 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第253—25 5页。)
三
马克思本人所曾经说过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吗?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体系是不可能在马克思本人的意图上再使用了吗?所有这些问题总是尖锐而必然地摆在任何一个马克思的诠释者面前。从我们的视角看,阿尔都塞并不是完全如今村仁司所指认的那样,是在毫不自知的情形下与马克思“诀别”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阅读总是将一段新 的话语连接在文本的话语之上,阿尔都塞不可能不认为,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保卫马 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如果他所使用的语汇中存在着与马克思的文本所使用的语 汇处于某种推论性关系之中,那么,他就有可能表明他本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 种更加本原的性质。不过,他把这种“对于某种更加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回归”, 与“原先以阶级为基础的对抗姿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在一起”(注:参见阿尔 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页,第246页,第169页,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 23页。)。在我们看来,在这样做时,他所愿意做的也许充其量在于继续沿着马克思的 书页,与马克思达成最小化的协和,而这一般地说来,只要他去解释马克思说了什么, 靠近马克思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当后来他跨出了马克思文本的页边,向一个孤独的思 想家后退时,他就既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也为马克思哲学所忽略。
可以说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的解释学特质就在于“深度观察”,分清经典文本的显性意义和隐微意义。在阿尔都塞的视野里,“‘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不是因为它能够被它的成败所检验,所以它才正确,而是因为它正确,所以它才能被它的成败所检验)”,(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页,第246页,第169页,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23页。)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历史生命与其说在于它的成功和显性的正确,不如说就在于“他的表述中没有出现的、却是他自己的思想的基本概念的存在”(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第244页,第246页,第169页,第23页,第517页,第177页,第23页。)。
照理说,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表面的显性意义和隐微的深层意义的区别,就会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意图的追问推到中心地位,因为他假定了马克思的真实想法不等于马克思在其文字中所表达的看法。但是,如果阿尔都塞想承担这个追问,就必须首先从马克思思想的一以贯之的中心出发,将其著述当作表白出来的整体加以理解。重要的是,他必须首先像马克思理解自己那样来理解马克思。这意味着,阿尔都塞应该从所谓马克思的“科学”论题与“意识形态”论题的“断裂”的历程中把握到一脉相承的东西。依据施特劳斯的解释学,在著作的连贯或思想的统一与否的问题上,我们宁愿断言马克思的所有文本是首尾一贯的,像施特劳斯那样,他总是极不情愿指责他所敬重的作者实际存在着前后矛盾,他会设法找到一种把矛盾与作者的意图视为一致的解释,致力于栓紧文本 机体中松散的经纬,以表明文本与作者的意图是不能分割的。否则,思想史的客观性惟 一标准就无从谈起。
这是一种很正确的想法,深刻的意义上正是这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即没有人能够预见一百年后马克思的文本,会被怎样读解,马克思的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解释情境下,可以允许几个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存在,到现在,人们不会不知道,开放式的撒播能够辐射出对“教条的真理”的解毒剂。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伟人的思想在人类思想传播上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其实是以颠覆这样一个观念为前提的,这个观念是:最好的诠释是忠实复制伟人内心怀抱的意图。在前面的文字之中多次提醒到,这种观察会令援引伽达默尔、利科尔的解释原则的某些人断定,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释都无法成为在知识论的“真理”意义上的“真解”,自从浪漫派以来,哲学中已经失去了一个“绝对者”。然而,这个观察之中所缺少的是:它没有真正看到,马克思在写作某一文本时,只从一个角度理解它的事实,这是任何一个重建理性主义的解释者都应 该坚守的底线。所以上述那种观察也无以用来否定“思想史客观性的惟一可行标准”, 以便解决“究竟什么是文本解释的‘真’?”的问题。相反,有学者批评利科尔那样的 解释概念对这么一个问题不仅只在无关痛痒的地方挠挠,而且在其自身中隐含着一条消 解“思想史客观性的惟一可行标准”这一问题的途径。
但是,我们也知道,伽达默尔、利科尔的解释概念实际上不能不预设“怎样的途径才能使我们正确理解文本解释行为的本性”问题,因而,他们的解释概念实际上仍含有方法及规范的提示,为的是显示文本中的力量与真理。由此暴露出了他们的解释概念与基础主义框架的残余性不情愿、不相称的结合,援引他们的解释概念为后援的马克思解读,也就必然都预设了马克思的作品中有某种可以追寻的本真意图。对于任何一位本色的经典研究者而言,文本的意义虽然不是自明地给予的,但是它的重要的问题总是如何去知道文本的真义,以及当面对不同的解释时,如何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并且我们确信,只要我们践行“从字里行间去阅读”的方法,它就会导致在理解方面比较健全的视野:拒绝见木不见林,尽管这在理解的目标上并不意味着去弄懂马克思所有的思想。
依据施特劳斯的解释学,研究过往学说的解释学的进路,首要的问题是“原作者的精言妙意是什么?”而不是某一过往学说“对我们的信念作出了什么贡献?”或者“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个学说里什么是原作者没弄明白的?”(注:参见施特劳斯:《如何研究中世纪》,见刘小枫《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1页。)如此,当我们在面对马克思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表面“错误”时,它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证实我们比马克思更高明。即使我们可以像卢卡奇那样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我们也“无须片刻放弃马克思主义正统”。卢卡奇的 这个看法对于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悖论:他自甘放弃马克思主义所有的论点,而将马 克思主义蒸发为一种独特的方法。例如,像人们习惯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历史的, 而非马克思主义则是非历史的;马克思关心的是实践,而费尔巴哈关心的则是理论;马 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整体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是个人主义的。凡此种种的证明都是把 马克思主义的论敌所持的方法论当作划界的尺度,充其量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 方法论结构形式,仍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什么独特的惟一的方法论。这表明确定马 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是一回事;与马克思深入讨论他所说的东西,即他之所以这 样说,从而揭示出它的实质性的内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显然,与当前的解释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基础主义的反叛而发生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抗拒解释学将马克思的作品“改变”或“翻译”为别的什么东西,就显示出一种对文本真诚而保守的愿望。我们认为,当代解释学者对基础主义的反对是正确的,但是,正像伽达默尔那样,他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释”,这意味着所有的解释都是非基础的和可改变的。这个观点被进一步的推论所加强:由于所有解释是可以改变的,所有理解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所有理解都是解释。这些推论实际上是可疑的,因为它在虚构一种什么东西也解释不了的东西,从而忽视了理解和解释的区别:解释通常意味着某些有意的或至少是有意识的思考,而理解则不必然有意识,甚至 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理解。如果没有前反思的、非语言的经验和理解的没有清楚说 出的背景,解释就无以存在。理解作为解释的基础的观点,不仅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 坦那里有过明确的阐述,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马克思自己就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启发性的进路去了解经典。要了解经典中关键性概念的意义,我们有时须将其产 生的社会背景及实践纳入其中。这样一种原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的具 体性原则。”这原则要求的是:“必须尽可能地就其本身来解释作者。”如何“回到马 克思”的这个审思在这个原则这里结束,它也应该在这个原则这里开始。
标签:解释学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的改造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 施特劳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