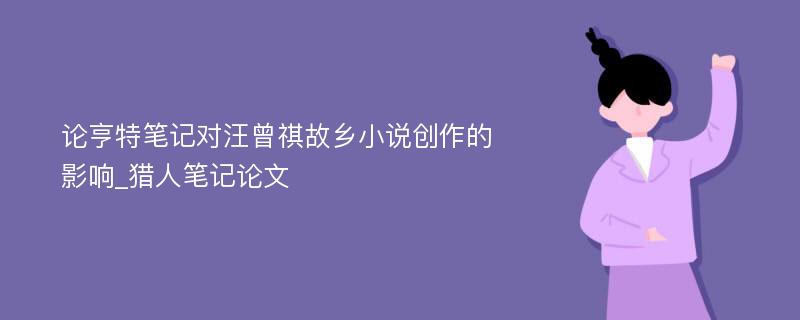
论《猎人笔记》对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猎人论文,故乡论文,笔记论文,系列论文,汪曾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世纪末俄罗斯文学被开始介绍到中国,便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影响,“五四”时期至二三十年代,其影响更是达到了一个峰值,其后,一直余响不绝,独特的效应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众多的俄罗斯作家中,无论是从被介绍到中国的时间、被介绍的全面性,还是从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等多方面考察,屠格涅夫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鲁迅、郁达夫、巴金、沈从文等诸多名家都或多或少地从不同方面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学界对此也多有论述;延及当代,这种影响依然迹痕可寻,尽管显隐不一,但在许多具有相当成就的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仍然能够发现此种渊源关系。汪曾祺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尽管在谈及自己所接受的前人影响时,在罗列的古今中外作家中,汪曾祺并没有让屠格涅夫置于其间,但同时,在很多文章及谈话里,汪曾祺又多次提到屠格涅夫特别是《猎人笔记》对自己创作的重大影响,并对其艺术多有点评,充分显示了这种影响的深远与重要。如在《自报家门》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1] 在80年代末的一封家书中,他说“我直到现在,还受这两个人的影响。”[2] 此类表述在《汪曾祺全集》中不一而足。因此,考察屠格涅夫及其《猎人笔记》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多重影响,对理廓作家间思想与艺术的影响和传承,凸现其中的意义及对作家、作品进行更明晰的定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3] 在普通平凡的世俗人生中,表达鲜明、朴实、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感,是《猎人笔记》和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一个显著的共通出发点和指归点。
《猎人笔记》的写作始于1846年,从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问世,作品就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赞誉,别林斯基、赫尔岑等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猎人笔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像雨果作品那样具有明显的理论与思辨色彩,其思想与情感更多地是通过对农奴制时代地主的揭露批判以及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对他们美好心灵的温婉歌颂体现的。
总观《猎人笔记》,其中大部分篇目都是以农奴制为对象进行的严厉批判。屠格涅夫曾明确阐述了《猎人笔记》创作的主导思想:“我不能和我憎恨的东西待在一起,……在我看来,这个敌人有明确的形象,有一定的名称:这敌人就是农奴制。对于我归并和集纳在这个名称下面的一切,我决定要斗争到底,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这是我的汉尼拔誓言……”。[4] 《猎人笔记》通过对俄罗斯形形色色的地主的全面、细致、生动的刻划,以一个独特生动的人物画廊,完成了对农奴制深刻、有力、形象的批判。在《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故事叙述者的祖父“他骑着马出来,用手指着说:‘这是我的领地。’”就残忍狂暴地夺走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当他的爱犬死了的时候,“奏着音乐,把它埋葬在花园里……并且在上面立一块有铭文的石碑。”[5] 在《总管》里,屠格涅夫刻划了一个“算是我们省里最有修养的贵族”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的形象,他的“房屋是依照一个法国建筑家的设计而建造的,仆役们都穿英国式服装,饭食很讲究,招待客人很殷勤”,“为人审慎而积极,照例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风姿翩然”,“和蔼地眯着一双明亮的、褐色的眼睛”,“说话时声音柔和悦耳,抑扬顿挫,仿佛每一个字都是自愿地从他那漂亮的、洒满香水的髭须中吐出来的;他又常常用法语的词句”,因此,在仆役端上没有温的酒时,招来另一个仆役对其进行惩罚的方式也就与一个文明而有教养的人的身份格外相符:“‘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泰然自若地低声说。”因为“照他自己所说,为人严格而公正,关心他下属的幸福,惩罚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当出行途中马车翻倒,轮子压住厨子的胃时,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这一吓非同小可,连忙叫人去问他:手有没有跌伤?得到满意的回音,立刻放心了。”[5] 与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的论调如出一辙,《两地主》里的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带着最仁慈的微笑”、“明朗而柔和的目光”,倾听着拷打农民的声音,“为了爱而惩罚”。[5]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描写刻划了大量实际控制着俄罗斯土地、农奴命运的各类中小地主,他们面貌不一,性格相异,但与农奴制相契合的残忍、贪婪、虚伪却是他们一致的本性。在似乎不动声色的描写、叙述中,屠格涅夫体现了对反人道的农奴制强烈的永不妥协的批判斗争精神。
与地主相比,《猎人笔记》的农奴及农民形象更为复杂。在这类人物形象中,既有对他们所承受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苦难的深切同情,也有对蕴含在他们之中的俄罗斯民族最美好特点的由衷赞美。展现农奴及农民在苦难生活中依然留存着的健全、美好的人性,是《猎人笔记》的一个显著特色,正如作者的自述:“凡属人性的东西,对我都是珍贵的”。[6] 《霍尔和卡里内奇》中的霍尔和卡里内奇是一对相映成趣的组合:“霍尔是积极的、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一个纯理性的人”,“我和霍尔谈话,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淳朴而聪明的言语。”卡里内奇则“是一个性情最愉快、最温顺的人,嘴里不停地低声唱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张望”,“伺候我的时候毫无卑屈的态度”。[5] 《歌手》里的两位民间歌手尤其是雅科夫的歌声更是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真挚而深切的热情,有青春,有力量,有甘美的情味,有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俄罗斯的真实而热烈的灵魂在这里面流露着,它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心,简直抓住了其中的俄罗斯心弦。”“他唱着,他的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给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熟悉的草原一望无际地展开在你面前一样。”[5] 对于与小说《孤狼》同名的守林人“孤狼”,性格则比较复杂,评论界也有指其为地主老爷的效忠者的,因为“据他们说,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能够尽职的人”,“毫无办法收服他,请他喝酒,送他钱,都没有用;无论怎样诱惑他都不行。”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我尽我的职,’他阴沉沉地回答,‘白吃主人家的饭是不行的。’”但是当听到农人的哭诉:“管家……把我们的家拆败了”,“实在是为了肚子饿……孩子们在哭,你知道。真实走投无路了。”[5] 他还是带着“懊恼”放走了雨夜偷树人。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看,尽管外表强悍凶狠,但蕴藏在“孤狼”内心深处同情、善良的人性光辉还是无可否定的。
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故乡系列作品最具特色,也是受《猎人笔记》影响最明显的。与《猎人笔记》比较,两者都着眼于普通乡村、市镇的世态人生,通过平凡日常的人事表达人道主义的思想与情感,但作者的心态、目光的投射点却显然有所不同。作为一种精神与理想,“人道主义理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诗人那里,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追溯到印度的斫婆伽派运动,还可追溯到其它卓越的理智和道德传统那里。”[7] 不可否认,人道主义是一种既有普世性又有民族性的价值取向,汪曾祺曾经这样写道:“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家?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8] 在汪曾祺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对性善论的高度认同,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汪曾祺的明显影响。汪曾祺曾自述:“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8] “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2] “给人间送一点小小的温暖,这大概可以说是我写作的态度”。[3] 表现在小说创作,对人性善的歌颂,对和谐人生的理想探求,便自然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季匋民是汪曾祺小说不同篇目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季匋民是一县人引为骄傲的大人物。他是个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同时又是大收藏家,大财主,家里有好田好地,宋元名迹。”[9] 在《岁寒三友》,当他看上清贫画师靳彝甫收藏的三块“爱若性命”的田黄石章时,并没有巧取豪夺,而是文雅率直地登门拜访求购,委婉被拒后也无愠色,反而倾心指点画艺,真心实意地代谋生计,一派名士风采。《鉴赏家》则更令人称奇,“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被称为“季四太爷”的季匋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而“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与季匋民相比,可谓地位卑微,正是这样一个的人,季匋民却对他“另眼相看”,“送给叶三的画上,常题‘泽之三兄雅正’。有时迳题‘画与叶三’。匋民还向他解释:以排行称呼,是古人风气,不是看不起他”。与此合好,叶三则是“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他真的是为了季匋民一个人卖果子”,而且,对季匋民送给他的画,无论出价几何,他一张不卖,“他把季匋民送他的画都放在他的棺材里”。[10] 《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他也好义,也好利”,好酒好赌,身在水边,既救活人,也捞死人,“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捞钱的”。为捞一具女尸,他敲人十块大洋,拿到钱,“大家以为他又是进赌场、进酒店了。没有,他径直地走进陈五奶奶家里”,因为陈五奶奶独自带着的小孙子正病得四肢抽搐而无钱就医,“陈泥鳅把十块钱交在她手里”,[10] 抱起孩子就上了药房。
当然,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并非只有和谐与温暖,面对人性受到的戕害,同样无所回避地表达着深沉的抗议。《故里三陈》之《陈小手》,主人公与作品同名。对这篇小说,汪曾祺自陈:“我写的《陈小手》,是很沉痛的。”[11] 小说中,作为“一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陈小手活人多矣”。正因为医术出众,当一个军阀团长的不知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的老婆难产时,便很自然地被叫来了,见面团长就是一句:“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外面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陈小手出了天王寺,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10] 《八千岁》里也有一个混世魔王式的“旅长”,“他是个霸王,没人敢惹他”,“他的旅部的小牢房里经常客满。只要他一拍桌子,骂一声‘汉奸’,就可以军法从事,把一个人拉出去枪毙。”“他还很风雅,爱字画。谁家有好字画古董,他就派人去,说是借去看两天。有借无还。”对靠八吊钱俭省起家的八千岁,“八舅太爷存心找他的茬”,要敲他一千大洋,“八舅太爷敲了八千岁一杠子,是有精神上和物质上两方面理由的。精神上,他说‘我平生最恨俭省的人,这种人都该杀!’物质上,他已经接到命令,要调防,和另外一位舅太爷换换地方”,[10] 于是,他终于敲来了八百大洋。
二
从小说艺术角度考察,尽管不能说屠格涅夫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唯一的和决定性的,甚至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但是,也确实可以理出两者之间或隐或显的传承关系。落实到《猎人笔记》与汪曾祺故乡系列的小说,这种影响,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小说的诗意营造和文体的运用上。
安德烈·莫洛亚曾说屠格涅夫“是一位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作家”,[6] 屠格涅夫也自称:“我容易感受诗意。”[12] 卓越的风景描写是《猎人笔记》最为人称道的诗意特征之一。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擅长风景描写的作家特别多,而屠格涅夫则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猎人笔记》的风景描写,则更以其集中、丰富而更具典范性,成为其一个突出的美学因素。在《猎人笔记》中,俄罗斯的山川、河流、草原、森林如同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被徐徐打开,似乎任意翻开一篇,都有树木野草的芳香、溪流小河的清响,充满生机活力的自然世界在作者饱含情感的叙写中展现出的无穷魅力,使人沉醉其中。《车轮子响》:“这是辽阔、广大、滋润而茂盛的草原,其中有无数的小草地、小湖泊、小川、尽头丛生着柳树和灌木细枝的小港,是真正俄罗斯风的、俄罗斯人所爱好的地方”,[5]《白净草原》:“在我的周围,在广阔而濡湿的草地上,在前面那些发绿的小丘上,从树林到树林,在后面漫长的尘埃道上,在闪闪发亮的染红的灌木丛上,在薄雾底下隐隐地发蓝的河面上——都流注了清新如燃的晨光,起初是鲜红的,后来是大红的、金黄色的。……一切都蠢动了,觉醒了,歌唱了,喧哗了,说话了。到处都有大滴的露珠像辉煌的金刚石一般发出红光;清澄而明朗的、仿佛也被早晨的凉气冲洗过的钟声迎面传来……”。[5] 而《树林和草原》则完全如同一篇描写四时不同、阴晴迥异的俄罗斯自然的写景散文。
在屠格涅夫笔下,自然万物仿佛都是具有灵性、情感的,是作者可以体察和与之对话的。《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在那里,新近砍倒的白杨树悲哀地横卧在地上,把青草和小灌木都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在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斧头钝重地响着,有的时候,一颗葱茏的树木好像鞠躬一般伸展着手臂,庄严地、徐徐地倒下来。”[5] 对此,汪曾祺也曾感叹“这写得非常真实。‘庄重’真好!”[8] 在诗学意境的营造上,汪曾祺的小说也是特征鲜明的。他曾说:“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抒情诗成分”,[2] “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2] “这类作品所写的常常是一种意境”。[2] 汪曾祺写过诗,中国传统书画造诣深厚,两者的艺术特征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11] 其故乡系列小说承袭了唐宋以后文如画的美学追求,具有突出的写意特征,艺术境界空灵多于真实,人物形象神似大于形似,生活实境因为与作家的心灵体验和情趣相融会而被诗意地虚化,虚实真幻结为一体。这种意境的营造,既是其心态情志的外化,也加强了小说的审美情趣,使小说具有了浓郁的诗意美;不仅为作品的人物设置了一个非此不可、两两相宜的境界,还对他始终希望通过小说来反映“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8]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屠格涅夫和汪曾祺小说都注重诗学意境的营造,但比较之下还是可以发现两人有所不同。虽然屠格涅夫也有对人物诗意的内心世界的叙写,如《歌手》、《车轮子响》等,但从总体考察,屠格涅夫的作品主要以大量、细腻、鲜活的自然景物描写为手段,创造如诗如画的人物活动背景,达到营造诗化意境的目的,相对比较单纯,“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很优美。但那是屠格涅夫式的风景,屠格涅夫眼中的风景,不是人物所感受到的风景”,[8] 而汪曾祺小说这种单纯的景物描写则比较少,更多地是通过对人物的诗化达到营造诗学意境的目的。而且,相对于屠格涅夫的不经意间时常流露的明显的忧郁,汪曾祺的小说间更多展示的是一种与屠格涅夫迥然不同的欢愉。比如《大淖记事》中大段的对挑鲜货的姑娘媳妇的描写:“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9] 《受戒》里,僧俗的界限荡然无存,和尚不做功课,倒挑水喂猪,买田娶妻,甚至放债收租,相好私奔,赌钱杀生……有滋有味地过着世俗众生的日子,总而言之,“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9] 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欢愉自由和诗意。对这两篇小说,作者有很多自述,如“我写《受戒》,主要想说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的解放。”[2] 透过汪曾祺的艺术世界,我们也鲜活地感受到作者本人的诗心、诗眼、诗样情怀。
从文体、取材及人物设置等方面看,《猎人笔记》也对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在文学评论中,因为《猎人笔记》极具特性的文体,而有了所谓“猎人笔记”式的特写、“猎人笔记”式的素描等称谓。这种文体,往往以情绪的流动作为小说结构的依据,更多地以生活的原生态作为小说素材,根据情感需求进行不多的裁剪,具有片断性、不联贯性、不讲求故事情节、不注重人物性格塑造等特点,带有散文诗笔调,自由灵活,不拘一格。比如《白净草原》、《歌手》、《树林和草原》。汪曾祺曾评述道:“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些篇近似散文。”[1] 从汪曾祺的小说同样也多被评论界冠以“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等不同的称谓看,两者之间的相通处是很显著的。“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8] “《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有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8] 确实,《故里三陈》之《陈小手》、《陈泥鳅》等大量篇目就像人物特写,而其中的《陈四》则更为奇特,全篇直接叙写主人公的文字只有淡淡几句,几乎通篇都在描写故乡的“迎会”场景,更像是一幅风俗画。《桥边小说三篇》之《幽冥钟》,全篇根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人物,也无所谓情节,当然也就谈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以一般的小说理论无法对这样的作品进行理性解析,因为作品全然就是因故乡的一点民俗所引起的一连串充满人文色彩的自然怀想。
从小说人物设置看,屠格涅夫认为,什么样的小说“臆造”也不能和真正的生活真实相比,因此,尽管并不局限于原型,但其小说人物往往原型特征非常突出,而且相当具体。对此,不仅作者本人屡有阐述:“我从来都没有能光凭自己的想像来创造人物。我必须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依据,才能塑造人物。”[6] 评论界也指出:“白净草原、察普雷金森林、祖莎河、里果甫——这些都是真实的名称,而猎人叶尔莫莱——则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从前那个热爱大自然的农奴阿法那西·伊凡诺夫。”[13] “他的才能的主要典型特点在于:如果在现实中不曾遇到类似性格特征,他未必能够正确地创造出这种人物性格。他必须永远牢牢地立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从事这种类型的艺术,他具有雄厚的天赋……”[14] 汪曾祺的故乡系列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事件,也具有同样的与生活原型可以一一对应的特征,而且,这种原型运用的取用广度和保真度是相当突出的。汪曾祺评述自己故乡系列小说道:“大部分是有生活根据的,……我很同意德国一位心理学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所谓想象,不外是记忆中的一种重现和复合。我的一些作品就是写有关故乡旧事的记忆。”[15] “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1] 关于《异秉》,汪曾祺说“《异秉》里的那个药店‘保全堂’,就是我祖父开的,我小时候成天在那里转来转去。”[2] 对《受戒》,作者也有相当详细的原型材料解说,并称“这都是真的,我就在这小庙里住了半年,小英子还当过我弟弟的保姆。”[2] 而《徙》的主人公——作者的国文教师高北溟,作者甚至连名字都没改,就让他进入了自己的小说,小说中其女儿高雪与那位“还订了好几份杂志,并且还看屠格涅夫的小说”[9] 的中医汪厚基的爱情也多以实事为基础,汪厚基同样也是以原名出现,乃至小说发表后依然健在的他坦承其中情节大多为事实;《鉴赏家》中的季匋民本是作者家乡高邮著名画家王陶民,地方史中多有记载;《大淖记事》中的故事情节是汪曾祺童年时亲身经历过的真实事件;《幽冥钟》中的承天寺是作者童年时代常去的地方,寺里的那口钟自然也是很熟悉的;陈小手虽非作者亲见之人,却也听过继母的介绍;“我的小说《珠子灯》里所写的孙小姐的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3] 由于汪曾祺与父亲感情深厚,再加上其父亲性格鲜明,充满了生命活力与乐趣,因此其人其事也就很自然地多次进入了作者的小说作品中,“我在《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3] 《受戒》中的特立独行的石桥和尚,就是其父亲的好友铁桥和尚,甚至《岁寒三友》里那三块田黄本也是作者父亲的爱物。对于自己小说的这种特性,汪曾祺曾说:“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起隐来,我将会有吃不完的官司的。出于这种顾虑,有些想写的题材一直没有写,我怕所写人物或他的后代有意见。我的小说很少写坏人,原因也在此。”[3]
尽管空间上相距千万里,时间上相隔百余年,屠格涅夫与汪曾祺两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迥然不同,但是,人道主义精神如一条闪亮的红线联结沟通了两位不同民族作家的心灵世界,在思想的传承与诗意的共鸣中,其心灵与艺术之美因此而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其小说也进入了常读常新的文学精品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