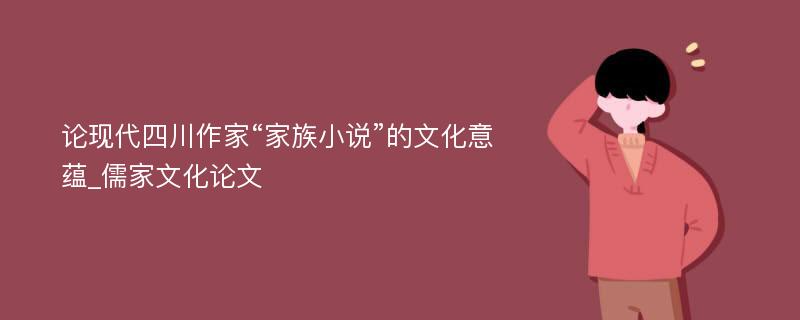
试论现代川籍作家“家庭小说”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试论论文,作家论文,家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论述中国家庭结构时说,“一对夫妻和其未婚的子女所构成的生活单位”,一般称为“小家庭”,“儿女成婚后继续和父母在一个单位里生活”,“兄弟成婚后都不独立成家”,这类家庭统称作“大家庭”。[1]北方及江南作家多写“大家庭”。老舍把小说命名为《四世同堂》,祁家与周家(《雷雨》)、曾家(《北京人》)、胡家(《呼兰河传》)、蒋家(《财主底儿女们》)、姚家(《京华烟云》)、金家(《金粉世家》)、倪家(《活动变人形》)、隋家(《古船》)都是大家庭。在现代川籍作家中,巴金的《家》、《春》、《秋》写的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其他作家多写“小家庭”。李其他作家多写“小家庭”劼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中的蔡家、顾家、郝家、伍家、黄家,沙汀《淘金记》、《还乡记》、《三斗小麦》、《呼嚎》中的何家、冯家、刘家、廖家,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的周家,周文《山坡下》中的赖家,罗淑《生人妻》、《阿牛》中的打草人家、阿牛家,陈炜谟《狼筅将军》中的赵家……全是“小家庭”。巴金《憩园》、《寒夜》中的姚家、汪家也只能算是“小家庭”。“大家庭”小说多反思正统的儒家文化,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小家庭”小说反映出巴蜀地域、巴蜀文化的特性,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巴金的家庭系列小说暴露了家长制、等级制、婚姻制、财产继承制以及维护这些制度的思想、礼教、道德、迷信……的危害性,总体上反思了家族文化。传统“大家庭”以男性为纲,以尊卑长幼为等级秩序来确立家庭成员关系。父子关系是家庭的核心,夫妻关系只是父子关系的附庸,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2]同一宗族的男性“上级”有权干涉“下级”家庭的“内政”。在高家,高老太爷与社会上的政治、思想、文化势力结盟,成为高家的统治力量,他的话就是法律,具有绝对权威。克安、克定虽然不是觉新、觉民、觉慧的直接“上级”,但作为家族中的上辈人,他们仍然对“觉”字辈指手划脚。家长制确立了“一家之长”的权威,等级制严格限制着家庭成员的自由度。因此,父子冲突,婆媳矛盾成为“大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焦母与花金子誓不两立(《原野》),曹七巧嫁到姜家受到婆婆的摧残,人性扭曲的曹七巧又肆意摧残儿子长白的妻妾(《金锁记》),祥林嫂被婆婆逼迫改嫁(《祝福》),双喜的妻子被婆婆逼疯(《疯妇》),小团圆媳妇因长得“太大方了”“见人不知羞”被婆婆活活烫死(《呼兰河传》),李瑞珏、钱梅芬(《家》)与曾树生(《寒夜》)这些小姐、大学生也在“儒家轨道”上被辗得粉身碎骨。汪母顽固、守旧,不喜欢媳妇,把媳妇当仇人。尽管曾树生不服“管教”,但汪母声称:“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在婆婆的“家庭暴力”下媳妇们成了无谓的牺牲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戒条像“紧箍咒”一样笼罩在她们的头上,她们的生命之花,青春之花,爱情之花,理想之花慢慢枯萎、凋零,随风而逝……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性昭然若揭。
巴金笔下的人物更多地体现出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巴金的《寒夜》与曹禺的《原野》都有一道“儿救母”难题。花金子问焦大星,要是我掉在河里,你妈也掉在河里,你先救哪一个?汪文宣做过一个梦,梦见敌人打来了,曾树生对他叫喊“你不能丢开我们母子”,但他还是首先“找妈去”!“儿救母”难题带着极浓的儒家文化色彩。汪文宣、焦大星(其实还有高觉新、曾文清、祁瑞宣等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身上背负着民族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他们孝顺母亲,又爱妻子,在带有传统宗法社会色彩的“孝”和带有自由恋爱色彩的“爱”之间徘徊,无所适从,矛盾困惑。在这两难选择中,中国人心里差不多如焦大星所想:“我两个都救,我左手拉着妈,我右手拉着你。”在只能选择其一时,中国人差不多都是选择尽“孝”。高觉新为了尽“孝”不惜牺牲妻子和未来孩子的生命!巴金挖掘了人物的深层文化心理,让我们看到儒家文化支配着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使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二
与北方及江南地区不同,巴蜀地区存在着消解正统的家族文化、道德文化的机制。“四川,四川,四面都是山。飞机飞不过,大炮打不穿。”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难于上青天的交通条件,使得四川远离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成为儒家文化的“边缘区”。从历史上看,巴蜀地区家族文化与道德文化的积淀远远不如北方及江南地区那么深厚。《汉书》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3]《华阳国志》载巴蜀“少儒学,多朴野”。[4]《宋本方舆胜览》载,潼川府路绍熙府“蛮獠杂处,姓名颠倒,不知礼法。”[5]四川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流也冲击了宗族、家庭关系。移民入川以后,天远地远,山高水长,时间一久,多数与原来宗族的关系断裂了(比如艾芜的家族)。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几弟兄都来到四川,也是分散居住,各自为政(比如陈毅的家族)。清同治《巴县志》所载《刘氏族谱序》中说:“善人处乱世,父子兄弟且不能保,况宗族乎?”[6]父子关系、家族关系比较松散,联系、来往浅淡。至今四川还流传着这样的俗话:“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认不倒。”甚至家族之间、家庭内部闹出矛盾,自己解决不了,还对簿公堂,官司不断,以致史书称“川峡之民好讼”。[7]自家人“打”自家人,人情淡薄,民风嚣薄。
北方地区,崇尚多子多福,以大家庭为荣耀,以数世同堂为模范。四川并不注重人丁兴旺,有弃杀不养的习俗。杨时说四川居民“计产育子,习以成风,虽士人亦为之,恬不知怪……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8]据《洪武实录》、《明史·地理志》、嘉庆《江津县志》、嘉庆《三台县志》、同治《彰明县志》所载户数、口数来测算,户均口数并不高。[9]嘉庆《四川通志》载,成都县户69597,丁口386397,户均约5.5丁口,华阳县户85974,丁口389656,户均约4.5丁口,温江、新繁、郫县等地户均丁口数还低一些。[10]四川虽有世家望族,但遍布城乡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小家庭。四川人不太重视家庭、家族义务,子女一旦成年,便热衷于和长辈分家,与兄弟争夺财产,另立门户,组成小家庭。《隋书》记载,巴蜀之地“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11]宋代以伦理纲常治国,禁止父母健在而子孙异居。四川却是《宋史》中唯一被指责“亲在多别籍异财”的地方。[12]中央政府严重关注,“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陕诸州蜀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治死。”[13]朝庭下诏书明令禁止,但并不很管用。清人张澍《蜀典》载:“州中风俗,其家富裕者,早分诸子,其父分食诸子,按月计日,不肯稍逾期。”[14]至今,四川还存在子女轮流赡养长辈的“转转会”、“吃零供”的习俗。由此可见,家族制度和礼教并没有完全占据四川“家庭市场”。
现代川藉作家的“小家庭”小说反映出巴蜀地域的特征,体现出巴蜀文化的独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小家庭”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父子退位,夫妻登台,即使有老一辈存在,如小说中的邓大爷、邓大娘、伍太婆、赖太婆、廖太婆,也是居于从属地位。这样的家庭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更利于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发展。四川女性有点不讲“妇道”,敢于“犯上”,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于不顾,公然向婆婆们挑战,与丈夫们对抗。同样的“婆媳战争”,四川媳妇不仅没有变成牺牲品,反而“占上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非常惹眼、令人惊讶的文学现象。伍大嫂(《暴风雨前》)刚过门就懒懒散散,自由自在,不要说饭不煮正事不做,连换下来的裤头都得伍太婆洗。睡懒觉总是睡到日上三竿,当伍太婆忍不住上去掀帐揭被,猛然间竟当肩挨了一掌,被打翻在地。而床上的伍大嫂已经大吵大闹起来:“老不要脸的!白日青光来看媳妇的活把戏吗?亏你是老人婆!若是老人公呢?我也是十八九岁的人了,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老人婆!”粗鲁、粗野的行动,“没大没小”的语言足以显示伍大嫂的“天棒”品性。一场不可避免的“婆媳大战”正式“开打”,硝烟弥漫之后,主动妥协的不是媳妇,而是老人婆!这有什么办法,伍太婆仔细想了想,这一定是命中注定,以前的妄想,只好一齐收拾起来,将就她,让她,权当她是老人婆,但求耳根清静,过点太平日子。”媳妇变成了老人婆,老人婆变成了媳妇,乾坤颠倒了,何其惊人!廖二嫂(《呼嚎》)直率、嘴硬,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同婆婆拌嘴”。她去赶场还要给婆婆安排“劳动任务”:“你挖一锄头算一锄头,再不然,把磨刀石地里的豆子扯了。”这样的媳妇,婆婆是又喜欢、又讨厌、又惧怕。金大姐(《还乡记》)是冯家的童养媳,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公公婆婆的争吵,“心粗气浮,举止心思都带野气”,公婆拿她毫无办法。赖大嫂(《山坡下》)与赖老太婆吵嘴,赖大叫她少吵几句,赖大嫂“鼓起腮帮子,也一挺地站直起来,两手叉腰”说:“唷唷,我哪里跟她吵?”婆媳之间你来我往,斗嘴斗气,直到赖老太婆气得嘴唇发抖,才算“停火”。
四川媳妇不仅与公婆、丈夫公然对抗,更有越“雷池”、犯“天条”的女性。他们没有“从一而终”、“守贞”、“节烈”的观念,“国法家规”、“女儿经”、“女诫”对他们不起作用。洗衣婆的女儿(《在祠堂里》)与“世现宝”青年有私情,金大姐到处惹事端,有戏赶戏,有会赶会,是人是鬼她都来往,弄得污七八糟。公婆劝她,嘴皮都说起茧疤了,“可是有什么用处呢?这只耳朵进去,那只耳朵出来,——她当你把胡豆吃多了!”竟然自作主张改嫁给了“野男人”徐烂狗。邓幺姑(《死水微澜》)既嫁蔡兴顺,又迷罗歪嘴,最后还改嫁顾天成,而钟幺嫂与邻居顾天成也“花花草草”的。伍大嫂嫁给伍平,暗中与郝又三、魏三爷等人往来。旧版《大波》中的尤二小姐不仅在生活中把几个男人玩得溜溜转,而且大张旗鼓发出理论宣言:“妇人家真是值不得,偷了人就要着耻笑,说是失了节。胆小的,只好忍耐到害干病死,发狂。我就胆大了,可是也只好偷偷摸摸的。敢同男人样:只要有钱,三妻四妾,通房丫头,不说了,还能在外面随嫖,嫖女的,嫖男的,大家凑合他的风流。会作诗的,还要古古怪怪做些来跟人家看,叫做啥子情诗艳体。我不信男女既都是一样的人,为啥女子就该守节?人人都不明白这道理……”真算得上是“前卫女性”。陈莉华(《天魔舞》)、尤金菊(《秋之惑》)、甚至曾树生(《寒夜》)都有“四川操妹”品性。汪母就说曾树生“不守妇道,交男朋友”,跟着情人到处跑。
如果说夫妻型小家庭为四川女性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内部环境”,那么巴蜀社会儒家思想、伦理道德文化积淀的相对稀薄则为四川女性的自由成长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巴蜀向来不服“王化”,时时“越轨”,不信正统、不服王法的“割据意识”浓厚。清代移民入川,“由湖广来者系刁狡之辈,不讲道德”,四川成为令政府头痛的“民刁俗敝之区”,四川人被视为“野蛮”之人。[15]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助长了四川女性无视“道德”的行为倾向。刘三金“教唆”蔡大嫂:“蔡掌柜真老实得可以,你倒尽可以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挣几顶绿帽子,怕啥子哟!”蔡大嫂与罗歪嘴“勾扯”,公开打情骂俏,并没有人出来指责,反而得到众人的谅解,因为“这件事又是平常已极,用不着诧异的,不说别处,就在本镇上,要找例子,也就很多了。”成都下莲池那些年轻妈妈,哪个没有几个“男朋友”呢?张嫂主动来“开导”伍太婆替儿媳妇找“男朋友”,伍太婆是老人婆,不仅接受了建议,而且每当儿媳妇在家里“接客”时还主动“站岗放哨”。四川人哪里把贞操、贞节当回事?哪里信奉“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社会舆论公然支持“越轨”行为,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社会现象!而东北的王大姐(《呼兰河传》)自主嫁给冯歪嘴子遭到好多邻人的讥讽。江南的子君与涓生(《伤逝》)同居,并没有招谁惹谁,但“老东西”和“小东西”总是“鬼头鬼脑”的,子君的胞叔甚至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萧涧秋(《二月》)来到芙蓉镇,不过同情文嫂而已,却招致“交头接耳的社会”的“毁灭性”打击。北方及江南社会充满儒家文化的冰霜雪雨,那里的人们如入枪林弹雨,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祥林嫂是被婆婆逼迫改嫁的,但仍然被认为没有“从一而终”,“落了一件大罪名”,是伤风败俗的肮脏女人,要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捐了门槛,鲁四太太仍然不准她去动与祭祀有关的一切东西,她的精神支柱被摧毁了,倒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但还是遭到鲁四老爷的“鞭尸”:“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祥林嫂连死的时间都错了,她不该死在“祝福”声中!两相对照,四川女性太“受宠”了!蔡大嫂、金大姐弃夫再嫁,伍大嫂、黄太太与多个男人“打交情”,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活得尚好!只有巴金小说中的李瑞珏、钱梅芬、鸣凤、婉儿、曾树生受到了家长制秩序的约束和伤害。这说明,巴金反思的是儒家文化,而其他川籍作家反映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三
在北方及江南地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儒家礼法比较森严,“男主外,女主内”是普遍的家庭模式。连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的子君最后也落入了传统的家庭模式中不能自拔。四川的情况有所不同。《隋书》载四川地区“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16]陆游《入蜀记》载:“大抵峡中负物率著背,又多妇人。”她们汲水、卖茶、卖酒。[17]巴蜀之地曾经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夷夏杂居”,在风俗民情方面不同于北方,呈现出“非礼法”的特性。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加“案”语:“汉中先贤,女子入赞者九人。在诸郡中,数量不大而质量最高,其家庭礼法之严,家庭教育之美,虽如宋、明贤媛,莫或过之。处世接物,彬彬有礼。修身行义,出以雍容,较之三蜀诸女,淑德为多。……然此九女,皆出于封建巨家,不如犍为、广汉之多有草野奇女。”[18]四川历史上确实少“淑德贤媛”,多“草野奇女”。“富敌祖龙”的巴寡妇清,私奔相如的卓文君,率“敢死队”上阵的浣花夫人,“四川花木兰”韩娥,习武征战的秦良玉,“海”袍哥的大娘大嫂……“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胆大敢为、英姿飒爽,充满山气、野气、蛮气和豪气,是出名的“川辣椒”。巴金之外的其他现代川籍作家的家庭小说中,女性的地位凸显,而男性的地位旁落,不再具有权威性。
“一家之主”成为“影子人物”,在家庭文学中是不多见的。但现代川籍作家的家庭小说却多“丈夫缺席”现象。阿牛妈、何寡母、田畴妈、魏老婆子,她们的丈夫早死;廖二嫂、伍大嫂、周四嫂、石青嫂子的丈夫当兵。在“小家庭”中,“丈夫缺席”使得妻子扮演了“丈夫角色”,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和主心骨,独立不倚地行走人生,练就了一身真功夫,非常坚韧和刚强。李劼人的母亲,沙汀的母亲、岳母,都是这样的“寡母”型人物。周文回忆说:“我的母亲张氏,性格很强。我的祖母爱四叔五叔,所以对四婶五婶很偏爱,而对我母亲却非常苛刻,我母亲愤于那种压迫,便当卖所有陪嫁的首饰,出钱为我父亲开一药店,离开了祖父母,另立门户。但当我五岁时,父亲因肺病去世了,母亲遂独立撑持药店,但从此我们就开始受到封建社会更残酷的待遇和压迫。”[19]罗淑的《生人妻》与柔石的《为奴隶和母亲》都反映“典妻”现象。“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20]浙江的春宝娘被丈夫“典”出,默默无语,低声抽泣,顺从丈夫的安排。而四川的“生人妻”大喊大叫:“呵唷喂!好听呵!”立直了身子指着男的骂道:“你好人!……你狼心狗肺!……你全不要良心的呀!……”出现这样的差异,与其生活的人文环境相关。北方及江南地区儒家思想、文化相当浓厚。女性们虽不知“书”却极为识“礼”,身上留有更多的儒家礼法的烙印。她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儒家文化的毒害,患了先天性缺“钙”症,始终软弱,无能反抗。那位秀才典用别人的妻子,还在夜里读起《诗经》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生了儿子要取名,他翻开《易经》、《书经》来找,最后确定叫“秋宝”,说《书经》里不是有“乃亦有秋”么?“我真乃亦有‘秋’了!”在这样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中,春宝娘还能有什么“出格”的举动?沱江流域的刘嫂(《刘嫂》)与祥林嫂有相同的命运,从小受欺凌,做过帮佣、小贩甚至乞丐以求生,嫁过三个男人,但绝不肯做夫权的奴隶,最后因“打不过第三个男人”而逃出来,当她被地主辞退时,别人劝她说好话求情,她坚决拒绝:“人只要有两只手,两只脚,到处好找饭吃。好日子和坏日子全是一样过,过不得也要过下去”、“哪里黑就哪里息,一个人总不会饿死的”。刘嫂的身上体现出强悍的生存意志。这是儒家文化相对稀薄的巴蜀土壤孕育出来的性格,是桀骜不驯的巴蜀“蛮夷风”薰染出来的品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浙江的茅盾塑造的“时代女性”梅行素(《虹》)大胆反叛,“我行我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可梅行素不是江南女性,而是“川妹子”(事实上梅行素的原型确实取自巴蜀女性胡兰畦)。茅盾描写时代的反叛女性,没有以江南女性为模特儿,而是“借”用四川女性,多少反映出二者的差异。四川女性长在山野之间,沐浴天地之气,远离儒家文化的中心地带,没有精神重荷,自然勇往直有,辣味十足,是“天棒”、“操妹”。
于是,四川男人在家庭生活中“退居二线”,显得懦弱无能,普遍患有“妻管严”,是出名的“粑耳朵”。蔡大嫂是不要人管、不安本份、说得出做得出、不怕哪个的“歪人”,而蔡兴顺憨痴痴的,除了吃饭睡觉,啥子都不晓得,“不说男子汉,就连婆娘的见识,他都没有。”就是后来嫁的顾天成,也憨不憨痴不痴的,比蔡傻子精灵不到多少。伍大嫂是无畏的,敢跟老人婆吵嘴打架,而伍平呢,“自从讨了老婆,一直是很驯谨的,成日守在家里,任凭老婆如何指挥,总是喜笑颜开地做事。”黄太太聪慧能干,思想开放,有主见有魄力,是一个能够旋转乾坤的人。事到最紧要关头,老于官场的黄澜生彷徨不定,干练的孙雅堂给大风浪吓住了,独有她冷静地支持吴凤梧的“快然一掷”,把大权抓到手中来。而郝达三、郝尊三、郝又三、苏星煌、田伯行、尤铁民、黄澜生、陶二表哥、孙雅堂、徐独清、楚子材个个缩头缩脑,畏首畏尾,遇事惊惊惶惶,全无一点男人气。曹聚仁说:“在女人面前,那些读书人,真是不够‘种’!”[21]洗衣婆的女儿“私情”暴露,面对丈夫的淫威,毫不示弱,嘴硬到底:“我是喜欢他!——你丑不了我!”而她的“情人”,那个“现世宝”青年“自己倒跑掉了”!何寡母很能干,她的丈夫却“柔弱,懒惰,只有躺在床上抽烟”。她的儿子天天沉醉于“闺房之乐”和“烟毒之好”,没有多久,“他的肩头上耸,背有点驼,嘴唇皮尖尖的,四肢都显得过于细小。神情懒散的眼睛上面,躺着一双过份弯曲的近乎女性的眉毛。”周四嫂是顽强的,不睬事的,而“周老四是个好心肠而没定见的男子,做起事来也有些轻率,常常在枕头上受着教训,渐渐变成害怕老婆的人物。”
综上所述,巴金关注“大家庭”,反思儒家文化,其他川籍作家多写“小家庭”,反映出巴蜀地域、巴蜀文化的特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