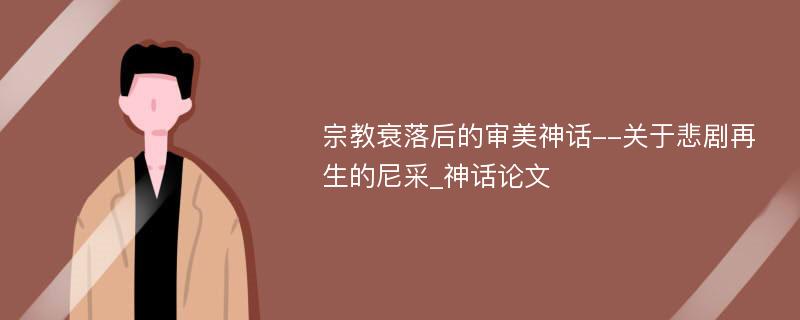
宗教衰落之后的审美神话——尼采论悲剧的再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悲剧论文,宗教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5)02-0116-06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也被认为是其惟一集中处理美学问题的著作。但尼采对古希腊的欣慕之情使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文化怀乡(Cultural Nostalgia)的主题。文化怀乡是现代以来的一个独特现象,德国人的文化乡愁自然要落实在欧洲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的诞生》并不是一部仅仅讨论美学问题的著作,也不是对古希腊文化的一项历史研究,而是针对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症侯,对现代西方理性启蒙主义的一种根本性的批判。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于苏格拉底主义的批评,即对于理论乐观主义的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托古论今”,其“醉翁之意”在于对现代性进行剖析。
尼采对观代性的批评
尼采曾以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来比照现代文化:“整个现代世界被困在亚历山德里亚文化的网中,把具有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其原型和始祖便是苏格拉底。”[1](P76-77)何谓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我们可以在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之第四个考察《瓦格纳在拜洛伊特》中找到一个形象地说明。尼采在其中提到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戈尔迪打上的错综难解的“戈尔迪之结”[2](P209),传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用利剑将此结斩开。尼采以“戈尔迪之结”指称希腊文化的完整性、聚合性,与之相反,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是一种以分裂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以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比照现代文化,就是要突出现代性的主要问题:分裂性问题,现代性的其他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分裂性问题的衍生物。现代文化的分裂性是指文化的统摄性力量分崩离析,文化的各个方面各自独立,不再构成统一的整体。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到,尼采将现代文化之分裂性问题的真正病因归结为理性力量的过度扩张。尼采认为,现代以来,理性主义开始占据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宗教的统一控制中挣脱出来,彼此独立,不再是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在尼采看来,神话是一切宗教的必要前提,而现代文化的理论批判精神却将神话纳入历史的发展轨道,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神话,视之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神话由之便转化为系统化了的历史,现代人因而失去了神话的家园。但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规束力,能够将文化的各个方面聚合成一个整体,同时,正是由于这种规束力,神话使文化保持健康的天然创造力。因此,失去了神话首先意味着失去了文化的凝聚力,一切成为抽象的存在,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其次,失去了神话还意味着失去了文化自身的创造力,而只能向其它文化寻求滋养,但理论批判精神的侵蚀将一切本可利用的资源转化为“历史和批评”,将注定该民族的文化不能从其它文化获得实际的滋养,只能停留于对其他文化的饥饿的寻求之中。简言之,断裂和贫困是失去了神话家园的现代文化的必然处境。很明显,尼采在此思考的是西方文化的宗教衰微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困境。所谓理论乐观主义将宗教的神话前提纳入史实,使宗教失去它的神话根基,即是指启蒙主义的现代文化对宗教釜底抽薪,以理性的扩张置换信仰,造成宗教在西方现代的衰落,而宗教在西方传统中曾经至关重要的整合作用也就随之不再有效了。
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不仅造成文化的分裂,还从根本上弱化生命。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批评苏格拉底主义,在他看来,苏格拉底主义持有一种理性的妄念,即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理性的认识得以掌握,人生的幸福也是通过理性可以操作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消除人生的痛苦、灾祸。这实际上是以理性替代了对于自然真理、人之可怕命数的领悟,使人遗忘了生存的真正本质,也就是说,理性乐观主义使人失去了对命运的切身感受,逃进由理性架构的避难所中,不去观照生存之恐怖可怕的深渊。生命的悲剧意识使古希腊人出于生命的强力肯定和承担生命的流逝和毁灭,并以此颂扬生命的强大,与之相反,现代人失去了生命的悲剧体验,现代社会是以理性计算的方式规避可能的风险。理论乐观主义最终走向“奴隶的乐天”,导致对痛苦的惧怕和想方设法的躲避,对舒适享受的满足,生存失去了英雄维度,生命走向衰竭、腐败、退化。另一方面,理论乐观主义不仅因其排斥对生存本质、人之命数的切身感受,还因其同时是一种道德主义而弱化生命。在理性的妄念中,德行也是可以通过理性传授的,而道德在尼采看来是对生命的否定、敌视和打击。
理论乐观主义破坏了神话,现代人失去了生存的宗教根基,随之而来的便是世俗化倾向,是生存的庸俗化和瞬间化。现代人缺乏对永恒的信仰,只追求尘世幸福,追求眼前的舒适享乐,满足于瞬间的生活体验。尼采一再批评那种“奴隶的乐天”:奴隶不相信理想的过去和未来,不懂得给予过去和未来比现在更高的尊重。在此尼采批评的是现代性的时间意识所导致的问题。现代性注重现在的权利,在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中,追求现在不同于过去的独特性,拒绝过去对现在造成的负担。这种时间意识的一个极端形式是:以现在的权利拒绝过去和未来,将现在从时间之流中独立出来,视之为与过去和未来断裂的一个个单独的瞬间。注重瞬间体验的生存方式是这种时间意识的体现。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没有过去便意味着没有了生命的历史,没有未来便意味着没有了生命的理想,瞬间化的生存使个体生命失去了统一性,是个体生命的分裂。这意味着在宗教衰微的现代境遇中,失去了永恒信仰的心灵不再能从宗教中获得安宁。
悲剧的再生
面对文化的戈尔迪之结被斩断的现代,尼采认为现在紧迫需要的是一种反亚历山德理亚文化的力量,将被斩开的结重新打上。寻找文化的整合力,这是所有深切领受到现代性分裂问题的思想家的共同倾向。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性问题就是在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整合力量衰微之后寻求宗教之替代物的问题[3](P98-99)。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企图通过他的思辨哲学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虽然早期的黑格尔也曾有过艺术救赎论的倾向;尼采则是明确地开出了艺术救赎论的方案。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成为这种替代物,世界是绝对精神自我认知、自发运动的统一世界。而尼采,这位理性之虚妄的激烈批判者,则将理性弃置一旁,以未来为旨归,回溯进古代世界,意欲返回“原始的混沌”,寄望于悲剧在现时代的再生。
在尼采看来,悲剧的消亡正是理性乐观主义所导致的后果,理性乐观主义将悲剧的根基——作为自然至深本质原始回响的酒神音乐——变成“音乐图画”,即音乐成为现象世界的简单摹拟,由此,音乐也就失去了它创造神话的能力,悲剧的形而上的慰藉沦落为悲剧冲突的世俗解决。由于悲剧的世界观与理性的世界观之间有着永恒的斗争,只有当理性的世界观走到了它的界限,悲剧的世界观重新苏醒,悲剧才能再生。
悲剧的再生并不仅仅指一种艺术门类的复兴,而更主要地是指一种悲剧世界观的重建。
首先,这种悲剧世界观的重建意味着要回复到对自然至深本质的酒神式认识。自然本质上是一个永恒奔流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看作是一个永恒生命,而酒神就是这永恒生命的象征或名称。在此过程中,万物不断地生成、毁灭;生成意味着个体存在之界限的获得,毁灭则不仅是个体的死亡,更是个体界限的破除,意味着个体消解并重归永恒生命之流。对手个体生命而言,悲剧的世界观也就是对于个体命数的深切感受、对生存的恐怖深渊的直面。现代以来,自然的酒神本质被科学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掩盖,理性的妄念取代了悲剧的世界观。但同时,理性的妄念最终推动理性文化奔向自身的界限,理性的世界观必定由于面对自身的界限而突变为悲剧的世界观,个体重新一无护佑地直视自然的酒神本质。
其次,这种酒神智慧还意味着一种“无限深刻和严肃的伦理观和艺术观”[1](P86),既洞察到自然的至深本质、自然恐怖可怕的深渊,同时又以艺术来达到对自然生成与毁灭的永恒奔流的整体观照,以此超越对自然本质的悲剧认识。所以,悲剧世界观的重建还意味着悲剧艺术精神的回复。在尼采看来,艺术的最高使命是“使眼睛不去注视黑夜的恐怖,用外观的灵药拯救主体于意志冲动的痉挛”[1](P84),如此,艺术能够超越对世界的悲观理解。艺术既将自然永恒的生成与毁灭的本质展示出来,同时又美化这一本质,从而达到对此本质的最大肯定。艺术使我们信赖永恒生命,将自然看作是一个原始艺术家,一切生成与毁灭是永恒生命为了摆脱生命过剩之痛苦出于自身之必须而进行的审美游戏,个体世界的价值在于成为这一审美游戏的作品,而个体世界的毁灭同时也是个体重归万物合一的永恒生命之流,流逝、毁灭、痛苦是一切生命的前提。艺术通过审美的眼光看待自然生成与毁灭的永恒奔流,达到对自然生命的最大肯定,从而超越了悲剧的认识。
具体来说,悲剧艺术精神的回复就是悲剧音乐以及音乐创造神话的能力的再生。悲剧音乐是悲剧的酒神根基,是自然酒神本质的直接反映。音乐的酒神内容追求形象化的再现,它从自身产生酒神普遍本质的譬喻性的个别事例,悲剧神话就是这一个别事例,所以悲剧神话从酒神音乐中产生,是酒神本质的形象化,悲剧神话以个体的受难和毁灭所指向的是一切个体现象背后的原始生命之永恒奔流的过程。悲剧神话以形象世界的生成和毁灭象征自然原始艺术家永不止息的审美游戏,悲剧便以悲剧音乐和悲剧神话实现“形而上的美化”,即实现艺术的最高目的。
现代文化破坏了这种悲剧的艺术精神,尼采认为,现代是缺乏艺术精神的时代,现代文化是非艺术的文化。艺术在现代沦落为满足上流社会的所谓有教养之士虚假需要的工具,现代艺术或者是麻醉、或者是刺激,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使人回避自己,摆脱生存的无聊和贫乏。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艺术形式是歌剧,歌剧虽然被看作是一个艺术品种,但实际上与艺术相去甚远。首先,歌剧产生于完全非审美的需要——对牧歌生活的向往,尼采称之为“歌剧的牧歌倾向”[1](P83)。这种牧歌倾向源自对人本身的乐观主义的看法:认为原始时代的人类既与自然相和谐,又达到了人类的理想,是自然与理想相协调的美好生灵,并且是天生的艺术家,随时准备歌唱。因此在尼采看来,歌剧完全是理性乐观主义精神的产物。其次,在歌剧所使用的抒情调和吟诵调中,音乐与歌词的关系完全背离了音乐的酒神本质以及语言、形象作为酒神真理之象征的意味,因而也就背离了真正的酒神与日神的艺术冲动,音乐沦为现象世界的摹拟,与此同时,现象的意义也被贬低。必然的结果是,艺术失去了它的最高使命,沦落为娱乐倾向。
现代文化便以歌剧这种完全非艺术的倾向取代了真正的艺术精神。但是,尼采断言,真正的艺术精神正在德国音乐中重新兴起。德国哲学和德国音乐的新的发展——具体来说是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从巴赫、贝多芬到瓦格纳的音乐——正代表了德国文化悲剧精神的复归,它们指向希腊民族在悲剧时代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其中德国哲学标志着悲剧认识的重建,而德国音乐则表明真正的艺术的复归。音乐精神的复生也将是悲剧神话的复生。藉此,德国文化重新找到并返回它的神话家园,悲剧世界观得以重建,悲剧再生。
尼采在现代文化的细微变化中看到了悲剧再生的迹象,由此他还深思这样一个问题:悲剧的这种再生对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尼采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再次表明,他决不仅仅是在谈论一个纯粹美学的问题,而是寻求对现代文化的救治方案,是对民族生活方式的全盘谋划,因而主要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因为在尼采看来:“艺术与民族、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1](P101)在根本上是联生共存的。对自然至深本质的悲剧认识以及用以超越此种认识的悲剧艺术精神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悲剧政治,换句话说,悲剧的再生同时也是一种悲剧政治的复兴。
尼采认为,必须回到悲剧时代的希腊生活方式才能回答这一问题。希腊人处于酒神冲动和日神冲动的强烈作用之下,这两种冲动可能导向两种不同的道路。其中,酒神冲动——即一切皆流、无物永存的永恒流变——否定一切个体的存在,打破一切个体界限,不断将个体形式化入无形。这种对个体束缚的摆脱一方面导致政治本能的削弱,另一方面,个体为了克服对人世生存的厌弃,可能走向印度佛教式的“坐禅忘机”。日神冲动则创造并停留于个体形象,维护个体化原理,肯定个体界限的保存,追求持驻的形式,而城邦和家乡意识或者说政治本能便以日神冲动对于个体化原理的肯定为前提。日神冲动的危险在于:对界限、范围、疆域的追求及对现世个体生存的执着可能沦为极端的世俗化,导向罗马式的政治扩张,追求世界霸权。但是希腊人并没有选择这两条道路,而是找到了第三种方式,在印度佛教的坐禅忘机和罗马的极端政治世俗化中间保持平衡,既有酒神的激情,又保持“最单纯的政治情感、最自然的家乡本能、原始的男子战斗乐趣”[1](P90)。这种希腊方式之所以可能,正在于希腊人的悲剧。悲剧作为酒神冲动和日神冲动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以一种强大的统一感消泯个体的界限,另一方面,又以日神的外观力量保护这个体化的存在世界,因此,悲剧对希腊人而言,成为一种调节力量,使其在完全否定个体存在的界限和对界限的过分执着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有一种观点将尼采思想与纳粹政治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有内在相似之处。但如果我们反观尼采对于希腊方式的尊崇,细察尼采标举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不同的政治意味,就可以看到,尼采完全反对罗马式的谋求世界霸权的政治扩张道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言,尼采从悲剧精神出发的政治谋划与纳粹思想迥然相异。
就现代性问题而言,这种对生活之本质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对现代性所导致的分裂问题的救治方案。在尼采这里,是悲剧而不是理性成为宗教的替代物,悲剧作为文化整合力量,力图恢复文化的统一性。悲剧是对自然本质的认识,也是艺术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政治理念,文化的一切都因悲剧而联结起来,从而文化的整合成为可能。对于尼采的这种方案,哈贝马斯曾经在两个方面进行批评。首先,他认为,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整合,是以抛弃现代性的成就——个体的解放——为代价的,因为由悲剧而来的统一感是以忘我、以个体界限的打破为前提的,在尼采这里,“‘个体化原理的崩溃’成为摆脱现代性之路”[3](P94)。但如果我们回顾以上所述尼采同时标举悲剧的酒神与日神双重因素,就可以看到,哈贝马斯的批评是有问题的,根据尼采的说法,个体化生存和个体的崩溃都是永恒生命奔流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个体化生命以获得统一感来克服厌世,而进入永恒生命之流恰恰是为了使个体生存本身获得可辩护的理由,其真正的目的是执着于个体化生存本身。第二,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救治现代性问题的方案企图将理性完全弃置一旁,但在根本上又不能排除理性的影响,因为他的重估价值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运用理性的行为[3](P96)。然而这一批评似乎同样未中鹄的,尼采是以艺术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救治现代性问题,这与哈贝马斯的启蒙立场下的理性主义有所不同。归根到底,尼采重估价值是从艺术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而非启蒙理性的立场。
艺术形而上学
生命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得救,这是《悲剧的诞生》不断强调的观点,正因如此,尼采把艺术作为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在前言中,尼采就提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1](P2)。
艺术形而上学即是指艺术的形而上的美化,艺术将自然现实转化为审美现象而赋予自然现实以价值,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赋予价值的活动,人通过艺术赋予自然现实以价值又由此赋予自身的生存以价值。从尼采对悲剧的论述我们得知:自然现实本身无所谓价值,它是生命的永恒奔流,在此奔流中无物永存,对于个体的生者来说,自然至深本质全然是恐怖、可怕的;艺术则将这一永恒奔流的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将之转化为一个原始艺术家的审美游戏,个体世界是这审美游戏中的瞬间作品,由此,艺术便赋予自然现实以及个体世界以审美价值,并通过这一赋予价值的活动来为现世辩护,个体生存的价值也由之得到辩护。这就是《悲剧的诞生》中一再出现的命题: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的生存和世界才有充足理由。
赋予自然至深本质以价值还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如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在前一种方式,自然本质被认为是符合因果联系和逻辑辩证法的东西,因而是可以通过理性通达的,理性可以掌握自然并给存在造福;后一种方式则在自然中区分善恶,高举善、德行等作为最高的价值,而灾难、不幸则被视为对罪的惩罚。在尼采看来,前者的典型形式是科学,后者的典型形式则是基督教。可以说,人类迄今标举的3种价值——真、善、美,即是人类通过理性、道德、艺术分别赋予自然本质的3种不同的价值。
《悲剧的诞生》所做的就是对这3种价值的重新估量,在尼采后来的反思中,这部著作恰恰被他视为“第一个一切价值的重估”[4](101),其任务一是“以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1](P272),二是用人生的眼光考量道德。价值重估的结果是:尼采只承认一种价值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即审美的价值;只承认一位可作为人的终极关怀的“神”:艺术家之神。这就是以“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的结果。以人生的眼光来看,艺术是对生命的最大肯定。艺术肯定生命的永恒流变,将生命的奔流看作是生命出于强力之逼迫的必然的行为;同时,肯定生命的流变也就是肯定流逝、毁灭、痛苦,因为流逝、毁灭、痛苦是生成、创造的前提,是生命不可穷尽的担保。可见,艺术是对永恒的大生命、对总体生命的肯定;就个体而言,艺术担保个体生命的意义,使人执着于生存。艺术激发生命的本能,成为求强力的生命意志本身,强力意志也就作为艺术而出场。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是高涨的生命力量的表征,出自生命本身的充实、丰盈、健康。
与此相反,以人生的眼光考察理性和道德,尼采认为二者都是对生命的否定,都是求毁灭的意志,是生命衰退、匮乏、羸弱的征象。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是生命弱化的表现,生命的衰败、垂暮使其缺乏直面可疑可怕事物的力量,便以理性掩盖、忘却自然的真正本质,以逻辑和推理制造稳定感,以乐观主义的辩证法提供对事物的明确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认为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出自怯懦和虚伪,是对世界之悲观主义理解的惧怕和逃避。理性既是生命弱化的结果,同时,完全违背生命本质的乐观主义又反过来加强了这种弱化。同样,道德也是生命蜕化的表征,在尼采看来,基督教、尤其是现代以来的基督教是现代道德主义的典型,这种道德主义根本上是与生命意志相背离的。基督教以道德的眼光看待生命,只承认道德的价值。基督教区分出善与恶、区分出彼岸的天堂世界和此岸的尘世世界,以所谓天国的幸福来否定人世生存的价值,以善的名义否定一切此岸的、感性的生存价值,包括否定艺术的价值。而在尼采看来,一方面,在生命之外寻求理想,在生命之外设定目标、意义,本质上是对于虚无的信仰,是求虚无、求毁灭的意志,生命成为实际上无权的、不应当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在生命之外对于生命的规定是生命的外在立法,作为外在的依靠和命令,是生命对于外在强制的服从,因而是生命弱化的表现。
尼采不仅仅使审美价值成为最高的价值,同时还强调形而上意义上的艺术精神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分。一方面,尼采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痛苦,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悲观主义。浪漫主义苦于生命的贫乏,因而求助于浪漫的激情,为的是靠浪漫的激情来平复痛苦、求得灵魂的安宁、平静或通过激情来摆脱涣散、虚弱之感,其根本前提是生命的疲弱以及对痛苦的极度敏感和极度厌倦。尼采所提倡的酒神式悲观主义则出自生命之过剩的痛苦而挥霍无限丰盈、无限充实的生命自身,这是对旺盛的生命意志的领悟与认可。
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艺术创作的两种尺度来区分形而上意义上的艺术精神和浪漫主义。一种尺度是追问“是饥饿还是过剩成为创造性的”[5](P329),这对应于上述两种不同的痛苦:苦于生命的贫乏和苦于生命的过剩。前者是出于“寻求和渴慕”而创造,后者则是出于“丰盈和赐赠”而创造[6](P445)。另一种尺度是就创作动机而言的。尼采认为,悲剧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是由生命的充实、丰盈的力量而来的一种“对破坏、变化、未来、生成的渴望”;而日神艺术与浪漫主义的创作动机则都是一种“求永恒的意志”,是对于“存在”的渴望,日神艺术的求恒的意志是“出于感激和爱”,浪漫悲观主义者的艺术则是出于“苦难深重者、挣扎者、受刑者的暴虐意志”。所以,浪漫悲观主义者的艺术实际上是一种非艺术,从事的不是肯定生命的创造,而是匮乏者、失败者对生命的憎恨,企图将自身衰败的形象固定化、永久化,以期腐蚀败坏生命本身。
标举审美价值为惟一最高的价值,并将真正的艺术与浪漫主义区分开来,尼采便强调绝不能以道德、理性的标准来评判艺术,也不可对艺术进行浪漫主义的解释,艺术要求自身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对悲剧的解释:亚里士多德从激发和净化恐惧和怜悯的情感来理解悲剧,叔本华则把悲剧看作是放弃个人意志、听天由命的手段。尼采认为这都是对悲剧的非审美的理解,依照这种理解,悲剧就全然成为否定生命的、衰败的东西。尼采把自己当作第一个能真正理解悲剧和悲剧艺术家心理的哲学家,悲剧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而是为了超越、控制恐惧和怜悯,而悲剧艺术家对恐怖可怕事物的热爱是生命强力的象征,他之传达毁灭、痛苦完全是由于勇敢、由于无所畏惧。
由此可见,在尼采那里,形而上意义上的艺术精神是贯穿统摄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总体力量,就人类的生存而言,也是实现强健生命的真正良药。面对文化涣散、生命疲弱的现代,要恢复文化的完整和生存的强健,就是要张扬此种艺术精神,呼唤悲剧的再生,使之成为宗教的替代物,行使宗教曾经对民族的文化和人类的生存所发生过的作用。如此,通过对悲剧艺术与悲剧精神的独特理解,尼采针对宗教衰落之后的现代性问题构建了一个以艺术为核心的救赎方案、一个新的审美神话。
收稿日期:2004-12-20
标签:神话论文; 艺术论文; 尼采论文; 现代性论文; 酒神精神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哲学家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毁灭世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