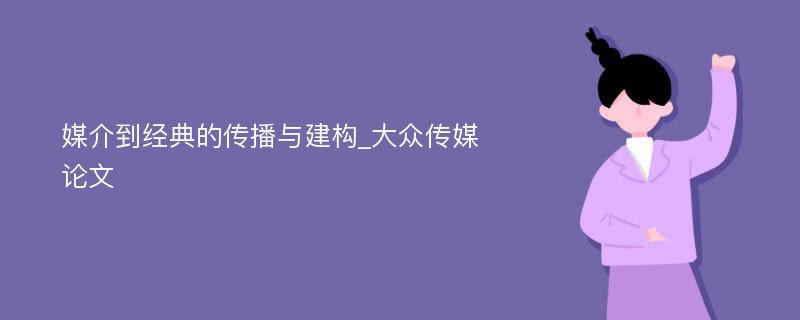
媒体之于经典的传播和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于论文,媒体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典的传播与建构历程中,对传播与建构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政治权力的,应该是今天所说的媒体。
在古代,经典的传播途径除了口耳相传之外,其主要的物质手段就是雕版印刷,而现在的传播媒体,除了传统的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外,还包括了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经典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果说可以用影响与被影响及反影响、同流和非同流来概括的话,考察经典与媒体的关系则远非那么简单。媒体对经典的评价、传播的影响比政治更直接,在某种意义上甚于政治权力的干预,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要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读者,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将作品介绍给读者的机构而成为人们的注意对象”①。将作品介绍给读者的机构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媒体。一部作品的存在,要靠这些媒体;一部作品不仅存在,而且成为有生命力的阅读活体,即引起读者的注意,更需要这些媒体。传播媒体对经典的影响,虽然并非如同政治权力那样,表现为强制性的干预,但是却发挥着比政治权力更直接、更强大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称其为“亚权力”。
从经典流传的历程考察,经典无论多么优秀,都必须依赖于媒体才会传播久远,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确立它的经典地位。如果我们接受经典是建构起来的理论的话,那么经典的建构则是在经典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建构理论只有用于经典的传播才适用,才有意义。文化遗产是经典的基本属性,它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淘洗,才得以确立。所以经典传播的过程就是经典接受时间检验的过程,也就是经典的建构过程。换句话说,经典的建构不是当下完成的,而是历时完成的。从经典的本质属性方面来看,也就是从理论界常说的本质主义立场来看,经典之作正因其为优秀的文化遗产,才得以被历代读者不断重视,因而付诸版刻,所以可以说经典因为其优秀而得以流传,但这仅仅是考察经典传播的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理论界所说的建构主义立场来考察经典,经典之作必须依赖媒体而得以传播,也因传播而被确立为经典。如现在热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人们可以说,对莫言小说不同语种的翻译、电影改编和诺贝尔奖的获得,证明了莫言小说优秀,说明了他的作品的广泛影响。但是,反过来看,如果没有诸多对莫言作品的不同语种的翻译、特别是瑞典语的翻译,使莫言的小说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注意,就很难说莫言的优秀小说能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2012年12月11日在诺贝尔奖晚宴演讲时说得好:“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②因此可以说是媒体帮了莫言的大忙,换句话说,是传播媒体影响了经典的确定。由此可以看到,媒体所发挥的是类似于权力的作用。媒体之于经典传播的重要从上所述可见一斑。
的确,经典就是在历代读者传播过程中得以确立的。如果没有出版印刷,中国古代诸多文献包括经典文本就难以保存下来,经典地位的确立也就无从谈起。当然,保存下来还仅仅是精神产品的留存,只能说是经典确立的前提,但是一部作品能否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说的,由“无生命力的积存”③变为读者关注的精神活体,媒体所发挥的则是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古代,经典显然要依赖出版而得以流传,也因出版而得以传播广远。如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所说:“圣叹深恨前此万千年,无限妙文已是觑见,却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今刻此《西厢记》遍行天下,大家一齐学得捉住。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真乃一大快事。”④在中国古代,诗文为正宗,被冠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所以,历代官刻(包括宫廷刻本、藩府刻本、书院刻本等)都以诗文为主。这自然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以诗文为主。然而,自唐代书坊出现,尤其是宋代以后书坊大量涌现起,出版的内容逐渐有了变化。书坊的出现,主要是缘于社会对精神产品大量阅读的需求。如果说唐代之前书籍的阅读,以士大夫为主的话;宋代之后,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书籍的阅读开始向有一定文化的市民阶层延展。阅读群体的变化,带来了阅读取向的多元化。以科举和获取知识为目的的阅读,分化为既有为了以上目的的诗文阅读,也有市民以及士人中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阅读。正是迎合了阅读群体阅读需求的变化,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书坊,除了印制满足举业需要的图书以及医学、宗教书籍外,开始大量刻印小说、戏曲等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作品。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在北宋时已有书坊,南渡后私人书铺更多,纷纷设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书籍铺,又叫文字铺。”⑤可考的有20家。南宋时期,福建建阳与建宁府附郭的建安县,作为南宋出版业的中心之一,可考书坊有37家之多⑥。这些书铺,从称谓即可看出,所谓“上自六经,下及训传”,仍以刊印经史及诗文为主。但是,这些书坊,也开始注意印笔记小说、异闻杂录。《中国印刷史》载,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除了刊有《释名》、《画继》、《图画见闻志》外,所刻《湘山野录》、《灯下闲谈》、《剧谈录》、《续世说》、《挥麈录》,多是笔记小说。而临安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所刻书籍10种,除了《箧中集》外,《述异录》、《续幽怪录》、《北户录》、《康骈剧谈录》、《钓矶立谈》、《渑水燕谈录》、《茅亭客话》、《曲洧旧闻》、《却扫编》,都是小说异闻类。而到了明清两代,书坊极度发达,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统计,明代南京可考者94家,杭州可考者25家,苏州37家,建阳84家;清代北京114家,苏州57家。“明代两京国子监及各省布政司衙门刻了不少制书、官书及一般所谓正经书,远不能满足社会上的需要,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在南京、北京、苏州、杭州、徽州、建阳的书坊上,尤以后者能迎合顾客心理,书坊主人自己或请人编写了很多举业切要的八股文试策、字书、韵书、杂书、类书、小说、戏曲及带图书。”又写道:“文学类有诗文总集及汉、晋、唐、宋、元、明各家文集六七十种,同时又出版了大量通俗文学书籍,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列国志》、《西厢记》、《全像牛郎织女传》、《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琵琶记》等。万历甲午双峰堂余文台梓《水浒传》云:‘《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十余副,全像仅一家。’《三国志演义》就有余象斗、刘龙田、熊冲宇、杨起元、杨美生、黄正甫、郑少垣等家版本,多为上图下文连环画式,成为畅销书。”⑦又据黄仕忠为《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丛刊》所作序言,现在尚存的《西厢记》明代刊本,就有六十余种⑧,其中多为坊刻。如起凤馆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玩虎轩元刻崇祯间补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文秀堂原刻金阊十乘楼印本《新刊全像评释北西厢记》、明末笔峒山房刻本《新刻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等。另有陈旭东、涂秀红《明代建阳书坊刊刻戏曲知见录》一文考证,仅明代福建建阳坊刻《西厢记》就有:黄裔我存诚堂刻本《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刘氏日新堂刻本《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刘龙田乔山堂刻本《重刊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刘应袭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潭邑书林岁寒友刻本《新刻徐文长公订西厢记》、王敬乔三槐堂刻本《重校北西厢记》、萧氏师俭堂刻本《鼎镌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熊龙峰中正堂刻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游敬泉刻本《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⑨。又据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明末又有孙月峰评点、明末诸臣刻本《硃订西厢记》⑩。现在人人尽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经典名著以及《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经典,如果没有明清以来极其发达的版刻,尤其是民间书坊对小说和戏曲的大量印制,就不会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因为它们不似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那样,依靠官方的力量成为国学和地方官府乃至书院的教材得以大量印刷传播;它们的传播主要是因书坊出于营利目的、迎合了读者的需要而大量出书实现的。所以,在古代,由于传播途径的单一,出版印刷对经典的传播与确立,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书坊的出现,固然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但是它却打破了印刷出版的官方垄断,使出版的内容冲开了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的观念,带来小说和戏曲的繁荣。书坊对小说和戏曲的大量印制,扩大了包括四大名著等经典在内的小说和戏曲在读者中的影响,巩固了经典在读者中的根基,为经典的确立提供了契机。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明清两代版刻的小说和戏曲品种很多,但是被确定为经典的却为数不多。比如坊刻历史演义小说,除了《三国演义》外,尚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西汉演义》等等,但是真正可称经典的却只有《三国演义》。这是因为精神产品在某一时期的传播多寡,固然是我们考察经典的重要视角,然而这些作品能否得到长久的流传,却取决于作品自身的质量,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永久而又普遍的价值。小说四大名著和《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传播原因之外,亦有这些作品自身的品质在。坊刻使小说、戏曲这类本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精神产品,不仅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同时也引起士人的关注,并吸引他们积极投身于小说、戏曲的创作和改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品的内容含量、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为作品成为经典奠定了文本基础。如《三国演义》,其故事在宋代就已流传,金元杂剧也多用之,但却经文人罗贯中而闻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勇武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东坡(《志林》六)谓:‘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在瓦舍,‘说三分’为说话之一专科,与‘说《五代史》’并列(《东京梦华录》五)。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如《赤壁鏖兵》、《诸葛亮秋风五丈原》、《隔江斗智》、《连环计》、《复夺受禅台》等,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其在小说,乃因罗贯中本而名益彰。”(11)《水浒传》一书,也是先有民间的口头和书本创作,尔后经过施耐庵和罗贯中等文人加工而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宋江亦实有其人……然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已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12)《西游记》也是如此,在其成书过程中,文人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言:“所以,吴承恩之为罗贯中、冯梦龙一流的人物,殆无可疑。吴氏的《西游记》,其非《红楼梦》、《金瓶梅》,只不过是《三国志演义》和《新列国志》,也是无可疑的事实。唯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采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远在罗氏改作《三国志演义》,冯氏改作《列国志》以上。只要把《永乐大典》本的那条残文和吴氏改本第九回一对读,我们便知道吴氏的润饰的功力是如何的艰巨。”(13)郑振铎的意见就是说,《西游记》同《三国演义》一样都不是文人的原创,乃是文人改编润饰之作,但是,却对小说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小说皆因文人的参与创作,得以成书,并扩大影响。
中国古代的书籍,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的总集类,既有“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搜罗殆尽的文章汇编类,亦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14)的作品选编类。而作品选编类总集,比起全编类总集,流传量大;而且因为选编者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个人修养以及对精神产品的兴趣不同,选编目的和所选作品自然也有很大差异。如鲁迅所言:“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昔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出选本。”(15)虽然不同选本对作家作品有个人不同的好恶评价,但是,依据经典在历代阅读过程中“趋同”和“共识”的规律,历代众多的选本,自然会呈现出判断趋同的倾向,而这种趋同倾向是我们考察经典的重要视角。所以,历代作品选本是我们考察经典如何得以确立的重要因素。譬如宋代的著名词人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等,根据刘尊明和王兆鹏所著《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统计,其存词数量、版本种数和词选篇数都可以反映出其经典作家的地位。下面是他们的统计情况:辛弃疾存词629篇,在综合名次排行榜前30名中,存词数量第1;版本34种,排名第2;古代词选选词235篇,排名第4;历代品评篇数478篇,排名第4;当代词选207篇,排名第1。苏轼存词362篇,存词排名第2;版本23种,排名第6;古代词选选词197篇,排名第6;历代品评篇数861篇,排名第1;当代词选163篇,排名第3。周邦彦存词186篇,排名第21;版本28种,排名第4;古代词选选词320篇,排名第1;历代品评523篇,排名第3;当代词选186篇,排名第2。姜夔存词87篇,排名第54;版本41种,排名第1;古代词选选词153篇,排名第12;历代品评547篇,排名第2;当代词选116篇,排名第5。秦观存词90篇,排名第52;版本33种,排名第3;古代词选选词186篇,排名第8;历代品评452篇,排名第5;当代词选100篇,排名第8。柳永存词213篇,排名第14;版本14种,排名第14;古代词选选词246篇,排名第2;历代品评409篇,排名第7;当代词选71篇,排名第11。欧阳修存词242篇,排名第12;版本18种,排名第11;古代词选选词236篇,排名第3;历代品评258篇,排名第10;当代词选92篇,排名第9。吴文英存词341篇,排名第4;版本18种,排名第11;古代词选选词165篇,排名第11;历代品评325篇,排名第9;当代词选116篇,排名第5(16)。分析以上统计数字,可以得到以下印象:词人作品存世的数量固然是衡量词家重要与否的参照之一,但是和别集的版本种数、历代词的选本选词数量以及历代评论条数相比,其影响的分子显然位居其次。这是因为词人的词存世多少,有多方面原因:既有词的质量的原因,也有词人写得多少的因素,之后才是传播。所以从存世作品多少无法判断词人优秀与否,当然仅凭此项数据也不能判断词人是否为经典作家。但是综合版本种数、词选篇数和词评篇数这些传播情况,应该可以初步判断出词人及其作品在历代优秀与否,并从而确定其是否为经典词人。所以做此项工作的刘尊明和王兆鹏说:“词人的文学影响和历史地位,主要是由历代词评家和词选家予以认定和确立的。词评家通过理论性的阐释、批评和品赏等形式,来判断和评估词人词作的价值、意义、影响和地位;词选家则是通过选择、介绍和刻印等手段,来传播和宣传词人的作品,并动态地显示其文学影响、凝定其历史地位。”“可以看出,词评家和词选家在对待以上词人的态度和评价上,绝大多数都是相同、接近的,有些还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就是说,词评家和词选家在对待宋代这些著名词人及其词作时,其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是大体相近的。这也表明,我们所作的‘宋代著名词人综合名次排行榜’对词人历史地位的排名,乃是历代大多数词评家、词选家的共识。”(17)
近现代以来,期刊成为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据刘增人统计,仅文学期刊,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就有3504种之多(18)。由于期刊发行量大、传播迅速和连续性传播等特点,拥有众多的读者群,因此对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而言,其重要作用既类于古代的选本,又比古代的选本影响更大,尤其是中国现代精神产品中经典的形成,与期刊的传播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现代,期刊不简单是作品的发表之地,同时也是精神产品的组织生产之地和精神产品评价之地。从组织生产到期刊发表,再到产品出书和推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营销线。因此,期刊不仅成为作家、人文社会科学专家的摇篮,也成为经典潜在的建构者。由于期刊办刊的目的及方向的不同,编者的趣味不同,编者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更带有鲜明的主观性。例如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七月派、左联、文协等等,都有自己的期刊。这些期刊都贯彻了不同文学流派的文学主张,所以一些作家被推崇,其作品得以不断刊出;另外一些作家不被欣赏,作品遭到拒绝甚至批评和封杀,这些都给精神产品的传播带来一定影响。当然刊物都有其特定的读者群,对精神产品传播的影响也多在其特定的读者群内。地方刊物和专业刊物以及同人期刊,其传播有一定的范围。但是,有的期刊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和程度很大,属于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所办《小说月报》,就是一本办刊时间长、发行量广的刊物。据刘增人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称:“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算起,一直坚持到1931年1月日本侵略者炸毁出版该刊的商务印书馆为止,刊行时间在十年以上。”(19)而且发行广及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地区,拥有“数万的老读者和无数的新读者”,“具有全国的影响,乃至海外的影响”(20)。《小说月报》不仅推出鲁迅、周作人等知名作家的作品,还注意发表当时不甚知名的作家作品,培养出了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以《小说月报》为背景而成长起来的知名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朱自清、李金发、徐志摩、丁玲、巴金、老舍等等,这些属于不同流派的作家,大都是首先在商务印书馆的知名期刊露面,然后才一举成名的。”(21)“粗略统计,在商务版的‘小说月报丛刊’和‘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出现的著名作家除冰心、许地山、叶绍钧之外,还有徐志摩、周作人、朱自清、王统照、鲁迅、黄庐隐、孙伏园、沈雁冰、郑振铎、老舍、李金发、朱湘、刘大白、顾一樵、敬隐渔、瞿秋白、王以仁、徐玉诺、张闻天、梁宗岱、许杰、张天翼、萧乾、蹇先艾、巴金、卞之琳、艾芜、李健吾、李广田、王任叔、沈从文、靳以、熊佛西等等。另外还有许多著名译者、理论家。这些作家的成名,大部分都是经过商务的文学期刊——主要是《小说月报》的一番策划,由期刊走向了丛书。”(22)从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与现代著名作家的关系,可以发现,在期刊媒体十分发达的现代,作家与读者交流的渠道,由古代发行甚慢而且数额有限的单本书籍,变为以期刊为主。不仅如此,期刊同时还扮演着读者阅读指导者的角色,它评价作品的优劣,扩大或减损作家及其作品的声誉和影响,因此,作家的成名越来越依仗期刊。正因为如此,期刊也成为潜在经典的孕育者。从《小说月报》来看,在其旗下,不仅汇集了鲁迅、周作人等经典作家,同时还培养和推出了冰心、巴金、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等经典作家。
到了当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传媒上的广泛应用,精神产品传播的媒介和途径异常发达,精神产品已经不再是少数作家、学者的专利,也不再单靠书籍而传播,这给大众参与精神产品的生产以及精神产品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带来了便利,由此产生了网络文化。有一些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与经典相对立的文化,大众在网络上的文化狂欢,就是对经典的消解。孟繁华在《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章中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的关系,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虚幻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23)其实网络文化与经典既非完全对立,亦非没有矛盾。网络文化的基础是大众,大众写作,大众传播,大众评价,是其主要特征。经典自然是文化产品中的少数精品,但是作者之众,传播之广,乃是建构经典的雄厚物质基础。因此可以预测,流传于未来的当代经典,有的可能就产生于当代的网络作品;而经典作家,有的可能就来自网络的无名写手。不仅如此,现代传媒的高度发达,从理论上说,经典和当代优秀精神产品也因此而应该具有快速拥有广大读者的条件。但是我们要看到,实际情况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也给经典的生产、传播和确定,带来了诸多变化和不确定性。就网络写作而言,互联网自由的发表空间,确实给大众的精神产品写作与发表提供了广阔天地;相对宽松的检查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少禁忌,也激发了创作者的自由想象。这些自然都是网络传播手段给精神产品生产带来的解放。但是,以互联网为发展趋势的现代传播手段,传播快,更新亦快。快速更新带动了精神产品生产的快速度。然而经典恰恰是经典作家沉潜相当长一段时间思考与打磨的产物。如果作者没有定力,被网络的更新速度所左右;更有甚者,被媒体或利益所牵绊,其精神产品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影响到优秀精神产品的产生。
从传媒手段来看,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播媒体,分化为传统媒体和现代大众传媒两种类型。而这两种类型的传播媒体,对于精神产品的传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传统的传播媒体,如书刊等,有一部分已经向着大众化方向发展,向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大众化方向靠近,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媒体还在坚守着传统,以发表纯文学作品和学术性作品为主,并以阐释和创造当代文化精品作为自己的责任,是当代传承经典、传播经典精神的重要阵地。而现代大众传媒,则表现出明显疏离或颠覆经典的倾向。现代大众传媒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其传播手段的迅速快捷,同时还体现在其受众范围的极其广泛。所以追求传播的受众范围、收视率、收益的最大化,既是其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其利益所决定的。如王一川主编《大众文化导论》所言:“作为感性愉悦型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背后的商业机制显然起着极为重要的塑造作用。保持大量受众、充分占有市场、通过审美娱乐的提供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这是电视产业作为大众文化在生产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制约性机制。”(24)就客观原因而言,经典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产品,其思想的高度、内涵的深度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阳春白雪,对以视觉影像及快速传播手段为主的大众传媒来说,自然成为其传播的一个短板。而就主观方面来说,投合普通受众的文化水平和趣味,以追求受众范围之广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利益的最大化,亦是现代大众传媒疏离经典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经典作为文化遗产,亦是现代大众传媒无法回避的重要文化现象。对于这样的文化现象,现代大众传媒既然不能轻易绕过,就要设法把它转化为可以传播并且能为受众接受的文化资源,因此经典也成为现代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之一。
考察经典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关系,重要的不是看大众传媒是否传播了经典,而是看其如何传播经典。那么,现代大众传媒是如何对待经典的呢?从形式上看,现代大众传媒传播经典,主要是改编和讲授两种。改编经典,无论中外由来已久,发端于电影,延展到电视。而利用现代大众传媒讲授经典,如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则是中国近年的新事物。无论改编,还是讲授,对待经典一般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真实地想要传播经典、力图忠实于原典的态度,如1987年版的《红楼梦》、1986年版的《西游记》、1995年版《三国演义》等;一种则是非严肃地对待经典,或解构经典、或利用经典,把其作为材料,另搞一套的态度,如1995年在中国港台和内地放映、并且在高校热极一时的《大话西游》。但是,无论是严肃对待还是非严肃对待,现代大众传媒下的经典传播,都带有明显的削平经典思想高度、减损经典内容深度,以投合大众接受水平的倾向。譬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其讲《史记》、讲《汉书》,讲中国古代名著等等,都带有古代勾栏瓦舍讲史的特点,一讲之中,十之七八是在讲故事。当然也有讲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的,如于丹讲《论语》和《庄子》。但是,无论是出于普及的局限,或者是受制于编导以及主讲者的思想和专业水平,所讲内容,多比较肤浅。如在“百家讲坛”上讲过的《于丹〈庄子〉心得》就颇具典型性。本来,在中国古代先秦诸子中,《庄子》最难讲,其原因不仅仅来自其“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25)的表现形式;更在于《庄子》“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的思想,以及其思想内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26)的深刻。对于这样一部经典,主讲人能够以轻松之语,讲述其内容,自有其普及经典之功在。但是,主讲者不把《庄子》作为经典来对待,却给讲述定了认识水平不高的调子:“《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27)这自然不错,反映的是《庄子》这部书的实际,但是又说:“在所有的先秦经典中,它也许是最不带有经典意味的,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奇思异想。”(28)这就颇叫人无法理解。显然,“奇思异想”,不是主讲者把《庄子》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原因。如果这样看,就把主讲者的水平看得太低了。主讲者之所以说《庄子》不像经典,恐怕并未认识到《庄子》的奇思异想,并不是思想的片段,而是有其思想体系的,并且都是出于庄子对于社会人生深刻的思考。然而于丹讲《庄子》,为了使《庄子》的思想嫁接到当代人的生活实用,则把庄子的类似于《逍遥游》中的大鹏之思,降低为枋榆间的蜩与学鸠之飞。如《庄子·逍遥游》篇,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的是庄子面对个体人的生存困境所展开的极为深刻的思考,逍遥游就是他思考的结果。这一思想的本质,就是摆脱所有对人的精神的束缚和制约,追求个体人精神的自由境界。这一境界的基本特征表面看起来描述得很神秘,所谓“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六极之外”,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其实质就是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既要外物——超越现实,同时也要外生——超越自我,与道为一,达到一种合于道的自然状态。于丹说:“我们知道,庄子是大智之人。大智慧者,永远不教我们小技巧。他教我们的是境界和眼光。”(29)这段话讲得很好。但是,于丹讲的境界和眼光是什么呢?因为此书是心得,没有严格的逻辑,亦缺乏明晰的表达,因此非耐心寻觅,很难得其要领。但是认真阅读于丹的心得,还是可以看出,于丹实际上已经把庄子的自由境界降格为人调整自己心态的三个方面。首先,此书认为,调整人的视野宽窄和人的识见的短浅与长远,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由此而带给人不同的效果和人生。如同此书给读者介绍《隐藏的财富》里的故事一样,哥哥目光短浅,只能在金矿上种菜;而弟弟换了一种眼光,则在菜底下发现了一座金矿。因此,于丹在此书的第16页至18页,告诉读者,不要安于现状,要跳出自己现有的经验系统,换一种方式生活,让自己目前所拥有的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只要打破人的常规思维,用一种完整的眼光看待事物,就可以使人实现有用和无用的转换,人们就能够抓住从眼前走过的每一个机遇。因此,于丹提醒读者,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要问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自己“究竟有哪一点是不可替代的”(30)。其三,在现代社会,不要急功近利,要有一种大境界,这个大境界就是人生的觉悟,“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31)。其实稍微懂得一点《庄子》的读者都会知道,于丹关于《庄子·逍遥游》的前两点解释似是而非,根本与庄子无关,或者说违背了庄子的精神,因为庄子“逍遥游”的实质就是要超越现实与自我,而于丹之所讲落脚点恰恰正是在现实与人的自我。抛弃眼前的遮目一叶,不过是为了谋取人的更大利益而已。所以于丹教给读者的不是超越,而是讨巧,是谋求更大利益的机心。这岂不恰与庄子的精神超越和由超越而获得的精神自由南辕北辙!第三点解释表面看来似乎与庄子的超越现实和自我比较接近,至少提倡“看破名利”这一点还是符合庄子精神的,但是再深究一下,于丹所说的觉悟又偏离了庄子的原义。在于丹看来,看破荣华富贵、是非纷争,目的是有一个快乐人生。然而庄子“逍遥游”之意,不仅要做到无物,即超越外在生死功利的束缚;还要做到无我,摒弃人内在的欲求乃至情感的负累。《庄子·庚桑楚》云:“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32)庄子所说的四个方面各六种使人胸中不正的因素中,除第一方面的六种属于外在的物累之外,其余三个方面的十八种都是属于人的主观范畴,其中就包括于丹所提倡的快乐情感。庄子认为,人的精神若想获得充分的自由,首先就要解除所有来自个体人自我心灵的枷锁。就人的情感而言,不仅恶怒哀等负面的情感要解除,喜乐等正面的情感同时也要解除,由此才能进入无心无情的状态,保持内心纯然的宁静。于丹所谈至多只浅涉到了庄子“逍遥游”无物中的名利部分,然而“逍遥游”的关键恰恰在于无我。从逻辑上说,只有做到无我,才可能做到无物。因为执著于个人的快乐,必然无法实现无物,最终仍旧深陷于物我的负累之中,精神不得自由。当然,在书的第八部分,作者对庄子“逍遥游”有了更集中的解说,而且与前相比,也开始接近庄子,讲“解心释神”,即“解放自己的心灵,释放自己的魂灵”。如说:“天地万物纷纭,应该回归各自本性,浑然不用心机,其本性才会终身不离。如果使用心机,就会失去本性。”(33)“人的本性是无羁无绊的,只有释放了人的本性,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34)但是,一旦离开对庄子原话的串讲,谈起作者自己的心得,文章马上就从九天回到了榆枋之间。如说:“庄子一向不崇尚人的刻意,一向不崇尚人的矫情。”(35)把庄子的提倡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理解为不刻意,不矫情,就是对庄子原意的浅解或曰半解,因为庄子所说的自然本性,是从根本上反对人为和有情的,不仅仅是反对人的用心专心而为和违背常情而已。因此,庄子反对所有的对幸福与快乐的追求,包括刻意的和非刻意的追求。当然这还仅仅是望庄子门墙而不得其入的问题。于丹又说:“人生的幸福快乐,其本身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刻意追求,往往得不到,但如果认真地生活,幸福快乐就永远跟随着你。”(36)这就与庄子渐行渐远了,因为在庄子那里,既然坚持要回归自然人性,就必然反对所有的用心,反对所有的人为,而认真生活恰恰是用心之深者、人为之至者。在《于丹〈庄子〉心得》一书中,这种似是而非的解说比比皆是,如把“道”解释为规则,把“道法自然”理解为自然之中皆是道理;把“以天合天”,解释为不违背规律;把“心养”解释为修养心灵,看清自己;把“心斋”理解为回归心里,确认自我真正的愿望,等等。这既有作者理解的原因,亦有在现代大众传媒条件下,编导和讲解者投合观众的原因。虽然,作者和编导都没明言受众是哪些群体,但是,从作者的讲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面向的是职场的青年,并且把抚慰这些受众的职场失意和工作所带来的压力作为讲述的目的。他们既要贴近这些读者的关切,同时还要照顾到其接受能力,因此,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尽量用穿插的小故事来调节气氛,如同戏曲中的插科打诨,都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争取有更好的收视率。而其付出的代价,就是减损经典的内涵,降低思想的高度,甚至曲为之解,把庄子这只薄天而飞的大鹏变成抢树数仞的麻雀。在本文中,无意过多涉及此中问题,仅举个例以见现代大众传媒传播经典降格以媚众之一斑。
在现代大众传播下,不仅媒体本身面对经典出现了分化,而且也给经典的评价造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其表现如下:
其一,媒体的传播程度与精神产品质量的不对称性。
经典必然是传播久远、而且是拥有广大读者的精神产品,但是这里所说的拥有广大读者,是从漫长的阅读历程角度来说的,而不是就某一个时期而论的。具体说,有的经典可能在某一时期颇受欢迎,而且不同时代、不同时期都是阅读的宠儿。譬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李白,在唐代就有广泛影响,虽然宋代对他的评价有所贬低,与另一位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评价相比,影响有所降低,但是在元明清三代之后,又恢复了他的盛名。有的经典在某个时代或时期,却相对比较冷寂,读者较少。如陶渊明沉寂于当时,初知于百年后的梁代,终负盛名于宋代之后。但是,凡经典都会传播久远,从总体看,经典拥有的读者无疑是众多的。所以,以读者多少来衡量经典,历时性有效,共时性未必有效。现代的传媒,因为技术手段先进,打破了传统的传播手段下精神产品先在一个地区的少数人群中传播,然后逐渐扩散到更广大人群的局限,具有了迅速扩散、无有界域的特征,因此会常常见到一部作品迅速窜红、作者一夜成名的现象。但是,迅速拥有众多的读者,是否就意味着作品有着很高的水平,具备了经典的品质呢?这个问题无法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有一点确实可以肯定:即从历时性有效和共时性未必有效的验证来看,在发达的现代传媒条件下,精神产品仅凭其一段时间内拥有读者之众,还无法判定它的水平之高,当然也不能预测、更不能确定其是否可以成为经典。也就是说,精神产品在短时间内拥有众多的读者,有的可以和作品水平之高成正比,有的却不能。个中原因比较复杂。
现代传媒的出现之意义,在于带来了一场精神产品传播途径的革命,这还仅仅是意义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产品的解放。在以传抄和印刷等传统介质为手段的传播阶段,精神产品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少数拥有文化的贵族和知识人(即中国古代的士人、士大夫),既是精神产品的创作者,又是占有者。而现代传媒则打破了这种局面,使大众也成为精神产品的创作者和拥有者,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和文化解放运动。但是,精神产品普及之后,马上面临的则是精神产品以及精神产品占有者的提高问题。而现代传媒恰恰居功于精神产品的普及,掣肘于精神产品和精神产品占有者品位的提升。之所以如此,从中国与外国的实际情况看,问题即出在传媒对集团利益的追逐,使其故意忽略了精神提升的责任,结果就是迎合大众现有的精神品位,表现为削平思想高度,追逐时尚。而大众的时尚,就精神产品阅读而言,更多地表现为快餐式的消遣文化和娱乐文化。因此我们既应看到现代传媒造就了传媒大众,也应看到大众文化也造就了大众传媒。基于以上所分析的情况,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传媒下,一个作品利用传媒迅速而广泛地占有读者,达到一夜成名,是作者、传媒与时尚的合谋,而非常规所理解的精神产品质量发挥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如果说在媒体不发达的古代,基于传播的数量,能够从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考察是否经典的话,在发达的现代传媒环境下,仅据精神产品一时传播的多寡,已经很难判定精神产品的质量,所以也不能以之作为判定经典的依据。有句话说得好:时尚未必经典,经典未必时尚,此其然也。所以,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时间在经典确立中克服时尚的作用,就更为凸显。
其二,评价信息的多元和虚假性。
现代传媒条件下,对精神产品评价的信息日益多元化。旧有的官方评价机构自然还是评价的主体,如中国的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欧美的教育和文化机构等等。但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兴传播形式的快速发展,个体对精神产品的评价,打破了官方和少数人文学者的垄断,通过网络传播而得以实现,体现了不同层次人群价值判断的评价信息,呈网状弥漫式特征迅速扩散开来,对来自少数评价机构的评价信息形成挤压之势,或顺势趁风扇火,或壁垒分明形成对峙,由一元而多元,众声喧哗,这自然是值得庆贺和欢迎的精神产品评价机制的进步。但是,这种大众的网络声音,是一种纷纭无序、泥沙俱下的评价信息,也造成了对一部作品判断的困难。如在中国,一部作品,会有官方、学院派学者和大众都公推说好的情况,但是也有学院派学者评价甚高,而网络大众却一片嘘声的现象;或者相反,网络大众一致推许,但是却遭致学者的坚决否定;或者官方评价机构评为优秀作品,但是却遭到普通读者的冷落。譬如,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红楼梦》和于丹讲《论语》的节目,在一般观众中颇受欢迎,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也创下很高的发行记录,但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中却多评价不高或很少给予关注。既有无数的拥趸者、无数的粉丝,也会有无数的批评声和反对声,成为现代传媒下对待精神产品常有的现象。这给读者的阅读选择与判断,带来不小的麻烦。过去,在精神产品旧的评价机制下,少数学者是精神产品评价主体,对精神产品的评价颇具权威性,因此也成为读者阅读的引导者与辅导者。现在则不然。学者的意见,或湮没在嘈杂的众声之中,或失去了导师的光环,成为众声之一。此种情况,对于习惯于精神产品旧的评价机制的社会而言,实在是一种挑战。谁来评定其优劣?似乎已经成为问题,更何况经典的确认。事实情况是,学者仍然还是精神产品评价的主体,但是大众对精神产品的声音不能不影响到学者的评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学者对精神产品的评价,从而形成学者与大众评价整合的新的精神产品评价机制。而读者对精神产品的选择与判断,也必然适应这种新的评价机制,做出调整。
不仅如此,对精神产品的评价,在现代传媒条件下,往往伴随着虚假性。在网络环境下,由于评价主体的非真实性、身份的虚拟性,造成精神产品评价主体与评价意见本体不对接,精神产品评价主体或托名,或遁身,或置换,因此评价主体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意见不负任何责任。在此情况下,受利益的驱动,恶意炒作的事件层出不穷,评价道德缺失。以作品的点击率为例,有真实自然的点击率,也有受雇佣的“水军”的点击率。因此,从点击率无法真实地判断作品受欢迎与否的程度。还有,是否点击就是阅读了呢?也不尽然。既有点击而且完全阅读了网络传播作品的情况,也有虽然点击了此作品,却没有阅读或者读之半途而弃之的情况。因此可见,网络评价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精神产品的判断,尤其是经典的确定,就更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克服现代传媒下对精神产品判断的不确定性给经典确定带来的困难。
注释:
①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②参见《文艺报》2012年12月12日“本报综合消息”《莫言领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③爱德华·希尔斯认为,积存的传统,有的会被沿袭下来,有的则变为没有生命力的积存,处于无法发展的状态,详见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27页。
④《金圣叹全集》第二册,陆林辑校整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页。
⑤⑥⑦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第66—68页,第272页。
⑧黄仕忠:《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丛刊·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⑨陈旭东、涂秀红:《明代建阳书坊刊刻戏曲知见录》,载《中华戏曲》第43辑。
⑩(13)郑振铎:《西谛书话》,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4页,第47页。
(11)(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5页,第145—146页。
(14)《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一八六《总集类序》。
(15)鲁迅:《集外集·文选》,《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38页。
(16)(17)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141页,第149页。
(18)(19)(20)(21)(22)刘增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第3页,第76页,第76页,第79页。
(23)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24)王一川主编《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5)(26)《庄子·天下》,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53册第130页,第53册第130页。
(27)(28)(29)(30)(31)(33)(34)(35)(36)《于丹〈庄子〉心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第2页,第21页,第22页,第26页,第107页,第103页,第111页,第111页。
(32)《庄子·庚桑楚》,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53册第95页。
标签:大众传媒论文; 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读书论文; 西游记论文; 西厢记论文; 琵琶记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