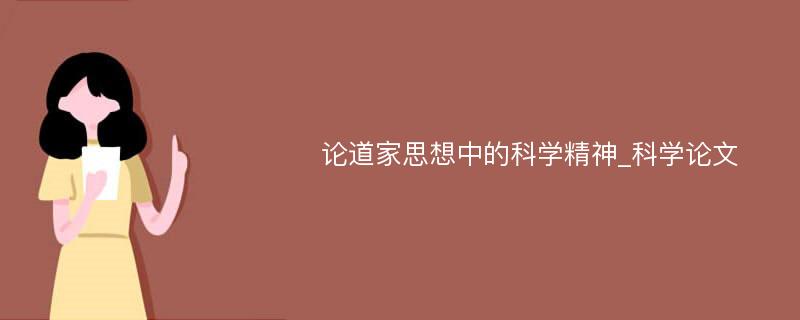
论道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没有“散文”概念之前,人们就用散文写作一样,在“科学”概念诞生之前,人们也有了科学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把炼金术士叫做“化学家的祖先”、李约瑟把道家称为中国科学的先驱者的缘由。佛讲来世得福,道说即世成仙;前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后者必须承担风险责任,因为佛无对应后验,而道却有现实“验证”,让“验证”把“风险”压低到最小限度,是其全力以赴的动力。这就是求“真”去“妄”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就是那时的科学精神。只是这种精神一方面淹没在许多玄妙甚至荒诞的形式中,另方面也从未被其创始人意识到。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阐明其本来面目,剥去其神秘外衣,就成为可能的了。下面,拟逐一加以分析。
一、道统万物,尊道循道的理性精神
“道”是道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范畴,这一关于世界总体和本质的理性观念,否定了上帝、鬼神等传统人格神的主宰地位,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又是统领、支配天地万物和人的总规律、总法则:“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下引该书,不注书名);“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庄子·渔父》)。由于“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规律,故人类必须循道而行:“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尊道”而“不敢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不强作妄为,以求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庄子·养生主》中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强调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重要性,启示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道”这一自然规律,进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
以上论述包含了如下观点:第一,对于“道”这一世界规律存在和可理解性的坚信,否定宇宙由神权支配;第二,天地万物和人类虽然纷繁万端,但皆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本源,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统一性;第三,天地万物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无视规律而主观妄为,而只能尊重和因顺“道”这一世界的根本规律。这些思想正是科学理性精神的基石,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92页),对于世界的统一性、简单性的坚信和追求,是科学家们进行科学探索活动的“积极的动机”。
中国科技史的事实也说明,正是上述因素推动着道家探索自然和人类生命之奥秘,“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以求体悟“道”这一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在《老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等众多道家著作中,都记载了作者探索自然的真知灼见,我国天文学的重要流派“宣夜说”、“浑天说”的形成就与道家“道”、“气”等学说有密切联系。(见吕子芳:《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黄帝内经》也认为,只要能够认识和掌握“大道”这一本质规律,就能触类旁通,由浅及深。《素问·气交变》说:“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可见,道家为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武器。
二、率性而行,探玄索隐的人生旨趣
由循道而行、顺应自然的原则,又导出了物各有宜、率性而行的主张。《庄子·至乐》篇中说:“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这就启示人们,万物各有特性,各有好恶长短,应该充分认识和因顺万物的特性。《淮南子》的《泰族训》、《主术训》等篇章中更是明确提出“物各有宜”、“各便其性”、“率性而行”等主张。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庄子》,将顺性、无待的人生哲学发展为“独化”、“自生”的主体精神。他认为,万物独立生长而无所资借,“独化于玄冥”。任何事物都是自己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郭象:《齐物论注》),“无待”于任何力量的主宰。故应“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从事物的内部寻求力量,才能够“任而不助,则本末内外,畅然俱得,泯然无迹”(同上)。沿着“独化”的思路,郭象向往“因众之自为而任”(郭象:《在宥注》),“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郭象:《逍遥游注》)。
这些思想充分肯定了不同主体的多样性及其价值活动的多元化倾向,突出了主体自身的力量,有助于发现和肯定人的自我价值,确立起从事科学探索所必需的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道家这种人生旨趣为探玄索隐的科学活动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从那些对高超的解牛技术的生动描写中,人们不仅感受到那位率性而行的庖丁“好道”而“进乎技”的求索兴趣和热情,更体现出作者循道率性的思想主张和追求本质规律——“道”高于追求具体技术的价值取向。对行为主体而言,“技”主要是谋生的工具,它是与世俗的功利联系在一起的,而“好道”、“率性”则是超越了功利层面而达到了精神的升华和人性的觉醒,它涵蕴着一种乐于探索的可贵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轻视科学技术、扼杀个性和自主精神的氛围中,它启发人们认识到主体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从而突破“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观念,从皓首穷经、科举入仕的狭隘道路中超脱解放出来,在广阔的大自然中上下求索。
三、兼收并蓄,公正不偏的倾向
物各有宜、率性而行的思想主张又逻辑地导出了宽容不苛、兼收并蓄的气度。宽容精神是道家学派的共同倾向,《道德经》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第二十七章)圣人能够包容一切,兼收并蓄,因性而治,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庄子》体察到个体的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故书中强调“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天下》);《淮南子》亦强调应充分认识人才的特性,使天下之才“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无可弃者”;玄学家郭象更在注解《庄子》时阐明广采众长、兼收并蓄的重要性时说:“己与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专制天下,则天下塞矣,己岂通哉!”(郭象:《在宥注》)“以一己而专制天下”是封建独裁专制统治的特征,郭象指斥其导致“天下塞”的弊端,代表了道家人物对封建专制制度阻碍思想文化发展的批判态度。
道家思想中还蕴含着中立性的倾向。郭象在注《庄子》时对这一思想作了深入的阐发,他反对封建统治者固执己见、禁锢民众的思想,斥责“以得我为是,失我为非”的文化霸权,认为“物无定极,我无常适,殊性异便,是非无主”(郭象:《秋水注》),反对以权威者的个人意见或人为的固定标准去评判万物。这既是对唯我独尊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的深刻批判,亦启示现代人类放弃自以为是的狂妄,表达出一种非伦理、非情感的理性精神和客观精神。这种中立性倾向正是科学精神的要义之一,正如巴伯所说,这种“感情中立的价值,它是实现完满理性的手段和条件……它能扩大理性实践的范围及其威力”(B.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5页)。 因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只有保持中立性,才能作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描述和理解。
兼收并蓄、中立不偏的主张凸现出道家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追求,弘扬这一精神是极具意义的。从本质上说,科学概念和理论是人类思想的自由发明,是一种自由创造活动。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会由于知识背景、观察角度、思维方法、知识结构和认知程度等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结论或观点,形成不同学派,但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不同侧面,都或多或少蕴含着真理的颗粒,即使是谬误,也能从反面给人以启迪和教训。因此,尊重并能够宽容地对待这一切,允许各种意见或学派的并存和自由争鸣,才能促进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克服片面性,取长补短,促进科学技术的更新与发展。
四、不为物役,宠辱不惊的独立风骨
爱因斯坦曾分析人类投身于科学和艺术的动机说:“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1页)道家的人生旨趣与这种精神也是不谋而合的。
道家主张超越世俗的物质欲望,倡导淡泊名利、俭啬寡欲的人生态度。老子告诫人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不要为财货物欲或名利地位而抛却人格,丧失自我;庄子反对“丧己于物”(《庄子·缮性》)。这种价值取向,不是来自外在的权威或舆论压力,更不是出于某种冀利望誉的需要,而是出自主体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的热爱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道家认为,人生的真正幸福或快乐不在于外在的感官享乐:“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务矣。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依靠外在的物质享受所获得的快乐是短暂而且浅薄的,“有主于中”的精神充实和“以内乐外”的精神快乐才是持久和可贵的。这种崇尚与自然相和,追求精神充实的信念,可以引导人们致力于科学探索、理论研究等创造性活动。
道家还以“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的宽阔胸怀和祸福相倚的辩证智慧,引导人们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来看待物质利益和眼前得失,启迪人们不要为声名、财货这些世俗利益而丧失了自我,扰乱宁静的心灵,损害身心健康,而应“安时而处顺”、“不与物迁”(《庄子·养生主》)。这既是一种淡泊名利的高贵品德,又体现出宠辱不惊的心理调适能力。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宠辱不惊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心理素质。这是因为,科学探索这种创造性劳动具有较大的风险,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发明创造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被众人理解或接受;同时,科学发明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誉、地位容易使意志薄弱者忘乎所以,在鲜花和掌声中走向平庸甚至陷入深渊。而不为物累、宠辱不惊的恬淡心态则为科学家奠定了超越急功近利之辈而创建重大科学成就的心理基地,帮助人们从容坦荡地对待人生历程中的成败得失,既能从挫折和失败中较快地摆脱出来,又能在成功的喜悦中保持清醒和冷静,支撑着科学家不计眼前得失,心无旁骛地向着科学高峰勇敢攀登,从而“达到光辉的顶点”。
五、贵和有度,谦下不骄的协作胸怀
由于老子洞察到“反者道之动”这一普遍规律,为了防止事物向不利的方向转化,《道德经》强调知止知足,贵和有度,“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保持事物的动态平衡。书中还告诫人们不要固执己见:“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第二十二章)这些思想有助于推动科学共同体成员相互合作交流,取长补短,不断地充电加油,并与他人建立起积极联系。这种合作协调能力在科学活动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科交叉趋势的日益加强,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复杂化,都需要科学家们建立起更为广泛和密切的合作关系。
贵和有度、知止知足的主张,对于人们在科学活动中调整与自然界的关系亦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确如卡普拉所言,道家为人类提供了“最深邃的生态智慧”(转引自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在这一方面,道家显然能够弥补西方科学精神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谦逊地顺应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六、求真尚朴,绝伪弃诈的价值观念
老子视“朴”、“真”等品质为最高的理想道德,主张保持淳朴天真的自然本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本质和规定性,“见素抱朴”(第十九章),渴望改变浇薄浮华的世风,使天下“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
真朴弃诈追求人的情性之真,它是推动科研合作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科学事业是合作性很强的事业,以诚相待,斥虚去诈才能产生人际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才能维系科学活动所必需的合作与和谐,才可图事业兴旺。
真朴去诈又体现为对于理性之真的向往,理性之真用于衡量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程度。这更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原则。科学活动的目的是求真,是要获得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斥虚去诈,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才能在科学实践活动中及时地将人们的行为调整到最佳状态,取得预期的效益。
道家求真尚朴、绝伪弃诈的思想是针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虚伪欺诈等各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它启示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应桎梏或违逆人的自然本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合乎人性,如果高科技的发展不以道德和人性为标准,势必造成灾难,甚至带来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现代人类有必要将老庄这一智慧作为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
结语
道家思想中蕴含着值得珍视的科学精神,它陶铸着中国古代科学家所必备的气质,开启着科学家的智慧,激发着他们弃旧图新的创造精神,这就是中国古代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科技文化人才灿若群星的奥秘之所在,也是道家思想为不少西方现代科学家所推崇的深刻原因。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道家思想中蕴含的科学精神未能得到长足发展,这是非常遗憾的。而且,道家所提出的概念较为笼统模糊,缺乏严密的实验验证和逻辑分析,这就影响着人们对于客体进行精确的认识,堵塞了实证科学的发展道路,也限制了自然科学理论的完善和分门别类地深入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又必须融会吸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分析方法和科学精神。然而,无论是现代文化建设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学习,都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根深叶茂,花繁果硕。因此,对道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进行发掘、提炼和整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引、融会西方科学精神,从而铸造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发展的科学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