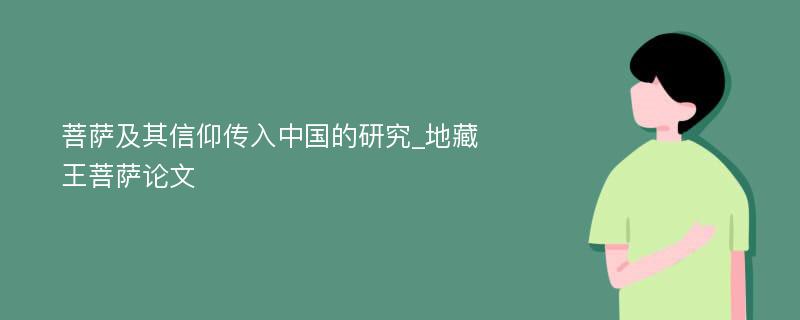
地藏菩萨及其信仰传入中国时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菩萨论文,地藏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2—0063—08
在中国佛教中,地藏与观音、文殊、普贤一起被尊为四大菩萨,他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大誓愿与自我牺牲精神而著称,更以“幽冥教主”的身份和神秘的死后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了普遍的崇敬与膜拜,在民众的信仰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对地藏信仰的介绍与研究已较多,但关于该信仰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还存在许多未明及有争议之处,地藏菩萨及其信仰的传入时代即是其中需要首先加以考察的问题。
地藏菩萨及其信仰是何时传入中国的?这一问题中包含了两个子问题,而以往的回答往往把它们混在一起。实际上,由地藏菩萨发展出地藏信仰,其中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因此对它们应分别予以回答。从笔者收集到的研究情况来看,关于地藏菩萨在中土出现的时间,目前尚无人作出明确的回答;而对地藏信仰的传入时代,由于佛教在流传、发展中的复杂情况以及中国本土文献记载的驳杂,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例如,有学者根据唐代道宣(596—667)所撰《释迦方志》所云“自晋、宋、梁、陈、魏、燕、秦、赵,国分十六,时经四百,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获其将救者,不可胜纪”[1],认为地藏信仰早在三世纪后半已传入中国;① 另有人根据倡导地藏信仰的《金刚三昧经》的译介时代及对其译者的推定,认为地藏信仰在中国的产生,应是从姚秦时代(384—417)开始的。[2] 还有人则根据对地藏信仰的产生影响颇大的如来藏系经典的出现时间,推测大乘佛教化的地藏信仰在印度出现应当在五世纪以后,从而认为中国地藏信仰的传入时间应该在五世纪之后,六世纪中叶以前。[3] 这些说法之间相差甚远,究竟哪种说法与事实更为接近,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加以验证。本文将在考察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得出自己对此问题的回答。
一、地藏菩萨名的传入时代
“地藏”的梵语为Ksitigarbha,其中Ksiti本意为“堪”或“住”,转化而有“地”或“住处”之义;garbha为“胎藏”或“含藏”之义,因此,地藏一词,即“含藏于地”或“地中之藏”的意思。② 在汉译佛经中,“地藏”一词的用法有三:其一指地中所藏的宝物。例如《佛本行集经》中“自得地藏见贫穷”、“尔时兵将见此地藏悉皆是金”[4] ③ 等等;其二用以比喻佛性,如后魏中印度三藏勒那摩提所译的《究竟一乘宝性论》卷四中说:“佛性有二种:一者如地藏,二者如树果。无始世界来,自性清净心,修行无上道。依二种佛性,得出三种身。依初譬喻故,知有初法身;依第二譬喻,知有二佛身。”[5] 另外一种用法当然是指地藏菩萨。
在汉译佛典中,《罗摩伽经》最早提及地藏菩萨。该经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早期译本,“罗摩伽”就是梵文“入法界”的音译。在早期的佛藏目录中,《罗摩伽经》的著录情况颇为混乱。僧祐《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仅著录“罗摩伽经三卷”,不出译者[6] (21页下);法经《众经目录》(以下简称《法经录》)著录为:“罗摩伽经三卷(入法界品)(西秦乞伏仁世圣坚别译)”④,稍后的隋翻经沙门与学士所撰的《众经目录》(因沙门彦琮主其事,故以下简称为《彦琮录》)著录相同[7] (159页上),这也就是今本《大正藏》中该经题录的来源。但是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以下简称《长房录》)关于此经的著录却值得注意,费长房在三处提到这部经典:其一,卷五著录《罗摩伽经》三卷,曹魏时(220—265)安法贤译,并指出它见录于“竺道祖、宝唱、法上、灵祐等四录”[8] (56页下)。其二,卷九著录圣坚所译《方等王虚空藏经》时说:“(乞伏西秦)《方等王虚空藏经》八卷(亦云《虚空藏所问经》,或五卷、六卷,第二出,与法贤所译《罗摩伽经》本同文异,见《晋世杂录》。出《大集经》)。”[8] (83页中) 其三,卷九又说“《罗摩伽经》一卷(第二出,与魏世安法贤者有三卷广略异)”,此为昙无谶译[8] (84页中)。
对比《法经录》与《长房录》,我们首先可以发现《长房录》关于此经的著录存在一个问题。《罗摩伽经》出自《华严经》,《虚空藏经》出自《大集经》,费氏将它们搞混了。这可从上文介绍的“罗摩伽”即“入法界”的音译作出初步的判断,而更有力的证据来自《长房录》本身:卷九录昙无谶译经,除《罗摩伽经》一卷外,还著录了他所译的《虚空藏经》五卷,并指出其“与西秦世圣坚译《方等王虚空藏经》同本异出,出《大集经》。”[8] (84页中) 这就说明《罗摩伽经》与《虚空藏经》完全是两回事,并不是同一个经。不过《长房录》这一错误唐初诸录包括明佺等撰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以下简称《大周录》)均一仍其旧,直到智升等撰《开元释教录》(以下简称《开元录》)时才被发现并加以改正。⑤ 其次,安法贤与圣坚是否都译过《罗摩伽经》,需要加以考察。《法经录》没有说到安法贤的译本,而剔出错误之后的《长房录》在著录圣坚所译十四部二十一卷经中,实际上也没提到圣坚的译本⑥。圣坚又名法坚,“坚”与“贤”形近,因此法坚与法贤很可能搞混,那么两种著录谁的可信度更高一些呢?我认为应当是《长房录》。《长房录》在《法经录》之后,肯定看见过《法经录》,但费氏却在三个地方强调了安法贤译《罗摩伽经》,而且有两个地方都明确地指出了其时代是在曹魏。特别是在第一次著录时,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支持其论点的四种目录。《长房录》中基本上没有直接驳斥《法经录》的言论,费氏这样做,其意或正在辩驳。当然,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圣坚也译有《罗摩伽经》,但《长房录》在肯定安法贤译经的同时,因疏忽而将其遗漏。上文所引《长房录》第二条著录之所以出错,很可能是费氏将《方等王虚空藏经》和《罗摩伽经》两个条目混到一起了。这种可能已为后世目录承认为事实,《开元录》就将圣坚所译经增加为十五部二十四卷,将《罗摩伽经》添加了进去。[9]
综合以上情况,以持论较平正的《开元录》为依据,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罗摩伽经》最早由曹魏时安法贤译出,其后圣坚、昙无谶都有别译,三者仅广略有异,但都出自《华严经》。不过据《开元录》载,安法贤、昙无谶二人所译在当时已是“有译无本”,没有流传下来,圣坚所译现存。在该经中有两处提及地藏菩萨,均在卷上:一是与佛同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的菩萨中有“持地藏菩萨”之名;二是比丘尼为诸菩萨说普依止清净地藏法门。[10] 虽然现在我们已看不到安法贤所译的《罗摩伽经》,但其内容与圣坚所译当相去不远,那么,地藏菩萨之名至少在公元三世纪中叶时已出现并已被传入中土。
《罗摩伽经》既然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异译,通过考察《华严经》或许会使我们得到更多有关地藏的材料,以与《罗摩伽经》相互发明。汉译《华严经》有多种,而以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所译六十卷本(或五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最早。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华严经记》云:“《华严经》胡本凡十万偈,昔道人支法领从于阗得此三万六千偈。以晋义熙十四年(418)岁次鹑火三月十日,于杨(扬)州司空谢石所立道场寺,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胡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时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为檀越,至元熙二年(420)六月十日出讫。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421)辛丑之岁,十二月二十八日校毕。”[6] (61页上)而惠远命支法领等往天竺寻获梵本、法领于于阗遇佛陀跋陀罗是在东晋义熙四年(408)⑦,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该六十卷本所译部分的《华严经》的梵本已存在。⑧
在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圣坚所译的“持地藏菩萨”被译为“大地藏菩萨”[11] (676页上),同样也有佛为众人说“普地藏法门”的记载[11] (715页下);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卷五十五“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十二”中关于“勇猛精进至佛地藏菩萨受生法”的解释:
佛子,何等为勇猛精进至佛地藏受生法?此菩萨摩诃萨,悉于三世诸如来所受灌顶法,一切世界境界无障碍。菩萨悉知三世众生死此生彼,修菩萨行,知诸众生心次第起,知三世佛次成正觉,善巧方便知法次第,知一切劫次第成败。随应众生,显现庄严;成等正觉,显现次第;转正法轮,教化无量无边众生。佛子,是为第十受生法。[11] (752页上)
林天向善财童子阐述了十种菩萨受生之法,地藏菩萨受生法为其中最后一种,也是最高一种。这里的“成等正觉”即是成佛,后文又云:“住是法已,……于一切世界,护持佛法;悉于一切境界,以微妙音说不可说佛正法云。住诸法门趣无碍道,以一切法庄严道场,随所应度成佛兴世,教化成熟无边众生。”[11] (752页上) 也就是说,修持菩萨行,达此种受生法,可以随时成佛了。以地藏菩萨作为此种菩萨受生法的典范,由此可见地藏在诸菩萨中已非一般的菩萨,而是具有了较高的地位,是佛的重要候补者。
二、现存《金刚三昧经》真伪考
如上所述,地藏菩萨名在三世纪中叶已传入中国,至少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已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菩萨,或许对其崇拜在当时或此前已经展开⑨,但这一推测需要得到文献和实物的支持。在实物方面,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地藏菩萨像出现于七世纪中叶,即使是南朝梁张僧繇画地藏像一事属实,其时代也应是六世纪前半⑩。在文献方面,前引《释迦方志》的说法是在唐初地藏信仰已较为兴盛的情况下道宣对几种信仰的一个总括性颂扬,其中的夸饰成分一望即知,显然不能作为地藏信仰于三世纪半已在中土兴起的证据。而自《大周录》以来被认定为北凉(397—439)翻译的、宣扬地藏信仰的《大方广十轮经》其实并非当时所译,这一结论已得到学界公认。因而,在现存的佛学典籍中,最能支持地藏信仰在四世纪中叶已经出现且已流传至中土的当数《金刚三昧经》,但很多证据都显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金刚三昧经》是一部产生于初唐的伪经。
《金刚三昧经》在佛典目录中早有著录。《祐录》卷三“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第三”中收有此经,标为一卷,无译者。《法经录》卷一、《彦琮录》卷五、《长房录》卷九著录的情况相同。这说明,早在东晋(317—420)此经已存在。至于该经的具体译出时代,今《大正藏》中题为北凉,恐怕有问题(11)。《祐录》卷五云:“安为录一卷(今有)。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康宁二年(按:康宁当为宁康,原文误。宁康二年为公元374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6] (39页-40页上)则知道安经录撰成于晋宁康二年。又据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道安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即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七十二岁时去世[12],那么,即使是他后来对经录有增补,也不可能将北凉的译经收入。同样,后凉、南凉、西凉建国时间也都在道安去世之后(12),故我认为,此经如果确实属凉土异经的话,那么可能前凉时期(345—376)已被译出了。
现存《金刚三昧经》共分八品。在第八总持品中,地藏菩萨虽已得文义陀罗尼,但为了普化众生,于是“总持诸品所有文义及忆大众起疑之处”[13],向佛问难,请佛除去大众心中之疑。发问毕,佛对地藏菩萨大加称赞:
尔时如来而告众言:是菩萨者不可思议,恒以大慈拔众生苦。若有众生,持是经法,持是菩萨名者,即不堕于恶趣,一切障难皆悉除灭。若有众生,无余杂念,专念是经,如法修习,尔时菩萨,常作化身而为说法,拥护是人终不暂舍。[14]
如果此《金刚三昧经》即为前述诸录所著录者,那么,地藏信仰毫无疑问在四世纪中叶已出现,并已传入中国,但该经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其被重新“获得”的神话上看,都存在着相当多的疑点。
关于内容方面的疑点,主要是“本觉”、“九识”等名词,以及有人认为其中“理入”、“行入”的概念是从菩提达摩所说的“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15] 托化出来。对于“理入”、“行入”的问题,持此经非伪作论的刘素兰女士认为,达摩到中国,是在《金刚三昧经》译出很多年之后,因此应该是达摩参考了《金刚三昧经》。当然,对“本觉”、“九识”等名词已见于《金刚三昧经》,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是后来的经论吸收了《金刚三昧经》的思想,而不是相反(13)。但刘女士认为本经非伪的一个重要论据——题为龙树造、筏提摩多译的《释摩诃衍论》所依的一百部经典中包括《金刚三昧经》,却是有问题的,因为《释摩诃衍论》除在《长房录》卷十二中引隋代法上之语涉及外(14),《祐录》、《法经录》中都无记录。而且,此后的《开元录》、《贞元录》等亦无记录,故此论作伪的可能性极大。日人永超《东域传灯目录》即指出:“《释摩诃衍论》十卷,释《起信论》,新罗大空山中沙门月忠撰云,云龙树造者,伪也。”[16] 因此,刘女士进一步从对佛陀的“尊者”称呼相同上,将《金刚三昧经》的译者判定为筏提摩多,从而将中国地藏信仰兴起的时间定为姚秦时期,当然也就更值得商榷。(15)
如果说内容方面的疑点还不足以对现存《金刚三昧经》的真伪作出判断的话,那么,该经被重新“获得”的神话则有助于我们对其伪作性质的认定。《祐录》及《法经录》都未标明该经当时是否还存在,《长房录》也不清楚(16),但《彦琮录》卷五明确将其归入“阙本(旧录有目而无经本)”一类之中[7] (176页中)。此后,释静泰编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84)的《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卷五、《大周录》卷十二均认定其有目而无本,直到《开元录》中,此经才重新面世。(17) 其间相隔近一百三十年,如果说此经本存而为诸录所遗漏,实在是说不过去。我们且看该经被重新“获得”的神话:
释元晓,姓薛氏,东海湘州人也。……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任意随机,都无定检。时国王置百座仁王经大会,遍搜硕德,本州以名望举进之。诸德恶其为人,谮王不纳。居无何,王之夫人脑婴痈肿,医工绝验,王及王子臣属祷请山川灵祠,无所不至。有巫觋言曰:“苟遣人往他国求药,是疾方瘳。”王乃发使泛海入唐,募其医术。溟涨之中,忽见一翁由波涛跃出登舟,邀使人入海,睹宫殿严丽,见龙王。王名钤海,谓使者曰:“汝国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宫中先有《金刚三昧经》,乃二觉圆通示菩萨行也。今托仗夫人之病,为增上缘,欲附此经出彼国流布尔。”于是将三十来纸重沓散经付授使人。复曰:“此经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腨肠,而内于中,用蜡纸缠縢,以药傅之,其腨如故。龙王言:“可令大安圣者铨次缀缝,请元晓法师造疏讲释之,夫人疾愈无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药力亦不过是。”龙王送出海面,遂登舟归国。时王闻而欢喜,乃先召大安圣者黏次焉。……安得经,排来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将付元晓讲,余人则否。”晓受斯经,正在本生湘州也,谓使人曰:“此经以本始二觉为宗,为我备角乘,将案几,在两角之间置其笔砚。”始终于牛车造疏,成五卷。王请克日于黄龙寺敷演,时有薄徒窃盗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录成三卷,号为略疏。……疏有广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华,后有翻经三藏改之为论焉。[17]
这里,无论重获《金刚三昧经》的地点、缘由、过程、运送方式,还是对铨次与疏释者的预命等等,都充满神异的色彩,其伪妄之处,一望即知。考元晓生于隋大业十三年(617),(18) 其活动时代大致与另一新罗名僧义湘(625—702)相始终,二人于龙朔元年(661)入唐,咸亨二年(671)义湘返国,元晓之返国,想必亦在此年前后。(19) 则《金刚三昧经》的伪造,当在671年前后至702年之间,它被编撰于开元十八年(730)的《开元释教录》收入,在时间上也是相当吻合的。(20) 此后,《贞元录》明确指出该经现存。而据慧琳《一切经音义》所注解的《金刚三昧经》中诸词来看,他当时所看到的《金刚三昧经》即现存收入《大正藏》第九册者,[18] 因此,现存《金刚三昧经》的伪经性质几乎是肯定的。
三、地藏信仰的产生及传入中土的时代
既然现存《金刚三昧经》不足凭信,地藏信仰传入中土的时代就不应是四世纪中叶,那么地藏信仰产生于何时?它又是何时传入中国的?由于在印度本土地藏菩萨并未获得普遍的崇奉,因而不能为我们提供更为直接的资料;而该信仰发展成为与观音、弥陀等相颉颃并对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信仰是其传入中国以后的事(21),故以上问题可以放在一起来探讨。
日本学者望月信亨与西义雄通过对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的分析,认为地藏信仰的产生深受如来藏思想的影响。(22) 这启发我们从如来藏思想的发展来看地藏菩萨及其信仰的产生问题(23)。如来藏思想发源于公元三世纪,它指于一切众生的烦恼身中,所隐藏的本来清净(即自性清净)的如来法身(24)。这一思想同大乘菩萨观的结合,可能正是以地藏、虚空藏、日藏、月藏为代表的某某藏菩萨命名的原因。在这些菩萨中,一方面,大地所具有的承载、长养的功德,以及坚固、伏藏的特性,正是如来藏思想最好的体现;另一方面,早期佛教中地神在弘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佛陀与地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地神已经具有较高的地位;再加上农业社会中土地与人们生活的普遍联系,这使地藏菩萨很容易从众多的菩萨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那么,这样的崇拜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们知道,佛驮跋陀罗所译之《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地藏菩萨的地位已相当高,是佛的重要候补者。另外,在这部《华严经》中,还出现了“大地天佛”、“大地王佛”[11] (764页中)的称呼,这些称呼除在几部佛名经中有以外(25),并不见于其他经典。这也似乎表明,早已被佛教吸收的地神在大乘化的过程中,一开始同样是以成佛为目的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较早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大方广十轮经》中,地藏菩萨已由佛的候补者,发展成为不入涅槃的大悲菩萨。该经中有多处提到地藏的大悲誓愿:“地藏菩萨,以不思议功德成熟众生,于过去无量恒河沙诸佛所,久发大悲坚固誓愿,皆悉成熟一切众生。”[19] (684页上)“能以正法示众生,作种种形随应说。具修布施诸功德,欲救众生起大悲。”[19] (687页上)为了实现本愿,地藏宁愿不成佛:“我要不舍本愿誓,而亦不住胜菩提。一切众生如如相,亦见群盲受苦切。如是思惟为众生,便能勤修大精进。”[19] (682页中)这很可能是受后期如来藏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早期的如来藏系经典《如来藏经》中,尚无“一阐提”的概念[20],后来,该概念被提出并被用来指称不信佛法,永远不得成佛者。再后来,《涅槃经》中提出一阐提辈也有佛性,菩萨摩诃萨应像父母之爱子、不惜与之并命那样,与一阐提辈同受苦难,只要他们稍有悔改之心便与说法,使其得生一念善根,从而得成佛之根性。[21] 但比《涅槃经》稍后的《楞伽经》仍然坚持一阐提不能成佛,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经提出一阐提有两种:
一阐提有二种:一者,舍一切善根,及于无始众生发愿。云何舍一切善根?谓谤菩萨藏及作恶言,此非随顺修多罗毘尼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二者,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般涅槃,一切众生而般涅槃。……菩萨一阐提者,知一切法本来般涅槃已,毕竟不般涅槃,而非舍一切善根一阐提也。[22]
这段话是说,有两种人不能成佛,一种是不信佛法,心无善根者;另一种是知一切正法,本来已能入涅槃,断诸烦恼而成佛,但为了救度众生,宁愿不成正觉的菩萨。后者被称为“菩萨阐提”,也叫“大悲阐提”。“菩萨阐提”或“大悲阐提”的思想是《楞伽经》最为独特的思想,在汉文佛藏中,除有关《楞伽经》的注解,以及中土僧人所撰的论疏中涉及外,其他经论中都不见此种思想。很显然,《大方广十轮经》中的地藏菩萨,为了救度末世众生而不愿成佛,已是一位大悲阐提。这也就是说,地藏信仰很可能是在《楞伽经》出现之后产生的。
据日本学者高崎直道的考察,《如来藏经》的出现是在公元三世纪前半,但其他同系的重要经典,如《涅槃经》的出现是在四世纪后半以后,《楞伽经》则可能出现在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23] 则地藏信仰的产生也应该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以后,而其传入中国的时代,当然也就不可能早于五世纪。这一推测是与早期几部地藏信仰经典的传译情况相吻合的。剔除《金刚三昧经》之后,早期宣传地藏信仰的经典主要有三部,分别是《大方广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须弥藏经》。《须弥藏经》由那连提耶舍与法智于北齐天保九年(558)译出,后来被合入《大方等大集经》中成为其一分。《占察善恶业报经》真伪情况自隋代以来就有很多争论,但其产生或者说翻译于隋初则是肯定的。相比较而言,《大方广十轮经》的翻译时代较为模糊,在今《大正藏》中该经被标示为北凉时译,失译人,这是根据《开元录》来的。《大周录》卷二说此经是北凉沙门昙无谶于姑臧译,并指出这一说法来自《长房录》[6](384页上),对此,《开元录》卷十一予以了批驳:“检长房入藏录中乃云失译,《周录》误也”[6] (588页下),但《开元录》却又接受了该经译于北凉之说(26)。考现存唐前诸经录,《大方广十轮经》既不见于《祐录》,在隋代诸录中也未标明其译者及译经时代,因此说该经译于北凉显然也是缺乏根据的。今人聂士全先生认为此经乃北齐时译出[24],不知何所据,但此经的译出在六世纪初以后隋建国之前,大致不差。(27)
因此,虽然公元三世纪中叶地藏菩萨的名号已经传入中国,但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传入相对较晚。《须弥藏经》应算是中土有确切翻译时间的最早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虽然《大方广十轮经》的传入时代可能更早一些。那么,至迟在六世纪50年代末,地藏信仰已进入中国。
注释:
①日本学者真锅广济即持此种看法,见氏著《地藏菩萨の研究》,京都:三密堂書店,1960年版,14—15页。
②关于此词的解释,可参考望月信亨主编《望月佛教大辞典》,东京:世界圣典刊行协会,1973年版3597页中。他并认为不空所译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中的Ksāharana亦地藏之梵号,Ksā指地,harana有含摄之意。此外,矢吹庆辉认为Ksitikosa也是地藏之意,见《三阶教之研究》651页。
③本文引《大正藏》原文时,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一些断句作改动,若非必要,不一一说明。
④隋·法经《众经目录》卷1《大正藏》55册119页下。另,“乞伏仁”当为“乞伏国仁”,乃西秦开国之主,其在位时间为公元385年至388年。再,本文所据历代年号及起讫时间,无特别说明,均据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⑤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4著录圣坚译《方等主(王)虚空藏经》八卷时云:“亦云《虚空藏所问经》,一名《劝发菩萨庄严菩提经》。或五卷,是《大集虚·空藏品》异译,见《晋世杂录》及《法上录》。云与《罗摩伽经》同本,非也。”见《大正藏》55册,518页上。
⑥费氏指昙无谶译一卷本《罗摩伽经》为安法贤三卷本之后的第二出,也反映了他将圣坚的译本排出在外。
⑦宋·志盤《佛祖统纪》卷36,见《大正藏》49册,342页中。另,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4还提到汉灵帝建宁元年(168),有北天竺僧人名支法领,曾与人译出《四分戒》等经律,但此支法领并非带来《华严经》者。见《大正藏》49册,604页上。
⑧英国学者渥德尔(A.K.Warder)认为,《华严经》等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主要契经象是在公元三世纪编造的。“固然在某些例子上后来有所附益和修改,但公元四世纪哲学家们有讨论它们的著作,公元三世纪有其中一部分和四世纪时一部很长的大经集(按: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汉语翻译可以确证我们的年历编排。”见渥德尔著《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391页。
⑨此处所说的崇拜指的是如对观音、文殊、普贤等菩萨那样的、有独立性及独特性的崇拜,念诵或抄写各种佛名经时,对佛菩萨的普遍崇拜中所包括的地藏崇拜不算在内。
⑩张僧繇主要活动于梁武帝时期(502—549)。
(11)《长房录》卷九虽将《金刚三昧经》等五部经附于北凉译经之后,但其后的说明中并没有肯定它们即北凉译经。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乃《大周录》,该录卷十一在列举五部经后,明确指出它们为北凉时译,其后各藏录均因之。分别见《大正藏》49册85页上;55册,439页下。另,从《开元录》始,此经卷数亦有两卷一说。
(12)后凉,公元386—403年;南凉,公元397—414年;西凉,公元400—421年。
(13)有趣的是,“本觉”、“九识”等名词在被判为疑伪的马鸣菩萨造《大乘起信论》、龙树菩萨造《释摩诃衍论》中广为运用。《大乘起信论》一卷,有人云梁武帝时天竺三藏真谛译勘,又有人云大同四年(538)出陆元哲宅,种种情况十分可疑,故《法经录》将其判入疑惑。见法经《众经目录》卷5,142页上。《释摩诃衍论》的疑伪情况见下文。
(14)见《大正藏》49册105页上,译者作鸠摩什波,与筏提摩多应是一人。
(15)刘素兰女士对《金刚三昧经》的相关考证及论断请参看《中国地藏信仰之研究》22页,41—43页。
(16)《长房录》卷十三虽将该经收入“大乘录入藏目”中,但在该目之首,费长房曾声明自己“未觌经身,犹怀惟咎,庶后敏达贤智共同扇簸糠粃乎!”所以入目之经是否现存,费氏是不清楚的。见《大正藏》49册109页中。另,《祐录》、《长房录》以个人之力而成,对所录经论未能详考其有无,可以理解,但《法经录》以众人之力编成,且受国家之资助,其录《金刚三昧经》等134经入录仅凭“古录备有,且义理无违”(见《大正藏》55册122页上),不考察各经之有无,实不可理解。
(17)《开元录》卷19“入藏录上”云:“《金刚三昧经》二卷(或一卷),二十七纸。”表明此经当时已存在。见《大正藏》55册688页下。
(18)参看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4“元晓不羁”条,见《大正藏》49册1006页上。
(19)义湘生平事迹请参看《三国遗事》卷3,见《大正藏》49册994页中一下。
(20)《开元录》为何会收入此经,值得探讨。我以为:其一,该经名一直见于诸录,或许智升等对其内容与来源未细加考察;其二,恐怕与唐时藏录之“对既成事实的认定”有关,例如《占察善恶业报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虽然来源有疑问,但因为已比较流行,故亦被收入藏中。而伪《金刚三昧经》中的禅观思想与当时禅学的风行很合拍,这可能导致它被收入藏中。
(21)据真锅广济研究,在《高僧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等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所写的游记中,都没有有关地藏信仰的记载。同时,在西方学者的考古报告中,地藏菩萨多出现在八大菩萨曼荼罗、五佛五菩萨曼荼罗中,这一现象表明,似乎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以前的印度佛教石窟遗迹中,并没有单尊的地藏菩萨像,而只有在密教造像中才能见到地藏。与真锅广济这一研究结果可以相互印证、补充的是,唐初高僧法琳在《辩正论》卷五中提及六位“功被生灵,泽均彼此”的大菩萨时,云:“文殊屈迹于当世,弥勒补处于未来。观音普现色身,惠覃遐劫;地藏护持震旦,化洽无穷……”也特别指出的是地藏与中土的关系。参看真锅广济《地藏尊の研究》,京都:富山房書店,1976年版,14页;法琳《辩正论》卷5,见《大正藏》52册524页下。
(22)西义雄并认为地藏菩萨是最为粹正的“大悲阐提”菩萨,因为文殊、普贤、观世音等菩萨,本来是作为佛的候补者,在如来藏的“大悲阐提”思想出现以后,才成为不入涅槃的大悲菩萨。据此,他进一步指出地藏信仰在菩萨信仰中,是发展比较晚的。我认为,虽然地藏信仰发展比较晚,但地藏一开始并不是一位粹正的“大悲阐提”菩萨,他也曾作为佛的候补者出现。二氏对此问题的讨论请参看: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京都:法藏馆,1946年版489—490页;西义雄《地藏菩萨の源流思想の研究》,见氏编《大乘菩萨道の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77年版129—134页。同时请参看庄明兴《中国中古的地藏信仰》21—23页。
(23)庄明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探讨地藏信仰的产生及传入中国的时代的,但他的研究遗漏的资料较多,特别是回避了对与其推测相矛盾的资料的辨证。
(24)关于如来藏思想的产生及发展情况,请参看印顺法师《如来藏之研究》,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修订版。
(25)如,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失译人附梁录《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三十卷本的《佛说佛名经》等。
(26)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恐怕与玄奘重译《十轮经》之后,《十轮经》被认为是《大集经》之一有关。对这一问题,我将另文予以解说。
(27)《祐录》撰集于南齐建武年间(494—498)。另,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卷一在罗列了包括该经在内的100多部经后指出:“前一百三十四经,并是失译,虽复遗落译人时事,而古录备有,且义理无违,亦为定录。”(见《大正藏》55册,122页上)这表明在隋前该经已被著录。再,《大方广十轮经》在内容上与《须弥藏经》及《月藏经》多有关联,后两经是由北齐三藏那连提耶舍带入中土,并分别于天保九年(558)、天统二年(566)译出,则《大方广十轮经》的携入与翻译估计也在这些年前后。
标签:地藏王菩萨论文; 地藏论文; 金刚菩提论文; 地藏菩萨本愿经论文; 华严经论文; 佛教论文; 楞伽经论文; 大正藏论文; 罗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