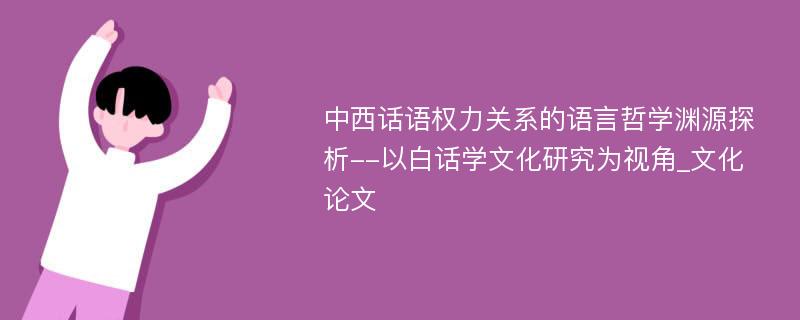
中西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探源——话语学的文化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权势论文,中西论文,视角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2—0170—08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正对传统的科学思维进行重要反思,其焦点是语言。在这一学术思潮下兴起的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或称话语学)是推动这一反思的重要前沿学科。它打开了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为社会学、媒体、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以文本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时也改变着我们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兴起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还没有把它放在东西方特别是自身文化背景下进行思考。批判话语研究与传统语言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以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功能为最终目标,而是通过语言剖析社会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1]60,如全球化、新资本主义、种族与性别歧视、恐怖主义、人权、知识异化、机构运行、媒体,等等。这一研究思路是由20世纪哲学和社会学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带来的,其基本理念是:当代社会重大问题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各种思潮运作和相互作用的产物,本质是话语(discourses)的重组、混杂、渗透、流传、扭曲和支配;社会势力群体(如文明圈、国家、阶层、行业、学科领域)通过语言操纵人的意识,达到维持和重组社会结构的目的。现代性的危机实质上是语言的危机,因此,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是对语言的批判研究,社会变革也是语言的变革[1]。这种新型的语言观(或话语观)是在对以现代性为特征的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后出现的,就像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特别是道家)那样,它把语言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使人们有可能超越西方话语去重新认识多元文化的价值。由于该学科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在社会科学不同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推动话语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经常是西方话语支配下的产物,这样就有必要从文化和语言哲学的层面对这一问题的渊源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话语学研究的方法和课题。
一、中国话语的西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如果将五四之前的中国语言和今天的语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能在公共场合发表的话语不少已是西方语言活动的变种形式,现代中国话语不管是关于社会还是科学的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语言来表述的①。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里充斥了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和用西方理性逻辑化了的语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说话、行事的方式,我们的教育、政府、商业、法律、媒体等社会活动不少是从西方话语模仿来的。由于历史和空间的距离,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哪里来、由谁引进、出于什么目的以及背后推动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话就是我们自己的话,而不知道不少混杂在其中代表权威的声音是属于别人的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比较的不是简单的字、词、句或语法,而是实际使用中的话语活动方式,用话语学的术语可称之为“语类”(genre,也翻译为体裁),奇(Gee)把它理解为一种有别于传统概念的第二语法[2]。 语类是随着社会活动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言语类型,其多样性、复杂性和相互渗透的程度就像人类活动一样不能明确界定和穷尽[3],但它却规范着我们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知识、信仰和认同感(identity),即规定了一种“生活方式”[4]。也许有人会认为是生活方式决定了话语,而不是语言引导生活。其实,这种语言观只是一种假设,以为语言只是反映客观世界的镜子,自身并不构成社会,这恰恰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Fairclough认为,话语“不仅仅反映和呈现社会事物和关系,其本身就构建和构成它们”[5]3,换句话说,语言就是社会,在话语之外不存在文化。我们也可以从索绪尔的语言观里理解这一点,他认为,一种真实(authentic)语言本来存在三角的指向关系:形式、意义和客观物体(signifier、signified、referent),但是由于语言在天性上具有“歧义性”,这种三角关系在歧义滥用中逐渐失落,尤其是当文字篡夺了言语的优先地位时。索绪尔把语言特征表述为:一个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它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而是由该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来定义的,即符号是某一差异系统的产物,它们不是实体[6]97—103。也就是说,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可以只存在双向的指向关系,而不需要与客观世界有联系;代表文化现象的一切语言命题可以纯粹停留在符号内部,语言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割断了与外界经验意义的联系,成为可供人们玩弄概念的游戏,即在一种“空谈”中进行社会活动。这种意义所指的空洞性恰恰就是施展欲望和权力的地方,各种利益群体利用语言去制造社会现象,并通过语言在心灵上达到人的自我控制。于是,语言里便浸透着一种以支配为目的的权势关系,由话语构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简单说就是福柯定义的权力和知识联姻成的话语(discourse)[7]。在西方观念支配下的现代性语言因此越来越朝着没有指向客体的含义方式演变(signification without reference)[8]142,海德格尔用德国诗人格奥尔格《词语》中的一句诗道出了这种语言的本质:“词语破碎出:无物存在”③。
中国语言现代化就是受这样一种话语的支配,我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和模仿的话语活动方式经常是谁也不清楚,或者说根本就无法搞清楚它真正的经验意义是什么。哈贝马斯认为,真实的语言意义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Lifeworld)里④,但是在中文的西化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经历西方生活世界的体验。那些表面上可信的翻译(包括语类),可能完全指代不同的事物。于是借助于根本无法忠实反映事物的语言,我们想像了一个西方世界,并通过这样一种语言实践把幻想转化为真实的社会现实,而且相信这就是我们从西方学来的。经常听说一些西方的行事方式到了中国就会变样,达不到其初衷,这种扭曲的根源就是语言。依赖语言来决定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是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在这种话语霸权支配下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中,中国传统的语言活动,或者说生活方式被贬落到权势结构的底层,被认为是落后、愚昧并应该被淘汰和改造的,因为他们的生存结构不符合我们的语言意识结构。于是,资本朝城市转移,因为那里有西式话语,人们的欲望和目标都朝着能说“西方话”的地方聚焦,“西方话”成为生活的诱惑、思想的对象、先锋的意识、资本集散地和权力战场。四合院被拆除,古老的城区被整个毁灭,其中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蹂躏、嘲讽,并不许发出声音地被淘汰。在西式话语“命名”到的地方,对传统的破坏就随之降临。中国语言西化起因于枪炮带来的物质因果力量(causal power),在摧毁语言的纯洁性的同时,也把语言的真理交给只能靠这种力量来维持的权势关系。中华文明由于扎根于自身生活世界的语言的失落而导致一系列合法性和价值取向的危机⑤。这就是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话语研究的目标。
二、从西方文明离根到中华文明被割裂的语言原因
海德格尔运用批判的眼光探讨了西方文明离根的语言原因,在他看来,从古希腊语发展到现代西方语言的过程中,语言便在转换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发和初始的(primordial)经验意义。“语言向欲望和交易投降,成为支配存在的工具”[9]278,海德格尔称之为离根:
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过程并不是像今天人们认为的那样简单和无害的。在表面上准确和可靠的翻译之中,隐含着把希腊人的经验翻译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这些词语所表达的真实经验。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态即始于这种翻译。[10]
对海德格尔来说,将古希腊语翻译成现代西方语言是对希腊哲学之原始本质的割裂和疏远,由于缺乏原发(primordial)和真朴的生活意义的支撑,这一语言逐渐游离人的存在之根。那么,当这种本来已经扭曲了的语言通过德语、英语、法语甚至日语等再次转换成中文时,其原初的经验意义更加无处寻找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语言风景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西方思潮影响下涌现的新的词、句、语类(genre),准确地说是整个话语活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自然存在, 退一步说中文与西方语言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对应性,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说它巨大,是因为正是这种维持在虚幻意义上的语言在构建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它曾经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
原文:The weapon of criticism,to be sure,cannot replace the criticism of weapons; material force must be overthrown by material force,but theory itself becomes a material force as soon as the masses grip it.
在这里,“群众(masses)”是一个关键字,它本来是一个表示纯粹数量概念的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建立在数量概念上的哲学命题,即理论一旦被一群人掌握时便成为物质力量。但这句话在流传过程中,“masses”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比如在革命运动中,它被赋予一种“正义”的价值取向,理解为人民的力量。我们在转述这一哲学命题的时候, 也不断赋予其不同的价值含义,把“masses”转换为“群众”就是一次语言的改造过程,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文明的割裂和离根的过程。当然,这不是翻译的错误(“群众”一词是“mass”的最好选择),而是从西方文明演变过来的这类语言命题本身的一个问题,它建立在客体和主体的对立和分割之上,让语言本身成为知识,并自我膨胀起来,其中的每一项抽象语义(物质、理论、推翻、力量)都经历漩涡式的转述和流传,每一次都会在无意识中赋予不同的价值,但却没有真实的经验可以参照。这种流传和变化绝不是天真无邪的,它不断注入目的、欲望和冲突的价值观。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话语的特点就是口头及书面的“流言”和“闲话”(gossip),但它却以权威和有自己内在说服力的形式出现,且流传越广就越显得权威:
它不是让事物以原发的方式交流,而是沿着闲聊和流言的途径交流。话中谈论的东西以权威的特征在更广大的圈子里扩散。事情是这样就是因为人们都这么说。[12]
虽然这类“闲话”流传到后来谁也不清楚到底在说什么,但说话者都觉得自己在以严密的逻辑和理性宣示真理。这时语言插在人与人之间,使得交际双方含混不清地相互探摸对方的意图,试探各自的底线,说话双方“在戴着为对方好的面具之下,进行着一场相互争斗的游戏”[12]。但这并不是一切文明的特征,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演变出这类语言,即使像老子、孔子和庄子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用我们今天哲学课中的语言。这不是说中华文明没有这些哲学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中不需要甚至于忌讳用这类语言。著名汉学家陈汉生(Hansen)认为,哲学的问题源于我们普通的言谈和写作,“它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提出来并朝着不同的方向理论化,不是中国人不能把握这些抽象理论,而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13]。但今天,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也无论是机构还是教育,都越来越依赖这类形而上的语言。庄子早就提醒我们语言的危险性,并指出说话者必须有能力先忘掉语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也许正是古代哲人的这些警示在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演变,使其没有发展出这类形而上的语言。
三、语言、思想与话语幻觉
庄子的“得意忘言”告诉我们,意是脱离语言而存在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但当今种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却是靠语言存在并传递的,这就是话语幻觉(discourse illusion)。语言与思想本属于不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把言看作是包装,包装绝不是思想本身,而是为了包装本身的目的而缝制的:
语言给思想着装,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我们不能从服装的外表去推导所包装的思想形式。这是因为服装的外形是完全为了不同的目的造型,而不是为了展现身体。[14]
这种包装物想干什么呢?产品包装是为了寻求经济利益,服装变化在追求流行时尚。现代语言活动就是一种不断随着流行趋势去包装人们追求的利益和权力的行为。比如写作是为了发表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发言(包括被迫发言)是为了表现发言者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位置。而真正属于原发思想的言语则早已被挤出了公共交往领域。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不是存在于被知识对象化了的语言之中,而是在语言之外。叔本华指出:“思想留在纸上只不过是一个沙漠行者留下的脚印。确实我们看到他走过的路,但要知道他一路上看到的,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眼睛看。”中国的风水学说在科学思维下已经很难被人接受。但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语言的合理性应从其展现的生活(即言外)去考察。如人们在谈论风水时,试图构建出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建筑格局,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从事人的生产活动,这种存在形态就是风水语言的真理性。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就是一种游戏,“想像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是不可预知的,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什么依据上面的,它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它就在那儿,如同我们的生活”[15]。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属同样的道理。我们会认为中医理论并不科学,而恰恰是这种非科学语言让身体感觉到一种实在的意义,但我们却经常不愿意用生活体验去判断语言的合理性,而要用从西方流传来的话语,如理性、逻辑、科学分析去测量和论证,结果就得出与生活体验相反的结论,并由此拒绝这样一种话语。这恰恰是现代性话语的悲剧。我们误以为科学符号都是可信的,不能对其进行批判解读,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已被符号窒息时才会发现某些话语的荒诞性,就像城里人自豪地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烦躁空间里炫耀生活质量时,突然发现最愉快的体验原来是在未经科学改造过的山涧湖泊中。
在西方话语逐渐对中国话语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汉语的原发性不断丧失,汉语的每一个字都被注入了上面海德格尔提到的“流言”意义幻觉。索绪尔在区别词语的意义与价值(value)时,认为后者是根本[6]37—47,111—127,因此,即便是字面意思没变,如“忠、义、礼、智、信”,但其延伸意义却发生了变化,被加上了落后、先进、好、坏之类的价值取向。这种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语言大致都会蒙上一种与落后、次等、愚昧有关的内涵,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因为各种权威话语不会把这类语言放在与“真理”相关的语境中来炒作。古人用来探讨知的语言(如道、神)也不断被形而上学化,使其蒙上愚昧和迷信的色彩。如庄子《庖丁解牛》中“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里的“神”一旦放在科学范畴中讨论,就会把庄子的思想打入神秘主义,否定其现象学意义上的原发智慧意境,这种现象就与“神”这一词在种种权威言谈中被滥用有关。当语言被如此表象化后,我们便不再愿意仔细领会庄子的本意,准确地说不是不相信庄子,而是不相信他的语言,不相信那种缺乏权威和科学光环的话语了。这种破坏性更严重的是在语类(genre)层面, 对中国古代哲学价值的怀疑更多地来自于其使用的表述形式。人们不相信故事以及其他传统的叙事、论证方式是一种值得信赖的语类,我们不相信真理可以用诗一样的故事去讨论,这是因为今天的学术讲坛、政府文件、科学辩论中不再使用这种语言语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经常要等西方人,准确地说要靠西方话语来“弘扬”,而把孔子、老庄、四合院、中医等等思想用存在论、认识论、建筑学、医学、教育学的概念去解释和梳理,并最后把它们消解在这些话语范畴中。语言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西方强势话语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支配和梳理的过程,这个让人迷恋的现实可能是建立在西方话语幻觉上的;一个用“进步”、“发展”、“标准化”、“技术化”、“全球化”等话语构建的世界,也许只是强势话语留下的海市蜃楼(discourse illusion)。在那里,真实不取决于生活体验,而是话语的“厚度”和流传声势[16]。
四、话语批判的内涵与对象
什么是话语批判?话语批判是一种语言批判,它不是建立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上,也不是令人困扰的政治对抗,而是对一切建立在语言之上的话语结构的批判。必须承认的是,在实践上,批判经常不自觉地陷入意识形态冲突的误区,这使许多人对批评一词敬而远之。
批评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认识论上的价值。社会科学是通过批判来认识世界的,批判是探索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度阐释和领会的研究方法。用批判的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是把我们的思维带入由生活世界构建的意义视域(horizon),这就是哈贝马斯所指的以解放为目的的交往理性。批判是人能够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认识方式。近年来,国内一些社会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理念的影响,但在表面中立和科学的范式背后却隐藏着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支配性话语体系的认可,并无意识地接受西方话语的支配,由此,一些科学研究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成为纯粹的学术游戏。可见,批判话语研究不仅仅代表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而且还宣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批判也不只是针对语言的字面意义或命题意义,这种在语言中明显阐述的意识形态不是批判的真正对象。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经历了重组,这种重组基本上不是显性宣言,而是隐藏在语言背后,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变迁。推动这种语言变化的是国际强势话语。举例来说,以“机构化”、“标准化”、“国际化”、“数字化”为特征的话语体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管理的一种支配性语言,这种理念以不容挑战和无需论证的假设及隐喻规定着日常管理方式。我们把考试数字化,让学生在这种游戏中丧失基本思考能力;我们按照西方的数字规则去测量学术研究,以为一流高校是由它来表述的,而把支撑学术思想的生活世界——传统和群体交往环境肢解。我们投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里,由它们来决定我们的学术价值。这些数字之所以会起到这样的破坏作用,是因为在数字范式背后隐藏着以功利和权力为目的的价值观,它通过建立可测量的分类(classification)语言项目来施展不被人觉察的权力⑥,不同的意识形态就用不同的类别去划分社会群体,并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形态。比如“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就是少数富国、 强国对世界的一种控制语言,但却又给人一种包括多数人的错觉。事实上,“国际社会”这一概念不是以人口或国家的数量来定义的,而是由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集团及其媒体来代表。北约、欧洲联盟、八国首脑集团,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通过BBC、CNN等媒体定义“国际社会”的概念,而这些机构并不代表真正的国际社会。正是这些国际集团所创造和使用的话语,才造成当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类语言已不能让我们听到世界人民的声音了。
通过话语批判,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带着中国特色的语言活动是如何在进行语言的殖民化工作,那些将中国和西方话语混杂的语言经常是在运用西方的话语逻辑制造社会问题。譬如法轮功,它声称是非政治性的,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词语作为表述工具。他们把中国的传统语言与西方的话语混杂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把人权话语和气功话语捆绑在一起,前者作为“主语”和“谓语”(或称Theme),后者作为“宾语”(即rheme)⑦。法轮功在介入中国政治的同时, 也在破坏中国传统语言的纯洁性,因为气功话语已被所谓“人权”的政治话语所支配,传统的语言就这样被自我查禁。用批判话语分析去揭开语言活动的虚假性,就是要让社会科学时刻检查我们的生存状态,并使自己不会卷入飘忽不定的由话语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轮番冲突之中。
批判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而是对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已经习以为常的具体文本(包括口语文本)的实证分析。因为正是在这些细微的话语物质形态中,我们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是匿名的,没有人能占有它,但却作用于每个人,包括表面上掌握着权力的人。管理者也受制于一定的话语结构,也是话语权力作用的对象,对话语结构的分析恰恰能帮助领导者找到问题的根源。
以上就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语言学起因进行了探讨,目的在于澄清批判话语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深层语言哲学理念。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对具体的话语分析理论、技巧和方法展开讨论[17—18],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探讨,使语言学的研究能走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前台,推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包括教育与知识异化,技术与数字思维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西方学术霸权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困境,经济活动对人的异化,台独、藏独语言的形成与特征,中国意识形态的演变与重组,中华文化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商业与行政机构的交往方式,西方话语对中国媒体(尤其是互联网)语言的支配和控制,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民族意识与地缘政治的话语基础,反恐话语在国际政治格局重组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话语这一层面介入,并通过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跨学科交流达到理解和解读社会现象的目的。此外,由于该研究方法广泛吸收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并基于对真实文本的实证分析,因此,它尤其适合在外语院校的语言学群体中展开,这将有助于改变外语院校的工具型办学理念,提升其人文性和社会性,从而恢复它应具有的对东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和沟通的能力。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中心资助项目
注释:
① 中国话语西化不等于汉语白话文化,后者已经结束,但前者还在进行中。
② 巴赫金认为,一切语言都是一种话语混杂(heteroglossia),我们嘴里的每一句话(utterance)都包含两种意识——自己的和别人的, 而别人的话“以权威的和具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在进行”。详见BAKHTIN M.The Dialogic Imagination.Austi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342.
③ 转引自孙周兴《神秘:说不可说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8页。
④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相对于科学的前科学经验世界,具有直接、原初、透明和开放的特点。在当代实证科学的主宰下,生活意义与科学的统一性被割裂。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结构与语言观念的结构存在内在的联系……语言和文化既不等同于参与交际者用来定义情景的现实形式概念,也不是某种看上去类似内心的东西。语言和文化构成在生活世界中。”参见HABERMAS J.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Lifeword and System:A Critique of Functional Reason.Heinemann,1987.p.124—125.
⑤ 哈贝马斯认为,产生于生活世界交际活动中的意义是文化和传统更新的保证,离开了它人们就无法对新事物有真正的理解,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危机和个人心理上的异化。参见HABERMAS J.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Lifeword and System:A Critique of Functional Reason.Heinemann,1987.pp.140—141.
⑥ 福柯认为,分类给予权势关系不为人觉察和怀疑的合法性,它决定了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事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不可以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参见FOUCAULT M.The Order of Thing's.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XV-XX.
⑦ Fairclough把这两种话语的捆绑形式称为主角与反主角的对立结构:主角一方在文本中创建问题,并拥有符号权力;后者则试图消解问题并失去权力。参见FAIRCLOUGH N.Analysing Discourse:Text Analysis of Social Research.London:Routledge,2003.
标签:文化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哲学论文; 读书论文; 科学论文; 生活方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