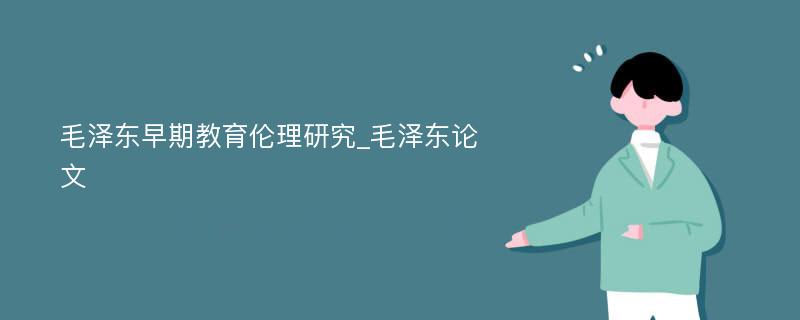
毛泽东早期的教育伦理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1-0018-04
毛泽东的早期教育伦理观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毛泽东的早期既有作为学生的“学习实践”,又有作为职业教师的“教学实践”。他“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1](P363),说出了许多关于教育伦理的令人信服的真切的体会,有些思想至今闪闪发光,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提倡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大背景下,更显现出灿烂的光辉。
一、毛泽东早期教育伦理观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早期教育伦理观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毛泽东读私塾开始至1910年以前为自发的反传统教育的阶段;1910年秋到湘乡东山学校读书开始,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主要为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影响的阶段;在一师毕业前毛泽东出任一师学友会总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追求新的教育理念的尝试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一种相互衔接、相互包含的关系,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1902年开始在韶山读私塾的6年,是毛泽东较全面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6年,但对当时私塾的死记呆背为主和体罚学生的传统教学方式很反感。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就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2](P106)除了逃学以外,毛泽东在私塾学习期间还经常私自下塘游泳,上山采果摘花,偷看《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杂书,成了公认的“孩子王”。毛泽东童年时的这种倔犟的个性、反抗精神和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反感成为他教育伦理萌芽和生长的重要基础,但这时他对传统教育的反抗是纯粹自发的,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学堂读书。他说:“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穿着比别人都寒酸……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2](P112)尽管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只读了半年书,但却在这里明白了教育伦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地主子弟和农民子弟受教育权利极为不平等。
1911年春天毛泽东随国文老师贺岚岗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又只读了半年,就报名参加了新军,辛亥革命失败后退伍,于1912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著名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只读了半年,他就认为:“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2](P120)于是,开始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毛泽东自己说“就像牛进了菜园”[3](P40),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尤其是卢梭、达尔文、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使毛泽东集中地受到了一次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这两年的经历对毛泽东早期教育伦理的影响主要是:一是新学不新,不改革课程体系就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二是学校的校规不能太严,要为学生的自我发展留下余地。三是自学也是获取知识、发展个性的好形式。因为生活费用和湘乡会馆被士兵所占,才迫使他终止了自学。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师袁仲谦劝毛泽东多读古文,尤其要多读韩愈的文章,以改变文风,于是毛泽东从旧书坊买回一部《韩昌黎全集》认真批读。对于在中国教育史上很有影响的韩愈,毛泽东既有“此论颇精”、“言之成理”、“甚合吾意”的评价,也有“不通”、“荒谬”、“陋儒之说”的批评,可见他认为不能一味迷信古人,也不应该把古人全盘否定。[4](P32)考入四师对毛泽东教育伦理的意义有两点:一是毛泽东选择了教师作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职业;二是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本态度是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
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师范生生活,也遇到了对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影响极大的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徐特立和良师益友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一师对毛泽东早期教育伦理的影响有以下几点:一是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思想的萌芽;二是通过杨昌济等较全面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伦理和西方教育伦理的影响;三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方法;四是学生可以偏科;五是体育应该是学校教育极重要的内容;六是学生应该以学为主,兼做些社会调查,应该多关心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少谈女人和生活琐事。优秀学生应该组织学会深入研究学术和社会。
1917年10月,毛泽东被推选担任了第一师范学友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开始在教育方面按自己的教育理念着手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首先把一师1917年上半年开办的夜校办成“工人夜校”,自己印发招生广告,自己组织教学,还担任了历史常识的教学。其次,组织新民学会,并于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中成立。此时,毛泽东还设想在岳麓山建立工读新村,并于1919年12月写出《学生之工作》。第三,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第四,1919年7月,创办了《湘江新论》,共出5期和一期“临时增刊”。第五,1919年9月1日撰写《问题研究会章程》,在所列71个大问题中把教育作为第一个大问题列出来,并包含了17个小问题。第六,毛泽东在1920年完成“两个转变”的过程中创办了文化书社,年初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工读互助团。7月他与在长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商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并由他撰写和发表了宣言。其后在同何叔衡一起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使其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培养新型干部的学校。
二、毛泽东早期教育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1.受教育权利:人人平等
毛泽东在1910年到东山学校读书时感受到了地主子弟与农家子弟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1917年暑假,毛泽东同肖子升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游学,加深了他童年时代就体认到的农民因为缺少文化而受到经济政治方面的不平等待遇。这年下半年毛泽东了解一师附近的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和粤汉铁路的武昌—长沙一段和长沙—株洲一段的工人和人力车夫、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生活都十分贫困,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到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民众大联合》(一)中指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1](P338)因此,毛泽东认为首先只有通过民众大联合、通过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使农夫、工人、女子等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才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其次,要举办多种形式的教育,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外,还要兴办学校、自修大学、工读学校、扫盲活动等来普及教育。再次,要特别重视女子教育和贫困生的教育,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就特别照顾和帮助贫困学生。还要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才能保障受教育权利的人人平等。
2.教育目的:培养“新民”,改造中华
毛泽东不是教育救国论者,但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看到了教育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命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1](P452)“今以学校对于学生之目的而言之,为‘养成有独立健全之人格之人’。”[1](P453)而培养这种具有独立健全之人格之人必须依靠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有机结合,即创造新学校、实施新教育,必须与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社会。“新社会之各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1](P454)尽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新教育观带有空想的成分,“新村主义”社会理想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追求无疑是20世纪世界各国的追求,在新的世纪里有许多目标仍将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的方向。
3.教育方式:发展个性,提倡创新
1921年5月1日《湘潭教育促进会》第1期的会报《发刊词》中说:教育的真理就是“新教育”。新教育的条件很多,概括一句,就是“适合人性的教育。会报本这种宗旨,借文字之便,和各方面商榷,以期共同解决这个湘潭教育问题。换一句话,就是共同促进湘潭教育。”[1](P497)其实适合人性的教育不仅是湘潭教育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教育的问题,不仅是20年代的问题,同样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问题。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无个性是中国国民保守性的根源,毛泽东从他早期伦理思想的核心精神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出发,对传统教育压抑个性、培养奴性是深恶痛绝的,他不但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以实际行动不断地反抗,而且将这种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宣称:“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P151)“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P152)正因为毛泽东能够从自发到自觉地反抗传统教育对个性的压抑,他一辈子保持着旺盛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他早期的“工人夜校”、“工读新村”、“自修大学”、“组织留学”等教育创新活动,中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中国特色建设道路的奠基”、“三个世界的理论”,都是这种表现个性的活动的结果。
4.师生关系:师生平等、互教互学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毛泽东的这一至今悬挂在一师的题词概括地表达他的教师伦理观。毛泽东1921年11月中旬,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填写《终身志业调查表》时,把“教育学”填入“终身欲研求之学术栏”,把“教育事业”填入“将来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可见,早期毛泽东是立志当一个好老师的,他的早期教师伦理观和学生伦理观均是相对成熟的。其教师伦理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事业对教师的客观道德要求。毛泽东从小就反对教师要求学生死记呆背和体罚学生,在一师就特别崇敬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懂得教育规律、具有新的教育伦理观的杨昌济、徐特立等人,而对黎锦熙等人却一直是当作老师加好朋友看待。新教育的师生平等观对毛泽东影响很深。二是作为教师的自我人格塑造问题。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对内圣的人格追求是十分强烈的,因此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对杨昌济教师的修身课听得十分认真,并把他作为行动的指南。因此,他一毕业就成为一个自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好教师,很快在湖南教育界有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早期学生伦理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应该尊敬教师,遵守合理的校规校纪,但对无知无德的教师和极严的校规是极为痛恨的,是要号召学生起来反抗的。二是学生应追求新生活,树立新的道德观,成为新民,建立新家庭,建设新社会。而教师伦理与学生伦理的关系是一种互动模式,而不是一种单向的传导,先生和学生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
三、毛泽东早期教育伦理观的特点
1.反传统性
毛泽东的反传统主要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传统,但同时也反对资产阶级新学中一些已经变旧的成了传统的东西。因此,反传统性这一特点的内涵包括:一是反对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传统德育和封建教育方式。认为“压抑个性之三纲在所必去”。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连续撰文批评康有为反对广州因为修马路拆除明伦堂,说世界各国都没有明伦堂,质问康有为难道定要留着“君为臣纲”才是“民国所宜”吗?二是反对资产阶级新学的文化科学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相脱离。他说:“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撅,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1](P97)“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1](P676)三是教育腐败的原因“皆由主持教育者,不察世界潮流,不知自身缺陷,无责任之观念,无振奋之精神,有以致之也”。[1](P475)四是“教育救国”是空想,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改造中国和世界。
2.创新性
毛泽东早期的教育伦理观在本质上尚属于资产阶级教育伦理思想,但已包含了许多转向马克思主义教育伦理观的新因素。除前所述1917年办工人夜校开始一系列实践创造活动外,还包含着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要创办为平民教育服务的学校,打破资产阶级学校为有产者服务的垄断性。二是人才培养目标不是培养“少爷”“小姐”或“糊涂麻木”的人,而是培养能积极向上“养成健全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革新社会”的人才。三是学生要注意劳动,以“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动两阶级的接近。”[6](P333-335)四是提出了学生自决,自决即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意思[1](P555)五是把培养新人作为社会革命和建设新社会的基础。
3.平民性
这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阶级性问题,毛泽东终生以维护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为己任。从其早期教育伦理看,就特别注意维护普通老百姓的教育权利和发展机会。但对“教育权利”和发展机会的理解和维权活动的自觉性是呈现出阶级性特征的。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是站在精神个人主义的角度,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发展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到最高的道德义务。因此平民(尤其是女子)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自身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毛泽东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认为教育能启迪民智,培养民德,激发民能,最终达到救国的目的以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受教育的权利。在毛泽东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后,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上,通过社会革命(包括教育革命)来解放普通老百姓、使他们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来维护普通劳动者的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的。
收稿日期:2000-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