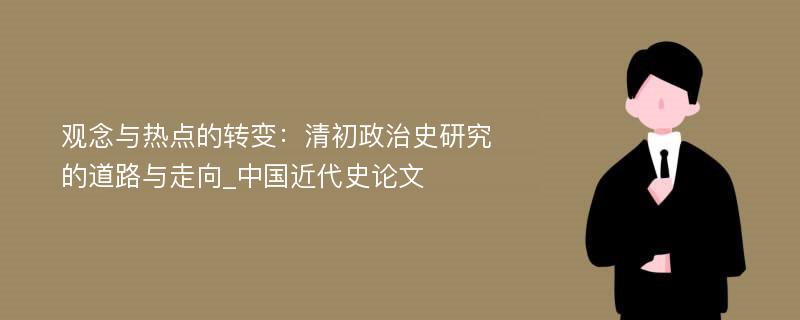
观念与热点的转换: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史研究论文,观念论文,道路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传统王朝统治在中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完整的清王朝的历史呈现在治史者的面前。百年以来,清史,特别是清代政治史的书写及研究,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经历了不同观念、理论和方法的打造以及历史谱系的构建与重大史事的解构。伴随史学观念不断更新的是人们对于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与重置,而史学的镜鉴功能也在不时提醒着人们去反思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回顾历史研究的历程与回顾研究历史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价值。 政治史研究一向是清史研究的主阵地,不仅集结着众多的学者,且其研究领域的维度甚广,几乎没有哪个问题不与政治史有所牵缠。所以,要对政治史研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不仅限于篇幅,也实在力所难及。本文将从观念带来的热点转换这一线索试说政治史研究的发展及其趋势,论及之话题或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或仅就方法路径与问题意识而言,且难免挂一漏万。 一、重大史实的考订及旧史学的奠基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后世修前朝历史的传统,清亡未久,自1913起,在短短数年间便有汪荣宝、许国英的《清史讲义》、吴曾祺等人的《清史纲要》、刘法曾的《清史纂要》、蔡郕的《清代史论》、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等十余部清史著作问世。① 动荡的政治局面与突变的社会现实带给时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复杂变化,不同的立场观点也反映在清史研究之中。肯定清朝,进而为之唱挽歌者有之,如诸葛汝楫在《清史辑要》中对“从开国之原”至“共和告成”的一切反清运动都持否定态度,均称为“贼”、“匪”,将太平天国称作“发逆之乱”,说“发逆洪秀全倡乱于广西”,对捻军则称“发捻回诸匪,纷纷而起,民遭涂炭,且与英人启衅,连年用兵,东南各省,糜烂已极。”② 但在更多的撰述中却流露出时代的信息,对清王朝的尊崇之情日渐衰微和对部分反清运动的含蓄首肯,已然为这一时期的叙史特征。如吴曾祺在《清史纲要·例言》中指出,“凡人民抵抗的吏之举动,大都由政治不良而起,即有一二魁杰但为少数人谋私利,并非救民水火,亦究与寻常窃盗行为不同”,所以书写中将官书奏报中的“寇贼”、“逆匪”等字样予以删改。直言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本无定位。”陈怀的《清史要略》,虽对太平天国仍用“内乱”一词,但却对其失败充满同情和惋惜。且书中不乏对清政府的指斥之言,称“(慈禧)太后骄侈淫佚”。③ 这一时期的清史著述,虽然仍未摆脱天命观、英雄史观,但在治史的观念上已悄然变化。他们或从政治立场,或于指导思想,或在学术内容与体例等方面,已与传统史学发生了分离,可谓20世纪初叶史学的新事物。然而,其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开启了中国史学中的清史断代研究之先声。正所谓“20世纪的清史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一个分支”;“断代清史研究最早从近代历史学土壤中破土而出”。④ 刚刚诞生的清史研究,还根本谈不上有政治史、经济史等方向的分野。所幸是,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热点都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所以,本文的讨论也就从清代的几部通史论著谈起。 至30—40年代,清史研究的突出成绩,除了官修的《清史稿》外,有三位学者的成就最大。首先是孟森以《心史丛刊》、《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所奠定的清史考实的基础,接着是萧一山的鸿篇巨著《清代通史》所开启的以政治叙事为纲的通史研究“丽作”,稍后又有郑天挺所著《清史探微》的刊行,寓意研究起于考证之细微。他们的成就,在研究内容上拓展了新的领域,在学术观点与风范上又是不同程度地各领风骚。 《清史稿》于1929年出版,被认为是清朝遗老宣扬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之作,并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禁书。但是,《清史稿》的断代史意义及其在编纂体例、资料汇拢等方面的奠基作用,是其他任何成果无法取代的。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问题与史实研究的精品,首推孟森的系列之作。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他的清史研究始于清亡之际。自1914年,孟森以“心史”名号发表了《心史史料》第一册,从澄清历史的角度开始了他的治史之路。鉴于清朝对入关前史,也即臣属于明朝的历史多有隐讳,并有肆意篡改、焚毁之事,孟森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了《满洲名义考》、《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等系列考实文章。1916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将上述部分论文汇编成册,以《心史丛刊》之名分三辑发表。而后,在《心史史料》的基础上,孟森的《清朝前纪》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明元清系通纪》于1934-193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而同一时期,孟森在国立北京大学还开设了《满洲开国史》、《明史讲义》、《清史讲义》等课程。其中《清史讲义》也在1934年出版。 建国后,孟森的研究,诸如《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八旗制度考实》、《孔四贞事考》、《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以及《女真源流考》、《横波夫人考》、《太后下嫁考实》、《董小宛考》、《世祖出家考实》等计85篇文章,由其弟子商鸿逵编辑成《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刊》,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通观孟森的研究,可知其着力于史事原委的考订及史料的梳理,诚如商鸿逵在编辑说明中所指出的:其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历史事实的论述,二、文献资料的考订。”⑤而就是在这两点上,也可以看出孟森对问题的把握与史实判断上的精到敏锐。诸如他的“八旗制度考实”、“建州考辨”等篇,至今仍为学界奉为定论之作。他对满洲族称国号、族源等的研究,奠定了清朝开国史研究的基调。而他对清朝统治者多次篡改《清实录》目的的分析,以及《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的毁书用意的揭露,以及《科场案》、《奏销案》等对专制政治的鞭辟,都可说明其史识、识才的难能与可颂。 在《清朝前纪·叙言》中,孟森表述了他治清史的目的,曰:“盖清帝逊国以后,国人以习知清世禁纲之密,清纪载之难信,于是妄造瞽说,流传失实,多污蔑清室之谈”,“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从流俗好奇之听。”⑥表达了他作为史家的担当。他要澄清清朝近三百年的疑案,同时也要厘正辛亥革命以来对清朝的一些偏激成见,强调不应把民族革命的政治立场用于学术研究,而视清朝的历史真实性于不见,把清朝和满族的历史置于一个客观的基础上。正是在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下,孟森开拓出清史研究的一片天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孟森在清史研究中有披荆斩棘之功,可被视为清史断代研究的鼻祖。 但孟森的研究仍受制于他生活的年代,作为旧史学家,孟森依然无法摆脱英雄史观的时代窠臼,“他把一代的兴亡治乱归结为帝王将相等少数统治阶级首脑的奋发有为和荒淫燕嬉。”“对农民起义还加以敌视。”⑦ 孟森的学术成就,既源于在治史方法遵循传统的考据学,又得益于五四时期近代思想的影响。商鸿逵有曰:“心史师治史,多本中国传统之方法,而于史料分析甚详,于史事论述极明,又不尽同于传统史学,从而开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心史师治史重于考证,对所论之事,辨误纠谬,力求明了史事真相。”⑧这对清史走上真正的研究之路具有重要的示范与促进作用,其研究风格至今仍为部分清史研究者所秉承。 孟森研治清史,前后不过三十年,其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非后辈之学所能望其项背。而孟森于1938年去世,而1937年也被学界作为清史研究的一个时段。 在旧史学家中,萧一山是又一位重要的奠基人。他生于1902年,卒于1978年。江苏徐州人。萧一山小孟森30余岁,而能够与孟森齐名,是因为他以一人之力用两年的时间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清代通史》,在体例上,他一改以政治史文明史混搭的治史时弊,堪称新创。更讶人者,是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两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萧一山不过是一个21岁的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在校学生,而当时的名家梁启超、李大钊、蒋百里、蒋梦麟、朱希祖等前辈及日本今西龙博士皆为之序,称萧一山为“奇人”。1950年,萧一山又对《清代通史》进行修订,历时12载,完成下卷,全书共400余万字,距上卷之脱稿问世,已近40年。 同孟森一样,萧一山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并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学者,《清代通史》的撰写也以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入手、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广为搜罗与爬梳的基础之上。1922年,北京大学在明清史教授朱希祖与孟森的倡导下,建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组织力量对清代文献进行清理,而萧一山适逢有幸参与其间。由此,他接触了大量原始资料,诸如誊黄、敕谕、诰命、实录、考卷、题本、库表等等,其内容涉及有清一代的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河政、盐行、课税等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的资料,从而为《清代通史》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⑨虽说萧一山打造的是一部通史,但书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以国家政治为纲所形成的对清朝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使是书构建起清史研究的脉络与脊梁。 萧一山是一位旧史学家,但他却是梁启超所倡导的痛批君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新史学”的身体力行者,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国民史学”或民族革命的史学。 首先,萧一山对大众革命极尽讴歌。诸如,他称天地会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把义和团运动看成一种民族自觉。他尤其推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编纂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及秘密会党的史料。对此,李大钊在初版序言中有中肯的评价:“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叙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及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余故乐为之叙,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各史之先声也。”⑩ 其次,萧一山对清朝的统治及其历史多持否定态度,将自身置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如他在《清代通史》中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11)而在他的研究中更渗透着对现实的关怀。正如他在《民族文化概论》导言中说的那样,他最初发表这些论文的时候,原本就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阐发民族的潜德幽光。 可见,生活于清亡未久的萧一山是一个深受辛亥革命思潮影响、主张国民革命和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激情仍是他这一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与追求。而当民族革命的历史观构成萧一山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时,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影响到他对清朝历史的判断,其研究难免失于过多的否定。 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中,郑天挺的史学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王钟翰曾有言:“回首百年,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先生,他对清史研究做出的开创之功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次席者为萧一山、郑天挺两位。”(12) 郑天挺(1899-1981),又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郑天挺的清史研究始于30年代初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期间。其所著《清史探微》也于1946年出版发行。有关郑天挺的清史研究,诚如其弟子冯尔康所言:“早期的重点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之外,有《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释阿玛王》、《清史语解》、《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等文,并汇集于《清史探微》一书。他在研究的后期关照历史的解释,如作《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却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指出清代史的六个特点。”(13) 郑天挺在研究中仍然沿袭了中国史学重考证的传统,十分重视档案等新资料的发掘。在研究方法与选题上又多遵循孟森的治学路径。但他却是一个从旧史学中最早走出来的学者。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郑天挺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社会演进与变革,并对满族的族源及满汉民族关系投入了精力与笔力。 此外,历数清史研究的前辈,还有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曾给予清史大量篇幅,并著有以诗证史的《清诗纪事初编》。罗尔纲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其《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考证集》及《绿营兵志》等也有开山之功。 历史研究离不开对新史料的发掘,这一时期正是抢救清朝档案并开始整理出版的关键时期,首功应归罗振玉、傅斯年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清朝的千万件档案免遭灭顶之灾。而《明清史料》、《清三藩史料》、《清代文字狱档》和故宫《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自30年代得以陆续出版,《清实录》也于此时印行。《满文老档》的发现,更丰富了满族入关前史的文献史料。与此同时,谢国桢则侧重于对明末清初历史和文献的研究,他以个人之力自3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系列明清史料与专著,如《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清初史料四种》等,(14)其中,对清朝入关前史料的考录和对中外清史研究论著的评介,已具有了研究指南的性质。 学界认为,建国前夕,即1937-1949年是清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为时较短,且国家动荡,学术环境不佳,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缺乏必要的整理和爬梳。而“清史在史学界被视为不古不今之学,不像先秦汉唐能发思古之幽情,又不像辛亥革命前后有现实的需要,清史的重要性没有被认识。它在断代史中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令人生畏。”(15)因此治清史者寥寥。但是,其奠基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后的清史研究的发展,与这一时期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 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叙史体系的建立 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开创的“新史学”,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胡绳、吴玉章、刘大年、尹达等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将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开启了崭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例如,范文澜的“历史的发展不是由英雄豪杰,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发展”(16)的论点,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英雄史观的否定,以及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解释模式的认同。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生产力,一方面既还保有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自然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将遵循着老公式缓慢地进行。”(17)其论点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国以后,唯物史观更是被全面地应用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侯外庐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自序中明确指出:“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18) 任何学术研究都摆脱不了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清史研究的道路亦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是以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劳苦大众的政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学说,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权,在建国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农民战争史,近代史上的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斗争研究也在不断升温。(19)五六十年代的清史研究正是在这一环境下展开的。 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中,建国初期10余年间的历史学,经历了对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也正是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提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峰”。(20)由此掀起史学界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研究热潮,清朝历史上的白莲教起义、捻军及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等都受到格外重视,得到不同程度的深度“挖掘”。而发生在晚清史上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也由于反压迫、反侵略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需要,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线。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大都将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晚清,如范文澜,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研究,他于1945年在延安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写作,阐述了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01年义和团爆发这61年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书中诸多论断及观点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又如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更是清代政治史中的亮点之作。 随着近代史研究备受重视,研究细化,成果不断增多,以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前后分割的历史断限也更加固定成型。 当然,这一时期的清朝政治史研究并未完全停止,形成了一种重史实考据的潜流。诸如,郑天挺对于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分析,(21)王钟翰对清朝重大史事的考证,(22)以及商鸿逵的“康熙平定三藩”、“明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等诸文,(23)都以微弱的声音强调着这一领域的存在。但这些研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环境中不过是大海中的小小浪花而已,其涟漪也自然汇入到“起义”与“革命”的大潮中。清前期的政治史研究还是属于一个亟待开垦的蛮荒领域。 80年代文革结束后,政治史方迎来了研究者的春天。清史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表现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论著激增诸方面,专门的学术刊物《清史研究》、《清史论丛》问世,一大批前辈学者与新人耕耘于此。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度的清史之作。198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发行《清史简编》为肇端之作,此后有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4年),以及自80年代开始撰写、至90年代陆续出版的,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十卷本和林铁军等主编的《清史编年》多卷本。此外,还有几乎囊括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清代人物传稿》,上下编各十卷等。这些成果皆系众人研究的精华荟萃,传统史学的纪传、编年、通纪等史学编纂体例被应用其中,代表了当时清史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而李洵的《明清史》,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谢国桢的《南明史略》,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晋藩、郭成康《清代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等,(24)则以争鸣的形式成为个人的代表作。这一时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更是难以数计。 在上述研究中,有三项研究值得一书。一是清前史有关社会性质、主要社会矛盾,以及民族起源等方面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二是对清朝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三是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认识的深入。而这些研究的理论聚焦又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对社会演进与历史变革、忠君与爱国等宏观问题的论述上,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清入关前史研究。 清前史的研究热潮在这一时期仍以极强的势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阵容,其中,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的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王钟翰在1957年出版的《清史杂考》中,以《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作为开篇,阐明满族在占据辽沈地区之前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文中体现的从社会经济、阶级结构入手分析的方法,李鸿彬称之“是我国老一代学者运用历史唯物论新方法研究清史的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60年代初,郑天挺在《清入关前满洲族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25)1979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以大量资料重申此前的观点。(26)而他的立论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的论断。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等文,从“诸申”身份与地位的变化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主张满族在入关前即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进入辽沈后,“诸申”成为“计丁授田”的农民,满族方进入了封建社会。(27)李鸿彬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中,对于以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作为奴隶与封建两种社会形态的划界没有不同意见,但他对满族奴隶制的性质与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属于家内种族奴隶制。(28) 可见,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有关社会历史演进阶段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着学界治史的价值取向。而与社会形态有密切关联并同样被关注的还有对满族的由来及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一致的意见是,明代建州女真为满族形成的本体,在统一战争中女真人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50年代,有王钟翰发表的《明代女真人的分布》、(29)莫东寅发表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与建国》,(30)70年代有薛虹的《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31)滕绍箴《明代建州女真人》等,(32)这些文章大都是从整体上探讨满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封建化的程度等,并说明满洲出于建州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系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至90年代初期,相关研究仍有未艾之势,虽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但在对满洲崛起的历程,入关前的政治准备,以及具体到八旗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等基本史事的考订上,都不同程度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与内容。 第二,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出于对宏观问题考察需要的认知,学者们对明清鼎革、康乾盛世,以及清代国家统一等重大历史课题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直接面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一直以来,如何认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存在不同的声音。民国初年,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民族革命志士站在排满兴汉的立场上,对清朝历史的否定不遗余力。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有多处直接表达了他的排满思想。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33)这种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认知,被学界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也即民族革命史观。其对清王朝的否定,等于强调清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断裂。对此,孟森则直言不可“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明确指出,“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34)但是,民族革命的史观,一度仍为主流声音。 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影响下,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认同,仍成为对清朝历史地位重新评价的最大障碍。 如谢国桢说:“在十六七世纪(明朝),我国科学技术本不让与欧洲,但到清朝却停滞不前。”明朝在边疆开拓、巩固国防,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上,也都有卓越的成就,只是到清朝才落后了。(35)郑昌淦亦认为:清前期近200年的历史,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清后期70年处于挨打的状态,就是前200年落后的结果。他说:“统一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拉拢汉族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官僚集团,镇压各地人民的抵抗力量,建立起来的。”“虽然他们逐渐地接受了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但所接受的也大都属于落后的方面。”清王朝的统治政策从主要方面说,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36)直到90年代后,顾诚仍然认为:“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37) 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清朝是落后的王朝,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之处于停滞状态。这与西方社会把18世纪的清朝称作“停滞的帝国”有着相同的结论。(38)而其观点背后的理论依据,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演进中五种社会形态递进学说的认同,即认同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 例如,李洵认为,中国在17世纪出现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清王朝的建立及其民族征服战争与民族政策,虽然对18世纪以后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封建社会的解体起了缓解和稳固的作用。四十天完成的明清鼎革,却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延长了一个世纪。(39)傅衣凌也撰文指出,“(明)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到了雍乾两朝则严峻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是以新的因素往往中断、夭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国家不易产生资本主义的状态。”(40)冯天瑜同样认为,清军入关中断了明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综合各种资料,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我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清代整个社会的主体仍停滞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41) 不言而喻,在这种理论认同下,学界形成难以割舍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而代表新中国史学成就的“五朵金花”之一,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又是史学界用力最多、争议最久的一个话题。对明清易代的认识,仍难免脱离这种学术观念认同的影响。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即具有缺陷,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社会历史演进模式。而清王朝的建立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结论,也并非建立在对清朝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最起码它忽略了清朝在康乾时期养育了3亿多人口的史实。 于是,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学界重提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而如何认识与评价清朝的历史,也已不再是简单地对清史研究进行定位与定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满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清朝对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等重大理论的认识。而在这次讨论中,学界的认识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42) 如王钟翰指出:在康雍乾中叶以前(1662-1765)这一个世纪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还是居于当时世界文明发达国家的前列。”“单单揭露清朝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就迅速地对康雍乾这一历史时期作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断,为时尚嫌过早。”(43)戴逸明确指出,对清朝“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戴逸还强调:清代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前期经济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44)郑天挺也认为,清朝“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的一个时期。”“我们今天的疆域是当时确定下来的,各民族的联系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统一巩固了。这三者的发展和巩固是从清代开始的。”(45) 在这场讨论中,王思治撰《清前期历史地位论纲》,强调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由此清史研究的立论起点被刷新。他认为,明清之际不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即清朝不存在阻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能否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从而担负起抵御外国殖民势力入侵的历史使命,应该是评价明清两朝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同时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以往不同,这就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已经到来,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来的侵略势力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他说:“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清军入关及清王朝的建立,使国家的统一得以早日实现,多民族国家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因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抗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使我国的领土疆域最后稳定下来”。而清政府在统一喀尔喀蒙古、天山南北、西藏的过程中,将一系列对领土行政有效管辖的制度推行到这些地区,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到确立并巩固。“所有这一切,应该说是清代前期所取得的历史业绩超过了历代的封建王朝。”(46) 尽管早期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入侵的可能性及能量还有待商榷,然而,这些建立在对既定历史环境及历史趋势深入分析基础上的问题预设,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视域和理论上探索的空间。 而后,对明清鼎革的理论探讨与叙事一直是持续研究的议题。80年代中期有孙文良、李治亭的《明清战争史略》,(47)90年代,代表作有陈生玺的《明清易代史独见》、(48)孙文良的《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49)刘凤云的《清代三藩研究》,(50)李鸿彬的《清朝开国史略》(51)等出版,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角度,对清军入主中原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指出,清朝能在明末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中获胜,正如恩格斯所言,是历史上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三,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 明清之交,明军、清军及农民军等社会各种势力逐鹿中原,阶级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政治与军事冲突尖锐而激烈,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千姿百态。清军入关后,明朝官员将领的分化尤其剧烈,仅就其对清王朝的政治态度而言,有人始则抗清最终战败降清,有人则战败自焚,有人降清后甘为鹰犬,继而复叛、反复无常,有人痛恨农民军,又与清军血战到底,有人先降农民军继而又降清,还有人以遗民自诩,志不仕清。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该如何评价?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80年代,学界对明清之际的人物评价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以民族气节为标准在降清与抗清者之间划线,有人以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为判人准则,还有人坚持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论是非。这些认识既涉及理论问题,也有史实考订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评价明清之际投降清朝的“贰臣”,更是考验着学术界的眼力。对此,学术界争议很大,或谓其大节有亏,或谓其乃弃暗投明,可谓针锋相对。 王宏志在《论贰臣》中指出,清朝用儒家的传统气节观把降清的汉官汉将,划入“贰臣”之列,贬斥他们“大节有亏”。我们不加分析,甚至歧视,是不妥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不科学。他强调要对这一群体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贰臣“这些人大都对新王朝的统一安定起了重要作用”,而那些不愿仕清的故明士大夫,表现出“狭隘民族思想”,也“不值得称道”。(52)张玉兴对上述观点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明清易代之际所涌现的忠贰两大人群,其忠义人群体现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爱国、报国之情,爱国是一切忠义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叛贰者的卑污与丑行,是他们只为一己之私,便叛卖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行径。“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他们降后金—清之后,助纣为虐,替满汉地主阶级杀戮人民”,(53)故不能给予肯定。 王思治在《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从理论上探讨了评价的标准,认为对明清之际的人物评价不能设统一的评判标准,“贰臣”之说出自乾隆皇帝,“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清统治者的标准之不足为训。”王思治指出,“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历史的大局来看,是应予肯定的,这也是评定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他同时强调,“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不能因为肯定清的统一,对降清者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肯定。反之,凡抗清者一律否定。”抗清斗争中所包含的“爱国”之举当然是不应否定的。自然,反复无常而无一定信念者不在此列,而那些为求一身高官荣禄而降清者也不应肯定。(54)他举例说,以多尔衮和史可法为例,他们虽然是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彼此势不两立,却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地位,多尔衮以为完成国家统一立功而载入史册,史可法血战不屈的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以立德名垂青史。这种评价,注重了历史的“客观性”,不再给历史人物贴上英雄、忠臣、叛徒、汉奸等标签,纠正了以往历史人物评价上的片面性。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除了上述列举的讨论之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重大事件的综观考察,即所谓的“革命叙事”,不同程度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如历史规律、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历史发展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向纵深给予了推进,对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与前一阶段相比,纯粹考证的研究有所减少。此外,由于信息交流的不畅,致选题集中,研究重复率过高。为适应政治需求,先立论后史料的命题作文式研究也参差其中。 三、在史料与史实的考据中建立起问题史学 进入90年代,政治史研究的势头朝着深化与全面伸展的方向发展。虽然明清易代、社会矛盾等问题仍为学界所关注,而国家统一、边疆民族,以及帝王政治、宫廷政治、官僚政治与其制度等研究已逐渐取代前者,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话题。在不断发掘新资料、重视档案利用的同时,强调“问题意识”,倡导“问题史学”也成为研究的新路径。就研究的学术价值而言,有这样几点值得提出: 第一,对清朝重大史事的考订,基本夯实了民国以来对诸多疑案及问题的研究。 任何一项有解释力度的研究,都始于微观的史事考订,并由此构建起立论的逻辑与范式。清史学界的考订之功首推孟森,并由孟森的考据结果引发出一轮新的研究,如雍正继位问题。孟森最早提出雍正帝“矫诏得位”之说,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他根据王先谦《东华录》、《上谕八旗》、《上谕内阁》、《大义觉迷录》等资料,认为雍正帝“在京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于隆科多”,“以遗诏中‘十’字改作‘于’字之故,并非久后野人之语,实是当时宫廷中宣布之言”。孟森之后,王钟翰亦认为雍正帝得位“不正”,是“夺嫡说”的倡导者。但他不同意孟森的篡改遗诏、改“十”为“于”之说,认为整个遗诏都是伪造的。对此,他在40年代就指出:“予最先发表的为《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二文,刊于《燕京学报》46、48两期上。因予不同意先予发表的清史大家孟心史(森)所撰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的观点。”(55)80年代,他又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康熙遗诏”满汉文对照原件的缩印照片,在经过比对分析后,得出了“无论《遗诏》的汉文原本,或满汉文对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写成的,而是雍正继位之后再制造出来的”结论。而且,他以发现的关于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禵的史料,提出康熙帝欲传位十四子的说法,从而将雍正帝继位疑案的讨论引向深入,其说也越居“擂主”之位。戴逸在其主编的《简明清史》中也赞同此说,有曰:“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56)此后,许曾重、杨珍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化了雍正帝“矫诏得位”之说的结论。 但是,冯尔康在《雍正传》中的发议却翻了前案。(57)冯尔康提出“合法即位”说。他通过对雍正帝即位的全过程,包括康熙帝晚年对诸皇子的态度、康熙帝之死、“传位允禵说”等系列史事的全面梳理,认为“联系康熙生前比较看重他(胤禛)的情况分析,在弥留之际决定传位给他,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位是完全可能的。”“康熙原本要在胤禵和胤禛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确定了胤禛。” 可以看出,冯尔康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没有否定王钟翰的研究,只是在对问题的认知上进行了不同的阐释,既有视角的转换,也有对问题的思考。此外,杨启樵、史松,以及吴秀良等也都持雍正帝继位合法的论点。这意味着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于中国史学传统中“以史为证”的钟情,对史事的考证、考察仍在继续。 例如,王钟翰自《清史杂考》之后,于90年代又陆续推出《新考》、《续考》、《余考》、《补考》诸书,共计五考,对于清史学界治史重视实证的学风起着示范的作用。(58)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是这一时期科举研究的考实之作。(59)而史实的考证与辨释并非仅仅是史料的汇集,更需要独到敏锐的眼力。何龄修在对清初“朱三太子”真伪的考证中,就是通过对史料的逐条辨析,得出北方朱三太子为真的结论。此外,杜家骥对八旗制度的系列考证尤显其用力勤谨。诸如《顺治朝八旗统领关系变化考察》、《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衮与多铎换旗问题考察》、《关于清太宗兼并正蓝旗问题的考察》、《正蓝旗主德格类又名费扬古及其事迹考》、《清初汉军八旗都统考》等,都是以史实考订为研究主旨的成果。(60)这些研究都是在追求传统考据学的治史路径,从微观视角出发,对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不失为铺路之作。 第二,如何认识清朝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对该领域的考察,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及康乾盛世的评价,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如果说还存有分歧,那就是如何看待清朝统一的历史进程、国家为统一实施的政策以及统一带来了哪些后果等。一种可以代表主流的观点认为:清朝统一西北等边疆,“是一场维护统一的战争,是与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战争的结果,巩固了西北边疆,有力地遏止了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61)1993年出版的《清代全史》,系邀集国内顶级学者协力写作、为代表当时清史研究水准的学术著作,书中也充分肯定:清朝对准噶尔分裂势力的平定,“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统一使清朝“用民族团结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抵御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这是清代统治的伟大功绩。”(62)此外,学者还指出:正是“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清代社会出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国力强盛,国防巩固,清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从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抵御了西方资本殖民势力。”(63) 但是在如何认识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上,学界却存在严重分歧意见。王思治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对清朝绥抚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以及用兵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政治军事行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其论点多集中在《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64)一文中。他认为,17世纪末清政府为解决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问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这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而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的平准也就具有了抵御外来势力的内涵。但是,成崇德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一观点。他说:谈论统一自然要提到分裂,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许多学者认为,准噶尔与沙俄建立联系,对抗清朝的统一,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应属于分裂政权,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他指出,17世纪中叶准噶尔建立的政权不隶属于其他任何政权,与清朝之间是国家尚未全部统一时期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清王朝入主中原,已经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准噶尔保持遣使进贡,就是对清朝入主中原的承认和支持,准噶尔与清朝对抗,不是为了分裂国家,而是要推翻清朝取而代之。”“在清朝尚未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之前,边疆民族政权、部落与邻国、邻落建立联系是正常的。”“准噶尔游牧地北邻俄罗斯,与俄国发生通使关系是正常的,不能仅仅根据双方遣使频繁与否这种表面现象,而简单地判定是非。”(65) 冯尔康也认为,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存在左的倾向。他说:“社会流行‘凡是现在国内的56个民族,都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民族’之说。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员,历史追得越古越好,似乎多民族国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发展中形成的。因此讲到蒙古人一支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说他是叛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不顾及他并非清朝臣民的事实。对满人作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早期人们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情绪,称之为‘满清’、‘满清政府’,而后为了民族团结,又不让称‘满清’了。这类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令学者在研究清史时不能不受其影响,时而是‘东’,时而又是‘西’,没有个准谱。不能以应从现在‘民族团结’出发叙说历史,而掩盖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其实多民族国家是在斗争中融合形成的。”(66) 上述认识的差异,所反映的是研究中对理论认知的不同,同时也提出了应该划分学术研究与政治之间界限的客观要求。可以看出,研究者的注意力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普遍规律等大而空洞问题的关注了,对固有的学术定见也已经开始了新的思索。而学术质疑的背后,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随着问题的设置,带动的将是学术的创新。 第三,皇权与官僚政治及其制度等研究逐渐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在研究取向上,围绕内阁、军机处等官僚机构,对皇权及其权力关系的研究是重点。 如郭松义指出:突出皇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清代的事权集中,必然导致皇帝的独断专行,但由于中枢办事机构干练,减少了中间环节,工作效率提高了,也加强了中央决策应变的能力。”(67)郭成康认为,18世纪的清朝是“极端专制政体强化与完备”的时期,而这一政治体制又是导致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68)高翔则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并提出新的观点。他说: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雍乾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军机处和皇权并非同一概念,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非但如此,在政治运行中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独裁方式,反而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清朝君权的强化绝非军机处、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9) 此外,徐凯通过对《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70)的研究,就八王分权向中央集权的制度演进进行了梳理和讨论。王思治的《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71)以及稍后杨珍的专著《清代皇位继承制度》,(72)都是从清朝皇位(汗位)继承制度入手,探讨了国家最高权力在承继过程中满洲贵族如何围绕权力与利益展开角逐与斗争。这些讨论,是推动政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政治史中,另一个热点问题是政治制度的研究。政治的核心范畴是权力,制度规定了权力伸展的尺矩,任何一项政治史研究都不会缺少制度史的登场。有关清朝的政治制度,在80年代便有系列成果问世,诸如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李鹏年等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刘子扬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等。(73)他们利用档案及官书勾画出国家行政制度的概况。90年代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著有《清朝典制》,随后,郭松义等又参与了由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的写作,(74)对这一时期的清朝政治体制与制度的研究起了率先的作用。而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一书也是制度史研究中的推进之作。(75)2000年之后,又有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王志明的《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白新良的《清代中枢决策机构》、赵志强的《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等相继出版。(76)不难看出,90年代以后的政治制度研究已出现向各个领域伸展并深化的趋势,而且对中枢决策机构的关注热情不减。 值得提出的是许大龄对《清代捐纳制度》的研究,他开辟的是清代官僚选举制度的研究领域。《清代捐纳制度》作为许大龄的硕士论文,最初发表于195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燕京学报》专号第22号刊出,后收入许大龄的《明清史论集》。(77)该文以资料汇集的功力见长,各章附有大量统计表,同时又是一项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其意义正如许大龄在自序中所言:“捐纳为清代秕政,吾人欲究其原委,考之官书,既乏有系统之记载,求之私人著述,又复为数不多;即询之当日躬与铨政者,亦皆语焉不详,视为书办之学问,不屑齿及。《清史稿·选举志》中虽有叙述,唯以材料不足,遗漏滋多。余有鉴于此,因搜集各种事例章程及诸家零星笔记,著为是编。”许大龄在研究中利用了不少“捐例”以及相关“公牍”,并走访清末曾任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的崇彝,将清朝的捐纳划分为开创、因袭、变更三个时期,并从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的区别、捐纳的具体规定和报捐者的铨选问题三个角度入手,梳理研究了整个清代的捐纳制度,是一部拓荒的力作,冯尔康评价说,许著“开辟了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78)而其在研究中多处使用的朱植仁辑的《六部则例全书·户部则例》已作为原始资料由该书保留下来。此后刘凤云发表的《清康熙朝的捐纳制度及其对铨制的影响》、《康熙朝捐纳对吏治的影响》等文,(79)都是在许大龄研究的基础之上借助其提供的基础资料完成的。许大龄的学生、现在供职于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伍跃新近完成的《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之作,从捐纳与科举、捐纳与社会、捐纳与铨选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捐纳制度的研究。(8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文革”后恢复高考培养起来的一代新的学人,他们在前辈学者及导师的带领下,在承继史学传统的同时,逐渐形成新的治学风格。虽然传统话题仍在继续,但问题意识却十分突出。 刘小萌的力作《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虽然同样在研究满族的兴起与逐鹿中原统一全国的历史,但是却赋予了游牧与渔猎民族如何在自身发展中实现从部落到民族国家构建的视野,植入了如何认识历史上落后民族与先进文明之间的征服与融和等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的预设。(81)定宜庄的《八旗驻防制度研究》,也将八旗制度研究放置在清朝兴衰的广阔视角下。(82)而刘凤云自1990年陆续发表的《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康熙朝汉军旗人督抚简论》等论文,则是基于对权力关系及其运行的思考,将问题设置在省级地方政府在国家政治推行的角色作用上,(83)因为“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84) 历史学要在趋新求变中发展,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同样可以后声夺人。这就要求治史者对蕴藏于历史背后的问题锐意于考察与研究,进而去找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四、重置政治史的叙史原则 伴随世纪之交的到来,史学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现代史学理念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受到质疑,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的宏大叙事备受冷落,直接形成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易位。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史研究,自研究领域、研讨的问题,到语境、文风,甚至是方法等,都处在变化与调整中。 其最大的改变,就是一些学者把研究的精力从政治史的核心范畴,即国家权力等宏大题材转向对社会的微观考察,研究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碎,以致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为一种潮流。结果是放弃对重大理论的研究,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研究,将政治史隐身于社会史之中,从而导致了政治史显学地位的丧失。 对此,学界不乏批评的声音。何龄修指出:“史学是以具体史实为基础的学问。上世纪最后阶段的清史研究,出于对空洞的僵化的教条式论著的反感,微观化、具体化倾向较明显。但理清史实只是研究的重要一步、深入分析的前提,如果只停留在此,则对历史的认识仍没有完成。上世纪末清史史籍、档案大量问世,为理清史实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新世纪的清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85) 杨念群则尖锐地批评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政治史研究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并说: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86) 带来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仍然是人们在治史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客观地说,自90年代中后期,当社会史研究走热之季,在史学中产生了扭转“精英本位”研究格局的呼声,随之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学界对帝王政治、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话题的厌倦,以及对政治权力攫取中的暴力和血腥的厌恶。而由于社会史强调“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87)这一研究视野的转换对那些亟待在研究中寻找突破点的史学界新秀而言,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从社会下层出发去探讨国家政治及社会重大问题的新路径、新视野,很快成为20世纪末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与文化史对史学的改造。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研究热潮的兴起与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得到追捧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尤大,以至于在叙史模式上,推崇由微观切口嵌入的方法成为风气。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历史片段介入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孔飞力的《叫魂》以民间割辫的故事揭示君臣关系与官僚政治的实态。这些方法带给史学界的除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外,还有对传统史学方法在价值判断上的震撼,从而对政治史研究构成极大的挑战。 对于政治史的衰落,学界的“回归”呼声从未停止。2004年,杨念群在《历史研究》发表《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明确指出要重视政治史研究;和卫国也提出,“政治史研究需要认真反思”,历史学研究大有再次走向另一极端之势,即偏重了“社会”,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等实政性问题的研究被淡化。(88) 但是,使政治史研究走出迷茫的,也正是受到来自社会史研究的某些启示,这就是以权力做桥梁,连接政治与社会,从而找回“国家”,找回“权力”,重新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与此同时,政治同样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研究自概念、内涵、理论及空间都得到拓展。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借助年鉴学派“总体史”的概念,把政治史各个层面的问题“总”起来。 也就是说,政治史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融入许多新的元素。新的时代不仅要求政治史研究必须在方法上吸收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从理论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上开拓研究的视野。具体而言,有如下要点: 第一,将国家政治与权力重新放置在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地位。 研究国家及其权力运行是传统史学的叙史模式,有人将其称作“君史”。但是,传统史学之所以能够在推动价值认同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亦源于自身的史学传统,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的事功。换言之,传统史学从未放弃服务于社会的根本追求。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史学价值认同面前,更没有哪一项专门史可以与政治史在史鉴方面的重要性相较,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89)那么,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历史是否仍然可以成为一部好的教材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国家政治与权力关系中,任何一种政权的性质都有对权力分配与权力约束的需求,在制度缺失与制度漏洞面前,任何政府都杜绝不了腐败的滋生。从史鉴的角度出发,历史上围绕国家权力与权力制约所发生的任何故事,无论是矛盾斗争、权力更替、权力转移与控制,乃至政策推行等,都不再是帝王一家一姓的事情,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政治过程所产生的历史经验。因此,把政治过程和结果视为理性的政治执行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就势必要关注那些权力的把握者。其中有两点尤其重要,一是国家将权力交给什么样的人?即所谓“用人”;二是国家对权力如何实行合理而又有效的管束,使权力监督不致缺失。这首先涉及对儒家传统政治中一个重要理论的重新认识,即“有治人无治法”。 “有治人无治法”出自荀子。《荀子·君道》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可见,在先秦儒家文化中,“治人”是指有仁心仁德的贤人,得“治人”可以推行“治法”,无“治人”,“治法”不能自行。成就“治人”自然要从自我修身开始,《礼记·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选拔“治人”则需要权力者的伯乐慧眼。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将“有治人无治法”理解为重“人治”、轻“法治”的帝王政治,这应该是后人误判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一桩“冤案”。 诚然,“选人”、“用人”是中国历代帝王的第一要政,“有治人无治法”是其核心理论,特别是清朝康雍乾三帝,几乎成为他们在用人上的意识自觉。如康熙帝常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90)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表示:“(治)天下唯以用人一政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91)乾隆皇帝也多次强调,“用人尤为行政首务”。(92)但是,他们口中的“治人”并非“人治”,而是对权力者的执政能力的高要求,即“务得有猷有为,悃愊爱民者”。(93)而这一点,也是建立在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和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等认识之上。因此,他们追求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德政”。而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作用中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先觉。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清朝是一个法网密集的政权。所谓“大纲小纪,无法不修。畿甸遐荒,无微不至”。(94)甚至连清朝皇帝的部分权力也被网罗其中。而且,以雍正朝政治之严猛,可令所有官吏都必须成为“清官”,以乾隆帝惩贪之铁腕,二品以上之大臣以罪诛杀者至二三十人。但是,清朝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贪官屡禁不止。那么,这是为什么?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是专制政治之下的法律与制度缺失,还是统治者政治道德沦陷?其症结究竟在君道、臣道抑或是治道?而官僚政治的腐败问题、利益集团对国家蚕食、对政府执政的破坏等问题,都是政治史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第二,从国家与政府的行政作用出发,将国计民生等经济问题纳入政治史的视野中,也就是将政治史研究的触角伸向经济等领域,以多种范式来处理政治史的题材。 事实上,国家的任何方针政策、经济措施与手段,都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对此,雍正朝大学士鄂尔泰有过议论。他说:“窃惟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故孔子不讳言财,曰有大道。”(95)可以看出,鄂尔泰把“理财”视为国家政治之大端,是基于传统儒家文化对政治的认识,是对孔子视“财为大道”的进一步阐释。这也说明,将国家经济,即国计民生视为国家政治的范畴,早已纳入古代政治家的思想体系。 对于今天的研究而言,在政治视野下对经济活动的考察,就是要将那些属于经济事务的河工、漕运、钱粮、仓储、盐政、铜政等项事务统统收入政治史的研究课题,通过经济现象与活动去探讨其实施的政治过程,对其中的政治与经济得失,各势力之间的利益消长、利害得失等问题进行直接的揭示。 这一转换意味着要将研究重点放置到那些身体力行的社会精英,即经世官僚身上,关注他们在国家经济中所实施的政治行为。研究表明,18世纪的清朝政府仅以二万左右的官僚管理着全国三亿多的人口,也就是说清朝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承担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僚群体又是如何撑起社会的脊梁,解决了国民的温饱等社会问题的呢?国家及各级政府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呢?带着这些问题,学界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研究。 2002年,高王凌在《政府作用与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力图说明,“中国古代就存在一个大政府时代”,“人们也一直没有放弃由一个强有力的好的政府出面包揽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期望”。(96)此后王志明也认为:以往的政治史研究,只是“用专制一词涵盖的清前期政治史,而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则关注不够”。(97)在这一认识下,有关政府行为及作用的研究,也开始成为近年最受瞩目的学术成果。其中,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被誉为国际中国史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魏丕信通过对18世纪荒政的研究,论证了清政府对社会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有效救治。(98)而国内的类似研究多出自年轻学者之手。诸如,倪玉平关于水旱灾害发生时政府的应对机制的讨论,(99)和卫国对政府在江浙海塘修筑过程中作用的阐述,(100)穆崟臣对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101)等等。近年,刘凤云通过对两江总督介入河务、由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变的实例,进一步说明政治史的研究话题已从对国家政治、官僚体系以及民族问题的再认识,向政府行政的微观运行即经济手段、技术措施等问题领域伸入。政治史提供的观察和理解的诸多维度,可以渗透到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 第三,让政治制度背后的“人”走出来,成为制度史研究中的主角。 针对以往制度史研究中只见制度条文,看不到制度如何运行的研究状况,在2001年宋史学界的学术讨论中,邓小南发出走向“活的制度史”的研究话语。(102)她认为制度史应该把握制度变迁与其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而非将制度孤立于政治运作与人事之外。这一发议在史学界引发了很多的反响,并得到不少青年学者的认同。在近年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有关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系列成果,呼应了“活的制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 但是如何将制度史作活?既不是简单地对制度与法制条文的解读,也不仅仅停留在从文书传递上研究制度的运行路径。因为文书传递过程提供的历史仍然局限在一个程序的过程中,是活了起来,但这并没有达到“活的制度史”的要求,仍停留在见物不见人、更难以见到时人的思想的状态中。所以,要作成“活的制度史”,最关键的是将与制度相关联的人纳入研究的视野,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任何制度从制定到执行都依赖于人来进行,离开人,任何制度都不过是僵化的教条而已。也就是说,在制度史研究的过程中,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所有官僚都站到前面来,成为研究话题中的“主角”。 第四,在政治事件与政治过程中发掘其背后的文化因素。 近年,伴随文化史的兴起和走热,学界将概念、观念、话语,以及知识、信仰等思想领域里的文化资源都发掘了出来。比如,黄兴涛提出,语词的使用,也即文化态度和语言认知,多代表了个人的政治和文化意志,一旦成为社会习惯,多无法轻易加以改变。(103)这或许就是关注社会文化的史学家从“后现代”的视角去注视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的一种方法,其意义在于唤起人们对自身文化构成的关注,并认同了在史学研究中文化的重要意义。正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104) 在史学研究中,人们素来重视理论与文化的关系,因为理论突破的前提需要基础研究的深入,更需要通过对蕴含其中的文化解读找出事情的本质。所以,文化或者说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应该是政治史研究中最终的追求。而忽略了隐藏于历史表象后面的各种动因,就无从进入历史的深处。余英时说:“以研究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105)他对朱熹政治生涯及其活动的研究,也正是建立在将文化作为理论纳入政治研究之中的这一思路。 可以说,史学理论研究的提出和探讨,是历史学自觉程度提高的体现,而从对历史规律的追寻,到对政府行为、行政运行、政治过程的关注,并将这一切纳入政治史的视野,都必须关注其背后的历史精神乃至民族文化。这是政治史走出低谷、冲破瓶颈的重要选择,而文化视野下的广角镜头,无疑将给政治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在文化史不断向史学其他领地殖民的学术氛围下,政治史也可从反向实现转身,既可借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模糊边界,把一些文化题材揽入政治史的视域,同时也可在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政治议题的解释资源,而这项资源将是取之不尽的。 综上所述,历史是一门需要不断反思的实证学科,同时也在反思中不断发展。自20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同时各种新思想、新路径也源源而入,积蓄起新的活力。这些都将成为今后将史学研究推向纵深的力量源泉。 ①汪荣宝、许国英:《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吴曾祺等:《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刘法曾:《清史纂要》,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蔡郕:《清代史论》,上海会文堂书局,1915年;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文明书局,1915年。 ②诸葛汝楫:《清史辑要》,福音印刷合资会社,1914年。 ③陈怀:《清史要略》,北京大学出版,1925年第二版。 ④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⑤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商鸿逵作《编辑说明》,中华书局,1959年。 ⑥孟森:《清朝前纪》“叙言”,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页。 ⑦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商鸿逵作《编辑说明》,中华书局,1959年,第2页。 ⑧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商鸿逵作《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⑨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⑩萧一山:《清代通史》,李大钊:《清代通史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1)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92页。 (12)王钟翰:《清史满族史研究百年回顾及未来展望》,《满学论丛》第1辑(2011年)。 (13)冯尔康:《清史研究与政治》,《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14)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清初史料四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1932、1933年。 (15)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16)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另见《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17)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 (18)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自序》,人民出版社,1956年。 (19)建国前在面对外来侵略的政治环境中,出现了蒋廷黻、郑鹤声、郭廷以、范文澜、华岗等人所著的多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论著。 (20)参见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1)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其中收录他50年代以来撰写的《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等明清史的论文43篇。 (22)王钟翰:《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 (23)商鸿逵:《论康熙平定三藩》,《历史教学》1963年第8期;《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历史研究》1978第3期。 (24)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王钟翰:《清史杂考》,中华书局,1957年;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郑天挺:《探微集》,《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25)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26)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1979年第4期。 (27)周远廉:《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第4期。 (28)李鸿彬:《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参见李鸿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29)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见《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30)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与建国》,《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 (31)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32)滕绍箴:《明代建州女真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参见滕绍箴:《满族发展史初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33)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92页。 (34)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364页。 (35)参见谢国桢:《对于研究明清史的一点体会》,《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亦见《明清史谈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8—249页。 (36)参见郑昌淦:《明清之际的历史潮流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37)顾诚:《南明史·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38)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在1989年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讨论的是18世纪的清朝。 (39)参见李洵:《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 (40)傅衣凌:《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史学集刊》1982年第1期。 (41)参见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42)这次讨论的文章大都以论文的形式收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编的《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 (43)王钟翰:《对清前期历史必须作综合比较研究》,《清史研究集》第1辑。 (44)参见戴逸:《清前期的历史地位》,《清史研究集》第1辑。 (45)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6)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1辑。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47)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48)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49)孙文良:《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50)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51)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 (52)王宏志:《论贰臣》,《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5期;另见王宏志:《洪承畴传》,《前言》,红旗出版社,1991年。 (53)参见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清史论从》2003-200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54)参见王思治:《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王思治著:《清史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 (55)王钟翰:《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序言》,中华书局,2004年。 (56)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 (57)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 (58)王钟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清史续考》,华世出版社,1993年;《清史余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 (59)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60)杜家骥:《顺治朝八旗统领关系变化考察》,《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衮与多铎换旗问题考察》,《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关于清太宗兼并正蓝旗问题的考察》,《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正蓝旗主德格类又名费扬古及其事迹考》,《满族研究》2000年4期;《清初汉军八旗都统考》,《历史档案》2000年4期。 (61)郑天挺主编:《清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62)王戎笙:《清代全史》第4卷,《绪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63)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1辑。 (64)王思治、吕元骢:《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65)成崇德:《论准噶尔政权》,《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1期。 (66)冯尔康:《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67)郭松义、李新达、杨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 (68)郭成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辽海出版社,1999年。 (69)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70)徐凯:《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71)王思治:《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满学研究》第3辑。 (72)杨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 (73)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74)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 (75)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76)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白新良:《清代中枢决策机构》,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77)许大龄:《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78)冯尔康:《清史研究与政治》,《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79)刘凤云:《清康熙朝的捐纳制度及其对铨制的影响》,《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康熙朝捐纳对吏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1期。 (80)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81)该书原名《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再版时改为此名。 (82)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83)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3期;《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康熙朝汉军旗人督抚简论》,《满学研究》第7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 (8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4年。 (85)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86)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87)参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88)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2期。 (89)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 (90)《清圣祖实录》卷83,康熙十八年八月辛卯,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 (9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奏陈所知滇黔大小文武各官情形以备采择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92)《清高宗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庚申。 (93)《清高宗实录》卷536,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乙丑。 (94)《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 (95)鄂尔泰:《论人材疏》,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卷10,中华书局,1992年。 (96)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海洋出版社,2002年。 (97)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导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98)[法]魏丕信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99)参见倪玉平:《水旱灾害与清代政府行为》,《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6期。 (100)参见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以十八世纪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01)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穆崟臣:《试论乾隆朝社仓的管理与运行制度》,《满族研究》2008年第4期。 (102)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 (103)参见黄兴涛:《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 (10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版。 (10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自序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满族文化论文; 清史讲义论文; 清朝论文; 八旗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满族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清代通史论文; 清史稿论文; 孟森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武昌起义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