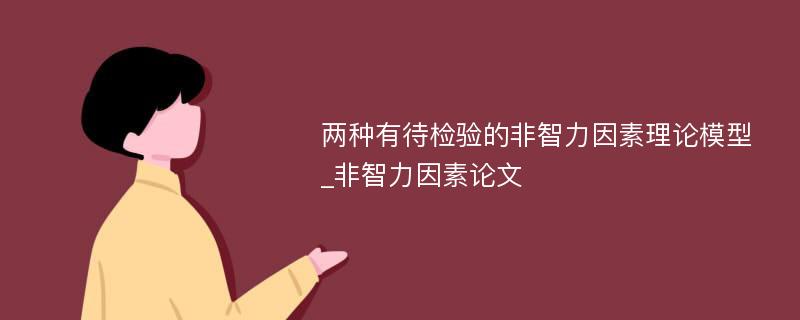
非智力因素理论的两个模型待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智力因素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非智力因素理论曾经有激争。虽然大家都想把个“真理”越辩越明白,可是唇枪舌剑沉寂后,虎踞龙盘今胜昔。尽管这是学术中的稀松平常事儿,不过怕就怕时间,它那无为而为的惯伎是以不了而了一切:一个理论只要十年八载没有新的思想来光顾,就会风化剥蚀成旧说。去岁,我怀着偶然产生的这种感慨去随便翻翻那场争辩的旧文,不想应了孔子“温故而知新”的话,意外的收获是发现两位教授当年的滔滔雄辩仿佛你向东走我西行,渐行渐远,最终走到了一起来;我觉得这个发现兴许能够成为非智力因素理论学术研讨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且看下文分解。
大水莫冲龙王庙
燕国材教授畅谈非智力因素理论时,屡屡提到他的函数式(注:燕国材:《论非智力因素及其在教育工作中的意义》,《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A=f(I,N)[1]
式中的A指学习成绩,I指智力因素,N指非智力因素; 全式含义的一个通俗说法可以表达为学习成绩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共同决定的。
皮连生教授在发表异议的时候也亮出了自己的函数式(注:皮连生:《智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学习成绩=f(动机,原有知识,IQ水平) [2]
式2的“动机”对应于式1的N,是N的具体一项;“IQ水平”不但对应于式1的I,而且约束精当,可以操作;这都是聊胜式1处。式2还添加了“原有知识”这一项,从而显得与式1不同。 不过皮教授把“原有知识”说成是属于“非智力因素”的(注:参见皮连生:《智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 以及《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分类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载《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2期。),这虽然值得玩味,可字眼儿毕竟没扣准, 我想,那个“力”字该改成“商”字吧?当然,这是小毛疵。
若论大体,则式2挤兑不了式1,因为式1 中的I 并不是只能表征为IQ的,在学校实际工作中,它是可以更宽泛也更实用地表征为“认知因素”的,其中自然包括着为学习新知识而必需的知识基础。因此,当我们把式2的“动机”纳入式1的N,把余两项合并为式1的I后, 两式就了无差别了。说到底,式1与式2,貌离而神合。既神合,就莫要大水冲了龙王庙;貌离呢,则权当黑猫白猫看:式1更概括,宜作理论概述用; 式2颇具体,可派实际研究用;两式何妨笑相联袂携手行?
惜乎浪费了函数式
式1和式2,还都是乔装改扮的Y=f(X),同属函数一般表达式, 本身不可操作,没法作计算,也就无法检验它们作为假设性理论是否被经验证据所支持。这样的“函数式”没有数学意义,于是乎大材只能小用,聊充一个比喻,显得很浪费。而比喻有“两柄”兼“多边”(注:钱钟书:《管缀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1页。),不但筑不成理论的严阵,反有按下葫芦却起瓢的尴尬。惟此之故,“比喻总是跛脚的”(斯大林),推倒它们很容易,只是此起彼伏都在原地未尝向前进。
式1和式2,含义也朦胧。以式1为例, 我们既可专业化地说:A 是I和N的函数;也可大俗话地讲:A是I和N共同决定的。 但是只要两式都冻结在眼下的表达形式上而不化开,那么前一说法就只是同语反复,因为函数表达式自然表示函数关系呀;后一说法又宽泛无涯,因为函数一般表达式包含的具体形式五花八门,其间的经验涵义甚有差别,那么式1、式2究竟刻画怎样的函数关系呢?在这最要紧的关头,两式都仿佛咬紧了牙关不交代。所以我想,那两式若真要成为理论建树所必需的数学工具,就该接着把方程拉出来,把模型建起来,然后检验之,这才算物尽其用不浪费。
实证研究实不证
燕教授是有意实证其理论的,这是他高于那场争辩中各路持异议的学术力量所在,具有科学研究一般方法论意义,该发扬。而从深化学术探讨的视角看,最好的发扬方式莫过于揭示重要的欠缺,以使后来者的添砖加瓦方便些。比如这样的一组研究(注:详见燕国材主编:《非智力因素的理论、实证与实践研究》中《第四编:实证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分别考察动机、兴趣、意志和性格对学习成绩的关系;它们的设计清一色,只计算相关系数r,结果呈一律, 都是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然而最重要的欠缺恰恰出在这旮旯。
首先,那些研究只做二元相关分析,式1就坐了冷板凳, 因为按照式1做研究,起码也是个三元的回归分析, 所以那组研究根本就没“去”实证式1,这要算个退步。我因此而担心,以式1为精简形式的非智力因素理论恐怕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经过科学研究的证实。其次,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常识上,抑或从研究策略上看,式1 都是蛮好的一个支撑研究的“桥墩”理论。那组研究把它撇在了一旁,自己也就没了依托,结果是不但修不成平坦通达的“桥面”理论,反成了多余的劳作,因为即使在那场争辩中,好像也没有见谁否认过非智力因素与学习成绩的正相关,因此值得做个研究专门给他瞧一瞧。第三,或云r 的重要性在此不是判定相关之有无或相关之正负的“性”,而在厘定正相关的“量”。此言固有理,却差在不知有其二。其实,与自然科学一个样,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分析也是为了确定变量间的比率关系,这就需要获得估计参数。可惜r不是这样的参数,它只定性地描述“N越好,则A也越好”,却不能定量地描述“N若提高1个单位,则可使A大体上提高多少个单位”。这样一看,那组研究就没有什么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了。前者是因为N与A必为正相关的,否则这世界就荒诞了;后者是因为假如不知道N提高了1、3、5……分后, 大体可以分别“换来”几分的A,我们就设法心中有“数”地帮学生确立提高成绩的目标,更不能指导学生恰如其“分”地努力。显然,学生的努力不能无“度”,过犹不及,反伤其身。第四,要是那组研究报告了完整的描述统计资料就好了,这样我们仍可联系着r来算出二元回归的估计参数, 非智力因素理论的说明也可以有明显的改善,何况那还是“一组”的研究呢,这样的“一批”估计参数对后续研究是极有价值的。所以我建议:如果数据还在,就值得补做回归分析,再次发表,以飨学界。
不过即使补做了,那个至少三元的式1也还是未曾证实过。因此, 为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当前亟需拉出关于式1的方程。 以下两节就分说两个简单的、有待检验的、也是可以检验的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燕教授在1988年说:“一个智力水平(I)很高的学生, 如果其非智力因素(N)没有得到较好的培养,他只能成为‘小器’, 而不能成为‘大器’。这就是说,学生是否学习得好(A),是否能够成才, 不能单从智力方面找原因,还要看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水平如何。”(注:燕国材:《论非智力因素及其在教育工作中的意义》,《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我把这段话称为“燕说A”,它讲的乃是 I和N“各”对A的影响。比如“单是”I好,只能成“小器”,如果N“也”好,则“小器”变“大器”。于是从逻辑上说,(大器)-(小器)=(N“单独”增加的那部分A)。基于燕说A, 我们可以说明一个固定效应的直线模型(注:燕说A本身并不提示一个“直线”的方程, 但从直线方程做起来,却是符合科学研究的经济学和美学原则的。),其系统部分(注:完整的模型说明是:A[,i]=b[,0]+b[,1]I[,i]+b[,2]N[,i]+e[,i]。)如下:
A=b[,0]+b[,1]I+b[,2]N[3]
式中的A和I、N都是观测变量,如果输入数据, 即可算出估计参数b[,0]、b[,1]和b[,2];有了这些b,就可以在样本所属的总体内,联系特定学生的I和N的观测值,估计其A, 这就是回归分析优于相关分析的地方。方程中的b[,0]是截距,逻辑上不重要,我们设b[,0]=0而取消之,于是有本文专论的部分:
A=b[,1]I+b[,2]N[4]
式中的b[,1]和b[,2]是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当I、N变化1个单位时,A将变化多少,很像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比如,假定b[,1]、b[,2] 都等于1,那就好比说:1分I与1分N将各自“换来”1分A, 合起来就总共“换来”2分A;现在援引方程4,就有算式写如右:A=b[,1]I+b[,2]N=1[,1] ×1+1×1=2。该算式表明方程4丝丝入扣地支持燕说A。比如甲乙的I都是9,而甲的N=1,乙的N=9,代入方程4以后,将算得A[,甲]=10,A[,乙]=18,于是甲即“小器”,乙为“大器”,“器”之大小在此皆由N的高低所决定。但是方程4也同样有力地对抗燕说A: 若甲乙的N都是9,而甲的I=9,乙的I=1,那么将算得A[,甲]=18,A[,乙]=10, 这时“器”的大小就由I的高低决定了。何以会这样?
原来,方程4并列了I和N, 这就使得重智力因素和重非智力因素的理论都可以持其一端而相互发难,上面就是一个小演示。但是这恰好表明方程3实质上是个无偏不袒的公允模型, 它仿佛宣告:“逻辑上”认为I和N对A的影响力是同等的,至于“实际上”是I还是N 的影响力更大,这不靠理论论辩来确定,而要做“实事求是”的检验。在这里,实事,指落实一个数据集,切实输入方程3运算;求是, 指依据计算结果再来确定指导“当前”工作的理论重点在哪里。这就是方程3 的强处之所在。
方程3也有软处。它虽然落实了“共同决定”的思想, 但这是“怎样的”共同决定呢?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假定b[,1]、b[,2]都是1,再设甲的I=9,N=1,而乙的I=1,N=9, 那么代入方程4之后,两人的A就都是10;这好比说:甲比乙少的那8分N将由甲比乙多的这8分I“补偿”了。可见方程3 是以“简单补偿”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决定”的,而这种决定方式也是对抗燕说A的。
那么这种“简单补偿之共同决定论”又潜藏着怎样的实质性思想呢?我们仅举b[,1]谈,b[,2]可反参。且写b[,1]=(0+b[,1])=b[,1],并定义b[,1]是I的“汇总的”或“最终的”估计系数,于是可见在方程3中,b[,1]总是等于b[,1],亦即I的估计系数是不变的,这就是“固定效应”之含义。固定效应的别解是“独立效应”,即I 的最终系数b[,1]是不受N影响的。譬如b[,1]等于1,则不论N多大或多小,b[,1]总是等于1。由于b[,1]表示I最终能够“兑换”多少A的单位效能,因此固定的或独立的b[,1]就意味着说:不论两人的N高低多悬殊,他们的I 的单位效能是一样的。这个说法中听吗?如果觉得此说“不”顺耳,那就意味着我们“相信”非智力因素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智力因素的单位效能发生变化的,这样的“信念”将鼓励我们扬弃方程3, 建构一个新模型。
制约效应模型
1994年,燕教授有一段表述言简意赅真精彩(注:燕国材主编:《非智力因素的理论、实证与实践研究》的“前言”。),我称“燕说B”:“智力因素对学习活动起直接作用,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活动则起间接作用。……;非智力因素……不能帮助人们直接获得‘双基’,它只能通过对智力活动的支持与促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学习。”对比“1988年的话,真个是焕然一派新气象:寥寥数言两次提到“直接”与“间接”,其肯定与否,简直是斩钉截铁,而并列以对比,端的似白雪红日,令我想到新的模型该取消N与A的直接联系,也就是取消方程3的b[,2]N那一项;再稍变燕说B的最后一语之句法,即成“N促进I的活动”,此乃点晴之笔,令我想到该把N与I直接相联系,这就是在方程3 中新增一个二路交互作用项,其中的变量写作I与N的积,其系数为b[,3]。 于是严格采用燕说B,便有新的方程写如下:
A=b[,1]I+b[,3](IN) [5.1]
通过提取公因式I,遂有
A=(b[,1]+b[,3]N)I
[5.2]
再定义(b[,1]+b[,3]N)=b[,1],终有
A=b[,1]I
[5.3]
方程5.3中的b[,1]仍旧是I的汇总系数,表示I的汇总单位效能。
方程5.3虽然简单得只有1个项,但是b[,1]中有奥妙。且看b[,1]=(b[,1]+b[,3]N),虽然其中的b[,1]和b[,3]都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因为括号里有变量N,所以b[,1]是依N而变动的。于是我们可以说:N(的变化)制约着I的汇总单位效能b[,1](的变化)。这与燕说B 中关于N支持和促进I的活动之说相契合。再看方程5.3,它说b[,1]的变化导致b[,1]I的变化,也就是A的变化。我们组合这两个说法, 就有一个完整的陈述曰:N(的变化)通过制约I的汇总单位效能b[,1] (的变化)而导致了A的变化。这个陈述是与燕说B中关于非智力因素“只能通过对智力活动的支持与促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学习”的说法严丝合缝的。下面就对N的“间接”影响做个小演示。
假定:①b[,1]=b[,3]=1;②甲乙丙的N不一样,赋值也不同,乙为中等,即N[,乙]=0,而甲、丙分别为高于、低于中等水平1个单位,即N[,甲]=1,N[,丙]=(-1);③3人的I一样, 都高于中等水平(I=0)的1个单位,即I[,甲]=I[,乙]=I[,丙]=1。于是, 将上述假定值代入方程5.2以后,则有3人的估计式如下:
A[,甲]=(1+1×1)×1=(1+1)×1=2×1=2
A[,乙]=(1+1×0)×1=(1+0)×1=1×1=1
A[,丙]=[1+1×1(-1)]×1=[1+(-1)]=0×1=0
3式中有放大加黑的数字3列,左起第1列表示N的高中低;第2 列斜体数字是b[,1],它们随N而不同,甲是2,乙是1,丙是0,表示同样的1分I却有不同的汇总单位效能;通俗地说,同样的1分I对A的最终“兑换率”是不同的,因此“换来”不同的A,这就是最后的一列数字。
我们还可以对上面的3个式子作更加贴近日常经验的描述, 为此定义N为“努力”,分勤—中—懒3个水平。先说乙。乙的努力程度属中等,即是不懒也不勤。不懒,则I活动时,N不会拖后腿;不勤,则I 活动时,N亦不推一把。于是乙的成绩高低就单看智力水平高低了。 由于乙的智力本来就高于中等水平1个单位, 因此乙的成绩也就高于中等水平1个单位(A[,乙]=1),这很好。再说甲。甲比乙勤1分,勤则I活动时,N再来助一臂,这就把I的单位效能提高了1分,加之I本来就有1 分的单位效能,于是甲的1分I就产生了2分的汇总单位效能,“换得”2分的成绩(A[,甲]=2),这更好。最后说说丙,可以这么说:如其不懒, 则I活动时,自有1分的效能,也就会和乙一样,获得高于平均水平1 个单位的成绩;惜乎丙懒乙1分,懒则I活动时,N拖后腿,这就抵消了I本有的1分单位效能,于是丙就不及乙, 只获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成绩(A[,丙]=0)。总起来说,甲乙丙的智力都高于中等水平1个单位,我们因此期望他们的学习成绩也都高于中等水平1个单位, 但是由于非智力因素水平不同,这期望的成绩呵,乙达到,甲超过,丙未及。至此,制约效应模型完全支持燕说B。
但是制约效应模型也是公允的,这就意味着:它以多大的力量支持燕说B,也就以多大的力量对抗之。 理解这点很简单:咱们干嘛只想着N制约I呢?为何不来个“逆向思维”,构想I制约N呢?如果这样想,则从方程4开始,模型的核心部分将首先写作方程6.1:
A=b[,1]I+b[,2]N+b[,3](IN)
[6.1]
然后提取公因式N,遂有
A=b[,1]I+(b[,2]+b[,3]I)N [6.2]
再定义(b[,2]+b[,3]I)=b[,N],终有
A=b[,1]I+b[,N]N[6.3]
方程6.3中最重要的是b[,N]N一项,由于N的最终系数b[,N]=(b[,2]+b[,3]I),这就意味着非智力因素水平的作用是依智力水平的高低而变化的。于是我们又见一个有待检验的课题,即:究竟是说N制约I更合乎实际呢,还是说I制约N更合乎实际?这同样要求我们去做如前所说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注:本文为方便,主要讲式1,但对式2基本也适用。不过式2的独特意义主要在教育行政学方面, 有关问题待以后联系实际资料再论说。)
小结
①根据燕说A,可有固定效应模型, 以检验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各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力。②根据燕说B,可有制约效应模型,以检验在燕说A与B之间,何者更加符合实际。③根据模型的公允性, 可以检验:在智力和非智力因素之间,究竟说谁制约谁是更加符合实际的。
标签:非智力因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