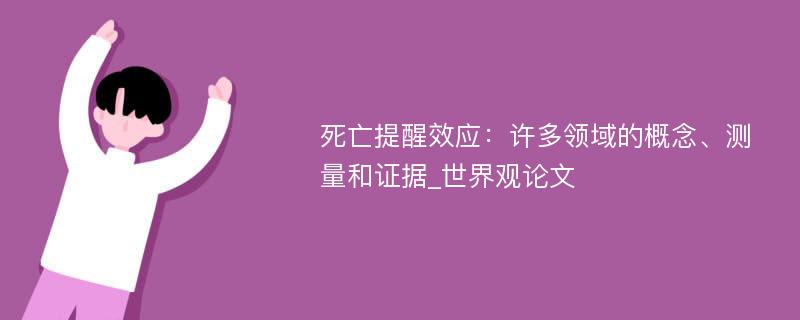
死亡提醒效应:概念、测量及来自多领域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测量论文,证据论文,效应论文,概念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除了死亡和纳税。”实际上,死亡比纳税确定得多。虽然传统儒家思想并不重视死亡,所谓“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十二》),但谁又能否认死亡对于人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家贝克尔在其普利策获奖作品《拒斥死亡》中指出:“死亡是人寻求幸福这一核心要求中深藏的蛀虫。”[1]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可是在心理学领域确有理论与之一脉相承,这就是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有一种求生怕死的本能,但人类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并且“必死无疑”的物种,这一宿命昭示着可怕的无意义和彻底的虚无,因此在潜意识层面,死亡极端令人恐惧[2]。为了“管理”死亡恐惧,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发展出了世界观与自尊来缓冲死亡焦虑。个体的世界观和自尊是社会的产物,它需要社会群体中其他人的确信与维系,所以个体的许多行为都指向对世界观和自尊的维护[3]。死亡提醒效应(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s)整合了理论中涉及的死亡焦虑、世界观及自尊等要素,并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引发了众多研究。
1死亡提醒效应的概念
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是恐惧管理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意指对人们“必死性”的提醒和揭示。死亡提醒假设(mortality salience hypothesis)是恐惧管理理论的核心假设之一,它认为如果世界观或自尊能起到缓冲死亡焦虑的作用,那么死亡提醒将增强人们对此的需求[3]。研究者最初关注的焦点是在经历死亡提醒后,人们会更强烈地捍卫自己的世界观,即对于与其世界观相符的行为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而更消极严厉地对待那些与其世界观相左的行为[4],这也是死亡提醒效应在早期的主要含义。在最早的一项实证研究中,Rosenblatt等人让被试评定该给一位举报谋杀犯的妇女多少奖金,结果死亡提醒组给出的奖金额度显著高于控制组。同时在死亡提醒后,法官被试对于涉嫌卖淫的妇女提出的保释金数额显著高于控制组[4]。此后,又有众多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死亡提醒效应。例如,在进行死亡提醒后,被试对于内群体和称赞他们文化的人评价更积极,而对外群体和批评其文化的人评价更加消极[5];对威胁其世界观的人具有敌意等[6]。这些现象被概括为世界观防御(worldview defense)[7]。
后来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依据死亡提醒假设指出,死亡提醒也可以引发人们对自尊的寻求(self-esteem striving),即死亡提醒会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去迎合某些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的实现与自尊密切相关[8]。有研究发现,如果被试认为驾驶能力与自尊相关,那么在死亡提醒后,他们会倾向于发生更多的危险驾驶行为[9]。另外,在死亡提醒后,身体自尊水平较高的被试会更加认同自己的身体[10];被试会出现更强烈的自我归因偏差,以利于维持其自尊等[11]。Solomon等人认为这些现象是由死亡提醒假设派生出的另一核心推论,暗示其也是死亡提醒效应的一部分[2]。近期在一篇关于死亡提醒效应的综述中,有研究者也归纳指出,死亡提醒既可以引发世界观防御,也可以促使人们维持自尊[12]。鉴于此,有理由认为,由于死亡提醒而引起的世界观防御或自尊寻求,可以统称为死亡提醒效应。死亡提醒效应在多个国家及不同文化背景中均得到了证实[13],表明其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2死亡提醒效应的测量
对死亡提醒效应的测量,首先需要进行死亡提醒。考虑到人们通常忌讳死亡,所以在经典的死亡提醒操作中,研究者先让实验组被试完成一些人格测验题,以隐瞒真实的实验目的。在测验题后面,会附带两个与死亡相关的开放式问题,事先说明这是一个最新的人格投射测验,以消除被试的疑虑[4]。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即是进行死亡提醒:“请想象你自己的死亡,并简要描述你此时的情感体验”、“你认为当你死去时,你的躯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请快速并详尽地写出”。控制组被试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不过主题是中性的(如观看电视),或其他与死亡无关但能引发焦虑的话题(如在公众面前演讲)[14]。
接下来,研究者会让被试填写情绪量表,并完成填字游戏等分心任务以进行短暂延迟,然后测量他们在世界观防御或自尊寻求上的反应[14]。世界观防御的常见测量方法是让被试评价支持或反对其世界观的对象。例如,在死亡提醒后,研究者先给美国被试呈现一篇赞扬或批评美国的文章,接着提供一些正性及负性的描述词(如“热心的”、“傲慢的”),要求他们以这些词对该文章的作者做出评价(9点量表,从“1=完全不符合”到“9=完全符合”,负性词反向计分),这样就可以得出他们对作者的态度。得分越低,说明被试的世界观防御水平越高[15]。而在自尊寻求的测量方面,研究者通常先调查被试是否认为某种行为与自尊有关,如果是,那么经过死亡提醒,若被试增加了参与该行为的意愿,就说明被试存在自尊寻求的倾向[9]。
3死亡提醒效应在多领域中的证据
由于世界观防御和自尊寻求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者提出死亡提醒效应后,大量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就应运而生,领域涉及健康、消费、司法、政治以及和平领域。这些研究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死亡提醒效应,而且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富有启示作用。
3.1 健康领域
在对死亡提醒效应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众多防御行为均与健康有关。Goldenberg和Arndt提出了恐惧管理的健康模型(terror management health model),试图从恐惧管理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与健康相关的行为。根据该模型,如果某项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增强(减弱)了自尊,那么在死亡提醒后,人们会更多(少)地从事该行为[16]。一项研究发现,低自尊的老年被试在死亡提醒后,更愿意参加那些利于健康的活动,而高自尊的老年被试则没有出现此倾向。研究者推测高自尊的老年人在生活的更多领域获得了足够的意义感和满足感,而低自尊的老年人只能通过寿命的延长而获得些许自尊,因此他们对于促进健康的行为反应不同[17]。另一项研究显示,因为外在原因而抽烟的被试,在经历死亡提醒并观看了一段宣传抽烟损害个人自尊的短片后,更倾向于戒烟[18]。
3.2 消费领域
死亡提醒可以导致人们对世界观的遵从,而消费主义是当今社会流行的世界观之一,死亡提醒效应是否会影响消费行为?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发现:1)死亡提醒会导致人们更多地追求名牌消费品。Mandel和Heine的研究显示,在死亡提醒后,被试对雷克萨斯汽车、劳力士手表等高档消费品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其广告的评价更高,也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购买欲望[19]。另一项研究也证实,死亡提醒会导致被试更倾向于名牌消费和冲动消费[20]。2)死亡提醒会引发人们对本国产品的推崇。在死亡提醒后,德国被试对于大众、奥迪等本国汽车品牌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偏好,同时也更加喜爱本国的饭菜[21]。Friese和Hofmann也发现,死亡提醒后,被试对本国食品的评价更高,实际消费量也更大[22]。3)死亡提醒对消费的影响还与自尊寻求有关。一项研究发现,高身体自尊的女性被试在死亡提醒后,更少选择容易令身体发胖的巧克力[23]。另外,认为酒量与自尊相关的被试在接受了针对酗酒的死亡恐惧诉求(fear appeals)后,对酒的消费量反而呈上升趋势[24]。
3.3 司法领域
司法领域中常常会涉及死亡,因此死亡提醒效应有可能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在死亡提醒后,如果被告威胁到了审判人员的世界观,那么对于被告的审判会更加严厉;而如果受害者威胁到了审判人员的世界观,那么他们会倾向于对被告从轻处罚[25]。Rosenblatt等人的经典实验就是以法官为被试,发现在死亡提醒后,他们对于涉嫌卖淫的妇女提出的保释金数额显著高于控制组[4]。另一项研究模拟了这样一个案件:被告殴打了一名参与同性恋集会的男子,同时在殴打过程中对该男子进行辱骂,内容涉及反对同性恋的主题。然后要求异性恋取向的被试写下保释被告的合适金额。结果表明,在死亡提醒后,被试提出的保释金金额明显低于控制组[26]。
3.4 政治领域
近年来,死亡提醒效应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有数个研究以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为大背景,发现人们对于总统候选人布什和克里的选择也体现了死亡提醒效应,这与“9·11”事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恐惧管理理论的角度,“9·11”事件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强烈的死亡提醒,而在第一时间宣布要捍卫国家尊严并采取强硬反恐政策的布什,无疑是与多数美国人的世界观相吻合的。因此可以预见,死亡提醒后美国人会更加支持布什。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控制组中,被试对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支持率是高于布什的。但在死亡提醒组,被试对布什的支持率却明显上升。研究者据此推测,布什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的获胜,也得益于美国人潜在的死亡焦虑[27,28]。
3.5 和平领域
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威胁和平的重要因素。在恐惧管理理论看来,不同的文明意味着不同的世界观,当涉及死亡提醒时,人们对各自世界观的捍卫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29],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一项研究表明,死亡提醒会使伊朗学生更加支持针对美国人的自杀式袭击,甚至表达出更强的参与意愿。同时,在政治立场上持保守态度的美国学生在死亡提醒后,会更加支持美国军队强硬的军事行动[30]。那么死亡提醒效应对于和平进程是否只会产生消极影响?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指出,死亡提醒效应可能导致对外群体的偏见、刻板印象、种族主义、攻击等不利于和平进程的结果,但也可以启动世界观中亲社会的成分,如友爱、无私、宽容等[12]。换言之,对于和平来说,死亡提醒效应犹如一把双刃剑。死亡提醒使人们更加遵从世界观,但不同文化中对行为的价值判断有可能是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如何让死亡提醒引导人们往相同方向前行?有研究表明,死亡提醒是与标准提醒共同影响社会判断的,所谓标准提醒是指人们当前所注意到的行动标准,它不一定与原有的世界观相符合[31]。Niesta等人建议,利用宽容、仁爱以及和平主义的标准提醒,有可能使死亡提醒效应对和平进程产生积极影响[12]。
4总结与展望
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的。死亡并非一个遥远的结果,而是在人活着的每一刻都存在着并产生影响。作为一个本身结合了哲学思想的心理学理论,恐惧管理理论,尤其是其中的死亡提醒效应,与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不谋而合。自从恐惧管理理论诞生以来,与死亡提醒效应相关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并得到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然而,目前的研究也还存在着某些争议之处,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首先,不论对于世界观防御来说,还是对于以符合世界观的要求为标准的自尊寻求而言,世界观均是重要的基础性概念。虽然研究者为世界观下过定义,但世界观到底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其中是否存在着优先和不同的权重,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者却很少进行探讨,这可能造成一系列问题。有研究者指出,世界观可以是个性化的[32]。Arndt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男女在世界观的建构上是不同的,男性更看重爱国主义,而女性对亲密关系更敏感[33]。但许多研究中对世界观防御的测量都偏重于爱国主义,当涉及较多女性或是不看重爱国主义的被试时,就有可能造成结论的偏差。另外,有研究者主张,亲密关系是独立于世界观和自尊的恐惧管理机制[34]。恐惧管理理论的支持者虽然承认亲密关系的重要作用,但却试图把它纳入到世界观的范畴中[35]。这种争议就是由于未细化世界观的概念而造成的。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恐惧管理理论无法完全排除存在着其他恐惧管理机制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明确界定世界观的范围,宽泛的定义有可能“包罗万象”,导致许多类似的争议,这不利于死亡提醒效应研究的发展。
其次,国内对于死亡提醒效应的研究还十分匮乏。在本土化过程中,国内研究者除了完成对研究工具的修订、进行一般的跨文化比较以外,还需要关注死亡提醒效应研究的新趋势并重视本土文化中的生死观。比如,死亡提醒效应更强调人们对于死亡恐惧的防御反应,但是否存在超越这种恐惧的可能?近年来,研究者初步予以了肯定。他们发现,正视死亡可以使人产生类似创伤后成长的效应,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在目标[36]。而此研究结果,与不忌死亡,主张回归本真的道家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对于现今的死亡提醒效应研究,古老的生死智慧依然有着独特的启迪作用。国内的研究者可以积极借鉴,以探寻死亡提醒效应研究可能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