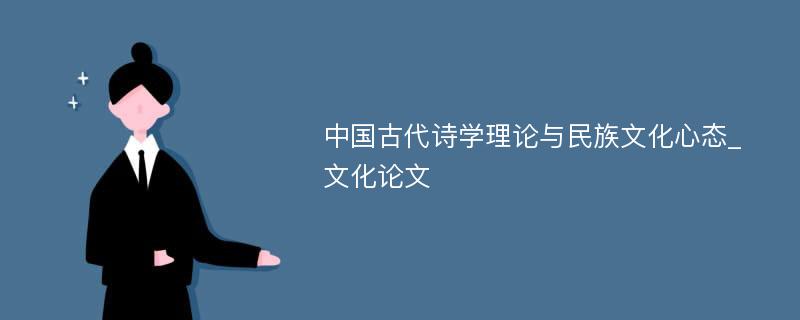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与民族文化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民族文化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心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在中华文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其特点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态紧密相联的,尤其是传统的认知方式、思维习惯和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对古诗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对古代诗学的特点略加分析。
尚情:天人合一与古代诗学理论的支点
以情立本是我国古代诗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文论以“再现说”构筑其文论体系相区别,我国古代诗学理论是基于“表现说”这一支点的,一个“情”字正是这个理论的核心。首先,在对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上,古诗论贵情思而轻事实。古人认为,情是诗的本质、灵魂,物象虽在审美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不具有自在性和独立性,因而不具有本质性,它只是诗人抒情的媒介,“景者诗之媒,情者诗之胚”[①],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当“专作情语为妙”。由此出发,古诗论强调写诗要情真至诚,作诗要出于“无意”,不以力构,否则,便会强作情语,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无心偶会,则收点金之功;有意更张,必多画墁之梢。”其次,在对诗作品内在系统性质的认识上,古诗论强调诗之灵在空,不在巧。“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②]“空”是诗人为作品创造的意境,“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③]所谓“用心造境”之“虚境”,便是意境的实质,它可以引导人在形象之处用心、用情去感受诗主体的情绪体验,身临其境,从而达到欣赏的极致。再次,在诗歌情理统一问题上,古诗论主张介贞情以求性。以情立本和以理驭情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对矛盾,情是不能不要的,理是不能不讲的,于是就有了中和理论,“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己者情也,动焉而不自待者欲也。”[④]尽管“中和说”实际上造成了中国诗歌史上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遗憾,但它仍不失为中国古诗学的一大特色。最后,在诗歌欣赏上,古诗论提倡披文以入情。古诗论认为诗的欣赏过程是情的感应过程,体验是欣赏的极致,因而,欣赏往往陷入难言状态,古人因此把读诗喻为参禅,盛唐时有“诗为儒者禅”之说。读诗与参禅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它们都强调一个“悟”字,李之仪在《赠祥瑛上人》中说:“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强调一个“悟”字,是为了避免因具体分析而阉割了作为整体存在的情感体验。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诗学是一种尚情文学,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随着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礼”和“理”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是最为亲密的家庭感情也受到了无情的绳限,《孟子·离娄》载:“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权也。’”这里的“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儒家对女子所作的“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⑤]的限制便是一个注释。这种以“礼”节“情”、拘谨自制的儒家文化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弃“宣泄”而存“中和”,导致了阴柔有余,阴刚不足的局面。但不管如何,中国古诗创作终究没有背弃浓郁的“尚情”传统而走向“达理文学”,其根源何在?
诚然,情和理本来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两根支柱,任何以理驭情的企图都只能因为其违背人性而不能得逞,但除此以外,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取向从根本上支撑着尚情文学的恢宏大厦。
天人合一观作为一种思想在《易经》中首先得到较完整的体现,其实,作为一种观点和主张,它早在《易经》之前就形成了,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天人合一观认为,自然法则与人事规律是一致的,人在天人关系中是能动的主体,天和人应当相融。《素问·宝命全形》中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玉版》中进一步强调:“人者,天地之镇也。”天人合一观的广泛影响,尤其它对“人”的重视,使历代思想家们想谈“礼”,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董仲舒在《天辨在人》中说道:“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他不得不承认作为“百神之大君”的“天”也和人一样有着志欲情感。《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论语·雍也》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理学大师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心包万理,万理其于一心。”这至少在客观上是对人的情性的褒扬。
天人合一观对古代诗学最重要的贡献应当是它对我古代诗歌美学精髓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现说和意境说是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两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命题,它们都特别强调情与景的有机融合,“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⑥]这种诗学理论与天人合一观的基本思想相符,认为诗人所发之情,都可以在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为寄托,而天人合一观认为,宇宙是人的放大,万物是心的外化,人心之性与天地之道乃为同一。《乐记》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周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收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又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通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可见,在天人合一观中,心性的抒发就是宣明天地之理,对自然和外物传神的描摹必然能表现人的内心情感,而这正是我国古代诗学表现说和意境说的基本依据。因此,可以这么说,正是天一合一观影响下的中华民族对“情”的独特理解及其对“情”的深刻表达铸成了我国古代诗学理论体系浓厚的民族特色。
点悟:圜道文化与古代诗学的理论形态
所谓理论形态指的是对理论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的存在形式。
我国古代诗学强调情感的体验,而情感是个“黑暗的世界”,它具有丰富性、隐蔽性、个体性的特点,任何人都难以完整地、清晰地、准确地用有形的语言传达无形的情感,更不能通过语言完全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全部情思,对情感的体验往往陷于“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状态。正基于这种认识,古诗论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当行,乃为本色。”[⑦]对诗歌的理解强调一个“悟”字,对诗歌评论,以及对诗歌创作方法和理论的总结也就出一个“点”字,如六朝僧人汤惠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缕金”的评论便是点评式。诗歌大家谢灵运与佛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与诸道人辨宗法》就是宣扬顿悟成佛的,所以,他的第十世孙皎然在《诗式·文章宗论》中评谢的创作历程时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公为文,直于情性,尚于功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其实,不仅仅谢灵运,几乎所有的古代诗人都认为言语道断、以顿悟入境是诗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通常把贾岛“推”、“敲”之择看作准确地描摹情态的典范,其实,如果从意境说出发,贾岛的一字之斟酌正是为了给读者创造一个内涵更加丰富、意境更加深远的理解空间。
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以“点悟”为特点的诗歌批评方式的形成,这种点悟式批评的实质便是“比物取象,目击道存”[⑧]。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为例,它以生动的意境勾勒出二十四幅不同的印象图画,它的所有评论都摒弃了一切有目的的逻辑思维,凭直觉评诗。如“夫岂可道,假体为愚,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流动”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含蓄”篇)这种以经验性、直觉性为基础的点悟式的批评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形态的其他两个特点:理论的零散性和概念的模糊性。
点悟式的批评在文字上表现为只言片语,在理论上则很少见到严密的逻辑分析。这与西方文论不同,西方文论从《诗学》、《诗艺》起就带有浓烈的思辨色彩,以论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其内在系统往往体现出坚不可摧的逻辑力量,而有较大零散性的中国古代诗论只能以其整体的力量与西方文论相抗衡。
以直观的方式进行诗歌批评,这决定了批评的语言表达不可能是理性分析式的,而只能形象描绘式的。《文心雕龙》、《文赋》、《诗品》诸作以赋的形式写成便可证明这一点。因而,我国古代诗学既是诗的理论,也是诗的理论,它是以诗的语言总结诗的创作规律的,这种诗的理论,在概念运用上很难使用意义单一的纯概念,而往往使用含义模糊的类概念。比如“兴”,古人一方面把它与“感”结合,贾岛《二南密旨》称:“感物曰兴”,“感兴”成为诗歌生成论的基础;另一方面,古人又把“兴”与“情”联姻,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语曰:“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袁黄在《诗赋》中也说:“感事触情,缘情生境。……斯谓之兴”“情兴”成为诗歌本体论的核心。此外,后人对“诗言志”驴头马嘴的争论,对“气”、“境界”等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大多如是。
中国古代诗学点悟式理论形态的形成直接受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影响。与西方人把多元看作是世界的特点,以分析的方法寻找世界的差异和矛盾不同,我国古人认为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混沌整体,任何矛盾对立的现象在本质上都可以归而为一。这种认识起源于《周易》中的圜道观。圜道观认为,日月阴阳始终做着永恒的环周运动,“天易谓之乾。乾,健也。健行不息也。”这是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天》中对《易》首卦乾卦的解释。既然世界的运动是循环往复的,那么世界万物就必然是一个整体,《吕氏春秋·情欲》说:“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的圜道观是强调综合而轻视分析的。这一点还可以从具有民族图腾性质、体现民族主体精神的“龙”的综合性和兼溶性特点上得到佐证。世上本无龙,龙的形象是集中了我们祖先的意志、希求、情趣、道德和审美标准以后才定型的,它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综合后,才成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所勾画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神物形象,它的形体的创造和神性的赋予,还融入了风、云、雷、电、水、火诸种自然现象的形象和伟力。
由于把一切对立、矛盾的事物都看成是相联系的整体,而整体又是不能被分割的,所以,古人认为如果对整体进行解剖式的分析,就难以完整地把握整体,主张以“神会”、以直观对世界进行认知,事物的本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即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的精神应当在极端的虚静境界,凭直观的体验、在无言中与宇宙相统一,所以古人崇尚“大辩若讷”。这些认识在诗歌鉴赏和批评上必然发展为点悟式的批评方式。
蜕变:循例从众与古代诗学的发展形式
农业文明给东方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重情轻利和重悟轻析的文化特质,它还使循例从众成为民族文化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具有单调性和重复性的农业生产使人们感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只不过是一种大循环,任何变化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进行的,万变不离其宗,儒家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家讲“枢始其环中,以应无穷”,都是这种认识的具体阐发。正因为此,“祖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显得非常重要,它被公认为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支柱。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产生的儒家学说把这个认识阐释得很清楚,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⑩]所以,孔子倡导“述而不作”,要人们因循祖制,不必创造。这就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循例从众的认知方式。
这种循例从众的文化心态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古代诗学在发展形式上的特点——蜕变,即,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发展表现为历史性的积淀,对前人的理论总是先继承后发展。比如,作为中国诗歌开山性纲领的“诗言志”的命题一直影响到现在,后人所做的研究工作不过是对这个命题不断论证、丰富,使之趋于完善。
这种蜕变式的研究给我国古代诗学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使这种诗学体系能在不断丰富、强化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扼制了一些精辟的“离经叛道”的诗歌理论的发展,使古代诗学的研究不能多角度地伸发。
在这种研究状态下形成的诗学体系是种一元性的理论体系。显然,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源头是“诗言志”,正是围绕着这个命题,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个诗论大家,这些大家都从不同侧面为这个命题寻找各种理论的和事实的证据。“诗言志”作为诗论体系之“元”,是一个丰富的“混沌体”,它既指诗创作,也指诗欣赏,既对诗主体提出了要求,也对诗作品作出规范,还对诗的批评提供了准则,更重要的是对诗本体的揭示。这样就给后继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中国古代诗学以“情”为核心的本体论、以“才”、“气”为内容的主体论、以感兴为基点的生成论、以意境为主体的作品论、以感应为中心的欣赏论因此而在后人的互相验证、互相补充的蜕变性研究中逐步形成。
自然,循例从众的认知方式和蜕变尚通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古人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排它性,人们指责“离经叛道”的理论。比如:正统的儒家称相信鬼神的墨子“乱儒义”。在诗论中,凡是与“诗言志”的命题相抵触的理论都没有市场(当然,在古代诗论中,这种抵触性的理论原本鲜见,而且大多是对诗的反动,比如形式主义诗风等),一旦有这类“理论”,世人便或兴师问罪,或将之诱到“正道”上来。例如,从“思无邪”开始,儒家竭力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试图把诗学改造成儒家政治的工具,但是,以钟嵘《诗品》为代表,那些试图从审美角度研究诗学的人们则强调诗的审美性,这两种理论互相争夺“市场”,但最终全都走向末路,前者经程朱理学的发展,完全堕落为理性说教,后者在明末清初演变为李东阳和前七子等只从诗歌的外在形式入手论诗的伪古典主义诗学。在这种情况下,王夫之应时而生,他把诗歌的功利性和审美性统一到一个整体中(传统的整体性观念!),一方面承认“兴观群怨,有取于诗”,另一方面,他也推崇“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11)],诗歌的功利性和审美性的矛盾在此得到虽是中庸之道的但却是和谐圆满的统一,诗论被引上了“正道”。
中国古代诗学一元性的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元论体系相适应并受之影响的。在古代哲学中,人们把“气”作为想象中的构成宇宙万物的原始基质,《管子》:“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列群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名为气。”《淮南子·天文训》:“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轻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四时之散精为万物。”气育万物的观念便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不否认“气”作为万物之“元”而存在,它们的区别是只在于一个认为“气”是客观存在的,另一个则认为“气”只存在于人的精神领域,是超客观的。
中国古代诗学蜕变式的历史发展形式和由此形成的一元性的理论体系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态在诗学领域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注释:
①谢榛《四溟诗话》卷三。
②袁枚《随园诗话》。
③方士庶《无庸庵随笔》。
④王夫之《诗广传》卷一。
⑤《礼记·曲礼》。
⑥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⑦严羽《沧浪诗话》。
⑧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
⑨《论语·为政第二》。
⑩《论语·八佾第二》。
(11)参见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