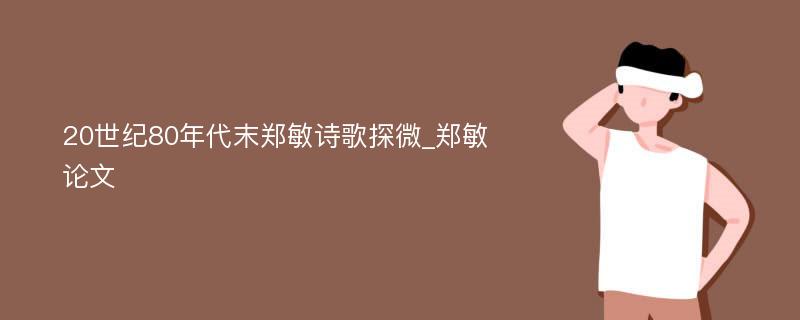
论八十年代后期郑敏诗歌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诗歌论文,郑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后期的郑敏诗歌,在诗歌内容和手法上都表现出与40年代很大不同,并显示出独特的品格。郑敏在诗歌手法上将西方存在主义、玄学和中国老庄、禅宗相结合,并对悟性、境界、意象等有关诗的创作方面提出自己独到见解。这一方面来自于诗人对诗歌的长期探索,而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诗人人生的一次契机。用诗人自己的话说:“1984年—1986年是我的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因为在这时期我找到了自己在新时期诗歌创作的新的艺术形式。”(注:郑敏:《诗歌自传(一)闷葫芦之旅》,《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481页。)
1984年后郑敏对美国二战后诗歌创新之处的研究,特别是“无意识”与创作关系的认识以及对西方解构理论的研究,使她的诗艺观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在诗歌中更加注意中国国画的“留白”效果,在意境中追求意外之意,象外之象;在思想内容上不仅关注生命存在的本质,更关心生命留下的痕迹以及不可见的无意识;在语言上,表现为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认可和接受,强调语言的不透明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一一对应性。
关于“无意识”,郑敏有着切身的体会:“1985年后我的诗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我在重访美国以后,受到那个国家的年轻的国民气质的启发,意识到自己的原始的生命力受到‘超我’(Super-ego)的过分压制,已逃到无意识里去,于是我开始和它联系、交谈。因为原始的生命力是丰富的创造源泉,这样我就写了《心象组诗》,我竭力避免理性逻辑的干扰,而让积淀在我的无意识中的力量自己活跃起来,形成图象和幻象出现在我的心象。它们形象地告诉我的思维和情感的状态。”(注:郑敏:《诗和生命》,《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420、422、423、425页。)
“无意识”赋予郑敏以激情和全新的感受,使诗人思维更敏锐。然而,诗人不只是关注“无意识”,而是要关注深埋在无意识中的人生记忆和过去的时光。于是对“无意识”的感受和思索,在郑敏诗歌中表现为对“不在之在”的描绘。“不在之在”是郑敏80年代后期思考的一个主要哲学命题。通过写“不在之在”,郑敏希望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在诗的文字方面能够洗去那种种别人或传统的调、色、声所遗留下的色迹,让每首诗有它自己所需要的颜色和光线”(注:郑敏:《诗和生命》,《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420、422、423、425页。)。这一境界要求诗人既要超越前人及同时期的诗人,又要超越自己。而要超越自己,就需要诗人无论从诗歌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有所创新。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研究,无疑为诗人审视世界、人生提供了新的哲学观和审美视野。郑敏在研究、剖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时,接受了他的踪迹说、歧义说、滑动的能指说和心灵书写说。并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德里达的解构转向“不在”而背弃“现在”。“现在”受本体——神学玄学的崇尚,被认为是神、永在、权威等不朽力量的表象,受到解构主义的批判。德里达认为只有纯“不在”——不仅此物彼物的不在,而是每一承认“现在”之物的不在——能启发我们,它能工作而后让人去工作。德里达认为纯粹的书必须是关于“无有”(nothing)的那本书。郑敏完全接受了德里达的“不在之在”理论,并将之纳入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中,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实践中去。
郑敏接受德里达的“不在之在”是有时代背景的。80年代末90代初,诗歌由“朦胧诗”的兴盛变成“新生代”诗歌的崛起。以韩东为代表的“新生代”应和着当时文坛的反传统、反崇高、反英雄的所谓市民文学、新历史小说等。它强调反文化、非文化,刻意取消诗意构成中的文化底蕴,削平意义结构的深层模式。从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的对比中就会看出诗风的重要变化。在杨炼笔下,大雁塔被赋予了浓重的历史感与人文色彩,它是民族命运的象征,是民族苦难历史的见证者:“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而韩东则全然不以为如此,他笔下的大雁塔就是一座平平常常的建筑物,没有什么更崇高的文化内涵,更没有救世者一样的人格力量:“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而于坚等人的诗则完全否定了英雄,取消了崇高,他诗歌的主体完全“是一群小人物,是一群凡人,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还酗酒,打架……”美学追求上的“反崇高”也使这批诗人远离了人文精神,他们不再对历史和文化意蕴进行探索。如“大学生派”宣称:“它们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与之相依的还有李亚伟为代表的“莽汉主义”,声言“捣乱、破坏以求炸毁封闭式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对神圣的破除和对审丑的刻意追求,而且还常以“反讽”的口气来表现,如李亚伟的《中文系》将以往涂满神圣肃穆的油彩的中文系写得如此浅俗戏谑:“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它刻意表现生活的平庸、烦扰和俗不可耐,除了表象、过程和孤立的琐碎之外,没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些描写显然都过于策略和极致化了,作为艺术作品,它们是缺少意义的。
总之,80年代末至90年代,文坛上众声喧哗,价值失范。尤其随着商业主义大潮突起,“精英”文化受挫,后现代主义开始消解知识分子中心话语,它以消解意义颠覆价值为乐趣,高举弑父、渎神、佯狂、游戏的旗帜,反抗文化、反抗传统,面对这股恶俗倾向,郑敏不断发表论文呼吁诗歌应该坚守传统,回归传统的同时,她很快建立了自己新的思想,即在40年代的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德里达及海德格尔的关于“不在之在”哲学思想,并将“不在之在”本质内涵化为自己的诗歌内容,运用到自己的诗歌语言中。郑敏诗歌由此找到了自己的诗意化表现内容和方式,并对90年代的诗歌商业化、恶俗化倾向进行了反驳,将被颠覆的价值重新颠覆过来,被否定的传统文化重新加以肯定,而在一片嘈杂的文化垃圾中,为我们呈现出一片宜人的绿荫,提供了一份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那么,到底什么是郑敏的“不在之在”?在诗歌中,它包括哪些内容?
存在是什么?存在是人的本质和意义,是人的诗意化存在状态。有人说,存在就是存在本身。这一循环论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表明存在本身不可以言说。因为存在不是任何实体性的或观念实体的东西。因而,当我们去思索存在时,就只能把握着实体物,而遗忘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存在不是摆在一个地方可以让人去认识的,它与人的关系不是认识关系,不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关系。因此,一旦人们提出要认识存在,存在已经不再存在。因而,郑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不在’是那种能产生丰富事物的真空和空虚,它是对萌发的许诺,是将诞生者的潜在,又是已退入过去时刻的消逝者的重访的可能性。”(注:郑敏:《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什么是“不在之在”呢?它是被遮蔽了的存在,是没有敞亮的存在。“不存在”与“存在”之间并不是一对矛盾关系而是限定关系,不存在是用来修饰存在的,揭示存在是一种无有状态的存在,它并不明显在场,但它是人存在的本质。正是“不在之在”使生命处于高蹈状态及诗意化的生活境界。然而,“不在之在”不是冥思苦想的产物,它需要用心去体验,在生活实践中把握它。
诗歌是对生活诗意化的表达,诗人的职责便是表达这种诗意化状态。关于这一点,里尔克作过精辟论述:“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赢弱的、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默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不可见’地苏生。我们就是不可见的东西的蜜蜂。我们无休止地采集不可见的东西之蜜,并把它贮藏在无形而巨大的金屋蜂里中。”(注: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附录之四,1939年德英对照本,第157页。)里尔克这段话启发我们:诗歌应该表达“不可见的”东西。这不可见的东西即“不在之在”,如何表达?只有拥抱大地,体验生活。并将“不在之在”——不可见的生活之蜜,写成具有感染力的诗。
“不在之在”虽然不可言说,但它其实已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只要用心去体验,就能感觉到它,它其实是曾经拥有的美好的情感,一段永生难忘的爱情,一个美好的理想,一支曾令人陶醉过的曲子,是一个人人性的光辉,它无时不在我们心中,我们的记忆深处,这份记忆使我成为我,而不是其他。也就是说,“不在之在”使我意识到我之为我的美妙——一种诗意化的生活在“不在之在”中得到确认。
郑敏的后期诗作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对“不在之在”的追寻变成了对生命、命运的体验。如,对生命之谜的困惑:“轻轻地擦过窗槛/当静夜在冬夜的灯下/提醒你一切存在都有声音/一张迟落的梧桐叶手掌/擦过夜的窗户带给你/不知如何解答的习题……是生命就有声音 但哪比得上/这一声 在死寂的深夜/神谧 诡秘 静谧 一个谜”(《叶落花落在深夜》);对人生之路的思索:“从那儿通向什么地方?/我寻找了一生,你们又陷入困顿/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一个路标,又一个路标/我们仍在摸索着走/也许智慧是跨过的树林/是山下的野果、水中的鱼”(《没有尽头的路》);对复杂多变命运的体验是:“那掠过万叶的鸟影/不知道是否消失/那凝伫不动的远峰/不知是否停留/在恍惚中行过险峰的双脚/并不知自己的存在/只看见云团的沸滚/意识到一种莫名的力量/超出了人世的悲欢。”(《夏日蝉声与禅语》)
从以上诗作可以看出,郑敏借用自己的感觉和体验,准确地将自己对生活之谜的思索表达出来,其目的是揭示生活、生命的本质,寻求并建构自己诗意化的生活。
而《梵高的画船不在了》、《两把空了的椅子》、《手和头、鹿特丹街心的无头塑像》,则是通过“不在了”、“空了”、“无头”这样一些语汇暗示“不在之在”具有的内涵和意义。如,《梵高的画船不在了》:“踉跄在北海的岸边/天上乌黑的云团滚动着/摘走浪峰/大风吹跑了所有的游人/从空了的咖啡廊看出去/只有/灰暗得发狂的海水/梵高的画船不在了/那令人难以入睡的/鲜艳的红色和蓝色/不在了。
“幸好有暴风雨/逐散晴天时的幻想与失望/梵高的画船,其实早已不在了,自从/人们踉跄在北海岸边/不再抱有对‘彼岸’的信念。/也许是白内障的发展/人们看不见那/不再存在的存在/但诗人斯特伦特说/‘不管在哪里,我总是/那遗失的部分。’”诗人借斯特伦斯的诗句:“不管在哪里/我总是那遗失的部分”,把被遮蔽的“不在了的存在”敞亮出来,启示人们去思考理想、彼岸问题。又如,《手和头,鹿特丹街心的无头塑像》:“头和手是罗盘和路标/在太阳耀斑的干扰下/头和手失落了自己/ 没有方向的逻辑/和没有逻辑的方向/同样可怕/虚伪的真理/用狡猾的路标指引行人/等待着的是陷阱和地狱/ 在这个世纪/太阳几次爆发耀斑/人们被指引向不只一个/布亨瓦德和煤气室/艺术家在鹿特丹的街心/留下一座没有头的人像/他的胸膛像海洋宽阔/迎接四方来的游人/ 没有头,也不伸出手/太阳的耀斑因此失去了魔力/这塑像只有人体的雄浑和强壮/还有自然赋予他的/不可干扰的生命之泉/艺术家用他的敏感/捕捉到那不存在后的存在。”
“无头塑像”这一触目惊心的艺术形象,是艺术家运用“他的敏感”,“捕捉到那不存在的存在”后才完成的。没有头也没有手,启示人们思索人类曾有过的那段失去理性和方向的疯狂岁月,从画和雕塑,郑敏看到了艺术的本质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启示。在于以少胜多。在诗中,“不在之在”已不仅指历史,而是指艺术本质以及彼岸、理想等东西。这样,诗人的诗思也一步步走向潜深。
怎样触摸“不在之在”?“踪迹”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中介,通过寻找、触摸、挖掘生命的踪迹,发现埋在意识之下的潜意识、欲望以及有关过去的记忆,使郑敏的诗歌中的“不在之在”变得色彩斑斓,异常丰富。
海德格尔严厉抨击语言工具论,将语言工具论所掩盖的语言多层次性开发出来,揭示了语言的既显现又遮蔽的二重性。而拉康受到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的启示,着力强调语言的被压制部分。到了德里达,他发挥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显现/遮蔽本质的论述,提出包括语言的在与不在的“踪迹”之说,以“书写”的沉默替补语言的声音在场性,大大丰富了语言本性的认识。这些都给予郑敏很大的启示。郑敏认为:“每部作品,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是性质十分庞杂的踪迹团,其中至少包括社会、时代的踪迹、审美的踪迹,以及其他文学作品投射给它的文字、隐喻等文本间的踪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注:郑敏:《两种文学史观:玄学的和解构的》,《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这一理论大大地拓展了郑敏诗歌的“不在之在”范围。郑敏的许多诗歌是对踪迹的直接描写。如:“林径的温暖掩盖了无数记忆/寂寞蜿蜒于无人的山谷/载着多少车痕轨迹/一条似有似无的道路。”(《生命之赐语言:我说》)“我总觉得在发黄的书页里/有诗人的声有哲人的呼吸/一息相通虽然不见/却也在冥冥之中感知。”(《夏日蝉声与禅语》),再一次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踪迹的理解。郑敏善于通过写各种自然界的踪迹,来还原“不在之在”的原生状态,从而印记生命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小至一片叶子,如:“叶子,自然的日记/一页页地飘落/人们不会遗忘/即使是两千年前的泥俑/也在阳光下重新驾车飞驰。/消逝的时间是地下水/又回到江河湖海/它们见过古人的喜怒/听过琵琶声,像落在玉盘里的珠子,/还有青松浓郁带来猿鸣/都在镜子似的江水上/印下了影子和声响。”(《秋的组曲,三落叶》)这首诗,揭示了生命虽然可以消亡,但踪迹还在,有关生命的记忆还在,生命本身的价值不会因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历史会永远记住它。大至关于死亡这样的哲学主题,如《在一个追悼会上》,人死了,诗人问他曾来过世界吗?世界能抹去他生命人的痕迹吗?不能。相片,暗示着他曾有的梦——理想及那个时代。死者与生者不同时,死者无法进入生者的物质世界——有信用卡和驾驶证的世界,但生者不会忘记他,正象哈姆雷特无法忘记老王。郑敏在这首诗中揭示了生命本身的存在便具有意义,既使人已死去,生命的价值仍然不能抹杀。
我们知道,弗洛依德是“无意识”的发现者,从弗洛依德到拉康再到德里达,有一条清晰的承传脉络:弗氏的“无意识”的幽暗、深邃被改造成德里达的“踪迹”的无形、浑然,德里达将“踪迹”看作语言在差异的运动中不断留下的印痕。差异或歧异(difference,一译延异)是德里达的另一重要术语,它们都显示了“在”的不在性或“不在”的在性。郑敏很好地结合了两者的观点,在诗歌中描绘踪迹时,不忘挖掘无意识存在的广大土壤。在捕捉踪迹时,她也打捞被淹没在意识海洋深处的无意识,因而对无意识的表达也成为郑敏诗歌“不在之在”的重要内容。如《海底的石像》意在告诉读者:海底的石像,是记忆深处的印象,打捞它才会打捞上生命的一点碎片,这碎片就是无意识。在《“它”》中诗人再一次对无意识进行了把握:记忆不易造型,对此时我来说这记忆是过去之我的描绘。虽时过景迁,但它不可忘记,所以它有时要回来,穿过时间黑洞,穿不透的铁甲,回到我现在的意识里,激活我现在的思想。
郑敏在诗歌中大量的写无意识,因为郑敏认为除了意识的理性之外,还有无意识,这个无意识之中,是混沌一片,没有逻辑性的,用诗的语言来说,又是一种不存在之存在。它是无形的,而且是不固定的,但它里边却积累了许多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身的文化沉淀、欲望沉淀,任何不属于我们的逻辑范围,逻辑所不能包括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因此,它可称得上是一个地下宝藏(注:郑敏:《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下)》,《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255页。)。
郑敏对无意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促使她越过无意识表面向更深处探索,她抓住了生命的本源——欲望,这一长期被压抑的生命本质。并在后期诗歌中,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如《渴望:一只雄狮》:“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得大大的嘴/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狮/它冲到大江的桥头/看着桥下的湍流/那静静渴过桥洞的轮船/它听见时代在吼叫/好象森林里象在吼叫/它回头看着我/又走回我身体的笼子里/那狮子的金毛像日光/那象的吼声像鼓鸣/开花样的活力回到我的体内/狮子带我去桥头/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
描写了欲望所具有的强大生命活力。而在《看不见的鲸鱼》中,对生命力的象征——欲望再一次进行礼赞:鲸鱼如同雄狮,是生命力的象征,是爱的象征,不可外求而求诸己。
无论是写踪迹,还是写无意识、欲望,郑敏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对“不在之在”的诗意表达,为了重新确立失范了的价值坐标,在一切被解构了的废墟上重新寻找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通过对“不在之在”的由浅而深的把握,在自己的诗歌世界中为诗化人生探索出路。从这一意义上讲,郑敏后期的诗歌着眼点是非常高的,她的诗歌在同时代诗人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那么,郑敏是如何发现“不在之在”的呢?
首先,从艺术手法上,郑敏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郑敏打开“不在之在”这扇神秘之门的钥匙。郑敏多次撰文阐释海德格尔的理论,她说:“海德格尔认为:在好的诗歌里,必然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东西存在,有这个东西存在,诗人自己才真正对语言及生命拥有自己的经验……。他要听的是什么呢?他要听的是那种无形的语言。”(注:郑敏:《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下)》,《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255页。)郑敏不仅多次写论文阐述海德格尔的语言观,而且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后期诗歌创作中,听语言,听无声的语言,寻找人的和自然的律动,郑敏从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得到启示,于是无声的语言,不仅变成了郑敏追求的诗美境界,而且也变成郑敏诗歌内容的一部分。郑敏80年代后期的许多诗歌就是表达对“无”的理解,其中也包括无声的语言。如《心象组诗十二·无声的话》写道:“无声的话,不是话/只是震波/聋了的耳朵/能听见它/一个天南/一个海北/背靠着背/目光瞧向/相反的方向/突然,那听不见的竖琴/琴弦颤动/所有的树叶都颤抖了/他们转过身来/听着树叶的信息/感谢自己是聋子”。这首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郑敏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阐释,这首诗对“无声语言”进行了生动地描述和形而上的思索。“听语言”,让语言自己去说。自己去说的语言主要包括这样两方面:心灵语言和潜意识语言。这两部分语言成为诗人后期诗歌挖掘的对象,构成了“不在之在”这一世界的主要内容,具体外化为对回忆、欲望、理想、此岸与彼岸关系问题、寂寞、死亡、偶然、命运等哲学命题的表达。
其次,境界也是帮助郑敏发现“不在之在”的手段之一,而且境界本身对于郑敏来说就是“不在之在”的一种具体表现。
郑敏对于境界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她认为:“境界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种渗透入文史哲的精神追求,它是伦理、美学、知识混合成的对生命的体验与评价,它是介乎宗教和哲学之间的一种精神追求,也许是中华民族的呼吸吧,既有形又无形……。”(注: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郑敏感觉“境界本身是非具象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能力,影响着诗篇。……境界是一种无形、无声充满了变的活力的精神状态和心态。它并不‘在场’于每首诗中,而是时时存在于诗人的心灵中,因此只是隐现于作品中。”(注:郑敏:《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什么》,《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358页。)
那么,如何打通诗与心灵之间的厚障?诗人认为,悟性和诗人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种虚怀若谷的境界就会使诗人有独到的领悟,也即所谓自己的语言经验。但这种‘功’是很难的修养,是文化至高的硕果,它要求诗人的创作冲动不是浮躁的,而是一种透彻的激动。这种难以言传的意之所以难以寻觅,因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它即在此又不在此’,……作者必须用他的悟性去发现他和语言间的一种诗的经验,也就是与语言对话……。”(注: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今天新诗创作和评论的需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最后,敏锐的感觉(注: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今天新诗创作和评论的需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尤其是对色彩、音乐、绘画作品、雕塑以及爱情、寂寞、痛苦等的感觉,也是郑敏体悟“不在之在”,体会虚无的重要手段。诗人早在40年代就表现出过人的细腻和敏锐,如《音乐》,表达音乐对人灵魂的浸润,写音乐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魅力。而《无题》则是诗人运用自己丰富的感觉来写记忆、情感这些“不在之在”。诗人写少男少女的爱情,是通过无声的语言传达出来的。
如果说郑敏40年代诗歌表现出运用感觉来传达“不在之在”所蕴含的信息只是与现代派诗歌艺术手法的运用所表现出的诗歌特征暗合的话,80年代后期,用感觉来发现、传达“不在之在”则是郑敏的有意为之。郑敏运用感觉来寻找“不在之在”,不仅拓展了诗歌内容,而且在哲学层面上使诗歌更具包容性和启示性。郑敏说:“我的第六感知在寻找影子/影子的世界,没有存在的存在。”(《心象组诗(之二)根》)甚至将感觉直接化为诗行:“记住的不是哪一片水/哪一丛树,哪一个落日/而是那化在无形中/不断释放震波的/一闪欢乐、美和幸福。”(《快乐·蓝色的诗》)感觉使诗人找到了心灵之门,寻找到“不在之在”。其实,许多大诗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感觉。如韩波认为:“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位,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注:韩波:《韩波的书信选·致保尔·德梅尼》,《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在我们看来,正是敏锐的感觉培育了郑敏丰富的灵魂,帮助郑敏走近“不在之在”这一神秘世界,并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空灵、玄远、朦胧的艺术世界。
“不在之在”的一大部分内容是被埋在潜意识里的,为了将潜意识这一“不在之在”表达出来,诗人采用了将潜意识意识化、形象化、感觉化的艺术手法。如《黑马》(唐三彩)。黑马是生命、文化、历史的象征,“我知道你的故乡就在我灵魂深处。”看到黑马,唤醒诗人黑色的记忆,使诗人想到充满生机的沙漠和中原。诗人将埋藏在潜意识的本质力量和黑色记忆借黑马的形态,以及与黑马有关的环境传达出来,使我们感到诗人潜意识所富含的信息和能量。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则是将潜意识形象化、感觉化、诗人借用第二人称“你”,将潜意识赋予人的形体和灵的神奇。将潜意识出没的神秘性及潜意识的美妙写得栩栩如生,诗人与潜意识的关系在诗中变成“我”与“你”的关系,以实写虚,由于诗人饱含激情,全诗充满宗教情绪,令人想到《圣经》中《雅歌》的许多篇什。不同的是《圣经》中的《雅歌》赞美的是全能的上帝;而郑敏歌颂的是潜意识。非常有趣的是郑敏这首《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与《阿尔丁顿的意象》非常相似。现在将它们的部分诗歌内容放在一起,郑敏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因此你神秘无边/你的美无穷/只像一缕幽香/渗透我的肺腑”……“虽然我们从未相见/我知道有一刹那/一种奇异的存在在我身边/我们的聚会是无声的缄默/然而山也不够巍峨/海也不够盈溢。”阿尔丁顿说:“象一只满载嫩绿芳香的果实的平底轻舟,/在威尼斯暗黑的运河上徐徐飘来,/你,噢美艳绝伦的人呵,/驶入我荒凉的城中。……风儿吹浇的花朵呵,/即刻又为雨水绽开;/同样,我的心为泪水绽开了,/一直等你回来。”从以上的诗句中看得出两位诗人几乎用了完全相同的艺术手法,塑造的是美仑美奂的艺术形象,两者的语调表达爱慕的方式也是一致的,我在这儿无意于比较孰胜孰劣,只是想说明一下,无论是《雅歌》还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还是《意象》都成功地运用“拟人化”将无形有形化、将虚实化。而且这种手法,尤其是用第二人称“你”作为主人公,这种方式其实更适用于写爱情诗,更便于传达诗人幽微的心曲,便于直接抒发自己强烈的情感,由于诗人深谙象征、隐喻的运用,因而能够将浪漫的感情写得既热烈又不失含蓄。
总之,“不在之在”是郑敏80年代后期诗歌的主要表达内容。郑敏80年代后期使用解构思维创作诗歌,即是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颠覆,也是对理性价值观念的质疑,又是对40年代诗歌创作的突破,更是对90年代价值失范的对抗,对“不在之在”的思考与表达标志着郑敏诗歌在哲学上的变化,而娴熟艺术手法的运用,与“不在之在”诗歌内容的完美结合,标志着诗人诗歌已走向成熟。郑敏的诗歌是哲学化的诗歌,由此,形成了诗人独有的诗美特色——朦胧之美。
标签:郑敏论文; 无意识论文; 德里达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诗歌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雅歌论文; 踪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