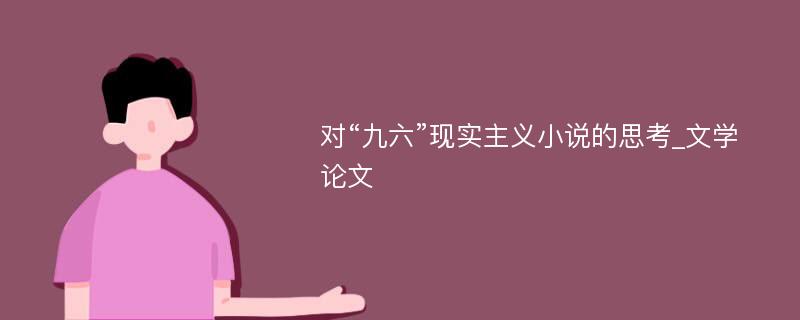
’96现实主义小说的回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吗?不,它是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
新时期文学与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关系历经了三个阶段,'96出现的现实主义新景观(即第三阶段)是水到渠成的文学选择,而非对前两阶段的“复妇”。
在过去一年的多样纷呈的文坛上,现实主义新浪潮可以称作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文学现象了。近几年来还不曾有过如此纷至沓来的中短篇及长篇小说,如此视野凝聚地关注浪涛汹涌的改革,佳作连袂,反响热烈,有人说这一浪潮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与 “复兴”,是现实主义“高潮”的到来。果真是这样吗?今天当我们对'96文学新现象回思的时候,充分肯定它的同时,不能不追问与探询这一现象究竟怎样发生的,它给当下文坛提供和带来了什么新特点,从文学的明天发展要求,又有哪些得与失。
如果说现实主义有一个“回归”和恢复期,我以为那是新时期伊始,针对“四人帮”制造的背离现实主义的瞒和骗的反动文艺。20年来,现实主义虽然浪波起伏,但在多元多样文学竞争中它处于主导或主流的位置。恢复的现实主义有着双重的使命:一是频仍回视,反思历史;一是直面现实,尤其关注改革开放,否则在“伤痕”“反思”潮流之后怎会涌现“改革文学”大潮呢。现实主义如果对它不仅仅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作为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我认为新时期文学与改革开放的现实关系,历经了三个主要阶段。先是以《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为标志的充满浪漫的阶段。80年代初期,改革初见成效与开放的社会气氛,给刚从“文革”阴影走出来的人们,点燃起希望与浪漫的情怀。认为只要像乔厂长那样锐意革新的官员“复出”或“上任”,“小康”仿佛一夜之间就会降临。这篇作品鼓舞效应是巨大的,乔厂长这一叫响的名字,曾唤出一大批“上任”小说,但它们并没有摆脱贤官良将、出山上任的传统模式。第二阶段社会心态由浪漫趋向务实。商潮冒出的光怪陆离现象令人困惑,新旧体制嬗变中暴露的腐败弊端与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泛起了重私利与实惠主义之风。它推使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文学疏淡社会,退回自我与回归家庭。新写实小说有其缺陷,但像《烦恼人生》、《风景》等原汁原味描述普通人怎样过日子的琐琐碎碎,与改革现实仍然存在或隐或显的联系。况且,方方、池莉后来的《一波三折》、《你以为你是谁》等小说,无不蕴藉着现实改革的辐射波。
第三阶段即'96出现的现实主义新景观,文学注视点由家庭又回到社会。这是不是否定之否定、文学又回到第一阶段了?题材虽然同属改革,但文学精神大为不同。将《大厂》的厂长吕建国与乔厂长二者形象稍加比较,你就会发现文学由浪漫色彩而求实求真、直面重重矛盾的社会现实了。'96现实主义的小说与其说它“回归”传统,不如说是前一阶段新写实的延伸与拓展。《分享艰难》、《九月还乡》、《大厂》、《穷人》、《扶贫》这些小说怎能纳入那种强调艺术典型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规范中去?那么多的人物有哪一个算得上典型形象?它的叙述特点一是不回避世俗性,一是其乐不疲地描述“原生态”的生存本相,这跟新写实特性何等相似。不过,历经10多年的改革,变革中的包括作家在内的多阶层人们在走向成熟,参与意识与使命感在增强,于是文学由小家庭小日子走向大社会大改革,勇于正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发生的艰难。因此,当文学与现实关系经历了第一、二阶段尔后跨入第三阶段,这恰恰是水到渠成的文学选择。现实主义“复归”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现实主义与历史时代、与社会心态思潮是一起流变的,它的表现方式与艺术特征,也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悄然而又明显地演化着。它承继着优秀的传统,但绝对不可能回归过去的原位,它在新写实、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多元多样竞争中,已是相撞互补的开放的现实主义了。
关注现实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题材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一条创作规律,关系着文学的生存和生命。文学与现实是互动的。
文学不能滞留于现实断面,要从历史的纵向上去把握当前,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关注凡俗人生。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不仅仅是“写什么”的题材层面上的问题,它关系着文学的生存与生命。如今有一种错觉,认为关注与贴近现实只是现实主义一种创作方法的要求。事实并非如此,现代主义与其它艺术派别也不是与现实隔离的。如存在主义作家保罗·萨特,他主张文学必须反映人生,干预生活,如他所言,“写作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情”。大名鼎鼎的现代派作家阿尔贝·加缪1957年给厄普萨拉大学讲演时说得明白:“没有现实,艺术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因此,文学“应当表达大家都明了的东西,表达我们大家都密切相关的现实。”而且他还警告文学家们,“一旦与自己的社会相隔绝,他就只能创作出形式主义或抽象的作品”。可以这样说,关注现实不是哪一种创作方法问题,而是关系着文学的命运,也是创作的一条规律。
'96现实主义新浪潮的文学现象,再一次向我们提醒这一规律的重要性。文学与现实二者当然是互动的,现实不是被动的描写对象,现实对文学拥有永恒的魅力。刘醒龙、谈歌、关仁山、周梅森等,他们的文学起步或起家,或热衷于先锋、或对通俗小说操作自如、或长于历史,但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改革这一现实焦点上聚拢起来。周梅森谈他创作长篇小说《人间正道》时,为什么写下《感谢生活》的标题,因它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改革开放对文学的馈赠与现实的巨大魅力。
然而,当文学凝视现实的时候,不能滞留于现实某一横断面或角隅之中,需要的却是历史眼光与纵深的把握。'96这批改革小说的得失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缺乏历史深度几乎是它带有普遍性的弱点。《分享艰难》应一分为二,一是这类作品不回避乃至意在揭示现实改革中所面临的重重艰难;一是对艰难的分享,从村民到村、镇长,从一厂之长到众多职工,无不苦熬苦想着如何分担一点艰难。阅读这类小说,对于那些心地善良的平民百姓和基层公仆,你怎能不为之感动与激动呢?可是当沉静下来作一点深层思考时,你就会发问,这“艰难”为什么会发生?是改革还是旧体制酿造的苦酒?要回答这一连串问号,文学就不能拘囿于一厂一村,不能不把现实的横断面与深远的历史相衔接,从当代中国(甚至更为古老的)历史的曲折道路中,才会深深认识到这场改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改变贫困落后的必由之路。这艰难是新旧体制转型期的“阵痛”,它不仅需要“分享”与心理承受,更需要深化的改革。还有的批评作品把现实生活写得琐琐碎碎,发不出工资、缺房、报不了医疗费以及男男女女的个人欲望等,太细碎了。我认为历史上的杰作并不拒绝琐碎细节,关键在于它是纯属私人化的琐屑,还是表现与大时代相联系的人之生存状态。说到底,一部作品的成败取决于历史意识,取决于从现实横剖面、从城乡各样人物、“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是否探掘出使其“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恩格斯语)。
丰富的生活积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思想深度。
探索新的价值理想,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项任务。
人物形象还要深入挖掘。
我们需要平民意识,但更需要高于生活的现代哲学意识。文学的突破从某种角度上讲,就在于哲学思想的突破。
当注意了现实的魅力和文学与现实紧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掉了思想,不能轻忽了作家思想深度对于艺术高度的特殊意义。对于'96表现改革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果说它缺少什么,我觉得缺少的不是生活不是艺术技能而是思想。有些作家拥有的生活及创作素材太丰富了,几乎不太注意或不大懂得吝惜生活材料。有些小说叙述的生活故事显得很拥挤,如果从中撷取一、二个人物和情节,足够营造另一篇小说了。艰难与分享主题的作品一时间联袂而至,说明多了一点相同的、流行的思想模式,少了一点独特的新鲜的思想智慧。的确,作家对生活没有深切的体验,不大可能写出好作品,但那些直感的、情感或情绪性的体验,仍然需要经过作家思想的感悟、咀嚼和透视,才会在创作中升华。
眼下小说在缺乏思想深度方面至少不能忽略了这样两点:其一,作品在接触新旧思想冲突与社会弊端时虽有一定的批判,但因缺乏思想深度而大大削弱了文学批判功能的力度,甚至那些无论道德还是法律都不能容忍的举动,一旦因了为村镇为企业为一个社区解救经济危机或别的不能免俗的缘由,也就变成可以理解可以通融以至可以赞许了;其二,作家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寻找新的观念和思想支撑点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又回到原有道德观和价值观,把它当作小说价值判断的底蕴了。面对转型期的种种艰难与沉重,文学固然承担着延伸传统,从怀旧与历史传统中汲取壮丽与豪情,但是不是还应注意从改革的现实和明天中探寻与时代相通的新的伦理、信念和新的思想支撑点呢?
从现实关系探索新的价值理想,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欣赏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女工小水在艰辛磨折中,曾有的“我是国营的”自豪感消失了,“合资”的梦想也破灭了。当然她也会得到伙伴们的“分享”与互救,但她凭自己双手走上了自救与自立的人生道路。我想,砸碎了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在日趋深化的改革进程中,《学习微笑》在参与和竞争中所把握的自立自救的人生价值理想,或许尤为可贵吧。
不少评论指出当下的改革小说缺乏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我觉得缺乏对特定人物心理性格的思想穿透力是主要的原因。如《分享艰难》的洪塔山和《大雪无乡》的潘老五,二者颇为近似,他们私欲澎涨、为所欲为的性格背后,蕴藏着历史与人性的内容,可惜小说未从思想深入把握使其形象显得简单化了。关仁山是一位有才华有创作潜力的年轻作家,善于敏锐捕捉生活初露的新东西。《九月还乡》是较早发现农民土地观念新变迁的一篇小说,仁山笔下的乡下女九月,由乡村而都市又回到了乡土,创办了新型的农场,这不仅是谋生所经历的圆圈,更是标志她重新找回一度失落的人生价值。潘老五这个人物也是作者的一个发现,这个乡镇企业主为什么那样颐指气使?小说已经注意并记下了他的一句话,“老子打下的天下”,可是作品却停住了追询,未能充分撕开他的灵魂。潘老五说的那句话,潜台词是说,天下应由“我”说了算。潘老五式的身影在今天生活中并不乏见,改革初期他们凭胆量“闯”办了企业,现在以“打天下”自居,霸气十足,那种小农经济孕育的守成守旧意识,在今天已是粗放型转向现代科学经营管理型的一种抵制力量。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成为艺术典型的人物,被仁山发现了,但又失之交臂。这一遗憾在别的小说中也不无存在,它要求对人物对生活的把握,文学亟需强化思想的深度与力度。
有的文章还谈到这一批小说的成功,在于作家的“平民意识”或“公民意识”。作家们对于改革大潮表现出执著的参与精神,与小说人物平等地、同命运地分享着艰难,这一切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动人之处。我想补充的是,作为“人学”与揭示人物灵魂的作家,不仅要具有一般公民意识,进入生活,还要超越,要把握时代的制高点,以思想的电击,穿透笔下人物和情节故事,才有可能出现震撼性的力作。即使呈现的是像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小的生活场景,作家腹内仍应是一个时代的整体;当审视时代整体的小小“邮票”时,需要平民意识,但更需要超越意识,从历史与时代中汲取精华,需要那凝结着经济、政治、文化和伦理为一体的现代哲学意识。常常听 到作家朋友说,如何突破自我,如何突破现有文学水平。我想,从特定意义说,文学的突破在于哲学思想的突破。'96现实主义新浪潮的现象,向我们提示,作家拥有了生活沃土与丰盛的艺术,再拥有跨越世纪与时代的思想,形而下与形而上如果高度完美地融合,且不说众所希冀的多出精品,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也不会十分遥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