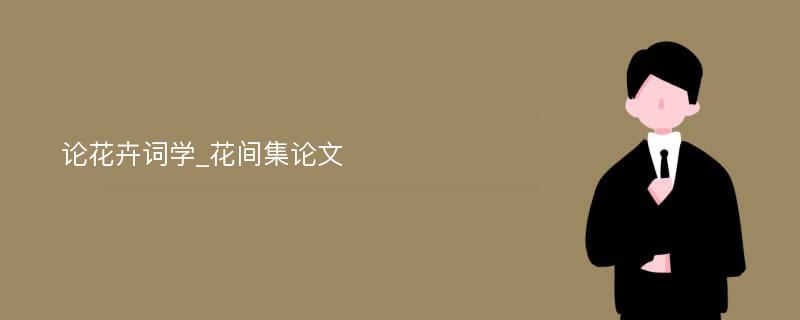
花间词派评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间词派评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374(2001)02-0228-06
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大文人词派。该派宗旨特出,风格迥异,自出现以来,即为世人瞩目和论家垂青,或褒或贬,迄今莫衷一是。然统而观之,要皆各言所好,各极其致,纵不无真知灼见,终未脱深刻的片面。有感于此,本文作者本着求是之心,不揣浅陋,期望在吸纳众说的基础上,权衡利弊,明是辨非,就该派之名称由来、创作旨趣、主导风格、以及历史功过等,依次略申一得之见。
一、花间词派不宜又名西蜀词派
在古今词学家眼里,花间词派得名于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乃不争之事,由于近乎定论,所以大都不深究其所以然,以至当今某些论家述及花间词派时,常常置定论于不顾,擅以“西蜀”二字取“花间”而代之,至谓“因后蜀赵崇祚收录始自温庭筠、终至李珣等18位词人的作品凡500首,编成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故又称西蜀词派为花间派”[1](第66页),造成不应有的名实不符、名称歧出现象。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正名,特于评辨花间词派之始,不惜小题大作,将其拈出而明辨之。
欲为流派定名,先须了解流派概念。古今文学理论家对文学流派之涵义多有界说,当代较具代表性的意见见于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谓“文学流派,就是一定历史时期里,在思想倾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上相近或相似的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派别。”名由实定,如果用这一界说检核花间词派之名实关系,可以说基本相符,并无明显抵牾之处。因为《花间集》所选录的温庭筠等18位作家都生活于晚唐五代这一“一定历史时期”,由《花间集序》揭示和《花间集》中作品显示的作家“思想倾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确乎“相近或相似”。又“花间”二字虽系方位词,极为平常,但作为一种符号工具、信息载体,用于日常生活和文学活动领域,常具有明、暗两重意蕴,“明”指的是与花这一自然现象相关的空间环境,“暗”指的是与美貌女性有关的人事环境,后一重意蕴与花间词派的创作实际正相吻合。从《花间集序》可得而知,所谓“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其创作取向取的正是与男女有关之情事。又所谓“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南国蝉娟,休唱莲舟之引”,其功用价值的实现也与女性密切相关,即离不开歌妓的有效配合。撇开《花间集》不谈,就是把目光转向《花间集》所辑录的500首作品,也足以找到相吻合的证据,因为其中近4/5的作品皆以与男女情事相关的生活为题材。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归根结底应取决于它特有的风格,“花间”二字至多只是花间词派风格特征的提示而非其特有风格的准确概括。不过遗憾的是,花间词派的特有风格迄今尚在探讨待定之中,故在最后定论未作出之前,作为权宜之计,仍当以《花间集》的“花间”二字为其定名,而不宜随意易以它名或使其兼有如“西蜀”这一不实之名。
花间词派其所以被称为或兼称为“西蜀词派”,其缘由大抵因于《花间集》所录18位作家有14位系生于蜀或仕于蜀的蜀地作家。然其说看似能成立,实乃似是而非,其所以为非,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文学史上以地域命名流派的例子虽非少见,如明之公安派、竟陵派,清之桐城派、常州词派等,但有一条不成文的定律,即用以命名的地域名皆系流派之开创者并对流派风格之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者的出生地名,而花间词派的实际开创者并对花间词风之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者的温庭筠却生活未及于五代,既非蜀地人又从未仕于蜀。二是五代期间,蜀地能词且风格与花间词风相类的作家并不止于已入录《花间集》的十四位,如还有前蜀国主王衍、后蜀国主孟旭,以及据考为《花间集序》作者欧阳炯的妹妹欧阳彬等。三是以“西蜀”二字为名,至多只能指明其地是晚唐五代时期词家较多、创作较为活跃的一个地区,或示意其地聚有许多词家,词家相互间交往沟通,易于形成某种词风而已,于流派本质特征之揭示,了不相涉。据此,“花间”与“西蜀”是否能轻易相互取代,两者之间是否能随意划等号,其答案不难自知。
二、花间词派的创作纲领见于《花间集序》
文学流派的形成大抵有自发、自觉两种形式,自觉形式大都有共同的纲领、组织、名称、以及若干关系较为密切的固定成员,且多自我标榜,互相鼓吹。自发形式则既没有共同的纲领、组织、名称、若干关系较为密切的固定成员,也没有标榜和鼓吹行为,所有的只是在同一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于不自觉意识状态下所形成的一种相近或类似的创作倾向、创作风格,由后人发现、界定和命名。这两种形式既出自文学理论家的一般归纳概括,也基本符合流派现象产生的客观实际。如果用这两种形式衡量花间词派这一流派现象,不免让人咄咄称怪,因为两种形式与它的实际形成形式好像都有一点相符,又都不完全是。其实,说怪也不怪,殊不知一般中时见个别,普遍中偶有特殊,花间词派的形成只不过例属个别,所取的是自觉形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形式。其特殊乃特殊在,它是有纲领的,只是它的纲领并非明扬于流派形成之前,而是形成于流派形成过程之中,先以感性经验形式,借时尚作中介规范流派成员的具体创作,最后升华为理性观念,较完整地宣示于流派既成之后为流派成员的创作总集《花间集》所撰写的序文中。它也曾自我标榜过的,只是为现存资料所限,无法知其详,可依为凭据的资料,仅止于《花间集序》而已。有此两点,如果不囿于惯例,《花间集序》所言种种,实质上就是花间词派的创作纲领。
花间词派的创作纲领见于《花间集序》,是可以通过《花间集》的体例辨析和《花间集序》中有关文字的解析予以证明的。众所公认,《花间集》是一部晚唐五代文人词总集,但忽视了一点,《花间集》在体例上貌似总集,实系选集。总集和选集体例不同,后者显示的目的性、倾向性远较前者大而显著。在体例观念上,总集乃相对于别集而非相对于全集而言,相对于全集而言的是选集。在客观形式表现上,总集由多家作品合编而成,重在量之大,并不一定求其全;选集所选作品则既可限于一家,亦可博取多家,重在质之精,但不一定求其多。衡诸事实,《花间集》乃十八位词家作品之合编,当然非某一词家作品之别集。而将《花间集》和今人张璋、黄畬所编《全唐五代词》稍作比较,不难发现其所辑录的十八位词家之作品多非词家作品之全部,当然也非尽收晚唐五代西蜀词家作品之全集。既非别集又非全集,便只能是总集或选集。如果再看看《花间集序》所透露的《花间集》编辑情形:“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乃命之为《花间集》。”华钟彦《花间集注》注云:“拾翠,犹寻芳也。《洛神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即其例。此指选集新词而言。羽毛之异,谓佳作也。梁元帝《怀旧赋》云:‘长安郡公,为其延誉,扶风长者,刷其毛。’是其例。……机杼,指织绩,引申为编辑。”由《花间集序》所言和华钟彦所注可知,《花间集》之成书有一个先选后编过程,既经先选后编,其系选集而非总集自属无疑。《花间集》的选集性质既明,则凡选集必依一定选辑标准编辑而成,选家的选辑标准和作家的创作准则本难一致,但由于花间词派的形成方式特殊,《花间集》所依选辑标准和花间词派所依创作准则不但理应相通,甚至可能完全相合。创作准则属于创作纲领范畴,因为一派的创作纲领无非由一系列有关该派创作性质、目标、价值的指导性、规范性意见所构成,今《花间集》的选辑标准已具见于《花间集序》,依理类推,内容包括花间词派一系列创作准则的创作纲领亦必具见于《花间集序》。既然如此,为了证实,同时也为了论述方便,兹将《花间集序》全文展示于下: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减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含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慰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绢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以阳春之甲,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序。
序为花间词派成员之一的欧阳炯应编选者赵崇祚之请所撰。全文约分三段:自起句至“用助娇娆之态”为第一段,围绕词之体性集中述说词之观念。“自南朝之宫体”至“无愧前人”为第二段,侧重谈词之一体的远渊近承,于所渊承对象有褒有贬,复于褒贬之际杂以自我标榜。“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下为第三段,主要交待《花间集》之由来,兼及所录词之类属及功用价值。文中就词的性能界定和创作要求要而言之有四:一,词应有美的形式,即“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二,词应为应歌合乐、娱宾佐欢而作,即“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用助娇娆之态”,“用资羽盖之欢”。三,作词应以“宫体”、“倡风”为鉴戒,要言而有“文”,秀而有“实”,即“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四,作词应以李白、温庭筠为典范,与之媲美,即“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四点易言之,即词要有美的形式,也要有与之相称的内容;词系音乐文学,首先须重音乐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文学性;词应把实用价值、娱乐功能放在第一位,教化功能可置而不同;词家对前人的创作示范应有所选剔,能追蹑的须追蹑,应避弃的须避弃。其所言各点虽未深入具体展开,但系有关创作的指导性、规范性意见,概属创作准则则无异,作为创作纲领的必具条件已备具。此外,文中还特别指出其所言各点既系“粗预知音”者的夫子自道,又系“广会众宾,时延佳论”,集思广益之所出,即既具代表性,又具权威性。由此更可看出,推断《花间集序》所言种种实质上就是花间词派的创作纲领,完全成立,花间词派的创作纲领确然见于《花间集序》。
三、花间词派的主导风格是柔靡绮丽
在评辨完花间词派的创作纲领之后,接下来再评辨其创作风格。因为一个流派的创作纲领对其创作风格的形成通常具有直接和重大影响,纲领的价值意义最终须通过流派的具体创作实践获得实现,而一个流派在一定的纲领的指导和规范下进行创作,通常富有创作个性,个性特色最终须通过风格予以展现,是以继评辨花间词派创作纲领之后紧接着评辨其创作风格,不仅合理,而且必需。
一般说来,所谓风格,无论作家风格还是流派风格,都是创作个性的具体表现。具体地说,都是个性在其作品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有机统一中的一贯表现。流派风格不同于作家风格之处,仅在于它是一定历史时期里艺术倾向、创作风格相近或相似的若干作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倾向和风格,系建立于作家风格基础之上。因此,凡风格都具有独创性,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是独特的一个。既然如此,花间词派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人词派,是否有其独特风格?如果有,如何予以界定和描述?两问中的前一问,词学界的答案基本上一致,都是肯定性的。后一问的答案则因人因时而异,迄未取得一致。这里就从介绍、归纳现当代居于多数一派词学家的意见入手,结合花间词派的创作实际予以评析,同时参照少数一派的不同意见,融其所长,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答案。
现当代词学界居于多数一派词学家的意见是把花间词派的风格归于阴柔一类,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如廖仲安《花间词派选集·简谈诗歌流派(代序言)》:“词,又名曲子词,唐代初起于民间,……风格有刚有柔,曲调有短有长。但晚唐时流入温庭筠、韦庄等文人手中之后,遂成为供给贵族们花间尊前娱宾遣兴之用的作品,以温柔婉约为主要的风格。”华钟彦《花间集注·前言》:“《花间集》收词五百首,多咏女子生活与男女相思情事。所选十八家,……显然是以气类相引,遂构成以柔靡婉丽为主要风格的花间派。”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词派》:“宋人奉《花间集》为词的鼻祖,作词固多以《花间》为宗,论词亦常以《花间》为准。花间词婉丽绮靡的作风,因此也就成了词的传统风格,对后世词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蒋伯潜、蒋祖怡《词曲·词的初创期》:“唐五代词的风格可以说是富丽的、温柔的,‘吟风弄月’四字足以尽之,因此便有《花间》一派。”这些论述有关花间词派风格描述的具体用语虽不尽相同,字里行间的语气虽不尽一致,但小异中有大同,即不仅俱将其风格类型归于阴柔一类,而且在其具体特征的界定上有惊人的相似,即:一,“柔”;二,“丽”;三,“婉”;四,“靡”。这些具体特征的界定其所以不约而同地出诸不同的词学名家之手,是因为皆系从同一文本即《花间集》中作品的风貌抽象概括而来,且不同程度地符合花间词派的创作实际。例如所谓“柔”,无非指花间词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花间集》有近五分之四的作品写男女情事,不是聚合之欢,就是离散之恨。又如所谓“丽”,无非指花间词措词华丽,设色富丽,这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花间集》至少有过半数的作品具有这一语言特征。再如所谓“婉”,无非指花间词抒情手法委婉,意蕴含蓄深长,这一点只符合部分事实,因为《花间集》颇有意既不藏,情亦毕露的浅率冲动之作。最后如所谓“靡”,无非谓花间词词藻太丽,情欲太浓,以致给人以郁而难解、靡而难立之感,这一点倒基本符合实际,因为《花间集》中的作品大都有一点唯情、唯美倾向。通过以上介绍评析,不难看出,现当代诸多词学名家有关间词派风格特征的界定和描述,由于大部分与实际相符,确有其合理性,值得肯定和借鉴。但同时由于不尽与实际相符,尚有不确不实之处,合理性不甚充分,尚有待更正与完善。就以不确不实而言,除了“婉”的特征与实际不完全相符,还有两点事实受到忽视。一、《花间集》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作品未以男女情事为题,据何尊沛《论“花间词”的题材类型》一文统计,其题材类型多达20余种,已远远超出男女情事的狭窄题材。二、《花间集》中不乏语言清新朴实之作,亦有不止一位风格较清丽的作家,如韦庄、李珣、孙光宪其人其作。唯其如此,早在清代,词家兼词论家张惠言即为之慨叹:“词之杂流,由是作矣。”(《词选序》)其后,李冰若因之论析:“花间词十八家,约可分三派:镂金错彩,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一派也。清绮丽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者,兼书感兴者,端已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也。”(《栩庄漫记》)近20年,亦有论家以之为据,于多数名家的共识之外,别申异议。看来,如何准确界定和描述花间词派的风格,确是当今词学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说难不难,只要平心静气,以创作实际为依据,以有关流派的合理定义为尺度,稍事借鉴和思考,要解决这一问题并非不易。具体办法是,不妨先借鉴李冰若和现当代多数词学名家之所论,再结合实际,用流派尺度加以衡量,其结论自必趋于确切,去客观真实不会太远。
现当代诸多词学名家既已认定花间词派的风格特征具体有四,不妨留其三,换其一,即换“婉”为“绮”,因为“绮”有精美之意,较“婉”更符合花间词派的创作实际。李冰若既析定花间词派约可分为三派,不妨易“派”为“体”,视花间词派系由三类风格相近又相异的作家所组成,因为“体”本有风格含义,多指某一家之风格。这种融汇变通所得的“柔靡绮丽”是否不符花间词派的创作实际、有违流派的合理定义呢?否。理由和事实根据是:流派本由一定时期思想倾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相近或相似的作家所形成,其风格建立于成员的创作风格基础之上,故无论流派还是流派风格,都是一种多样统一体,大同中有小异,本不排斥一派中有多体,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多体间的关系既非对立,亦非对等,而是有主有次,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即为流派的主导风格。用“柔靡绮丽”四字界定和描述花间词派的风格,所界定描述的是其主导风格即在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体,柔靡偏指其内容倾向尤其是题材倾向,绮丽偏指其艺术特征尤其是语言风格,四字合而言之,则兼括其价值与功能取向,而这样的界定、描述和花间词派的创作实际,应该是相当吻合的,因为有关花间词派的创作实际,已于前文多处加以揭示。据此,可以说花间词派的主导风格即以温庭筠一体为代表的风格乃是柔靡绮丽,因为温向有“花间鼻祖”之称。
四、花间词派创立“艳科”传统功大于过
最后简要谈谈词的“艳科”传统及花间词派创立这一传统的历史功过。词的“艳科”概念始自宋人,据今人谢桃坊《词为艳科辨》考索,最早见于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六:“《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闻其歌使人怅慨,良不与艳辞同科。”而作为词的一种创作风貌的理论概括,则出自现代学者胡云翼的《宋词研究》:“我们看宋朝的时代背景,是不是适宜于词的发达呢?……既是国家平靖,人民自竞趋于享乐,词为艳科,故遭时尚。”至于成为一种为人宗奉的文人词之创作传统,则创自花间词派,因为《花间集》被宋人尊为“倚声填词之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谓“艳”,许慎《说文解字》云:“好而长也。从丰,丰,大也, 盍声。《春秋传》曰:‘美而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小雅》毛传曰:‘美色曰艳。’《方言》:‘艳,美也。宋卫晋郑之间曰艳,美色为艳。’按今人则训美好而已,许必云‘好而长’者,为其从丰也。丰,大也,大与长义通。《左传》言‘美而艳’,此艳进于美之义,人固有美而不丰满者也。毛传及《方言》皆浑言之也”本义系指女性既好且长,既美且丰,非一般之美,乃特出之美。唯其如此,汉魏以后,或引申指美女,如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或借以指歌曲,如左思《吴都赋》:“荆艳楚舞。”李善注:“艳,楚歌也。”或用作修饰词,指情歌或婚外恋情,如萧衍《子夜歌》:“朱口发艳歌。”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以“艳情”为题。无论怎样引申和借用,皆指一种与女性相关且不无感官刺激性的享乐之美。而所谓“科”,人品类之义,与“艳”合成一词,义为写美显美一类。“艳科”一词的基本含义既明,再观照文人词的创作实际,则不难发现,词史上最先表现出这一特色,且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最先符合这一含义的创作群体,只能是以《花间集》而得名的花间词派,因为《花间集》中的五百首词大都以艳语写艳情,不是堆红砌绿,满纸华词丽句,就是摆阔炫富,通篇珠光宝气。不是情、色杂糅,体、貌毕陈,情挑性逗兼而有之,如常被论家引证的欧阳炯[浣溪沙]“相见休言有泪珠”,就是食色本性、淹没理智,或豁出去了,赌一把,或自我麻醉,颓唐自甘,如韦庄的[思帝乡]“春日游”和[菩萨蛮]“劝君今夜须沉醉”,即使写的不是艳情,也少不了艳语,如鹿虔扆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即使不用艳语,也脱不开艳情,如李珣的[南乡子]“相见处”。总之,艳语艳情要么两般兼有,要么至少有其一,这就是花间词派所创立的“艳科”传统。
“艳科”传统既为花间词派所创,由于其内涵与诗歌固有的“言志”、“缘情”传统迥然有别,有违“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礼教,创立后不久,有关其功过是非之争即接踵而来,开始尚有褒有贬,嗣经豪放词派以成效卓著的创作实践予以有力反拨,声名遂一落千丈。自宋以后,虽时有论家从艺术角度肯定其价值,但从社会学、道德学角度立论的论家大都认为其过大于功,甚至认为只有负面价值,毫无正面价值。黑格尔有一段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2](第43页)汤因比曾断言:“在文明的起源中, 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3](第95页)如果结合黑格尔和汤因比这两段论断,观照花间词派创立“艳科”传统这一文学史上的颇不寻常现象,可以看出,看似不寻常,实系寻常,因为作为一种现实现象,它有充分的合理性即必然性,其充分的合理性乃在于:它既是晚唐五代国家崩裂、战乱频仍、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乃至醉生梦死、追欢逐欲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必然反映物,又是中国古代文学依持“言志”、“载道”创作准则向前推进,虽迎来盛唐的诗歌繁荣、中唐的古文复兴,但盛而后衰,必趋变异这一内在发展规律的必然派生物,更是随着城市经济畸形繁荣、市民阶层悄然崛起,以儒雅为宗旨的传统士大夫文化开始向以艳俗为宗旨的市民文化演变这一文化转型期的必然产生物,而人的生存意志和文学的创新天职决定了人对现实环境的巨大挑战作出有力应战,具体应战形式势必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叛逆传统的方式向根深蒂固已有千余年之久的文学传统提出挑战,这种既应战又挑战的具体成果,就是花间词派的出现和经由其手的“艳科”传统的创立。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由不完美到完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艳科”作为一种初生之物,自难避免不完美和不完善,如情、色不分,志为情掩,过分重视娱乐与享受等,但它开拓了创作领域,把创作引向开掘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深层世界,凸现了文学固有三大功能之一的娱乐功能,从而示意文学功能应趋于全面,于诗歌创作传统之外另树立新的创作传统,以示诗、词有别,供后来的诗人词家比较鉴别,推动诗词是词的创作全面发展,向新的阶段迈进。功过相较,花间词派创立“艳科”传统之举,实属功大于过。
收稿日期:2000-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