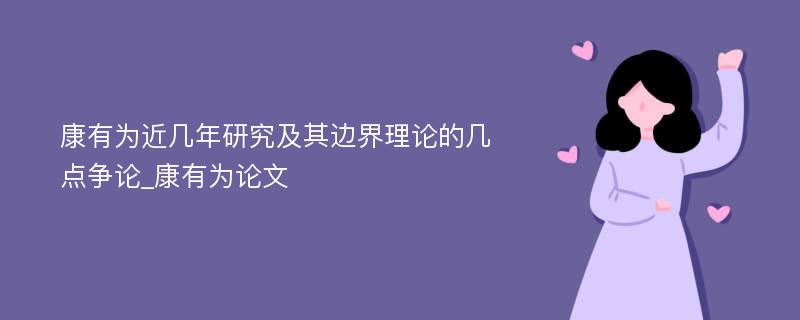
近年来关于康有为研究的一些论争及其界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界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7-0064-04
康有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目前关于康有为的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真实性、“衣带诏”问题以及康有为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基本的梳理。
一、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相关问题
学界的研究似乎总避不开康有为的作伪问题。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因袭著名今文经学家廖平的代表作《辟刘篇》和《知圣篇》;《大同书》的成书时间是否有假等①。近年来,曾被人们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重要史料的《康南海自订年谱》,也由于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有不同的名称,最初名为《我史》,1931年顾颉刚抄本时使用《康南海自编年谱》的名称,赵丰田先生1936年发表《康长素先生年谱稿》,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才根据赵丰田所藏抄本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后,取名《康有为自编年谱》。1996年,朱维铮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刊载时恢复《我史》之名,并在括号中注明《康有为自编年谱》。
长期以来,《我史》是研究戊戌变法与康有为的必备资料。但是,近年来学界对该年谱文本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些质疑集中在成书时间和具体内容方面。
《我史》成书于何时?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其主要依据是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有学者指出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没有疑问,是可靠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年谱的定稿时间似乎不能看成是1899年初。毕竟,年谱在康氏生前从未刊印,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揆诸以上情形,可知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不断的修订。期间到底有过多少次增删、修改,现在无法得出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1899年以后康氏年谱依然处在不断修订中[1]。那么《我史》到底成书于何时,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岁暮”,地点是东京的“早稻田”。对于这一说法,茅海建先生认为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从手稿本来看,康后来对《我史》有不小的修改和添加,大体改到光绪十八年,康已将手稿本分为五卷;康在手稿本有五处修改之贴条;据此似可以认为,康有为晚年打算较大规模地修改《我史》,并准备出版,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由此茅海建先生进一步指出这“很可能意味着他打算进行诸如《戊戌奏稿》一般的再造”。事实上关于《我史》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增删修改问题,在此之前就是学界至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如著名学者朱维铮先生就指出康氏对年谱原文有“点窜”,所以有些内容并非是《我史》原文。如此,有些学者明确指出:我们在研究戊戌变法及康有为时,对于康有为的著作及其谈话,应仔细审核其内容,不可盲目轻信。
应该说,对于《我史》的作伪问题,目前基本上没有分歧,学界基本认同康有为对此做过删改,特别是茅海建先生通过对康有为的“手稿本”修改手迹的辨认,发现《我史》已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那么经删改过的年谱是否具有可靠性?对此,茅海建指出:“康在《我史》中所记录的事件是大体可靠的,其之所以为不可信,在于他用了张扬的语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当时朝廷高官之上。”基于此,“康在《我史》中作伪次数还不是很多,似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的结论:《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2](p.14)
综上可见,《我史》的确是康有为出于自身的癫狂性情而作了一些删改。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小心使用研究资料,不能单纯依赖康有为的这一文本进行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它自身的史料价值。与此同时,对于康有为删改《我史》的做法,我们似乎也没必要从道德上过于苛责,对处在当时历史情景下的康有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应给予理解。
二、关于康有为“衣带诏”问题
所谓衣带诏,就是藏在衣带间的秘密诏书。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衣带诏之事。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流亡日本之际,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其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报纸上发表过。然而这一事件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特别是康有为是否篡改过密诏,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曾相继颁发两道密诏,按照康有为所记载的密诏内容如下。
第一道密诏的内容: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缪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第二道密诏的内容:
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熟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
针对上述两道密诏的内容,在当时就有人提出怀疑。后来在学界也多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汤志钧先生、台湾黄彰健等学者都提出了康伪造密诏的看法。那么到底如何看待此事?尽管目前还不能非常清楚地对此作出说明,但是根据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基本可以厘清此中头绪。
首先,康有为所披露的密诏,并非原件,而是根据其回忆所做。现在流传的密诏基本上是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第九卷中收录的,而这一件则是依据杨锐之子杨庆昶于宣统元年向督察院呈交的那份而成。
其次,对比康有为与杨庆昶所呈交的密诏内容,二者有明显不同。那么到底哪份较为真实呢?学者们经过考证指出,当初在戊戌变法中较活跃的王照曾经亲眼见过密诏;与此同时,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也记录了光绪皇帝的密诏。将王照与袁世凯提供的密诏内容相对照,内容基本上吻合,但是却与康有为所披露的密诏明显不同。1910年,陈宝琛等人也曾提议宣布杨庆昶所呈交的诏书是真实的,由此可以推断康有为公布的是伪诏。
那么,康有为主要做了哪些修改呢?杨庆昶提供的密诏内容,其中有“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这里的“尔”应该是指杨锐,而康有为公布的则将其改为“汝可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这里的“汝”明显是指康有为;另外杨庆昶提供的诏书里“可有何良策”,在康有为那里则改为“设法相救”。看来经康有为改过的密诏内容与原来之意并不完全相符。对于第二道密诏,由于是写给康有为的,个中情形似乎并不好核对。但是有学者指出其中两句话令人生疑,一为“出外国求救”,二为“共建大业”,其中前一句并不符合光绪皇帝发诏的环境,光绪帝让他出外是去上海,而不是去海外,后一句并不符合皇帝对臣下的口气[3]。事实上,如果再将此与康有为所说的“奉诏求救”相联系,恐怕就更能说明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康有为所公布的密诏,的确是经过改编之后而发布的,它与原来的密诏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明显的“自述”痕迹。也正是如此,康有为所公布的密诏,从一开始就遭到人们的质疑,及至后来在海外“奉诏求救”,也由于人们的不信任而收效甚微。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康有为改编的密诏呢?
应该说尽管康有为更改过密诏,使其与原来的意思并不完全相符,但是并没有改变实质内容。比如原诏中虽然没有康有为的名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其中的“诸同志”,应该包括康有为,甚至首先应该就是康有为。另外,康有为所提到的“设法相救”,尽管在原诏中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其中确有这个意思;对于“出外相救”,康有为认为是“出外国相救”,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他海外活动的一种需要。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待密诏问题,我们就该更平心静气一些。
三、关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的历史细节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人们对康有为的认识也更加明朗化。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康有为历史地位的认识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一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因此,关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问题,也就成为近年人们关注度较高的一个话题。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实际上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人将康视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也有人,如梁鼎芬否认这一说法,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似乎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挖掘,特别是康有为在一些问题上态度和做法的清晰,人们对康有为的领袖地位提出了质疑。故此有学者指出,戊戌时期的康有为并非处于中心地位,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其职位之微、权力之薄,即便是当初的梁启超也讥为“可笑之至”。而且康有为在上书期间,并非是康一个人,此时的“康”更多的时候体现的是一个集合名词,是“康党”,所以认定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则过于褊狭[4]。更有学者指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基础《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实际上除了康门弟子和少数人之外,几乎受到所有新旧派人士的反对,仅就这一点就不能将康认为是中心人物,而且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所依赖的也并非是康有为的理论,而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于康有为本身而言,也难当此重任。此外尽管康有为的学问根基依然是传统儒学,但由于他的自命不凡,所以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他的学术地位与声望都不能胜任学界领袖的重任,也难得士林的认可,所以康有为绝非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5]。更有甚者,有人针对康有为篡改自己的著述与密诏,指出康有为乃诓骗之徒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变法维新不仅仅是康有为等人的基本主张,更是一种社会思潮,除主张变法的康梁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思潮,只是康梁上书及变法的声势更大而已。
当然,也有不少人主张康处于变法的核心地位。有学者指出,判断康有为是不是变法的核心,主要是看变法过程中光绪帝是否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和主张。实际上,在变法过程中,从开制度局、懋勤殿到设立议政机构这些变法内容都是由康有为提出来的,康有为自然是变法的核心人物。
也有人另辟蹊径,指出,判断康有为的领袖地位与角色,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层面的角度来认知,更应该从康在思想启蒙和社会革新的影响上来认知。在社会革新方面,康有为发出首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政治斗争方面,康利用媒体舆论,影响国内政治,这些都在造就康有为维新领袖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作用[6]。
到底该如何面对上述争论呢?我想,恐怕还是要基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康有为,也就是说,如果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来看康有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认可戊戌变法在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而只要认可戊戌变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所颁布的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我们也很难绕过康有为这样的人物。尽管从康有为本身的个性特征来讲,有着不为人所认可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从政治斗争的策略上来讲,我们也应该给予一定的理解与认可。
四、结语
毋庸讳言,康有为作为一个身处社会剧变中的历史人物,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他的性格与性情,最为人们所诟病,有人认为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大正派,近乎骗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康氏所处的实际环境。当初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西方所独具的“市民社会”,知识分子可资利用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少得可怜,这样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不可能对现实政治生活展开公众意义上的讨论。康有为能利用的社会资源和思想资源“先天不足”,再加上没有足够的时间体验“现代”生活,形成这种性格是难以避免的。另外从总体上来说,康有为似乎并不能完全定位为一个政治家,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才这样说,而是因为康氏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充其量也只是书生论政,并没有多少政治经验可言,而且也毫无运用政治的章法。康有为在各个领域里的主要活动是爱国、改革、进步的,所以无论如何也应该将其看做是一位想急切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爱国改革者。
总之,作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康有为生活的时代距今已逾百年,但如果盖棺论定,康无疑应该是近代中国极可陈述的思想家和活动家。
注释:
①关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否“剽窃”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尽管目前仍有争论,但是个中情形显然还存在着诸多疑点,因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都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说明。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创造其理论体系时,固然不可因袭旧说,但是借助前人积累的资料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实在是必不可少。因此至少从目前来看,认定康有为是“剽窃”廖平的学术这一结论还不太成熟。另外,关于《大同书》的成书时间问题,由于20世纪80年代,相继在上海与天津发现了康有为亲笔《大同书》手稿,基本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始于1884年,完成于1903年。可以说至此以后,有关康有为《大同书》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