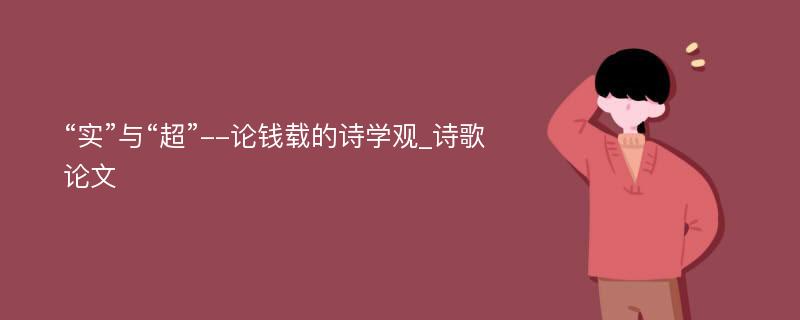
“实”与“超”——论钱载的诗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论钱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8)04-0028-05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石,又号瓠尊,晚称万松居士。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曾视学山东,典武会试,屡主乡试,多次为会试同考官、殿试读卷官等,累官至礼部左侍郎。诗文词画兼善,著有《萚石斋文集》二十六卷(末卷为《万松居士词》),《萚石斋诗集》五十卷。诗集有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和光绪四年重刻本等。
以诗而言,作为秀水诗派的代表人物,道咸等时期宋诗派的“先驱”[1]573,钱载不愧名家,甚或可称与其同时的袁枚、翁方纲等齐肩的大家洪亮吉《江北诗话》遍观当时诗坛之后,“以钱宗伯载为第一”[2]2255;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亦许为“卓然大家,在雍乾间无敌手”[3]5403。但是钱载诗歌研究,总体上却甚为寂寥。鉴于此,钱载诗歌研究是必要的。
钱载诗学观的研究,是钱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钱载,对诗文画均有论述,有着丰富的文艺思想。其文论主要包含在文集之中,政教色彩较浓。诗论最为丰富和重要,诗艺居于突出位置。
钱载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论主要见于诗作批注和诗序中。其批注主要有:《钱载评〈翁覃溪诗〉》(稿本,不分卷)、《钱载批〈樊榭山房诗〉》(传钞本)、《钱载评〈杜工部诗集〉》(朱鹤龄辑注本)等,诗序则主要存在《萚石斋文集》中。
《钱载批〈樊榭山房诗〉》和《钱载评〈杜工部诗集〉》,多是较短的评点,主要涉及音韵、诗法和审美风格等。《钱载评〈翁覃溪诗〉》,除片语短章外,多理论性较强、篇幅较长的一般性诗论,代表了钱载主要的诗学观点,尤为重要。
钱载诗论,总体而言,源自杜甫、黄庭坚等,以据“实”求“超”为特色。
七律第一要亲切,第一要明亮。有亲切明亮之思路以取径矣,而引用又不浅泛,而接转又发得开,此则稳稳写入,不在于过求深远。盖凡事以实为主,容不得一分客气也。然而超则元要超。七古依经傍注则路在亲切一边矣,……一面谨严,一面充拓,原是愈进而愈难也。然却须适可而止,一过火即入旁门耳。[4]萚批十二
无论律诗,还是古诗,均须以“实”为主、以“超”辅,做到“亲切”与“明亮”,“一面谨严,一面充拓”,追求参差而同的中和之境。结合其他诗论,大略可具体为:内容上求实意与真情,艺术上求成法与活法,质地上求卷轴与书味。试分而论之。
一、“用古谊据今情”——实意与真情
钱载有诗人、学人和缙绅三种身份。作为诗人,其求“真情”,即重情尚气;作为学人与缙绅,其求“实意”,即充“实”于情气之中,使情气,含有丰富的社会、历史、伦理和法度等方面的因素。在这里,二者处于不同层次,“真情”,是第一层次,“实意”,是第二层次。“真情”,居于诗歌表现对象的层次上,整体上是感性的,表明钱载诗论重情尚气的取向。“实意”,主要指“真情”同一体中理性的一面,在与感性一面的比较中,而成其“实”。也就是说,在情或气的同一体中,感性居于主导地位,理性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其中理性成分,与唐诗、袁枚的“性灵”诗相比,明显增大。简言之,钱载诗学主张诗歌抒发有着质厚内涵的真气和感情。从三个方面论述。
首先,钱载对诗歌的主情尚气取向有着明确的理论表述。钱载认为诗歌“第一原要气厚”[4]萚批又二。尚气取向非常明确。诗歌在本质上是尚气的,同时,又须充沛有力和内蕴丰富。内蕴丰富的“气”,是诗歌内容的第一要素。
钱载在其《纪心斋楚游集序》中称许友人诗说:“其于诗,往往用古谊据今情。……其古体戛戛独造,非恒蹊。近体五言高可企‘河岳英灵’、‘中兴间氣’诸家。”[5]403—404此话虽是评语,但理论色彩明显。其中“用古谊据今情”与“第一原要气厚”,有着相同的涵义。
其一,是其“今情”的感性本质。所冠“今”字,应有当下、临机而非宿禀、原有之义。“情”,仅从字面讲,可有感情和情况之义。而联系下文,则应为感情、生气之义。友人之诗,古体不泥蹊径,有生发有创新,近体则可及盛唐、大历诸诗家。我们知道,古体诗多以气胜,尤其是不泥于蹊径者;唐诗,总体而言,皆以主情重气为宗旨。盛唐诗自不待言。大历之诗,虽然送行、酬答、投赠之类作品明显增多,但是,写景抒情的构思仍然被主要倚重。所以,“今情”,应释为当下、临机的生命感和感情。其二,是“今情”与“古谊”关系,是本与用的关系。“今情”统摄“古谊”,理性寓于感性之中。蕴含“古谊”的“今情”,是诗歌内容的首要因素。
要之,“第一原要气厚”、“用古谊据今情”,是钱载诗学重情尚气完整而准确的概括。
其次,“情”、“气”,是钱载论诗常见的术语。先看“情”。评厉鹗《雨后坐孤山》说:“此则性情之独至。”[6]106称誉诗有独至的性情。“今已入妙境,有味之至,此后只要准绳,秾郁以情胜,则更好矣。”[4]萚批七诗如要“有味”、“入妙境”,必以“秾郁以情胜”——强烈的感情作为内在根据。另如“而仍自兴会飚举”[4]萚批一,“而总要是我之诗,此则可传矣。”[4]萚批又三其“兴会飚举”与“我”中之“情”等,皆禀感性。再看“气”。以“气”论诗,《钱载评〈杜工部诗集〉》中尤多。评《野望》说:“三四句,其句中之气甚长”、“其魄力神气比前乃十倍”[7]卷八;《怀旧》:“生死论交,一时之作,大笔直书,略无渣滓。读之但觉其气已舒矣。再读之始知其气仍未舒矣,此中大可跻攀”[7]卷十一;评《奉送萧二十使君》:“重规叠矩以再振其气”[7]卷二十;评《戏为六绝句》第一首:“惟此一首末句以反笔勒住,所以下章之‘江河万古’、‘掣鲸碧海’,气更伸长也。”[7]卷九可见用“气”评诗之多。
当然,其“情”、“气”,不是了无根柢的肆心而发,而是质之以醇厚的,此为“实”。诚如上言,“此后只要准绳,秾郁以情胜,则更好矣。”诗之“更好”,除了“情胜”,还须伴以“准绳”。情法不离,可避了无根柢,游心肆发。同时,又是浓情积气的必要方式,如前所说,“重规叠矩”可以振气;“反笔勒住”,可以使“下章之‘江河万古’、‘掣鲸碧海’,气更伸长也。”钱载为得情浓气厚,不仅求诸法度节制,而且诉之于“道”。如其在《查天池诗集序》中称誉友人诗曰:“喻道于文,盎流真气。”[5]404明道于诗文,遂流真气,其“气”伦理性等因素,是明显的。当然,钱载论诗涉及伦理等内容的地方不多,这与其文论形成明显对比。
多以情气论诗,是钱载诗学重情尚气取向在批评实践方面的体现。
复次,钱载反对为诗敷衍强作、滥用序注和议论等。
第一,钱载认为做诗要有积而发,量力而行,不宜敷衍强作。在《钱载批〈樊榭山房诗〉》中,对一些作品,钱载常评以“敷衍”、“凑”、“竭”、“廓落”、“阔疏”等语。胸无要言之物、欲抒之情,势必空洞的排字凑韵,敷衍成篇。胸有感发兴悟,却辞繁韵多,衍为长篇大作,整体而言,造成大而空而浮、内容与形式两相不称的情况。这样,必然造成为诗之源供给不暇的情况出现。这样的作品,也必然是廓落与阔疏的。所以,钱载亦告诫翁方纲:“如今要将充实工夫随时做去,亦多做不得,多做则容易不长进”[4]萚批又二,“所以小则成小,大则成大,只要成就,且莫骛广也。”[4]萚批又二认为翁氏写诗数量过多,少物而薄和勉强做大、好高骛远。
当然,这种少积而多出的情况,在抒情和言理的文体中都可能出现。但是,一方面,钱载这是在论诗,另一方面,从上述对其观点的分析中,也看不出钱载之昌言之有物,是针对以学问为诗而提出的建议。所以,这可以从另一角度佐证钱载诗歌的取向。
第二,与重情尚气相应,钱载反对诗中叙事与议论成分的过量增加,从而违情背气,或者效果上的挤退、谈化情气的做法。他建议翁方纲说:“其有长序者,略节之,否则改为题下注,又有成题。诗后有一段记出者,此皆非本例。况亦不可烦言。诗所以不注而自明,不多注而易明者为上。不得已而注则亦不可多。”[4]萚批七我们知道,诗中序注,旨在标明做诗的缘由、事境、故实、事与物的考证、文字训诂等,体现了中唐,尤其是宋代以来,诗歌由类型化而生活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诗歌所表达内容如人事和情感等,所处的具体时空、背景和因由等定位性的因素日益成为必要而被凸显出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在诗歌正文中致力言志抒情,另一方面,也利于在诗歌中加注较为理性的内容。为此,诗歌题目的加长,序注的应用便成为必然。到清代学人之诗,尤其是翁方纲以学问考据为诗,更是变本加厉。钱载作为学人,自然也赞成诗中加序补注的做法,并认为这是为诗“不得已”的必然。这与其重视诗歌质厚、充实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作为诗人,他又反对翁方纲式几乎没有节制的在诗中运用序注的做法。而且,明确表示诗后加注,非诗歌“本例”,持“诗所以不注而自明,不多注而易明者为上”的看法。这既与其在创作中此类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言:“既济之以‘学’,特别是润养以书画金石气,又能力求回避繁碎考订、抄书作注,也就与翁方纲式的诗法分野各异。”[8]895-896又与其强调诗歌“气厚”、“情胜”、“今情”等相一致。
基于此,他亦不满为诗滥用议论:“诗入议论,终涉恶道。”[7]卷十三其“终”字,从语气推测,钱载似并非完全反对诗用议论,而似与对诗用序注的态度相近:诗中可用议论,然毕竟不是“本例”,能不用时,尽量不用,以免涉于恶道。
总之,钱载诗学推重有根柢的情和气。既与姚鼐、翁方纲等诗观有别,又与袁枚“性灵说”不同。
二、“章成”“无法”——成法与活法
“以实为主”,其“实”,有法度一义。重视诗法,是钱载求实诗学极为突出的方面。文艺之“法”,有成法和活法之分。成法指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形态和要素,是法的基本形态;活法,则是在遵守成法的同时,又能够顺人情、合事理、遂物理,是法的高级形态,所谓法之神境、化境,自由之境。这二者之间,又形成了“实”与“超”的关系。
第一,看成法。守成法,是艺术之成为艺术的先决条件。钱载重视法度,一定意义上,有屈意伸法的倾向,而法意的同一是其重要追求。
首先,显著的重法意识,是钱载诗论的重要特征。钱载创作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则是“专于章句上争奇”[9]60,并取得了世人的瞩目。钱钟书先生称其“荟萃古人句律之变,正谲都备,格式之多,骎骎欲空扫前载。”[1]573钱仲联先生亦说“乾嘉诗坛,诗艺最高者为三鼎足,即钱载、宋湘、黎简”[10]60,许之为诗艺巨手。
钱载对诗法,亦有显著的自觉意识,对用法密微的诗人常常向而往之,如说“看樊榭诗,觉得清深密微实不可及,其传乎得无疑也。”[4]萚批又三评厉鹗《过丁茜园斋观陈洪授合乐图》说:“蹊径且须明,章法岂可无”[6]105。为诗须明法度、有章法。一个“岂”字,不容置疑的明确态度。再看两则话,虽是就具体诗法而言,但引而申之,可见其思想实质。“七古仍以对为佳,又必以整为佳。不可专作长短句,此亦要紧说话也。”[4]萚批七“对叠是第一义,不知而误用笔,终身门外汉矣。”(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7]卷一,把仅为修辞的“对”“叠”,与对整个诗体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并将对其的正确运用,作为衡量作诗者入门的“第一义”标准。
其次,钱载诗论还有一定意义上伸法屈意倾向。分古体、近体论之。
先看古体。评厉鹗《杭郡庠掘地得苏文忠表忠观碑宋刻二片》云:“斤斤保守,但见其韵之可,未见其力之充。然叙次不乱,所谓成章者也,比于欠缺凌杂者已加数倍,难乎不难乎?”[6]108此为七古。斤斤于韵律、成章,固然可能失于力弱。然而比之“欠缺凌杂者”之“力之充”,“已加数倍”了。立足点在诗法一方。此亦可从对王安石和元好问的取舍评价中得到印证:
王半山七古亦太紧,直然笔力直跻颠顶,一笔可抵十笔,一声可抵十声。骨胜之难如此。元遗山《马蹄一蹴荆门空》诸篇有间架、有声调、有色泽,规规矩矩,何尝不好,然如小试考卷,其品格不高。然则非遗山之难于高,正见遗山之谨守绳尺耳。[4]萚批一
王安石七古笔力凝练、高健,颇具阳刚之质。但钱载嫌其“太紧”。而元好问的《马蹄一蹴荆门空》,“有间架、有声调、有色泽,规规矩矩”,虽说“如小试考卷,其品格不高”,但“正见遗山之谨守绳尺耳”,亦“正见”其称善之意。宁失于品格低弱,也要谨守诗理法度。本来,钱载是重视古体之骨力品格的,如“古体则全靠典故、神韵、骨力”[4]萚批一。阳刚之质,是古体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当“骨力”与“绳尺”发生矛盾时,“骨力”还是要被舍弃的。
古体已然,近体更是如此。评厉鹗五律《络纬》云:“次序不得乱,未免太苦,然不失步。”[6]106依坤一看来,次序至于拘泥,固然失于“苦”——创作过程的费力和表意的晦涩与板滞等,然而至少避免了“失步”的缺陷。其中轻重取舍明显。再看:
此第八句亦如前“只有青房绿雾霏”之乾直,此必须得一吞吐之法方妙。“麾下赖君才并入,独能无意向渔樵”,末尝佳也,然极吞吐矣。“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之类,皆有吞吐,而不曾佳,何碍。至于“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之类,其佳者固是,何如此处正须寻一出路也。山谷亦尝说,须寻一个出场之法。出场之法不穷,惟有杜工部矣。[4]萚批又四
“麾下赖君才并入,独能无意向渔樵”,为杜甫《赠田九判官梁丘》末联,前句为“入”,后句是“出”,一入一出,吞吐转折。又“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是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末联,一送一归,为一吞吐。且前句直叙其事,后句则用舜时夔龙和魏晋间荀勖故事,表意乍离还合,此又一吞吐。至于这两联诗意本身,坤一并不以为“佳”,但其意脉中,因有转折、离合的结构,故“极吞吐矣”,遂入妙境。而诗句“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杜甫《野老》),意佳,但只有“进路”却无“出路”、没有吞吐之致,故亦是坤一所不称取的。其法意的取舍态度极明显。但是,亦可见出钱载对源自章法等形式自身所禀之理致、理趣的欣赏。这种形式意味,类似于文人画之“笔墨”“情趣”。对于绘画被潘天寿称许为“摆脱俗格”[11]257的钱载,诗画融通,重视律诗章法之“理致”、“意味”,则是自然而然之事。所以,从这个意义看,钱载并没有走向形式的极端,法意的相反相成,才是更重要的追求。
复次,法意的相反相成,钱载诗论中,大致有助成气厚、才情和劲健之质等几种情况。看前文已引用的两句话:“重规叠矩以再振其气”、“惟此一首,末句以反笔勒住,所以下章之‘江河万古’、‘掣鲸碧海’,气更伸长也。”“重规叠矩”可以振气;“反笔勒住”,可以使“气更伸长”。法度在适宜之处予以节制,从而助成情浓气厚。
“蹊径且须明,章法岂可无,字眼岂可杜撰,蛮做岂是才情,莫说此种拘拘也。”[6]105做诗须明蹊径,有章法,“字眼”要有来历,不可杜撰。规矩、拘牵可谓繁多严格。至此还不算完,却进一步将规矩视为“才情”得以形成的一个质地、一种规定性因素,否定没有规矩的“蛮做”。
刻意法度,有意为诗,固然有时可能妨碍内容完美表现,但是,却可能成为促成某种风格产生的必要因素。“七古且作七言之长调,则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邂逅生发。若有意为之即不真,然若无意为之,却又不健。”[4]萚批一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健”的形成,除了沛然胸臆的自然流露,还须借助于诗艺的刻意提炼、拔高等。是一定刻意的安排与经营,成就了诗歌风格之健。其二,其言语之间,创作的无意与有意、“真”与“不真”之间,似宁愿舍弃前者,也不愿使作品失于弱,不愿放弃有意为诗的安排与经营。
这种借法度成就气厚、才情与劲健的理路,远者近于苏轼之“寄豪放于妙理之中”,近者同于翁方纲的“始知真放本精微”[12]1414,基本精神源于杜甫。
简言之,法意之间,矛盾也好,同一也罢,均在不同程度上,突出了诗歌法度的重要性。法意的同一,是通向活法的必要途径。再加上创作的自然、自由,法意融通,法便是活法了。
第二,再看活法。循法是“实”,用活法,则是“实”基础上的“超”。活法,是灵机条件下、自由表现的艺术能力。活法的应用,是一种技进乎道(艺术构思等)的境界和法意相随的神化过程。钱载追求活法。评杜甫《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亦真境诗,而真则章成而本无法耳。”[37]卷八诗意从胸襟中自然流出,此为“真”。“无法”,无须经营安排,而“章成”——章法自成。不泥于法,亦不离于法。合法就是适意,适意即是合法。
钱载评诗,多用“妙”、“趣”、“味”等语,而且,又多与诗法相联系,也即多数是在赞叹诗法用的“妙”、有趣、有味。“安顿清楚,然有顺逆在,所以妙。”(《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7]卷二十“转得妙。”(《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待御》[7]卷二十“‘贾’‘褚’紧承‘人’字,妙是开拓。”[7]卷十九(《发潭州》)“‘屋前’接妙”(《玄都坛歌寄元逸人》)[7]卷一。其妙,与“顺逆”、“转”、“承”、“开拓”、“接”等章法有关。章法之妙主要源于章法与意关系的自然融合,亦即法可以自由呈现、表达所欲呈现、表达之意。此时之法,即为活法。厉鹗《病中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首句》第三首,被评为有“趣味。”[6]108对此作一些具体分析,以见法意融通而成趣的具体情况。“趣味”,是一种主要诉诸心灵和感情的审美体验和感受等。其“趣”,有旨趣一义,即意理之趣——给人以愉悦美感的意理,近于理趣。在钱载看来,则为法意结合的神化体验与境界。其诗为:
满城风雨近重阳,及至重阳霁色苍。问疾客来时一二,登高人想不寻常(时朱丈鹿田招集吴山登高不克赴)。琉璃水浅盛新月,玛瑙天空映拒霜。谁道秋容丽如许,闭门也有小篇章。
此诗“趣味”,主要来自起承转合的章法和作者曲折心情之间,了无迹象的两相符节。一二句,由风雨折出霁色,重阳登高成行看来不再存在障碍,此谓“起”。可是,三四句,诗人此时却偏偏生病了,酬愿又一次出现障碍,此为承中之折。而且,这两句中,又雪上加霜,从注中得知友人此日偏又召集众人进行集体登高活动。虽时有一二问疾客人,非但不足除“霜”,反而有可能因此又额外勾起或加重未能赴会的惆怅,此又为“病”之承。五六句,言出行登高的好天气好景致,进一步加重三四句惆怅之心情,是为承。末联,以“秋容丽如许”,再次递进承接,几使诗人坠入“万劫不复”之域了。“谁道”,开始转折。“闭门也有小篇章”,简直“劫”中逢生了,此回合首联的心情。复杂的起承转合之章法,与作者曲折变化之心情,水乳交融,无一丝牵强处,自然合节,法意相随。合法就是适意,适意即是合法,是为理趣活法。
另外,钱载对活法的生成机制,亦有一定的认识。如他说:
但骨力太过露了出来,亦非必该如此,终以肉采相附者为妙。……要于此随其吞吐自生肉采实难,惟其难,所以要观古人诗多,要书卷多,要路头开阔得多,则无一字无来历。而仍自兴会飚举,宽然有伸缩自如,读之令人生趣勃勃,津乎其有味焉,此所以无尽境也。……题目有贴骨之典切,此不希罕,全视运用吞吐何如。题目有旁面侧面之可以典切,此则全在胸次得之古人者深。则一经驱使,确切不移,触景生情,无乎不妙矣。[4]萚批一
此处至少谈两种诗法入妙。“骨力”与“肉采”“相附”为“妙”,既为风格刚柔的相济,又是创作的原则与方法,即刚柔相济之方;题目与内容“典切”的“吞”与“吐”之法。两法为成法,只是一种原则,一般来看,本身无所谓妙与不妙。从全文来看,其入妙须两个条件:兴会飚举;多书卷、古意盎然的胸次。“兴会飚举”,是创作的灵感状态,自然是妙境生成的必要前提。而品学根柢与诗法入妙之间,亦有必然的联系。
总之,钱载对活法有着显著的自觉意识。既有明确的表述和理论思考,又有以“妙”、“趣”、“味”等术语进行批评的实践。
三、“书味”——书卷与趣味
钱载修养诗论,以“多”“书卷”为“实”,以见“书味”为“超”。乾嘉学术的特征是通经尚古,历史性凌驾于现实性之上,所以,此期诗学及其修养论,多以“古”为特色。“古”,主要来自“书”,故其又可表述为以“多”“书卷”为特色。此为“实”。同时,钱载又倾向于书卷以间接、抽象的方式入诗。也即书卷入诗,主要以人的心理、精神为中介,参与诗歌审美境界的创造。这样,书卷就从知识材料形态,提升到“趣味”、“书味”等艺术形态。此为见“书味”,为“超”。试分论之。
首先,看“多”“书卷”。钱载诗论,一再标举“多书卷”、“无一字无来历”。如:“要观古人诗多,要书卷多,要路头开阔得多,则无一字无来历”[4]萚批一、“无字无来历为主”[4]萚批一、“诗境只是与年俱进,随时随地随题取书卷灌注之”[4]萚批又三等。为诗须多读读书,多读古人书,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又“词场祖述,必取则于先贤,此亦三王祭川之义也。山谷亦曰:‘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7]卷九“取则于先贤”,为诗所必须。而诗之“质厚”,亦主要源于古人。乾嘉诗学之“质厚”、“实”,与“以古人为师”之间,可以说有着一种当然的联系。而古人与书卷也本然的连在一起,“取则先贤”,则意味着以书卷入诗。书卷入诗,对于钱载,可谓观念根深蒂固,态度坚定不移。
对于书卷入诗的功用,钱载亦有明确的认识。从钱载诗论看,书卷入诗,可以助成诗歌的雅正品质、诗法运用的自由化和理趣书味等。其一,如:“必以古来大家之明理正人为之师,则心与力俱在正大处,……有卷轴古今者必胜空疏伪雅”[4]萚批五。为诗“以古来大家之明理正人为之师”,可使作者的精神以至作品的特征等俱在正大之处;读古今之书,能够促成诗歌充实雅正的质地。这是钱载诗论所反复称述的。雅正是其诗论重要的美学追求。其二,如:“题目有贴骨之典切,此不希罕,全视运用吞吐何如。题目有旁面侧面之可以典切,此则全在胸次得之古人者深。则一经驱使,确切不移,触景生情,无乎不妙矣。”[4]萚批一诚如前文所析,品学胸次和“吞”“吐”之法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书卷的入诗,是诗法入妙——诗法的运用,进入自由状态的必要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卷还能够助成诗歌生趣有味。详见下文。要之,书卷的入诗,是钱载作为学人,在修养论上的必然取向。
其次,论见“书味”。书卷于诗歌中的理趣化、书味化,又是钱载作为诗人的必然追求。看三则引文:
诗境只是与年俱进,随时随地随题取书卷灌注之,所以看书要多,则书味盎然。……读书亦焉能一口吸尽西江,只得随时勉力。……厉樊榭即是如此一生灌注都在诗词。厉樊榭有味,都在两片嘴唇上见书味。[4]萚批又三
有卷轴古今者必胜空疏伪雅,夫岂可限量哉。申之以岁月,由生得熟,由熟得生,……持之机,非可以预必也。[4]萚批五
无字无来历为主。然须参活句,不死于句下,如此,亦是自拔一队矣。[4]萚批一
其中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钱载将“书”和“味”连接在一起。这意味着书卷于诗中的存在方式是非表现对象的,书卷材料在诗中经过了虚化、诗化。“味”、“趣味”或者“妙境”等,表示的是一种审美属性、审美境界。在钱载看来,“书”之灌注于诗,不仅语言形式上要“字字有来历”,更重要的是将书的因素,融涵在兴会、感情中间,进到一种或深厚,或悠远的审美境界。这样,书卷就从知识材料形态,提升到“趣味”、“书味”等艺术形态。这是钱载的理想追求,如他称羡厉鹗于声调上见书味,即将书卷意味灌注于诗歌的节律声调中,如歌似曲,是对学问不着痕迹的、抽象的处理。其二,钱载对书卷趣味化的机制,亦有一定程度上的自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读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读书不能一口吸尽西江水,只能像厉鹗那样,天长日久随时随地用心勉力,将书卷灌注于诗歌。这样,诗境才能够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书卷入诗,是一个艺术创新的过程。在钱载看来,这是一个近于黄庭坚“以故为新”的过程。“申之以岁月,由生得熟,由熟得生……持之机,非可以预必也”,可以理解为:读书是一个须假以时日岁月、由生而熟的过程。而书卷入诗,与之相反,是一个由熟而生,也即“以故为新”的过程。而且,由“熟”至“生”的变化,又须两个条件:一是其方式,是间接、抽象的,“须参活句,不死于句下”;一是处于“持之机”、“非可以预必”的灵感状态中。这样,书卷就能升入趣味妙境。
概言之,重视书卷入诗,是“实”。入诗之书卷的艺术化,则为“超”。这些,亦反映出钱载较多的诗人立场,与翁方纲直接以学问为诗的实践与理论形成了差别。
综观全文,钱载诗学以“实”、“质厚”为主,符合雍乾诗学离虚就实的发展趋势。但是钱载以凸显“超”字为特色。钱载诗论主张“用古谊据今情”、明蹊径而用活法、多书卷而见书味等,表明了学人与诗人合一、学问与性情相济的旨趣。较之姚鼐、翁方纲,钱载诗论是较多站在诗人的立场上。而姚、翁则是较多站在古文家和考据家的立场上。因为较为显著的程朱伦理性,汉唐经学的历史理性,影响了他们诗学非感性因素的凸显。但作为兼备缙绅与学人风度的诗家,钱载又不能赞同袁枚肆心为诗的“性灵说”。这便是钱载诗论在乾嘉诗坛的基本定位。而在诗歌史上,钱载之学问与性情相济的观点,则又是之后宋诗派诗学的主要观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