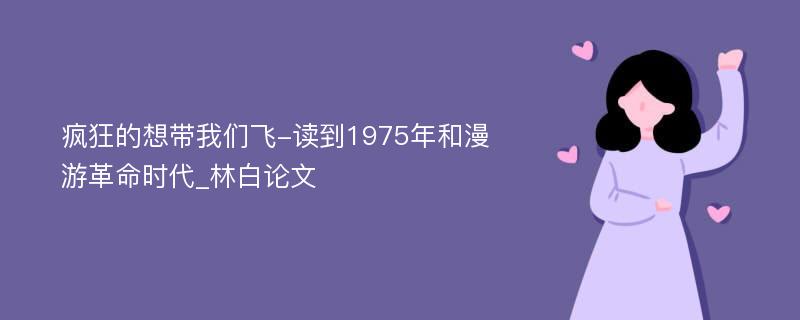
狂想带我们飞翔——读《致一九七五》和《漫游革命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想论文,一九论文,七五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白的新作《致一九七五》和《漫游革命时代》(《华语文学》二○○七年第十期)既可单独阅读,也可合二为一为长篇。其中的人物是贯穿的,情感是延续的。虽然前一部叙述的是学校生活的尾声,带有个人回忆录的性质;后一部叙述的是知识青年下乡改造的农村生活,而且这种插队的生活被叙述者的“狂想”气质所附着,不同于过往知青小说的苦难或诗意。
自《一个人的战争》发表以后,林白就被牢牢地贴上了“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的标签;直到十年后《妇女闲聊录》的出版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觉得林白终于从闺房中勇敢地走出来了,走到了一个风雨雷电兼有的现实的女性世界中。可是,这口松了的气还没有安稳地落到腹腔,林白又发表了她的新作《致一九七五》和《漫游革命时代》。这两部前后历时十年、写作时间跨度非常大的文本,叙事上完全依循回忆的特点:舒缓、闲散、婉转,有如日常流水,到了一种彻底轻松彻底自由的挥洒境界,时而蜻蜓点水,时而浓墨重彩,随情绪流转。宏大的革命事件被付诸日常流水及个人记忆中零落的珠片。这两部小说一起打乱了林白往常的写作节奏,打乱了我们对她的阅读期待,也打乱了我们对于小说文体的理解以及对故事和真实的追求。同时它与林白既往的作品一道构筑致命的飞翔,被翅膀深度诱惑。
回忆与历史
历史是那样地整齐而必然,记忆却如此地琐细且偶然,然而光辉的历史正是通过琐细、跳跃甚至残缺的记忆获得生命,只有唤醒记忆之真才能通往历史之美与重,因为记忆意味着事实和责任。美学家高尔泰在《又到酒泉》一文中说:“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关上记忆的闸门,事实就会消失,历史就会黯然,责任就被遮蔽,就像我们在血淋淋的场景面前下意识地闭上双眼一样。
林白的回乡不经意地触动了记忆的雷管,于是,叙述之门顺手推开:
再次回到故乡南流那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
南流早已面目全非。我走在新的街道上,穿过陌生的街巷,走在陌生的人群里。而过去的南流,早已湮灭在时间的深处。
这个开篇为叙述者确定了回忆的视角,还有一个阔大的时空。“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四十六岁介乎二者之间,从不惑从容地走向天命,这个年龄奠定了全篇不慌不忙的叙事基调,但回望的是三十年前的青葱岁月,是面目不再的故园、故人故事。“新的”、“陌生的”拓宽了这种与故乡的距离感,一切的事物的面貌、意义乃至真相都像内心的故乡一样发生改变,今非昔比、物是人非这种陈旧的感慨难免不泛上心头。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提醒我们:重要的是时代的叙述而不是叙述的时代。时光不仅改变着叙述者李飘扬,也改变着她的记忆以及记忆中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到的《致一九七五》不再是历史上的一九七五年,而是二○○七年回望中的李飘扬的一九七五,是林白一个人创造的一九七五。她曾在不同的文本中提到一九七五,她将它当成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十八岁的成年礼总是那样叫人难忘叫人回味。岁月最是无情物,它不带表情地流淌。时光的漩涡不仅使南流在其中走样了,也使她的一九七五在不断的冲洗中走样了。
历史上的一九七五年也许并不比别的年份更为特别,不过它多少有了点转折意味,知识青年的高中因下乡而不成样子,他们的下乡因为有人告了御状就与往昔物质的苦难相去甚远,精神上的迷茫却在继续。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如既往,并没有因为“知识”的到来而有太多变化,对整体的乡村生活来说,知识青年的到来就像小鸟飞过天空时振翅扰动几圈涟漪然后复归平静,但对于个别青年来说,却可能别具意义。比如二翠,她对赵战略既不会有结局也不会有过程的单恋却在心理绵延,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更深维度的革命呢?对于单个人来说,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爱和被爱也许就是命运的圆心,其他的一切只是围着圆心旋转罢了。
一九七五年之后的下乡多少带着游戏的成分,此时的知识青年大多也不过把下乡看成“十八岁出门远行”,城市才是他们身体的归宿,乡村只是生命的驿站,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与领袖的要求背道而驰,总而言之就是告别农村,回到城市。毛主席的语录依然不时而至,可能还带有某些地域理解和想象上的偏差,但被叙述者记住的似乎是那些于己有利的顺耳的断章。宏大的事物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偏差,视角决定了叙事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白的叙事也在消解革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叙事逆着走样的时光回溯,班主任孙向明成了打通青春世界的纽结,他的正牌学历、他的异地身份,他的军装、性感的人字拖鞋、印着喜字的脸盆,他的排球,他的梅花党的故事……无一不沾染着爱情的光芒。所有的青春期的姑娘不约而同地明恋或暗恋着这位外地来的老师。不过他只是昙花一现,姑娘们又陷入各自的情感秘密中。然而昙花到底是昙花,一现也别具魅惑。孙向明有意无意地没有跟同学们告别,姑娘们仰起头也见不到梦幻中的白马王子,操场上的喧闹、课堂上的激情全都失色,但是各种消息依然沿着不同的校园小径穿行而来。孙向明的名字依然像炮弹一样点燃每个人心中的情感世界,她们小心守护着这个秘密腹地又忍不住要互相分享。生活就在这种晦明中匆匆向前。
我的情如姐妹的朋友雷朵恋爱了,为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喻章而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直至消失在世俗生活的尽头,我探长脑袋也看不到她的背影。我只能回忆起她的声音和模样:“那是最灿烂的日子。空气中满是蜜蜂的声音,甜丝丝的,纯金般的音色终日缭绕。”并发出无奈的叹息:“即使找到了雷朵,我们精神上也早已远隔重洋。雷朵啊,李飘扬,时光夺走的东西,就再也不会归还你们了。”
孙向明,我们中学时代的轴心,调回他的家乡了,从此不再谋面。
雷朵,为了爱情抛弃了事业,为了一个人抛弃了整个社会。
安凤美,她的电话因欠费而停机了,联系不上。
离多聚少。这就是人生的常态,经常会有熟人旧友消失在人海中,就像水淹没在水中、沙跌落在沙中一样踪影难觅。只有回忆是他们曾经存在的依据,而这些被记载的片段则像票根一样被保存下来。时光总是匆匆向前,而人心却会见缝插针地后退,退到有障碍物的地方方能打住。这些阻碍人心的记忆纽结、让人沉醉的细节就构成了个人的内心史,它属于历史却不同于历史。历史追求的是意义,个人史讲究的是趣味。历史绝大部分的体积被宏大事件垄断,而个人史大部分被卑渺的生命细节所占据,就像李飘扬关于玉林的记忆不过是吃米粉时那只底部有一个小孔而漏汤的碗。如果这是一只完整的没有一个小孔的碗,那么叙述者的记忆如何承载南流人们对玉林这样一个让人想往的大地方的想象?米粉碗底的小孔裹胁着米粉的气味打通了玉林的记忆通道。这个让人牢记的小孔是否也像通向记忆世界的防盗门上的小孔,我们只能通过这一小孔朦胧窥见无法真实触摸的记忆海洋。
个人与社会
在个人内在生活的核心中,永久地居住着一对矛盾——身体与灵魂、本能与信仰、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之间的搏斗与人类的历史一道延绵。林白的写作有效地呈现了身体依循本性对披着神圣面纱的宏大事物的反抗,呈现对“飞翔”状态的向往,写作在她看来正是飞翔的脚注之一:“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吸大麻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它们全部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① “狂想”也是一种飞翔,就像堂吉诃德那样举起长矛冲向风车,让自由战胜现实的世俗桎梏变成内心的真实。自由历来就是生命的首要诱惑,不仅对身体而且对心灵。对自由的歌咏构成了文艺真正持久的主旋律,尽管自由和主旋律都是被滥用了的符号。在诗人裴多斐看来自由值得人付出生命和爱情的代价。自由的价值越高,通向它的阻力也就越大,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枷锁在林白这里就是维持平常的力量,而飞翔才能打破平常,通向自由。
超出平常和维持平常是两股同时潜在的制约力量,它们互相搏斗也互相妥协,个人性往往要求一个人离开现实的轨道振翅飞翔,而社会性则要求其成员墨守成规,维持常态。无论个人性如何强大,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社会性对于个人性的压抑。但成就命运的个性,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脱下社会性的华美衣服,显示出自身的真相以及携带的密码和力量。而且正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成正比一样,越是在社会控制作用严苛的时候,这种个人性的反叛力量也越巨大。
在主人公李飘扬的成长道路上,孙向明和安凤美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个,也是不同的两极。为人师表的孙向明代表着激情和理想,他的个性完好地承载了社会赋予教师这个角色的责任和魅力,可以看作社会性的正极;而安凤美则代表着社会性的负极,她展示了个性的奇异、茁壮与美,她表达的是完全个人的气质,我行我素,社会性在她的范围内失灵了,她仿佛是天外来客。社会总是力图管理、规范和钳制每个人,但它并不能彻底战胜个人性的对抗作用。正如涂尔干在《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中的论述:
在人类身上有两类意识状态,它们在起源、性质和最终目标上都互不相同。其中的一种状态仅仅表达了我们的有机体以及与有机体最直接相关的对象。这类意识状态具有严格的个体性,只与我们自身有关,我们不能让它们从我们自己身上分开,就像我们不能把自己同我们的身体分开一样。相反,我们的另一类意识状态却来自社会;它们把社会转移到我们身上,使我们与某种超过我们的事物发生关系。它们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们使我们转向我们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目标;正是通过这类状态,而且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与别人交流。 ……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是社会存在,它只是社会的扩展。我们所描述的对立显然起源于它所包含的要素的真正性质。我们列举的例子是感觉和感官欲望与智识和道德生活之间的冲突;显然,各种激情和利己主义的倾向都来自于我们的个体构造,而我们的理性活动,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都依赖于社会因素。我们经常可以适时地证明,道德规范是社会精心构造的规范;它们所标有的强制性质只是社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够传递给予之有关的一切。②
正是社会性与个人性之间永不间歇的运动形成了社会稳定的杠杆,维持着社会的常态,其内在的平衡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每个人内心力量的合力之大小,所谓民心向背即谓此。社会性无处不在,个人性恰如春草,他们虎视眈眈同时彼此渗透,最终短暂妥协。社会性选择了主流,并通过主流影响大众,形成时代的精神河床,流经安稳庸常的日常生活;而个人性剑走偏锋,成就了河流中巨大的漩涡,成就了生命最隐蔽最饱满的汁液,像夜间群星中最亮最孤单的那颗星,其散发的清辉让人眩目却又让人忍不住要抬头仰望,给夜勇气,给人力量。
个人到底是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活在跌宕的革命事件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人生与历史的通道在何处?林白无意于回答这些问题却通过叙述呈现了自己的想象。有些人天生是为了故事甚至事故而来,她们被口头讲述、被记忆或者被记载被怀念,比如孙向明、安凤美、雷红、雷朵;而更多的人只是汇聚成时代的基石,她们内心也向往自由却耽于行动,她们的脚步止于幻想,更多时候他们无意识地被时代的洪流挟持着,就像李飘扬们的积极应考挤独木桥。人生像谜一样吸引着我们,最后却很可能图穷匕首现。一个班级是这样,一个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时代也是这样。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是懵懂的,而隔着时光的面影回望,事物会露出蒙娜丽莎式的迷蒙隐约的微笑。
通感:人的感官以及人与物
最后,我要特别提一提林白的通感——这可能也是她的写作秘密和她的写作动力。这种“狂想”所致的通感构成了她的语言奇观,构成了她独特而丰富的意象世界:色彩斑斓、浓烈,气息馥郁,芳香缭绕,让人沉浸并吐纳。
我相信不止在写作的瞬间,而是在所有生活的时刻,林白开放着自己所有的感官并完好地储存着这些信息,她不要归纳,不要分门别类,不要理清头绪。这时候,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皮肤一起张开,接受各种信息的刺激,那些微妙处让她会心;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交响曲齐奏,错综复杂的感觉蜂拥而至,互相通达互相传递互相缠绕。回到写作的时刻,叙述者只是忠实地支取其储蓄的百感交集的记忆,以声音来叙述视觉,以颜色来替代味道,以气息来抚慰饥渴……有时也会变本加厉地提取利息,夸张、演绎、想象、变形,百般齐来,似乎混乱然而却更真实,鲜花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不是经常像美食一样让我们垂涎么?
在《漫游革命时代》中,林白的通感范围极大地扩张了,不仅仅是人的感觉能够相通,就是物——动物乃至植物统统被具备了人的灵性和感觉,一个麻袋也能讲话,一只猪也能像主人一样追求自由,一条通向远方的小路也能与行人对话,一只公鸡恰如一个贴身保镖。这些对物的叙述在小说中闪闪发光,照亮了整个叙事情境。我不愿意将此简单地看成拟人的修辞手法,更愿意将它看作是物和人的情感相通,看作林白独有的叙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万物有灵,万物花开。一旦物拥有了这种通感的可能,它就拥有了与人同样的主体性,它就拥有了被叙述的权力,它们也要自由,它们也要反抗死亡追求精彩的生活。菜还是草,花还是药,鸡、猪、牛屎、猪屎都获得了相应的温度,它和人一道展翅飞翔。
人和物的对应关系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与他的道具,道具是角色的符号和象征,道具甚至比演员本身更长久,比如文本中的“我”正是因为竹喷筒才记住了宋谋生,因为这个小小的自制的有点粗糙的竹喷筒,平常得可以淹没在人海中的宋谋生才可能蛰居在李飘扬的记忆中,并穿越三十年的时光来与她的叙述相逢。又如“我”和特立独行的小刁、孙向明和排球、张飞燕和座位表、安凤美和二炮、赵战略和蘑菇都有着某种难以言传的关系。在文本中,物是沉默然而有灵性的,它跟懂它的心对话,它不需要语言却能理解人的感情。当人需要倾诉秘密的时候,物是多么称职的对象,它静默、安稳,从不出卖人的秘密,无论秘密的轻重等级,它一律照单容纳。在人多情的视角中,物和人心情相连,气息相通。
隔着三十年的日月,重新回到当年,叙述者依然能够依凭身体的记忆渐次开放,带着细节带着时代的总体气息纷至沓来:观看、抚摩、呼吸、倾听、回味……历史究竟是什么?是口号、精神、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述,还是个人的情感、创痛、爱和沉甸甸的生命细节?叙述者跟随意识的流动,慢慢地从前细数。
安凤美是两部中平均着墨最多的人,也是小说中浓墨华彩的部分,就连跟着她的二炮也被叙述得卓然独立,它的鸡冠似乎也格外鲜艳,它的鸣叫与鸡不同,它的作息也有别于众,它有灵性,懂得主人的心思并精心地护卫着她。虽然最后它懵懂地领受了命运的寒霜,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勇敢地为它的主人付出了生命。它牺牲了。但它与安凤美的神秘纠缠,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卓尔不群的日子,那些灿烂的记忆,谁又说它是白白地来到世间一遭的呢?
在一个道德话语至上的宏大时代,怎么能够容纳下安凤美这样的异数?尤其到了《漫游革命时代》,大家在农村无不希望早日回城而争取好好表现的时候,安凤美依然如故,她的身上显示了充分的个人性,彻底的我行我素,个人的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她与我们的道德教育“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南辕北辙。她身体单薄,但内心坚定,她不求上进,她卓尔不群。她听从自己青春激情的讯息,她感受身体欲望的涌动,她要满足身体本身提出的要求。她甘愿承担一切流言蜚语,甘愿背负所有的恶声以求得身体的自在和自由。她逆时而动,在最严酷的道德诉求的时代过着最自我的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道德诟病的安凤美并不孤单,还有罗明艳这样着墨不多的女性和她一样异曲同工,弃所谓的社会道德于不顾。刮宫,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禁忌,是对当时道德最严峻的挑战,而刮宫过程中罗明艳始终没有喊一声疼,这时积聚在她身体中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世俗的流言,也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无怨无悔。而未婚的安凤美希望将肚子里的孩子留下来、雷红渴望与爱人拥有一个私生子的念头无不展示了女性内心潜藏的韧性和力量。雷朵头也不回地走到社会的视线之外,雷红到底与有妇之夫私奔了,这些艰难而决绝的个人选择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和反叛。
在三十年的时光流动中,叙述者也不断地调整着评论的尺度。越是当年,叙述者离主流道德越近,越压抑自己的个性;而越是到了今天,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整个环境的轻松,使叙述变得越宽容、越尊崇自己的内心。叙述者对这些勇士们的赞赏直白地流露笔端。“我”的记忆让安凤美平稳地度过危机四伏的青春并华彩四溢:
她的声音里布满了细小的玻璃珠,尖细,同时又有一种明亮的欣喜,她从土坎上跳下来,玻璃珠飘动起来,在她的身上闪烁……
多年后我意识到,安凤美没有被毁掉,她的青春年华是开出花的,她既懒散,又英勇,她的花开在路上,六感和六麻,香塘和民安的机耕路,自行车和公鸡,五色花,和左手,和土坎,到处都是她的花。
此后,为了让安凤美的生活方式更可信,又让她简略地叙述了家史。父母离异、父亲作风有问题,这与众不同的成长环境似乎为她日后的离经叛道的生活选择奠定了更合情理的基础。
安凤美不仅自己对社会要求不管不顾,她还要伺机诱惑叙述者,她要钻进李飘扬的被窝,抚摸她纯洁的身体,告诉她爱情的滋味和性感的观念。她带着她的道具二炮招摇过市,她肆无忌惮地谈恋爱而且不忠,她听从本能的呼吸。她不勤劳却贪吃。物质匮乏的时代,食物总是越过一切被津津乐道,食物的香味总是让其他一切芬芳相形见绌。在这部长篇中,关于吃的片段散落在不同的章节中,发出珠落玉盘的声音来。“我”吃胎盘的事情不止一次被细述,炒通菜、桂林米粉、玉林米粉、南流米粉、清煮柚子皮、炒茄子头、晒瓜子、烤红薯……一些家常的食物却得到了无比饱满的叙述。这时候,时代的整体氛围像水彩一样慢慢洇开来,一幅古旧的画在读者面前徐徐抖落,和当下富足而挤压的消费气息泾渭分明。时光的隧道豁然洞开,黑暗中的那点亮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如何逼真地展现一个时代以及一个人的时代的问题,重新严肃地摆到了每个写作者的面前。
每个时代总会选择一些人来代表,这些光亮并不一定全部来自伟大、英勇和崇高,有些亮光来自黑暗深处,比如安凤美就是那个禁锢时代最耀眼的作品之一,她灼痛了一些人也照亮了一些人。她属于一九七五,她和一九七五互相偎依。假如时光直接走到了二○○七或者再倒退三十年,安凤美也许不会聚光,孙向明也可能会逊色。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投入历史的怀抱,而历史却总是漫不经心地筛选,并不依循固定的程序或公正的天平,最终,只有那些与众不同的片段汇流成河、百川归海。
二○○七年十月于穗
注释:
① 林白:《守望空心岁月》,第23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② 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第187-188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