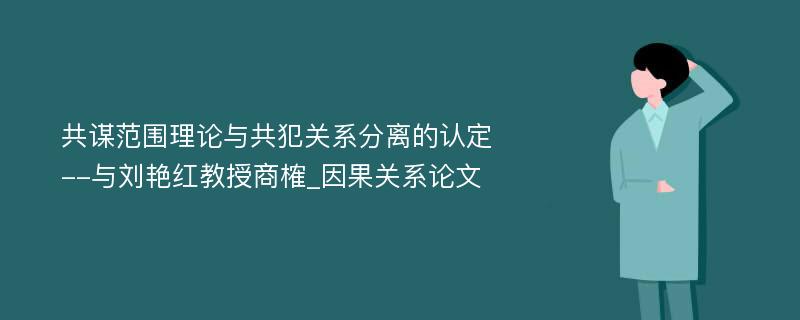
共谋射程理论与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犯论文,射程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205(2016)01-0058-(014)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1:被告人甲与乙、丙、丁等人在马路上闲聊时,醉酒路人A突然冲过来拉拽丁女的头发,为了让A放手,甲、乙、丙等人对A实施了暴力(反击行为)。A松开丁的头发之后,退往停车场之际仍保持着应战的态势,乙、丙继续追赶,结果由乙的追打行为导致A摔倒在水泥地上(追击行为),造成头盖骨骨折的重伤。对于追击行为,甲在现场既未参与也未制止①。 案例2:被告人杨某提议并与其他三名同伙经合谋和踩点之后,于2011年某日凌晨,先后两次进入某公司仓库内窃得手机摄像头共计73750只,赃物价值人民币250余万元。其中,四人一同窃得2万余只摄像头之后(第一次盗窃行为);在驾车返回途中,杨某因故中途离开,另三人待其下车后商议返回仓库窃取剩余的摄像头,三人又窃得5万余只摄像头(第二次盗窃行为)。事后由杨某负责联系销赃,获赃款18万余元,由四人分赃②。 案例3:吴某为杀蔡某准备了菜刀并邀请王某帮忙。一天夜里,吴、王在蔡必经的小巷将其拦住,吴一刀扎中蔡的腹部。蔡负伤逃跑,吴、王紧追。此时被警察发现,吴、王二人仓皇逃离。王逃回家后就睡觉了。吴则在现场某处躲藏,待警察走后,又四处寻找蔡某并在蔡家附近发现了蔡某,吴连捅蔡某数刀,致蔡某死亡。[1] 案例1中的甲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防卫过当,案例2中的杨某是仅就第一次盗窃行为还是应就两个盗窃行为成立盗窃罪,案例3中的王某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还是既遂,均取决于是否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 共犯关系的脱离,是指部分共犯在犯罪完成之前退出共犯关系,但剩余共犯继续完成了原定犯罪的情形③。共犯脱离理论由日本刑法学界率先提出,其实际意义在于,在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基本理论体系的框架之内,确定犯罪结果的归属主体,解决退出者的归责范围(是否对脱离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与归责程度(成立何种犯罪停止形态)。现在一般认为,若成立共犯脱离,退出者则不对退出之后由其他共犯所实现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仅就退出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共犯脱离?对此,因果关系切断说是日本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通说观点。该说立足于因果共犯论,认为共犯脱离的实质在于退出者消除自己行为的因果影响力,主张不论是在着手之前还是着手之后,是否成立共犯脱离,均取决于退出者是否切断了本人退出之前的参与行为与退出之后剩余共犯的行为及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物理上、心理上的因果影响力)④。亦即,在退出者消除了自己行为所已经引起的物理性以及心理性效果的场合,或者消除了剩余共犯利用这种效果而继续实施犯罪之危险的场合,即可认定切断了因果关系,成立共犯脱离。然而,要消除一旦给予的事实的因果性影响几近于不可能,[2]“如果以因果性作为问题,几乎所有场合均难以成立脱离”,[3]因而会不当限制共犯脱离的成立范围;并且,共犯脱离理论还被运用于共犯的量的防卫过当的情形。对于案例1,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该案中的反击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乙的追击行为成立量的过当防卫,由于“不能认定就追击行为重新成立了共谋”,最终判定甲无罪⑤。但在诸如案例1那样的案件中,显然难以谓之为已经切断了因果关系,按照因果关系切断说,甲势必也应成立故意伤害罪的防卫过当。为此,立足于因果关系切断说,主张即便事实上没有完全切断因果关系,但如果能从规范的角度给予“切断了因果关系”这一法律评价即可成立共犯脱离的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日益成为多数说。该说试图缓和因果关系的切断标准,是对因果关系切断说的修正与发展。但正如该说内部仍存在诸多观点那样,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标准来“规范地”判断才是问题之所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明确。 共犯脱离理论已为我国学界普遍接受⑥。作为其中的重要论文之一,刘艳红教授在《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撰文“共犯脱离判断基准: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以下简称“刘文”),在承继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认定标准,且力图通过具体案件予以确证。然而,刘文一方面主张共犯脱离理论的性质在于救济中止犯规定之不足,另一方面又承继了主张严格区分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的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这之间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整合性呢?刘文提出的认定标准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呢?这些都尚存疑问。 有鉴于此,本文意欲结合日本共犯脱离理论的最新动态,在检讨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以及刘文所提出的判断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对上述三个案例提出解决方案,揭示共犯脱离问题的解决路径,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二、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及其认定标准之检讨 (一)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之基本主张 1.内容。对于如何“规范评价”,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的论者间视角不尽一致,在日本学界主要存在下述不同观点。前田雅英从处罚必要性的角度提出,“在共犯的场合,心理因果性之解消属于主要问题。不过,虽说是‘解消’,但不以因果性为‘零’为必要,而属于‘是否减弱到不必要对结果(包括未遂结果)归责的程度’这种规范性评价。”[4]井田良从有无相当因果关系的角度提出,对于脱离之后的行为与结果不承担刑责的理由在于,退出者解消了与退出之前的行为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因而应要求退出者“解消或者消灭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危险或者因果性影响(至少降低到相当低的程度),能够认定存在可以评价为,只有其他实行者应对其后的行为与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事态”,那么,“(即便能肯定条件关系)这种因果进程也已经不能被评价为‘相当’⑦。松宫孝明提出,在向其他共犯提供有关犯罪现场的相关信息的场合,严格意义上,只要没有阻止犯罪行为就不可能切断因果关系,但“如果又给予了其他共犯足以消除此前已经给予的‘犯罪能量’的负能量,由此创造了与试图脱离者未曾加担过的情形相类似的状况的,就应该认定共犯脱离。这里其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因果性思考,而是规范性、评价性思考”。[5] 山中敬一从客观归属的视角提出,要完全消除已经给予的事实的因果性影响,这几近于不可能,因而应该从规范的角度来评价因果性贡献。例如,共谋抢劫并一同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因内部冲突而被视为“搅局者”的行为人提出退出,其他共犯回应称“请便”的,退出者虽然没有完全解消此前的因果性贡献,但由于可以规范地评价为,共谋关系已经因相互之间就“退出”所达成的合意而解消,对于剩余共犯此后的抢劫行为,就可视为已经脱离了共犯关系。[6]岛田聪一郎基于有些案件尽管仍然存在因果性影响但认定脱离更为合适这一问题意识,主张在因果关系切断说的基本构想之外,还需采用“另外的犯罪事实论”。具体而言,剩余共犯将退出者排除在外而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就切断了退出者退出之前的参与行为与退出之后剩余共犯的行为之间的关联,即便作为事实能认定存在诸如由提供工具等行为所产生的因果性,但对于剩余共犯的行为及其结果,仍然应理解为退出者不承担罪责。所谓应该对因果关系之切断进行规范性评价,就是指这种可以评价为“另外的犯罪事实”的情形。[7]盐见淳主张从脱离行为的视角来规范性地考察共犯脱离问题,认为所谓“切断”的规范化,研究的不是先前的参与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影响是否已经事实上丧失,而是能否将中止措施本身规范地评价为脱离。相较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性,退出者所采取的行动、态度等是否具有作为脱离的“适格性”才具有意义。“‘如果采取了处于行为人之立场下所能实施的、通常情况下足以消灭行为人所引起的危险’的措施,就无需研究是否属于异常的因果进程,根据其行为本身就能肯定脱离”⑧。成濑幸典从强调社会一般观念的角度提出,如果退出者实施了当时所能采取的、通常足以消灭危险的行为,即便未能消灭危险继而实现了构成要件结果,这里所实现的危险,就不再是共犯行为所创造的危险而是另外的危险。至于应采取何种措施,应该“基于各个案件的事实关系,在具体确定共犯行为所创造的危险的基础上,比照社会一般观念”来确定。[8] 2.评析。在有些案件虽未彻底切断因果关系,但仍有必要作为共犯脱离来处理的司法现状下,通过“规范评价”因果关系之切断与否,缓和因果关系的切断标准,这种努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鼓励犯罪人“迷途知返”积极放弃犯罪,进而防止法益实际遭受侵犯(或者遭受进一步的侵犯)。是否切断了因果关系,其本身是一种客观事实,因而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实质上是将“事实认定”转换为“规范评价”。[9]退出之前的行为的因果影响力有多大、退出行为多大程度上解消了这种影响力,当然不可能按照数学的、科学的方法精密测定,因而不可否认,对因果关系切断与否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评价,具有规范的性质;但也不允许藉此在规范评价的名义下,忽视对事实本身的正确认定。而且,法律评价作为一种规范评价,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种规范评价的明确性与客观性。基于以下几点,本文认为,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的问题意识虽值得肯定,但难以提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不能成为解决共犯脱离问题的基本观念。 第一,对于是否成立脱离,因果关系切断说研究的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立足于该说的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却以“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提出因果关系的“程度”问题,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问题转换;[10]而且,明明事实上“存在”因果关系,却可以通过所谓规范评价而认定“不存在”因果关系,该说与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因果共犯论之间是否存在整合性,也不无疑问。[11] 第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成立共同正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此外还需存在“正犯性”,如果以因果共犯论作为理论基础,就应明确区分“共同正犯性的解消”与作为共犯处罚根据的“因果性的切断”这两个问题。具体而言,按照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的逻辑,要成立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不仅需要“规范地”切断因果关系,还需要“另外再研究脱离行为对正犯性的影响”。[8]然而,首先,要脱离“共同正犯关系”,理应只要解消“正犯性”即可,未必需要切断因果关系(虽解消了“正犯性”但未能切断因果关系的,尚存在成立狭义的共犯之可能),因而要求“规范地”切断因果关系,这属于“过度要求,并不妥当”。[12]其次,既要求“规范地”切断因果关系还需要解消“正犯性”,这种做法也不符合该说试图统一解决广义的共犯脱离问题的理论旨趣;而且,共犯脱离理论研究的是能否将结果归责于退出者的问题,而正犯性则属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同时研究“共同正犯性的解消”与“因果性的切断”这两个问题,是“将结果归属问题与正犯性问题混为一谈”。[9]因而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存在理论上的内在矛盾,会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造成适用上的混乱。 第三,尽管各个共犯对犯罪结果的因果影响力有大小之分,但因果关系本应是“有”或者“无”的问题,而无程度之别;即便因果性存在程度之别,但对于通过何种努力减弱到何种程度才可成立脱离,也难以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标准。该说内部存在上述诸多观点就已经表明,所谓“规范评价”本身含有极大的随意性。例如,就案例1而言,鉴于“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说提出了几种解决思路:(1)既然当初的共谋内容是“共同实施防卫行为”,共同正犯的心理因果性就仅及于侵害当时的反击行为;[13](2)以共犯脱离不是要求消除因果影响力,而是从规范的角度否定客观归属为前提,主张既然当初的共谋是以正当防卫为内容,就应从规范的视角对追击行为认定成立脱离;[6](3)在由合法行为诱发了违法行为的场合,即便存在事实上的贡献或者事实上的盖然性关系,且没有积极消除危险,也不能将违法结果直接归属于合法行为;[14](4)对正当防卫行为的共谋,其本身不能为成立犯罪奠定基础,不能因为没有解消这种共谋,就对基于这种共谋的行为追究罪责。[15]这几种观点肯定甲成立共犯脱离的实质根据在于,因为共谋的反击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行为,所以即便与反击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不能追究刑责。但是,如后所述,是否成立共同正犯,属于是否共同引起了构成要件该当事实的问题,这种判断应该先行于对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因此,共谋的内容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理应对此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为此,另有论者提出,即便存在“没有当初的反击行为,就没有后面的追击行为”这种条件关系,但仍然可以说,甲对于追击行为的因果贡献很小,尚未达到共犯构成要件所预定的程度,因而能成立脱离。[16]然而,归责问题属于是否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而非程度问题,按照因果共犯论,只要能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该结果就理应可以归责于甲,所谓“因果贡献很小”不过是量刑上的问题。[9] 另外,共犯的实行过限与共犯的脱离是两个紧密关联相互对应的概念,但在实行过限的情形下,行为人往往对过限行为并无预见,而无法采取措施以消除自己先前行为的因果影响力,先前行为所产生的促进效果一般会延续至结果发生当时,因而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即便能解决共犯脱离问题,也无法解决实行过限问题,其理论本身存在局限,难以为司法实务解决共犯疑难问题提供统一路径。概言之,共犯论的核心是归责问题,共犯脱离研究的正是可否将剩余共犯的行为及其结果归责于退出者的问题;要将结果归责于退出者,当然要求其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只是解决了处罚根据问题,并不能确定归责范围⑨。按照责任主义,共犯也只应对自己行为以及可以评价为自己行为的其他共犯的行为担责,因而是否成立共犯脱离,应该取决于剩余共犯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可以被评价为退出者的行为。 (二)基于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的认定标准之问题 鉴于既往的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未能提出明确的共犯脱离认定标准,刘文提出了三点成立条件:(1)主观基准条件:表达了脱离的意思并为其他共犯者所了解。(2)客观基准条件:停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且解除了共犯关系。(3)效果基准条件:规范考察是否切断了物理与心理的因果关系;并且,满足了主客观基准条件,未必能得出已经切断因果关系以及可以成立共犯脱离的结论,最终还需要从法律评价的角度规范地考察是否已经切断了因果关系,需要规范地考察是否消除了自己贡献的因果影响;但即便尚未完全消除自己贡献的因果影响,也有成立共犯关系脱离之可能。[1] 但是,第一,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之所以要对因果关系进行“规范考察”,其目的在于论证“即便存在因果关系,亦可认定共犯脱离”,其观点概言之就是“是否成立共犯脱离,应该进行规范性考察”。然而,何为“规范考察”,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规范考察”的问题,且所有法律评价都是在进行规范性考察,因而刘文的标准是否真正解决了认定标准的客观性、明确性问题,就不无疑问。 第二,成立共犯关系,以主观上存在“共同故意”与客观上存在“共同行为”为必要,要解除业已形成的共犯关系,也理应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所谓主观上“表达了脱离的意思并为其他共犯者所了解”以及客观上“停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就不过是解除共犯关系的认定要件,将“解除了共犯关系”作为与之相并列的客观要件之一,是将“认定要件”与“认定结果”混为一谈,不存在逻辑上的自洽性⑩。 第三,尽管共犯关系的存在与否本身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共犯关系的成立或者解除则是基于主客观方面事实的规范评价(而非刘文所谓“‘彻底解除共犯关系’是对共犯脱离是否成立的事实评价”),既然已经通过脱离者的主客观方面的表现,已经规范地认定“彻底地解除了共犯关系”,这就表明,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是不包括退出者在内的剩余共犯的行为,最终结果是由不同于包括退出者在内的既存共犯关系的、剩余共犯基于新的共谋而形成的另外的共犯关系所引起,按照责任主义的要求,退出者原本无需对此行为及其结果负责,根本没有“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与否,最终还需要从法律评价的角度规范地考察是否已经切断了因果关系”之余地。因而在已经“解除了共犯关系”的基础之上,再进行所谓“规范性”评价,不仅是一种违背逻辑上的先后关系的无谓的重复,会使得认定过程繁琐复杂,而且,要求过于严苛,也实质背离了刘文所追求的“相对宽宥地认定共犯脱离的成立范围”这一“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最大的意义”。 第四,刘文在将“解除了共犯关系”作为客观条件之一的同时,一方面认为“只有当相互利用及补充的行为关系即脱离者与其他共犯人行为的因果力不再存在时,才能认定共犯关系的解除”;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在满足了前述主观与客观基准条件之后,并不一定就能得出因果关系已经切断以及共犯脱离可以成立的结论;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与否,最终还需要从法律评价的角度规范地考察是否已经切断了因果关系”。[1]然而,虽能证明“因果力不再存在”,却不能认定“因果关系已经切断”,不得不说,刘文观点不无自我矛盾之嫌。 第五,最大问题还在于,刘文一方面主张“所谓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是指规范地考察脱离者当初的加功行为与其他共犯人行为及结果之间的物理及心理的因果性是否切断的学说;如果认定为成立脱离,则脱离者对其他共犯人其后的行为与结果不负责任”,[1]但作为论文结论却又提出“停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且解除了共犯关系之后,脱离者当然无需对脱离之后的行为承担罪责,脱离者此前与其他共犯人实施的共同行为才是共犯脱离问题所要关注的核心”。[5]这无异于是说,只要满足“客观基准条件”就“当然无需对脱离之后的行为承担罪责”,是否成立脱离与是否对最终结果担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其他两个条件(即“主观基准条件”与“效果基准条件”)只是脱离的成立要件而不是对最终结果不承担罪责的根据。这不仅是对己说的自我否定,更是对脱离问题的根本性认识错误。正如刘文所言,研究共犯脱离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认定为成立脱离,则脱离者对其他共犯人其后的行为与结果不负责任”,脱离理论研究的是,不对退出之后由其他共犯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的理论根据,脱离的成立条件正是退出者对剩余共犯所继续完成的犯罪免予刑事处罚的要件。[17]至于“脱离者此前与其他共犯人实施的共同行为”,退出者即便成立脱离也仍应对此承担相应罪责,但这只是在认定成立脱离之后,具体确定退出者的罪责之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反之,若不成立脱离,退出者不仅要对“此前与其他共犯人实施的共同行为”,还要对退出之后其他共犯所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因为,按照责任主义,与单独犯一样,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也需对自己已经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无论退出者是否成立脱离,都应该对自己退出之前的行为承担相应罪责,不可能因为退出行为而对自己已经实施的行为不承担罪责。 由上可见,刘文所提出的共犯脱离的成立条件不仅不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更内含矛盾,难以真正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例如,就案例1而言,“对于追击行为,甲在现场既未参与也未制止”,按照刘文观点,甲在现场,就意味着对其他共犯的行动仍然在给予心理支持,难以规范地评价为切断了因果关系。但如后所述,让甲就乙的追击行为承担罪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共谋射程理论的优越性 (一)共犯脱离的理论定位 要确定共犯脱离问题的解决路径与认定标准,首先有必要明确共犯脱离理论的定位。共犯脱离多发生在部分共犯退出之后,剩余共犯继续实施犯罪且最终实现了既遂结果的情形下,若按照传统观点,将共犯脱离作为中止犯成立与否的问题来处理,对于那些虽经积极努力仍未能防止结果发生的退出者而言,只能是承担既遂罪责,不仅过于严苛,也不利于保护法益。有鉴于此,大塚仁率先系统研究共犯脱离问题,提出了障碍未遂准用说。该说立足的前提是,在处于同一共犯关系之下的其他共犯实现了既遂结果之时,对于任意或者真挚地消除了自己行为之影响的共犯,仍然应追究既遂之责,但同时主张“为了救济此类共犯,在能认定存在消除影响的任意性或者真挚性之时,可以作为共犯关系的‘脱离’,准照未遂予以任意性减轻”,[18]在于“力图弥补中止未遂所不能救济之处,属于中止未遂的救济之策”。[19]在当时的判例态度与学术背景之下,这种观念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共犯脱离理论的原点。但随着判例态度的转变尤其是共犯脱离理论的日臻完善,学界对脱离理论的定位逐步形成共识: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是属于不同理论层面的问题,必须明确区分二者。[20][21]亦即,“共犯关系脱离是基于共犯的处罚根据论的共犯处罚的极限问题,先行于共犯关系中是否成立中止犯的问题”,[8]成立共犯脱离是成立共犯中止的前提,只有退出者成立共犯脱离且具有任意性之时才成立中止犯。[22]因此,“由于该观点(即障碍未遂准用说)的前提本身并不妥当,因而再主张这种观点并无实际意义”。[23] 刘文对此共识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将脱离与中止交错探讨的做法,其实是试图建立一种广义的亦即涵盖中止犯在内的共犯脱离理论概念。这种脱离概念不但极易导致理论上的混乱,不利于建立富有准确内涵的脱离概念,而且会使共犯脱离概念失去独立的存在意义,使共犯脱离理论的发展也演变成为对共犯中止理论的完善,从而失去共犯脱离理论自身深入扩展的机会”,并主张“对共犯脱离的把握必须从弥补共犯中止理论之不足的角度,才能形塑有效的脱离基准理论”,“共犯脱离理论天然具有弥补中止理论之不足的机能,否定此点是对共犯脱离理论自身意义的抹杀”。[1] 然而,客观事实是,自平野龙一、西田典之等主张明确区分二者,倡导因果关系切断说以来,非但没有“抹杀”“共犯脱离理论自身意义”,反而演变至刘文所推崇的、以明确区分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为理论前提的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因而刘文对上述学界共识的批判,不免过于“武断”;而且,在发生了既遂结果的情形下,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是基于因果共犯论来论证行为人为何不对既遂结果承担罪责,而不是论证因为不能成立中止犯而成立既遂犯又过于严酷因而需要寻找一种救济之策,因而刘文对脱离理论的定位,与刘文所推崇的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之理论前提之间,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整合性就不无疑问;并且,主张明确区分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的观点“会使共犯脱离概念失去独立的存在意义”,而主张“共犯脱离理论天然具有弥补中止理论之不足的机能”,共犯脱离理论只是“中止未遂的救济之策”的观点,反而有利于“形塑有效的脱离基准理论”,能突出共犯脱离理论的“独立的存在意义”,其逻辑推理委实令人费解。另外,如后所述,刘文批判的所谓“将脱离与中止交错探讨的做法”,实质上是主张明确区分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力图明确二者在认定顺序上的先后关系,因而难以理解刘文何以得出“其实是试图建立一种广义的亦即涵盖中止犯在内的共犯脱离理论概念”这一结论,因而刘文基于这种错误理解而提出的批判,其理论价值何在,就不无疑问。 重要的是,大塚仁之所以提出共犯脱离理论“属于中止未遂的救济之策”,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判例态度与理论背景。基于下述三点理由,本文以为,刘文不仅未能准确把握这一点,也未能精确理解大塚仁观点之实质,更未能具体明确当下究竟应如何进行“救济”,因而只是形式地、表面地接受了该观点。 第一,在大塚仁提出该观点的当时,日本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均尚未意识到共犯脱离问题的存在,而完全是作为中止犯的问题来处理,因而大塚仁才会认为,对于那些为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付出真挚努力的退出者而言,要求其对整个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承担既遂罪责过于严苛,进而尝试采取准照未遂犯处罚这样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以谋求刑罚上的均衡,仍然是立足于“只要共同正犯达到既遂即无法成立中止犯”这一前提。但现在“‘共犯关系的脱离’就是在讨论其他共犯人的既遂结果是否可以客观归责于脱离共犯者”,[24]且不以退出行为具有任意性为必要。在已经发生既遂结果的情形下,至少对于那些不具有任意性的退出者,原本就没有成立共犯中止的余地,又何来“救济”之必要呢? 第二,“救济说”是将退出前后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行为,研究的是如何对最终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而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是将整个行为区分为退出之前的行为与退出之后的行为,研究的是,是否可以将退出行为规范地评价为,切断了退出者实际参与的前行为与退出者并未参与的后行为及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决定是否应对后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责。因而这两种观点对行为结构的理解存在根本区别,不可能一边采取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又同时主张“救济说”。 第三,大塚仁提出的“救济之策”的本来旨趣是,在已经发生既遂结果的情形下,为了与因阻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成立中止犯的情形保持刑罚均衡,而让那些虽做出积极努力但未能成功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退出者,就最终结果承担“障碍未遂”之责。虽然在退出者不构成共犯脱离的情形下有一定“救济”效果,但在退出者成立共犯脱离的情形下,原本就不应对既遂结果承担罪责,而只应就退出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相应罪责(若具有任意性,还可就退出之前的行为成立中止犯);而且,“救济说”还会将持续犯等既遂之后退出犯罪的情形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因此,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是,实质上难以实现其“救济”的初衷,甚至会让退出者蒙受“不白之冤”。 另外,刘文提出,“如何有效解决此类行为人停止参与共同犯罪但犯罪结果又已发生的案件中行为人的归责问题,因立法上的漏洞继而成为理论上的难题。共犯关系的脱离概念正是为了解决此类问题而生:它不同于共犯中止,因而也无需依照中止犯的严格条件;它以数人共同犯罪中个人的罪责为基础,有效矫正了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缺陷,最充分地贯彻了刑法个人责任原则。”[1]由此可见,刘文之所以一边承继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同时又批判该说之理论前提即“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是属于不同理论层面的问题”,主张业已被学界摒弃的“救济说”,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厘清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之间的关系,没能正确理解“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实质。 1.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之关系。共犯脱离问题之所以成为共犯理论中的一个难点,根本原因在于迄今仍未能厘清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之间的关系。尽管二者存在重合部分(既遂之前退出共犯关系),在理论上相互交错容易引起混乱且实际已经引起了混乱,但共犯脱离是通过确定犯罪结果的归属对象,以解决共犯的归责范围(是否对最终结果承担罪责)与归责程度(就退出之前的行为成立何种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而共犯中止解决的仅仅是共犯的归责程度问题(就整个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成立何种犯罪停止形态),二者原本属于不同理论层面,共犯脱离理论与共犯中止理论并行不悖。具体而言:(1)二者的存在阶段不同:共犯中止仅限于既遂之前,而共犯脱离可发生在共犯关系成立之后犯罪完成之前的任何阶段,只要存在共犯关系,就有脱离的可能;(2)二者的成立要件不同:共犯脱离不以结果未发生与任意性为必要;(3)二者承担罪责的范围不同:共犯中止是就整个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共犯脱离则对退出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不成立犯罪,而仅就退出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4)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不同:共犯脱离属于共犯论特有的问题,共犯中止与其说是共犯论的问题,毋宁说是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因而前者从共犯论的角度研究最为有效,而后者则从犯罪停止形态的视角探讨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概言之,研究共犯脱离的首要目的在于,确定退出者是否对退出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成立中止犯只是退出者就退出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形式之一。反之,若采取刘文所谓“救济说”,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判断退出者的刑事责任时,势必应首先判断退出者是否成立中止犯,只有不成立时,才有必要为了“救济”而判断退出者是否成立共犯脱离。那么,在已经发生既遂结果的情形下,若退出者具有任意性,又该如何“救济”呢?而且,按照其观点,理应是立足于犯罪停止形态而非共犯论来研究脱离问题,但刘文在研究脱离标准之时却完全立足于共犯论,其间难言存在理论上的一贯性。 2.“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之实质。刘文认为,“‘部分实行全部责任’是团体责任的形式,它与个人责任之法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违背的,同时也是在共犯的个人责任难以分清的情况之下理论向实践妥协的结果。但是,在能够分清个人责任的情况下,比如共犯脱离可以认定之时,只要求脱离者对自己脱离之前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则正是化解‘部分行为全部责任’之弊端的体现,亦是贯彻刑法个人责任原理之结果”,共犯关系的脱离概念正是“以数人共同犯罪中个人的罪责为基础,有效矫正了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缺陷,最充分地贯彻了刑法个人责任原则”。[1]也就是说,在刘文看来,共犯责任是一种团体责任,共犯胼离理论可以有效化解“部分行为全部责任”之弊端。应该说,这是对共犯性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的错误理解。 要成立共同犯罪,必须是“两人以上”基于“共同犯罪故意”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对于共犯,仍然必须坚守个人责任原则,行为人仅仅在与自己的参与存在因果关系的限度之内,承担共犯的罪责。[25]换言之,对共同犯罪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或者结果,其实质性法理在于,某行为人尽管只实施了“部分行为”,但由于该“部分行为”是在“共同犯罪故意”之下所实施,共犯之间由此形成了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该“部分行为”已与其他共犯所实施的“部分行为”(或者“全部行为”)结合在一起,属于“共同的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与由“共同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共犯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体而言,要将现实发生的某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在单独犯的情形下,必须是行为人“自己的行为”引起了该结果,同样,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虽然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但归责范围仍然限于行为人“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不过,由于是“共同”完成了“犯罪”,这里所谓行为人“自己的行为”,除了行为人自己亲自实施的行为之外,还包括虽然是由其他共犯实施,但能被评价为是包括行为人在内的全部或者部分参与者的“共同的犯罪行为”的行为。例如,在实行过限的情形下,之所以其他共犯无需对过限结果承担罪责,正是因为引起过限结果的行为只是过限行为人的个人行为,不属于“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之下的“共同的犯罪行为”;同样,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退出者之所以不对最终结果承担罪责,也正是因为剩余共犯实施的、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不属于“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之下的“共同的犯罪行为”,不能被评价为退出者的行为。因此,共犯责任采取的不是刘文所谓“团体责任”,仍然坚持的“个人责任原则”。如果真如刘文所言,共同犯罪是“团体责任”,“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存在有悖责任主义这一法治基本理念的“弊端”,需要共犯脱离理论来“化解”,那么,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就是“赤裸裸”地以法的名义“强制推行”背离法治基本精神的“团体责任”,“完全违背”了个人责任之法理(而非刘文所谓“与个人责任之法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违背的”),这就远非刑法解释论所能“纠错”、“弥补”乃至“化解”;而且,按照刘文之逻辑,司法实务部门适用共犯规定,学者规范解释共犯规定,更无异于其“帮凶”(11)。这无疑是荒谬的! 概言之,共犯脱离理论对退出者罪责的处理,仍然是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运用有关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等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而绝非是在法律规定之外通过解释论“另搞一套”。只要精细分解共犯关系的发展阶段(全体共犯形成共犯关系——退出者解消既存共犯关系——剩余共犯重新形成新的共犯关系),准确把握退出当时的共犯关系,不机械地甚至错误地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不因最终发生了未遂乃至既遂结果,就无视共犯个体之间的差异,简单地认定所有共犯均统一构成未遂乃至既遂,就完全可以准确界定脱离者的归责范围与归责程度。因此,我国刑法的中止犯规定并不存在刘文所谓“力有不逮之处”,更不存在刘文所谓“立法上的漏洞”,根本无需通过共犯脱离理论来“救济”。 由此可见,无视脱离理论的演变历程,重拾日本刑法已经摒弃的观点,这无异于是说,脱离理论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存在方向性错误,这不仅有欠客观过于武断,对我国司法实务亦无积极意义。例如,在前述案例2中,如果被告人杨某可以成立共犯脱离,若如刘文所言,脱离理论只是一种“救济”,那么,法院仍然可以经过所谓“规范评价”,依据自由裁量权,认定没有“救济”杨某之必要,判定杨某应就前后两次盗窃行为成立盗窃罪;而且,即便法院认定有“救济”杨某之必要,倘若只是以未遂犯来“救济”,原本无需对第二次盗窃行为承担盗窃罪罪责的杨某则要就该行为承担未遂犯的罪责(忠实解读大塚仁的救济理论,应就两次盗窃行为所组成的整体行为成立盗窃罪的未遂犯),未必能达到所谓“救济”目的。反之,如果认为脱离理论是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解读,倘若杨某可以成立共犯脱离,则根本不应就第二次盗窃行为成立盗窃罪,法院判定其应就两次盗窃行为成立盗窃罪,就属于定性错误,应当予以改正。进一步而言,如果被告人杨某不能成立共犯脱离,如果通过所谓“规范评价”,认为对其有“救济”之必要,让其享受未遂犯的“恩惠”,则无疑超越了刑法解释论的应有之义,其合法性根据何在呢?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尽管共犯脱离理论不具有“中止犯的救济之策”的性质,但与中止犯一样,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鼓励犯罪人退出犯罪、分化瓦解共同犯罪的效果,因而在具体认定时,有必要考虑刑事政策的因素,在让其对退出之前的行为承担相应罪责的基础上,相对“慷慨”地认定共犯脱离(想必这也是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所谓“规范评价”之本意)。 (二)共谋射程理论的解决路径 学界在研究共犯关系的“脱离”之时,经常会同时采用共犯关系的“解消”这一表述,未必有意识地区分了二者(12)。在本文看来,共犯关系的“脱离”意味着,不能将退出之后剩余共犯的行为及其结果归责于退出者;要认定共犯关系的脱离,就要求“解消”了既存的共同关系。亦即,一旦成立脱离,即对其后的行为及其结果不承担罪责,由退出行为解消此前的共犯关系是脱离的成立要件;退出行为是一种法律事实,解消共犯关系是对该事实的法律评价,成立脱离是解消共犯关系的法律后果。区分“脱离”与“解消”的意义在于,可以进一步明确,共犯脱离问题本质上仍属于共同犯罪本身的问题,需要立足于共同犯罪的本质论来解决,取决于退出行为是否达到了解消既存共犯关系的程度。 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基于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实现了结果,为此,“与其他人处于共犯关系者(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除了自身的参与行为之外,还需对其他共犯的参与行为承担罪责,这就是所谓共犯责任原则”。[26]这种“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之所以符合“个人责任原则”,正是因为该人与其他人处于同一共犯关系之下,相互利用相互补充地完成了犯罪,行为人虽然只是实施了部分行为,但其他人的行为仍然可以被评价为该人之行为。为此,部分共犯形成了不同于既存共犯关系的新的共犯关系,并在新的共犯关系之下实施了犯罪的,就不能再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具体就共犯脱离而言,退出者是否对退出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取决于是否解消了既存共犯关系:该行为与结果究竟是由包括退出者在内的既存共犯关系所引起,还是由不包括退出者在内的新的共犯关系所引起(13)。因为,退出行为一旦解消了既存共犯关系,对退出者而言,属于共犯关系的脱离,而对于继续完成犯罪的剩余共犯而言,则属于共犯关系的再生(新生)。 那么,如何认定解消了既存共犯关系呢?共犯射程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决路径(14)。共谋射程理论,是指认为只有引起结果的实行行为处于当初的共谋的射程之内,能被认定为行为人的行为,行为人才可能就此行为成立共同犯罪,并对此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的一种理论。共谋射程理论的目的在于,确定对哪些行为及其结果具有归责可能性;要解决的问题是,最终结果是否是由“共同实行的意思”支配之下的“共同行为”所引起。同样,在教唆犯、帮助犯的情形下,只有引起最终结果的正犯行为属于教唆、帮助之故意影响下的行为,才能就此行为对教唆者、帮助者追究罪责,对此,亦可以分别称之为教唆的射程、帮助的射程(以下统称“共谋的射程”)。考虑到论述上的简要性,这里仅以共同正犯为例(15)。 共谋射程理论是基于对因果共犯论机能的反思而建立。从理论渊源来看,因果共犯论原本是为了对抗责任共犯论而提出,其本意在于说明,之所以成立共犯,是因为实施了直接或者间接地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行为,解决的是归责根据问题:共犯行为之间若没有彼此促进这种因果影响,就不可能构成共犯;共犯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若没有物理或者心理上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对最终结果承担罪责。但共犯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是成立共犯的最低限度要件,存在因果关系未必构成共同犯罪,亦未必对最终结果承担罪责,另外还得存在作为共犯之本质的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存在“共同意思”与“共同行为”。而能够为这种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奠定基础的,正是参与者之间的共谋,要成立共同正犯关系,必须是基于当初的共谋而实施了实行行为。反之,若形成了不同于当初的共谋的新的共谋或者犯意,并基于这种新的共谋或者犯意实施了实行行为,就不能谓之为,是由基于当初的共谋的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实现了结果,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具体就共犯脱离而言,因果共犯论只能说明为何担责,其本身并不能界定担责范围,而是否成立共犯脱离,要解决的是归责范围与归责程度的问题,两者处于不同理论层面,因而不能过度夸大因果共犯论的作用,简单地以“归责根据”来确定“归责范围”,混同处罚根据理论与归责范围确定理论。因此,在本文看来,对于共犯脱离问题的解决,以因果共犯论为基础的因果关系切断说、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的路径选择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与因果论相比,更应该从共犯论本质来考察,取决于退出之后的行为是否仍然能谓之为是基于当初的共谋而实施,最终结果是否是由“共同实行的意思”支配之下的“共同行为”所引起。 共谋射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有参与共谋的意思;(2)实际参与了共谋;(3)行为是基于共谋而实施。该理论研究的是,已经实际存在的行为是否是基于当初的共谋而实施,以确定行为的实施主体,进而决定该行为及其结果的归责对象。这种研究决定的是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影响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有无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问题。因为只有就行为的实施进行共谋,由此形成共同实行的意思,并且基于这种共谋(共同实行的意思)实施了行为,才能认定该行为属于“共同意思”支配之下的“共同行为”,属于共谋射程之内的行为,进而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也才会对该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承担罪责;反之,尽管行为造成了某种结果,倘若该行为不能认定为行为人的行为,则不可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自然也无需再研究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等问题。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实质上可以将整个行为进一步界分为,退出之前的行为(第一行为)与退出之后的行为(第二行为),如果第二行为是由剩余共犯基于不同于当初的共谋的、新的共谋或者犯意而实施,最终结果就并非是基于当初的共谋所形成的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实现,因而当初的共谋就不及于该行为及其结果,不能将最终结果归责于未参与新的共谋的退出者。因此,共犯脱离的判断标准应该是,通过自己的退出行为,达到解消既存的共犯关系,其他共犯要继续完成犯罪就必须基于新的共谋或者犯意而实施的程度。若第二行为不是在由当初的共谋所形成的、包括退出者在内的既存共犯关系之下所实施,该行为根本就不能被评价为退出者的行为,按照责任主义原则,退出者无需也根本不应就此承担罪责。 脱离理论的旨趣在于,从共犯论的视角对既存的共犯关系是否依然存在进行实质性考察,进而界定退出者的罪责,因而问题的实质在于退出行为是否能够解消既存的共犯关系。既有不少判例持此态度(16),亦有部分学者从另外的视角得出了与本文观点类似的结论。例如,(1)“共犯关系脱离的问题,不是促进意义上的因果性引起的问题,而直接属于该结果是否仍属于‘共同管辖’之下这一规范问题(有无共同义务的问题)”;[9](2)“所实现的事实不能认定为是在以前的共谋范围之内”之时,“具体而言,以前的共谋一旦解消,剩余者(有时候会重新成立共谋)基于另外的决意实施了犯罪行为之时,就可以认为,对于基于新的决意所实行的事实,以前的共谋没有促进效果,能认定为共犯的脱离”;[27](3)“尽管一旦对抢劫进行了共谋,只要在着手之前向其他共谋者表明脱离的意思脱离了共谋关系,即便其他共谋者日后又实施了犯罪行为,也不能说是实现了由脱离者的共谋所形成的犯意”;[28](4)若其他共犯做出了消灭当初共谋之因果性的其他意思决定,就当然处于共谋射程之外;[29](5)“从因果共犯论的立场来看,行为人之所以对某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其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在已经脱离共同犯罪的场合,犯罪结果是由其他剩下的人在新的犯罪意图支配之下,重新组合而成的共犯群体所引起的,和已经脱离该犯罪群体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或者不存在成立既遂犯所要求的程度的因果关系”。[30]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所谓“其他犯罪事实”这一观念,[7]但是否属于“其他犯罪事实”,也只要根据“是否是基于新的决意的行为”进行判断即可。[8] 事实上,即便是持因果关系切断说尤其是持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如果能认定在退出者退出之后,剩余共犯是“基于新的共谋”而实施了其后的犯罪,也往往会认定或者规范地认定切断了因果关系,因而共犯脱离问题最终归结于,具体以什么标准来判定,退出行为解消了既存的共犯关系,剩余共犯是“基于新的共谋”而实施了其后的犯罪? 四、共谋射程理论之司法适用 (一)认定标准的再造 按照共谋射程理论,只有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是共谋射程之内的行为,该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行为人的行为,行为人亦才能就此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共犯之间的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是指物理以及心理方面的影响,因而可以通过综合考虑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确定共谋的射程。具体就共犯脱离而言,是否成立脱离,不问是着手之前还是着手之后,均取决于脱离之后的行为是否属于退出之前的共谋的射程之内的行为,若退出行为达到了剩余共犯要继续完成犯罪就必须基于新的共谋而实施的程度,即可以认定解消了既存的共犯关系,成立共犯脱离。我们可以通过综合考察下述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来判断剩余共犯的行为是否是当初的共谋射程之内的行为。具体而言,客观因素包括:(1)退出之前的行为的贡献程度与影响力大小;(2)当初共谋的行为与退出之后的行为在内容上的共同性、关联性;(3)法益侵害在“量”上的改变程度(17);(4)行为样态、行为状况的改变程度;(5)时间与地点上的间隔程度;等等。主观因素包括:(1)犯意的改变程度;(2)共同完成犯罪的意思是否已经消灭或者减弱程度;(3)动机、目的的改变程度(18);等等(19)。不过,如果部分共犯强行将某共犯排除在外,或者部分共犯重新明确地进行了共谋,则原则上可以直接认定,其后的行为是基于新的共犯关系而实施。例如,甲与乙等人对被害人丙实施暴力之后,甲放弃犯意,并将丙扶到凳子上询问情况,乙看见后非常生气,与甲发生口角,并突然将甲打昏,然后置其于不顾,将丙带至其他地方予以拘禁,并继续对丙实施了暴力的,第二次暴力就可以认定为,是基于新的犯意而实施(20)。 考虑到成立脱离只是不对退出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不承担罪责,仍需对退出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相应罪责,且相对“慷慨”地认定脱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瓦解共同犯罪利于保护法益,一般而言,对于基于共谋的犯罪,如果因所有参与者(或者主要参与者)的合意而一旦放弃,或者因某种障碍而一时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或者犯罪一度呈现结束状态之后,部分共犯在退出者不知情的情形下继续完成犯罪的,由于当初的共谋所造成的危险已经客观上一度被消灭,就基本上能认定,没有参与后一行为的共犯成立脱离。例如,数人共谋实施强奸,其中两名共犯完成强奸之后,某共犯提出放弃强奸,得到其他共犯的同意之后离开了现场,剩余共犯其后又在其他完全不同的地点(或者是相同地点)两次实施了强奸的,尽管三次强奸行为可以被评价为“包括的一罪”,但将后面的两次强奸视为“另外的社会性事实”可能更为合适,因而退出者只就第一次强奸行为承担既遂罪责,而不对后两次行为承担罪责;如果强奸行为造成被害人受伤,只要无法查明究竟是由第一次强奸行为还是由后两次强奸行为所引起,退出者也不对该伤害结果承担罪责(21)。 在具体认定时,需要重点考察“退出之前的行为的贡献程度与影响力大小”以及“时间与地点上的间隔程度”等因素。首先,退出者在共谋阶段的影响力大小往往直接决定共谋的射程。例如,作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及对于犯罪计划的提出、确定发挥主导作用的主犯,或者提供了关键信息等技术性帮助者等,一般会通过共谋对其他共犯施加较强的影响,相对容易认定共谋射程及于剩余共犯所实施的实行行为;反之,诸如胁从犯或者从犯,则更容易得出否定结论。但是,即便退出者在既存共犯关系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若总是要求采取积极措施以阻止其他共犯的犯罪行为,或者认为只要其他共犯完成了犯罪就没有成立脱离的余地,这种要求就过于严格。如果主犯表明退出的意思并发出停止犯罪的指示,其他共犯一旦放弃犯意之后,又改变主意实施了犯罪的;或者,尽管主犯采取了通常情况下足以使其他共犯改变主意的方法,要求其他共犯放弃犯罪,但其他共犯不为所动而“独断专行地”完成了犯罪的,尽管尚存在“没有共谋就没有犯罪行为”这一意义上的条件关系,仍然可以认定,其后的犯罪是基于新的共谋所建立的新的共犯关系而实施。倘若其他共犯主动将主犯排除在外,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犯罪的,就不宜让该主犯对最终结果承担罪责。当然,若剩余共犯对放弃犯罪明确表示反对,而主犯也并未进一步采取制止措施的,就有让该主犯成立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余地。 其次,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与基于当初的共谋的行为在时间上、地点上越接近,当初的共谋的影响力就越能持续,也更容易被认定为在共谋射程之内;反之,如果因时间上、地点上的间隔,各参与者所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或者引起了动机、目的甚至共犯成员的实质性改变,就可以认为,该行为是在基于新的共谋而形成的新的共犯关系之下所实施。例如,一起生活的甲等5人盗窃了6罐甲苯,5人约定共同用去1罐,售出剩余5罐,并平均分赃。但其后5人分别在4个地方生活,且各自随意使用甲苯。距离当初的共谋两个月之后的某天,甲将剩余的1罐甲苯售出并独吞了赃款。对于此案,日本的刑事判例认为,“在本案中,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属于共谋之背景的各种情况已随之大幅改变”,至迟在出售行为当时,可以认为当初的共谋已经在“暗默中”归于解消(22)。又如,被告人甲提议并与其他3名共犯共谋,趁某廉价超市早上只有店主A一人时,袭击A并抢夺店内的销售款。2007年1月29日,甲等人按照原定计划伏击守候A,由于A并未出现,遂离开了现场(第一行为)。此后,甲由于工作倒班未再参与其后的行动,但甲的考虑是,等自己的倒班结束后,自己一定会积极参与,以实现当初共谋的犯罪。当月31日,其他3名共犯以及未曾参与当初共谋的其他人按照不同于当初计划的分工,在没有甲参与的情形下袭击了A(第二行为)。甲在报纸上得知此事后,打了其中1名共犯的耳光,要求分赃。对于该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认为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属于“不同的犯罪事实”,甲只应就第一行为承担未遂之责。其理由在于,犯罪时间与原定计划不同,已实质性地僭越了当初共同制定的犯罪计划;实施犯罪的成员不同且分工也不同;甲自认为若没有自己的进一步参与就无法实现犯罪。[7]当然,如果退出者虽未参与新的犯罪行为,但分手时曾明确表示,自己可以不实际参与,倘若其他人实施,自己要从中分赃,就不能仅以时间间隔为由而将该行为排除在共谋射程之外。 (二)典型案例的再认识 下面通过对前文三个案例的分析,来检验共谋射程理论在共犯脱离案件中的具体运用。对于案例1,一审与二审均以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可以评价为是在共同的意思联络之下所实施的整体行为”,理应就追击行为成立共同正犯为由,判定甲、乙、丙三人成立伤害罪的防卫过当。但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应将整个行为区分为“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分别考察,其中,反击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乙的追击行为成立量的过当防卫,但由于“不能认定就追击行为重新成立了共谋”,最终宣判甲无罪(23)。 对于该案,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对于正当防卫行为有无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对此,有观点立足于只有共同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才可能成立共同正犯这一前提,认为反击行为属于阻却违法性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能就此成立共同正犯。[31][32]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就追击行为成立共谋,才能就追击行为成立共同正犯,由于本案中甲与乙之间就追击行为并无共谋,因而追击行为只是乙的单独犯,未参与该行为的甲当然不对该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但是,是否成立共同正犯,属于是否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问题(在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之下,属于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问题),这种判断应该先于对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因而该行为是否合法不应对是否成立共同正犯产生影响,在共同实施正当防卫的场合亦有可能成立共同正犯。[33]实际上,数人共同反击“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之时,要判断反击行为是否具有防卫行为的相当性,不是分别探讨各人的行为,而是将所有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探讨该整体行为是否超过了防卫限度,这就有必要将该防卫行为作为共同正犯来认定。 量的防卫过当,是在侵害当时的行为与侵害结束之后的行为在时间上、地点上相互接近,且基于同一防卫意思而实施时才得以认定(24),因而当初的共谋与侵害当时的行为通常对侵害结束之后的行为存在因果影响力。在本案中,甲明知乙有追击殴打丁的危险,却只是旁观而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因而无论是从事实的角度还是从规范的角度,均难以否定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至少在本案中,甲仅仅参与了反击行为,不应对乙的追击行为承担罪责,这一结论本身应无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理论上为此找寻依据,亦即,如何认定追击行为不是当初有关反击行为之共谋的射程之内的行为。正如日本最高裁判所所言,这取决于追击行为是否是基于不同于当初的共谋的新的共谋或者犯意而实施。 判断数个行为能否谓之为一个防卫行为,重要的是这些行为是否是基于同一防卫意思而实施。所谓防卫意思,是指认识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试图避免侵害的单纯心理状态,因而要成立量的防卫过当,一般应限于侵害结束之后误以为侵害仍然存在的情形;以及因侵害行为当时的诸如恐惧、惊愕、兴奋等心理动摇仍在持续而继续实施攻击行为的情形。本案即属于后者。因此,对于共谋射程的确定,共谋以及反击行为的因果影响力是否持续至追击行为,虽然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决定性因素应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是否仍在持续(即客观因素中的“行为状况的改变”),以及侵害结束之后行为人是否仍然存在防卫意图(即主观因素中的“动机或者目的的改变”)。一般而言,在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权利而就防卫行为进行共谋的场合,在不法侵害仍在持续的状况下所实施的行为,就可谓之为基于共谋的行为;反之,即便并未直接参与追击行为者对防卫行为发挥了主导作用,侵害结束之后依然强烈存在其行为的因果影响力,但只要其他共同行为人虽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却继续实施追击行为的,原则上,该行为就应评价为是基于新的犯意的行为。[34]本案中尽管甲、乙等人就反击行为进行了共谋,且追击行为与反击行为存在时间与地点上的接续性、机会的同一性,而且在乙实施追击行为当时,甲就站在离乙不过2到3米的地方旁观乙的行为,但乙是在认识到A已经松开丁的头发并后退之时即侵害行为已经结束之后实施追击行为,因而乙不具有继续防卫丁的人身权利的意图,可以认定该追击行为是乙基于自己个人的犯意而实施,属于超出当初有关反击行为的共谋的行为。因此,可以认定甲脱离了有关反击行为的共同正犯关系,不成立故意伤害罪的防卫过当。反之,如果案情是,在甲的主导之下实施了正当防卫行为,当时,甲怒骂A,体现了强烈的攻击欲望(当然,也并非仅此即可否定甲的防卫意思),那么,乙等人就完全有可能受此影响而实施追击行为,因而也有认为追击行为处于有关反击行为的共谋的射程之内,进而认定甲成立防卫过当的余地。[29] 案例2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杨某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参加第二次盗窃行为,能否对两次盗窃行为承担盗窃罪罪责?对此,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事先与其他三人合谋,“表明了盗窃无锡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内摄像头的概括性犯罪意图,其主观上具有共同盗窃犯罪的故意,客观上亦实施了共同盗窃犯罪的行为,案发后又联系收赃人代为销售全部所窃赃物和进行分赃。其策划、指挥盗窃活动的行为与公私财物损失的结果之间存有因果关系,应当以盗窃共犯论处,并对共同盗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25)对此,该院相关人员撰文阐述了两点判决理由:(1)被告人杨某对实施盗窃犯罪具有概括故意;(2)被告人杨某参与销赃行为系对全部盗窃活动的事后追认。[35] 诚如判决所言,杨某主观上具有盗窃犯罪的“概括的故意”,且不能否定其行为与第二次盗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事后销赃行为也是对第二次盗窃行为的事后追认。然而,概括故意尤其是事后追认显然不能直接成为定罪的主观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次盗窃行为是否属于共谋射程之内的行为?也就是,该行为是否属于当初的“合谋”范围之内的行为,能否被评价为杨某的行为?具体而言,在主观方面,杨某等四人实施第一次盗窃行为当时,是在明知仓库内有大量摄像头的情况下,仅盗窃了其中的2万余只,且随后驾车离开犯罪现场,可以说杨某尽管对实施盗窃存在“概括的故意”,但其内容仅限于“四人共同”盗窃其中的“2万余只”摄像头;而且,虽然其他三人实施的是继续盗窃摄像头的行为,但盗得2万余只摄像头之后四人驾车离开犯罪现场,且杨某“因故中途离开”,就表明至少在杨某离开当时,四人均认为已经完成了当初合谋的盗窃行为,杨某对其他三人所实施的第二次盗窃行为并不知情,可以说“共同完成犯罪的意思”已经消灭。更为重要的是,在客观方面,尽管是由杨某提议实施盗窃,“退出之前的行为的贡献程度与影响力”较大,且“当初共谋的行为与退出之后的行为在内容上存在共同性、关联性”,但在完成第一次盗窃行为之后,杨某等四人已经离开犯罪现场,第二次盗窃行为与第一次盗窃行为之间存在时间上尤其是地点上的间隔;而且,其他三人是在明知杨某已经放弃犯罪意图而离开的情形下,基于三人的意思而决定继续实施第二次盗窃行为,因而可以说,与第一次盗窃行为相比,第二次盗窃行为的行为状况以及行为目的也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有关第一次盗窃行为的共犯关系已经因杨某的“因故中途离开”以及“另三人待其下车后商议返回仓库盗窃剩余摄像头”而归于解消,第二次盗窃行为就属于“另三人”基于新的盗窃故意而实施的行为,是由不包括杨某在内的新的共犯关系支配之下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是杨某的行为。(亦即,虽然是“另三人”的“共同行为”,但不属于杨某等四人的“共同行为”)因此,判定杨某仅就第一次盗窃行为承担盗窃罪罪责,而就第二次盗窃行为所获赃物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更符合案件事实。 就案例3而言,吴某与王某共谋的内容是“杀死蔡某”,在追赶负伤逃跑的蔡某的过程中,因被警察发现而仓皇逃离之后,吴某继续独自寻找被害人并最终杀死被害人的行为(第二行为),可谓之为实现了共谋的内容;而且,吴某尽管知道王某已经逃离,也意识到自己是在单独实施第二行为,但吴某只是知道王某为了躲避警察而已经逃走,对王某逃回家中睡觉的行为并不知情,不能认定吴某知道王某已经放弃了犯罪意图退出了共犯关系,或者说,王某尽管已经回家睡觉,但完全有可能意识到吴某会继续实施第二行为;再者,被警察发现后,吴某躲在现场,一俟警察走后即马上实施第二行为,在时间上与第一行为(拦住蔡某并刀扎蔡某的腹部)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不能说行为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也不能说其动机与目的有所变化。因此,第二行为属于当初的共谋射程之内的行为,王某不能成立共犯脱离,仍应对第二行为承担罪责。当然,如果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在时间上存在一定间隔,且吴某知道王某已经放弃犯罪意图(例如,第一行为之后,吴某与王某之间形成了“可能被警察抓住,不如就此收手”这种合意),而吴某仍然单独实施杀害行为的,则可以认为,吴某的第二行为属于基于新的犯意的“其他犯罪行为”,进而否定共谋的射程及于第二行为,王某成立共犯脱离,仅承担故意杀人罪未遂的罪责。 司法实践中,共犯脱离的现象并不少见,我国司法实务一直是作为是否成立共犯中止的问题来处理。但是,共犯脱离往往发生在已经出现既遂结果的情形下,且退出行为未必具有任意性,尤其是退出之后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有时候并不能被评价为退出者的行为,因而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准确评价退出者的归责范围与归责程度,更有机械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进而违反责任主义之嫌。共谋射程理论为此提供了相对明确且可行的解决路径:是否成立共犯脱离,取决于剩余共犯的行为能否谓之为是当初的共谋射程之内的行为。要让司法实务部门接受并适用共犯脱离理论尚任重道远,不仅要为之提供相对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更需结合具体案例比较分析共犯脱离理论采用与否之利弊。这也是笔者此后仍需努力的方向。 ①[日]最决平成6年(1994年)12月6日刑集48卷8号509页。 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刑二初字第0006号。 ③如果剩余共犯不是完成原定犯罪,就可能属于实行过限的问题。 ④有关日本相关学说与判例的内容及其评述,详见王昭武:《共犯关系的脱离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2卷(2013年),第101-116页。 ⑤[日]最决平成6年(1994年)12月6日刑集48卷8号509页。 ⑥有关我国的共犯脱离理论研究,详见王昭武:《我国“共犯关系的脱离”研究述评》,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2卷(2007年),第130-148页。 ⑦参见[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505页。浅田和茂也主张,原则上应采取因果关系切断说,但应根据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来缓和切断标准(参见[日]浅田和茂:《刑法総論》,成文堂2005年版,第465页);黎宏亦主张,“如果部分共犯人表示了从共同关系中脱离的意思,并且实施了脱离共犯的行为,切断了其和其他共犯之间的物理和心理上的相当因果关系,其他人即便实施了犯罪行为,引起了犯罪结果,也必须说,脱离人和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其对于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不能承担既遂犯的刑事责任,而仅就其脱离之前的行为承担中止犯的刑事责任。”(黎宏:《共犯脱离论文评议》,载林维主编:《共犯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以下。) ⑧参见[日]塩見淳:《共犯関係からの離脱》,载《法学教室》2012年第12号,第100、101页。反之,岛田聪一郎则认为,“如果采取了处于行为人之立场下所能实施的、通常情况下足以消灭行为人所引起的危险的真挚的努力,但仍然发生了结果的场合,那就属于异常事态,应否定因果关系或者客观归属”。([日]西田典之等编:《注釈刑法》,有斐閣2010年版,第866页[島田聡一郎执笔]。) ⑨亦即,“共犯的因果性仅限于揭示处罚根据,并不能左右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别以及共犯的成立范围”([日]佐久間修:《共犯の因果性について》,载《法学新報》第121卷第11=12号[2015年],第191页)。 ⑩不限于此,刘文在解释为什么在停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之后还必须解除既存的共犯关系时,以“对于共同正犯而言,仅仅停止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仍然为其他共犯人提供物质或精神等帮助,则意味着行为人未能有效切断与其他共犯人行为及结果之间物理心理的因果性”作为理由。(参见刘艳红:《共犯脱离判断基准: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759页。)但是,对“仍然为其他共犯人提供物质或精神等帮助”的共同正犯而言,能“规范地”评价为已经停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吗? (11)进一步而言,若“‘部分实行全部责任’是团体责任的形式”,是“共犯的个人责任难以分清的情况之下理论向实践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无疑是对责任主义的背叛!因为,若“共犯的个人责任难以分清”,本应疑罪从无,理论何以能不惜背离法治基本精神而“向实践妥协”呢?而且,在“共犯的个人责任难以分清的情况之下”,司法实践是否真如刘文所言,机械地坚持了“部分行为全部责任”,本文对此存在极大怀疑。 (12)日本最高裁判所调查官原田国男将放弃共同实行的意思的情形称之为“共犯的脱离”,而将共同实行之后的脱离命名为“共犯的解消”。(参见[日]原田国男:《共犯関係が解消していないとされた事例》,载《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说[刑事篇]平成元年度》,法曹会1991年版,第178页。)但前者是着眼于主观意思,而后者是基于客观事实,姑且不论其命名是否妥当,至少在将二者当作一组对应概念这一点上,是存在疑问的。 (13)亦即,共犯脱离是指在犯罪实行途中,部分共犯“已经不再是共犯”的情形。(参见[日]佐久間修:《共犯の因果性について》,载《法学新報》第121卷第11=12号[2015年],第181页)。正因为如此,共犯脱离与承继共犯之关系才被评价为,“在时间进程上处于反向关系”的问题(参见[日]坪井祐子等:《共犯(3)の1》,载《判例タイムズ》第1387号[2013年],第69页。) (14)另有学者认为,共犯脱离不仅是共犯的因果性的问题,还属于共谋的射程的问题。(参见[日]高橋則夫、杉本一敏、仲道祐樹:《理論刑法学入門》,日本評論社2014年版,第237页。) (15)详见王昭武:《论共谋的射程》,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161页以下。 (16)参见[日]东京高判昭和25年[1950年]9月14日高刑集3卷3号407页;[日]大阪高判昭和41年[1966年]6月24日高刑集19卷4号375页;[日]最决平成元年[1989年]6月26日刑集43卷6号567页。 (17)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剩余共犯一般是针对法定符合范围之内的相同对象完成了相同犯罪,因而在法益侵害的“质”上往往没有变化。 (18)有学者指出,“实行行为人出于什么目的实施了行为,对于确定共谋的射程范围,与客观行为样态的相同性相比。属于更重要的判断标准”,因而若事前共谋的内容与实际的犯罪行为之间,动机与目的发生很大改变,就可以成为否定共谋射程的重要依据。参见[日]桥爪隆:《共谋的射程与共犯的错误》,王昭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2期,第35-36页。 (19)参见[日]十河太朗:《共謀の射程と量的過剩防衛》,载《川端博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上卷),成文堂2014年版,第722页。另外,山中敬一认为,作为是否完全解消了共谋关系这一标准的下位标准,具体包括“被排除在共谋关系之外”、“共谋关系的消灭”、“共谋关系的强制结束”等(参见[日]山中敬一:《共謀関係からの離脱》,载《立石二六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第547页)。 (20)参见[日]名古屋高判平成14年(2002年)8月29日判时1831号158页。 (21)参见[日]神户地判昭和41年(1966年)12月21日下刑集8卷12号1575页。 (22)[日]东京地判昭和52年(1977年)9月12日判时919号126页。 (23)[日]最决平成6年(1994年)12月6日刑集48卷8号509页。 (24)[日]最决平成20年(2008年)6月25日刑集62卷6号1859页;[日]最决平成21年(2009年)2月24日刑集63卷2号1页;[日]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13年第3版,第372页以下。 (25)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刑二初字第0006号。